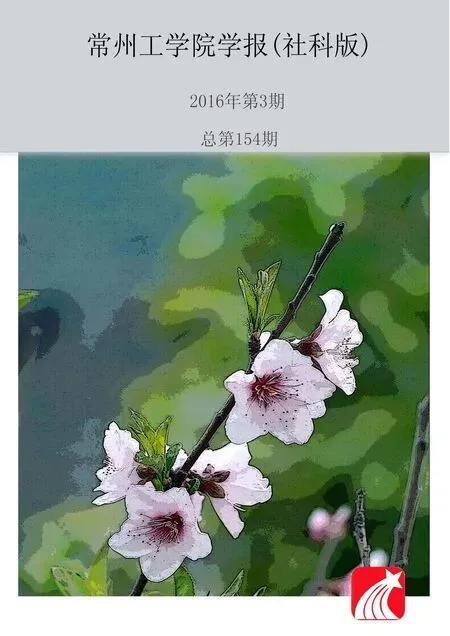重绘逝去的时空
——论《吉陵春秋》的美学追寻与罪恶书写
2016-03-29李欣池
李欣池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重绘逝去的时空
——论《吉陵春秋》的美学追寻与罪恶书写
李欣池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吉陵春秋》刻意遵照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型,移植了传统、属于过去的世界的古典文学符号体系,写实意味与难以捉摸的象征意义构成了小说的美学矛盾。小说通过互文、不断重写的文本,重复、循环的时间与事件,呈现出一个神灵死亡、人类堕落的罪恶世界,显示出作者对人世风情的生动还原之外关于罪恶、命运、人类存在深刻、沉重的思考。作者对原乡、古老中国的追寻与人类对救赎希冀交织在一起,最终以文字的异彩作为救赎,展现了亦真亦幻的美学中国。
关键词:李永平;《吉陵春秋》;美学;文本;时空中图分类号:I206
关于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的小说《吉陵春秋》,论者大多从中国底层小人物的现实书写、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民性批判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诚然,文本对现实的指涉、批判与反思的确值得探讨,但小说所建构的想象世界是对传统、社会的主观化的投影,具有超越现实的象征意味。《吉陵春秋》的深层意涵并不能以写实主义一言蔽之,李永平超越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思维范式为中国传统村镇写照,正如作者所言“吉陵是一个象征,春秋是一个寓言”。然而,关于李永平作品中的写作技巧、文本构型与美学意蕴却没能引起足够的讨论与重视。众所周知,李永平出身台大外文系,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吉陵春秋》的文本构型与写作技巧显示出现代主义的色彩,在语言方面,李永平又借用了白话小说中对人物、对话、场景的细腻、写实的描写模式,追求清新、纯化的中国古典意蕴,形成了极为复杂、卓异的美学特质。《吉陵春秋》的小说文本既具有较为单一、稳定的现实意义,反映了古老中国的历史侧影,更显示出作者对人世风情的生动还原之外关于罪恶、命运、人类存在深刻、沉重的思考。
一、循环的时间、重写的文本
时间与空间是个体感知世界的直接方式,叙事也就意味着在时间维度上重新获得世界,赋予抽象的时间以具体的文本空间形态,通过叙事使被讲述的时间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叙述者靠节省和压缩把与意义无关的东西引入意义领域;正当叙事力求描绘无意义时,它使后者与意义解释领域建立起联系。”[1]小说“不表现,它寻求。而它所寻求的,正是它自己”[2]。叙事话语所表现的不是事件之间的关系而正是事件本身,在叙事这一与时间的游戏中,文本拟仿了一个动态的时空复合体,揭示了比日常世界更真实的人类存在世界。《吉陵春秋》所展开的画卷是去中心的,作者无意通过繁复高超的技巧向读者揭示一个总体性的、静态的、一贯的真实,工业时代所建立的单一、线性、普遍的时间模式在小说中被瓦解,代之以古典、前现代的混沌的时间。重复、循环,叙述的折返、回溯形成了小说文本的构成模式。
《吉陵春秋》以长笙之死为起点,即观音菩萨的圣诞日“六月十九”,而小说的时间跨度虽有十余年,关键的时间节点处则出现了巧合般的重复。这个绝对的时间点反复出现在文中,它既是一个起点也标记了生命、历史循环与复归的进程。小说中无论现实还是想象中所发生的事件都与“长笙之死”有着神秘的联系,这一死亡事件成为了吉陵镇的纪年的开始。“漫长的岁月,吉陵这个市镇,其实只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长笙之死。其他故事不过是后果,余波。”[3]小说的十二个部分以各异的聚焦者审视了长笙生前命运的可能及之后的影响,长笙音同“长生”,暗示了时间上的永恒循环,长笙以自身命运的复现、重写对小镇产生着影响。张葆葵仿佛是长笙的轮回转世后的重生,她的人生给出了长笙之生命未尽的可能性的一种演绎方法。即如果长笙受辱后未曾自尽,也许会像张葆葵那样怀上孙四房的孩子,为流言蜚语所淹没。作为妓女的春红的形象又与纯洁美好的长笙相对应,仿佛是其人生可能的堕落结局的显现。而秋棠在象征希望、美好的春天出场,她的故事投射出长笙的少女时代,是向前世的一次回望。长大后的秋棠带着小说中被寄予厚望的萧克三走向万福巷,走向一条绝望的旧路。同样是六月十九的迎神拜观音途中,燕娘遭遇了与长笙一样的侮辱,其性格、命运如同长笙的复演。女性悲剧的重演完成了小说首篇与末篇之间的呼应,形成了小说历史时序的一次大循环。在“血点子般”的鞭炮声中,小郁道士跳着老郁道士当年血腥、可怖而诡异的舞蹈,这个场景既是小说的开端也是小说的结尾,暗示了小说首尾相续的循环模式即将又一次开始。在这个乡村世界中,时间是环形的,地域是封闭的,而长笙是这个时空的中心所在,这种螺旋形的重复手法构建了小说中死亡的循环,形成了小说情节的潜在推动力。“六月十九”在小说中成为了一个强大吸引力之源泉,小说中的事件、行为都向着这一点以差异的循环模式复现,刘老实杀孙四房、穿州过府寻找孙手下的四个小泼皮,他的行为由最初的“正义”目的,即为长笙复仇,演变为孙四房的“恶”——在燕娘身上复现了孙四房对长笙所做的一切。在小说的终篇,代表“恶”的刘老实毁灭了良善的鲁保林一家,而鲁保林如同刘老实当年的影子,仿佛自我将自我毁灭,使小说形成了更具悲剧色彩的“恶”的循环。
《吉陵春秋》还使用了不断折返、回溯过去的叙述手法,对直线步进的时间进行了扭曲、反弹。“每一篇新的故事对前面的几篇都有所补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里,今昔的交替也相当频仍,在时间上不断反弹,颇能产生张力与立体感。”[4]4《吉陵春秋》的十二篇故事力图营造出一种互相关联又断裂的文本结构,是局部不断重写的文本,“其模型属生产式,而非再现式,它取消一切批评”[5]6,通过写作,作者打破了小说中诸事件的整体性,暗示了事件、人物互相关联、影响的网络,并将最终意义的赋予、真相揭示的时刻延迟,不断重复探索这个时刻到来之前的现在,形成了文本“永不终止的(infinite)差异的区域”[5]6。同一事件在全新的时空、情境中得到别样的阐述,通过不断重写、补充,文本片段之间的界限被逾越。例如《雠蛇》《荒城之夜》两篇重复出现了萧克三对母亲的回忆,同一事件场景却有着两种讲述方式,前一篇的叙述较为连贯,而后一篇中萧克三关于母亲的叙述不断卷入现在、即目所见的情境中,过去的场景嵌入现时,难解难分。《荒城之夜》中对鲁记绒线铺的描写仅一带而过,点出了铺子对面蹲坐着“穿州过府的一个浪人”。而到了《思念》中萧克三眼中的情景却以燕娘与婆婆的眼光写出,成为小说中一个隐含危险的核心,预示了燕娘的受辱。在《万福巷里》里许多匆匆一瞥的场面到了下一篇《日头雨》中却有较为详尽的描写,例如,长笙受辱时作者突然将视线投向迎接观音神轿的群众,到了《日头雨》中这一关键性的场面才继续展开,《好一片春雨》中小说在秋棠发现五阿姐遇害时突然终止,到了《大水》一篇秋棠才又出场了一瞬,而实际上在小说伊始,秋棠就已成娼妓。关于秋棠,作者先展示了其结局,以此为基点对其过去进行不断回忆、追溯。《日头雨》在时间线上不断往返于现在与过去,“交叠之中寓有发展,似曾相识而推陈出新”[4]4,如同音乐中同一主题的变奏。小说的十二篇文本之间、每一文本在今昔之间形成了小说空间与时间上的差异的重复的推进形式。而在长笙死亡事件的外围,在浩瀚的时间中寻找其余波与先兆,时间的起点、时间之终点皆是不可知的,而这些互相关联的叙述之间互相冲突、互相阐释,从而构成文本、小说美学的张力。故事时间的渐进式表达与文本的并列式扇形结构,文本空间形态的共时与叙事时间的历时相对立,使得《吉陵春秋》的文本看上去像是时间碎片的拼贴。
二、失落的神话与缺失的古老中国意象
长笙与观音神像之间的相似性及其受辱的经历暗示了小说的主题:凡人对神性的亵渎;善的堕落与苦痛的轮回。“《吉陵春秋》里的长笙原应该是李永平理想的青春女性化身,但她的出现带来诅咒,她的美和死亡脱不开关系”[6]104,长笙是被亵渎的过去世界的神灵的一个影子,如同《浮士德》中的玛格丽特,是一个“永恒的女性”形象。在长笙之后都是无尽的堕落、放逐的罪恶的旅途,并将无穷地循环、复现。人类的原初堕落在《吉陵春秋》中以女性的堕落来展现,暗示了永远无法返归的伊甸园。雨、乌云笼罩在吉陵的天空,这样的景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那光景就仿佛天上观音老母死了,神道,菩萨,满天哭出了声”[7]245,暗示了作为观音“化身”的长笙死后留下了一个诸神离去的世界,自此后,罪恶在吉陵镇蔓延。
在基督教神话中,人类因蛇的引诱偷食智慧之果而被驱除出伊甸园,李永平在《吉陵春秋》中展现的是一个堕落之后的世界,人类一再重复着被诅咒的宿命,在时间、历史中漂泊、流散,挣扎在宿命之中。作者通过小说似在追溯人类最初的堕落、原罪的起点,渴望着被剥夺的神恩——伊甸园,同时也在追问、想象自我生命的历史、起源。作为定居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侨、古老中国的游子,“李永平必须回到他的家乡,探寻他不得不离去的根源,罪的根源”,“这里的罪不只是律法的违逆,也不只是伦常的乖离,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生命共同体的先决条件”[8]6,“原罪”成为了生命缘起时的一种共同背负,是人类从其始祖被驱逐出伊甸园时的烙印,吉陵镇的人们及其子子孙孙注定挣扎在罪恶与良善的命运循环中。在小说中,吉陵镇“中心有一条花街……万福巷,每年六月十九,观音老母过生日……西王母又开了蟠桃宴,请来诸天的仙女神道菩萨,在这万福巷里吃酒,唱曲,划拳”[7]208,西王母意指妓院老鸨,万福巷、吉陵镇都带有中国传统的吉祥字眼,善之名下却暗藏了罪恶与堕落,这并非仅仅是反讽,作者意在揭示人类建造的地上“仙境”实质上是众恶所归之地,善恶呈现共生的形态。在小说中,罪恶是广泛、多样的,是众生的共相,甚至是一种人与人行为、形象之间的相似性纽带,小乐、十一子、劫走秋棠的少年以及燕娘的丈夫,他们的人物特征极其相似,都与长笙之死有关,令人疑惑的是这四个角色实为变换了不同身份的同一人。刘老实最终堕入孙四房所代表的“恶”中,并将鲁林保推上一条堕落与罪恶之途,“恶”与罪孽始终在传递、复现。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循环、转化关系,善与恶并非绝对,一切都似乎是命定之路,这些具有相似性的人物虽然以不同的名字命名,却都是共名的神性的损害者与背叛者形象。作者要彰显的并非罪恶行为本身,而是背负罪孽的人类群体。
失去的永远无法追回,无论是伊甸园、童年,还是李永平想象中的那遥远、久远的中国意象。作者通过小说一方面怀思、追忆人类堕落之后的瞬间,另一方面又耽溺于古典的文字、语言,一面渴望救赎,另一面又沉沦于罪恶。小说的循环模式象征着对原罪的无止境的忏悔,而忏悔也伴随着对罪恶与堕落的耽溺,“罪恶书写”成为了标记原乡、自我的更为有力的工具,反衬出那永远失去的“善”“神恩”的圣洁可贵。作者似乎并不愿走出人类那原初的堕落,人类堕落的最初,在《吉陵春秋》中,这个“最初”就是象征过去之神的长笙受辱的日子“六月十九”。由此,时间的纵深感被解构,罪恶降临世间,对人类而言,西绪弗斯的苦役永无终结。
李永平所沉思的是现代性的罪恶、人类启蒙的代价,藉启蒙之光,人类不断解构神话、抹除光晕(aura),这一过程的终点在哪里?堕落、罪恶的悲剧超越了世代,在无尽的时间中、一个封闭的小镇的诸人身上一再复现。小说本身也是现代性之内在矛盾的体现:回望传统、反现代的论述实际上是以现代世界的立场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以历史投射现在、未来,是对传统的重写甚至是背离,恰恰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从另一方面来说,革新有时亦不能脱离旧日世界的阴影,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并非判然有别。无论是主张对古代伟人的崇敬,对昔日荣光的复现,还是进步、舍弃一切陈规旧俗的现代主义者,二者途径虽不同,但都希冀从现代的罪恶与堕落中超脱、飞升。然而,现代主义的理想也许只是一个痛苦的无尽循环,一条无终点的漂泊之路。渴望革新与重复过去的矛盾情绪极其复杂地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包含了差异性的历史循环复归过程。
吉陵镇是“一个模糊、无法找到具体定位的地域,评者有人认为吉陵是华南、台湾、南洋的综合;有人则视为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笔者认为,李永平创作《吉陵春秋》时应未去过大陆,他对中国的想象纯然是文化性的”[9]。对李永平而言,“原乡/中国”意象在文本中是缺场的。“上帝死了,但在他死后他的位置仍在。人类想象中上帝和诸神的所在,在这些假想消退之后,仍是一个阙如的空间”[10]166,人类只能通过想象与渴望,停留在向着这个阙如的空间的眺望中,并通过文字所建构的拟仿物形构它的样态。人们的想象只能遮蔽这个缺场的意象,却无法完全填补它。小说中吉陵镇是一个欲望的、文本的转喻空间,这个“往昔的世界”代表了原乡、古老的中国意象的损毁、残余之物而非其本身,作者所使用的古典化的语言是古老中国的残余物,而不是其所在。与小说世界对应的原乡的象征、救赎后的图景从未被作者直接描写,文本的缺失之物——古老的中国/乌托邦,成为作者、写作行为所追逐的中心,它虽缺场,却是文本终极意义的来源,是文本中种种欲望、希冀的旨归。而作者文字符号的耽溺、狂欢,语言与其蕴含的现实意义分离,来源于对救赎、回归渴望的存而不论。人类的堕落与对救赎的希冀,作者个人对原乡、古老中国的渴望与追寻在《吉陵春秋》中叠合在一起,铸造出一个罪恶之域,最终以文字的异彩作为救赎,展现了亦真亦幻的美学中国。
三、瞬间与永恒——美学时空的重绘
张诵圣认为若以《声音与愤怒》《罗生门》等文本中的多重视点来解读这本书,其实是误用了适用于较早阶段现代主义作品的解读模式[11]33。在小说文本的建构中,《吉陵春秋》刻意遵照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型,移植了传统的、属于过去的世界的古典文学符号体系。吉陵镇切近写实的意味与难以捉摸的象征意义构成了小说的美学矛盾。由于小说文本被抽离了历史时空,“任何传统的,对其主体意涵、道德架构的解读方式都失去了最关键性的依据,又由于写实手法,象征主义的解读方式被否定”[11]33。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吉陵春秋》中的写实主义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文本透露出独特的美学色彩,“《吉陵春秋》所代表的则是唯美主义出现在现代主义后期的一种存在形式”[11]34。
在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中,指符与意符的结合仍然体现出一套有机逻辑,外在的社会、世界的参照系不再有决定性的作用。《吉陵春秋》小说文本中意符与指符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文本中依然成立,小说文本的十二个片段故事建构起一个诡谲的乌有之乡,它们互相关联,互相阐释。在语言方面,作者超脱了中文写作中不时出现的西方翻译文体的弊病,作者被中国文字的外在形式之美感强烈吸引,意义已被搁置一旁,对李永平而言,“文字/书是写一种符号、仪式……是一种秘戏”[8]6,中国象形字是“撒旦亲手绘制的一幅幅东方密戏图,诡谲香艳荡人心魂”[12]。作者对语言、叙事方式、文本架构方面的古典化艺术追求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个人化的使用形成了矛盾的两面,不仅是一次旧世界向我们所在世界的美学复归,也是一次现时的文本建构。当具体的时空标记失落后,从历史长河中流落下来的语言、符号仍引领着我们重建现世的“原乡”。
“现代性是转瞬即逝、捉摸不定和随机偶发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10]339,波德莱尔的瞬间与永恒的对立美学中永恒无疑是重点,漫游的过程始终在寻找超越瞬间之上的永恒。李永平追寻的却是瞬间,动作、声音、表情、色彩等等历史车轮下所堆积的残片,李永平对词语的沉溺与着迷,使得词语从句子原有的秩序中跳脱出来,变得无比醒目。在罪恶的丛林中,作者寻找着命运、文本的诗性的应和之声,如《思念》《好一片春雨》中,都出现了对蓝天、水塘纯美诗意的描写,《大水》《好一片春雨》中出现了相似的芦花、水声以及鸥鹭从塘水上惊起的场景,富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而关于雨水与日光的描写在小说中也重复出现,句法、节奏也较为相近,如“日头水濛濛的一团红”,“红滟滟的一团大日头”。瞬间意象的复现标记了时间、命运的复归。而这样的应和之声中却是深深的无法解脱悲剧的循环的绝望。在小说文本中,这些瞬间“通过错位相互交织,而只有在结尾时,这个结构才获得稳定性”[13]。李永平将瞬间循环、延长、重演改写出来一种“虚拟的永恒”——过去被转化为一个现时的美学幽灵重临这个世界,并供人不断审视。
过去与现在,怀念往昔与耽溺现在的情绪,以循环、折返式追溯的模式联结为一体,形成一个向着未来收缩的时空。而李永平向读者提供了这一可能在美学上的推演与实验。“当时间的连续性打断了,对当下的感受变得很强、很明晰和实在:世界以惊人的强烈程度,带着一种神秘和压抑的情感”[14],在凝视与想象中,时间的先后被否定,历史的次序被切断,读者面对文本很难不陷入如小说人物朱小七一般的默然呆立的状态,人们不禁要问,吉陵镇所在的虚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小说文本的存在模式是什么?暗示了对世界本体、“真实”的质疑。
现代主义者认为存在可认识的真实,他们在作品中追逐真实,揭示出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解读真实的方式,以多重视点讲述的文本仍未放弃对世界本体的追寻,这些文本聚焦的还是人们所生活、观照的世界究竟是如何的面貌。长笙之死是唯一确知之事,是小说中不可置疑的绝对真实,而作者对其命运的推演、复现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现代主义选用表现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的假设性建构”[10]121,长笙命运的不断重复,体现了现代主义式的写法,作者并没有通过假设来求证生存的真相,而是不断重复假设的过程,沉浸、耽溺在长笙之死这一事件中,对其进行诗性重演与可能性的假设,由此编织出一个小镇的众多人物影像及其交织的命运网络。小说是对基于假设、想象的追寻过程本身的耽溺,而并不去追问、验证世界的本源,因此小说在真实的建构、描写手法上有着浓厚的想象、回忆的意味。它作出现代主义者的追问姿态,却始终在追问、凝视、描述,认知或知识已不是写作的主因,而是写作过程、追问过程本身。
王德威认为,李永平是“以现代主义的信念与形式,重铸写实主义题材”[6]102,审视文本,我们不得不追问,吉陵镇中发生的一切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它是小说世界中的绝对“真实”,在这里有其天然的逻辑、秩序与法则,然而小说所显示出的宿命意识、暴力与罪恶的轮回,又仿佛一个古老、原始的世界,是封闭、无法打破的想象空间。作者着力营构的“逼真”的现实与时空的失落形成了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倒错,这与小说中揭示的生命—死亡、善—恶循环之间有着结构上的相应之处。时空的塌缩使得吉陵镇中的诸多事件的细节描写越真实越无法反驳、质疑,就越显示出想象、虚构的色彩。真实变成了自身的反讽之物。小说中的人物无法避免循环的命运,而作为小说文本而言,时空的缺失、历史纵深度的阙如使得读者寻找到了脱离小说层层包裹的虚构想象的路径,从而重新审视历史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之间复杂、倒错的循环关系。
[参考文献]
[1]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作品中的时间塑形:时间与叙事:第2卷[M].王文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137.
[2]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M].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88.
[3]封德屏.李永平答编者五问[J].文讯,1987(29):123-127.
[4]余光中.十二瓣的观音莲:序李永平的《吉陵春秋》[M].李永平.吉陵春秋.台北:洪范出版社,1986.
[5]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王德威.原乡想象,浪子文学:李永平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4(4):101-105.
[7]李永平.吉陵春秋[M].台北:洪范出版社,1986.
[8]王德威.原乡与原罪:李永平《雨雪霏霏》[J].扬子江评论,2013(5):5-7.
[9]齐邦媛.序:《雨雪霏霏》与马华文学图象[M]//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纪事.台北:天下出版,2002:17.
[10]马泰·卡林内库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6.
[11]张诵圣.文学场域的变迁[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
[12]李永平.文字因缘[M]//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40.
[13]CLAUDE LEVI-Strauss.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M].Tristes Tropiques,transl.London:Jonathan Cape,1973:191.
[1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54.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3.004
收稿日期:2016-01-26
作者简介:李欣池(1990—),女,博士研究生。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3-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