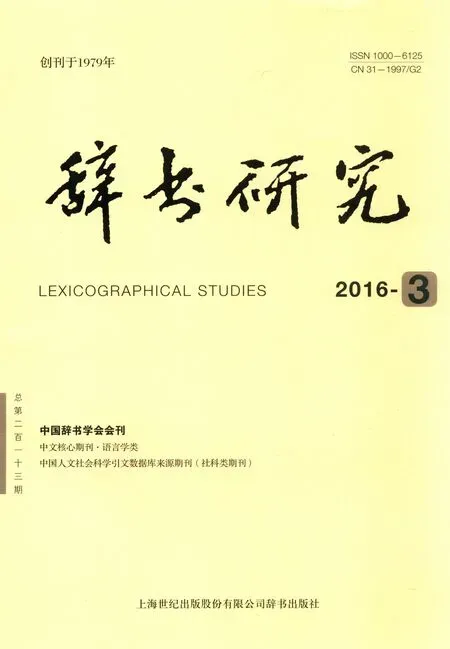汉语词汇史的一座新丰碑
——《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述评*
2016-03-29华学诚
华学诚 李 红
汉语词汇史的一座新丰碑
——《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述评*
华学诚李红
摘要汉语词汇史中现代汉语部分研究最为薄弱,《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构筑了一座汉语词汇史的新丰碑。辞典选收了1.1万余条词语,按词语出现时期分为三卷,记载了旧词语的新发展、新词语的产生过程和不少词汇的过渡现象,在立目、释义、引例方面都有鲜明特色,其中按语的增加最富创意。不过,辞典修订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收词立目标准、处理好释义与按语的关系、考证词语出现的时代、解决儿化词语的书写问题。
关键词词汇史新词新语现代汉语辞典
在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这三个分支学科中,属词汇史的研究最为薄弱,这是学界共识。这个共识是与另外两个分支学科相较而言的,稍微考察一下词汇史研究本身就能发现,它在各阶段的表现并不一样。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最多,那是因为秦汉时期留下了《尔雅》《方言》《小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和东汉经注等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资料,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又把上古传世文献做了穷尽性研究并贡献了丰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上古汉语词汇研究自20世纪以来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这些杰出的成就奠定了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代不乏人,散见于历代注疏、辞书、笔记、杂著中的零星成果也不少,但真正作为断代研究对象得到学界重点关注则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事,不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形势十分喜人。我们相信,再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水平完全可以与上古比肩。研究最为薄弱的是现代汉语词汇史。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汉语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是汉语史最近的一个阶段,现代汉语词汇自然也是词汇史最近的一个阶段。可是,词汇史研究者中却很少有人去研究现代汉语词汇史,而现代汉语研究者又很少有人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描写、分析,以及不断引入各种“先进”理论进行“学”的建构。当然,现代汉语词汇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多年来大学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划分为两门课和汉语史与现代汉语区分成两个学科所形成的误导也不无关系。
宋子然先生是汉字史、汉语史、汉语言学史研究学者,他识高见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把精力集中于现代汉语词汇史研究,并着手进行基础研究资料建设工作。1997年出版了他所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至2011年一共出版了6卷“年编”;2010年由他领衔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研究”获准立项;2014年底由他主编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1912—2011)》上、中、下三卷(以下简称《大辞典》)正式出版。《大辞典》除了主编宋子然先生之外,副主编杨小平、雷汉卿、杨文全、郑剑平等都是汉语史或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编写队伍由来自四川8所高校的30多位骨干专家组成,有100多名硕博士研究生参与了相关工作。因此,《大辞典》是学术团队合作的成果,是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他们共同构筑了一座汉语词汇史的新丰碑。
一、 《大辞典》的史学价值
所谓“史学价值”,即汉语词汇史的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大辞典》收词上起1912年,下至2011年,整整百年;选收词条1.1万余条,按新词新语出现时期区分为上、中、下三卷,如百年中新词语意义又有新发展时,该词条会在后卷中重复出现;此外,又特别发掘、整理、收载了一批民国词汇,为现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个时段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这充分反映出编者的词汇史理念,更表明《大辞典》就是一部现代汉语词汇史工具书。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史实来看,新词语主要包括新创词语和旧词新义两类。我们知道,语言发展是一个连续统,新产生的词语无论是语义结构还是形式常常并不固定,这是成词的必经之路。编纂新词语大型工具书,收集资料需要下甄别的功夫,整理编纂需要下研究的功夫,只有这样,记录的新词语资料才可靠,保存的新词语面貌才可信,做出的解释才有参考价值。《大辞典》正是这样一部基于整理与研究而记载100年新词新语的大型工具书,其汉语词汇史的价值追求不言自明。下面举例具体评说其史学价值突出表现的三个方面[1]。
1. 《大辞典》记载了旧词语的新发展
创造新词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现象,而在原有词语的基础上发展出新义则是语言发展的经济性要求。由旧词产生新词可以分为组合派生和意义发展两种类型。前一种的形式发生变化,但组成成分是旧有词语,近来出现的网络词语比较典型,它们多用音译+意译形式,如“凉粉”“盒饭”“玉米”(周明芳,朱金花 2010)等;第二类为意义发展型,包括术语义域扩大,常用词义域缩小和常用词意义扩大、缩小、转移或色彩和修辞变化等。《大辞典》收词就涵盖了旧词发展的三种类型: 一是常用词变为专业术语,如“割肉”(高价买进股票后,大盘下跌,为避免继续损失,低价赔本卖出股票[2]),“切掉肉”这样一个具体动作行为与卖股票止损具有相似性,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义域缩小,发展出新义,也就成为这个意义上的新词;二是义域扩大,如“勾兑”(喻指为融洽或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采取的行为),由专业术语发展成为普通常用词,即为此类;三是义域变化,如“板块”(引申指相互间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内在联系的某种组合),本为地质学术语,后变化为股市术语,甚至其他行业术语。旧词语当然都有自身的意义,但随着新时期语言现象的日益丰富,在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机制,借由相似性或相关性,这些词都是“旧瓶装新酒”而产生了新的意义。“割肉”“勾兑”是术语和常用词之间由于义域变化而产生的意义转换,而“浇花”(光顾博客、空间或者个人主页留言)、“洗胃”(戏称喝饮料)则是常用词意义的引申。这种发展也有一定的外部动因,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使用便捷性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人们发生语言行为时求新求异的心理要求。
2. 《大辞典》记录了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新词新语的迅速增加是社会经济生活飞速发展的折射和反映,这些现象中的一部分与旧有事物存在联系,另一部分则是新事物、新概念的外化。这两类词语的差别在于,旧有词语发展出来的新词词素与原词词素的结构和意义相关,而新创词语的构成词素之间原来并没有相关性。例如“伴游”(陪伴旅游的行为或者人员)、“裸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退休行为)等。词素“伴”有陪伴的意思,在陪伴旅游的方式产生之前,与“游”并没有意义上的联系。“裸退”行为的直接关涉主体是担任一些职务的官员,词素“裸”与表退休的“退”联系在一起是在“裸退”这种现象出现以后,此前二者并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汉语以复合构词为主,从构词机制上看,截搭机制在新词语的成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截搭”,“好比是将两根绳子各截取一段重新接成一根”,参与整合的两个概念“相关”而不是“相似”,这样的整合就是“截搭”。(沈家煊2006)“伴游”“裸退”一类的词语,两个组成部分并没有相似性,但却具有概念上的相关性,通过截搭机制完成概念整合,将没有关联的“伴”和“游”、“裸”和“退”整合为一个概念。《大辞典》所收新词语中比较特殊的是“下课”,在上卷(指上课时间结束)和下卷(喻指下台或停止干某事)各出现了一次;《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列出了两个义项“上课时间结束”和“指辞职或被撤换”。《大辞典》和《现汉》在后一个义项上有所区别,但最重要的是,《大辞典》不仅确认了“下课”是一个新词,而且还提供了这一新词意义发生变化的时间,因而就具有了鲜明的史学价值。
3. 记录了不少词汇过渡现象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考定新词新义,新词新义是汉语词汇史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但词和非词的界限是难点,也是讨论的热点。语言及其词汇的发展变化,无论是形式,还是意义与功能,都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孤立过程,很多情况下都不能一刀切开,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统,是一个过程。新词新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一次性成词的,大多数都有成词过程,因此必然有相当多的结构处于过渡阶段,其表现就是形式、意义的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性不会永久存在,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要么逐步趋向稳定,要么消亡而成为历史词汇。《大辞典》所收词语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现象。例如,字母词“ABC”收入《大辞典》下卷,释为“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人”,所引之例出现在2003年和2004年。这与人们的通常认知不相符合,因为“ABC”在汉语系统中的常用义为“初步、入门”或者指最简单的知识,《现汉》的解释正是如此:“A、B、C是拉丁字母中的前三个。用来指一般常识或浅显的道理(有时也用于书名)。”显然,《大辞典》所释“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人”是新义。疑问是,表示“初级、入门”义的“ABC”也应该是100年新词语,《大辞典》为什么没有收?原来这个词刚刚出现时是用音译词“爱皮西”,而“爱皮西”收录在上卷,引例出现时间最早的是1916年。据此,我们就能理清这一外来词的发展脉络了: 在“初步、入门”这一意义上,“爱皮西”是原始形式,后来由于语言经济性和构词多样性的发展,简单易懂的字母词“ABC”代替了“爱皮西”成为常用形式;而《大辞典》释作“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人”的“ABC”,不仅义新,而且是一个同形异义词。《大辞典》还保留了一些词语的过渡状态,这些词语经过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进入普通词汇。例如“白金”(豪华的或者超值的),《现汉》解释为“铂的通称”和“古代指银子”。《现汉》讲究规范而相对保守,《大辞典》追求史学价值则更为灵敏,该词的形容词性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已经非常高,很有可能会固化为常用义而进入普通词汇系统。
二、 《大辞典》的主要特色
宋子然先生在《大辞典·前言》中概括了这部辞典的五个特色和价值。这些特色和价值同时也可视为《大辞典》的成就,本文评述《大辞典》的主要特色准备从立目、释义、引例三个方面去谈。为使本文的举例具有说服力,我们采用了随机抽样的办法,这部分所举例证均来自上中下三卷中词条首字汉语拼音为C的词语(以下简称C组)[3]。
1. 从立目方面看《大辞典》的特色
《大辞典》选收100年新词新语万余条,前无古人。以C组为例,《大辞典》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词条与《现汉》一样。《现汉》是中型语文词典,推广普通话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这就决定了它的规模不能没有限制,收词释义不能不具有规范性质。但《大辞典》与之不同,收录新词新语并予以解释是其任务,因此可以说,《大辞典》的收词标准就是一个“新”字,只要是新出现的词语或出现新义的词语均在收载之列,目标就是一个“史”字,保存下百年词汇发展史资料。宋子然先生在《大辞典·前言》中说:“历代的新词新语中,有的经过长期使用逐渐成为全民性一般词汇,流传至今;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或者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便不再被人们使用了,于是退隐为历史词语或者成为消亡词语,不再进入人们和词典编纂者的视野。但是,从语言学的研究角度看,这类‘消亡词语’恰恰是学者眼中的珍品;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看,‘消亡词语’所承载的社会历史信息,又如绝版文物,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大辞典》中真正的历史词汇占比并不大,以C组为例,735个词语中有690个一般词汇,仅有45个是历史词汇。这些历史词汇记录了某一历史现象或事件,如“查三代”“查田运动”“吃大户”“插队落户”“朝农运动”“除四害”“传帮带”“赤卫队”等。
上述收词特点决定了《大辞典》在现代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此外,《大辞典》收词还兼有继承性和创新性,代表各个历史时期新现象的词汇先后依次呈现,就是《大辞典》这一特点的表现。如包含词素“吃”的词条,上卷有“吃大户”“吃老本”“吃请”“吃私”,中卷有“吃大锅饭”“吃国库粮”“吃会”“吃角子老虎”“吃偏饭”“吃商品粮”“吃透”“吃小灶”“吃子孙饭”,下卷有“吃包装”“吃不饱”“吃差价”“吃车轮”“吃床板”“吃公款”“吃官粮”“吃拿卡要”“吃螃蟹者”“吃企业”“吃肉骂娘”“吃软饭”“吃市政”。上述词语除了“吃透”“吃不饱”“吃拿卡要”外,其他均为[吃]+[受事(吃的东西)]或[吃]+[与事(费用来源相关)]。上中下三卷都有该类词的分布,说明了这类现象一直存在,数量的不同说明不同时期同类现象的多样性也不同。从词语内容上看,《大辞典》兼顾了通用性和专业性。在C组735个词条中,普通词语有636个,百科词语有99个。例如在包含词素“财”的16个词条中,9个为普通词汇,如“财东”“财商”等,7个为百科词汇,如“财产申报”“财产协议”等。
2. 从释义方面看《大辞典》的特色
《大辞典》除了遵守一般辞典的释义要求之外,还要尽可能地体现历史资料性特质,编者因此进行了新的尝试——释义+按语。《大辞典·凡例》说: 按语“对该词语的由来与构成进行分析,对该词语的用法、色彩加以说明和辨识,介绍该词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补充相关资料和数据,介绍其意义与用法的演变情况。按语或长或短或无,视具体词目而定”。不仅“按语”是一大特色,《大辞典》的释义也有特点。以C组为例,与《现汉》进行比较的结果是,C组735个词语有310个见于《现汉》,但释义完全相同的极少。那么释义差别何在?例如“擦边球”,《大辞典》释:“喻指在规则边缘做事。”《现汉》释:“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边沿的球。后来把有意做在规定的界限边缘而不违反规定的事比喻为打擦边球。”例如“材料”,《大辞典》释:“供参考用的资料;提供著作内容的事物。”《现汉》释:“① 可以直接制作成成品的东西;在制作过程中消耗的东西;② 写作、创作、研究等依据的信息;③ 可供参考的信息;④ 比喻适于做某种事情的人才。”《大辞典》对“擦边球”和“材料”的释义仅为《现汉》中的部分义项:“擦边球”对应《现汉》的引申义,“材料”对应《现汉》的引申义项②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原因是,《大辞典》所关注的是新词语义,包括新词语出现的意义和旧词出现的新义,这是其历史辞典性质的突出表现。而有关这个词需要交代、说明或者进行分析的内容,《大辞典》通过“按语”来实现了。比如上述二词,前者有按语:“‘擦边球’原指乒乓球比赛中的擦边险球,后喻指在规则边缘,但不违反规则做事。”后者有按语:“‘材料’原指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械或其他产品的物质,即能直接制成成品的事物。后多指供参考用的资料。此外,材料还比喻适合做某事的人。”
此外,“按语”是《大辞典》释义方式的特色。其主要作用至少有四。一是说明词语的出处或来源。例如“纸老虎”的按语为:“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纸老虎’的说法更加广泛流传。”二是说明词语的结构或构词法。例如“彩迷”的按语为:“‘彩迷’仿‘球迷’而造成,指迷恋彩票的人。随着中国各种各样的彩票的发行,彩迷大量涌现。”三是说明词语的意义演变过程。例如“爱人”的按语为:“‘爱人’源自英语单词sweet heart。20世纪40年代开始,革命者流行称呼配偶为‘爱人’。建国前这个词又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又有爱情关系的男女的互称,后来在解放区人们彼此叫‘同志’,夫妻互称为‘爱人’。”四是说明词语意义的外延。例如“安家费”的按语为:“‘安家费’由国家或某个组织按规定发放的用来安置、安抚特定对象的费用,是一项人性化的福利政策。”词典释义通常要求准确、简洁、易懂,倾向于使用“属+种差”的定义式释义方式。“按语”的设立除了释义作用外,还可对词语的来源、使用和意义演变做出分析,运用“非元语言”对词义进行描写性解释。《大辞典》所收均为100年内出现的新词新语,它们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伴随某些新生事物的出现而出现的,所以不少新词新语缺少基本词汇的常用性、稳固性和构词力,部分词语甚至完全不为大众所熟知,因此,通过“按语”这种灵活方式予以说明,十分必要。
3. 从引例方面看《大辞典》的特色
《大辞典》引例“源流并重”,每一义项的例句一般为一到三个,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引例的格式为例句+作者+文献+时间。例如“常识”引例:“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常委”引例:“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词条释义后的第一个引例,多为编者在文献材料中的首见例,具有词汇史价值。引例同时还具有文献价值。上卷所引均为民国时期的材料,中卷所引涉及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政治运动的相关文献材料,下卷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材料。
引例对释义还具有补充作用,尤其是对词语使用和色彩意义等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明作用。例如“财东”,《大辞典》释义为“商店或企业的所有者”。从这一释义并不能看出“财东”一词的具体时代所指,甚至可能产生误解,以为包括现在的商店或企业所有者都可以这样称呼。看到引例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历史词汇:“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的东西也舍不得吗?(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徐一士《一士类稿》1937年)”当然,这一条《大辞典》还另有按语,说明得更为清晰。
三、 《大辞典》的修订建议
清代鸿儒阮元曾经说过:“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矣。”诚哉斯言!宋子然先生所率学术团队著成《大辞典》,其“功”、其“长”上文已经论述大概,此书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重大,惠及学子沾溉学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考虑到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收词立目的进一步完善、解释分析的进一步精准,等等,对于任何辞书尤其是历史性质的辞书而言,都必须在不断修订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所以“短”“误”可以不论,建议还是应该坦陈。
1. 关于收词立目的标准问题
辞书编纂首先要根据辞书性质与目标来确定统一的收词立目标准,纵观《大辞典》,这一问题显然还需进一步明确。例如“恭喜健康”,在语料库中检索所得用例并不多,《大辞典》所引两例都出自同一篇文章,能不能据此认定它是新词语,值得再酌。再如《大辞典》收录仅引一例的“城市化”,却没有收录“城镇化”,是否妥当。还有“超声波”即“超音波”、“超声速”即“超音速”,这类词语需不需要单独立目,可不可以使用“又称”或“互见”处理,值得思考。有一些词能否看作新词语入典,更要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逐条清理,例多不赘。
2. 关于释义与按语问题
《大辞典》在释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成绩突出,但也存在问题。例如“帮闲”,《大辞典》释义为:“受官僚、地主、资本家豢养的文人。”本条按语说:“‘帮闲’又称‘清客’,指给官僚、地主、资本家等装点门面、为他们效劳的文人。”引用了三例:“我在家里,你们又添了一个帮闲的了。(张恨水《金粉世家》1926—1932年)∣主门下的帮闲食客,只会偷懒,只会拍马,不知道怎样把事情办好。(茅盾《子夜》1933年)∣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门外文谈》1934年)”此条释义与按语的一致性在于,都把“帮闲”释作名词,而动词义没有说明。这是问题一。第一例是“的”字短语,“帮闲”肯定是动词;第二例中的“帮闲食客”有歧义,如果是并列关系则是名词,如果是偏正关系就是动词了;第三例也有歧义,句末“的”如是语气词,则“帮闲”是名词,如果是“的”字短语,“帮闲”就是动词。这是问题二。《大辞典·凡例》对释义和按语的作用有明确区分,但在实际词条中却存在混淆现象。例如“吃大户”,释义为:“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按语为:“‘吃大户’指旧时饥民聚集抢夺富家食物或去富家吃饭的行动。现在也指某些地方或部门超额向企业摊派和索取财物。”两者内容交叉,按语的后一部分更像是在释义。
3. 关于词语的时代断限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上卷,因为要做到不将更早出现的词语误定为民国新词语,是需要进一步花费考据之功的。例如“场合”,《大辞典》引了三例,最早的一例出自张恨水1926—1932年出版的《金粉世家》,时代显然晚了。最迟在清末白话文学作品中已能见到,如《乾隆南巡记》(1893):“遇有这样的场合,乌带便派家奴葛鲁葛温前往皇宫祝寿献礼,定哥也让贵哥去问候海陵和两宫太后。”该词在汉语中出现的实际时间还需要深入考证,但不属于民国新词则肯定无疑;另外,“场合”是源自日语的词汇,对此也应该加按语予以说明。
4. 关于“儿化”的书写问题
“儿化”是汉语词汇独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具有区别词义和词性的作用,但《大辞典》中“儿化”词语书写都简省了“儿”,注音也没有儿化,这就带来了问题。比如毒品海洛因俗称“白面儿”,《现汉》写作“白面儿”,注音为báimiànr;《大辞典》直接以“白面”立目,注音也相应作báimiàn,这就与小麦磨成的粉这种“白面”完全混同了。虽然《大辞典》有民国时期的三例书证确实都写作“白面”,但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准确,因为它没能够反映出北方话的事实;当然,其凡例也写明“例证中的文字悉遵原文,不据今天的规范而改之”,这样处理虽客观保存时代资料,但我们还是建议今后修订时应寻找一个妥当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上面四条相对宏观一些,《大辞典》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修订时可以一并思考。比如方言词要不要收,收录之后要不要标注;“29岁现象”“35岁现象”收录了,“26岁现象”“39岁现象”“58岁现象”“59岁现象”要不要收,还是干脆都不收;为了保持辞典的开放性,便于不断补充修订,是否可以考虑把名称改成《现代汉语新词语大辞典》之类,等等。
附注
[1] 本文第二部分涉及《大辞典》词汇史价值的内容也不少。
[2] 括号中的文字是《大辞典》的释义,下同。
[3] C部共有新词语735个: 上卷241个,中卷83个,下卷411个。
参考文献
1. 阮元(清).揅经室集(上),毛西河检讨全书后序.北京: 中华书局,1993.
2. 沈家煊.“糅合”与“截搭”.世界汉语教学,2006(4).
3. 宋子然主编.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4. 周明芳,朱金花.从认知语言学看旧词新义的产生与表现.渤海大学学报,2010(1).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100083)
(李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北京100026)
(责任编辑李潇潇)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七种明清《方言》校注本集成”(14AYY01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方言》集校集注订补”(13WYA00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