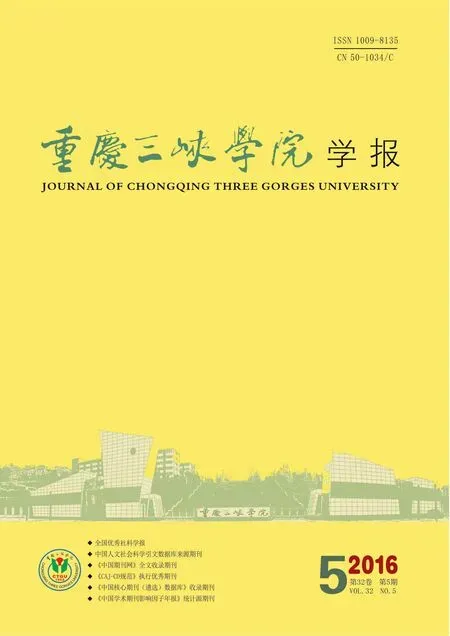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研究综述
2016-03-28杨艳君
杨艳君
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研究综述
杨艳君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因文献匮乏,秦文学(前770—前207年)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大量与秦文学有关的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抓住这一时代契机,将这些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诗歌、神话、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推动了秦文学研究的发展,对未来秦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使学界由来已久的“秦世不文”的说法有了重新检讨之必要。
出土文献;秦文学;诗歌;神话;散文
20世纪60年代以前,秦系出土文献非常有限,仅为一些青铜文字、陶泥文字、玺印文字。直到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才有了第一批秦时的出土简牍。此后,在四川、甘肃、湖北、湖南等地陆续发现了几批秦简,如:青川郝家坪秦简(1980年)、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江陵岳山岗秦简(1986年)、江陵王家台秦简(1993年)、沙市周家台秦简(1993年)、龙山里耶秦简(2002年)等。这些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编定出版,引起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等领域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注重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秦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秦文学的研究。
学界迄今尚未出现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的专著,对该问题的探讨以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及单篇论文为主,且多集中在世纪之交的这二十年。为进一步推动秦文学的研究,有必要对百年来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研究情况作相应论析,指明现阶段研究的重点、难点及趋势,冀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现以文体为依据,将相关研究成果分为诗歌、神话、散文三类予以论述。按照当今的文体划分为诗歌、神话、散文以便于对秦出土文献进行分类梳理与探讨。这些出土文献与当今所说的文体有着对应联系,而非直接对等关系。
一、出土文献与秦文学之诗歌研究
(一)出土文献与《秦简·成相篇》研究
不言而喻,秦诗当以《诗经·秦风》为典型代表。此外,近几十年出土的秦简中也有与诗体十分相近的全文押韵且情感强烈的篇目,以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成相篇》(又称《为吏之道》)为其代表。该篇的公布立即引来学界热议,文学研究者们也积极参与其中。
姚小鸥的《睡虎地秦简成相篇研究》[1]将《秦简·成相篇》与荀子《成相篇》两相对照,结合对“成相”这一特殊唱诵文体历史渊源的探讨,揭示了其在内容、句式及用韵上的特点。陈良武的《出土文献与〈荀子·成相篇〉研究》在对比《秦简·成相篇》与荀子《成相篇》的基础上,探讨了“成相辞”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应是在民间歌谣与瞽史说唱的相互作用与融合中逐渐定型的[2]。廖群指出《为吏之道》与《成相篇》存在极大相似性,最初可能产生于秦地,而训诫歌诀或为二者的文体之源[3]359-362。杨琳硕士论文《简帛文献俗文学研究》的第三章第二节“睡虎地《成相辞》”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指出《秦简·成相篇》易诵易记、词义通俗,源自民间亦能服务宫廷的特点[4]27-32。倪晋波的博士论文《秦国文学研究》分十章对秦国文学(前770—前221年)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了全面论述。论文在“秦简牍文学发微”一节中对《秦简·成相篇》进行了探讨,认为该篇各章的内容既各有重点又相互联系,有整体的形式美,其总体的文学成就相对《荀子·成相篇》较低[5]175-180。沈海波指出,《为吏之道》表明秦人的官吏文书也讲究形式和韵脚,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政府公文显得较为通俗、活泼[6]。刘跃进基于《为吏之道》《荀子·成相篇》二者间的相似性及王应麟对《汉书·艺文志》的考证,推断《为吏之道》应属杂赋创作[7]。
由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知,《秦简·成相篇》的发现不仅对“成相辞”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而且在辞赋、歌诀文学史方面也有重要价值。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秦简·成相篇》与《荀子·成相篇》的密切联系,并采用对比研究法对“成相辞”的特点、来源、应用功能、文学价值等方面进行探讨,拓宽并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但我们也应看到,关于“成相辞”来源及成因的研究依然不十分明朗,有待学者们继续探讨和更多相关出土文献的发掘。
(二)出土文献与秦乐府研究
随着大量秦简的发现,自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陶文公布以来,已有不少秦陶文、玺印、封泥相继面世,如:冷贤二印、临潼秦印、相家巷封泥等。它们的出现为学者们研究秦乐府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线索,也对乐府发展史的了解颇有助益。
许继起在其博士论文《秦汉乐府制度研究》的第一章“秦乐府考论”中结合出土材料介绍了秦宪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及秦代的太乐、乐府情况,对秦代乐府音乐进行了分类,并利用出土的秦封泥探讨了秦代乐府职官及乐律[8[5-39。这为了解秦地的礼乐文化及乐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陈瑞泉《秦“乐府”小考》[9]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出土文物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以充分的实物和论证说明了乐府机构的创设在秦王朝而非汉武帝时,并认为秦乐府的设立促进了俗乐的发展,为汉唐乐府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论断矫正并深化了学界对乐府的认识,是乐府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此外,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在第一册第四章的“关于乐府”这一小节中以夹注形式,引用出土文献材料对乐府始设于汉初的说法进行了修正与补充说明[10]181。由此可见,将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研究相结合不仅丰富了秦文学研究内容,而且能矫正、更新人们对乐府文学史的认识。
(三)出土文献与秦祝祷辞研究
祝祷辞,又称祝辞(祝词),是古代祭祀时用来祷告和祝愿的话。祝祷辞大都通篇押韵、句式整齐、情感强烈,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秦玉牍铭文和青铜礼器铭文中也有不少祝祷辞,它们的出现随即吸引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并陆续产生了一些新成果。
李学勤《秦玉牍索隐》[11]一文以20世纪末出土于陕西华山地区的秦玉牍铭文为研究对象,指明了它的用韵情况,认为该玉牍是秦惠文王借祭华山以使病体痊愈的祝祷辞,并推断该篇当作于秦惠文王末年。延娟芹在《论秦国的两篇祝祷辞》[12]中认为出土的《诅楚文》与《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是战国时期秦国两篇祝祷辞,分析了它们的文学特征,指出二者对前代祝祷辞有一定继承,且有了较大发展。刘原《秦青铜礼器铭文文学意义考论》[13]一文从出土的秦青铜礼器铭文对“三不朽思想”的继承、诗化的特征及叙事手法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它承袭了西周青铜礼器铭文的叙事手法和用韵方式来记秦事,具有独特的史学、文学价值。倪晋波指出《马谋篇》是一篇祭祀马神祈求马匹繁衍昌盛的祝辞,并分析了该篇的用韵、遣词造句及修辞手法,认为其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和明显的创作意识[5]185-186。
秦出土文献中的祝祷辞及其研究,为了解秦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线索和文本材料,同时也开辟了研究其文学特征的道路。这些祝祷辞是秦地先民(尤其是统治者)在丰富多样的祭祀活动中,采用韵文的形式表达内心愿望的真实写照,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对其加以重视与研究,有助于扭转祝祷辞常被文学研究者忽略的现状。
综上所述,学者们多利用出土文献对秦诗歌进行历史的、综合性的研究,着重探讨其文学特征和文学意义,并注重从文学史角度加以考察与定位,有效地推动了秦诗歌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二、出土文献与秦文学之神话研究
神话,是先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表达愿望的一种浪漫化创作,它具有幻想性、故事性、原始性等特征和奇异色彩。而神话的产生,则与他们在神秘莫测的自然环境下进行日常劳动时的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照此推理,长期处于西北一隅的秦地先民在自然环境恶劣与土地贫瘠的双重威胁之下,势必也产生了一些神话。但因传世文献的匮乏,秦神话极少被提及。甘肃放马滩秦简里的《墓主记》(又称《志怪故事》)、近年来出土的多批秦简《日书》及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又称《易占》)中所记载的大量诡异故事和神话传说,不仅印证了秦神话的存在,还客观反映了秦神话的创作水平。
(一)秦简《墓主记》研究
放马滩秦简《墓主记》记载了一个名叫丹的人死而复活,并向别人讲述自己死后经历的诡异故事。该简的发现立即引发了学界热切关注,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一文率先对其进行了文学上的探讨。李先生将秦简《志怪故事》与《搜神记》相比较,指出二者在故事情节的相似性,认为该故事具有鲜明的志怪的性质,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而该故事里丹讲了一些祭祀时应注意的事项,或为这则故事被收入简中的缘由[14]。李先生的文章具有开拓性,引发了后来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倪晋波指出《墓主记》的故事性质、内容情节与后世志怪小说的密切联系,认为其是以官方文书的形式出现的,为考察志怪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线索[5]172-175。杨琳指出秦简《墓主记》是志怪小说之始祖、反映了先民的死生观念,并认为《墓主记》的出土印证了志怪小说是上承史传文学下系古代小说的过渡文体[4]23-26。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一文指出应依据全篇主旨、表现手法及简册形制来命名,认为它是乙种日书的一部分,其篇题可按内容拟为“丹”或“祠鬼”[15]。可以说,《墓主记》的发现对丰富秦文学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古代神话小说发展,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发展上有着开创之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秦简《日书》及《归藏》研究
《日书》是古人从事婚嫁、生子、丧葬、农作、出行等各项活动时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参考之书,它反映了古代天文历法与先民思想观念、现实生活的相互影响。《日书》中通常记载了不少神话、历史传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二十年》[16]451-467中以牛女神话、钟馗传说、与禹有关的神话为例,论证了《日书》在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赵逵夫根据秦简《日书》中有关“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基本情节论析了该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并指出这足以推翻新编《辞源》中有关“织女”条的权威说法,更新学界对该传说的认识[17]。倪晋波认为《日书·诘篇》成功塑造了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鬼神形象,在遣词用语上充分体现了民间趣味,显露出一种生动活泼的文风特色[5]181-184。他还指出,秦简《日书》在牛郎织女、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等著名神话传说的流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186-194。可见,秦简《日书》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源头之一,对其所记载的神话、历史传说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揭示其流变过程,而其中的“牛郎织女”神话将有可能更新学界关于该传说的主流法说,刷新人们的认识。
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中也有不少历史、神话传说。廖群认为:王家台秦墓出土的“易占”类简文就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归藏》,这些秦简保存了远古神话原貌,对研究上古神话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秦简《归藏》几经传抄增饰,或已非殷商筮书原本[3]64-67。延娟芹论述了秦简《归藏》的特点与成书时间,并认为秦简《归藏》有关嫦娥、后羿及夏启登天等许多神话、历史故事,为订正其他传世典籍、梳理某些故事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资料[18]。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秦简《归藏》与汲冢书[19]、《穆天子传》[20]的关系,对其成书及渊源进行了探讨,也有助于厘清神话传说的流变过程。
上述研究成果大都从出土文献的内容出发,探讨其文学特征,并将它们置于神话传说的发展史中来探讨。同时,这些成果进一步扩展了秦文学的研究广度,丰富了秦文学的组成元素,并力图揭示其在神话发展史上的文学史意义,使学界对秦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与改观。它们的存在充分表明,秦地先民同样拥有着丰富、浪漫的想象力,秦文学也散发着奇异的色彩。
三、出土文献与秦文学之散文研究
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中就明确提出了“文笔之分”的论题,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21]655,是否讲究韵律音节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依据。如今的散文,正是由此逐渐演化而来的。它指的是与韵文、骈文相对,不追求押韵和句式工整的文体。从广义上讲,散文包括了除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那么,近年出土秦简中的书信和律法、公文便可视为当时的“散文”。
(一)秦出土文献与书信的文学研究
古时的许多书信虽在一定格式之下展开,但多运用文学表达手法,私人信件中常融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湖北睡虎地秦简里的《黑夫尺牍》和《惊尺牍》(又统称《黑夫惊书》)便是两封极富文学特色的家信。
张鹏立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指出云梦睡虎地出土的《黑夫尺牍》和《惊尺牍》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两封私人书信。文章在探讨简帛书信的书写惯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这两封简帛书信在文史上的价值[22]30-37。杨琳在介绍这两封信件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指出这两封家书语言朴实、情感真挚,类似于抒情小品文,是迄今见及的最早家信[4]36-42。付兴慧认为《黑夫尺犊》《惊尺犊》能在朴素之中贯穿着真情,令人动容。论文以这两封家信为典型,指出其在写作体例、格式上的特色之处[23]36-38。倪晋波指出这两封家信文字质朴动人的原因在于“真情”及其蕴涵的“悲情”,就情感表现的广度及其内蕴的深度而言,它们不仅在秦国文学发展史上别具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应占一席之地[5]180-181。
由上可知,学者们多从该书信的内容、语言特色及情感表达方面进行分析,尤其肯定了它在个人情感表达上的开创性及朴实真挚的感人力量。就书信文学发展历史而言,睡虎地秦简《黑夫惊书》在我国简帛书信史上的开创意义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值得深入探究。
(二)秦出土文献与律法、公文的文学研究
由于秦长期以来施行“奖励军功”“奖励耕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一系列发展军事和农业、严格控制文化思想的统治政策,有秦以来的秦文学十分萧条。但正因如此,秦的律法、公文则相对“发达”许多。这一点在近些年所发掘的秦出土文献上得到了充分验证[23]。事实上,已发现的秦出土文献中绝大部分就是这些律法、公文。但这些律法、公文中也含着不容抹杀的文学因素,某些篇章甚至极具文学意味,与秦文学关联密切。
付兴慧认为出土秦简中的地方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秦文学的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律文由叙述具体案例构成,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行文相对生动活泼,加入了一些文学色彩,是体现其文学性的典型代表。文章还指出,秦简法律文书中叙事性文学因素的存在有助于了解先秦叙事文学的发展[24]32-35。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利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金币》中有关“受(授)衣”的条文,揭示了早周豳地古民与领主的隶属关系,认为战国之秦存有此制或为其军队管制的一种表现[3]172-174。此外,该书还以云梦秦简《秦律杂抄》《效律》为例证,说明“漆园”非邑里之名,而是从事制漆业的生产单位,庄子曾做的“漆园吏”是官方国营重要生产部门的负责人[3]347-350。这一观点有利于人们深入了解庄子的思想情感。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里曾将哲学史的史料分为“原料”和“副料”,并重点论述了“副料”在史料钩沉、考见散佚学说、梳理学派系统上的重要作用[25]8-11。以此看来,秦出土的律法、公文等材料正可视为文学的“副料”。它们并非毫无文学价值,只要我们引起重视并加以利用,也能发现这些文学“副料”中所蕴藏的文学因素,或用它们解决相关的文学史问题。
四、小结与展望
近几十年围绕出土文献与秦文学所展开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许多富有创见、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在研究内容上,这些成果可大致归纳为诗歌、神话、散文三大方面,主要通过探讨出土文献的内容性质和形式特点来分析其文学特征、文学史意义,几乎涉及到了出土文献中的各类文字材料。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相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比、将出土文献置于相应文体的文学史中进行探讨的方法。另外,有一些学者还注意到了秦出土文献在解决文学史问题上的证据作用,并加以运用,取得了较好效果;也有一些学者重视秦出土文献中有关律法、公文的材料,并发现其中的文学因素,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阈。
利用出土文献在秦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有效印证了出土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文学研究中的突出作用,同时也引起了重新检讨“秦世不文”之论的呼声,受到学界热议。随着有关文博和出版单位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学界将获得更多的相关资料,会有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参与到出土文献与秦文学研究行列中来。在更为深入细致的考订的前提下,扩大研究视阈,改进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定能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突破,而秦文学也定能在文学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姚小鸥.睡虎地秦简成相篇研究[J].文学前沿,2000(1):86-100.
[2] 陈良武.出土文献与《荀子·成相篇》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6-121.
[3] 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4] 杨琳.简帛文献的俗文学研究[D].济南: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5] 倪晋波.秦国文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
[6] 沈海波.略论秦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与特点[J].河南社会科学,2010(3):153-155.
[7] 刘跃进.“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J].文学与文化,2010(2):76-88.
[8] 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博士论文, 2002.
[9] 陈瑞泉.秦“乐府”小考[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4):26-32.
[10] 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一)(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 李学勤.秦玉牍索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2):41-45.
[12] 延娟芹.论秦国的两篇祝祷辞[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3-67.
[13] 刘原.秦青铜礼器铭文文学意义考论[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4):91-94.
[14]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J].文物,1990(4):43-47.
[15] 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J].2010(5):46-49.
[16]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二十年[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7] 赵逵夫.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81-88.
[18] 延娟芹.王家台秦简《归藏》的特点及其价值[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2-85.
[19] 梁韦弦.秦简《归藏》与汲冢书[J].齐鲁学刊,2003(6):121-123.
[20] 朱渊清.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J].周易研究,2002(6):9-13.
[21]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2] 张鹏立.秦汉书信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
[23] 李国兰.从睡虎地秦简看秦国的控制制度[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1):74-76.
[24] 付兴慧.秦文学研究:从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
[2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李朝平)
A ComprehensiveReview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he Study of Qin Literature
YANG Yanjun
Because of the scarcity of handed-down documents,the study of Qin Literature (770B.C.-207B.C.) has been weak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many unearthed documents which were connected with Qin Literature have been found, which aro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Some literary scholars took this chance to combine these unearthed documents with literary study, and they have achieved breakthrough results on poem, myth, and essay. These results cannot only promote the study of Qin literature to a new phase, but also be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study of Qin literature. Moreover, they even caused the requirement of reconsidering the long lasting saying “there’s no literature during Qin Dynasty”.
unearthed documents; Qin literature; poem; myth; essay
I206
A
1009-8135(2016)05-0096-05
2016-03-22
杨艳君(1989-),女,湖南怀化人,闽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前文学与文化。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史论”(项目编号:14XZW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