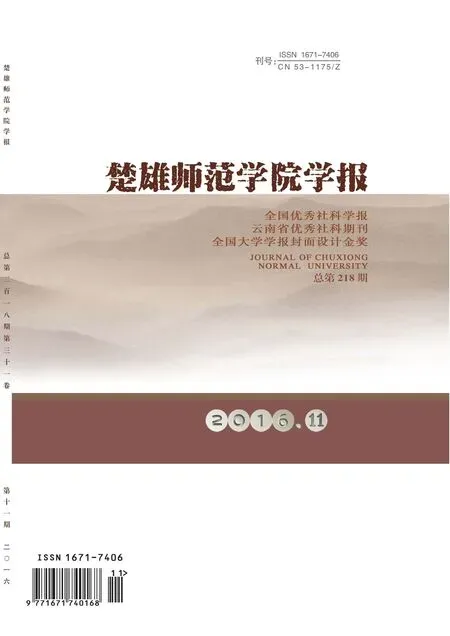从苏曼殊小说反观其心灵世界的困境与难局
2016-03-28伏涛
伏 涛
从苏曼殊小说反观其心灵世界的困境与难局
伏 涛
小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窗口,是时代的镜子。透过短命才子苏曼殊的小说世界,我们可以寻觅其心灵世界的失落与苦痛、困境与难局,惆怅与迷茫、挣扎与抗争,探究那个时代的不幸、社会的不堪。苏氏小说自传色彩浓、纪实性强,这增加了小说的个性化特征和时代感,此小说为我们读懂苏曼殊,了解苏曼殊生活的那个时代提供了最佳文本。
苏曼殊;小说;人生;困境
文学作品是生命个体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命体悟的文字外化,是作家心灵的显露,苏曼殊的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其生命悲苦的结晶。在短暂的三十五年的人生之旅中,苏曼殊历经了人生的多重悲苦,他将人生的多重思考,红尘中的希望、失望乃至绝望写入作品,特别是小说中。而小说世界和小说家的经验世界是两个不一样却又互相联系的世界。“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1](P238)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P251)中外文学理论间确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在思考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作思考的是苏曼殊的小说世界与其人生经历,亦即经验世界的联系。
苏曼殊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却被那个时代、社会遗弃。在家里他是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子、混血儿;在社会上,他又被边缘化,成为时代的孤儿弃子。正如其题画诗所云:“明日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3](P218)他可谓是“行云流水一孤僧”,[3](P219)他常常“无端狂笑无端哭”。[3](P219)“自古才子多冷落,一腔歌哭付文章”,[4](P252)曼殊小说是其抒发心灵的重要通道,因此,它成为我们走近其心灵世界的一条最佳路径。不可否定的是,曼殊创作小说亦有“著书都为稻粱谋”[5](P471)之因,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直抒胸臆,他在小说中真切地表达了对世事人生的诸多理解与各种看法。
在亲情上他缺失父爱,又得不到正常的母爱;在爱情上他是零食主义者,他纵情、滥情,却又钟情、重情。友情是其情感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可谓红尘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这在其诗歌和书信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和流露。曼殊小说中描写得最多的是爱情,“情僧”曼殊在男女之情上矛盾纠结,有诸多的困惑。作为曾经积极入世的热血男儿,他对人生、社会、世事均曾有过期待、向往,也曾失落、迷茫,男儿可能遇到的人生困境,苏曼殊在其短暂的尘世生活中皆一一碰到。生活中的磨难像沉重的铁锤不时地敲打着他柔弱的身躯,敏感的心灵。红尘中的悲欢离合,生命个体的种种痛苦遭际让敏感多情的苏曼殊无所适从,他痛苦迷茫、抗争消沉,百感交集、痛不欲生。生命的苦痛、生活的潦倒、生计的艰难无情地侵蚀着苏曼殊脆弱的身心,他最终禁不起这重重苦难的折磨,英年早逝,草草地结束了人间生活。
士子的心境、心态与心理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曼殊小说中透出的心灵世界的悲喜甘苦,紧紧伴随着那个时代政治风云的潮起潮落。苏曼殊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卒于民国七年(1918年)。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期间发生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八国联军的侵略、光绪变法、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作为曾经想有所作为的士子,苏曼殊在家庭变故之际,历史变革之秋,其内心世界的苦痛是难以言表的。他母亲是其父日本侍妾的妹妹,他属于私生子。因为他父亲所生小孩女多男少,他被带到中国,从此与生母远隔重洋,天各一方、难得一见。中日战争的爆发对苏曼殊的精神刺激很大,其父是中国人,其母是日本人,他的感情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游弋不定。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事实上,他又有日本血统,而且出生于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其精神之根更多的是在日本。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兵戎相见,战火连绵让苏曼殊茫无归所,这在小说中多有抒写。他想逃避尘网,到一个宁静、诗意化的没有世事纷争的世外桃源。在其小说中,既有老子小国寡民的追求,也有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向往,这些都是对人间不幸的逃避,说明作者想寻找人生乐土,安顿自己受伤的身心。
颇具诗人气质的苏曼殊在其人生之旅上努力追求着“诗意的栖息”,但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带给他的却是人生的不幸、命运的悲剧,这些不幸与悲剧在其精神世界的文字外化——小说世界中有着充分的表现。小说中对理想世界的多重虚拟的背后,是小说家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堪以及小说家自身处境的种种苦难与不幸。小说是时代的镜子,通过它可以照见那个时代的林林总总、世态百相。曼殊小说亦如此,它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在失落才子心灵世界中的投影,通过文本我们可以反观那个转型社会的诸多音讯,那个动乱时代的潮汐。曼殊关注苍生、悲悯同类,他有着显著的忧国忧民情怀,他把对世事人生的关怀更多地投注在小说中,故其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下面就从男女之情和家国之情两个维度来看苏曼殊小说世界中的思想纠结与精神困惑。
一、男女之情的思考
曼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在爱情中大体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一方面心仪优秀女子,欣赏她们美丽的容颜与出众的才华;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自己坠入情网,不能自拔。清幽绝俗、福慧兼修的女性是作家所喜爱的,小说写到:“鬓发腻理,纤浓中度。余暗自叹曰:‘真旷劫难逢者也!’”[3](P31)“玉人密发虚鬟,丰姿愈见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何所止。”[3](P24)“余且答且细瞻之,则容光靡艳,丰韵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3](P94)情状如见,真实感人。当爱如期而至或邂逅所爱时,他却又心存顾虑,认为“天下女子,皆祸水也!”[3](P91)在《碎簪记》中他借一青年之口说出“爱的深处便是烦恼”[3](P93)的道理。《断鸿零雁记》中的男主角说:“余乍闻是语,无以为计。自念:拒之,于心良弗忍;受之,则睹物思人,宁可力行正照,直证无生耶?余反复思维,不知所可。”[3](P36)“此夜今时,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躯,以还父母,又哪能越此情关,离诸忧怖耶?”[3](P36―37)“奚事一逢彼姝,遽加余以尔许缠绵婉娈,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有是处耶?嗟乎!系于情者,难平尤怨,历古皆然。”[3](P38―39)对男女之爱他有独到的看法:“须知天下事,由爱而生者,无不以为难,无论湿、化、卵、胎四生,综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3](P13)“今兹茫茫宇宙,又乌睹所谓情、所谓恨耶?”[3](P49)拒绝爱情后他心里又有丝丝不舍:“余目送静子珊珊行后,喟然而叹曰:‘甚矣,柔丝之绊人也!’”(《断鸿零雁记》)[3](P44)《天涯红泪记》中亦有类似描写:“生太息曰:‘甚矣哉,情网之罥人也!’”[3](P213)“生自还钗之后,心绪凄怆,甚于亡国。”[3](P116)此语甚妙,颇富新意,把男女之情和家国之情相比,新颖独特、生动感人。他一方面说红颜祸水,另一方面又对优秀女子投以无限的理解、同情与爱念:“谁料云鬓花颜,今竟化烟而去!吾憾绵绵,宁有极耶?嗟乎!雪梅亦必当怜我于永永无穷。余羁縻世网,亦恹恹欲尽矣。”[3](P56―57)悲悯雪梅的遭际,厌倦红尘。“雪梅是后茹苦含辛,莫可告诉,所谓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于冥府,较在恶世为安。此非躬历其境者,不自知也。”[3](P12)这里的“此非躬历其境者,不自知也”并非闲来之笔,乃作者曼殊的自道语。写到雪梅的遭遇时他不由联想到自身童年的痛苦往事,情不能自己。《焚剑记》中的眉娘自叙身世道:“继母遇我无恩,往往以炭火烧余足,备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问。邻居有老妪,劝余至石塘为娼,谓一可免阿母猜忌,一可择人而事。”[3](P82)读此令人心酸,世道险恶、逼良为娼,此中显见作者对薄命女子深切的同情与怜悯。曼殊借助《惨世界》中的孔美丽提出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传统观念的批判。孔美丽想继续上学,姑母不肯:“他就大怒起来,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来骂我”[3](P172)作者对女子读书求学持肯定态度,但对女子留学却不能接受,他曾用诙谐的语言予以无情的讽刺。
苏曼殊关注女性,对女子裹脚大加鞭挞:“更有可笑的事,他们女子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用白布包裹起来尖嵸嵸的好象猪蹄子一样,连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3](P171)女子裹脚乃一大陋习,对此苏曼殊给予彻底的否定、无情的批判,观点正确,表达幽默风趣,由此看来,曼殊对女性解放是有贡献的。他除了关心本土女同胞外,还把眼光投向西方女性,关注其服饰打扮:“你不要去笑他们吧。你看我们欧洲的人……说起这班妇女,把好好的腰儿,捆得这般细,好象黄蜂一般;还要把许多花草、鹅毛、首饰,顶在头上。你只晓得那支那人敬神、包脚的丑风俗,倘若世界上有了不信上帝、不捆细腰的一种人,也就要耻笑我们欧洲人了。”[3](P171)对欧洲女性好细腰的习俗颇有微词,苏曼殊虽醉心西方文学,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毕竟有限,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他说:“女子之行,唯贞与节。世有妄人,舍华夏贞专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习,向背速于反掌;犹学细腰,终饿死耳。”[3](P78)由此看来曼殊对女子好细腰特别反感,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他还说:“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竞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借爱国主义而谋利禄。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侩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灵果安在也!”[3](P101―102)由是观之,曼殊的女性观中先进与落后并存,这有时代之因,不能委过于曼殊一人。
二、不堪世俗的批判
曼殊小说多有对封建末世不古的人心和日下的世风的描摹与批判。这既源于作家身处的那个时代的腐朽与社会的不堪,也发自于作者忧国忧民的士子情怀。小说中这样的内容大多有其现实的影子,作品对末世林林总总的弊端进行了广泛的描写与深入的批判,由此可见作家的思想倾向、卓识与良知、胸襟与追求。
首先是对乱世情状的描绘。《天涯红泪记》有道:“世乱本属司空见惯也。”[3](P208)这是概括性的描述。《非梦记》和《惨世界》描写得比较具体。《非梦记》云:“二人至钦州,值江上盗贼蜂起,劫芸香以去。”[3](P120)《惨世界》中那老者寻思道:“现在乡下正是盗贼纵横,他二人的父亲,恐怕有些不妥。”[3](P172)与《焚剑记》相比,《惨世界》中写的有点浮泛,而《焚剑记》中有的描写则让人惊悚,触目惊心:“是间有乱否?何以军中以人肉为粮也?”[3](P83)“老者厉声曰:‘一何少见!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制,几忘之。’言已,出心且行且嚼。”[3](P83)该小说中“生”亦喟然叹曰:“嗟乎!有道之日,鬼不伤人。于今沧海横流,人间何世!”[3](P77)《天涯红泪记》中男主角垂涕曰:“嗟乎!四维不张,生民凃炭,宁有不亡国者?”[3](P208―209)
其次是对世风日下的感喟:“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则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长。世态如斯,可胜浩叹!”[3](P8)“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3](P28)“唐、宋之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3](P50)“哎!世界上这般炎凉凄惨,暗无天日,也和这天气一般,倒是怎么好呢?”[3](P151)《断鸿零雁记》云:“后此夫人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尔托根上国,故掣尔身于父执为义子,使尔离绝岛民根性,冀尔上进为人中龙也。”[3](P7)《焚剑记》有云:“不意今之丧乱,甚于前者。……不图季世险恶至于斯极也!”[3](P77)“今宇宙丧乱,读书何用?识时务者,不过虚论高谈,专在荣利;若夫狡人好语,志大心劳,徒殃民耳!”[3](P78)
再次是对世人重名利、重金钱的鄙视。《惨世界》第十一回店小二告诉男德:“这店叫做色利栈便是。……这虽是两个丑字,你看这世界上的人,哪一个不做这两个字的走狗呢?就是这尚海的人吧,还不是这样吗?……那‘名’字虽也是人人所好,但是有了‘色’,那名也就不要了。我看还是‘色’字好。”[3](P181―182)该小说第八回金华贱为了钱忘恩负义,准备手刃救命恩人时口里说道:“世界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我金华贱这时候也为金钱所驱使,顾不得什么仁义道德了。”[3](P155)在下一回中男德感叹道:“哎!臭铜钱,世界上哪一件惨事,不是你驱使出来的!”[3](P156)同一回中老婆子对孔美丽说:“我心爱的美丽呀,你看世上的人,哪一个不是弃少贪多呢?”[3](P163)《非梦记》中有云:“所以必为汝娶凤娴者,门户计耳。”[3](P119)此篇开头有云:“薇香但善画,须知画者,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岂如凤娴家累千金,门当户对者耶?”[3](P111)
另外,作品还描绘了所谓志士的众生相,这集中在《惨世界》中:“只恨那口称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几句歪诗,说两句爱国的话;其实挽回人间种种恶习的事,哪个肯亲身去做呢?”[3](P152)“但是那班志士,我也没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其实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那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3](P151)对不务正业、装腔作势、自私自利的所谓志士的批判中流露的是苏曼殊自身的拳拳爱国之心。透过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苏曼殊有很强的担当意识:“哎!世界上这般凄怆模样,难道我就袖手旁观?听他们这样不成吗?”[3](P151―152)他主张实干,反对空谈误国:“老者又忙说道:‘这是男儿分内事。你总要实心实意地做去,莫学尚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的人才好哩。’”[3](P178)
三、颠覆与重构
苏曼殊的排满情绪十分明显,《惨世界》中他给一个人物命名如下:“他姓满,名儿叫做周苟。”[3](P158)谐音“满洲狗”。谐音命名是小说家的常用手法,曼殊小说亦常如此,此不赘述。下面我们来看曼殊对那个时代及周围环境的不满与排斥。《惨世界》十二回云:“况且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3](P195)如此话语在那个时代极具鼓动性。对此世界曼殊已经绝望,借“凡妈”之口说道:“生在这样世界上,何必要做好人?古语道得好:‘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有尸骸。’”[3](P136)“哪晓得在这个悲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见钱眼开,哪有真正行善的人呢?”[3](P138)如此世界腐烂不堪,行将就木,绝非修修补补即能奏效,必须推倒重来:“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是难救这场大劫了。”[3](P156)“不必说了,说着也无用的。世界上都是这般狼心狗肺的事,也就没奈何。”[3](P158)在《断鸿零雁记》第五章中作家提醒读者道:“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污,复有何患?宁省后此吾躬有如许惨戚,以告吾读者。”[3](P10)他身处槛外,却心念红尘:“这好惨的世界,好惨的世界!我男德若不快快设法拯救同胞,再过几年,我们法国的人心,不知腐败到何等地步。”[3](P162)在这里作者借男德之口说出自己的焦虑,他立志拯救这个世界。“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3](P148)这里作者怒不可遏,禁不住大骂出口。“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象那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怎么就好听这鸟大总统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大皇帝呢?”[3](P199)作者反对独裁政府,追求自由独立。“法国文豪讲自由”,[3](P182)他借文豪之名表向往自由之志。作者借小说文本宣扬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班蟊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儿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3](P149)“世界上有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哪注定应该是哪一人的私产呢?那金华贱不过拿世界上一块面包吃了,怎么算是贼呢?”[3](P149)“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3](P149)他认为百姓的贫穷源于财主的为富不仁,主张劫富济贫,提倡任侠之风:“至于任侠之流,为人排难解纷,亦所受于天耳。”[3](P213)他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行侠仗义,不求回报:“哪里话来!我并不象那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也不过为着世界上这般黑暗,打一点抱不平罢了。”[3](P155)被他救助的女子为了赏银要拿他告官,那女子说道:“我们正在穷到这样地步,何妨趁着这个机会去发这笔大财,好比顺手牵羊了。”[3](P177)“男德听说,就两泪汪汪,一言不发。”[3](P177)此处的无言透出作者对世道人心的绝望与焦虑。人心不古,社会腐败,官府可憎,男德说:“大娘,我并不发癫,不过听了‘官府’两个字,就不由我火上心来。”[3](P159)这无疑是苏曼殊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宣泄对官府的憎恶。
生逢末世,遭逢不幸,那个时代的零余人苏曼殊想逃避世俗的纷争,在山涧水滨安顿身心。《天涯红泪记》曾云:“读吾书者思之:夫人遭逢世变,岂无江湖山薮之思?况复深于患忧如生者。”[3](P209)面对现实的不堪,失志迷茫、颇有魏晋风度的苏曼殊亦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或骑牛村外。幽恨万千,不自知其消散于晚风长笛间也。”[3](P8)“吾家去湖不远,鱼甚鲜美,价亦不昂,村居胜城市多矣。”[3](P9)《断鸿零雁记》中有对世外桃源景象的描写、勾勒,颇得归隐之趣:“时值崦嵫落日,渔父归舟,海光山色,果然清丽。忽闻山后钟声,徐徐与海鸥逐朗而去。”[3](P19)渔舟唱晚,海鸥逐浪,暮鼓晨钟,这是苏曼殊向往的美好去处,人间乐土。“吾自顾遣此余年,舍此采药济人之事,无他乐趣,若村妇烧香念佛,吾弗为也。”[3](P22)《惨世界》中姨氏所言流露的是作者的人生志向。“寺为明时旧构,风景大佳。生饮水读书,狷行自喜,人间幻景,一一付之淡忘。”[3](P121)“复感老人情极真朴,以为天壤间安得如是境域?”[3](P211)“余颇觉翛然自得,竟不识人间有何忧患,有何恐怖,听风望月,万念都空。”[3](P45)小说中的这些段落显见隆中之景,桃源之境。这既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作家逃避现实的心理体现。
曼殊小说的写实性、自传性源于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源于作者的赤子之心,在其小说中常常有些情节和他实际生活极为相似。他时常在小说中直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喟与政治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小说即是其人生的演绎,是其思想的呈现。曼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身上大多有作家自身的影子,熟悉曼殊生平后再读其小说,就觉得书内书外的人物有时实难分清。读其小说可以寻觅乱世中士子人生的艰难、命运的悲催、生计的艰辛,可以看出苏曼殊的希望、失望乃至绝望。“学道无成,而生涯易尽,则后悔已迟耳。”[3](P38)“回首前尘,徒增浩叹耳。”[3](P51)此乃对蹉跎岁月的感喟。多病之躯,该如何好好地生于红尘之中:“吾多病,殆不能归家,即于寺中长蔬拜佛,一报父母养育之恩,一修来世之果。”[3](P117)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余与法忍至上海,始悉襟间银票,均已不翼而飞。故不能买舟,遂与法忍决定行脚同归。沿途托钵,蹭蹬已极。”[3](P54)这是他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写入作品。“余以肠病复发,淹留湖上,或观书,或垂钓,或吸吕宋烟,自用已吾疾,实则肠疾固难已也。”[3](P93―94)“友人出百金纸币相赠曰:‘子取用之。’余接金,即至英界购一表,计七十元,意离沪时以此表还赠其公子上学之用,亦达其情。余购表后,又购吕宋烟二十元之谱。”[3](P102)“每人一碟子咸牛肉,一碟子鲍鱼汤,一大块面包,牛油,另外还有一大杯葡萄美酒。”[3](P173)这些都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描写。“余周历人间至苦,今已绝意人世。”[3](P42)“事到如今,且幸这世界上没一些儿系念,一些儿挂碍,正好独行我志了。”[3](P198)孤洁寡合之士苏曼殊面对挫折,发出如是之感叹,他甚至堕入悲观主义的泥潭:“昔日风流都不见,绿杨芳草髑髅寒。……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3](P51)“何由知君高义干云、博学而多情者也。”[3](P213)苏曼殊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博学多情的侠义之士:“一天风雪压巴黎,世界凄凉了无期。游侠心酸人去也,众生懵懵有谁知?”[3](P157)曼殊可谓是乱世独行侠,男德是他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写道:“哎!这钟的声音,也不过是不平则鸣,况是我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德吗?”[3](P151)“大丈夫四海为家,俗言道‘人间到处有青山’,不怕没葬身之所吗?”[3](P172)不过在现实中,曾经满怀豪情壮志,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苏曼殊最终却被红尘所抛弃,遁入空门,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1](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裴效维校点.苏曼殊小说诗歌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赵雪沛选注.倦倚碧罗裙——明清女性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责任编辑 徐芸华)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Exploring the Predicament and Dilemma of Su Manshu’s Spiritual World from His Novels
FU Tao
(Dept.ofChinese,JilinNormalUniversity,Siping, 136000,JilinProvince)
Novel is like the window of a writer’s spiritual world, the reflection of the time. Through exploring Su Manshu’s novels, we could discover something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is short-lived talent, such as the disappointment and pain, predicament and dilemma, melancholy and confusion, struggle and fight, and know the misfortune of the time as well as the mess of the society. His works have a strong flavor of autobiography and documentary character, adding the uniqueness and sense of time. This novel provides the best tex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writer and the time he lived in.
Su Manshu;Novel;Life;Predicament
2016 - 09 - 19
伏 涛(1966―),男,文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诗文。
I207.42
A
1671 - 7406(2016)11 - 0023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