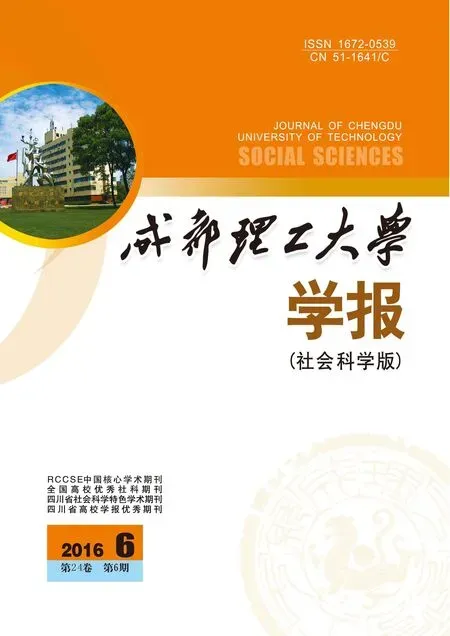环境治理的思想资源:站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分岔路口
2016-03-26刘雪怡
刘雪怡
(云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昆明 650500)
环境治理的思想资源:站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分岔路口
刘雪怡
(云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昆明 650500)
今天从中国到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对此,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崇尚“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取生态环境方面的观念,用以纠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古代农业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均存在严重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正是这一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古代农业文明的衰亡。传统农业社会虽不乏生态环境思想,但由于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这些古老的生态环境思想没能成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挽救这些文明的命运。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要有效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借助现代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能力,来探索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全新模式。
生态;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备受环境问题困扰的国家。从大城市恼人的雾霾到食品饮水的安全问题、再到物种资源的衰竭,许多事实向人们亮起红灯: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已经恶劣到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程度。研究中国环境资源的加拿大学者史祢迩(Vaclav Smil)甚至警告说:“中国不断恶化的生态系统和不断扩大的环境污染”可能成为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暴力冲突”的关键因素[1]。无论史祢迩的警告是否合宜,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是不争的事实。为求解这一难题,国内不少知识分子开出了类似的药方:以史为师,从中国这个有着古老“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吸取营养,以对抗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多年来,从各种角度阐释这种见解的书籍文章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经久不衰的声音。那么,中国古老农业文明传统中的环境思想到底能不能指导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治理?本文拟在史实和现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印证和辨析。
一、 生态环境难题的中国解法
许多尝试着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中寻求生态环境元素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出发点,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乃是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恶果。例如有研究者说,“随着近现代西方‘黑色文明’的全球扩张和资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榨取,西方工业文明……不仅造成了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资源浪费与匮乏,人际关系、群己、民族与国家关系紧张,世界动荡不安、恐怖主义泛滥以及文明冲突,同时也造成了人自身灵与肉、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是现代人心态失衡、人格分裂等现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2]将中国思想传统作为业已堕落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拯救力量,这样的论述思路在同类观点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是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那么回到农业文明,具体地说,回到中国传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项。如果工业文明的世界是一个物理的世界,那么农业文明的世界则是自然的、有机的世界,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正是利用生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农业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毫无疑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生态环境的改变都引起了古人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3]
在众多论证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的生态环境思想的学术作品中,儒、释、道三家均被提及。其中最受研究者重视的是儒家,中国思想界一些最有声望的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等均有相关论述[1]。“儒家文化的滥觞和发展建立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之上”,“抛去笼罩在儒家文化政统帝制的‘光环’,作为道统和学统的儒家文化对现代人类而言又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底蕴和思想启示,尤其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己的相互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自然生态伦理。”[2]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是很多学者的共识。有人指出,“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发掘生态启示。因此,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不断升温,学术成果日益增多。”[4]学术成果的增多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以儒家、生态、环境等关键词的组合进行搜索,结果显示这方面学术论文的数目高达上千篇。除此之外,尚有难以统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科研项目与此论题直接相关。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经常被用来作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态环境意识的证据,然而学术作品中有的将其视为儒家(这是多数),有的视为道家[5],甚至还有的将其与释家联系起来[6]。
不仅中国学者,西方世界对中国古老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效应也长期存在神话般的印象。约阿希姆·拉德卡(Joachim Radkau)在《自然与权力》一书中就提到过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环境可持续性的崇拜之情:李比希认为,中国“没有任何科学的指导却找到了我们的教师在盲目中徒劳地搜寻的智慧之宝”,中国“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三千年来它的肥力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继续增加”,尽管在那儿“每平方米的土地上生活着比荷兰和英国都多得多的人”。此外,《富饶的土地》这部作品也“向全世界的读者介绍了中国土地的不可摧毁的神话”[7]。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面,存在着一些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世界非常不一样的事实——这些事实未必是中国学者人人熟知的。
二、农业文明及其生态危机
世界史上,将人类社会的类型划分为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分法。与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学术界公认,农业文明虽然没有今天人人痛恨的工业污染,但普遍具有负面的生态环境效应。许多全球史著作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类从食物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之后,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均发生恶化。例如,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那本被称作是“别开生面的鸿篇巨制”的《世界:一部历史》就说:
前农业社会并不一定会发展进入农业社会。如果采集能够确保富裕和安全,并不能就此推断农业社会能够带来更多的富裕和安全。转向农业社会的后果并不总是有利的。在从采集过渡到农业生产的早期阶段,食物供应反而变得不太稳定了,因为人们只能依赖耕种收获的食物,甚至依赖于单一的食物,实际上等于食物的范围变小了。结果,整个社会更容易受到生态灾难的威胁。饮食的范围一旦变小,饥荒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了。何况,人们既要种植又要收割,等于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才能获得同等数量的营养(尽管驯化的食物收获以后更容易加工食用)。由于需要组织劳动,这就助长了不平等和剥削。集中驯养动物使得天花、麻疹、风疹、水痘、流感和肺结核等疾病更容易传播。[8]
这样的论断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所有农业文明——在许多观察者眼中,中华文明也并不例外。尽管中国的农业文明显示出令人惊叹的稳定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相当经济,然而放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来看,中国的生态环境在农业普及之后确实是朝着退化的方向在变化的。赵冈在对中国历代生态环境进行审视之后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中,而其变迁之速度愈到后来愈快。变迁最剧烈的是大片的森林消失。其次是草原之缩减与沙化,以及淡水湖泊面积之缩减或完全湮没”[9]。马立博(Roberts Marks)对华南的生态环境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认为中国农业在生态环境层面上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西方著名的环境史学家们将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然而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从华南地区的历史来看,到19世纪末,岭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而且这一地区正在不断‘漏出’大量的资源,因而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输入才能养活其不断膨胀的人口。简而言之,如果没有不断增加的投入,帝制晚期华南的农业发展就难以为继……”[10]伊懋可(Mark Elvin)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甚至重新阐释了夸父逐日的神话,将其看作古代中国生态灾难的一种隐喻:“中国人在过去三千年中,投下巨大而且大致成功的努力来改造他们的土和水,清除他们的森林,发展他们的经济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是不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灾难,不可阻挡的导致生命支持体系之衰弱或甚至破坏——在此是否可以河水既竭仍不足以满足夸父之口渴来象征呢?”[11]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指向了一个并不愉快的观点: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生态环境观念,然而这些观念甚至没能成功地保证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过去几千年中产生好的生态环境效应。对此,史祢迩直言不讳地总结说:“敬畏自然是中国恢宏漫长的文明中的一个古老观念——然而这个观念无法战胜不那么可敬的环境破坏的力量,结果环境破坏的力量不断积累,会给现代中国遗留下广泛的环境退化问题。”[1]141
三、制度缺失与制度供给
中国古代在生态环境理论上的丰富遗产与现实生态环境的困境之间的反差,不免使人产生罗兹·墨菲那样的疑问:“中国人既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观念,何以竟完全使他们的环境堕落。此一哲学观念似乎与西方的观念形成强烈的对比,至少从《创世纪》的年代(当亚当被告知要主宰整个自然世界)以后是如此。”罗兹·墨菲推测,“主要的原因似乎很清楚的就是人口的压力”[12]。人口增加诚然会导致向自然索取更多,然而这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回答,接下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一个文明会产生令它自己陷入生态环境危机的人口规模?这个文明的自我调整功能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
如果把视野和时段放宽,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农业文明均未能成功地调节好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它们最后归于灭亡的原因。柴艳萍在综合了当代环境史学者对玛雅文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古代农业文明衰落的生态原因之后概括说:“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是悠久,它对自然的开发越是深入,从而对它所在地区的破坏也就愈加严重。人类最光辉的成就大多是奠定在对文明基础的自然资源的毁灭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上”,“这正是文明由盛入衰的根源所在。”[13]显然,农业文明在驯服自然、为我所用的过程中,终于落入“生物圈是以它与人类较量的失败来打败人类”[14]的陷阱。这样的命运,是任何古代生态环境思想传统都没能挽救的。
参照现代社会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农业文明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跟治理生态环境的制度缺失有重大关系。早在20世纪初,E·A·罗斯就发现了中国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制度性困难:“如果中国没有过早摆脱封建制度,他们可能会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颁布严格的森林法、建造广阔的狩猎林地保护区,环境就不至于这么糟糕,他们也会从环保中获得裨益。再如果500年前中国能够制定一项保护环境的国策,他们的环境肯定比现在好许多。而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定出一套非常科学、有效的恢复环境的措施。这一措施甚至要求比最发达的欧洲政府能够制定的措施更为全面彻底。而这显然超出了当代中国人的远见和管理能力。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的自然环境将持续恶化。”[15]
然而,要想产生这种制度,传统的生态环境思想却无能为力。传统讲究的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是一种“无言之教”——事实证明,这种无言之教远远不足以承担起促成“制度供给”(institution supply)的功能。很多环境史学家注意到,孟子就曾经给梁惠王提出过相当正确的生态环境建议:“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这些建议从未能成为比较固定的国家政策,以至于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遗憾地评论说:“如果中国人曾注意到了孟子在最后这一方面的劝告,那么,他们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地位就会稳固得多。”[16]
观念始终无法催生相应的制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致命伤。观念仅仅意味着一个问题进入了知识阶层的认知,制度供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性机制。相对来说,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其古代社会的格局对促成制度供给的结果要有利得多。早在中世纪,英格兰在“环境立法方面的变革有时候是势不可挡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已经出现国王出于自身利益而将诺曼森林法引入英格兰的记录:“他对猎物大加保护,并为此订立法律,谁要是杀死公鹿或母鹿,就要被刺瞎双眼……”[17]24-25古代英国动辄通过制订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历史传统,成为它后来转型为现代国家的一个极其有利的历史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才宣称是英国“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而英国本身也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17]。因为“英格兰的最重要特点是其法律,它体现了也导致了英格兰的另辟蹊径。这个特点实在非同小可,因为法律和司法如同润滑油,使一个文明的所有部件能够顺利合作。”[18]206到1848年,英国为人类贡献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过一段经常被今天的环境史学家引用的论述:“法律给财产本身下定义的职能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人也许以为,法律只要宣布并保护每个人对自己产生的产品或在自愿原则下正当地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的产品的权利就行了。但是,难道除了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认作是财产的东西了吗?不是还有地球本身、地球上的森林、河流以及地球表面和地球之下的所有其他自然资源吗?这些是人类的遗产,必须制定法规来规定人类应如何共同享用它们。应允许一个人对上述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在何种条件下行使何种权利,是不能不做出决定的。无疑,对这些事情做出规定,是必要的政府职能,而且是完全包含在文明社会的概念中的。”[18]也就是说,政府和法律在平衡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问题上的功能是决定性的。环境治理亦与此同理。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环境治理正是沿着这个方向逐渐发展起来的。围绕着治理生态环境这一需求,一整套前所未有的国家机器和法律法规开始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并成为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机制。这个制度生长的过程已经成为环境史学研究的重点,如休斯所说,“环境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是,对环境政策中的政治表现的研究。这体现为,许多国家创立了一套体系,它由环境法、环境部等行政部门以及拥有环保执法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组成。在这一领域,环境组织与利益集团关于立法的斗争也是故事的一部分。”[17]9
四、“现代性问题惟有用更现代的方法解决”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在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席卷全球、农业的重要性甚至在中国也已经显著下降的今天,如果重新回到中国本土的生态环境思想传统,是不是能够对抗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呢?从通过民族情感来形成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的角度来看也许不无助益,然而关键性的力量不会是来自农业时代的思想传统——因为这个思想传统在过去就没能从思想层面贯彻到制度层面,从来没能将中国的农业文明从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中挽救出来,又怎能期待它在现代工业社会发挥出过去从未有过的社会功能?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19]。与农业文明一样,现代工业社会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较之农业文明相对缓慢、往往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态环境恶化过程,现代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显得规模更大、时间更短、毁坏更彻底。这一特点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位于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由于前苏联时期一次相当于广岛核爆量400多倍的核爆事故,切尔诺贝利成了人们闻之色变的无人区。封存在事故地点的数百吨核原料至今仍然是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而核物质对地下水的渗漏和污染至今仍在继续导致畸形婴儿的出生。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受到影响的国家,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在漫长年代中始终无法痊愈的巨大伤口。对于全世界来说,切尔诺贝利就是工业时代末日灾难的一次小规模预演。在切尔诺贝利这个极端例子的背后,还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全球性工业污染、物种灭绝、生态退化等现代性疮疤。
然而,前所未有的拯救力量也出现在工业文明时代。这个力量,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厄内斯特·盖尔纳(Earnest Gellner)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认为工业文明一个重要的不同特点就是进步性:“迄今为止,工业社会是唯一依赖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依赖连续不断的改进而生存的社会。毫不奇怪,它是第一个发明进步和不断改善的观念和理想的社会。”[20]体现在政治领域,现代工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公共权力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农业时代那种单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统治的情况,而是转向了造福公众的公共管理领域。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领域,在经济学上属于典型的“公共事务”——市场机制调节不了,统治型的古代国家利维坦(Leviathan)又缺乏动机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管理。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以管理公共事务为天职的政府一向受到广泛认可的常规职能就是治理生态环境。正是从现代工业社会开始,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再是思想家口头的观念,而是一种基于国家权力的公共服务。
这无疑直接导致人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按C·E·布莱克的术语,这叫做“决策强化”:“在公共事务领域,这种决策的强化采取了国家行政机构日益集中化的方式。”[21]由于无以伦比的现代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古代社会无力实施、只能长叹“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环境治理问题,在今天和未来却能够借助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和优化来得到解决。因此,完善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使其达到现代社会应有的效率和管理水平,才是今天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所谓“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要应对工业社会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社会的自我完善功能,而不是回到农业文明的思想传统——借用哲学家邓晓芒的一句精辟名言:现代性问题惟有用更现代的方法才能解决。
[1]Vaclav Smil.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141.
[2]赵金科,陈慧文. 儒家文化与中华农业文明生态伦理--以近现代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为参照[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8.
[3]李金玉. 农业文明——古代生态环保思想的重要源头[J]. 农业考古,2010,(4):9.
[4]范慧,乔清举.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综述[J]. 理论与现代化,2015,(2):125.
[5]张苏,赵芃. 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J]. 社会科学研究,2012,(5):170-173.
[6]魏学宏. 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与生态文明的构建[J]. 河池学院学报,2009,(6):18-21.
[7][德] 约阿希姆·拉德卡. 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 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122-123.
[8][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世界:一部历史(上)[M]. 叶建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3.
[9]赵冈.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105.
[10][美]马立博.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M]. 王玉茹,关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
[11][英]伊懋可. 导论[M]//刘翠溶,伊懋可. 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 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3.
[12]罗兹·墨菲. 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M]//刘翠溶,伊懋可. 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 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92.
[13]柴艳萍. 古代农业文明兴衰的启示——生态环境呼唤科学发展观[J]. 道德与文明,2004,(4):57.
[14]李工有. 生物圈:人类历史发展的怀抱[J]. 读书,2000,(7):7.
[15][美]E·A·罗斯. 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M]. 张彩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8-19.
[16][美]J·唐纳德·休斯. 什么是环境史[M]. 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23.
[17][英]艾伦·麦克法兰. 现代世界的诞生[M]. 管可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
[18][英]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M]. 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68.
[19][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M]. 徐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05.
[20][英]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0.
[21][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 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
编辑:鲁彦琪
Choosing Between Two Environmental Traditions :At the Crossroad of Agraria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s
LIU Xue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an 650500, China)
Mod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a tremendous environmental crisis. To meet this challenge,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advocating the approach of returning to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thoughts, which is believe to be an affluent trove of ways to reach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 The Chinese scholars also argue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uld rectify the deficiencies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tting the deteriorating human-nation relationship back to its right trajectory. However, if pu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history, the fact is that nearly all the ancient agrarian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caused severe negative ecological effects which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fall of those civilizations. It is true that the ancient agrarian civilizations did develop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oughts. Nevertheless, all of them, unable to engender a system of institution supply, were no more than ideas or opinions, and even failed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ir day which finall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their civilizations. This historical fact demonstrates the unavoidable conclusion that ancient environmental thoughts are no remedy to mod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Instead,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uld only be solved within the fram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at is, a strong government with unprecedent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bility.
ecology; environment; pollution; agrarian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6.06.010
2015-12-30
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制度移植’与‘渐进改良’:从民国成都的公共卫生管理看现代转型的路径”(13XJC770001);云南师范大学2013博士项目“社会进步与社会冲突”
刘雪怡(1973-),女,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比较现代化。
C913.9
A
1672-0539(2016)06-00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