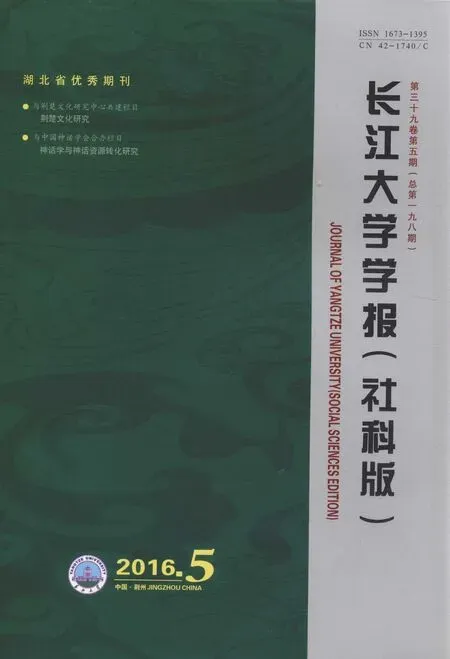末日悲歌
——科马克·麦卡锡《路》的创伤叙事艺术
2016-03-25彭秀芬
彭秀芬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
末日悲歌
——科马克·麦卡锡《路》的创伤叙事艺术
彭秀芬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麦卡锡在他的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路》里采用了创伤叙事艺术。大量的闪回、梦境与延宕手法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的逻辑叙事时间,使小说呈现出碎片化叙事的特点。这些创伤叙事技巧同时也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路;创伤叙事
美国当代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是一位创作题材丰富的小说家,他的创作题材涵盖了南方小说、西部小说和后启示录小说。有评论称“麦卡锡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唯一继承者”。①参见科马克·麦卡锡著、杨博译《路》,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麦卡锡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描写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1](P326)美国评论界巨擘哈罗德·布卢姆更是对他的文学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当今美国仍然健在的一流小说家”。[1](P4)小说《路》是麦卡锡的第十部作品,也是2007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该小说作为后启示录小说的代表作品,自出版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该小说讲述了核战爆发十年之后的末日景象下,一对父子的求生之旅。在末日来临之时,父子坚守道德底线,演绎了一曲凄美的末日悲歌。整部小说中并没有太多的人物性格塑造与丰富的情节,体现出一种简洁的叙事艺术。短小的对话、简洁的句子以及全文不分章节的文体特点,使小说充满了叙事诗的格调与韵律,充满了哲思与诗意。
末日危机下,悲剧色彩笼罩着整个世界。主人公不断被梦魇侵扰,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父与子不停向南,走向象征着希望与未来的海岸。父子不断遭遇生存危机,又不断强调携带火种。小说结尾父亲离世,儿子遇上了“好人”,似乎预示着希望的到来。然而,小说结尾段的斑点鲑鱼身上的迂回图案却又使结局扑朔迷离。“创伤叙事中作者借‘病态’的手段,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推迟谜底的出现。”[2](P50)这些“谜底”的推迟尽显了作者对延宕手法的巧妙掌握。梦魇与回忆的运用打破了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叙事,使小说摆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而延宕手法的运用,又作为一个曲折的线索,将梦魇与回忆叙事艺术性地串联起来,彰显《路》的悲剧性创伤叙事艺术。
一、难以磨灭的伤痛——往事的再现
“记忆的问题在哲学中占有一席中心的地位”,[3](P3)巴赫金如是说。记忆对于叙事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回顾过去对肯定回顾相关事实者的身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获得对过去真情的某种突兀的揭示,它迫使我们彻底地重新阐释以往我们对亲近者和自己所持有的形象。”[4](P279)男人对于亲人和逝去美好家园的回忆是一种身份诉求,和男孩相依为命的他迫切地希望可以从回忆中找寻归属感。这种对家园的回忆也体现了记忆的空间性。“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它的空间特性也非常明显,而这种空间特性必然会给叙事带来深刻影响。”[5](P60)小说中不断地运用回忆的心理时间,并将其穿插于叙事的物理空间中,通过男人对过去的回忆来书写创伤。
小说中,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男人对妻子的回忆次数在数量上有着绝对优势。显然,对于男人来说,失去妻子的创伤比核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影响更深刻。他多次回忆起不堪社会苦难而自杀的妻子。他回忆起她的自杀,自责不已。“她可能是用一片黑曜石自杀的。他曾亲手教过她。”[6](P49)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教她怎样自卫,也自责没有担起保护好她的重任。“男人的脑海里浮现出当时路上的景象,他想,自己本该努力保住她的命,让她和他们在一起,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救她呀……他喊着她的名字。或许在梦中,他也在念叨着这名字。”[6](P46)失去妻子的创伤在不断的回忆与叙述中得到了缓解,男人对妻子的回忆也不再局限于她的自杀,而是向着愉快的方向发展。“男人想,自己也曾在这样的夜晚醒来,几只螃蟹正咔嚓咔嚓地横行在前一天晚上留下来的牛扒骨的煎锅上……躺在满天繁星的夜空下……男人跪下,轻轻地爱抚着睡梦中女人的发丝,心想,若他是上帝,他也会造出别无二致的世界。”[6](P185)此时,妻子在男人的回忆中不再只是以自杀的形象出现,而是开始恢复到灾难发生前的快乐的状态。这便是创伤叙事的价值,即通过叙述来缓解创伤,治疗创伤。
除了对妻子的回忆,小说还多处叙述了男人对于童年的记忆。在他童年的时候,世界就已经出现了萧条的迹象。他回忆起小时候和叔叔去湖边拾柴的情景。“湖边就像一处乱石堆,全是枝丫扭曲残断的树……一条死鲈鱼翻起肚皮豁嘴浮在清水中,还有黄树叶……这便是他童年完美的一天,这一天塑造了未来的日子。”[6](P11)显然,生态灾难的到来并不是突兀的,它在男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彰显迹象。与现在相比,过去始终是美好的。他无法任由过去消失,于是便不停地通过回忆来安慰在现实中受挫的自己。他带着孩子走进了自己小时候的家,回忆起童年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他在看到扑克牌的时候试着回忆小时候玩过的纸牌游戏。“创伤对于个人经验来说,最初是一件难以承受、难以理解,因而也无法进入意识的事件,直到再次出现。”[7](P40)关于那场灾难的记忆实在痛苦,那是男人没有接受也接受不了的事实,因此它一时并未进入到男人的意识之中。路途中偶然看到的这些已经在记忆里逐渐淡化的物品又重新激发起了埋没已久的记忆。当灾难前的生活再次涌现,灾难留下的创伤再次侵袭男人的心智。
“你忘记了想记住的,记住了想忘记的”,[6](P10)男人对男孩说,话语中流露出些许无奈。“每一次回忆都是对往事本来面目的侵袭。”[6](P111)生态灾难带来的个人创伤和社会创伤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男人深知这些创伤是难以治愈的,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使孩子摆脱创伤。“我要将死人的脑子从他头发缝里清理掉。”[6](P63)小说中大量的闪回,使得作品的叙事打破了严格的物理时间,呈现出碎片化的叙事特点。这种碎片化叙事正是主人公受到创伤后混沌的意识状态的显现。
二、从未远离的创伤——梦魇的侵扰
“构成梦内容的全部材料或多或少来自经验。就是说,在梦中再现或被记起。”[8](P9)麦卡锡采用了大量的梦境来叙述主人公的心理创伤。末日来临前,男人接连经受了家园被毁、亲人丧生的灾难性创伤。对于这些创伤,文中并没有过多的进行直接描绘与渲染,而是通过隐性的创伤叙事手段来展现这些事件带给男人和孩子的伤害。面对这些灾难和伤害,男人和孩子有时表面上表现得相当平静,经常会重复“好吧(okay)”这个词。然而,表面上的平静并不代表男人和孩子已经在内心接受了这些伤害,它们化装入梦,不断地侵袭着男人和孩子的睡眠。“幸存的行为和创伤经验一样,是重复地面对自身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头脑不可能直接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幸存对于人类而言,就成为生活的一种不可能情况的无休止的证词。”[7](P43)因此,对于男人和孩子来说,幸存并不一定是一件幸运的事。幸存意味着他们要不断地克服家园被毁、亲人离世的创伤,同时还要鼓起勇气去面对被恶侵占的人吃人的世界和未知的未来。“创伤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梦,梦境和梦景赋予表现以无限的空间。”[2](P50)通过梦这一手段,小说的创伤叙事打破了线性叙事结构,开拓了更广阔的叙事空间。
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孩子来说,小说中女人的自杀都是一种灾难性创伤。男人不断地重复关于女人及其自杀行为的梦,孩子也不断被噩梦侵扰。“在一般意义上,创伤被描述成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事件的反应。”[9](P92)对于女人的自杀,男人和孩子当时并未有过多的感情流露。“早上,男孩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装好背包,准备上路的时候,他才转过身看着露宿过的营地,说道:‘她走了,对不对?’男人说:‘是的,她走了。’”[6](P49)男人和孩子“总是如此的从容不迫,即便遇上最奇异的事也难显出一丝惊讶之情,成熟得完美,直面死亡。”[6](P50)从容不迫便是两人并未能及时接受女人自杀这一事件的表现,这个事件日后以梦魇的方式不断在二人的意识中重复。“创伤经历重复出现在患者的梦中,说明了创伤经历的影响巨大,正如人们所说,患者被定格在其创伤上。”[10](P13)“在许多梦中,他都梦到他苍白的新娘朝自己走来。她于一片青翠中现身,蒙着绿叶状的纱。她的乳头用白黏土漂白过,肋骨上也涂了白颜料。她身着一袭轻纱,头发乌黑,以象牙梳和贝壳梳挽起。她眼神低盼地微微笑着。”[6](P15)“被漂白了的妻子”,显然是一个可怕的形象,她盼望着他的到来,轻轻地笑着。在另一个梦中,“她得了病,而他在一旁照料”,[6](P27)而现实中,女人是自杀的,死得突然,显然并没有得到他的照料。这些梦虽然与现实有所出入,却体现了男人对未尽到保护妻子责任的自责。
另外,孩子的梦也为小说的叙事增添了悲剧色彩。与父亲不同,孩子并未有太多关于母亲的梦。孩子自出生起便生活在恶劣环境里,他亲眼目睹了婴儿被父母吃掉、人们为了食物互相残杀、弱者被世界抛弃等场景。“创伤导致创伤影响和创伤表现的分离:不知原因地感到他说不清楚的东西,没有感觉地表现他自己不能感觉的东西。”[11](P42)孩子的梦常常是含糊不清、寓意不明的。在孩子的意识里,这是一个无序的世界,混乱的世界。因此,他的噩梦也是杂乱无章、难寻动机的。他曾梦到一只企鹅,“(企鹅)就从拐角出来了,但是没有人给它上过发条,真的很吓人”[6](P31)。在孩子的梦里,那只企鹅在没有上发条的情况下向他走过来。它毫无缘由地发动了。在另一个噩梦里,男孩梦到一大团蛇在相互取暖,“男子们朝蛇身上浇了汽油,把它们活生生烧死了”[6](P159)。这种残忍、恐怖的梦揭示了男孩内心根深蒂固的创伤。在一路向南的过程中,男孩一直是向善的,他不断地说服父亲向弱者伸出援手,即使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也不例外。男孩甚至还说服父亲要善待一条可怜兮兮的狗。然而,世界却没有善待他。世界不断地将人性之恶暴露在他面前,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再者,父子二人还经受了一些启示性的梦境的困扰。小说以梦开篇,男人做了一个关于怪物的梦。“在岸另一边,一只兽从石头圈成的池塘中抬起涎水涟涟的嘴,它的眼睛如蜘蛛卵般煞白无神,盯向光源。”[6](P1)这种怪诞的噩梦也展示了叙述者想象力的高超。叙述者通过设置怪物场景,来表现男人的意识在受到创伤后所经历的一种混杂无序状态。“他在梦里来了访客,是一些他从未见过的生物。它们不讲话。他感觉他睡着时那些生物就蹲伏在他的床边,待他一醒,它们就躲远了。”[6](P129)这些未知名的生物虽然与现实联系不大,却也是创伤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慢性创伤性噩梦”。“创伤如果被‘包扎起来’或‘封闭起来’,那么它仍然存在着,并在夜晚(噩梦)和白日(意念闪回)不时浮现。”[12](P190)看似荒诞无稽的噩梦,其实是主人公所受创伤的一种内化,在被压抑之后不自觉地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展现出来。
梦是这部小说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全篇241页的篇幅里,至少有10处有关梦的详细叙述,另外还有多处提及男人和孩子从未知的梦中惊醒。大量的梦境叙述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使读者跟随叙述者不断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自由穿梭,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
三、跌宕起伏的命运——延宕手法的运用
弗洛伊德在他的《摩西和单一宗教》中谈到了从埃及出来的人刚开始强烈拒绝强加给他们的单一神教信仰,然而他们出埃及后还是逐渐被潜移默化,开始信仰单一神教,他认为这是因为影响是滞后的。他进而从病理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和犹太单一教之间尽管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但它们之间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有‘潜伏期’。”[13](P137)这里的“潜伏期”和文学中的“延宕”有异曲同工之处。“延宕是后现代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创伤叙事中作者借‘病态’的手段,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推迟‘谜底’的出现。”[2](P50)在延宕的过程中,叙事者不断地设置障碍,以将“谜底”不断地往后拖延,迫使读者反复猜测、推敲。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层层深入。“延宕的过程就是作品意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过程。探寻的过程越艰难,获得的东西越珍贵。作品意义呈现的过程越曲折,读者的感悟越清晰、越深刻。”[2](P50)在创伤叙事作品中,延宕不仅是一种叙事手段,还指创伤的心理机制。“创伤事件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它的延宕中。”[9](P24)作品中延宕手法的运用增加了叙事的模糊与不确定性,迫使读者更加深入地探寻作品的意义。
上帝是否存在?他是否会来拯救他们?这个问题通过男人的内心独白多次被重复,答案逐渐模糊。“‘你在吗?’他呢喃道。‘我最后还能见到你吗?你有脖子,好让我掐死吗?你有心吗?你这该被永世诅咒的。你有灵魂吗?哦,上帝,上帝啊。’”[6](P10)男人对上帝显然产生了质疑,他对上帝进行谴责。上帝本应该拯救苍生的,可是他却允许世界变成这样一幅破败不堪的样子。“在这条路上,没有上帝派来的传讯人。”[6](P27)虽然对上帝充满抱怨,彼时的男人还是对上帝抱有希望的,他期冀上帝的传讯人,然而,上帝使他再次失望。后文“圣杯”的出现再次让读者猜测到上帝的拯救。“金色的圣杯,都已招待神仙了。请不要告诉我结局。”[6](P64)关于上帝,途中遇到的人的话语也不断给读者进行提示。途中的老者对男人说:“压根儿就没有上帝,我们就是先知。”[6](P143)叙述者将有关上帝的对话散漫地布置于父子的路途中,使“谜底”不断往后拖延。这个延宕过程直到男人不幸离世才结束。男孩遇上了“好人”,那个女人和他讨论上帝,“他试着和上帝说话,但他还是最想和父亲说话……她说上帝的呼吸就是他爸爸的呼吸”[6](P241)。至此,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谜底”才彻底揭开。对于男孩来说,上帝就是和他朝夕相处的父亲。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但希望还在。他是父亲生命与希望的延续。
延宕手法的运用还体现在男孩的命运以及故事的结局上。文中多次出现父子间有关死亡的对话。“你觉得我们要死了,是不是?我不知道。”[6](P85)在食物极度缺乏时,男孩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一路上,饥饿不时地困扰着父子。有几次,两个人连着好几天吃不上东西。叙述者极力渲染死亡的威胁,竭力使读者相信死亡的来临。然而,就在最艰难的时刻,叙述者通过父子关于“火种”的对话使读者内心重燃希望。后来,男人生病了,男孩的命运令人担忧。然而,男人却重复地说他不会让男孩独自一人留在黑暗中。叙述者不断地设置陷阱,让读者以为父亲离世时男孩也会随他而去。他留给男孩一枚子弹。后来,父亲却说:“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死在我的怀里。我以为我能,但是我做不到。”[6](P234)男人走了,剩下男孩独自一人。不过,也正是此时,男孩遇上了似乎是他与父亲一直在找寻的“好人”。这对夫妇及其一双年幼的儿女的出现也似乎预示着拯救的可能和希望的到来。叙述到此,故事已经可以完美收尾。然而,叙述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补充了一个寓意模糊的结尾。“(斑点鲑鱼)背上有一些迂回的图案,展示着世界即将变成的模样。地图和迷宫。那地图和迷宫象征着一件无法挽回的事。这错误终将不能被纠正过来了。”[6](P241)“迂回的图案”意欲何指?结尾段的目的在于什么?这种模糊的延宕叙事促使读者不禁发问,不停地探寻作品的意义。
《路》以其丰富的闪回、梦境以及延宕的典型创伤叙事手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时间,为作品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叙述空间。同时,这些手法不断地打破叙事逻辑,也使作品叙事呈现了碎片化叙事特点。麦卡锡对这些技法灵活运用,将小说的悲剧美描绘到极致,谱写了一曲生态困境下壮丽的末日悲歌。
参考文献:
[1]Roger Matuz.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ume (57)[M].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0.
[2]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前苏联)巴赫金.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A].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法)兹维坦·托多罗夫.恶的记忆,善的向往[A].热奈特论文选:批评译文选[C].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5]龙迪勇.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A].叙事丛刊(第三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Cormac McCarthy.The Road[M].New York:Random House,2007.
[7]王欣.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8]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1998.
[9]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0]Sigmund Freud.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5.
[11]Dominick La 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12](美)厄内斯特·哈特曼.噩梦:噩梦的心理与生理[M].董江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3]Sigmund Freud.Moses and Monotheism[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64.
责任编辑 叶利荣E-mail:yelirong@126.com
收稿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4ZS093)
作者简介:彭秀芬(1989-),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
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5-0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