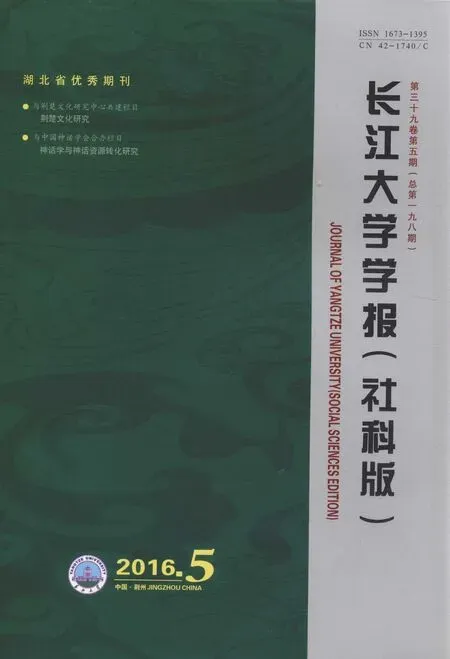面向城市的乡村意绪:晓苏转型小说简论
2016-03-25高艳芳
高艳芳
(安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面向城市的乡村意绪:晓苏转型小说简论
高艳芳
(安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晓苏近年来的转型小说,可以看作乡村转型文学叙事的典范。从《花被窝》《陈仁投井》再到《酒疯子》,晓苏突破旧观念与新时代的双重性禁忌,将人性与时代转型之间的剧烈冲突,寄放于性的世界之中,于朴实中透出深刻的人生情怀。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激活与重建的背景,使得其小说中花样的被窝意味、悠远的古井传统、深沉的酒瘾象征,有着别样的情趣。
关键词:晓苏;转型小说;乡村;意绪
晓苏转型小说中透出的渐次浓烈的乡土情怀,借助于真实可感醇厚迷人的故事缓缓展开。小说外部结构上的叙事元,叠放在古老的乡村图景中,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凸显出别样的光辉。
一、乡土伦理的秩序变迁
三部小说都以乡土伦理核心要素为线索:《花被窝》以婆媳关系为线索,《陈仁投井》以翁媳关系为线索,《酒疯子》以夫妻关系为线索。这三大关系,皆为乡土伦理中的核心伦理,而且都与性禁忌有关。因丈夫常年外出打工而得不到日常幸福的媳妇秀水,在婆婆的性监控中蒸发着亲情与信任,又在对婆婆的反监控中融合了人性与友情;老伴去世后倚靠儿子的陈仁,因儿媳的多次陷害不得不流离失所,最后连租住一间仓库也难以如愿,不得不以投井自终;以酒为生借酒浇愁的酒疯子,被妻子的力量控制着,这既是一种生活的力量,也是一种性的力量。但三部小说关乎性禁忌的叙事线索,却又并非同一层次的社会现实书写。[1]
《花被窝》更多地展示了边城野地的淳朴民风。生于斯乐于斯的人们,只隐隐约约地与遥远的城市发生着关联。秀水是不幸的,因为她是一个与丈夫恍如隔世的女人。她没有生活的依靠,也没有日常女人的快乐。[2]这种不幸,既是肉体的不幸,也是乡土社会面对现实转型时期的必然不幸;然而,更不幸的是,她被作为一个不正常的女人,被丈夫的母亲时时监控着。肉体的不幸,是人生的必然不幸,因为肉体原本就是在世上经受不幸的躯壳;可是,当一个经历着肉体不幸的人,还要终日因为这不幸的肉体而承担更不幸的精神的侮辱与欺压时,这将会是怎样的人生灾难呢?秀水因花被窝而最终有幸,为了自己,也为了油菜坡古老的感恩信仰,她获得了女人应有的幸福;可是,花被窝最终在阳光下鲜艳夺目地泄露了她微乎其微的幸福秘密。可怕的性禁忌,将秀水与婆婆之间的矛盾瞬间激化。秀水俨然成了千古罪人,被绣入花被窝的图案之中而不得抽身。值得注意的是,花被窝又是一种隐喻,即灾难的救赎者。当它使主人沦于灾难之中时,便也是它重生救主的开端。秀水发现了婆婆走亲戚的秘密。这个秘密也就是花被窝的秘密。于是,花被窝从婆婆监控秀水的秘密赃物,陡然化身为婆婆与秀水之间亲密友好的天使之花。这朵花,真正成为油菜坡神奇的乡土之花。它来自远古,无拘无束,自然天成地将两个女人与外出打工的秀水的丈夫隔绝开来,使外出者成为浑浊世外的被弃者与代言人。
与《花被窝》的温情古朴相比,《陈仁投井》则带有厚重的沧桑感。从安家角度而言,陈仁有三大不幸:老伴无缘终生相守,儿媳不孝将其扫地出门,爱女有志却花季凋零。从交友角度而言,陈仁亦有三大不幸:好友对其行为不解,村官不愿租房于他,邻里一心算计其爱女。陈仁的六大不幸,件件指向死亡,于是,便有了陈仁投井之必然。故事的缘起,在于陈仁的爱女去城市打工,因生计所迫而出卖自己的肉体。扭曲的城市,像龙卷风一般暴虐着,荼毒了来自乡土的陈仁那聪明、勤劳、美丽、有志的女儿。邻里在城里做包工头的周大本,是这场风暴的凶手,可是,由于女儿自己选择了死,遂使真正的凶手无据可索。陈仁投井,是小说家为大不幸的陈仁两肋插刀奉送的一门复仇绝技,虽然有点走火入魔。这口井是乡土之神,在现代无恶不作地疯狂摧残传统之时显身护法。
如果把酒看作酒疯子的立世之本的话,那么,性禁忌便是他妻子的立世之法。在酒疯子的虎妻手中,性禁忌是一方运用自如的法宝。就此而论,彰显《酒疯子》的意义的,不是酒疯子,而是以酒疯子为诱饵的酒疯子之妻。《酒疯子》以脱俗之笔,还原了酒的草根特质与凡夫本性。文化乡土的意蕴,沉淀在酒中,让人流连忘返,深爱不悔。酒疯子不拘于尘俗杂务,放浪形骸,说酒话,做酒事,看似疯子,却“酒醉心明白,酒后吐真言”。那些看来正儿八经的村长乡长的革命公务,被酒疯子批得一无是处。小说以革命干部的话语连接酒疯子混球式的酒话,恰与其妻把控性禁忌而迎合那些人的行为,遥相呼应。
二、乡土人生的符号化挣扎
花被窝其实是乡土人生的吉祥物。[3]每个女孩出嫁前,都会为自己的花被窝倾注浓烈的情怀。代表婚嫁喜庆的花被窝,本身也成为合乎伦理纲常的幸福的性意象,成为一个家庭乃至家族面向未来的文化载体,有性有人生。但在小说中,花被窝却深深地烙上了一个思夫女子的忧怨之情,而且成为儿媳被婆婆捉赃的罪证。于是,它从美好的吉祥物,一下沦为不幸与不良的证物。这就是特定的转型时期赋予花被窝的含义:守家的本分。而这里所谓的本分,实质上便是对女人的性禁锢。
与花被窝一样,井也是乡土人生的吉祥物,是延续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口井,就是一个传统。井就是一个村落乃至乡土社会的延伸,没有井就没有生命,所以,井其实也是一种性意象,只是这种意象并不面向个人,而是面向家族与村落,为整体的生命提供力量之源。陈仁为自己家打了一口井,后来因其被儿子儿媳逐出家门,这口井也就成了儿子家的井。无井无性,活画出陈仁最卑贱的生活现状。陈仁寻井情节中对井的细腻入微的刻画,本意上就是表达陈仁对性的向往,因而陈仁投井不仅被视为终结井的生命的恶劣事件,也被当作加害井主人生命传承的巫术行为。[4]井的性载体意象由此得到阐明。在转型时期,井被当作守护乡土的最后底线。这不是城市文明可轻易破坏的乡土情怀。随着自来水工程的推进,水源重新获得可靠的保障,井终将会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我们决不能说,这种新水源的兴起,就是彻底摧毁井意象的现代武器,因为乡土还有井的空间,井的历史。惟其如此,小说中的井最后被定格为生命的基点,井即人生。
如果说花被窝是关乎生命形成的意象,井是滋养生命、牵系情怀的意象,那么,酒则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意象。以酒醒神,以酒清毒,生命中的无数挫折与悲痛,都将因酒的刚烈而超越重生。小说虽未直接写酒的美味清冽,却处处洋溢着酒的清香,昏暗迷离的傍晚天色,有如酒的晕眩,朦胧浑浊的酒后神态,活脱脱地注入生命之中。因为酒疯子这个硬朗健谈的人物,酒的意象充满生机。酒注入其生命之中,成为其生命的内核。性的意蕴从酒散发出来的狂放无羁中不断升华,自然之性战胜了文明规训,个体张扬的力量得以释放。那些日常压抑的痛苦与无奈,因为酒而缓解,因为酒而消除。酒也是生命的麻醉剂。它让一部分现实的沉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使其在人们的感知中不复存在。这正是性麻木的酒疯子甘心听从妻子使唤的秘密之所在。酒意象贯串整部小说:沽酒,说酒,借酒论世,醉酒,醒酒。作品的内在线索,由于酒意象的存在而跌荡起伏。作为乡土意象的酒,又与作为现代意象的摩托车深深地契合为一体。两种意象不断冲突着,又交错地缠绕在一起。它们既是乡土守望与现代扩张之际不可避免的冲突,也是酒疯子的个人意趣与其妻的伦理欲望的无言辉映,还是村落生活与村长权力的参差交错。酒疯子狂飚着摩托车去“我”的小卖部。在“我”的印象中,摩托车是村长的专车。当此之际,酒疯子与村长因摩托车而角色重叠。因此,摩托车上急驰而来的酒疯子一点也不醉。他不是酒疯子,因为他还没有喝酒。他与正常人没有差异,甚至与村长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与这辆代表权力的摩托车有关。可是,酒疯子毕竟是酒疯子,他叫喊着要酒,不停地吆喝着不同口味、不同价钱的酒,甚至忍不住清着胃爽着口就喝,而且过分到“我”和妻子不得不留他在“我”家喝酒。就这样,狂奔而来的没有喝酒的不是酒疯子的酒疯子,因酒而忽然转变成真正的酒味十足的酒疯子。男人的性情从酒气中飘荡而出。野蛮流气狂傲,浑身散发着汗臭与酒香的性味浓烈的酒疯子,彰现的正是乡土男人的本色,但这种本色,是染了现代权力毒性的本色。在摩托车停靠下来的一瞬间,酒疯子其实已将另外两人带到了现场:他的妻子和车的主人村长。这种现代权力的毒性,从摩托车的汽油味中散发出来,融进了“我”卖给酒疯子并被他大口大口享受的美酒之中,酒疯子因此而变得不再纯粹:一方面,酒意象彰显出酒疯子的男人品性;另一方面,酒意象又隐藏了摩托车意象,重叠着酒疯子的妻子与村长的交媾,把酒疯子远远地排挤在性权力之外,让酒疯子成为一种玩偶与道具。这便是小说中酒疯子“真疯”的本义所在。
在乡土日常生活中,性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原欲的力量从性而来。油菜坡世界的人们,建构起了自己关于性的规范。这一规范,充满了温情与关怀,既没有道学家用来粉饰自我颠倒黑白的肮脏交易,更没有权力场上用以制造仇怨和满足贪欲的性控制。花被窝正是如此。或许它多少沾了点城市的俗气,但这点俗气却被真挚的乡土情怀所稀释,最终闪耀出的仍然是边城野地那活力四射的性的光芒。秀水的日子非常宁静,宁静得令人心痛。她没有丈夫的关爱,没有亲情的呵护,只有来自亲人的性的监控。花被窝以自身的本色抗争,来嘲笑拒绝远离这种反乡土的性监控。在这个意义上,花被窝其实是一种有关性的隐喻。它穿透了乡土社会里夫君打工外出的少妇们的冰冷的现实生活,以温和美好的“花”,解构着扭曲的性的监控。当花被窝上绽放出一朵湿润而新鲜的“花”样图案时,秀水的生活得到了滋润,乡土的自然力量被重新释放出来。古井的清冽甘泉,记忆着乡土的传统。子孙繁衍的信仰,在这个乡土村落中一口一口神圣的水井里延续着。大批的青年男女为了城市梦想而远去,原本的乡土成了老人的乡土,而没有传承的乡土必然会灾祸迭生,这正是致使陈仁女儿沦陷的现代语境。一个油菜花似的清新女儿,最终被城市诱惑而不幸死亡。这与其说是陈仁女儿的灾难,倒不如说是乡土的灾难,是城市人强加给乡土人的横征暴敛式的灾难。小说以性的书写来直面死亡,隐喻着对城市文明的反讽,以及对古井信仰沦陷的深深忧虑。酒是与花被窝、古井同在的乡土意象,是灵动快乐的充满激荡人心力量的意象。城市的权力意志腐蚀了酒,更腐蚀了酒疯子那可怕的虎妻,酒因而具有了双重的性的隐喻,既是乡土阳刚男人性征的表征,也是城市权力阉割男人的女人性征的表征。两种性征,与酒疯子疯狂飚车的无奈憋屈,以及酒疯子烂醉如泥的借酒泄愤纠缠在一起,最终达到了藉此真实穿透现实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吴晓明.回到社会现实本身[J].学术月刊,2007(5).
[2]郑震.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1).
[3]向柏松.吉祥物与自然崇拜[J].民间文学论坛,1998(4).
[4]萧放.楚地节日巫术形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015-QN-282)
作者简介:高艳芳(1983-),女,河南安阳人,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5-00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