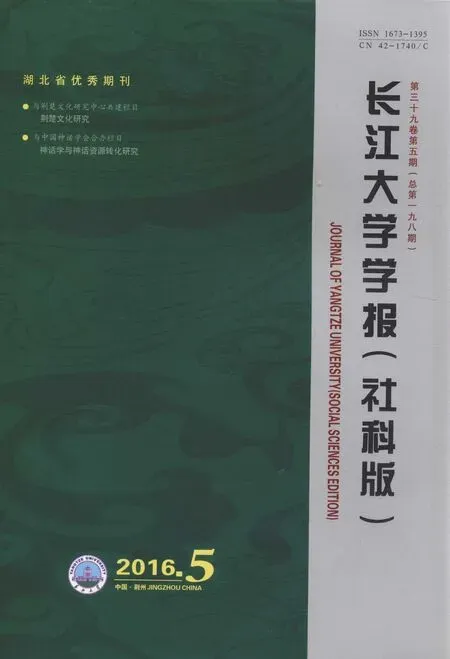探寻本土神话研究的路径
2016-03-25李子贤
李子贤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编者按:
探寻本土神话研究的路径
李子贤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在云南这个“神话王国”中,不仅有着神话存在形态的多样性,神话传承机制的历时性、完整性等特质,还以活形态神话为其主体。因此,如何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实际出发,深化对活形态神话相关论题的探讨,考察活形态神话与文化语境乃至更大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寻觅本土神话研究的最佳观察视阈,建构一个活形态神话研究的分析框架,便是云南本土神话研究的一种路向。
关键词:活形态神话;文化语境;观察视阈;分析框架
一
中国神话研究已走过了110年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对西方神话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中国汉文献经典中神话资料的梳理、考据,经历了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与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几代神话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神话研究在神话学理论研究、汉文献神话研究,以及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等领域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出现了茅盾、顾颉刚、丁山、闻一多、袁珂、肖兵、王孝廉、叶舒宪、马昌仪、杨利慧等一批神话学者。
由于神话所独具的特质,自欧洲近代神话学诞生以来,神话学就成为了一门“显学”。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专业背景,对神话进行苦苦探寻,试图解开神话之谜。然而,近两百年来,不论出现了多少学派,不论出现了多少神话学研究巨匠,似乎都只打开了神话这个迷宫的一扇扇窗口,离解开神话之谜似乎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纵然如此,神话研究者却不断出现,并对此道乐此不疲。这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也算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若要探寻人类的心灵史,探寻人类早期的思维模式,探寻文学的发端,探寻宗教的起源,探寻历史学的先声,探寻人类文化史的初始形态,都离不开神话的辅佐。其二,各种神话素的萌发与整合,神话文本叙事内容之奇特的组合方式及内在“逻辑”,直到当下仍然没有被人们清晰明了地完整解读。其三,为何在数千年前就被笔录下来的神话至今仍然有其独具的魅力?为何许多神话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得以存活?神话是人类所创造的,为何它一旦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实在”或精神实体之后,就一直与人类相伴随并以某种潜隐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四,在当下的所谓高科技社会或现代社会中,似乎早已隐退了的神话为何仍在发挥着它的某种功能,成为了维系并影响人类心灵的某种力量?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说:“当今社会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对心灵的内涵并不熟悉。反而只对每天、每小时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古老神话传递出的信息,既与几千年来支撑人类生活、构建人类历史、提供宗教内容的主题有关,也和人类内心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人类内在历程的枢纽相关联”,“神话使我们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神话是帮助我们发现内在自我的线索”,“神话是找出人类精神潜能的线索”。[1](P13~17)这些论述是耐人寻味的。总而言之,神话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是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所创造出的奇葩。神话不仅体现出了人类心灵巨大的创造力,是人类无限潜能的标识,神话还一直在伴随着人类同行,并预示着人类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神话必将是一门永远不会终结的学科。
当下,中国的神话研究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处于某种相对沉寂的状态,但实际上却在酝酿着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突破。这是因为,对中国汉文献神话的梳理和研究早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文献神话以及一直在民间传承的神话资料的收集、整理,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早已开启的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并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对于引进、吸收当下国外神话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早已摆脱了曾经的“描红”心态,开始警觉在这一研究领域由于缺乏学术自信而忽略了自主创新的理念,已逐步将学术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深耕本土文化,具备一定的国际学术视野,从中国立场、中国神话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逐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理论这一路向上来。
从国内外神话学史中可以看到,在神话学研究领域要取得新的突破、新的成果,必须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地超越与创新,这是一个首先要具备的学术理念。第二,在神话研究领域,应当以神话的本真状态、原生形态是什么,神话的本质是什么,神话何以在民间一直得以传承的动因是什么,怎样认识族群对神话的态度及演变,如何描述和把握神话的力量,神话如何与人们的心理需求结合在一起,以及民族神话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等论题为主轴展开探讨。第三,新的研究对象、新的资料的发现,必然会引发人们对神话本质及特征的再认识、再探讨。第四,新的学科理论的介入,必然拓宽神话研究的视野,例如历史上文化人类学与神话的邂逅。第五,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完善,也是神话研究取得突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丰富而独具特色的神话。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是中国神话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神话研究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与研究。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及凌纯声、芮逸夫、闻一多、楚图南、陶云逵、马学良、光未然等老一辈学者在少数民族神话发掘与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然而,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得以展开的。究其原因,其一,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系统调查,始于1958年大规模的采风。之后,云南大学等很多高校陆续组织师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出了许多少数民族神话。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相关学术机构,为编撰“五套集成”中的“民间故事集成”,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其中包括神话,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深入普查,基本上探明了各个少数民族的神话蕴藏情况,各个民族的神话大多得以收集、整理出版,这就为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二,开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与研究,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对相关论题所进行的分散式的零星研究,少有对神话本体论相关论题的探讨。其三,存活于民间的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一直是神话诸种存在形态的主体,与用文字书写的文献神话,既有很多共同点,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中最突出的是,书面文本神话与存活于民间的活形态神话,其存在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如何把握这二者各自的特质,并从这一特质的实际出发,探寻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路径,也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可能展开。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寻研究本土神话的路径就成为了摆在少数民族神话,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神话,与文献神话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换言之,从神话的存在形态来审视,少数民族神话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呢?笔者又是如何迈出探寻本土神话研究路径的脚步的呢?
这不得不从笔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讲起。1962年3~6月,笔者的首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是到宁蒗县的彝族地区以及永宁摩梭人地区搜集民间文学及相关民俗。1963年9~12月,笔者又徒步穿越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到独龙江畔,进行独龙族口承文学及相关民俗的田野调查。通过这两次田野调查,笔者首次接触到了存活于上述各民族民俗生活之中的活形态神话,并收集到了独龙族的创世史诗《创世纪》。当时笔者头脑中一个鲜明的感受是,它们都是存活于集体记忆之中,存活于民俗生活以及相关祭仪之中的神话,而不像笔者在大学的专业课堂上听到老师讲授的,或者从《山海经》、《楚辞》等文献中看到的早已用文字写定了的书面文本神话。这也让笔者联想起孩提时代在建水曾经历过的一幕:当出现月食的时候,整条街、整条巷的人都会拿起能够敲响的器皿敲打起来,大声喊叫:“天狗吃月亮喽!赶紧把天狗吓开,救月亮喽!”这,就是活形态神话。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多次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既有早已笔录进彝文经典、傣文经典、东巴文经典中的书面文本神话,但更多、更具普遍性的是存活于民俗生活之中,并仍在发挥着某种功能的活形态神话。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其主体是活形态神话。换言之,神话存在形态之一的活形态神话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一大特色。这些活形态神话大多与相关的民间信仰与祭仪相连属,从属于该民族文化这一大系统,是长期存活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神话。笔者于1987年发表于《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上的《活形态神话刍议》,以及1987年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发表的讲演《论佤族神话——兼论活形态神话的特征》等两篇论文,便是在这一阶段对活形态神话所作的初步的学术概括与阐释。此后,笔者便将神话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活形态神话上来,并试图探寻活形态神话研究的路径。
在神话学史上最早提出活形态神话这一概念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参加了去美拉尼西亚等地的蒙特人类学远途考察队,从此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所做的整整四年调查,是他后来学术成果的主要源泉。其功能主义理论最初在1922年发表的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中提出。后来在许多其他著作和论文中又进一步发挥,最后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要满足基本生物需要,而要满足这一基本生物需要,又必须有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来保证,而有了社会组织的人们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即精神方面的需要。因此,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器具都有满足上述三种需要中某一种需要的功能,因而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种功能。[2](P46)对于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上述学术见解,学界早已有所评价,笔者不再赘言。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活形态神话的相关论述主要见于《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该书关于“活的神话”、“活着的神话”的论述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根据我在野蛮人之间对于活的神话之研究,原始人很少对于自然界有纯粹艺术的或理论科学的关心;野蛮人底思想与故事之中,很少象征主义的余地;神话,实际说起来,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不是空中楼阁没有目的的倾吐,而是若干且极其重要的文化势力。神话底自然派的解释,不但忽略了神话底文化功能,而且凭空给原始人加上许多想象的趣意,并将几种清楚可以分别的故事型类弄得混合,分不清甚么是童话,甚么是传说,甚么是英雄记,甚么是神圣的故事——即神话。
神话这个部落里面神圣的民俗信仰,我们以后就要明白,乃是帮助原始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帮助他能使对于文化的结合出入相抵。我们更要明白,神话给原始文化的最大帮助乃是与宗教仪式、道德影响、社会原则等协同进行的。宗教与道德取资于科学趣意或历史的既是很少,所以神话所依据的乃完全是另一套心理态度。
存在野蛮社会里的神话,以原始的活的形式而出现的神话,不只是说一说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那不是我们在近代小说中所见到的虚构,乃是认为在荒古的时候发生过的实事,而在那以后便继续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的。野蛮人看神话,就等于忠实的基督徒看创世纪,看失乐园,看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给人赎罪等等新旧约的故事那样。我们底神圣故事是活在我们底典礼,我们底道德里面,而且制裁我们底行为,支配我们底信仰,野蛮人底神话也对于野蛮人是这样。
神话底研究只限在章句上面,是很不利于神话底了解的。我们在西方的古籍,东方的经典以及旁的类似去处得到的神话形式,已经脱离了生活信仰底连带关系,无法再听到信徒们底意见,无法认识与它们同时的社会组织,道德行为,一般风俗——最少,也无法得到近代实地工作者容易得到的丰富材料。况且说,传到现在的文字记载,无疑地已经大与原样的故事不同,因为经过传抄、疏证,以及博学的祭司与神学家等等之手而不同了。打算要在神话底研究中知道原始生活底奥秘,必得转到原始的神话,尚在活着的神话;而且这样作,要在祭司的聪明将它用木乃伊的办法装殓起来,保存在损坏不了但是没有生命的死宗教底圣龛里以前。
我们就要见到,研究活着的神话,神话并不是象征的,而是题材底直接表现;不是要满足科学的趣意而有的解说,乃是要满足深切的宗教欲望,道德的要求,社会的服从与表白,以及甚么实用的条件而用的关于荒古的实体的复活的叙述。神话在原始文化中有不可缺少的功用,那就是将信仰表现出来,提高了而加以制定;给道德以保障而加以执行:证明仪式底功效而有实用的规律以指导人群,所以神话乃是人类文明中一项重要的成分;不是闲话,而是吃苦的积极力量;不是理智的解说或艺术的想象,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上实用的特许证书。[3](P82~86)
马林诺夫斯基对神话学的突出贡献,概括起来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早发现并指出在原始民族中存在着“活着的神话”。第二,这种存在于原始民族中的“活着的神话”,与被反复修改而与其原始面貌相去甚远的文献神话或书面文本神话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保持着与生活的联系,而后者却早已被割断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第三,这种“活着的神话”是与人们的信仰体系、祭仪系统、文化心理等诸多文化要素融为一体的神话,因而是活在人们的民俗生活、心灵世界中的神话。第四,对神话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神话叙事文本的章句文字之上,而要关注这种“活着的神话”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对其进行整体研究。第五,神话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文化力量,发挥着其特殊的功能。第六,主张神话研究者要关注并且研究“活着的神话”,反对在书斋中坐在安乐椅上只关注文献神话或书面文本神话。笔者认为,即便从当下神话学研究的视点来审视,这些论述仍然是精辟而具启迪性的。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活着的神话”的相关论述,肯定存在着某些局限或不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其一,活形态神话曾产生并一直存续于原始民族之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后来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直到当下,活形态神话在某些地区、某些民族中仍在存续。中国的云南及周边地区、日本的冲绳诸岛、韩国的济州岛等地区,虽然已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时至今日仍有活形态神话存续,就是明证。可见,活形态神话并不仅仅存活于原始民族之中。其二,从神话的存在形态来审视,神话具有多种存在形态。笔者认为,神话至少具有以下四种存在形态:文献神话或书面文本神话;口头神话,即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活形态神话;以某种实物或虚拟物为象征符号的神话。活形态神话是神话的存在形态之一。当然,它是神话最初始、最自然,因而也是最典型、最本真的存在形态。其三,活形态神话与书面文本神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深入探讨二者之间不同的结构系统,寻觅出由此而产生的二者的文化内涵之差异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论题。其四,文献神话尤其是古文献神话,是弥足珍贵的一种神话资料,也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在其产生或在特定民俗生活中传承时的诸多文化信息,是我们在研究活形态神话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系。在某种情况下,将活形态神话与文献神话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审视,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环节。其五,粘合着许多文化要素的活形态神话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活体”,它必须存活于某种特定的“母体”之中。深入研究“活体”与“母体”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二者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保持某种调适、平衡状态,也是活形态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其六,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总是在发生着渐进式的或突变式的文化变迁或文化转型。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如何调适自己以适应这种变化,作为“活体”的某一特定的活形态神话,也会发生着某种嬗变,以调适其与文化语境的关系,这些也是活形态神话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论题。其七,活形态神话结构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动态性。神话叙事文本内容的稳态性是相对的,结构系统的动态性带来的变异性则是绝对的,除非它已被用文字将其叙事文本内容笔录了下来。这样看来,活形态神话结构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及内在规律,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审视和探讨的一个论题。其八,活形态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都从属于某一个民族之民族文化这一大系统,乃至于由更大的地域范围、许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某种特定的文化圈这一大系统。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审视活形态神话时必须加以关注的论题。当然,某种特定的经济文化类型亦与活形态神话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例如,采集—狩猎文化、畜牧文化、水田稻作文化、梯田稻作文化、山地旱作文化等,它们与活形态神话的内在联系也应受到关注。其九,神话的传承主要或重要的是活形态神话的传承。某一神话一旦用文字写定而成为了书面文本神话之后,也有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文献、版本中传承下来的问题。但一般而言,它远不像活形态神话在民俗生活中的传承那样,必须具备某些文化要素,诸如传承场、传承人,以及人们对神话的态度与需求度等因素的介入和参与,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需要加以认真探讨。以上,便是笔者对活形态神话相关论题的粗略思考。
二
活形态神话无疑是与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祭仪系统、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融为一体,存活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仍在发挥着某种功能的神话,因而必有其特定的载体。神话传承的主体是整个族群的成员,虽然有祭司、老者、民间艺人等为其主导,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活形态神话与信仰体系、祭仪系统、神话传承的参与者等文化要素的关系却有着某种程度或表现形态上的差异。笔者试以云南为例,将神话传承载体之变化情况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来加以考察: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文明社会的初期、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当下的现代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生活在独龙江畔以及怒江大峡谷的独龙族、怒族,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或其解体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盛行着原始信仰与万物有灵观念。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祭仪系统还不够完备,一些重大的、相对复杂的祭祀活动尚未出现或较为罕见,因此,活形态神话更多的是存续于族群成员的集体记忆、对神祇的敬畏与崇拜心理及一些较为简单的仪式之中。独龙族除了一年一度的“卡雀哇”(年节)有剽牛祭天、巫师吟诵《创世纪》或相关神话,整个家族或氏族成员参加这一相对大型的祭仪之外,平时只有极为简单的祭山神、祭猎神和驱鬼仪式。怒族虽然盛行图腾信仰,传承着许多图腾神话,但是人们除了对其氏族图腾保持着敬畏、崇拜心理之外,平时少有对图腾的专门祭祀,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对祖先及其信奉的图腾举行简单的祭祀活动。
文明社会的初期。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物质财富相对有所增加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祭仪系统迅速完备起来,对神祇的祭祀成了人们宗教民俗生活中的第一要务。于是,与民间信仰、相关神话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大型的祭祀活动便逐步形成,并频繁地举行。其中以四川及云南大、小凉山的彝族,西盟佤族的活形态神话最具代表性。在大凉山彝族地区,每年都会举行一些大型的、祭场布置极为复杂、祭仪程式颇为繁复、必须有祭司及其助手主持、全体族群成员参与的祭祀活动。祭祀过程中要献奉牛羊等牲畜,并且需延续数日才能完成相关仪程。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神话是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祭场既是文化积淀场、传承场,也是神话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历史上,西盟佤族猎头习俗中的拉木鼓、人头祭是一项重大的祭祀活动,活动必须由祭司主持,要有全体族群成员参与,祭祀过程中也要献奉牛猪等牲畜,并且也需延续数日才能完成相关仪程。参与祭祀活动的族群成员心中都知道举行仪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要举行这种仪式。因为神话中讲到是祖先用人头供奉了木鼓,天地才分开;是祖先用人头供奉了木鼓,才没有发洪水;是祖先用人头供奉了木鼓,撒下的谷种才长出了粮食。人们延续拉木鼓、祭木鼓的习俗,是为了让天神和谷神庇佑粮食丰收,人畜平安。此时,祭司作为神话传承的主导者,祭场作为神话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开始突显。
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犹盛,信仰系统犹存。在祭仪系统中,一些与原始信仰相关联的祭仪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导致某些古老的神祇及其神迹与祭祀活动渐进分离,而一些与当下民间信仰中相关联的神祇及其神迹便在祭祀活动中突显出来。人们对神话的态度虽与前述两个历史时期相比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但族群成员中的大多数依然笃信神话所述的一切,仍然对神话有着较强的依赖感、需求度。族群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神话传承的主体,但祭司、民间艺人作为神话传承的主导者之地位越发明显。古代传承下来的某些神话逐步成为了只是“讲一讲”的故事,然而尚有许多神话仍依托于民间信仰及祭祀活动而得以存活。虽然有的民族已产生了书面文本神话(如彝族、纳西族、傣族等),但活形态神话在神话诸种存在形态中的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神话的总体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点,值得关注。各个民族之神话的总体格局愈来愈各具特点,神话的民族特色愈加鲜明。在傣族中,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一些印度神话及佛教神话逐步在傣族中传播开来,甚至在傣族的神话系统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例如,佛祖释迦牟尼的神话尤其是佛迹神话,都以活形态神话的方式得以呈现。当然,一些古老的神话如寨神神话、勐神神话,以及谷神神话等仍然在民间传承,并与某种祭仪相连属。在白族中,一些古老的图腾神话在白族聚居的中心区多已失传,而只传承于白族聚居区的某些边沿地带。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黑天神神话、观音神话等迅速在白族地区传播开来,并呈现出活形态神话的样态。遍布于白族聚居区各地的本主信仰,其中有许多本主都有叙述其神迹的神话,并以活形态神话的传承方式在民间传承。在纳西族中,以《创世纪》(《崇搬图》)为依托的祭天仪式,其实是以道场设置、祭仪程式在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相关神话内容,可谓典型的“活着的神话”。值得注意的是,纳西族的祭天仪式除了就祭之外,还有望祭。望祭就是在各自的家中设置较为简单的祭坛,举行祭祀。悠远古朴的祭天仪式,一直得以传承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较为罕见的文化事象。一年一度在三朵神庙中定期举行的祭三朵神仪式,也在告诫人们应牢记三朵神的神威,祈求吉祥平安。在红河州的许多彝族地区,也有活形态神话的传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祭竜神(村寨守护神)仪式,叙述竜神神迹的神话便成了人们为何要祭竜神的神圣性依据。
当下的现代社会。就云南而言,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当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化之风几乎吹遍了每一个少数民族村寨,许多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地区已逐渐迈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那么,活形态神话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继续得以存活吗?毋庸讳言,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体系正在逐步退出社会、文化生活,某些祭仪逐渐淡化及萎缩,一些传统文化的积淀场、传承场已开始逐步萎缩乃至消失。重要的是,人们对神话的需求度越来越低,参与神话传承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活形态神话已经消失了。在当下的日本冲绳诸岛,活形态神话仍在当地的宗教民俗生活中存续;在当下的韩国济州岛,与某些祭仪相连属的活形态神话也仍在存续。云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已有100年工业化历程的开远市的碑格乡的仆拉人中,仍有祭司存在,仍有许多由祭司主持的祭祀活动存在,当然也就有活形态神话继续传承。在开远市的小龙潭镇的老勒村,与人祖庙,即供奉洪水后再造人类的两兄妹的神庙并存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依然依托于人祖庙继续在民间传承。人祖庙与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相互依存,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只要民间信仰还得以存续,只要某些祭祀活动还得以存续,只要在当地族群的一部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神话仍占有一席之地,只要活形态神话的传承场或载体还未丢失,那么,活形态神话还会得以存续,就是毫无疑问的了。
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来看,上述分期并不一定就具有普遍性。然而,对于探究云南的本土神话而言,力图对活形态神话的传承载体作适当的历史分期进行粗略的梳理,探寻其演化轨迹,则是十分必要的。
活形态神话是存活于宗教民俗生活中的神话,是神话最本真、最自然的存在样态,有着许多与书面文本神话不同的特点。因此,活形态神话的研究除了掌握一般的神话研究的理论、方法之外,还需要紧紧抓住以下三个重要环节。首先,要进行持续深入的田野调查。由于活形态神话的研究对象及其所从属的文化生态系统孕育在民间,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民俗文化事象存续在民间,所以,田野调查是活形态神话研究者必备的基本功,是活形态神话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学问在民间,功夫在田野:在田野调查中挖掘新的资料,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的问题,在田野调查中引发学术联想,在田野调查中反复求证答案。这似乎是一条普遍规律。活形态神话所具有的特质,也对田野调查提出了许多特别的要求。例如,“活体”(神话的叙事文本与讲述的场域)与“母体”(文化生态系统)如何互补与互动?从神话叙事文本,到吟诵或讲述神话的场域,再到传承着该神话的族群之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祭仪系统、文化心理结构等,又如何物态化之后而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反之,也要考察某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如何支撑着神话传承的载体,即在特定的吟诵或讲述场域中,又传承着什么样的神话,都需要在田野调查中逐步明晰并让其突显出内在的关系网络,以便逐步弄清“活体”与“母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达此目的,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点:首先,要具备多学科的学术视野,以提升自己捕捉相关信息和资料的能力,提升自己透过某些表层的民俗事象进行深度开掘的洞察力与穿透力,提升自己对某一活形态神话所粘合着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整体把握的能力;要将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与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从而得出某种较为准确的学术判断;要时刻把持并调适调查者之主位(内省)与客位(外察)的关系;要随时注意田野调查的客观性与准确度。诚然,对活形态神话的田野调查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进行发现、跟踪、回访等持续调查,保持对研究对象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努力成为一个熟悉那个异文化社会,熟悉该族群活形态神话的异乡人;对于活形态神话研究者而言,要保持一种对田野调查的魅力驱动,真正做到在田野调查中自得其乐、乐此不疲。其次,对活形态神话要进行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笔者早在1991年出版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后记中就提出了这一研究思路:神话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对神话必须进行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早已这样做了”[4](P326)。最后,要特别关注并深入进行对活形态神话的存续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即“活体”与“母体”的内在联系之深入探究。由于笔者已有相关论著对此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在此,笔者仅仅是试图提供一个活形态神话研究的观察视阈,建构一个活形态神话研究的分析框架。如果说我国学界对活形态神话的发掘与研究开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真正展开对活形态神话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话,那么,我国的活形态神话研究还正在路上,远远没有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系统的研究理论及方法,还有许多新的论题有待探索,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坎贝尔,比尔·莫耶斯.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M].朱侃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覃光广,冯利,陈朴.文化学辞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3](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4]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
Exploring the Path of the Local Mythology Research
Li Zixia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
Key words:living form myth;cultural context;observe the perspective;analytical framework
Abstract:In the “Kingdom of myth” in Yunnan,there exist not only the diversity of the myth form,but also the diachronic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and also the main body of the myth.Therefore,how to proceed from the actual myths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Yunnan,deepen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ed topics of the living form myth,investigat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ing form myth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even greater cultural system,looking for the best observation of the local mythology research,constructing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myth of the living form is a dire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local mythology in Yunnan.
收稿日期:2016-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ZW035)
作者简介:李子贤(1938-),男,云南建水人,教授,主要从事神话学研究。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5-0001-07
中国神话学的百年学术史,从多个视角切入,可以发现丰富多样的方法论模型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进入21世纪,神话学研究的多样性与转型特征十分显著。基于此,本刊与中国神话学会商议,自2015年1月起,计划用两年的时间,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当代中国神话学的20位代表学者,每期刊发两篇论文:一篇是代表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篇是对代表学者神话学研究的综述与批评。期望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来构拟中国神话学的当代形态,思考中国神话学的当代问题与未来走向,建立起古典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本土文化逻辑,进而为中国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贡献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与智慧。本期特推出李子贤先生《探寻本土神话研究的路径》及高健博士《神话王国的探寻者——李子贤神话研究评述》,敬请学界关注并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