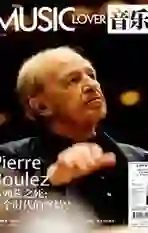高平:音乐厅不是我唯一的舞台
2016-03-22紫茵
曾经感慨遗憾,今生错过贝多芬、李斯特、肖邦等古典、浪漫音乐时代,现在,有几个钢琴家兼及专业作曲?有几个作曲家即兴登台演奏?
2015年12月19日,我在深冬寒意中走进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钢琴的独白与对话——高平钢琴、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带给听众无以言表的幸福与温暖。上半场,《窗外》《夜巷》《谷应》《匿吻》四部;下半场《旋律遗弃》《残余的探戈》《舞狂——向皮亚佐拉致敬》三部。这是我第一次听中国的钢琴家现场演释自己的原创作品。高平不止让你听他弹的钢琴,听他写的音乐,同时,还听他歌唱中的“戏剧”。
早就听说,音乐厅不是高平唯一的舞台。一年到头,他相守钢琴的创作,永远藏在公众视线之外;他相伴钢琴的表演,相当比例都放在音乐厅之外。在都市名流聚集的文化沙龙,那些远离繁华喧嚣、相对安谧雅静、有情调有味道的地方,高平和诗人、画家互为知音,和谐共处,琴·形·影和音·诗·画,互动交感,相映成趣。李西安教授认为,高平是第六代作曲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样精准的定位,将人们概念中的钢琴家划归到了专业作曲家行列。
● - 紫茵 ○ - 高平
● 高平你好,请原谅,最近我才真正开始关注你。在四川音乐学院宿舍大院,你的父母——高为杰老师和罗良琏老师,看着我长大成人。而我又看着你,从一个圆头圆脑、浓眉大眼的可爱男孩,忽的一下,长成英俊潇洒、儒雅健朗的阳光青年。
我和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可能还在于你,怎样完成一个钢琴家到作曲家的所谓“华丽的转身”?毫无疑问,作曲,肯定受父亲影响更多吧?声乐,你的母亲,优秀的歌唱家、教育家,她给你正式上过课吗?
○ 谢谢!你认识我父母比我还早啊(笑),应该比别人更了解我和我们家。我经常在说,如果没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肯定就没有高平的今天、今天的高平。
相比我父亲母亲那一辈人,我们真的很幸运。我父亲是非常偶然地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一下子就痴迷进去了,自己立志要当作曲家。我生于1970年,可以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听着琴声、歌声。好像川音的娃娃不学音乐都没对头,所以我五六岁就开始学钢琴。我妈妈没想过要教我学声乐,她非常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钢琴家。
最初,我母亲所在声乐系的刘振汉教授的大儿子三羊(刘毅昭)教我。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教过好多像我这样淘气的小娃娃。其中,刘忆凡后来考上川音,在1980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谐谑曲演奏奖”,他是“文革”后我国第一个重大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
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是林瑞芝教授。她的先生俞抒教授和我父亲同在作曲系,既是师生同事,又是朋友搭档。他们与朱泽民教授1981年合作的《蜀宫夜宴》,在1983年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暨首次民族器乐作品评奖中名列榜首。
七岁左右,我开始跟杨汉果教授正式学钢琴,从此不再磨皮擦痒耍耍哒哒,好像一下开了窍,越来越喜欢、迷恋钢琴。
重要的是,我发现可以用钢琴来说我想说的话,音乐比文字更能表达我的心情和想法。可能我音乐的记忆能力和模仿能力,要比一般孩子强一些?十岁左右,在川音琴房听作曲系学生何训田、宋名筑弹作业,我就想把谱子记下来,用钢琴弹出来。那时我的钢琴弹奏技术不是最好的,但即兴演奏能力特别强,经常在钢琴上弹些随心所欲的东西。十一二岁时,我已试着把自己在钢琴上即兴弹奏的、想要表达的音乐,清楚而准确地记在谱纸上,自得其乐。
我想,父亲很早就发现了我这方面的苗头。可能他在心里早就想象过、期许过,我将来会成为一名作曲家。我从弹钢琴到搞作曲,是一个自然“进化”发展的过程。我和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学生的动机不同,没有从附中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作曲,从四大件一步一步训练。我是从听音乐开始,音乐熏陶,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 现在你有五六十部作品,比有些专业作曲家都多。你还能想起来,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样的嘛?
○ 毫无印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出差到贵州,在他的学生胡晓那儿,第一次看到了我的“作品”:一首小前奏曲,是我送给胡晓本科毕业的一份礼物。那时我可能觉得自己会作曲,即兴弹奏的音乐,写了相当复杂的和声,父亲说用得很不错。

真正有印象的第一首作品是一首钢琴木管三重奏,早期大多是写小品类的东西。在川音附中钢琴专业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继续主修钢琴。硕士毕业考博士,还是以钢琴考入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可是作曲教授特别喜欢我,觉得我很有作曲的天分,硬拽着我读了作曲博士,2003年毕业。在正式学作曲之前,我已经写过一些作品,在音乐会上又经常演奏自己的作品,别人也把我当作是作曲家。这个过程简单而自然。
● 贝多芬和舒曼、李斯特、肖邦都是集作曲和演奏于一身,格什温钢琴弹得也很棒,《蓝色狂想曲》是他自己担任首演独奏的。
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讲座上,李西安教授说“现在的音乐舞台上,只有一个高平,他能把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合为一体。特别是他可以在现场即兴作曲和演奏,这是不可替代的,是极大的优势。”你所具有的开创性的、个性化的独特优势,前后的中国钢琴家、中国作曲家,好像还没有范例。
依我说,你是钢琴家的最佳作曲、作曲家的最佳钢琴,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最佳演唱,这和中央音乐学院盛原教授的说法“英雄所见略同”。他说,高平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钢琴家里作曲最好的或者作曲家里钢琴最好的。两者兼顾,有点像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家。在某种程度上,你的音乐让他想起了肖邦和德彪西。这种钢琴语汇,使演奏者在专业技术上与生理动作上都能得到很多无法言表的快感。
○ 盛原教授确实对媒体说过类似的话,还说他弹我的作品,有时感觉好像在弹他自己的作品一样,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虽然他不会作曲,但在性格或者内心深处某个角落,和我可能有种共通之处,好像他的话都被我说出来了。
盛原认为我的音乐十分独特,能捕捉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处,甚至能捕捉到人下意识的灵魂深处,这令他非常感动。单就捕捉而言,难;用语言表达,很难;用音乐表达,更难。重要的是,打破了国籍概念、种族文化和创作观念的限制,大量吸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文化,甚至是不同学科的艺术组合体。
● 一位音乐家能够得到同行的真诚好评和高度赞赏,可不容易。
最近我在翻阅一些旧报纸查资料,偶然看到雷蕾2006年12月8日发在《音乐周报》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充满激情的音乐灵魂——旅新音乐家高平最新室内乐专辑》,标题很有“煽动性”。这应该是我在任《音乐周报》副总编辑时,经三审三校读过的文章。雷蕾从作曲专业角度的表述,很有说服力。
如今的你不可与十年前同日而语。从附中学生的“业余”作曲,到博士毕业的专业作曲,你在技术层面的更新提升不言而喻。在音乐语言系统的建构、审美的取向、文本的调整上,你感觉有什么变化?
○ 我没有条条框框,无禁忌无顾虑。我希望自己能站在超越民族和国籍一个大文化的高度,理解表现音乐。
可以说,我学习作曲都是从我的经验里来的,而不是老师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早期即兴性、试探性的作曲,我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希望自己可以摆脱西方传统作曲相对固化的法则与模式。从1998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攻读博士转向作曲专业,这种自觉能动又有了更为坚实的技术支撑。
2002年,我写了一部钢琴与大提琴的中型作品,这应该是我作曲的转折点。2003年,我参加美国波士顿“奥诺斯”国际作曲比赛,为长笛与钢琴而作的《小奏鸣曲——风与雪的对话》获得第一名。这些年委约和演出过我作品的著名中外音乐家,包括钢琴家、小提琴家、歌唱家、指挥家有数十位,还有瑞士“金字塔”六重奏团、柏林钢琴打击乐重奏团、芝加哥室内交响乐团及上海爱乐乐团、厦门交响乐团、紫禁城室内乐团等数十个中外乐团。
我的作品曾在世界各地重要国际音乐节首演,如美国阿斯本音乐节、拉维尼亚音乐节、辛辛那提MusicX现代音乐节、荷兰高德雅姆斯音乐节、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Encounter音乐节、加拿大班夫国际音乐中心、新西兰惠灵顿国际艺术节、日本Hibiki Hall音乐节、澳门国际艺术节、北京现代音乐节,等等。新西兰作曲家协会2010年给我颁发了CANZ托拉斯基金奖。
美国作曲大师弗德里克·热夫斯基曾说,“高平是为古典音乐传统带来新鲜血液的青年音乐家。一场高平的音乐会,如同一次名副其实的历险与奇遇”。

● 现在就来谈谈你的音乐会,2015年岁末这场“独白与对话”。
如实招供,你回国开了那么多音乐会,我竟阴差阳错地再三错过。自1994年在北京音乐厅听过你参加中国首届国际钢琴比赛的演奏后,二十多年,我对高平钢琴演奏尤其是高平自创作品的听觉经验等于“零”。这样也好,从“零”开始,不带任何听觉经验、偏见成见地聆听,纯粹干净真实自然。
听了这场音乐会,我被你的音乐彻底征服,绝对是心悦诚服。重新认识一个新的高平,你的音乐让人灵魂出窍,感动莫名!听完音乐会后特别想和你聊,然后,好好出一篇文章。
○ (又是略带羞涩沉稳平和的笑)谢谢!
经常有媒体引用我一句话:音乐的创造仿佛是一棵树,千万的枝叶无不发自于树的根。我的音乐也有它的根,那就是记忆,个人的以及群体的记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趣的事情似乎总是发生在窗外。面对不得不做的功课,深陷练琴的无奈时刻,我的心思更容易飞出窗外。这样的感受,好像并不因为长大而改变。窗外始终意味着幻想,意味着解放和自由。
音乐会第一首《窗外》是我2011年为北京琴童张司滢小朋友而作的四首小品,不过这首曲子好像更适合成人来演奏,一般琴童恐怕弹不了,很难。张司滢小朋友是优秀的小演奏家,前几年就比我那天弹得好。呵呵,很抱歉,我没把它写成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钢琴曲。
在《夜巷》中,我想表达一种不期而遇的如梦幻般的诗境。读陈丹青先生的《阶级与钢琴》,同他类似的感受触动我的创作灵感。我也曾在无意中听到自己耳熟能详的音乐,这通常未必会让我激动的音乐,在特定的时空情景中,突然间有了新的含义、色彩与质感,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享受。我不得不说,我的确也像陈丹青先生,偏爱这样不经意间的惊喜的倾听。该曲受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委约而作,半决赛必弹曲目。2007年10月在厦门比赛期间由十二名入围选手首演。我把此作题献给敬爱的恩师周广仁先生。
● 我也喜欢读陈丹青的书,偶尔翻翻还记得那段文字:在北京、上海、南京,我几度有幸与巴赫或肖邦的钢琴幽灵在浓黑楼道中相遇。……奇怪,在纽约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正襟危坐聆听名家演奏,也不如在这陌生楼道的家常阵地驻足偷听,魂灵出窍,感动莫名,哪怕偷听的只是小童的初习。这种感觉深深触动我心灵的共鸣,只是我从未将其化为文字或音乐。
徐志摩的《月夜听琴》有类似感应:“是谁家的歌声,和悲缓的琴音,星茫下,松影间,有我独步静听……”还喜欢林徽因的《深夜听到乐声》:“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梦想永远比现实美好,所以我非常喜欢你的《夜巷》,音乐清幽散淡,却又跳脱林氏诗文的凄切哀怨。
○ 我喜欢山,经常跑到山里去游玩。那有很多在城市听不到的各种各样有趣的声音,人在山里能体会到种种的神秘与空灵。
《谷应》灵感就来自这种体验,它是我近年写作“山系列”中的一件。音乐中沉浮不定的旋律,如山中飘荡的浮云、缭绕的雾气,又像万物之声在山谷之间的回响。第一乐章由新西兰Promeathean出版社委约,2010年被收入该社出版的四手联弹作品集。
《匿吻》是一部多乐章组曲,这是类似音乐日记的作品,用它记录一些当时的感受,有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向情感,另一些则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客观因素发生作用时的心理状态。它就像一部将会长期处于“未完成”状态、可能还会不断后续新乐章的作品。钢琴家不仅要弹而且要唱,有时还要捶打喊叫,音乐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这类作品有时被称为“钢琴剧场”。第一乐章“匿吻”,焦虑的小夜曲,私密、不安;第二乐章“煤灰”如同来自深井煤矿下不见天日的黑色的声音,充满阴郁而愤怒;第三乐章“萧萧”像一支山歌,朴质,有点无奈。歌词来自沈从文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这段文辞可能不是他的原创,应该是他听过的乡谣?原曲什么样我没概念,只按自己的想法谱成曲子;最后乐章“一天一个世界”,带有滑稽戏谑、荒诞诡异、莫名其妙的感觉,形形色色嬉笑怒骂般的音乐以炫目的速度飞逝而过,而曲终却是一段伤感的小调,寂寞冷清,长吁短叹,渐渐消失在黑夜里。

● 在音乐中你的文字导引一一呈现,而且留有自由空间,令人浮想联翩。盛原作为你的嘉宾,两个大男人挤在一张琴凳上,四只大手这样舞过来舞过去的,《谷应》由此变得非常有意思,意趣横生,妙不可言。
一首《萧萧》横空出现,实在让人猝不及防,心灵震撼。我立马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那个短篇。沈从文,我青春期的男神,他的文字天然带出田园牧歌般的情调。在他的笔底,湘西少女萧萧,命运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你用“丝”的情歌比喻那个山野汉子再合适不过了,在花狗的山歌声中,一个少女变成了妇人,可见这山歌富于非凡的魅力。
深刻的印象更来自你的歌唱,非常独特。我就奇怪,一种最纯朴的吟唱,既不是美声,一点不像被你母亲调教过的美声;也不是民族或原生态,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肯定也不是通俗流行。你就是你,高平的天然有机“绿色”歌唱法。
○ 我认为,音乐是有质感的,应该是人的内心情感最真实自然的流露。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是一个消失的过程,生命消逝的过程,这是音乐最本质的东西,也是音乐最打动人的地方。音乐,其实也是音乐家对消逝生命本身的一种抗衡。演奏者在让乐谱“活起来”的过程中,无界越界或多种解读是一种必然。音乐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正是它独有的魅力。我经常说,即兴性具有音乐最原初最本真的质感,真正是转瞬即逝,一下抓不住就消失了。如果能把灵光闪现的瞬间记录下来,表现出来,那就太有价值了。
● 你的音乐中就有大量即兴性的灵光频闪的光焰华彩。这除了你的天分或直觉之外,还应该与你国际化的生活经历有关?○ 毫无疑问,如果我没有很早就走出去学习,很可能表演和创作又会是另一种形态、状态。这种跨文化的生活经历,可以让我在作曲中,自然而即时地找到自己的音乐语言,既可以与本民族语言对话,也可以与他民族语言对话,在音乐材料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认为时间和距离,可以让人更冷静、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文化。出国之前,很多东西都属于被忽视或轻视的范畴。出国之后,我重新认识、反思、自省,真正感悟到曾经忽视甚至轻视的东西非常珍贵。这些东西应该并且可以丰富或改变我的艺术行径与作为,钢琴甚至更多西洋乐器,可以说中国话也可以说外国话。
● 我非常喜欢音乐会下半场的《残余的探戈》(Lef Tango)。
○ 这首曲子说起来还有点意思。2013年1月,新年喜庆余兴未尽,我因左眼的小手术,好几天弹琴阅谱不便,这才发现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乃不易之功。无奈之余闭目“瞎摸”,竟也渐渐生成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
中文里有句成语“孤掌难鸣”,英文里有“it takes two to tango”,皆含有事与愿违、美中不足之意。左手弹琴势单力薄,应算是一种“不足”,但其局限恰恰提供了独特的可能性,或可以称其为一次“超越”的契机。困难之克服,常常能产生一种奇特的魅力。“Lef Tango”一语双关,Left既附会了左手弹琴的生理制约(Left在英语中有“左”的意思),也暗示了如同记忆碎片般的寂寥情愫。这首乐曲有很强的“情景感”甚至是“情节感”,有时我甚至想象它是一部默片的配乐。我把此曲献给远在新西兰、痴迷于Tango的一对朋友John和Collen。
有段时间,我对阿根廷作曲家阿斯图尔·皮亚佐拉的音乐非常着迷。在他的音乐里,新与旧和谐并存且生机勃勃,这是一种纯朴硬朗的作曲风格。《舞狂——向皮亚佐拉致敬》作于2000年,这是我和皮亚佐拉的“神交”对话。该作对我来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与我的中国文化背景无关。有人曾质疑,中国作曲家怎么可能写出外国作品。我认为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就不可能?荷兰钢琴家Marcel Woms曾在皮亚佐拉的故乡演出《舞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报以真诚的掌声!
● 曾听过高男高音歌唱家肖玛演释你父亲谱写的元曲小令三首,那是古典文学与现代音乐的隔空“穿越”。你的声乐套曲《旋律遗弃》却是现代诗歌与现代音乐的牵手“对话”。
如实招供,在木心《湖畔诗人》《论拥抱》《旋律遗忘》、翟永明《和雪乱成》《转世灵童》、张耳《雨滴》、宗白华《听琴》中,我更熟悉和喜欢木心和翟永明。后者为已故歌手陈琳写的挽歌,引起我的内心共鸣,只听那一句“一场华丽的雪厚葬了薄情/也厚葬了更薄的人心……”就会潸然泪下。
四位诗人七首诗作,无不个性鲜明,情思独特。你的音乐与之一一对应,这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
○ 麻烦吗?一点也不麻烦。我特别喜欢和不同的人,尤其是个性独特的人交往对话,很有意思啊。
现代诗人都很有个性,诗作的情绪基调也有明显差异,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感觉和氛围也不同,奇异而独特。《雨滴》清新雅致,《论拥抱》谐谑调侃,《听琴》感喟幽思,《转世灵童》神秘深远,《和雪乱成》孤寂哀婉……用七首诗作谱成一组艺术歌曲,声乐部分并非所谓歌曲,而是依从室内乐的写法,演唱难度相当高。肖玛完成的质量令人满意,他很棒。
● 简单归纳一下第一次听你作品音乐会的印象。
本来已提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从1994年5月听谭盾作品音乐会起,二十多年来听过的现代音乐会不计其数,我太了解现代音乐是怎么回事了。我想,既然要听比谭盾们更年轻的后现代音乐家的作品,就应该接受、必须忍受某些无缘无故、无端无序、稀奇怪异的噪杂之音,何况你在节目单里也提示,演奏者要“吹打喊叫”嘛。
正如许多中外评论所言,你称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音乐家、中国音乐界重要的特殊人才。在钢琴演奏和音乐创作上,你的天赋与造诣已高到一定境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这场音乐会如此可听、耐听。我喜欢这种音乐:耳朵不受强度刺激,心灵却有深度触及。我认为,你在作曲上,已超越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先锋派现代音乐的写作套路,音乐不落俗套,非同凡响,个性十分鲜明,风格极为独特。你也击掌跺脚、嘘嘻哈嘿、拍打喊叫,还从琴凳上站起来,躬腰俯身伸手去拨弄勾弹藏在琴体内的钢丝。《萧萧》从头至尾以这种姿势这种方式且弹且唱,第一次听到钢琴这件庞然大物被你驯服调理得如此纯朴温顺,音色却非常奇异,比柳琴柔和,比吉他单纯,如曼陀铃拨弦声声,琴声歌声和谐平衡,听者的耳朵与心灵无不感觉舒服熨帖。在你的指间,键盘打击乐器雄健华丽的天然气质被彻底改变了,有了乡土乡野、乡风乡情的趣味。《萧萧》平实平和、平朴平静乡谣般的气质富于极强的“欺骗性”,老牌资深的音乐学家李西安教授,开初一听都误以为是首原生态民歌。
我感觉,你的所有自创作品,既有温度又有力度,既有深度又有宽度。想法作法、笔法章法,法度合理。所有的表达,深沉含蓄,节制内敛,有分寸有尺度。音乐语言纯良优美,即便表现愤怒、讶异、喊叫也绝不虚张声势、刻意渲染、强行撩拨。现代音乐“花样”迭出,你的运用处理精道练达,机敏智慧,既有内在的情感动力,又有外化的技术支撑。
你的钢琴演奏技艺才能,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弹《残余的探戈》是我听过最好的左手钢琴作品和最好的左手钢琴演奏,实在太精彩、太高级了,再繁难高深的技术也毫无负担,决不让人为你提心吊胆。所以,你的音乐,意境高远空灵,和声色彩斑斓,极富创意性与想象力,优雅而简朴、亲切而平易,美。这是你原创原生、独一无二的独门秘笈,高平的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你的音乐让人想象自由,遐思无疆,视野开阔,心胸明朗。
我对盛原的预言深信不疑:高平的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仍葆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会被全世界的音乐家和爱好者发现认可。
○ 非常感谢!

我对于在音乐厅演奏总是不太满足。那种传统音乐会仪式感很强,经典作品总在重复演奏,感觉就有些越来越僵化了。演奏者正襟危坐,听众也正襟危坐,听完就礼节性地拍几下巴掌。我希望打破程式化的老规矩,在保持古典音乐的品质规格基础上,做些新的变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跟贝多芬、肖邦确实很不一样了。根据权威数字统计,肖邦一生,正式公演音乐会,有记载的无非就三十多场。这三十多场音乐会,重要的还有他自己的作品,在音乐史上树立了重要地位。现在的钢琴家一年弹百余场音乐会不算什么,但永远重复演奏别人的作品,有时我很怀疑这种演出的价值和意义。我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又很杂,哪儿都想去插一脚。我愿意自己保持感性的创作状态。
最近几年,我在国内的活动逐渐多了起来。2006年,我担任了瞿小松《行草》钢琴与打击乐版的首演,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艺术园区。我特别希望让我的音乐和更多的东西密切联系。我很喜欢美术,小时候画了不少的画;我很喜欢诗,很早就大量阅读中外经典诗作。我和陈丹青、何多苓、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的音乐会,他们都很关注,也真正喜欢。何多苓经常拉着我对朋友说,看到没有,这是钢琴家的手!只有钢琴家的手才能叫手,金贵得很啊!我们这些人的手,只能叫“爪爪”!呵呵(孩子般天真的笑)。
我始终觉得,音乐可以很纯粹,还可以和很多其他艺术在一起。音乐、诗歌和绘画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我们可以穿过一种艺术形式而走进另一片艺术天地。相互汲取不同领域的艺术能量,相互补充、相互激发,艺术创作由此焕发出神奇幻彩和健旺绵长的生命力。
在所有的文学艺术门类里,音乐和诗歌,可能是最为接近的两类,相对而言都比较抽象,优长也都不在于具体、具像的表现或者清晰完整的叙事性。从2014年到2015年,我和我们成都女诗人翟永明合作“音·诗剧场——大街上传来的旋律”。绝对不是用这样东西解释那样东西,或者用诗歌为音乐旁白、用音乐为诗歌伴奏。我们和过去舞台上的配乐诗朗诵可能不一样,好像两种东西相遇邂逅擦肩而过,在同一时空交错并存,互感顾盼互动照应,纯属偶然发生。大量的音乐,可能占到80%以上都是我现场即兴做出来的,带着一种诗的心灵感应演奏。这种东西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也许不那么成功,很多时候却会有很闪光的东西,参与者大多非常喜欢、享受。
在“音·诗剧场”,我不要求翟永明一定要多“专业”地表演。她就很自然、很随意地读诗,本身就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我们都不是那么刻意地在表演,她朗读,我弹琴,两人一起呈现诗韵曲风,更像是一种“对位”,或者“双人舞”,有时平行、有时交错,有时融合、有时间离,全凭感觉,感应互动。
● “音·诗剧场”演出最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艺术走出象牙塔,音乐冲出音乐厅,带来了“大街上的旋律”,奇妙无比。
正如翟永明的吟咏:“这就是那旋律/熟悉的北风吹动时呼呼作响的旋律/这就是那流行过、辉煌过的旋律/峭壁般上升、严肃的旋律。”好喜欢她这些诗句:“那是熟悉的母亲哼过的旋律/是秋风扫落叶也扫心灵的旋律/那是低吟浅唱又炮火连天的旋律/内心凄苦但又绽放笑容的旋律。”
旋律,秋风扫落叶也扫、心、灵;低吟浅唱又炮、火、连、天,内心凄苦但又绽放笑容。天呀,实在太绝妙了!
现在,我最想听到“大街上的旋律”!
○ 肯定有机会,这类演出活动会比较“热”。
实际上,“音·诗剧场——大街上传来的旋律”从2014年12月8日在成都东郊音乐公园记忆唯乐上演后,2015年1月2日就到了北京蜂巢剧场,10月又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演出了。我的“琴形影·高山流水”跨界音乐原创剧场,从2014年8月在成都、9月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之后,很快就于10月去新西兰惠灵顿、但尼丁和尼尔逊世界首演;12月又返回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2015年在上海、杭州演出;2016年1月在西安登台……这类演出在文化界反响很强烈。
● 谢谢高平,非常期待你更多的作品和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