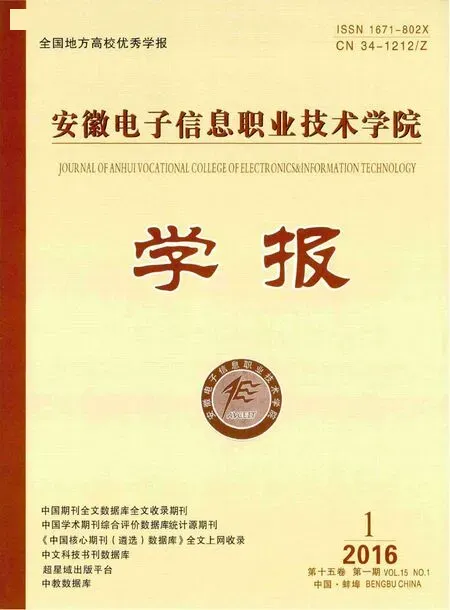翻译特性视阈下《庄子》文化词语英译探析
2016-03-19吕新兵
吕新兵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翻译特性视阈下《庄子》文化词语英译探析
吕新兵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庄子》是中国古典主义哲学和文学的重要作品,文中蕴含大量具有汉语特色的文化词汇和句子,充分体现道家思想的精髓。本文以翻译特性为视角,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五大特性为基础,分析《庄子》英译本中的词汇和句子英译问题,探析文中汉语文化词在英译过程中的选择和使用,以及其英译的方法,以实现《庄子》乃至中华古典文化的正确传扬。
翻译特性;文化词;英译;庄子
一、引言
传统观念里,翻译仅仅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是意义的传递,表现在语言层面就是语言的形式转变。近年来,翻译理论受多学科影响,发展迅速且多样。图里(Toury) 曾经指出“Theory formation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never been an end in itself.(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建构永无尽头)”(1988:11)。时至今日,翻译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融入诸多理论,翻译的意义也更加多样化。其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缺失和文化冲突的现象”(顾毅,杨春香,2012:54)。所以,译语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也成为翻译理论中不得不考虑的一环。我国学者许钧在《翻译概论》中从翻译特性的角度出发,将翻译的特征归纳为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型、创造性和历史性五大特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译作要在最大程度上让译者接受。
《庄子》一书是中国古典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巨作,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展现了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才华,无论是在哲学还是文学领域都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其综合文化的多样性在翻译中引起广泛的重视。正因为其承载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因素,所以如何翻译其中的特色词语对于中华文化理解传播至关重要。本文将从翻译特性角度对《庄子》英译的译本进行探析,分析《庄子》一书中文化特色词语翻译的特色,探讨不同文化视角,不同历史背景的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词语的不同理解,希望英语母语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庄子》乃至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文学和哲学表达。
二、翻译之文化特征
在不同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翻译所体现出的内涵和特点不尽相同。它与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历史传承、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有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内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之间的转换一定会有文化的烙印。或者说,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而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性也决定了翻译的动态性。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文化因素必须占据重要的地位,要充分利用文化特性,帮助译者更加准确清晰地展现原文的思想,同时也更利于读者接收译作,从而达到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最大化的表达。
早期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重语言轻文化”,正如许钧分析的那样:“长期以来把翻译活动当作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的简单主义翻译观,自然对人们的翻译研究有着观念上的影响,在研究中重视语言层面的转换便成了一种必然”(2002:220)。前苏联的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英国的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法国的乔治·穆南的《翻译的理论问题》,这三部对翻译理论影响极大的作品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论述。这三部作品中并没有注意到翻译中重要的文化因素,将翻译单纯地看作是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嫁接转换,忽略了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文化中心内核。对于历史文化因素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他)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维度,那就是除语言之外的历史与文化维度”(许钧,2002:222)。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给翻译进行重新的定义,开拓了翻译的新境界。至此,翻译中的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引起了翻译界的广泛讨论。在我国,许钧教授提出了翻译文化特性的五个方面,分别是:翻译的社会性、翻译的文化性、翻译的符号转换性、翻译的创造性和翻译的历史性。我们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结合《庄子》英译对翻译之文化特征进行归纳和分析。
三、《庄子》及其英译
《庄子》一书亦称为《南华真经》,是先秦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世之人所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共计52篇,但现存于世的仅仅33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七篇,被认定为庄子亲著;外篇和杂篇或有其门人和道家学派后来人的作品。《庄子》一书涉猎广泛,“是一部具有哲学、文学、宗教色彩的中国文化典籍”(顾毅,杨春香,2012:54)。庄子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对“道”的阐述,而“道”本身又具有“不可说”这样的特性,这欲说又不可说的哲学悖论就决定了《庄子》一书在用词上的考究。也正是由于这种悖论表述的复杂性,《庄子》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精美的隐喻来试图说明“道”的神秘特性,加之庄子本身具有的诗人才华,也就造就了其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博大精深的哲学视角配以独具匠心的文学表达使得《庄子》一书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庄子文本具有浓厚的诗思融合之特质”(刁生虎,2005: 109)。正是这种独特诗思气质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庄子》进行研究,英译工作开展有序,近年来发展迅速。
《庄子》的英译研究起源于1881年,巴尔弗(Balfour)出版第一部《庄子》英译作品,取名为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南华真经——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受译者水平限制,译本误译较多,但是拉开了《庄子》英译的序幕。在其后至今的近一个半世纪里,陆续出现了二十多种各类译本。其中全译本共计九部,汪榕培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庄子:汉英对照卷》一书是国内唯一全译本《庄子》。得益于译者深厚的翻译功底和广博的文化内涵,此译本质量较高,得到国内学者一致好评。其余的多是节译本,如哲学家冯友兰翻译的《庄子篇》,从哲学角度解释《庄子》中蕴含的哲学思想。Sam Hamill和J.P. Seaton翻译出版了The Essential:Chuang Tzu,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古典文化。编译本的以莫顿为代表,他的《庄子之道》就是其根据英译本进行的编译,但也基本传达了庄子的思想。
四、《庄子》文化词语的英译
(一)翻译特性之社会性
翻译是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两个社会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所以翻译受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极大。“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类思想交流的需要,因此翻译并非独立于社会,而是服务于社会,译论研究根本无法回避其社会性。”(俞佳乐,2000:40)。翻译的社会性实际上就是将翻译看作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它需要满足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的需求。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需要将文本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在特定的社会需求的指引下进行翻译工作。
《庄子》英译本中例子又有很多,如《逍遥游》第一段的“南冥者,天池也”,这一句的翻译。冯友兰译本和林语堂译本给出的是“the Southern Ocean,the Celestial Lake”,Sam Hamill and J.P.Seaton给出的翻译则是“the Southern Darkness,which is also called the Pool of Heaven”。此句涉及到两个地名的翻译,“南冥”和“天池”。在“南冥”的翻译上,冯友兰和林语堂都认定为“冥”实际上就是海,选择“Ocean”一词与之与之对应,这样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利于理解。而Sam Hamill and J.P.Seaton对于“冥”的理解则为黑暗,这样的翻译突出了鹏将迁徙地方的神秘。因为鹏是鲲的化身,而鲲为水生,所以并不是译者理解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这两种翻译的背后就涉及到的是译者或者是社会对于“海”的不同理解,西方人冒险精神驱使一代代人去征服大海,英语译者的社会观念里的海的神秘特性不是很强烈,用于故事中并不能表现出故事本身的神秘感。而汉语社会相对保守,对海的认识还是陌生,也怀揣敬畏之情看待大海及所发生的故事。同样还是这句话,“南冥者,天池也”。对于“天池”的翻译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差异。冯友兰和林语堂用的都是“Celestial Lake”,这一翻译中的“Celestial”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而在中国社会中“天池”也是具有神话色彩的词语,这样的翻译转换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原作意义,同时符合译文读者的社会风俗。Sam Hamill and J.P.Seaton译作更为直接的译作“the Pool of Heaven”,将宗教色彩更浓的“Heaven”直接用上,这样的译文就在社会层面上进一步融入读者观念中。
(二)翻译特性之文化性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语言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存在。“语言的独特性就在于作为文化的承载和表达手段,把文化的其他要素融汇于自身之中,使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各个层面都能在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袁庸新,2009:137)。语言根植于文化之中,同时又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文化的具体特征。翻译就是实现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一种手段,正如廖七一描述的翻译“总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2001:364)。而词语是构成语言的基础性元素,是文化的最为浓缩的反映,是翻译涉及的最小单位。对于译者来说,极具文化特色的词语的翻译是整个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基础性因素。
《庄子》作为一部文学性极佳的古典著作,在英译过程中就出现过大量文化词语的翻译问题。如《庄子》中存在大量对于“气”的问题的讨论,“气”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名词,哲学意味颇重。“‘气'作为万物存在变化的基础和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贯穿于天地万物,一切生命现象和精神活动都离不开它”(徐来,2005:56)。西方人的概念里没有与“气”这一概念完全对应的文化词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要着重对这一术语的处理。葛瑞汉在翻译“气”的时候用的是“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他理解中的“气”和西方观念下的“纯能”(pure energy)是有相似部分的,所以将“气”视作是一种能量,与“energy”可视作对等词语。而梅维恒对于“气”采用的是“his vital yin and yang breath”,“breath”的使用表现出的是“气”的生命力这一方面的特征,更多的含有“气息”的意味。而二者在翻译“气”的过程中都涉及到“阴阳”这个概念,阴阳是六气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要理解“气”必须先理解“阴阳”。“气”这个哲学术语本身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义,在英译中哲学意义的传递也就不会那么直接和简单,这也是翻译文化性的充分体现。
(三)翻译特性之符号转换性
语言在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包含语音系统和文字系统的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个角度下的翻译也可以理解成两种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学科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1982:38)。但是两种符号之间的转换并不是完全对等或者是等值的,因为每个语言符号系统的产生具有独立性,发展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每一个符号系统都受到各民族不同的环境影响,其发展轨迹不尽相同。所以,翻译作为语言在符号层面上的转换,其本身必然在符号的特点上一定会有所得失。
汉语在向英语转换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符号转换问题,包括押韵句、双关语、四字成语等汉语特有的语言符号。《庄子》在语言选择和使用上非常考究,所用词语和句式结构简单但是寓意深厚,是中华文化的沉淀和凝聚。例如《齐物论》中“大知闲闲,小只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句排列简单,句式对仗且存在押韵,充分体现出汉语排列和音韵之美。Sam Hamill and J.P.Seaton译本的翻译为“Great understanding cuts itself off and falls idle;small understanding grows lazier still.Big words can burst into flames and begin conflagrations;small words are mere chatter.”此译本打破了原文中的句式对仗,在结构上仍采用对比,却失去原文四两拨千斤的气势。冯友兰译本翻译为“Great knowledge is wide and comprehensive;smallknowledgeispartialand restrict.Great speech is rich and powerful;small speech is merely to much talk.”在译本中仍能看出译者尽力复原原文中的句式和意义,但是其中韵味和简洁明了之感却也消失殆尽。两个译文不可避免地舍弃了句式上完全对仗和表达上的简洁,在传递意义为第一要务的翻译任务中,这种符号的转换必然要牺牲原文中部分特色。
(四)翻译特性之创造性
创造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活动,创造性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译者在翻译之中充当中介作用,但是却是具有能动性的中介。“译者在这里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者,他必须通过自己的认识、理解,把原作反映为译作。译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积极的创造者,而不是消极的反映者”(马骁骁,张艳丰,2002: 76)。所以,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是经历了译者对其进行的创造性的再加工,使得加工后的作品更符合翻译的目的。
比如《庄子》中核心思想“道”的英译问题。“道”是道家学派的中心概念,这一个字的英译关系到整个学派思想的传播问题。“道”现在普遍认同的翻译就是音译的“tao”,这是英语中独创出来的,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词语。在探索“道”的翻译过程中,汉学家用过“The Way”、“reason”、“road”、“wag”以及“logos”等词语,但是由于“道”本身蕴含的意义过于丰富,而以上的词语都侧重某一方面,并不能完全表现出“道”的内涵,所以逐渐被放弃。而新造词“道”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全新的词语,是为中国哲学中“道”量身定做的词语,若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理解“tao”也就不是什么困难。用原有的词语翻译“道”也可能适得其反,误导读者。
(五)翻译特性之历史性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受到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必然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方面,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本身受时代所限,要符合特定时代的特色才能被特定时代接受。另一方面,不同的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时代所处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对译者主体性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可以左右译者的翻译意图和翻译手法。正如许钧所言:“翻译的历史性也是广义的翻译过程的体现。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译者主体性、理解的历史性、意识形态、翻译的动机和理念、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读者的接受视野和审美期待等等”(2009:40)。所以,不同时期的同一部作品相同内容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方式,各自体现时代特色。
《庄子》一书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有译本出现,不同时期的各类英译本层出不穷,所翻译的内容也各有差异。这里用《庄子》中“阴阳”的概念来作为例子,分析这部作品的历史性因素。早期的汉学翻译家受实用主义影响,对于“阴阳”的处理是忽略的态度。如理雅各的翻译就是“his breath came and went in gaps”,而冯友兰则为“the principle of his whole body”。这段时期更倾向于将“阴阳”的实际功能表现出来。而六十年代开始,“阴阳”的翻译几乎全部采用“Yin and Yang”的方式,这样的表达成为了通用概念,这样可能会使西方读者感到陌生,但是却也了解这是一个东方哲学词汇。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对《庄子》研究的深入就将“阴阳”的概念和“气”向结合,葛瑞汉将其译为“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梅维恒译为“his yin and yang breath”。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同一个概念的翻译呈现不同的特色,也充分说明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五、结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时刻受到两种语言内部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翻译的五大特性——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无形地溶于翻译过程之中,充分渗透到译者的翻译思想之中,为分析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将这五大特性与《庄子》英译本相结合,透过《庄子》中的例子分析翻译特性的体现,在突显出这五大特点的同时深入分析了英译本的得失,这不仅进一步论证了翻译的特征,而且剖析了《庄子》英译本不同特点的成因,希望对后续的研究有参考意义。
[1]Sam Hamill and J.P.Seaton.The Essential Chuang Tzu[M]. Boston and London:Shambhala Publications,1999.
[2]Toury,G.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Translation”and “Norms” [A].In Schaffner,C.Translation and Norms[C].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
[3]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冯友兰.庄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5]葛瑞汉.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辩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顾毅,杨春香.《庄子》内篇中文化因素翻译探析[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6).
[7]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8]李莉.符号翻译与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3).
[9]刘妍.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 2011,(9).
[10]马骁骁,张艳丰.论翻译的创造性 [J].山西大学学报,2002,(6).
[11]汝红兵.汉文化在符号转换中的失落 [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12]徐来.英译《庄子》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3]许钧.翻译概论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杨柳桥.庄子译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5]俞佳乐.翻译中的社会语言学观[J].中国翻译,2000,(6).
[16]袁庸新.论词语的文化性及其在翻译中的体现[J].南昌大学学报,2009,(4).
(责任编辑:卓如)
H315.9
A
1671-802X(2016)01-0049-05
2015-12-29
吕新兵(1991-),男,辽宁丹东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E-mail:jack_lv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