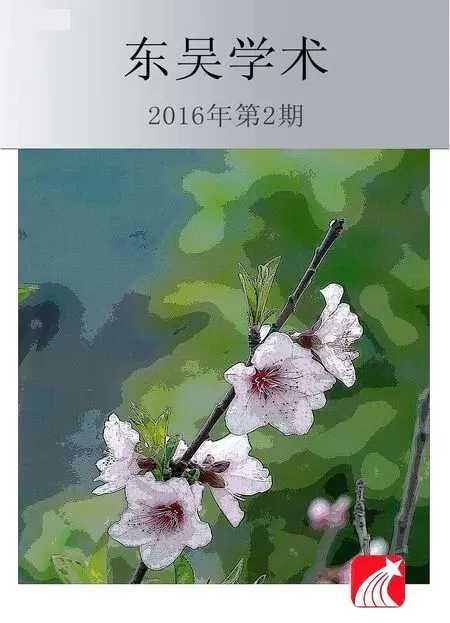论劳马小说、话剧创作中的“笑化”美学
2016-03-19于树军
于树军
论劳马小说、话剧创作中的“笑化”美学
于树军
劳马的小说话剧创作以幽默诙谐而受到批评界的高度关注,他这种自成一格的文风,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在长期致力于诙谐讽刺小说、话剧创作的同时,劳马其实一直在思索并尝试构建“笑”的美学,他将古今中西文学传统与理论资源有机整合贯通,赋予其当代性的内涵。表面上看,劳马的诙谐讽刺,意在为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造了一面镜子,画出了当代社会各阶层的群像;而实际上,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潜含着劳马对当下社会时弊与现状的深刻忧虑,“笑亦载道”、笑以化人,乃是劳马文学创作的真正意图。
劳马;诙谐幽默;笑;“笑亦载道”;笑以化人
劳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作至今,曾有多篇小说入选“二十一世纪年度小说选”、“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中国年度小小说”、“中国年度微型小说”等,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近年又有了新的尝试和突破,中长篇小说《抹布》、《伯婆魔佛》、《傻笑》、《哎嗨呦》相继问世,三部话剧《巴赫金的狂欢》、《苏格拉底》、《好兵帅克》也随之推出,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肯定。劳马的创作因其语言、文体的独特性,①阎连科称之为“幽锐体”、“短圣”新体,《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3日。张清华称之为“新笔记体”,《作为一种“新笔记体”小说来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以及深刻复杂的内涵而颇受好评。
有论者认为幽默诙谐、充满讽刺意味的劳马小说应被纳入现当代文学史视野中来加以考察研究,将其与鲁迅、叶圣陶、张天翼、老舍、赵树理,以及新时期以来的高晓声、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作家并置,试图梳理出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诙谐幽默的美学风格传统及其流变。诚然,这项研究工作确有必要。不过,劳马对诙谐幽默或其自己定义的“笑化”美学的执著追求与实践,与上述作家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劳马的创作极具个性,以幽默讽刺、诙谐调侃、狂欢化来概括其美学意蕴的话,未免有些简单化之嫌。尽管也有论者对劳马的“笑化”美学与西方狂欢化理论等相关话题有所触及,但大都缺乏深入系统地辨析和阐释。而这对于把握劳马的创作取向,以及对其文学史定位而言,无疑是一个首要且关键的要素。若从“谱系学”以及文学史维度来探究劳马的创作特质,或许是一种有效的路径。
一、“笑化”美学的实践:劳马的小说与话剧创作
确切地讲,劳马的小说应被称为“社会问题小说”,其关注的焦点大都是当下社会的时弊与历史沉疴。小说题材广泛,涉及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诸多阶层与领域,意蕴复杂深刻。高校、官场、农村(葫芦镇系列)这三类题材在劳马的小说创作中所占比重最大。
其中,高校与官场系列,揭示出了某些灰色知识分子的畸形扭曲的人格弱点,以及虚伪世故、清高而又世俗的双重面孔,将体制下的这群“新儒林”的世俗相、社会相暴露无遗。如《哲学》、《博学的人》,展现了当今社会中人文知识的贬值与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莫提包》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某些知识分子对名利的几近病态的贪恋追逐;《探视》在充满戏剧性的情景中,展现了不少知识分子之间为了物质、名利而明争暗斗,即便已经退休,甚至身患重病时仍要一争高下的那种可笑可鄙之举。《一封遗书》将锋芒直指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唯学历论的怪病,表达了深受体制束缚钳制的当代学人在残酷竞争中的困惑与无奈。《有意思》勾勒出了不少持有“读书作官”观念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假清高、真虚伪的皮相。《一碗面条》中,对几位将金钱看得比吃饭还重要的教授的言行的刻画相当到位,令人忍俊不禁。
劳马的官场题材小说创作,将锋芒直指当下某些官员们的“官僚主义”、“官瘾”与人性的“异化”,于不动声色的描绘中尽显其腐败贪婪的嘴脸与丑陋卑污的灵魂。如《某种意义》、《潜规则》、《个别人》、《讲话》、《佩服》、《述职》、《升迁》、《说心里话》、《幸福时光》等,篇幅精短、语言凝练犀利。对当下官场中的“人浮于事”、“讲大话说空话”、急功近利、贪婪自私、利欲熏心的种种病容予以了深刻讽刺与批判。此外,劳马还将笔触延伸至乡村社会,在《红皮鞋》、《制服》等小说中,以漫画式的手法,展现了乡村社会中基层干部对权力的畸形的贪恋的可笑一面。在某些篇章中,劳马还巧妙娴熟地将“京味儿”与黑色幽默融为一体,意味深沉。
当下普遍存在的教育体制与观念中的弊病,以及很多社会乱象也是劳马关注的焦点。如《一问三不知》将中国高校管理模式中舍本逐末——过分看重量化指标而缺失对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的培养的尖锐问题提了出来。《认识自己》表达了对应试教育制度扼杀孩子天性的隐忧。另外,如《排队》将计划经济时代残存至当下一直难以解决的供求矛盾的现象揭示出来。《乔迁之悲》、《家乡的讯息》、《我的理财经历》、《活死人》、《冷》等小说触及到了当今的种种“怪现状”,有很强的纪实性与社会效应。
然而,这其中以“葫芦镇”系列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意味最为深刻而复杂。《抹布》、《伯婆魔佛》、《傻笑》、《烦》、《抓周》、《哎嗨呦》等中长篇小说,以劳马最为熟悉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乡为背景,贯穿了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直至改革开放、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转型,从农村到城市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涵盖于小说之中,既关照当下现实,又有历史的纵深。犹如剪影般快节奏地重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与转型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的变异。可以说,劳马的小说既是放大镜也是显微镜,他以宏观与微观并置的双重视点,以“葫芦镇”(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浮作为蓝本,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从中流露出了劳马对“文革”前后,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常与变、得与失的深刻思考。
与“葫芦镇”系列同样重要的,还有劳马首度创作的话剧《巴赫金的狂欢》、《苏格拉底》、《好兵帅克》,在主题思想及人物言行的刻画上与以往的取向近似。需要强调的是,这三部话剧的创作进一步深化了劳马的“笑化”这一创作理念,对“笑化”美学作出了更为明晰的诠释。在程光炜教授看来,这是劳马“对二十年小说创作资源的一次清理,哲学的眼光,喜剧的结构,以及对狂欢化理论的独特解释……话剧……给了他的表达更大更宽松的艺术空间,在暂时摆脱小说时间结构的束缚后,劳马在他的话剧舞台上驰骋纵横,内心世界得到尽情的抒发”。①程光炜:《民间节日诙谐形式的精神风格化:评劳马的三部话剧》,《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的确,这三部向苏格拉底、巴赫金与哈谢克的致敬之作突显出了劳马创作中的“笑化”的美学意蕴,也体现出了与西方文学思想的精神谱系上的某种关联。
劳马的文字精炼犀利、诙谐幽默、寥寥数笔即可将人物的性格心理与人性弱点揭示出来,内在容量深广,文本充满了张力(复调性),给人以巨大的诠释和思考的空间。在笔者看来,劳马小说的独特,不仅仅体现在“短圣”的“幽锐体”与“新笔记体”这一层面,更在于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动的描写手法。劳马曾说过:“小说对每个人物刻画得是否形象、鲜明,取决于人物本身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一种语言,一种更为深刻的语言。”②杨新美:《别样的讽刺小说》,《金融时报》2007年11月6日。与之相比,“细节的描写……可以高度地概括和抽象,寥寥数语同样能刻画逼真,达到‘神似’。神似胜过形似”。③劳马、梁鸿:《“笑”的文学传统与轻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劳马的这一做法可谓“攻其一点”,不过,在某些文本中间,劳马也会对氛围烘托、深化人物心理塑造的景色与细节描写有所兼顾。虽然劳马的小说追求高度凝练,注重人物话语行动的刻画,但他对景物和细节的描写同样非常精彩。中篇《伯婆魔佛》中有两段文字显示出了其与以往小说不同的别样意味。
过了二月,葫芦镇变了颜色。雪化了,天气暖和了。被白雪包裹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农村小镇子像是睡醒了的孩子,从白被单子里钻了出来。
……
初秋的葫芦镇是一张以绿色为基调的巨幅油画。
树是绿的,草是绿的,庄稼也是绿的。而人们的脸色如同挂在树上的苹果、桃子和接近成熟的高粱、苞米穗子,黄里透红,黑中流金。
这段文字颇有东北作家萧红的诗化小说的韵味。此外,中篇《抓周》的一处细节描写,劳马的文笔也给人以某种惊异之感。
天快亮时,银才打了个盹,在他的记忆中他头一次梦见了奶奶,奶奶去世时,银才不过六岁。梦里奶奶的形象很模糊,既像一个老太太,又像一个老爷爷。醒来时,银才觉得好奇怪,梦中的情节几乎全忘了,但奶奶临终时的那句话在梦里十分清晰。奶奶咽气前,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只有一个字:“冷!”银才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朝窗外望了望,一篇雪白的世界。噢,窗户没关严,刺骨的北风从双层窗纸的缝隙里拼命地往屋里钻,还扯着尖尖的细嗓,那声音有点儿像唢呐。
劳马文笔的功力不可小视。当然,最能突显其“笑”的特质的还是在于其创作的表现形式。从中篇《傻笑》的各章节的标题即可看出,譬如“一个年轻的老头儿”、“一个人包围了一个营”、“花生壳里睡大觉”、“先擦屁股后拉屎”、“现在如了”、“结巴当上了广播员”……这些荒诞诙谐的文字,令人捧腹。而劳马对人物的刻画也充满了“笑”的意味,颇具代表性的是伊十(《抹布》)、东方优(《傻笑》)这两个经典的“傻子”形象,如伊十闹革命、万瘫子老婆借种风波,东方优向学校申领傻子证明等细节的描写也都令人忍俊不禁。劳马通过“狂欢化”的笔法将伊十、东方优的言行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劳马还以诙谐夸张的语言将伊老大(《抹布》)这个名不副实的村会计刻画得惟妙惟肖:“老伊在当会计的日子里,头发上抹的菜籽油能顺着脖子往下流。他胳肢窝下夹着算盘,在镇子里的大街上来回地走。‘算盘一响,黄金万两。’……‘三八二十三,不够再加点儿。’”
阎连科认为,劳马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幽默不仅是小说之趣雅,不仅是故事中事件、情节与细节的荒诞,而且幽默本身,就是文学的本身,就是那种庄严的现实与历史……(劳马)对‘笑的艺术’在写作中的操持运用之娴熟可以把政治、革命、饥饿、土地、风俗、婚爱、性以及我们历史与现实无处不在的庄严与神圣,全都纳入到幽默的思维中”,劳马所追求的幽默“超越了我们通常理解和看到的幽默”,而是将其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抵达了“文学的本质之境界”。①阎连科:《幽默原是一支箭》,《北京青年报》2009 年11月2 1日。这正是劳马创作的精神内核。可以说,“笑”即是劳马的创作理念、人生哲学与世界观。而选择笑,而非满腔怨怒、一“骂”了之,在轻松的调侃揶揄的同时,又有所节制内敛。劳马的文字里充满了调侃戏谑、荒诞夸张、嘲讽揶揄,又不乏机智敏锐而富有洞见。当然,在看似轻松搞笑、揶揄调侃的字里行间,其实却有着劳马冷静的判断与思考。
二、“笑化”美学的建构:对中西古今文学传统、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幽默”虽被林语堂引入中国,但它毕竟是“舶来品”,与中国本土资源仍有一定的隔阂。而劳马所执著追求的“笑”的美学,无论是思想内蕴,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似乎都要比幽默、诙谐一类的概念显得更丰富、更贴切,更具包容性。原因即在于,劳马所界定的“笑”实际上是融会中西古今的文学资源,将古典传统予以承扬,同时将西方理论资源加以创造性转化,即与本土民间资源有效整合而成。
美国批评家屈瑞林指出:“批评家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描绘一个连贯的传统,从而使很多作品更容易理解’。”②[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12页,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虽然“传统”在批评家和作家那里各有不同的定义,不过,劳马的确在有意识地做这样的事情。劳马二十几年来的创作一直秉承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笑”的传统。在《古老的笑声》中,劳马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笑”的传统的发生、发展与流变,并对“笑化”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界定。他指出,“笑”的传统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笑’很早就出现在经典著作里面,‘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郑人买履’、‘愚公移山’、‘刻舟求剑’等,都是经典的‘笑’。”③劳马、梁鸿:《“笑”的文学传统与轻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而“以笑为生,即以搞笑为职业,替王侯消愁解闷的滑稽艺人,最早出现于春秋之际。”夏桀时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俳优”这类艺人,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中也有不少关于俳优的记载。到了近现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冯沅君的《古优解》也都对其做了相关的所考证和论述。
俳优在向君王们提供笑料,以供娱乐消遣外,还有孔子所说的“怨”——“讽谏”这一重要功能。“‘俳优’们通过故意说反话、说疯话、说傻话、说风凉话等形式,‘谈笑讽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传递民意,为民请命。这种做法被称为‘优谏’。”“他们常常借助自己的独特身份、独特地位和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参与朝中某些决策。在搞笑的同时也兼搞政治,或者说是以搞笑为幌子,实现政治参与的目的。”在劳马看来,“排除‘俳优’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功能不讲,从其自身价值来看,它无疑是我国说唱艺术、喜剧艺术的渊源”。④劳马:《古老的笑声》,《笑亦载道》,第201-204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劳马的文学创作沿承了古典文学中这一“笑”的传统,其作品中的“笑”表面上仿佛在“说反话、说疯话、说傻话、说风凉话”,但其中却饱含智慧与哲理。劳马的文字中,让人感受到《孟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滑稽列传》、《笑林》等古代经典的“古老的笑声”在回响。
诙谐幽默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劳马对农民形象的语言行动的刻画,还汲取了民间文化资源,除相声、小品、段子外,东北民间文化也为其供了独特养分。东北地域文化向来富有诙谐俏皮的因子,尤其是民间故事传说、方言俗谚、二人转,乃至东北人的个性气质等方面都体现得非常鲜明。《抹布》、《傻笑》、《伯婆魔佛》、《烦》、《哎嗨呦》等小说,弥漫着浓郁的东北大地特有的风味气息。劳马善于将东北民间故事传说等有机地融会到创作中,从而强化了“笑”的元素。然而,他对当代文学(因政治原因而断裂)的“笑”的传统的激活,并非向古典传统的简单意义上的回归。劳马并未简单地模仿、重复古典文学中的“笑”的传统,而是将其有机地融合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高校、官场等诸领域。在诙谐幽默与轻松的调侃中,将反思、质疑及批判的笔锋悄然划向了历史与当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劳马化传统化得好。他所表现的“笑”超越了一般的诙谐与讽刺,冷嘲热讽的是人的不自知、愚弱、虚伪、卑劣等根性,即使在戏谑、调侃、讽刺的背后,也往往怀有怜悯之心,以一种人本的视角来关照之。劳马系统梳理、阐述“笑”的传统,试图将这一断裂的文学传统再次激活,并恢复文学中“笑”的位置,此举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对于还原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而言,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除古典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滋养外,西方的文学思想资源也被劳马巧妙地化用到了自己的创作中。正是劳马对古今中西的“笑”的传统以及相关理论资源的有机整合与创造性转化,才呈现出了其独特的个性风貌。从他的某些篇什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黑色幽默”、“荒诞派”与“存在主义”的意味。不过,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讽刺艺术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劳马的“笑化”美学的建构中所起的支撑性作用恐怕是最为突出的。巴赫金认为,在世界文学中,存在严肃和诙谐两种看待世界的观点,两者相互并存。①[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2-3、77、14、140页,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相比严肃性,笑(诙谐)更“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这是关于整体世界、关于历史、关于人的真理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看待世界的观点”,“其重要程度比起严肃性来毫不逊色”。“世界的某种重要的方面只有诙谐(笑)才力所能及。”②[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2-3、77、14、140页,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的确如此,“狂欢化”即劳马“笑化”美学的内在肌理。不过,这种狂欢节的“笑”与一般的讽刺挖苦不同,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③[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2-3、77、14、140页,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这种笑具有“非官方性”,与“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是不能共融的,“与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④[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2-3、77、14、140页,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拉伯雷的《巨人传》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参照,而巴赫金将狂欢节式的“笑”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在当时巴赫金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拉伯雷《巨人传》的诞生与中世纪的宗教政治的黑暗严酷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有本质上的相似性。事实上,巴赫金看重的正是《巨人传》这部小说所饱含的对中世纪严肃的宗教、政治秩序与权威的反抗精神,通过诙谐的形式、广场式的语言以及怪诞的节日形象等对官方文化进行消解,发出了民众内心深处最真实和强有力的声音,表达了民众的自由、民主意识。“其实,只要理解巴赫金在三四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亲身体验,抓住他的思想的深刻批判性及其在文化层面的革命和创造精神,就不难理解巴赫金为何一反常规,以大气磅礴的手笔来撰写这么一部将民间反文化的狂欢节极为理想化的著作。”⑤[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劳马字里行间的“笑”与拉伯雷、巴赫金及其张扬的民间立场是极为契合的,而且他们之间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透过劳马的小说话剧与学术随笔,能够让人感受到“狂欢化”的“笑”的背后的那种“民间性”以及复杂深刻的双重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的讽刺艺术及其直面现实、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颇受劳马的钦佩和欣赏。而劳马的创作中也充满了如契诃夫式的乐观幽默的一面。在充满暴戾的家庭中,契诃夫度过了他的童年,“泥泞阴暗、潮湿、愚昧、肮脏死气沉沉等词汇便是契诃夫童年的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但是,学医出身的契诃夫却在主业之外将文学当作自己的“情妇”,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他精心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其“小说取材广泛、结构精密、文笔简洁、意义深长”。“平凡人的日常事情,经过他的妙笔烘托之后,就有极深刻的人生和教育意义。”劳马感喟:“契诃夫式的笑是饱含哲学意味的,是闪着泪光的。”他的小说‘内容比文字多得多’”。①劳马:《诱人的情妇》,《笑亦载道》,第248-252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
客观地讲,劳马的创作含有一定的西方文学思想因子,但他却充分地将其“本土化”,既“接地气”,又恰到好处。劳马以狂欢化的“笑”的姿态去审视严肃的权力话语与社会病容,其文本的反思与批判的力度不可小觑。在话剧《苏格拉底》、《巴赫金的狂欢》、《好兵帅克》中,劳马通过书写苏格拉底的舍生取义,巴赫金即使身处艰难严酷的政治环境仍初衷不改,以及帅克的诚实正直,褒扬了探寻真理的勇气与秉持操守的可贵品格。从劳马的大量作品中,能明显感受到其鲜明的民间立场、独立的思考与批判意识。
三、笑亦载道、笑以化人:劳马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情怀
相比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尤前三十年)较为缺少“笑”的意味,曾一度为各种“口号”、“赞歌”以及宏大叙事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所压制和淹没,致使“笑”的传统的失落与断裂。诚然,“口号”、“赞歌”、宏大叙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过多的“标语口号”、“赞歌”有时候也是一种假话。因为“口号毕竟不是生活本身,热衷于炮制口号或习惯于空喊口号,吃‘口号’饭,终将导致悲剧”。②劳马:《口号》,《笑亦载道》,第176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劳马对于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说谎话而不敢说真话的社会病相,表达了深深地质疑和忧虑:
讲话就应该讲真话……最普通的习惯变成了最伟大的品质,讲真话者成为了万众景仰的不朽丰碑。可悲还是可笑?我不懂。
也许世上本来人人都讲真话,后来讲的人少了,巴金便成为稀有的“真”人了。巴金老人之后,再也没有敢讲真话的人了,于是人们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怀念之中。③劳马:《巴金死了》,《笑亦载道》,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第166页,2006。
“文革”年代,只有少数几个人敢站出来讲真话,实属我们这个民族的大不幸。某种意义上,巴金的伟大品质正是在于他敢讲出真话,敢于自我反省。然而在巴金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继承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当下现实的情境又是如何?颇值得反思。
其实,“笑”在一个和谐进步的社会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极端严肃的年代,人们只能“有组织、有纪律地笑”,抑或暗地里“窃笑”,这种出于“敬畏的感恩之笑”,无疑“成了人们对某种力量的供奉品”。④劳马:《极端严肃的快乐》,《笑亦载道》,第233页,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极左”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惩罚”下,“笑”的元素受到了严厉的打压钳制,即使是被允许“笑”,也是病态、异化的“笑”。正如劳马所批评的那样:
频繁严酷的政治运动,彻底摧毁了一些作家幽默诙谐的笑的勇气和能力,他们不敢真笑,更不敢放肆地大笑,也不敢哭丧着脸不笑,久而久之练就了要求“进步”的媚笑、谄笑,被迫或主动地通过作品皮笑肉不笑地讨好着、奉承着。笑的丰富内涵和批判功能被过滤、净化掉了。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几乎听不到也看不见那真正属于人所特有的笑声和笑容。⑤劳马:《笑的意味与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正因为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太多的“空话”、“谎话”、“假笑”,民间才会流行各种带有讽刺诙谐意味的笑话与民谣。劳马提醒我们,在对待民间广为流传的笑话、民谣时,要认真揣摩——“谁在笑?笑什么?为什么笑?”⑥劳马:《古老的笑声》,《笑亦载道》,第211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相对于严肃的官方文化,“笑”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被视为一种无意义的存在。然而,无论是民众的“笑”,还是文学中的“笑”,都是不应被压制和抹杀的。民众有“笑”的权利和自由,文学中的“笑”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劳马在其多篇学术随笔中系统地阐释了“笑”的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深意,他尤为看重“笑”所具有的严肃意义。劳马认为:“从一个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就是笑与严肃较量、抗争的过程。”相对于那些严肃的政令、法律、等级、神圣而又僵化的官方文化而言,非官方、非严肃的“笑”便是“对严肃性的摆脱”和“化解”。尽管民众的“笑时刻受到禁止和打压,(但)又时刻获得哺育和滋养”。因为人类离不开“笑”,“人类是笑的存在”。再者,从个人角度而言,“笑的态度背后是我们通常严肃表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笑在笑者那里既是立场,也是观点”。①劳马:《笑的存在》,《笑亦载道》,第196-199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若从社会视角来看的话,“笑”则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进步与否的显著标尺。实际上,笑(笑话)与严肃的官方文化是一种既对抗又对话的双重关系,作为饱含深意的笑话是民众表达诉求的一种特殊方式,“笑话是不经意的历史记载和轻松的传播方式。民心与民意,事实与愿望都因此得到表达与反映”。②劳马:《古老的笑声》,《笑亦载道》,第201-204、211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而民谣同样也“是民众喜怒哀乐的真实写照”,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意义”。③劳马:《民谣》,《笑亦载道》,第174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因此,不能忽视笑话与民谣这一民情民意的晴雨表所承载的内涵与功能。因为“笑是揭开全人类之谜的万能钥匙”(卡莱尔语),官方要肯于倾听笑话、民谣,以包容的态度视之,恐怕才是把握某一时代的社会心态,了解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重要信息的有效渠道,进而寻求改进的空间。正如劳马所言:
笑话属于民间诙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传播力的一种,其影响之深远和广泛难以估量……如果我们把“人民的情绪当做第一信号”的话,最好去听一听他们背后在笑些什么。
……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不应该也不能禁止人民群众的笑闹和调侃。允许并包容民众的嘲弄的笑声是走向民主和谐的标志之一。从笑话中了解民意和民情,找出被嘲讽的错误和荒谬之处并加以改正,这无疑是明智之举。④劳马:《笑话中的民意》,《笑亦载道》,第217-218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
民众能够自由自在地笑,乃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标志。而构建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官方需要认真思考——“民众为何总是笑个不停?在他们的笑的背后是否表达了某些不满和无奈?”⑤劳马:《政治与笑》,《笑亦载道》,第231-232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深入地体察民情民意,以包容的态度适当放宽对民间话语的“无形压力和控制”,“允许民间笑声的存在”,肯于倾听民众内心的真实声音,恐怕才能够做到为百姓谋福祉,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⑥劳马:《诙谐更接近和谐》,《笑亦载道》,第215-216页,香港: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
相比笑话与民谣,文学意义上的“笑”同样具深刻而丰富的蕴含,“是作家观察、把握、理解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和有效方式。笑不光表现快乐与趣味,还承载了丰富的审美追求、精神内涵、人文价值和社会功能”。⑦劳马:《笑的意味与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因为,这种“寓教于乐”式的笑“通过展示错误和邪恶来教化我们……在逗乐人的同时修正他的行为”。⑧转引自[美]埃蒙德•伯格勒《笑与幽默感》,第14页,马门俊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如果参照劳马的《哎嗨呦》、《抹布》、《傻笑》、《伯婆魔佛》等小说系列,就不难发现,劳马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与历史书写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历史关照与反思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虽已离我们远去,但狂乱荒谬的年代所遗留的历史沉疴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疗治与涤除。劳马的“葫芦镇”系列的历史书写,对正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补充和丰富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小说是时代的证词”(略萨语),小说也是一种史料(布罗代尔)。劳马的小说在充满笑声中展现了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激荡与浮沉,还原了当时的某些社会历史情境,让人们在诙谐幽默的文字中,重温历史,审视历史。可以说,如何认识理解过去、现在与展望未来,质言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正是劳马创作中所一直探寻的深刻的哲学命题。
阿诺德指出:“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①《阿诺德全集》第3卷,第209页,转引自(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8页,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劳马冷静地谛视着当下社会人们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在对现实与人性予以批判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他对现实与人性的深切关照。而且在其“笑”的背后,还饱含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态度。在他看来:“笑所反映的喜剧精神是人类生存必备的乐观态度和批评意识,它使人保持着必要的清醒、冷静和警觉,不至于自傲自狂或自卑自贱。笑是一种改正的力量,防止我们严肃地干蠢事、走向异化。”②劳马:《笑的意味与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而劳马的创作正是致力于帮助人们“获得一种善于发现各种各样笑料的能力”,使其在“行动中尽力避免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事情”而“成为最有教养和最有道德的人(莱辛语)”。③劳马:《柔软的一团•序》,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若结合劳马的高校、官场小说系列来考察的话,会发现其小说话剧中“笑”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劳马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世风日下、信仰危机、价值真空、道德沦丧、拜金贪腐、体制僵化,以及对民族的发展前途等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忧虑,试图让更多人在笑过之后反观自我与审视现实。由此也彰显出了劳马的知识分子情怀与社会责任感,若用“笑亦载道”、“笑以化人”来概括其创作意图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结语
劳马深厚的哲学底蕴、丰富的社会阅历、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他的自觉的、边缘化的民间立场,使其创作往往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身上以及历史记忆的深处以小见大,让人们从中看清自己的生存与精神境况,进而为人们开出一条自我反省的道路。这种“立人”与“重塑道德”的人文情怀与鲁迅、巴金、沈从文对世道人心的关照可谓一脉相承。
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创作虽然呈现出了高度繁荣之状,但不容否认,“笑”的元素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即便有,也只是对其稍作点染而已,鲜有作家赋予“笑”以本体性意义。在这一点上,当代的文学创作仍显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劳马在此方面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建构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让当代文学的格局更为丰富多元,其文学史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于树军,吉林省农安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