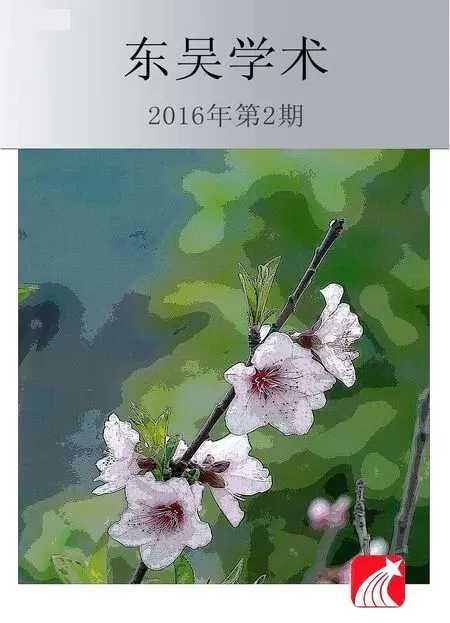哲学、寓言与症候式写作
——劳马小说阅读札记
2016-03-19乐绍池
乐绍池
中国文学
哲学、寓言与症候式写作
——劳马小说阅读札记
乐绍池
本文试图探测劳马小说的另一重世界,寻找被压抑之下的那个不断涌动与倔强的作家自我,同时也希望尝试读出劳马未被指认与尚被遮蔽的小说面孔。本文认为在劳马小说中,“哲学”是通过非哲学和反哲学而显现出自身的。“哲学”与“傻子”是一种颠倒的结构,这是劳马式的“哲学辩证法”。劳马小说的哲学气质还体现在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荒诞呈现与小说的寓言性质。劳马小说可以被视为一种“症候式写作”,即力图揭示出人物无意识深层的、潜在的空白、沉默与不可见部分,以反常、断裂为突破口,找到症候点,直指现代生活的病灶,获得一种直击人心、一针见血的效果。
劳马;哲学;荒诞;寓言;症候式写作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文化部大厅,中国作家劳马获颁蒙古国最高文学奖。劳马成为继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韩国作家高银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蒙古国最高文学奖是对劳马十多年寂寞而勤奋的写作的一次温暖回应。尽管近几年来,批评界对劳马小说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然而相对于其小说创作所呈现的成绩和为当代小说所开掘的可能性而言仍然远远不够。诚如作家阎连科在阅读完劳马小说集《潜台词》后所言:我们把他的小说看得简单了;我们本能地慢待了他的写作;他小说的鲜明与集中,阻隔了我们对他小说丰富的发现和研究,乃至于久长旷日地讨论着他写作中最为直切、便捷的呈现。①阎连科:《劳马“幽锐体”的短圣追求》,林建法主编:《说劳马》,第14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本文愿意听从阎连科善意的告诫,试图探测作家“直切、便捷的呈现”之后的另一重世界,寻找被压抑之下的那个不断涌动与倔强的作家自我,同时也希望尝试读出劳马未被指认与尚被遮蔽的小说面孔。
一、“哲学”与“傻子”的颠倒
尽管早就有人提醒,“我们不能过分坚持以往流行的艺术与哲学是相互对立的专断观点。如果人们执意要追寻准确的答案,这种对立论肯定是错误的”。而且,从文学史上看,“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巴尔扎克、萨德、麦勒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作者,还有其他许多”。①[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第114-118页,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但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哲学小说和哲学小说家都很罕见,可以说,当代中国小说的哲学气质是很稀薄的。然而,劳马,一位“文坛”的边缘者带着他富有哲理的小说闯入了小说与哲学的交叉地带,为当代小说增添了别样的风彩。在对劳马小说的谈论中,“哲学”是一个出现频度颇高的关键词。有论者认为劳马小说的实质,是喜剧形式和哲学内容。也有论者指出他的小说对于中国当下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哲学,它提醒我们,中国当下小说最缺失的是哲学,而其小说提供了一种哲学拯救小说的可能性,并在这个意义上,直接把劳马小说命名为“哲学小说”。还有论者认为劳马仿佛中国东北版的哈谢克,以狂欢化的小说风格作为工具,考察、反思何为哲学,何为哲学家。②分别见《当代作家评论》:程光炜:《读劳马的小说》(2008年第5期),贺绍俊:《劳马的哲学小说》(2008年第5期),敬文东:《小说、哲学与二人转》(2013年第3期)这些批评家的看法都提醒我们注意劳马小说与哲学的亲密关系。
劳马曾以研习哲学为主业,写作时赋予小说一种哲学质素与哲学气质,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加缪曾说“小说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像和美化修饰”。不过紧接着他就补充道:“但是,作品只是由于受到这种哲学的暗示才成为完整的。”③[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第114-118页,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韦勒克在谈到文学和思想之关系时指出“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④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13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套用韦勒克的说法,哲学本身不能成为小说。只有当哲学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和概念上的哲学而与小说肌理交织在一起,成为象征时,才会出现小说中的哲学问题。所以加缪更详细地说道:“艺术作品的产生是由于充满了使具体事物理性化的智慧。它标志着肉体的胜利。正是清醒的意识激发起了艺术作品,但在这同一活动中,它又否定了自己。它不会让位于要在描述中添加一种堂而皇之的、更深刻的意义的企图,以为它知道这种意义是不正当的。艺术作品象征着智慧的一种悲剧,但它只是间接地证明了这种悲剧。”⑤[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第115页,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劳马的小说就是叙事的“肉体”消化了“哲学”取得的胜利,是小说叙事的胜利。因而,其小说的哲学意蕴并不是“在描述中添加一种堂而皇之的、更深刻的意义”。劳马多写短篇小说,其哲理气质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片段即生活的截面里弥漫开来,颇有隽永之味。他的写作吸收了西方文学资源。比如拉伯雷《巨人传》的狂欢传统(劳马的写过一个剧本《巴赫金的狂欢》,对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独具体味)。劳马小说中引人瞩目的“哲学”与“傻子”的对立构造可能就来源于此。“傻子”与生活和时代的有效疏离,边缘的位置,反讽性的言行,使自己获得了澄明之境。相反,在劳马的小说中,“哲学”是通过非哲学,甚至反哲学而显现出自身的。在劳马的一部分小说里,主人公直接设置为“哲学”或“哲学教授”。《哲学》里杜教授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堂哲学课似乎大彻大悟地对他的那些不听课、对哲学无动于衷甚至反感的学生说“只有傻瓜和笨蛋才学哲学,因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聪明人本来就很聪明了,不需要再学它。笨蛋想变得聪明才需要学习哲学”。被哲学搞得一生既充实又空虚的退休教授语出惊人。在另一中篇小说《烦》里,出租车司机小葛问哲学教授沙胡什么是哲学,沙胡苦恼于不能准确地解释哲学,倒是出租车司机干脆利落地为哲学下了个定义:“干什么都是为了活着,就像我开出租一样,就是为了挣口饭吃。哲学就是你的出租车,而我的出租车就相当于你的哲学,都差不多!”非哲学、反哲学首先通过把“哲学”、“哲学教授”降格、降智达至的。这两篇小说里哲学几乎把两位教授折磨成了“神经病”,使其成为一种小丑式的存在。
哲学在物质主义时代遭到了嘲弄、降格。用小说人物哲学教授沙胡的话说,“时代变了。一个浅薄、势利的时代终于无法阻挡地横在他的面前。思想性的东西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藏身之处”。①劳马:《非常采访》,第2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普通人视哲学为怪言怪语,为疯话、废话和梦话的大杂烩,大而无当,玄而又玄,不着边际。而沙胡的学生则普遍认为哲学教授“有胡言乱语的特权,而听不懂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能》里,“我”作为唯一考上大学、学哲学的人,因为不会给村子里的一头老母猪治病,偶像形象彻底在乡亲们心中坍塌,村里流行的最令人捧腹的笑话就是“我”不会给猪治病的故事。生活是琐碎的、具体的,哲学是抽象的,诚如斯宾诺莎的名言:“狗”的概念是不叫的。劳马小说里的哲学家们不懂实务,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成了“哲学型傻瓜”(敬文东语)。“哲学”被颠倒了。不过,“一切在荒谬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的生命都需要某种深刻而持久的思想用以使自己富于生气,否则,它们就不能继续下去”。②[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第111页,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在劳马小说中,承担“深刻而持久的思想”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傻子。
傻子形象是劳马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的令人瞩目的人物系列。在当代文学中,塑造过傻子形象的作家很多,但都没有如劳马这般自觉,成系列,蔚为大观。在劳马的“约克纳帕塔法”——葫芦镇里,“几乎每家都至少有一个傻子,只要一家的孩子超过三个,其中必有一个下雨的时候不知道往屋里跑”。(《抹布》)在中篇小说《伯婆魔佛》里,哲学教授伊百援引了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来描述和理解自己的家乡葫芦镇,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在”,一个“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的在”。葫芦镇的乡亲肯定无法弄明白这句缠舌头的晦涩呓语,但伊教授知道他的大哥伊十能明白,因为伊十是一个标准的傻子。这一描写又出现在《抹布》结尾(稍有变化)。劳马两个重要的中篇小说富有意味地重复了同一情节,暗示了作家安置的玄机。罗兰•巴尔特提醒过我们,即使“一个词语可能只在整部作品里出现一次,但借助于一定数量的转换,可以确定其为具有结构功能的事实,它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③罗兰•巴尔特: 《批评与真实》,第 66 页,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巴尔特的提醒让读者有理由认为“傻子”才是劳马小说“哲学”的认识装置,它是结构性的。
伊家兄弟在长篇小说《哎嗨哟》延续了中篇的角色分配,伊十、伊百、伊万,一个是傻子,一个是哲学教授,一个做官。伊百、伊万与主人公成功的商人吴超然作为知识分子、官员和商人,他们的命运和轨迹在当代史与当代小说中都被判定了,这是人物所处位置和作家书写“改革史”决定的。而傻子伊十却在小说里氤氲着智慧的光晕,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抛掷硬币的正反面,最终得出正反面概率差不多的结论,极具象征性。傻子伊十才是《哎嗨哟》的“哲学”探测器。中篇小说《傻笑》中那个为自己向校长求“傻子证明”,“跨世纪的大傻瓜”的东方优,成为共和国几十年历史的镜子,以他的“傻”与历史形成了对照记,然而东方优才真正是“越活越明白”,小说结尾,东方优俨然是阿凡提似的智者。傻子伊十和东方优在当代史中都不是活的“最好”的,却是活的“最多”的,也即活的丰富。因为他们的“傻”,使他们与时代产生了一种可贵的疏离感,使他们最具灵活性,获得了意外的自由,能够在小说叙述的当代史中闪转腾挪,探测出伊百、伊万、吴超然和其他人之外别样的可能。
巴赫金说,傻是反过来的明智,反过来的真理。劳马小说里的傻子对正统价值、意义和规定的不理解和背离,反衬出时代、历史的荒诞。“在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中,愚蠢就是聪明,聪明就是愚蠢,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④敬文东:《小说、哲学与二人转》,《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也就是说,在劳马的小说中,“哲学”是通过非哲学和反哲学而显现出自身的。“哲学”与“傻子”被颠倒了。这是劳马式的“哲学辩证法”或“傻子辩证法”。
二、荒诞与小说的寓言性
某一天,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突如其来地让我把枪交由他们保管。“什么枪?开玩笑”,“我”一个普通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有枪?“我”自然是惊诧无比,莫名其妙,又异常恼火。
“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抢,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你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给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的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这是劳马令人击节的短篇小说《我有一支枪》的开头部分。“我”认为自己没有枪,中校却根据规定认定“我”有一支需要上交保管的手枪。“我”百口莫辩,纠缠不清,由此陷入一种“鬼打墙”式的情境中,最终被签枪支保管委托书,缴纳枪支保管费,补交、预交费用,“无中生有”地成了一位有枪的人。《我有一支枪》在劳马小说中极具象征性,它呈现出了其小说的另一副面孔:荒诞世界的呈现与劳马小说的寓言性。“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①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18页,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二十世纪以来,小说的哲学化趋势明显,杰出的小说往往具有一种寓言性质,作为一种现代性书写,内蕴深远的哲学与隐喻意义。卡夫卡的小说就是其中的典范。劳马小说的哲学气质还体现在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荒诞呈现与寓言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一支枪》是作家为当代人重写的一个故事。它直指现代生活、现代体制对人的摆布、异化和扭曲。《我有一支枪》中“鬼打墙”式的,或者说“迷宫”式的情境成为这部分寓言化小说一个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对这种“鬼打墙”、迷宫式情境的呈现是对当代生活的一个精妙隐喻。人深陷其中,不能自主,无以自拔,犹如西绪弗斯神话中命运对西绪弗斯的判决,他必须忍受着永无止尽的苦役,毫无意义的行为。另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活死人》再现了这一情境结构。“我”被医院认定失去了生命体征,已经死亡。但“我”活过来了。而医院的新闻发言人确认为死亡结论是专业医务人员反复检查鉴定做出的,程序严谨,客观审慎,不会出任何差错。死亡结论不可更改。无论“我”如何辩解,始终得不到积极的回应,“我”活了下来,却成了活死人。在这两篇小说里,人碰触到了现代官僚制度和科层体制这面坚硬的围墙,又似乎陷入了“无物之阵”的生存处境里,欲摆脱而不能。
现代日常生活少了波澜起伏的戏剧性,多了几乎“无事的悲剧”,多了日常生活的悲欢和荒诞。在颇有后现代风味的《脚不沾地的人》里,金波坐飞机上了瘾,对飞机产生了依赖,不管有事没事总喜欢在飞机上待着,不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坐飞机成了生活目的,他成了一个脚不沾地的人。金波就是中国版的“树上的男爵”。《演员》里演了一辈子的老演员,演尽了形形色色的角色和惟妙惟肖的人生百态,却一辈子都没有扮演好自我这个最重要的角色:“我演了一辈子别人,却不会演我自己”。他丧失了自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表演者”。小说以精湛的叙事触及了后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消解,对个人主体被构成之虚假性的批判,具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在“我”与“世界”的关系里,扮演各种角色的社会之我已经谋杀了“本真之我”,真我在象征性秩序里走上了彻底异化的歧途。这可能是现代人避无可避的荒诞处境。这些小说想象大胆奇诡,没有遵循现实的逻辑,而是以想象的逻辑推进情节,甚至夸张、变形,精细的情节是日常化、世俗化的,却溢出了日常和世俗,具有某种迷人的荒诞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荒诞性。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当代中国生活的一个个寓言。作为同道者的作家阎连科敏锐地指出:“劳马在偏于故事的小说创作中,把荒诞神奇无痕地化为了小说和生活的日常。而在偏于人物的小说叙述中,他又奇妙地把日常转化为荒诞,转化为某种精神荒诞的怪力对人的左右。”“他的写作有了荒诞在日常中的力量,有了今天中国政治、现实、社会在日常世界中对人的投射,以及人在日常现实中即便荒诞、荒唐、荒谬也不被动、不妥协的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的扭曲和人自身与现实生存的抗争。”①阎连科:《劳马“幽锐体”的短圣追求》,林建法主编:《说劳马》,第145页。
阎连科的洞见提示我们把观察的视线落在劳马对现实处境、人在当代生活中存在的理解和处理上,有助于抵达劳马小说的内部。一旦进入劳马小说的内部,读者会惊叹其因寓言性形成的内部空间之大,与小说篇幅之小形成惊人的反差。可能一篇几千字,甚至几百字的小说,却能“超越题材和主题本身,而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味,文字极具氛围感,不动声色,但意蕴尽在其中”。②劳马、梁鸿:《“笑”的文学传统与轻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小说内部的空间感是由其所触及的历史深度和所营造的悠远精神状态支撑起来的。在劳马新近创作的一组“小小说”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无语的荣耀》描绘老教授在领奖台上一句噩梦般的呓语这一瞬间,便泄漏出了历史暴力对人心灵、精神造成的伤害,日久弥深,穿越时间,成为永恒的创伤点。这是一篇精致的“伤痕小说”,具有历史的深度。《走遍世界》以反讽性的笔法写主人公老朱生活中足不出户,拘囿于一室,却热衷于在室内地板上铺就的世界地图上悠然“远游”,与地图纸面上的缩地术相反,在他虚拟的扩地术里自得其乐。所谓“有一种旅游叫足不出户,有一种交往叫一人独处”。小说的命意并不显豁,却反而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既可以理解为对现代人“精神胜利法”的遗传症的反讽;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人尽管身处逼仄枯索的生活空间,却不丧失追寻渺远时空的激情;甚至还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一篇元小说。主人公在世界地图上的精神远游是作家在短篇小说这么一个篇幅有限的体裁里探索无限意义内容的隐喻。《走遍世界》具有一种阐释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劳马对人物对自身所处时代和生活的反应的精准把握,以极为简省的笔墨对人物、情境复杂状态的描绘能力。
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42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劳马的小说没有陷入现实的泥塘,就像卡夫卡对现代人困境的探索,劳马的写作同样是对当代中国人存在处境的勘探。不过卡夫卡以一种沉重内敛的方式来表达荒诞,而劳马则一种讽喻、喜剧的方式来呈现人的荒诞处境。
尽管劳马小说多以喜剧性的形式呈现出来,但不可不察:“劳马主张‘笑的哲学,说明他发现现实中值得笑的东西太少;他喜欢在作品表面拼贴喜剧的标签,证明他想努力永远忘掉那内心的伤痛。’”。④程光炜:《读劳马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在一次交谈中,劳马说起他小说中的“笑”,他认为经历了苦难才会发笑。某种意义上,“笑”是对荒诞的反抗,《傻笑》里的东方优“那张夸张的大脸上挂着四季不变的笑意,以笑报恨,以笑报骂,甚至以笑报打”。面对一个荒诞的时代,应该如何对待荒谬呢?加缪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类:生理上的自杀,哲学上的自杀,努力抗争。东方优选择了以笑抗争荒诞的处境。他领受了时代加给他的一切,却并不混沌地“赖活”着,而是清醒地自命“傻子”,以“傻笑”的方式不屈不挠地抗争接踵而来的苦难与荒诞,因此他的命运在他自己的手中握着。东方优是劳马笔下的西绪弗斯。
三、症候式写作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时,提出了“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将拉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到对文本的阅读当中,认为一个文本不仅仅只说它看似要说的东西,它的‘显在话语’(explicit discourse)背后必然有‘无声话语’(silent discourse)的存在,就像无意识的症候深藏其后一样”。“‘症候式阅读’发现了文本的可疑性和非透明性,使得阅读行为本身增加了复杂性和多义性”。因为“症候式阅读”的巨大生产性,它被文学批评所青睐,批评家们在充满多义性的文学文本中查看“断裂和沉默”,以便能提供心理的或政治的无意识。①见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第67-7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劳马的小说写作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具有某种相通之处。那就是能够穿透人物/文本的非透明性,发现隐藏其后的疾病表征,也即症候。作家劳马就像一位医生一样,耐心而充满兴趣地勘探其笔下人物的症候,可见与不可见的潜在、微妙的关系。因而,作为对“症候式阅读”的挪借,姑且可以把劳马的小说写作称之为“症候式写作”。
在以这种眼光来阅读劳马小说之后,笔者突然惊异地发现,其小说所塑造的“病人”是如此之多。尤其是许多中短篇小说,几乎可视之为一份份病症单或病症报告。这些病症报告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理性病症(究其根本乃是由心理疾病引起的),一类是心理性病症(或文化性病症)。前者如《咳嗽》:苦熬了几十年的老莫在评上教授之前,经常废寝忘食,忍气吞声,胸闷腹胀。得知评审结果后则需要吞服两颗速效救心丸。在评上教授后,讲课和发言前,总是礼节性地咳几声,透着沉稳和自信,咳嗽却逐渐不可控制,最终检查出了晚期肺癌。《三笑》里的丁丑不会笑,患了“面部肌肉僵硬症”,病因是他在小时候、中学以及政府机关里因为“不合时宜”地笑受到了来自爸爸、老师和领导的创伤。后者则如《非常采访》,此中篇简直就可以另外命名为《一个女妄想症患者的病症报告》。一个精神病的妄想症患者(读者会联想起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凤姐等等)在“看”与“被看”中立体呈现在读者的阅读中,“看”与“被看”者都陷入一种病态中。《遗忘》里,“他”患上了“重度偏执型失忆症”,凡是涉及个人的事情,他丝毫没有记忆,但可以其极其清晰记得国际、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大事,以至于连说梦话都是这些内容。与《遗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制服》,主人公孙子孝也是偏执型人格,他只能穿各种不同的制服,只有穿上制服,成为组织的人,才会让他安心。这两篇小说塑造了肉体被驯服、被体制化,因规训而丧失了自我的生动形象。
社会学认为,“日常互动依赖于我们通过言语表达的内容以及通过多种形式的非言语交流——借助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行为举止等而进行的信息和意义的交换——所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微妙关系”。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第76页,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因而,无论是语言层面还是非语言层面,一个人都会暴露出无意识的症候表现。短篇小说《夙愿》里的老师,逢人便讲“我不愿意当官,我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课堂上,开会时,只要有机会他就重复他已经讲过上百遍的话题。整篇小说充斥着老师重复的话语“我不愿意当官,我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然而就在小说的结尾,师母私下问老师治丧小组组长的职务能否由死者担任。重复的话语只是老师意识层面的展示,而老师去世前的夙愿才是其无意识的泄漏。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虚伪人物形象在极短的篇幅里跃然纸上。小说让人忍俊不禁,又直刺人心。劳马小说题材广泛,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多变,呈现了短小说丰沛的表现力和迤逦多姿的可能性。劳马出色地呈现了一种当代生活的 “精神疾病现象学”或者说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疾病心灵史”,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恢弘气象。
这些病症的发现,仰赖作家娴熟的症候式“阅读”和写作。它善于捕捉、打开隐藏着的、被遮蔽的、被曲解的、被无视和忽略的细节和幽微、断裂和空白,它要求观察者时刻保持敏感。借用劳马的一篇短篇小说名,或庶几近之:《潜台词》。“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它指的是不明说的言外之意。俗话讲‘敲锣听声,说话听音’,就是让你去用心体会弦外之音,话外之音”;“潜台词属于暗示行为之一种,比使眼色还隐蔽,相对于黑夜中的眉目传情,它更像是美女戴着面纱,又半抱琵琶,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所以需要听者和观者用心揣摩”。换而言之,一种症候式的写作要求作家具有解读“潜台词”的能力,那就是绕开表层的、显在的、正常的、可见的部分,而力图揭示出人物无意识深层的、潜在的、空白的、沉默的、不可见部分,以反常的、断裂的、疑难的为突破口,找到症候点,直指病灶,求得一种直击人心、一针见血的效果。对此,劳马极为自觉地实践着症候式写作: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部百科全书的话,那么,我的每一篇小说就像一个词条,把生活现象与生活现象背后的东西呈现出来,尝试把大题材、大场景、大事件浓缩到狭窄的空间里面。我就是为人生这部辞书做注脚的,写词条的。我是用“关键词”的方式来提炼的,不见得从头说起。通过一个小事件、小场景,通过段落来展示整体。直接,一步到位,就像中医的针灸,找准穴位,直接进入。①劳马、梁鸿:《“笑”的文学传统与轻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劳马的创作开始于一九九〇年代之初的转型时代,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一切汹涌而来,政治的羁绊尚未解除,而市场和商业又给人带来新的压力。在这样日趋复杂化的时代背景里,劳马和其他优秀的中国作家一样都在用文学来发现“病症”,寻找“病症”的起源。症候式写作就是劳马给出的当代中国“病理学”报告。劳马自述中“中医针灸”的医学话语,无意间为我们理解其症候式写作打开了一重视野。中医善于由表及里,发现病因与病机。症候式写作如同中医一般的确有一种由小见大,由表及里、针灸点穴般的能力,找出症候背后的病因与病机。
在劳马的诸多小说里,坚硬的体制、环境与幽黯的人性都获得了作家医生般的长久注视。中国新文学自鲁迅“弃医从文”以来,作家/医生已经获得了稳定的隐喻关系。文学在修辞以及隐喻的意义上借用医学和卫生话语来为国家、民族、国民等病态的有机体施以疗救之术,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久远的传统。在阅读劳马小说时,的确能感受到其小说背后有一双医生敏感而深沉的眼睛。劳马的症候式写作也必须放置在一个这样的文学史视野里才可能获得其应有的位置,得到更好的理解。当然在这样一个传统里,还包括了鲁迅对自己作家/医生身份一直抱持的怀疑态度与不断交缠在疗救者和病人之间的犹疑不决,手术刀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传统。背靠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劳马的症候式写作中,同样看不到绝对自信的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作家的隐在背后,有着很强的分寸感。在中医针灸扎进穴位所引起痛感的同时,读者没有感受到高傲、冷漠和厌恶,相反,是“笑”,是某种善意与温情,进而有所反思。劳马小说的“笑”果某种程度上也是症候式写作带来。作家所发现所书写的人物无意识层面与意识层面发生了严重错位,然而,人物本身并不知道,他们的语言、行为只是无意识地被套上了枷锁,而作家则佯装不知。这就给阅读带来了一种喜剧性、反讽性的效果。喜剧、反讽的效果主要来自小说人物的言行或者言与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落差。
乐绍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〇一四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