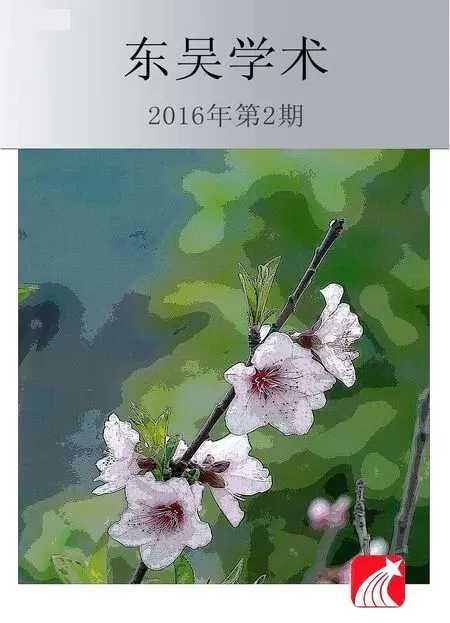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内在空间”的诗意漂移
2016-03-19李森
李 森
世界文学
“内在空间”的诗意漂移
李森
本文选译了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的组诗《内在空间》(The Inner Space)中的部分作品,并以语言漂移说的理论视角对具体作品中包涵的诗学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了作为心灵结构的“内在空间”生成诗意的有效途径。埃斯普马克诗意的“内在空间”,既是心灵结构的空间、语言结构的空间和世-界结构的空间诸多因缘的“凝聚”,也是佛法之所谓“蕴”的生成。诗是横空出世的“蕴”,而非其他,即便是各种强势文化的观念,也在诗意生成的时刻被化解。文章通过学理辨白,将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诗歌列入当代世界顶级诗歌创造的范畴。
谢尔•埃斯普马克;《内在空间》;蕴;凝聚;语言漂移说;诗意生成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初,我在黄山与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①谢尔•埃斯普马克,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生,瑞典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瑞典学院院士。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于一九八七至二○○四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至二○一二年,已出版诗集十一部;小说集八部,包括《失忆的年代》系列小说七部和《伏尔泰的旅程》;评论集七部,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等。相遇,并与之进行了一次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诸多事情的对话。谢尔作为一位诗人和作家,长期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且作为评审委员会主席主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十七年。他同时也是另一位伟大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的研究者,因之,我极力向谢尔推荐特朗斯特罗姆获奖。此刻,通过英文阅读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诗歌,感到非常亲切。埃斯普马克的组诗《内在空间》(The Inner Space,共一百首短诗)第一首第一句云:
There’s a haze as in the morning of time.
有一场雾像漂入时间的早晨
我将“in”翻译为“漂入”而不是“在”,是因为如果没有“早晨”,就没有“时间”。所谓时间,如此抽象。似乎人人都明白时间,但当人们要思考它时,它反而模糊不清,或者干脆溜走,或者遁入荒芜。这一点,我与奥古斯丁的体验相同。时间要变得具体可感,就必须变成“时间世”,即有万事万象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感觉系统中的绵延。诗,是时间的起源,是时间的一种表象。当然,它同时也是空间的起源,是空间表象的生发。是所谓“世界”的现身。依梵语义,“世”即时间(万物迁流),“界”即空间(万物存在的方位)。在我看来,世界(时空)并非凝固不变、按部就班的表象或本质,恰恰相反,它是变化中的“凝聚”。依佛法言,我谓之凝聚者,即是“蕴”,如五蕴之色、受、想、行、识。在我看来,“蕴”亦是漂移着的,它不断幻化生成具体的世界。因此,所谓世界,并非凝固的名词或概念,而是动词或蕴的漂移。故而,有时我将作为动词的世界书写为“世-界”。“世界”是名词,起源于外在空间,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说法;“世-界”是动词,起源于“内在空间”,迁流漂移为具体的世-界,这是语言漂移说①语言漂移说,是本文作者李森创立的一种诗学。这种诗学认为,诗、美、艺术都没有凝固不变的本质,也不存在凝固不变的表象,更没有凝固不变的艺术语言系统;诗意在语言漂移中生成,而生成也是没有目的的生成过程;诗意的生成过程在凝聚与崩溃、开始与终了碰撞的时刻。语言漂移说的重要概念包括“凝聚”、“暂住”等。的说法。“有一场雾像漂入时间的早晨”,“一场雾”生成了“早晨”,“早晨”生成了时间。此处的时间即是时空,是迁流而“暂住”的世-界。既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时间”起源于“内在空间”,那么,这个“内在空间”,当然是一个主体的“内在空间”。换一种说法,主体是“内在空间”的界限,也是世-界的界限。埃斯普马克的“时间”从某种抽象的时间中漂移而出,呈现出世-界的镜像。事实上,“内在空间”既是主体的心灵结构,也是个人的心灵结构。所谓主体,也是普遍性的一个范畴。普遍性的主体是无法自我呈现的,除非它一次又一次地与个体相遇。譬如诗意的生成。主体在寻找个体的途中与某个假设的诗意摩擦,以期生成个体的诗意:
Over the strait a freezing text travels
在海峡之上,一个冰凉的文本漂移
从“一场雾”到“早晨”,再到“时间”的事象生成,是《内在空间》组诗的第一次诗意假设。紧接着,又是“在海峡之上”和“冰凉的文本”摩擦着那个假设的诗意的“漂移”。这就是:
ripple by ripple.
波纹连着波纹。
“波纹”是“冰凉的文本”的形象,“by”是“漂移”之状,亦是某种推动力。“波纹”和“冰凉的文本”之间,横亘着巨大的空白。“波纹”既可以喻“冰凉的文本”,也可以喻任何物事。可以生成此诗意,也可以生成彼诗意。诗意的期待,也是对“空白”的摩擦。万事万物只有作为空相,才能漂移起来。也就是说,实相是不能漂移的;只有语言可以漂移,而语言皆为空相,这是语言赖以运动的本真维度。谢尔•埃斯普马克深谙诗之道,即诗是“能指”对“能指”的推演,是空相之真的推演。诗将事象(色)的能指激活为动词。能指在诗的推动下寻找、呼唤能指,在空白中穿越。能指既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组,或是无数词和词组的链接与对观。能指的漂移(迁流、运动)是在一个推动力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个推动力即是诗意的假设或曰假设的诗意。也即是说,在诗歌的写作中,无论具体而有效的诗意是否生成,写作者都需要假设那个诗意的推动力。诗意之所以需要假设,不是因为本来就有一个本体的诗意,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本体的诗意存在。还是以佛法言之,所谓整体的、需要假设的那个诗意,其实是个空相。能指和所指既然都处于语言漂移的层面,因此,都是空相。《心经》云:“是故诸法空相。”
一位卓越的诗人,其总是深谙观念、概念不能显示自身、也无需显示自身的诗意真理。因为只有实相才能显示自身,而所谓实相,也是语言的假设。语言本身是空相,但可以假设实相的存在,以使诗意的漂移获得动力。谢尔•埃斯普马克诗中的“时间”和“文本”,在“波纹”的实相显现之后,接着在空白中寻找实相,以期继续飞翔(漂移):
What could be a heron
tests its wings and lifts. The promise of leaves in the treetops is fulfilled.
那可能是一只苍鹭
试试它的翅膀,飞起。树顶上的叶子实现了一个诺言。
于是,我们看见“一只苍鹭”、“树顶上的叶子”在生成“一个诺言”。这里的“诺言”,可以是任何虚相、任何空相,也可以是那个假设的诗意,是心灵结构之蕴的迁流。“诺言”作为蕴,需要凝聚为事象(能指)的开显,它才能显露。“诺言”显露的时刻,是它正在穿越巨大的心灵空白的时刻。在埃斯普马克的诗中,“诺言”仿佛是“我”在一个男人的躯体里复活:
And I rise slowly
out of the slumped man on the bench. It’s time to invent the world.
我从瘫倒在长椅上的男人里
慢慢地起身。
此时,是创造世界的时间。
世间本无本质或本体的诗意,但有死亡的诗意与复活的诗意。在巨大的空相(空白)之中,诗意的复活,即心灵结构的复活,也是诗意空相在实相里的复活,或反之,是诗意的实相在空相里的复活,是词语的能指在所指中或能指自身的复活。在《内在空间》的第七首诗里,诗意是被大理石的雕刻家雕刻出来的,“亚述石狮”(复活的实相诗意)、“穹顶”(实相诗意的界限)都被雕凿出来与假设的诗意摩擦,似乎发出轰鸣的声响。与此同时,各种事物都开始复活,以“创造世界的时间”:
The blackbird’s song is chiselled,tactile,and round it billows a foliage of stone.
黑画眉的歌声被雕凿出来,可以触摸,周围涌动着石头的叶簇。
而在《内在空间》的第三首里,“冥府入口倾泻出来的黑暗”与“一种哲学”、与伟大的女诗人萨福和她创造的诗意彼此生成为漂移的“蕴”之“簇”,穿过诗人埃斯普马克的心灵,以构建一颗具体的心灵及其他与人类精神史摩擦的诗意:
The darkness pouring from the entrance to Hades
compels a philosophy into being,
and the cliff that Sappho will jump from
entices the vertigo in her poems.
冥府入口倾泻出来的黑暗
迫使一种哲学存在,
而萨福将要跳离的悬崖
诱出她诗中恐高的眩晕。
这就是说,在心灵结构的“内在空间”里,不仅有事象能指的漂移,还有文化隐喻(所指)的漂移。一位杰出诗人既要使能指有效地生成可靠的诗意,又要有清洗或澄清隐喻的能力。在语言中,所有事物都渴望得到存在的证明,但不是所有证明都有效并能显现为具体的诗意。有的事物在语言中被命名,仿佛事物已经到达了语言之中,尽管那只是一个假相;有的事物显现为意识形态的凝聚,仿佛事物中真的隐含着意识形态隐喻,其实那不过是人类语言的白日梦呓与癫狂。当然,语言中一切空相和实相的漂移都是语言的决定,是语言漂移中不能不承载着的心灵体积或重量。
在《内在空间》组诗第三十三首中,“星期日”这个时间“轮转”着的“太阳日”里,事物的“复活”与基督的复活在诗意中同时生成。文化的隐喻在摩擦事物能指的过程中隐藏了自身。“雪”与“布道”、“声响”与“流淌”、“文本的红斑”与“基督的血”,诸如此类的物事视相和隐喻作为诗意碎片彼此化有,又稀释为无。“有”和“无”摩擦为虚相,获得一种“形而中”的平衡: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is Sunday:
weightless snow,a silent sermon.
The naked tree is lit-up with bullfinches.
The only sound in the world
is the rustle of chewed seeds
trickling down through the branches.
The text of the day is flecked with red
paler than Christ’s blood
and seed husks tumbling slowly,slowly. Death slackens his pace.
Still no commotion among the clouds.
在生命中间的这个星期日:
轻飘飘的雪,一场无声的布道。
光秃秃的树被红腹灰雀点亮。
世界上唯一的声响
是种子被咀嚼的沙沙声
从树枝间流淌下来。
白天的文本缀满红斑
颜色比基督的血稍淡
种子的壳慢慢地、慢慢地滚落。
死神放缓了他的脚步。
云层中仍然没有喧嚣。
从埃斯普马克的诗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无论语词的能指还是所指,无论观念的表达还是事物的隐喻,亦无论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是解构,诗意的漂移都是以碎片漂移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语言的决定。只有语言的碎片,才能在巨大的空白中摩擦着穿行,接受万物的召唤。换句话说,漂移的永远不可能是整体,而只能是碎片,只有语言碎片中才有鲜活的生命气息。那些处心积虑让“整体”(一,The One)言说的艺术,其结果只能是对观念的粗暴表达。像所有杰出的诗人一样,埃斯普马克亦懂得对“整体诗意”的拆分,让语言碎片在生成中成就诗意。正因为如此,“文本”和“基督的血”才以事物漂移着的音声形色显露出来。这种显露其实是“内在空间”(心灵结构)中的“震颤”。第九十三首云:
I feel how you think in me-a thrill
like moonlight speeding to me on water.
I reply with some definitions:
Your face is like a trembling reflection
in a bowl of water.
I want to carry it through the years
without spilling.
我感觉到你如是在我身体中思考——激动的震颤
犹如月光踏着水面向我奔来。
我用一些轮廓来回答:
你的脸像一碗水里
颤抖的倒影。
我想端着它穿过岁月
而不泼洒一滴。
诗人倾诉的对象“你”,也要化为语言的碎片才能在“身体中”被激活。碎片即形象,碎片的漂移即是对形象的诗意重构:“犹如月光踏着水面向我奔来。”那是一些“轮廓”,我们所能感悟的、所能看见的仅仅如此。埃斯普马克看见的“脸”,是“一碗水里颤抖的倒影”;他看见,“脸”和“倒影”被“端着”,完好无损地“穿过岁月”。这正是无意义虚相或空相的绽放之美,第一次“穿过”,就到达了“无限”这个穿越之途。他也让读者看见了那瞬间锃亮的“时间世”,那迷离碎片的闪烁。诚然,一切初生的语言碎片的显露,都在开始与终了的时刻。也就是说,伟大的诗意在作为碎片漂移的过程中,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是瞬间初生的无限。无限不是预设的,而是被语词运动撞击着的一种回响。任何心灵结构中被激活的事物,都在被这种回响召唤着去流浪。流浪是语言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
是的,远方的孤寂心灵,古往今来之缪斯的叩门之声,比如埃斯普马克,比如特朗斯特罗默,我看见了,我又一次看见,我总是看见:世-界那个巨大的空白里漂移着的事物那么冰凉,即便我们假设万斛天光去照亮它们,它们还是那样陌生,且越来越冰冷,似乎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陷入困境。这一困境正是伟大诗歌的困境,也是一次次美轮美奂之诗意初生的滥觞。纯粹的心灵惟初生的诗意可以拯救、可以浸润。一切人为的价值系统都可能在诗歌中漂移、且饥饿如缀满大树的知了般齐声轰鸣,可是,当伟大的初生诗意纯净如沙漠中的最后一汪水、空谷中的最后一枝花,那些人为的价值渗透、隐喻鼓噪,都与此等诗意无关。这是孤荒地漂移着的“世-界”本身的启迪。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即将搁笔时写道(T.6.41):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它们之所发生而发生;世界中不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它也会是无价值的。
如果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定处在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之外。因为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都是偶然的。
使它们成为非偶然的那种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因为如果在世界之中,它本身就是偶然的了。
它必定在世界之外。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02页,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无端的语言碎片在空白、空相、实相、无限诸多时空打钻,如天光在海面打钻。一切都是徒劳,但杰出的诗人让徒劳的一切如歌如诉。在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诗中,我感到“水”和“沙”彼此倾诉般的那种永远的隔阂,那种徒劳的清洗和摩擦。此时此刻,无论埃斯普马克还是我,当我们使用了“水”和“沙”两个形象的时候,所有的语词和它们追逐的事物,就开始在心灵结构中颤抖。颤抖也是无端的。的确,语词和事物因被天光照见而更加陌生。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它不断地用诗意证明存在的毫无意义。这就是说,词与物的存在作为“凝聚”或“蕴”,它们不得不在“内在空间”里生成,又不得不在崩溃的边缘坠入深渊,与此同时,诗人又不得不将它们打捞。打捞即是歌唱,歌声的一咏三叹里,有无穷无尽的悲戚,也有迷离的欢欣。以下是《内在空间》的最后一歌:
At last
after the harsh acids of the Baltic,
wave after wave after wave,
the singer’s head,washed up here
on the outermost strip of sand in Austre:
a bird-skull,almost weightless,
weathered white,with sand in the eyesockets
a well-tested insistence.
A skull that trembles,trembles
with suppressed song.
终了时刻
渡过波罗的海严酷的酸水,
波浪推着波浪之后,
歌手的头,被冲上这里
在奥斯特最远的一线沙滩上。
一个鸟的头骨,几乎没有重量,
岁月的白,眼眶的沙——
一种历经考验的执。
一个头骨,随着被压抑的歌谣
颤抖着,颤抖着。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燕庐
李森,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华文艺复兴研究小组组长、论坛主席。已在国内外出版《李森诗选》、《屋宇》、《中国风车》、《春荒》等诗集与《画布上的影子》、《荒诞而迷人的游戏》、《苍山夜话》、《动物世说》、《美学的谎言》等十六部著作,主编《新诗品——昆明芝加哥小组》诗刊和《复兴纪》丛刊。《他们》诗派成员。“漂移说”诗学流派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