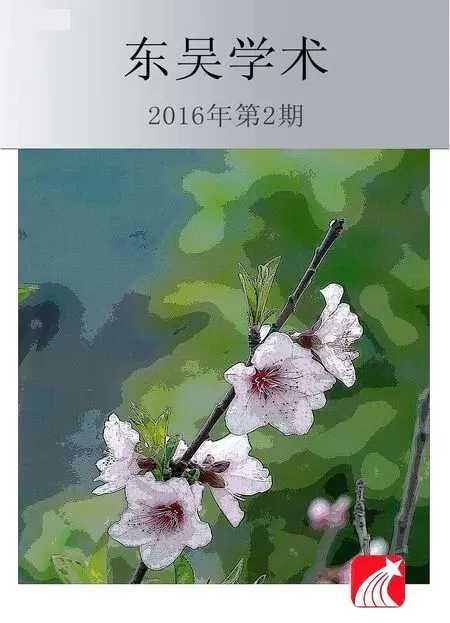国际现代主义和本土传统的会面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2016-03-19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Espmark瑞典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著 [瑞典]万 之 译
东吴讲堂
国际现代主义和本土传统的会面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 著 [瑞典]万之 译
许霆(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同学们,朋友们,下午好!我校东吴讲堂今天又开讲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东吴讲堂曾经来过多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并出任其中五院士组成的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十七年之久的院士,他的名字就是谢尔•埃斯普马克。让我们以掌声对埃斯普马克先生到东吴讲堂表示热烈欢迎!
谢尔•埃斯普马克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经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并且任院长,多次获得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埃斯普马克的多部著作都在中国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学人的比较熟悉的名人了,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我国出版的作品。他有一本诗集叫作《黑银河》,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本书是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叫作《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出版的时候书名改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当代瑞典诗歌各个出发点》也发表在我们学校《东吴学术》的二〇一三年第二期。埃斯普马克最为出名的代表作就是《失忆的年代》,它是由七个小长篇小说组成的一个系列,这本书用夸张近乎到极端的笔法,刻画了当今社会群体性的失忆现象,展示了现代人内心生活的一种焦虑。瑞典的《每日新闻》曾经把这一本书评为二战以后这个时代瑞典散文艺术中间最有批评说服力的艺术展示。中国很著名的一位作家阎连科读了这本著作以后说,原来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它给小说的写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这一次,埃斯普马克从瑞典到我们中国来,他十六号到上海参加了《失忆的年代》全集精装本的首发式和作品共享会,再赶过来的。我在前天晚上十一点多就收到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在那边人家作了一个采访,微信还长长的给我提供了很多在那边的信息,我想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今天在座的另一位先生,万之,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是今天埃斯普马克先生的翻译,他本名陈迈平,长期居住在瑞典的中文作家、翻译家,重要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文学评论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曾经担任《今天》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是《失忆的年代》的翻译者,曾经帮助我校《东吴学术》杂志编辑了瑞典文学专辑,以后《东吴学术》还将不断刊登他翻译的作品,万之向大家介绍说他出生在常熟,在虞山镇还有他的老宅,等会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刚才我们还聊到。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瑞典文学院,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刚刚宣布,二○一五年的瑞典文学翻译奖授予万之。下面我们抓紧时间,就把时间交给埃斯普马克和万之先生,大家欢迎。
在全球化的时代循环中,很多维护民族或者地区特性的呼声也在高涨。在欧洲,有很多国家合作,要保护欧洲的电影,对付来自好莱坞的巨大压力。法国甚至立法保护自己的语言,对抗来自英语的入侵。在瑞典,瑞典学院也为了瑞典语而多次出面干预,防止所谓的“域界损失”。
为了维护本土语言和文学而投入的这类努力,并非新鲜事。冰岛语很长时期就一直反对借用外来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在语言上的同仁都努力维护自己的语言,抵制西方的影响。文学研究者们也赞同语言纯洁派的看法,所以丹麦文学史家维尔赫尔姆•安德森认为,十九世纪丹麦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因为诗人和作家都努力摆脱外来影响,找回了本土的特色。到了晚近时期,在很多国家也能看到相当的反应。
维护自身语言的这样一种持续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部的尊敬,即使我们意识到本土语言也会因为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可以学习到其他语言的成熟和气魄。用相应的方式,我们可以赞赏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爱护,尤其是民族文化处于劣势要对抗强大的国际性潮流的时候。
但是,对本土文学的维护很可能忽视了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多少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刺激和本土元素或语言的会面中产生的。
在二十世纪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例证。英国诗人T.S.艾略特(一九四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具有突破性的诗歌创作是来自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的激励和来自本土十七世纪早期诗歌传统的会面。在早期的诗作《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艾略特让他的主人公抱怨,要说出“正是我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这个主人公梦想“神灯”有能力“在一个屏幕上用模式投射出神经”。
当普鲁弗洛克责怪人如何浪费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形式:“我用咖啡勺子量掉了我的生命”。这就是波德莱尔叫作“翻译灵魂”的艺术,把内在的事物用明显的形象展现出来。艾略特很熟悉的公式“客观的关联词”,就是指这种艺术。这种赋予内心事物可感知形象的方法,在伟大作品《荒原》里得到了最为人熟悉的表达:荒漠景色在作品里成为艾略特在其时代看到的内心枯竭不育的外在图像。
我在四十年前的一部研究著作里就说明了艾略特如何发展这种诗歌创作的方法:一方面是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启示,而另一方面是十七世纪早期英国的所谓玄学派诗人的影响。后者可以“就像感觉玫瑰香气一样直接感觉他们的思想”。艾略特的这种新艺术可以用视觉、嗅觉和手指尖的触觉去觉察到思想和情感。这是诗歌领域的革命——是发生在它把十七世纪本土传统重新唤醒而与法国十九世纪诗歌会面之际。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一九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用相同的富有成果的方式,把从法国超现实主义得到的启发和从墨西哥印第安人诗歌中得到的印象结合起来。而阿多尼斯(叙利亚出生的阿拉伯语诗人——中译者注)也用自己的方式在近代法国诗歌和古典阿拉伯语传统的会面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诗歌。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来说,福克纳富有幻想的方法和本土口头文学传统的交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的案例全都展示出,从外部来的刺激如何在一种本土传统中合法化了。
为了从瑞典文学中找到例证——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瑞•马丁松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当马丁松在多年当轮船锅炉工漂流过七大洋之后于一九二七年登岸生活时,他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对于传统瑞典诗歌也满怀信任。不过他当时笨拙的文学尝试说明他还是缺少一种表达他丰富经验的语言。后来他是从美国诗歌中得到解放自己的激励,包括卡尔•桑德堡和意象派诗歌的启发,这才发展出他自己需要的这种语言。
其结果就是他创作了非常接近中国古典诗歌的作品(意象派本身就可以追溯到中国诗歌的影响):
在海上我们感到春天或夏天只是一阵风。
漂流的佛罗里达水草有时在夏天开花,
而某个春夜里一只琵鹭朝着荷兰飞去。
仅用一两个富有内涵的细节,马丁松就再现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不同季节在大海上的呼吸是美国现代主义帮助了他,既能公正地使用自己丰富的素材,也能正确面对瑞典人的感性。
如果没有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真正的瑞典传统的会面,那就难以想象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我们就以他的一首诗歌为例,这首诗的开端是这样的:“十二月。瑞典是一条被拖上岸的,/憔悴不堪的船。它的桅杆斜立着/朝向黄昏的天空。”把风景描绘成一条拖上岸的船,这个图像贯穿了整首诗歌,于是风会抓住“橡木的全套桅杆”做一次穿越时代的航行中,还载着甲板下面的死者。
这种电影化的双重展现手法,是特朗斯特罗默从他同代人中不少诗人的共同老师拉格纳•图尔谢那里学到的。也是在图尔谢这里,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瑞典本土传统会面了。图尔谢通过不同途径和法国超现实主义产生联系,它们的写作方法打开了通往无意识的阀门,释放开了一种非常富有成果的荒诞图像的泛滥洪水。但是图尔谢同时又对有强烈视觉感的电影艺术很感兴趣,也对以一种社会结构为言说对象的形象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里又有晚近的瑞典诗歌。
这种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瑞典本土传统的会面中出现的诗歌一方面利用丰富的来自无意识的灵感启发,另一方面又紧紧抓住单一的图像,再用视觉连贯性来发展这种图像。就如在特朗斯特罗默这首诗中那样,可以成为有关一个延长了的隐喻的问题,其中两条线索可以平行发展,就好像是在电影的双重展示中那样的情况。
奇怪的是,马丁松和特朗斯特罗默都很快超过了他们的老师。
让我在此刻代表一下这代人中其他曾拜图尔谢为师学习诗歌人。我那首有关西安的兵马俑的诗歌——也有中文的翻译——正好也显示了这样一种两个事件的双重展示,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被固执地死死住的隐喻。一条线索是用土烧制的古代兵马俑,而另一条线索是今天的活生生的人。一个跪射的兵马俑拉紧了弓箭,对准一道近代战争的杀戮之光。
腐烂了弓和生了绿色铜锈的箭头属于很久远的古代,而放火烧杀的敌人和冒着气泡的烧伤伤口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首诗中的“我”是来自西安的一个兵马俑,能够认出朝他走来的现代士兵,“认出我们自己的风度”。这种双重视觉的结果就是一种“我”的感知,和一种既是古代又是现在的战争的感知。
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和我的诗歌之间,有一种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自由关联性和一种追求视觉性和串联的连贯性的瑞典式愿望。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国际影响和本土传统的会面,这样的诗歌就无从谈起。
相应情况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也是适用的。也许在莫言的创作里我们看得最为清楚。当人们试图描述莫言的创作特点时,已经有人指出过他和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相似性。不过,重要的是莫言和这两位外国文学大师的关系中具有独立性。莫言本人就公正地谈过一种对话的关系,是穿越了时代的一种谈话:“每当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时,就与他(福克纳)交谈一次”。
但是,对话不仅仅是建立在莫言所说的“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上。莫言也可以这样回敬说,“因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福克纳)之下”。①本文中引用的莫言语录引自莫言的文章《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莫言演讲集《小说在写我》,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以及《说说福克纳老头》,见中国豆瓣网。
福克纳能有什么可教中国同行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要点就是掌握打造一个自己的乡土,在这片乡土里,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遭遇可以发挥到几乎神奇的形式。相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设置了他的高密东北乡,而突出强调他的省份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点是和那个美国作家是不一样。
不过,关键性的区别在于莫言以一种和他的美国先驱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他的微观世界——“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能够概括这个国家二十世纪的历史。“一个中国的缩影”这种表述,其历史从义和团运动和抗日战争延伸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大饥荒和文化革命的迫害,一直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历史都捕捉进了围绕少数乡村人物的事件里。
问题在于要创造“广阔的视野”。而这种雄心不仅是美学上的,也是道德上的。莫言是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他把对作家的这样的要求表述为“站在人类的一边”。正是以这样有普遍意义的目的,他在自己的乡土风景中也利用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形特征——现实中高密县并没有的山脉、沙漠和沼泽。
但是,也正是在这样有普遍意义的目的中,他再现了事实上存在的历史。为了让现实可以显示“一个混乱的社会可以扭曲(人)的感情生活,让人失去理性”,作家必须“转换”历史的事实——而且在缺少事实的地方“创造出它们(事实)”。
这不仅展示了莫言利用了来自福克纳的激励来创造出了自己的一片中国天地。这也同时展示出,正是在来自福克纳的道路和地道中国经验的道路的交叉口出现了大师之作,没有这种交叉,这种杰作也就不可能产生。外来的激励是真相的一个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莫言自己也俏皮地减低他从福克纳那里学本事的意义。他说,“我感到福克纳像我的故乡那些老农一样,在用不耐烦的口吻教我如何给马驹子套上笼头”。福克纳可以教莫言一点本事,但笼头和马驹子还是莫言自己的。
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会面的问题上也可以作同样观察。莫言是在已经深入到《红高粱》的写作中时才读到《百年孤独》这部“独一无二”的长篇小说的。他那时就表示过遗憾,没有能在自己这部小说中用上那样一种写作手法。而在莫言随后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例子了。但是,就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不能匆忙下结论。莫言也完全有理由提到本土的故事传统对他的影响。比如他最初的文学阅读经验是《封神演义》,这部小说里充满超自然的生命体和想象奇幻的事件。
莫言每次可以借读这部书两小时,为此需要先给书的主人磨面。除了这样读书,莫言在自己成长年代和本土口头说书传统会面——并把这种会面叫作“用耳朵”读书。这种民间叙事文学也在蒲松龄的古典作品《聊斋志异》里占有重要地位,富有想象奇幻的组合和故事。比如在这部作品里没有人与兽之间的界限。莫言有一部小说中写到过女人为狐的情节,就属于这一说书传统。
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试试全面地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能给莫言提供什么,就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在使中国传说文学宝库合法成为参照文学这一点上具有最大的意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教别人魔幻现实主义,他只是对莫言说:你已经坐在这种文学财富之上,请使用它吧。当然,莫言需要这样的建议,把本土传说宝库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小说艺术中。
我们用这样观察的方式可以在一系列的案例中发现,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外来的道路和自己信赖的道路的交叉口处出现的。很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果没有这样的会面,就不可能创造出来。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看到年轻作家是通过和前辈大师的会面并通过这个大师向他阐明他已经拥有了他要锤炼的金属,才能找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外来的学识帮助他找到他自己,和他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
这种国际文学和本土传统的会面能教会我们的是,这种摸索的才能绝对不需要你成为一个模仿者。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激励帮助一种意义重大的创作主题找到本土自身的资源,也能找到自己的文学语言。在这样的会面场所,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当代的文学杰作。
许霆:这种国际文学的和本土传统的会面,这么多的例子能教会我们什么呢?这种摸索的才能,这样去接触国外的文学传统绝不是要你成为一个模仿者,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激励可以帮助一种意义重大的创作,让作家找到本土资源,也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在这样的会面的场所,在这样的会面交叉路口。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当代文学杰作的产生。总的来说,他的讲演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担心西方人的影响,那么样的恐怖、那么样的排斥。谢谢大家!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给同学们半小时的时间,让你们自由提问,当然最好首先举手。
其实埃斯普马克教授今天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全球视野的一个话题。也是目前国际前沿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话题,我昨天也看了这篇稿子,娓娓动听。举了大量的例子。历史上的,很近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人的例子。他代表了我们当代现代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家,特别是莫言的话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莫言受到国外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但是我今天听这个演讲,还有稿子,最大的感受就是莫言结合了他自己所接受的中国传统的文学的影响。比如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就结合了他读《聊斋志异》、读《封神演义》这样的一种感悟。你刚刚说,这些东西都融入了我们的作品,这样的模仿在小说里合法化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例子说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作家,走到世界的前沿去就需要两者很好的结合,而这个结合很重要的就是还要回到自己的那个点上去,回到自己的传统上去。
我还想说的就是今天的会面是非常精彩的,会面一直处在一种平等的而且就像埃斯普马克刚刚说到的,非常亲密的诗人关系。使用这样一个文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不是莫言叫他大叔吗,那莫言就是他侄子嘛。不是说我要对你怎么样,而是会面,然后成为了朋友。朋友之间见面,然后在见面过程中间把自己的原创性、独创性、独特性调动起来,然后创作出超越其他人的、高水准的作品。我听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些。
我抓紧说一些自己的感受,然后大家抓紧提问题。我看今天张维一直在拿话筒,下面我们请张维发言。
张维(诗人、虞山当代美术馆馆长):我是张维,下面我来读一段埃斯普马克的诗《语言死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和今天提问也有联系。我先朗读下这首诗,等下再问埃斯普马克是怎么理解的。
语言死去的时候
死者会跟着再死一次
那些潮湿的田埂
掀翻土地的词
装热咖啡的容器边角磨损的词
带着伤
对着窗和喧嚣的榆树
突然静思的词
黑暗中
手抖颤着寻找时
溢出暗香的词
给死者生命的词
鲜活的记忆
刚被历史刮掉
这么多影子在消散
被迫进入最终的流亡
没名没姓
五十四个字母组成的站牌
长满荒草,没人再读
你默默地忍着
只要这些死了第二次的词
留下泥土的苦涩
树冠的苍翠,溪流的清爽
脚就会突然跨过铁轨
没人知道风想让我们做什么
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
是的,我们听见树上的鸟鸣
但声音落向何处。
埃斯普马克:他其实涉及到一个瑞典语言学家所写的文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的小语种在消亡。每年有五千小语种在消亡,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这情况是非常让人忧郁的事情。之前这个文章配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大家都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发出声音,因为这种语言没人会。那篇文章其实就提到了《语言死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脑子就有了印象,当语言死去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人就又死了一次。这像个形象的种子一样,从这里发展出去。当然这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所以我又写了一首诗《当语言诞生时》,当语言诞生时东西存在说不出来,就像有些发芽的东西你又说不出来它在发芽,比如说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表达火,只知道能使我们温暖的东西,只能在尝试“火”(huo),只能这么读。一个小伙子想表达对一个女孩的爱慕,说不出来,他没有语言。他最后找到这个爱这个词时,可以带出来很多诗来。
万之: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小海。小海是位很重要的诗人。一九九〇年我在奥斯陆和北岛重版《今天》,第一期就发表了小海的一篇文章。
张宏:我是常熟理工学院二〇一二一年级的学生,我叫张宏,我想问一下埃斯普马克先生对于我们常熟理工大学生在文学创作上有没有一些寄语和希望?很多人都在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国籍的只有莫言,那是不是我们中国就可能没有了呢?
埃斯普马克: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沈从文先生没有去世的话,他会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事实上后来还有一个作家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是用中文写作的,其实我们评审的时候是不考虑政治,不考虑国籍,我们就是考虑到他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伟大作家,所以他特别提到。后来我们就开始读到很多莫言的作品,不光是已经发表的作品,而且还订购了十八、十九篇短篇小说,专门是给评审看的,他们还读了很多德语的、法语的、英语的,他们还读了西班牙语的,他们为了了解一个作家不是随随便便的听人家的评论,而是自己还要阅读,他们还要订购,他们觉得这是个好的作家,他们就给颁发了。他要我告诉你,入围名单上有没有中国国籍的作家,他说肯定有。文学的正教授和作家主席的,得过诺贝尔奖的人,这种人都有提名的权利,比如说提名二月一日结束,评委的工作就是删选出二百个作家,这二百个作家由十八个学院院士去讨论,经过这样第一轮、第二轮,二百个人删选到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再删选,比如今天他回去他就要提交五个人的名单,到底哪五个人的名单他也不知道,所以哪位中国作家入选这个都是要经过一轮轮删选才知道的。如果有人问我当初二百个名单中有没有中国人,肯定有啊,第一个长的名单上肯定有。因为中国文学真的很不错,中国文学的发展让我感到发展和吃惊,与八十年代初是不可以比较的。我刚刚补充那个大学生的寄语,埃斯普马克先生对想当作家的,那么他的建议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万之:我刚刚就是补充那个同学的问题,还没回答,他以为你们都想当作家,当作家的话他的建议只有读书读书再读书,但是你读书的时候不要觉得你是在拜师,只是在汲取营养,你是和作家会面不是磕头,我刚刚说他们并不是要当作家,他以为你们都要当作家,所以说作家就是要读。就是你不当作家,你要告诉他我要读书该读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被各种声音包围着,各种声音想对着我们说话,他说你要对这个声音作出回应,而在这个回应中你找到你自己的身影,他说实际上读者,也是完全里面的人物。有人认为很多小说是独白,他说实际上,这个独白最后成为对话,他是在对你们说话,当你们回应的时候,独白就成了对话,他说事实上,你们读到的小说,那么你们就参与创作,当读者在读的时候,我的创作才完成。我翻译《失忆的年代》,我自己就是这失忆年代的例证,我早上离开宾馆,居然把一箱书给忘了,所以我说我翻译这个失忆年代,失忆是真的,因为我身在这样一个社会,因为每天我太累,经常失忆,最后你们大学真的非常好,特地派人去上海我的酒店,把我的书给我拿回来,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一些学生,我建议今天提问的同学应该得到一本书。
许霆:看看大家有什么好讲的?
(某位外籍教师用英文提问)
万之:要是您能自己翻译成中文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么一个中国的大学读书,我想中文应该很好。我们去美国去英国学习的时候好像多要求我们懂当地语言,我希望我们学生,有外国学生来上我们的大学,如果能中文提问就非常好了。
(埃斯普马克回答)
万之:刚才埃斯普马克先生的回答意思是,文学的会面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它早就发生了,从很早的十四、十五世纪,一直到现在。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一直有这个方式,所以他认为这种文学的交叉呼应,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他还想补充的就是说中国文学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很多西方的诗歌是从中国的诗歌里汲取营养,我们刚刚提到的哈瑞•马丁松,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就非常感兴趣。这里我不妨多介绍一点,因为我也翻译过马丁松的一部长诗《阿尼阿拉号》,是一九五六年创作的,可以说是当代的一部现代史诗。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很前卫的问题,比如环保的问题,保护自然的问题,也涉及社会的问题,他觉得人类在地球上会生存不下去,人类将大规模向外星球移民。《阿尼阿拉号》其实就是一艘往外星移民的大型飞船,在太空中突然出了故障,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在清冷的太空向死亡飞去,最后走向死亡。马丁松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道家的那种对待自然态度,也许给我们提供一种好的可能性。所以这篇文章就叫作“良性可能”。我翻译以后在《江南》杂志上发表过。马丁松的意思就是说,丰富的中国文学也能给世界带来丰富影响。
埃斯普马克:我自己也受到过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我读过两本关于明末思想家李贽的著作。一本是法国人写的有关李贽的博士论文,还有一本是美国人写的有关李贽的传记。后来我就写过关于李贽的诗,题目《焚书》其实就是他的著作,还有《续焚书》,他就用焚书的意象写出一首诗来。刚才他也提到过我马上就要出版的一本书叫《缔造》,这里面有一首诗是关于中国的书法家颜真卿的。我直接的就受中国的影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我想说很对不起,埃斯托马克先生已经八十五岁了,他也是非常的累,所以说他如果回答的问题你们没有满足的话,我们想今天的讲演就到此结束。
许霆:埃斯普马克先生说的这个《失忆的年代》,有这么几句话在网上发的也蛮热的。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遗忘的时代,昨天你在那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也许不会记得,你前天晚上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当门打开的时候,你会想开门的是不是我的太太,而站在他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政治的丑闻只要逃出了舆论界的舆论四小时,就会被遗忘。埃斯普马克先生说这种失忆不仅局限于某个作家,这是一种全球性的通病。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年代,静静地来谈诗歌,来谈文学,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享受,我觉得埃斯普马克先生跟我们说了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学文学的、爱好文学的,都是有启发意义的。这部书七卷现在全都出齐了。我们非常高兴万之把这样一个大师的作品介绍到我们中国,一方面我们祝贺埃斯普马克的书完整地在我们这边出版,也祝贺万之先生获得了二〇一五年的翻译奖,我们非常感谢两位的讲演。我们请两位同学上来献花。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