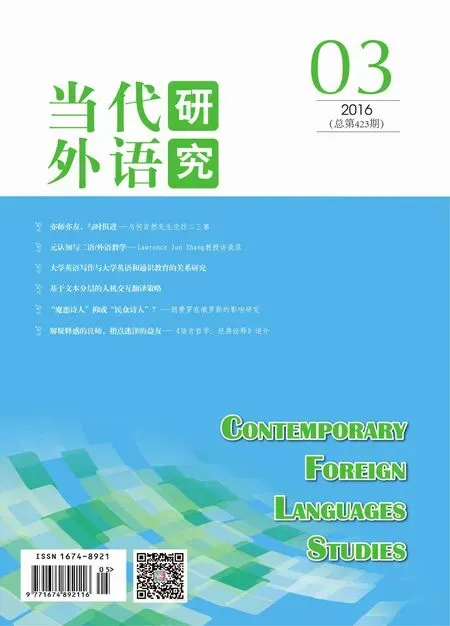亦师亦友,与时俱进
——与何自然先生交往二三事
2016-03-19俞东明
俞东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亦师亦友,与时俱进
——与何自然先生交往二三事
俞东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人生苦短,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要使这几十年的时光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却并非易事,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外在因素。我一直以为人生如遇两大幸事也就不枉此生了:一是求学时能遇到几位品学兼优的老师。我在南京大学念本科及硕士时,陈嘉、吕天石、王志刚、钱佼汝、郭秀梅、乐眉云和梁小平等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奠定了我一生为人为学的基础;在英国Lancaster大学留学时,Leech、Short、Thomas和Fairclough等名师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的学术趣味和取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时,何兆熊、侯维瑞、许余龙等老师的人格魅力、治学品格也同样鞭策着我不断前行。二是工作时遇到几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我在浙江大学工作13年,外语系的宋兆霖先生、原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任绍曾先生就是与我长期交往的忘年之交,他们的提携和帮助使我至今仍心存感激,真可谓亦师亦友,敦促我谦虚谨慎、与时俱进;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先生也是我人生前行道路上的一位良师益友、忘年之交。何自然先生与时俱进,他那自强不息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时刻提醒着吾辈不能有丝毫懈怠,应尽力做到“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我与何自然先生的交往可追溯到1986年上半年,记得当时我正在准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毕业前一年可以去上海和广州查阅资料和访谈调研。考虑到上海平时我常去,因此我就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选定中山大学和广外作为调研的学校。在广外我有幸访谈了桂诗春院长、李筱菊老师和何自然老师;在中山大学我访谈了王宗炎先生。我选这四位老师作为访谈对象是有所考虑的,因我硕士论文写的是英文专业教学的评估,采取的是一般系统论的视角;对王宗炎和李筱菊老师的访谈都是在两位老师各自家里进行的;对桂诗春老师的访谈是在他办公室进行的。三位老师对英语专业的教学等问题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回答,均使我受益匪浅;而何自然老师则约我在广外图书馆进行了长谈,谈话的内容除了有关英语专业的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外,何老师还向我介绍了英语界各个院校的特点和同行学者的研究特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外语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如数家珍,一一点评,使我茅塞顿开。我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界新人,但何自然老师一点没有架子,对我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几篇小书评也大加赞赏,这使我此后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良好习惯。至今回想起来,广州之行应该是我学术生涯迈出的第一步,其直接的成果即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顺利完成和发表在《外语界》和《浙大学报》等学刊上的系列论文。
十年后的1996年6月和7月,广州外国语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现代语言学暑期讲学班”,为期半个多月的研修课程涵盖了形式主义语言学范畴的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生成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其中功能主义范畴的语用学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但何自然老师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于1990~1991年间在Lancaster大学留学时主修文体学,但J.Thomas的语用学课程和何自然老师的语用学讲座可谓相得益彰,触发了我在1996年报名攻读语用学方向博士生的念头。当时在国内从事语用学的知名学者中有“二何”之说,即广外的何自然先生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先生。当时两位何先生都欢迎我报考他们的博士,并希望我学成之后留校工作。最后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原因我选择了上海,但对两位先生的知遇之恩我至今仍心存感激,并在学术上与两位先生保持着长期的交往和友谊。应该说,我在语用学、文体学及话语分析研究方面取得过的一些成绩应该归功于“二何”等前辈学者的无私教诲和提携,此外也得益于学术上的相互切磋和交锋。如1997年我发表了“语法歧义与语用模糊对比研究”的论文,何自然老师也先后发表了“浅论语用含糊”和“再论语用含糊”的论文。何自然老师的论文使我对这一论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引发了语用学同行的广泛关注。现在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用模糊与会话策略是冲突性话语中交际双方或多方广泛采用的语用策略,受制于交际和博弈的目的,可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论题。
2013年11月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建院十年庆典,何自然老师和我同时作为嘉宾赴该院讲学。令我欣喜不已的是何老师讲座的题目是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现状,而我讲座的题目是戏剧文体的语用研究。从何老师的报告可知: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语言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文史哲的跨界研究正成为新世纪学术研究的新常态。
从以上我与何自然先生交往的二三事的叙述中,我以为以何自然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的优良学术品格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 研究与世界同步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从引进开始。中国语用学学者在过去40年的努力使我国的语用学跟上了世界语用学研究的步伐,总体上虽说不上领先,但至少不算落伍。我们说我国以何自然为代表的语用学研究与世界同步至少有下列两层含义:从共时的角度看,以何自然、何兆熊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语用学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及时地将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引进到了国内。我们不会忘记正是何自然先生在1988年奉献了《语用学概论》,何兆熊在1989年出版了《语用学概要》,为国内高校的语用学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骨干教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何自然先生作为我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学者赴加拿大留学,何兆熊先生赴澳大利亚攻读硕士学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及时地将国外的语用学及话语分析等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成为国内高校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坚力量,保证了我国的语用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与世界同步。
从历时的角度看,何自然先生的语言研究也与世界同步。众所周知,由索绪尔创立的现代语言学已发展形成了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功能主义等学派;它们对语用学的发展均做出了贡献。何自然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在《现代外语》、《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语用学与外语教学方面的论文。我以为,上述极富原创性的论著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当下有关语言学研究中的形式化与非形式化方法的对立、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对立。同样,上述极富原创性的见解对回答“外文系如何办”和“语言学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等问题的回答也极富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2. 语言研究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发端于高校的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从事语用学研究的教师大多把语言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他们充分注意到自然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研究中往往以定性方法为主,以定量方法为辅,但随着新生代学者知识结构的变化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统计方法和定量方法在语用学研究中也已被广泛使用,许多研究成果做到了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统一。毋庸讳言,国内有学者主张成立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系或人文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系,彻底割裂语言与文学、文化的联系;国外文学界有的学者甚至不欢迎语言学、语用学插足于文体学和文学研究。何自然先生的语言思想与实践很好地回答了“两种文化”该如何相得益彰、优势互补的问题,尤其是回答了西方语言非“第二语言”而是“外语”的中国语境中如何从事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对纠正当下外语界存在的“唯科技主义”倾向,矫治“中西文化失语症”也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何自然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办好外文学科;应当看到现在的学科划分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
3. 语言文学互补、文史哲一体的知识结构
如上所述,我国外语界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研究的大多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出身,老一辈归国学者和第二代的部分归国学者在国外学的也是语言文学专业或语言学专业。正如1928年秋哈佛大学招生简章所言:“既要读语言,也要读文学。读语言课程,主要是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文学;读文学课程,更可以积累研究语言的资料。”(范存忠1986:5) 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学修养,有的是以文学研究为主,语用文体学研究为辅,如已故的王佐良先生、侯维瑞先生等,健在的胡文仲先生、钱佼汝先生等。改革开放后赴欧美澳加诸国留学归国的第二代语用文体学者均兼修语言学和文学课程,虽然以语言学课程为主,但大多有文学文本细读的丰富经历,保证了他们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学文本时得心应手,做到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统一。如何自然先生俄语、英语兼通的语言学论著,浙江大学的任绍曾教授和北京大学申丹教授近年来运用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诗歌和小说文本的深度阐释充分显现了语言文学互补知识结构的优势,值得当下在文学被边缘化的社会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语用学学者的学习和借鉴。在西方语言作为“外语”的中国语境下从事语言学研究,回归“文学和文化经典道路”,回归“文本语言事实”(hard linguistic evidence)也许是必由之路。何自然、许国璋等前辈学者的成功实践为新生代的学者树立了楷模。他们的成功之路也可帮助我们反思:现在的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当下外语界虽“群星灿烂”,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钱锺书这样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也许西方式的分科教育,可以培养专家,但不能培养“鸿儒”,更难造就大师。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过早定了位,缺乏深厚的中西文化学术积淀和功底。“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外文学科建设要上一个新台阶必须走古今会通、中西兼容、语言与文学并包之多元立体之路。“守正创新”才能面对整个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的挑战,真正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
4. 语用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如前所述,何自然先生的语用学研究始终与现代语言学发展进程同步,既注重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理论的研究,又避免了将语用学作为 “rich men’s game”。他在1988年主编的《语用学概论》中就将语用学的任务定位为:(1)为外语教学服务;(2)为语言学理论提供一个应用基地;(3)为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一种方法。不言而喻,何自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语用学与外语教学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更是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其研究成果对提高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很好的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5. 语言研究中克服“两张皮”现象的践行者
长期以来,我国语言研究队伍中存在着外语界与汉语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吕叔湘先生生前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张皮”现象。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生前也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何自然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则很好地克服了上述“两张皮”现象。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在中西结合和完善知识结构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真正做到了“英汉语兼修,学贯中外”。何自然先生推出的很多论文和专著充分显示了我国老一辈外语界学者对祖国的语言和文化不但没有隔膜,而是具有“学贯中西”、“汉语和外语兼通”的优势,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找到了汉语研究传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徐通锵2008),为我们树立了仿效的楷模,其研究的视角超越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其使用的语料也是“汉外兼用”、“古今兼用”,显现了深厚的外语和汉语的功力,完全避免了“外语界学人较多倾向于空讲、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不太善于结合汉语的实际,汉语界学人较多倾向于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一概不闻不问”(王菊泉2011:190)这一“两张皮”现象。
何自然先生的学术历程表明:汉语界和外语界学者之学术创新目标之实现应当有赖于多追寻越界研究之乐趣,多进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之越界、外语与汉语研究之越界、语用研究与话语分析、文体学研究之越界。
参考文献
范存忠. 1986. 英国文学史提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菊泉. 2011. 什么是对比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徐通锵. 2008. 汉语学本位语法导志[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丽)
作者简介:俞东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话语文体学。电子邮箱:yudongming011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