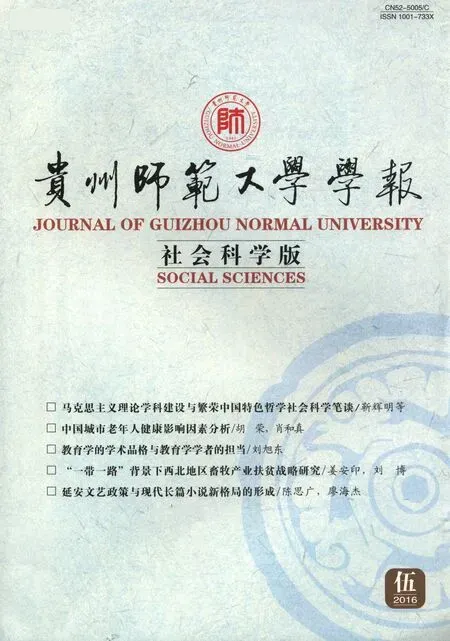中国新诗里的节日体验*
2016-03-19陈祖君
陈祖君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新诗里的节日体验*
陈祖君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中国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是不容漠视、无法弃绝的巨大存在。中国新诗实践留给中国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的诗行不可忽略。胡适的《除夕》显示新文化先驱者在借用蕴含传统文化的重要时间,闻一多的《忆菊》表明文化怀乡者在异乡使用另类时间,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揭示革命胜利者在构造新的时间,李瑛的《端阳》和《清明》显示文化寻根者在寻索久远的时间。对节日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新诗接近节日的几条路径和节日进入中国新诗的几种可能。
中国新诗;节日;体验
一
说到节日,绝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这样一些传统节日,而新诗标举的是新文化的“新”。传统节日的“传统”和新诗的“新”之间存在某种对立,所以新诗和传统节日之间似乎关联不大,从胡适和郭沫若等开始的整个新诗实践留给中国传统节日的诗行似乎不多,中国新诗中的节日体验看来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这里可能的质疑是,中国新诗诗人是否把节日作为感受和体验的对象?关于节日的感受和体验在整个新诗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是否能构成一个话题?
中国古典诗歌中众多和节日相关的诗歌显示,把节日尤其是传统节日作为感受和体验的重要对象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从中国最为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即可寻索到节庆的踪迹。法国著名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诗经》研究专著中发现,《诗经》里好多诗歌是春秋节庆的神圣情感的产物,表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带有仪式起源的印记。这些诗歌揭示出乡村节庆的存在,中国农民生活和两性关系具有的节奏性在其中得以显现。他发现,“这些歌谣让我们确实能够确定农业节庆的意义,确定季节仪式的功能,并由此理解社会实在本身是如何向前发展的。”[1]《诗经》之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的诗歌创作,与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中,屈原之于端午节、陶渊明之于重阳节更是具有某种源始性和标志性的意义。节日和诗歌之间的联系,在中国诗歌(包括字数长短不一、被同时称为长短句的词)创作趋于鼎盛的唐宋时期即表现得非常密切。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甫的《丽人行》、杜牧的《清明》、韩翃的《寒食》、王安石的《元日》、苏轼的《水调歌头》、陆游的《游山西村》、李清照的《永遇乐》、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与传统节日有关的诗歌创作。在元、明、清三代,关于节日的体验仍频繁地出现在诗人们的作品中。
中国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传统节日在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冷落,新诗创作领域也不例外。一方面,传统节日在中国新诗里受到冷落与五四以来反叛传统文化的策略有关。节日是特定共同体经过长时间生活确认的有重要意义的固定日子,它拥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确认的是此一时间而非彼一时间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国新诗产生于反叛传统文化而认同外来西方现代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很正常地会有意无意地以冷淡乃至批判的态度面对积淀了数千年古老文明的传统节日。另一方面,与20世纪中国采纳新的计年时间体系不无关系。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采取干支和帝王年号相结合的方式来计算年月,人们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和频繁更迭的朝代里体验时间的流逝,元日、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在干支所组成的我们称之为农历的体系里不断地、有规律地来临。从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政府引入了新的公元纪年法,旧的纪年法虽仍采用,但似乎只在农村流行。在城市、主流社会、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主要采用的是公元纪年法带来的新的时间体系。新的时间体系是和新的知识谱系及意义建构等联系在一起的,在新的时间体系和知识谱系里感受岁月的变迁,对旧时间体系里流行的传统节日有可能是不敏感的,于是,在郭沫若、徐志摩、冯至、艾青、穆旦等创作新诗的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关于节日的体验较少进入诗中。
然而,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是不容漠视、无法弃绝的巨大存在。节日是每个民族或其他共同体都会有的一些独特的时间,是所有人都要带着狂欢情绪迎接的日子,它是特定地域和特定种族的人们长时间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凝聚,是共同体集体生命体验的产物。节日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感应顺从,但又逐渐加进人们的观念、情感和意愿等,带上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它成为一种反复举行的仪式,“人们在重复出现的节日仪式与习俗中传承着历史与文化”[2]。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节日会消失,也会添加一些节日。但是中华民族的整个节日体系自先秦萌芽,经秦汉魏晋隋唐两宋时期的漫长发展基本定型之后,就一直维系到现在。重要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一旦确定,就得到年复一年的延续。事实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启的现代化历程并没有弃绝、也弃绝不了传统的节日体系,以及传统节日所象征的文化意义和内涵。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节日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3],因而中国的新诗诗人也不能不对节日产生感悟和体验。
笔者曾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中的作品及其“索引·史料”、佘树森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辞典》、现当代一些重要作家作品集等,辑录了“和传统节日有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础篇目”近1000篇,其中诗歌作品接近200篇,不妨列举部分(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
艾青有《除夕》,收入其诗集《他死在第二次》,1939年11月初版,上海杂志公司1941年9月再版。
卞之琳有《旧元夜遐思》,收入其诗集《十年诗草(1930-1939)》,桂林明月社1942年5月出版。
冰心有《中秋前三日》,收入其诗集《春水》,新潮社1923年出版。
陈雨门有《除夕》,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成仿吾有《清明时节及其他三首》,收入其小说、诗、剧、杂记合集《流浪》,创造社1927年出版。
戴望舒有《元日祝福》,收入其诗集《灾难的岁月》,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2月出版。
杭约赫有《岁暮的祝福》,收入其诗集《火烧的城》,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5月出版。
林庚有《正月》,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刘大白有《红色的新年》,收入其诗集《旧梦》,商务版,1923年。有《压岁钱》、《国庆》、《旦晚》,收入其诗集《再造》,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9月初版。有《劳动节歌》,收入其诗集《卖布谣》,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11月初版。
卢葆华有《端午你又来了》、《元旦》,收入其诗集《血泪》,1932年8月30日初版。
陆白人有《七夕》、《中元》、《鬼节祭》,收入其诗集《铁马》,北京艺术与生活社1943年1月1日出版。
路易士有《节日的街》,收入其诗集《出发》,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5月初版。有《重阳雨》,收入其诗集《夏天》,上海诗领土社1945年2月初版。
马凡陀有《过年》,收入其诗集《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生活书店1948年6月初版。有《今年新年大不同》、《送旧年》,收入其诗集《解放山歌》,1949年6月初版,新群出版社1949年11月再版。
聂绀弩有《论元旦》,收入其诗集《元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7月出版。
蒲风有《新年词》,收入其诗集《在我们的旗帜下》,诗歌出版社1938年10月9日出版。
沙鸥有《拜年》,收入其诗集《农村的歌》,重庆春草社1945年11月初版,上海春草社1947年3月再版。
臧克家有《元宵》、《新年》,收入其诗集《罪恶的黑手》,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有《元旦》,收入其诗集《运河》,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
曾卓有《除夕》,收入其诗集《门》,昆明诗文学社1944年9月出版。
朱自清有《新年》、《除夜》,收入其诗文合集《踪迹》,亚东版,1924年;后者再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诗集)。
北岛有《过节》、《岁末》、《新年》《中秋节》,收入《北岛作品精选》,跨世纪文丛精选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公刘有《五月一日的夜晚》,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顾城有《节日》,收入《顾城作品精选》,跨世纪文丛精选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吉狄马加有《星回节的祝愿》,收入其诗集《遗忘的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李季有《春节寄友人》,作于1958年,收入《李季》(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李琦有《新年快乐》,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舒婷有《中秋夜》,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肖三有《七二年元旦》,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周纲有《昆仑春节夜》,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以上挂一漏万地列举当然不能穷尽中国新诗诗人对于节日的歌咏,但也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是广泛的。事实上,中国新诗对于节日的感悟和体验连接着丰富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对于中国新诗节日体验话题的接近有多条路径,且散点扫描,我们从解读几位新诗诗人有关节日的诗入手(为节省篇幅,笔者未将这几篇诗作纳入上述列举范围)来进行分析讨论。
1. 新文化先驱者借用蕴含传统文化的重要时间——胡适《除夕》
1918年早春3月,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节刚刚过去,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位提倡新文学的文化人联袂出发,均以除夕为体验对象,各自写作了一首或一组关于除夕的白话新诗,发表在当时已有影响、专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上。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一次集体行动。在政府指令全国都按照现代世界日历(公历)安排生活的时代,他们集体出发对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除夕做了一次考量。作为新文化的鼓吹者,胡适等四人对传统节日及其裹挟的文化意义保持着一定距离,没有普通民众的亲近感;对传统节日文化他们并不认同,至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态度总的来看是疏离和反叛的;其中态度激烈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借传统节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一次清算和考问,典型的如陈独秀。不管他们各自亮明的态度有多大差异——包括对这个节日的不以为然甚至批判指责,但这次集体行动,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我们重点看其中诗歌创作成就最大的胡适的《除夕》: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吃完梨子喝完茶,/夜深风冷独回家,/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里的孟和即陶孟和,社会学家,当时亦任北大教授。诗最后的“他”即指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胡适是“白话诗”倡导者,也是第一个用白话写诗的作者。这首诗和胡适的其他诗作一样,平直如话,叙述了除夕这天作者从白天到深夜的经历,不外乎知识分子之间的请吃饭与聊闲天,可视为节日活动的真实记录。从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提倡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胡适有一种不在乎的情感姿态,似乎“除夕”这个日子一过去,就“一去不复返”,关于这个日子的一切都已淡忘。不过,他仍清楚也是近乎琐细地记下了一整天的活动。在他那里,吃的什么比谈的什么记得更详细;其实,谈的什么或许更可以深入心灵,达到诗歌所需要的形而上的高度。然而胡适的处理可谓高度地日常生活化,他采用记流水账的方式,把这个有意义的节日变成许多寻常日子中的一个。他的诗调侃味很重,诗味不足,散文气倒很浓,延续着他把作诗视如作文的创作路数,具备新诗研究者周晓风教授归纳的“胡适之体”“明白如话”和“题材的平实化”特征[4]。
在中国,“除夕蕴涵的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意义,成为凝聚家庭情感与民族认同感的独特方式,也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5],其中有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尽人皆知的,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个体所遵循、崇奉的。但是我们从胡适诗里看到的是一种不在乎、淡忘的立场和态度,把这个重要日子像对付平常日子一样打发过去,表明对除夕这一重要节日以及节日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的忽视和疏离。联系到新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对的总体姿态,胡适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笔者认为还可这样理解,除夕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即使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胡适这些文化人,他们无可逃避地都要面对这一时间,都要接受这一节日带来的影响。由此,除夕出现在胡适等人的诗中就突显一种悖反:他们漠视、淡忘除夕,乃至在这个日子里大唱反调(陈独秀就是这样),但却借用了除夕这个蕴含深厚传统文化的重要时间来展示自己,集体亮相。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胡适等人从反向利用了除夕这一节日具有的辞旧迎新等文化意义。如果舍弃除夕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他们这次写作将无法延展。进而还可这样认为,以除夕、春节为核心的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支援了草创期的中国新诗写作。胡适等四人针对除夕写作新诗,又在《新青年》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集体亮相,其实有意无意间以白话新诗的形式宣传了这一传统节日。
胡适等新文化先驱者针对除夕的这次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新文学和传统节日特别是年节的难解之缘。之后,与传统节日有关的作品不说是风起云涌,可以说接二连三地出现。虽然不能肯定这前后继起的现象之间有某种因果联系,但中国现代文学在发轫之初就与传统节日挂上钩,以后也就没有脱离干系。
2. 文化怀乡者在异乡使用另类时间——闻一多《忆菊》
《忆菊》是闻一多写于1922年的诗,专门标注副标题“重阳节前一日作”。当时作者到美国留学不久,身处异域的孤独感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使远在异国他乡的闻一多成为一个文化怀乡者,其时他内心显然仍保留和使用着传统中国的时间体系,但身处异境又使用的是另类时间,这样,在文明古国的重要节日重阳节来临时他与众不同地度过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并特地写一首诗来表达节日的体验。诗作以繁复华丽的笔触描写菊花的各个品种和姿态,接着由这“东方底花”联想到“祖国之秋底杰作”、“东方底诗魂陶元亮”,而那“登高饮酒的重九”,正是故国“诞生底吉辰”。诗人采取一种对抗性的、偏激的态度来对待异域的花。在他强烈的主观情绪里,异国的蔷薇是“热欲”的,紫罗兰是“微贱”的,都比不上“华胄底名花”菊花“有历史”、“有风俗”。诗作最后以急骤的旋律和奔腾的气势赞颂“如花的祖国”: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诗人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与所描绘的菊花绚丽多彩之景交融在一起,“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交相辉映,切实地诠释了朱自清对闻一多“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6]的认定。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里,菊花是标志重阳节的象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诗人的爱国情怀是通过一个节日表达出来的,它其实就是节日的感受和体验。
这份节日的感受和体验是由一系列文化事象或活动(如菊花、写诗的陶元亮、登高饮酒等)引发或串联的,它们本身足以营构浓郁的独属于重阳节节日文化氛围,对于它们的记忆属于这个特殊的日子,起作用的其实是一种已经成为传统的文化。闻一多说过:“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其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7]可以推知,重阳节的感受和体验是对祖国“可敬爱的文化”的怀想。不了解重阳节及其文化蕴意的读者面对这首各种意象如漫天落英缤纷的诗极可能会感到阅读的障碍,为什么在这个日子而不是另外的日子产生这些感受和体验呢?因为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上,节日已经连结一些特殊的文化事象或活动,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标志、象征着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沉淀下来,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即意味着在重阳节这天,预先培植的各种各样的菊花就要搬到公众场合,供人们观赏;人们就要登高饮酒,文化人当然免不了吟诗作赋。闻一多虽身处异国他乡,赏菊不成,也不能登高饮酒,但他还是会在记忆里复现与此相关的事象或活动;而且往往越不能亲自面临或参与,内心的向往和想念就越强烈,复现出来的记忆就越真切,也就难怪这个日子会产生如许纷至沓来的想象。
这首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在1000多年前写诗表达重阳节体验的诗人王维。闻一多此时的处境和王维相似,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肯定思念家乡和亲人。又逢重阳佳节,不能亲自参加节日的活动,只能在回忆和想象里过节,感到烦恼,于是生发强烈的感受和体验并诉诸于文字。然而他们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对王维而言,他只是从唐朝皇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烦恼只是不能在故乡和亲人们一起过节,其“异乡”应该是在同一语言以及民族文化环境之内,“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句表达的节日体验,是一种温厚的、略微有些超脱的遗憾。对闻一多而言,身处的“异乡”与家乡迥然不同,种族殊异,语言不通,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加之“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深入其内心,于是他的烦恼就不仅仅是不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共度佳节的遗憾,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语言和种族等诸多明显差异带来的迥异感觉。到美国留学不久,他在一封给吴景超的信里写道:“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仓皇无措,突兀不安。”[8]这样的感觉连结着的节日体验,必然是压抑、焦虑、愤懑等激烈的情绪,于是我们看到“热欲”的蔷薇、“微贱”的紫罗兰与“有高超的历史”、“有逸雅的风格”的菊花之对立,实则是两种文化的对立。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中,诗人贬抑异地文化的同时,热烈地赞颂故国的文化,这样的赞颂,释放、舒缓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压抑、焦虑和愤懑的情绪。其中,中国传统节日成为诗人实现文化对抗的手段和资源。
在《忆菊》这首表达节日体验的诗里,我们看到,与五四新文学其他先驱者如郭沫若决绝地反抗、摒弃传统不同,闻一多采取的是一种认同、服膺于传统文化的立场,使其整个诗歌创作明显增多了爱国的成分,以致给人他是“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爱国诗人”的印象。另外,他的诗在形式上讲究格律,提倡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这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是有渊源的,使他的诗显得更为成熟耐读,更具有诗的美,从而把草创期的中国新诗引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忆菊》提供给我们的超出这首诗之外的启示。
3. 革命胜利者构造新的时间——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何其芳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日的诗,发表在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创办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国庆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体系外新增加的节日,被赋予整个以前受到压迫的民族从此站立起来的崇高意义。作者是十多年前在民国时期即已成名的诗人,后来辗转到延安,成为一名革命者。在这首诗里,他视自己为群体的代言人,把刚刚确定的这个日子不容置疑地宣告为“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一份具有集体意义的节日体验。诗人对新的节日超乎一切的颂赞,表达的是铸造新的时间、建立新的文化认同的企图,同时伴随一种对传统节日的遗忘甚至有意识的反叛。诗作回溯过往历程,展开对这个前所未有日子的起源、也是革命胜利的起源的回忆和想象:
多少年代,多少中国人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梦想着你,/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路上/寻找着你,/在监狱中或者在战场上/为你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呼喊着你
在诗人的回想里,过去的日子是无比黑暗的、罪恶的、艰难的、悲惨的、受着敌人压迫的,而唯有这个日子,迎来了光明、希望、欢乐、平安、做主人翁的生活,于是,这个节日的伟大得到证明。诗人的新体验即,这是独一无二的时刻,是前所未有的时间,是美好光明时代的起始。
诗作表达幸福喜悦的激情,描绘节日狂欢的图景,这是胜利者的政治抒情,具有节日的典型的狂欢性质。节日的狂欢使诗人放弃自我,混融进“我们”,高唱对新的节日以及缔造这个日子的领袖的颂赞。他这样表达狂欢之情:
欢呼呵!歌唱呵!跳舞呵!/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
这些诗句和20世纪30年代何其芳留给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如论者所言:“诗人少年、青年时代的歌声充满了忧郁和柔弱,而这‘人到中年’的歌声竟如此欢畅和年轻,可见诗人此时激情的无可抑制。”[9]诗人歌颂的是一个具有始源性质的时间的来临,那就是许多人盼望已久的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诗人的表达里我们看到纵情欢娱的宣泄,不论贵贱的平等,广大群众的踊跃参与,仿佛听到诗中所言“如雷一般响彻长空的笑声”,正是这些构成节日狂欢的重要因素。
这一构造新时间的体验固然可贵,可它也有空疏和粗俗的地方。如在歌颂领袖时出现的诗句:“他叫我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喊出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美帝国主义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我们肯定作者表达情感的真挚,却不能否认这些句子于文学性、艺术性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距离。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只有社会政治的单一视角而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或者将其弃之不顾,就会丧失微妙的、柔和的自我体验,也无法产生美妙的诗句。
4. 文化寻根者寻索久远的时间——李瑛《端阳》《清明》
《端阳》《清明》是李瑛写于1993年3月的两首感悟中国传统节日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两首关于节日的诗歌,不仅对李瑛还是对中国诗坛来说,都是一次颇有意味的事件。
《端阳》一诗的主题是纪念屈原。众所周知,端午节本身的起源并非如此,但这并不妨碍纪念屈原成为这个传统节日超乎一切的主题。诗中把屈原视为“一个民族的心和嘴唇”,诗的主体与之建立起“直系血亲”的联系,缘由在此。屈原死后,“所有的江河都迷失了方向/ 使两千年前的鱼/ 失眠至今”,他要“寻向中国文学史的喉咙深处”,去把屈原的诗一行一行“捞出”。诗中的抒情主体似乎是失落的,为此要从屈原那里寻求精神的援助。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告诫我们的子孙,不要忘记/滋润了我们民族的生命的根的/那副精魂/这就是为什么/太阳/每年都要为我们发一次/讣闻
诗人意识到,屈原和“我们民族的生命的根”紧紧相连。这里,一种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喉咙深处”去寻根的企图非常明显,作者似乎从历史深处找到沉厚和凝重的力量。
《清明》一诗,抒发的是对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的感悟。诗中“这一天”不断复沓,以它开头的句子不断绵延,关于清明节这一天的感受和想象也汩汩流出,源源不断:
这一天,揭开隐痛和伤口的人几乎死去/而死去的人都将回到家里/使生存和死亡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一天,在人间,本来是有限的距离/却凝成无限的痛苦/时间和空间酿成一碗烈性酒
诗作把这一天中国人通常的祭奠祖先、缅怀死者的活动作了哲理化、艺术化的处理,演绎出一个特殊日子的深沉的文化含义。
李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无论上个世纪的50~70年代,还是80年代,他都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诗人,其诗作通常以肩负使命的战士的眼光,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感受和思考,表达社会政治性的思想命题。艺术表现上,善于“借助对于具体生活事件、场景的描述来抒情演理”[10]。90年代,随着之前两个时期一些流行的社会政治命题的淡化,他的创作也遇到难题。这两首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诗作凸显出他对创作危机的一种应对策略——那就是虽然仍立足于现实人生,却把视线从当下的社会政治移开,凝望久远的时间,向着传统回归,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去寻找命题、灵感,乃至安身立命的根。
三
从上我们看到,四位中国新诗史上前后继起的著名诗人都关注了节日,表达了对于节日的感悟和体验,表明节日和关于节日的记忆嵌入他们的生命、情感,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所以节日进入他们的诗,显现出耐人寻味的蕴涵。他们对节日的不同态度,也揭示新诗接近节日这一特殊时间的几条路径,显示出节日进入中国新诗的几种可能。
把他们对节日的态度放到整个新诗发展的历程中来探寻,可以察知:1)节日仍是整个中国新诗借取的重要文化资源,新诗不能不面对节日,因而新诗关于节日的体验是重要的。2)节日是中国新诗和古典诗歌乃至整个古代文化传统对接的重要桥梁,比较文中的几首诗,或可推想,实现这种对接比没有实现带来更多的意味。3)从胡适到闻一多,到何其芳,再到李瑛,中国新诗处于不断地变化中,关于节日的体验也在不断变化,从这些变化可寻到中国文化乃至整体的社会生活在百年间演变的踪迹。
如果我们把中国新诗的节日体验置于中国诗歌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以感受到诗歌的常与变,或许会发现有更大价值的话题。这里有中国诗歌发展恒常的一面:无论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要面对一些相对特别的、相对凝固的时间,处理这些时间的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归属于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时间不断循环,不过是绕着某些固定的点,这些固定的点包括一个个的节日。我们的心理驻留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以及特定的符号、特定的事象,由此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这些东西进入共同体中的每个单独个体唤起的体验,当然具有相同、恒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世道人心在变,对特定时间的体验在变,节日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主题在变,人们甚至重新规定节日,由此改变诗歌的面貌,改变诗歌中的意象营构和情感体验,包括节日和节日体验。不过应该明白的是,这种改变似乎不是根本的。以节日来说,节日的纪念性、狂欢性、娱乐性等根本、重要的性质一直未变;传统节日体系尽管一段时间内受到冲击,但始终存在着,近年来又表现出回归的趋向,每个节日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相对趋于固定;一段时间改变大些,一些重要的节日几乎消失,一段时间改变小,小到要尽量向传统节日回归,而这些,都会在中国诗歌里反映、体现、揭示出来。
[1]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和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5.
[2]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9.
[3]李汉秋.传统节日的奥秘:我们怎样过节[M].北京:中华书局,2015:2.
[4]周晓风.新诗的历程——现代新诗文体流变(1919-194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44-45.
[5]王文章.中国传统节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58.
[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245.
[7]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J].创造周报,第5号,1923-6-10.
[8]闻一多.闻一多作品精编[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442.
[9]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101.
[10]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47.
责任编辑郭利沙英文审校孟俊一
Festival Experience in Chinese New Poetry
CHEN Zu-jun
(School of Culture and Law, Guizhou Univ.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Chinese festivals, especially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the great exist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ignore, to reject. Practice of Chinese new poetry to Chinese festival especially traditional festival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Hu Sh's "New Year's eve" showed that a new culture pioneer was using the important tim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n Yiduo's "To Remember Chrysanthemum" showed that a cultural homesickness person in a foreign land was using alternative time,He Qifang's "Our Greatest Festival" revealed that a revolution winner was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time, Li Ying'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he Tomb-sweeping Day" showed a culturally seeking-roots person was in researching of very long time. These embody a few paths for the new poetry to festivals, and several possibilities for festivals to Chinese new poetry. Putting the new poetry festival experience in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we could feel the constant and change in Chinese poetry.
Chinese New Poetry;Festival;Experience
2016-07-15
陈祖君(1972-),男,贵州遵义人,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I206
A
1001-733X(2016)05-014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