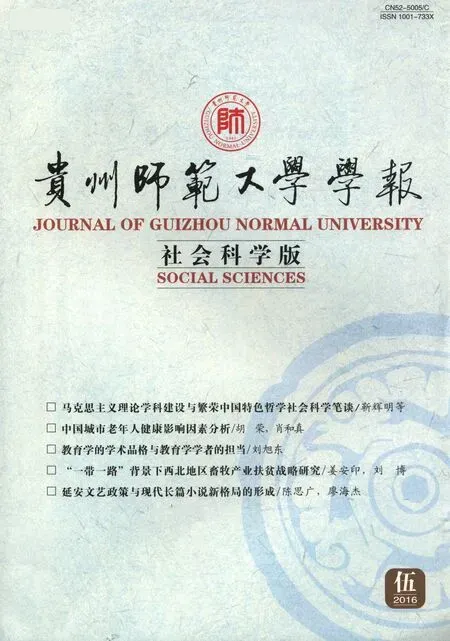论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之耦合
——正学、正心至正文的自然递嬗*
2016-03-19常威
常 威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论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之耦合
——正学、正心至正文的自然递嬗*
常威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有明之际,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士人学子为学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学而不行流衍成风。是故,王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以疗救为学沉疴。在追名逐利之风的熏染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已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于是阳明又倡“拔本塞源”之论以补正人心。当然,鉴于“心口不一”在文学场域已成流弊,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题中之意,于是阳明复倡“修辞立诚”以正之,而“文即其人”观,庶几可作为心学派文、道、人关系的终极诉求。
阳明心学;明代文学;正学;正心;正文
胡越曰:“天生阳明在中国,是中国民族的大幸”。[1]1诚然,作为“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2]1,王阳明掇菁撷华,持幽渺深湛之思,“以有明一代之奇才,倡良知求静之学”[3],其心学不惟沾溉时人,亦流泽惠远。可以说,自“有明中叶,风气初更,学问移于姚江”[4]4718之后,学术之分野渐明,阳明及其学说遂取得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拥有难以撼动的话语权。因此,在阳明心学蔚然风行之际,其与明代文学的耦合有必要加以推阐。
一、儒学式微与阳明心学的正学倾向
至于阳明心学的兴起,显然与明代社会政治及文化学术背景息息相关。除了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其中一个重要诱因就是理学盛极实衰的思想困境。盖当时程朱之学“以帝王之尊崇,及科举之需要,故凡向风慕化者,无不濡染浸渍于身心性命之说”[5]739,但是必须指出,此时的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众所周知,明代“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6]1131。于斯之时,程朱理学可谓值隆盛至极之时,然亦可谓流弊甚夥之际。对于其中缘由,何良俊曾阐述曰:“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其施之于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7]22-23可见,深受阳明心学濡染的何氏认为圣人之言重在体认之功,方可自得于心而施之于用,若穷究于程朱训诂之单辞片语而落于程式,其固已失之,何况又加之程朱之说已沦为科举名利之用,因此,儒家经典之精义遂晦而不明,学者竟至于不明孔孟之书为何物。
既然程朱之学已沦为八股取士之用,则其对圣学之害不免远甚于前,以致“学者诵诗书,称述古昔,人人能矣。至起而试官,乃辄悖其所习,违道而悦上,败度而事私者,不可胜数也”[8]。对此,时人多有论述。例如,庄昶有科举害道之论,其谓科举之学,其为害远甚于杨墨佛老,而于古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自近而远,自易而难,施之有本,进之有序”之学,绝不相类,其所能者“属联比对而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主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至于问其为学精义,则“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吊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卒丧,学春秋者不知……所谓义理,所谓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是以其学徒然“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是以其谓“夫道不明,岂道罪哉?科举害道也”[9]。而黄宗羲在《恽仲升文集序》中则直言“举业盛而圣学亡”,其曰:“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10]334观黄氏之言,盖谓此时的程朱理学仅可谓为科举之学,而与圣人之学杳无关涉,至于其流弊则在于其以一定之说羁勒天下士子之口,钳制天下士子之心,以至于万喙一音,动辄以离经背训视人,而要其奉为圭臬之说,不过皆肤论瞽言,所谓依样葫芦者。诚如以上诸人所论,自程朱之说出而圣人之言遂无发挥之空间,自举业盛而圣学至于亡歇。对此,邵廷采亦曾总结曰:“自宋世理学昌明,程朱大儒择精语详有国者,至以五经四书制科取士,可谓盛矣。人人崇用朱传而不知反验之身心,口之能言,笔之能书,顾茫然也。”[11]33-34不可否认,明代的程朱之说,牢笼圣人之言,而八股取士,又进一步拘囿天下士子之学,锢限学子之心,以致“自离怀抱而入学舍,无有不诵四书者,然而能知四书者,盖亦鲜矣。夫四书非可句解而字释也。……故先儒欲解四书者,必以心性为纲领,顽阴涤剥,则条目无滃雾矣。……然学者工夫未到沉痛,只在字义上分疏,炙榖淋漓,总属恍惚,决不能于江汉源头而酣歌鼓掌耳”[10]15-316。以故,朝廷求士之心虽切,但观其结果,显然难以选拔具备“道”与“术”的贤才高士。究其因,“程朱理学本来是一种脱离人们的生活实践、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的理论体系,充满着虚伪的道德说教。这样的理论一旦成了士人追求利禄的敲门砖,其虚伪与无用的本质就更加暴露无遗。”[12]157
而严苛且过于注重程式化的八股取士看似明晰而中道,实则却造成了士人主体独立求索精神的丧失,所以谢思炜曰:“八股文虽是议论,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虽讲究文字,却不许描摹形容,不能表情达意。……它唯一的用途就是供士子应试得官,一旦考中,便被抛置一边,所以人们把它叫做‘敲门砖’。”[13]50这样一来,僵化的程朱理学与禁锢士子主体思想的八股取士就极易诱发取士者与求仕者双重的“仕意不明”,而仕意不明表征背后潜隐的是统治者治学的教条化以及为学者求学的功利化。具而言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其所以求而示之士,应夫求者,亦不知其所以求而为之应。诚如黄省曾所曰:“予观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应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为之应也。是以士日卑污,而道日湮求,门愈辟而贤圣者不出,圭组轩符日授于人,而天下益趋于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14]902据上可知,受阳明心学影响的黄氏无疑道出了明代取士制度乏软无力的弊端而归结于仕意不明,以至于求士者“不问其心之颜跖,不择其志之高污”(《再寄冢宰乔公宇书一首》),而求仕者“徒以富贵为心”(《仕意篇下》)。因此,上下两端的仕意不明难免使士人学子无所适从而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而视儒家经典为进阶趋利的敲门锐器,以致为学不复观古人内在之热想与精神,竟至于弃孔子所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而不顾,徒取以实用处以资时文之用,一时风向所趋,进而弥盛,竟成流弊。
刘玉曾对追逐科举禄位导致的世风、士习日下痛心不已曰:“世变之下可胜道哉。古之为士者,知有道德而已,知有义理而已,修诸身而德以立,措诸人而道以行,证诸经而义以明,修诸词而理以达。……降世以还,管仲出而事功启。……道德变而事功遂,义理变而训诂述作,此士习之既下也。……(迨夫末世)功名变为科举禄位,训诂述作变为呫哔蹈袭,此又士习之愈下者也。”[14]838这里,刘玉所言“功名变为科举禄位,训诂述作变为呫哔蹈袭”堪谓有明为学一时风气的真实写照。薛甲亦曰:“古道不作,廉耻之风衰,世俗之教弟子者,稍知句读,则使习佔哔、课文字为利禄之谋。其既得之也,则藉声势、凭宠灵,为荣身肥家之计。”[15]130于此而言,科举之学显然已经“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脱解,以至老死而不悟”[16]149。然而若以科举禄位作为为学的价值取向,那么世人所研习的儒家经典不免仅剩下儒道的躯壳,这自然受到时人的不满而备受非议。如归有光《山斋先生文集序》曰:“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顾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常至于不能措手。”[16]25可见归氏认为,若能知文而学古,则不惟能通当世之故、达于治乱之迹,甚或能识性命之情,“而可以施于为政,”切不可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为务。王樵亦曰:“古者正学、外诱犹为两途,自有科举之世,而学者以利禄以为志,则是为一途矣。”[17]213观王氏之意,显然对科举导致的正学、外诱为一尤为不满。至于其解决途辙,自然是回归古之“正学”。至如“正学”之具体内涵,韩愈曾有养根俟实、加膏希光之论,庶几可作为解答,其《答李翊书》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18]99而王氏所谓正学者,当与韩愈所指古之立言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力”,惟以加强自我的人格修养为旨归同,而其旨要在表明自科举取士以来,学者汲汲于功名利禄,这样一来,正学与外诱实为两途的状况不免发生根本扭转,乃至于科举之世,学者之学与利禄之事合二为一,而士子学人凭借八股制艺即能见录于朝廷,因此遂至于有徒事虚言而不务实行的倾向。对此,姜埰洞见曰:“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6]4456是以取士者亦不免发出言易行难的慨叹而不得不有所诫勉。诚如梁储所曰:“盖天下之事,言之非难而行之为难。自古聪明文学之士能慎乎其始者常多,能不渝乎其后者甚少。今诸士子始以文学见录于有司,旬日后遂将入对大廷,驯有官守言责之寄,其亦能言行相顾、慎终如始,致国家有得士之实而无贻有司不明之诮也。”[19]583
因此,在士习愈下,学风沉沦的时代情势下,阳明不免发出“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20]77的喟叹与疑虑,从而不得不对为学做出了自己的修正与解读。在其看来,学而不行不能谓之学,学而笃行才能谓之学。是以其曰:“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21]101观阳明发皇之意,要在揭示“未有学而不行者”之旨,是以其谓躬行孝道方能谓之学孝,若只是空口言说,则决不能谓之学孝。诚如沈佳所云:“(王阳明)论入圣不在采摘枝叶,广博见闻,则笃论也。为学而不身体力行,徒资诵说,先生所弃哉!”[22]874可以说,阳明“不行不足以言学”之语堪谓针对时人徒事口说而怠于行的弊病而提出的中的之论,颇有摧陷廓清之功。寻绎阳明之意,盖谓君子为学,当知“无息非学,无息非行,若以学偏属知,便是务于口耳见闻以为博,此正是俗学之大病,且要博的完才去行,何时是知之日,又何日是行之日”[23]127。何况当时八股取士又限人于四书五经之中,使学者穷究于程朱注疏之内,此时人之学既不博且未可谓有真得矣,是故王阳明曰:“夫谓学于古训者,非谓其通于文辞,讲说于口耳之间,义袭而取诸其外也。获也者,得之于心之谓,非外铄也。必如古训,而学其所学焉,诚诸其身,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为有得也。”[20]183况且,当时研习儒道者,因为少有落实于行者,故而多败坏儒道之徒。于此之际,欲求为学之归正以及道德之恢复,固少可能。梁启超曾有“药疫”之譬,正可为此作一形象的说明,其曰:“譬言某药可以辟疫,而常备此药之家,乃即为播疫之家。是必所备药或非其真也,或备而未尝服也,或服之不以其法也,或其他不良之起居食息与药力相消也。不探其源以治之,而但侈言置药以御疫,疫不得御,徒反使人致疑于药而已。……苟无道以解其癥而廓其障,则虽日以道德论喃喃于大众之前,曷由有效,徒损道德本身之价值耳。”[24]诚如梁氏所言,某药可以解除疾疫,但是“常备此药之家,乃即为播疫之家”,则此药之功用及价值不免大打折扣。依此而论,当程朱理学盛行之际,则人人无不以研习儒家道德仁义为职事,若持此道德仁义之药以辟除为学不正、人心不古、儒道沉沦之疫,那么药到病除为可期。然而此时持此道德仁义之药者,多即败坏道德仁义之徒,是以虽备药,但是或药已非其真,或备而不服,或服之非法。兼之当时学人,不务简易,不探本源,不务践履,徒侈言置药,则儒家所谓道德仁义之事,为人所怀疑否定亦可以推知矣。
王阳明显然对此有深刻的体认,故而倡“知行合一”之说,而这也堪谓其心学思想精义所在。是以孙奇逢曰:“阳明良知之说,着力在‘致’字,故自谓龙场患难死生之后良知方得出头。”[25]537可以说,兼知与行的“致”,在激扬堕落沉沦人心之时,亦成为疗救为学沉疴的一剂良药。要之,此时学人治学虽多弊病,但所研习揣摩者毕竟不出儒家经典之列,因此,只要其将所为之学由悬空口说落实于行,则士子之学即使不博亦可谓有所创获,而作为辟疫之药的儒学奥义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当然,黄省曾提及的“士日卑污,而道日湮求”的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二、人心不古与阳明心学的正心诉求
据上可知,明代士人之学既已穷究末节且“徒悬空口耳讲说”而不行,而富贵名利终凌驾于颜心高志之上,既而渐滋日盛,流衍成风,积弊难返,于是正德之后,世风日下,醇厚不在。即使向来以醇厚著称的南都金陵,在时风世雨的冲洗下,亦在所难免。顾起元对这种变化曾有比较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26]25观顾氏言外之意,谓正、嘉之前,金陵风尚犹淳,而其后不免堕于求田问舍、投贽干名、奢靡淫佚之中。诚然,明中叶以后,风俗日败,人心不古。在此情形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已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上下不孚”(宗臣《报刘一丈书》)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王阳明对此有深切的洞见,其在《答聂文蔚》书中曰:“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21]159-160阳明后学黄省曾亦曰:“今之人也,口道德而心苞苴,赀藏愈多,嗜欲愈衍,夙夜遑遑然,求之而若狂也。是人者,虽自夸诩以为上符尼轲、下迈伊洛,空饰之言,曷足以掩污实之行乎。”[27]751而阳明后学李贽对此亦有论述,其《答耿司寇》曰:“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28]28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业已成为投机取巧者装点门面的工具,而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在士人群体中已成司空见惯的现象。王阳明曰:“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20]166诚然,对功名利禄肆无忌惮地追逐必然会导致道德仁义的功利化,而道德仁义的功利化自然会奏响人心沦陷的号角,王九思曾经对时人追求富寿之极而不以为怪,而至于道德者,则怪而不为有过论述,其《惑解》曰:“寿如籛铿,富如石季伦,世未有不以为极焉,而慕之者不惟冀诸其身也,而且冀诸其子孙焉。又祝诸其所厚者,所厚者无不受之怡然,而未有以为迂且妄而怪之者也。至于人之极焉,舜之孝,周公之忠,孔子之道德,世亦未有不以为然者也。……夫富与寿,命也,而欲必得之。而忠与孝也,道德也,可以力为者也,而怪而弗为,惑矣。”[29]63以上从王氏所论中,不难看出时人之心已为富寿充塞并怡然自得地追求之,且不特冀诸其身,而且冀诸其子孙。但是一旦至于道德仁义之域界,则怪而以为迂妄,竟至于惑而不为。可以说,其富贵之欲莫极于是,而其本心之失亦莫甚于是。诚如孙奇逢所曰:“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贵也哉?求富贵之人有一念不在富贵也哉?求之途广,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复返,人尽失其本心,不得不以习心为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知怪。”[25]549显然,若本心全放于富贵名利之中而恬不知怪,必然会导致本心的丧失,而如此之人亦不免沦为欺世盗名与瞒心昧己者,以致产生较大的危害。对于其危害性,吕坤揭示曰:“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语欺人,人虽不知,即未发觉之盗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道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道也;才发一个真实心,骤发一个虚妄心,是心者心之盗也。谚云:‘瞒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盗名,其过大;瞒心昧己,其过深。”[30]616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时人的警觉与重视。陈寅恪尝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31]可以说,值此儒道式微之际,深受儒家文化浸渍的王阳明等人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得不思纠偏之良方以复振之。
虽然程朱理学依然在薛瑄、吴与弼等部分士人的价值导向中发挥余热,例如刻苦奋励的理学家吴与弼,“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32]3,焦竑评骘其曰:“吴先生与弼,司业溥之子。读书穷理,累辟不就。不教人举业,弟子从游者,讲道而已。……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亲农事,弟子亦随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实践,乡人化之。”[33]7-8而经学家王樵《镇江府重修学记》(方麓集卷六)因洞见时弊而推阐程颢正学之精义曰:“明道先生所谓正学者,以为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乐,其要在诚乎身而适乎世,用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17]212尽管如此,但是整体而言,在大部分士子学人心中,程朱理学不过沦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罢了,而自家对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用已生疑虑,因此以自家之疑欲求取信于天下,实不可得。由上可见,通过程朱理学秉持的博学于文进而实现正心、诚意的理想进路,已成镜花水月的幻影,思想文化领域的儒道沉沦,已成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故阳明曰:“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见,而又饰之以比拟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训,其为习熟既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诳己诳人,终身没溺而不悟焉耳!”[20]206诚然,对于汲汲于章句假借之训的程朱理学派诸人来说(尤其是其后学),更大程度上他们只是“知经之为经,而不知心之为经,知求经于经而不知求经于心,见其似而疑其真,得其牝牡骊黄而忘其天机,务博以为知,阞长以为行,若是者,虽其勋名塞宇宙,文词汗简册,均之于心无得也,于经无合也”[15]131。因此,在程朱理学“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造成的“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的情况下[21]63,儒家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病症的仙丹妙药,期以扭转人心不古、儒道式微的颓势。这样一来,由内而外的德性体认与道德践履,在明代日趋加强的专制政权导致的道与势的冲突下,不失为一种融通且有效的捷径。诚如薛甲《与朱近斎书》(畏斎薛先生艺文类稿卷一)所云:“学问之道,不过两端,有求之内者,有求之外者,求之内则言虽不同而其归一也。不然,虽逼真圣经亦无益矣。”[15]106
而于求之于内的学问而言,有明一代,陈白沙已开其端绪,至阳明出,承继陆氏“心即理”之说而发挥之,倡言良知,去物欲之蔽,反身归诚,以复圣人之心,于是“拔本塞源”之论横空出世,以补救时弊世病。其曰:“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圣人)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克其私,去其弊,以复其心体之同然。”[21]113-114由上可知,阳明认为圣人之学至简至易,其大端则在于“复心体之同”,而非知识技能,若天下之人能达成“全其万物一体之仁”,则“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但是现实情形却不免令人大失所望,其实际是天下之人心,“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是以“圣学晦而邪说行”。对此,钱穆尝评曰:“人人想立功业,人人想获财利,功业财利未可必得,而各人把自己人格先看轻先丢了。王阳明全书卷二中有一篇《答顾东桥书》书,其末后一大段所谓‘拔本塞源’之论,正是发挥了此道理。”[34]162-163而圣学既远之后,“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21]113-116显然,阳明已经烛见“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的现实,因而“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20]1594。而其“致良知”的思想奥义庶几可用“正心”一语阐释,是以阳明曰:“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21]167可见阳明“致良知”的终极旨归是期望臻于心正之境,而若心正,则百行可立而真心不失,诚如阳明后学薛甲《乡愿论》(畏斎薛先生艺文类稿卷一)所言:“盖吾人之身以心为主,心正而后百行可立。彼有恒者,真心不失,可以进于圣人君子之域,乃天德王道之基也。”[15]97毋庸讳言,阳明之学,“惟以正心诚意立其纲,知行合一明其旨,”是故对于正心,阳明每有强调,而若“正心诚意之学,良知良能之念,施于一家,扩之四海,则大地皆红炉,而人心无歧路”[20]1621-1623。
至于如何达到心正之境,阳明认为正心需要诚意,其曰:“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21]58又曰:“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故欲正其心在诚意。”[21]263诚意之外,王阳明也提倡自得解悟,是以其有不着意于物之论,所谓“无所意必固我”者。其曰:“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谓真洒落矣。”[20]190对此,焦竑尝总结阐论曰:“余观先生之始也,其为虑深。尝示人以器,而略于道,俾守其矩矱而不为深微之所眩。然使终于此而已,学者将苦其无所从入,而道隐矣。乃遴一二俊人,时以其上者开之,如所谓‘无善无恶’者是已。……究且举‘意必固我’而绝之,则空洞之中,纤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无美者,天下之真美也;无善者,天下之真善也。是非都捐,泯绝无寄,而变化兆焉。此道之窾系而名曰‘大本’者也。”[35]845这里焦氏谓阳明“以其上者开之”,且绝舍意必固我之羁绊,才能臻于无善无美之境,而无善无美者,在其看来才是真善、真美,此当是诠释阳明教人开悟之意。至若一旦开悟,当其“于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体了然现前。情累棼棼,自然无处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35]730
三、文章趋伪与心学派“修辞立诚”观的突显
由上可见,既然阳明已经烛照到人心不古的迹象而举起正心的大纛,洞察到为学不行的弊端而高扬起正学的旌旗,作为“心口不一”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文章与主体心性名实不符的现实境况亦不能不引起相应的关注,何况此时文章之伪尤甚于“五官百骸之奉者”,对此,徐渭曾论述曰:“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至于文,则一以为筌蹄,一以为羔雉,故曰轻。然而文也者,将之以授于人也,从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赵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事鲜不伪者,而文为甚。”[36]908以上徐氏所发文章之伪尤甚的感喟并非危言耸听,其显然植根于现实的膏壤沃土。盖古“作文字者,虽不必存载道之见,然道德实不可无”,然明代“文字之坏,时文实为其大原因。时文之弊,在求速化,于是本未能为文者,亦强为之文,为文者遂多不明事理之徒”[37]162-163,因其不明事理,故而为时文者亦每少践履之行,以故,言行难免趋向于崩离。然而“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顾行者伪也。真则言或有偏,不失为君子;伪则其言愈正,愈成其为小人。有人于此,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掇拾程朱绪论,……遂自以为程朱也,则吾子许之乎?”[38]152-153可见只有言行合一方可谓真,徒事口说显然无益,那么在程朱理道日益加强后,世人期冀的言行合一是否就取得了理想效果呢?恐怕未必这样。申而论之,在“文以载道”的大背景下,“代圣人立言”的科举制艺之学使文章必然合于儒道,但是鉴于当时学而不行之弊已经流衍成风(前文已论),这样就会出现极正之言(文)与空言不行交相抵牾的情形,如此,依王源之说,则徐氏文章伪甚之言显然不辨自明。因此,鉴于“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的情形,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必然结果与题中之意,也正是因为这样,言(文章)与心的关系常为时人所论。例如罗汝芳曰:“言者,心之声也。”[39]38袁宗道亦曰:“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礙,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42]283诚然,言为心声,然而如果学人本心已为物欲充塞,其所专注者多在以言词求利一端,而于心之创获而言,不免一无所得,兼之濡染于学儒道而不行其实的浇漓风气中,因此,他们创作的诗文,难免落于“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窠臼。王阳明裒辑朱熹《答杨子直》云:“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然于语言中,罕见有究竟得彻头彻尾者。盖资质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终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实。”[20]138严复《王阳明集要三种序》亦有总结曰:“夫言词文学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20]1626以上不管是王阳明借朱熹之口所言的“心实无得”,还是严复称指的“求诸吾心而不必安”,应该说均道出了文章写作与主体心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隔阂与矛盾。虽然这种情形的产生与前七子形式主义的文风以及时文的写作紧密相关,但是若推本溯源的话,显然依旧难以跳脱心性失正的范囿。徐复观曰:“文学、艺术乃成立于作者的主观(心灵或精神)与题材的客观(事物)互相关涉之上。……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越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修养。”[41]2-3这大概可以说明正心与正文之间的内在关联。
综上可知,心的偏离正道易从根本上造成文的“心口不一”,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并非易事,而阳明心学正己立诚的理论诉求庶几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王艮曾以古人射箭失正鹄而反求自身来申论君子行不得而正己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不怨胜己者,正己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42]7然而若正己,务须返本归诚。诚然,为学需诚,“若不诚,只是不明,”[42]6而修辞亦需立诚。是以阳明《书王天宇卷》曰:“君子之学以诚身。格物致知者,立诚之功也。譬之植焉,诚,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20]271而“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20]1001可见,在阳明看来,学须立诚,修辞亦需立诚。而修辞作文非以徒事雕刻藻饰为能,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和儒道文化信仰浸融在一起,所谓道德与文章为一者。诚如章学诚所曰:“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37]82而阳明心学“修辞立诚”的返本立论在道出心正与文正之间关系的同时,亦为如何到达“文正”的康庄大道指明了向上一路。张岱年曰:“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诚。……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把自己当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43]245-247但是立诚殊非易事,是以郑善夫曰:“今之豪杰之士不为少矣,其能谈圣人之道亦不为少矣。及观其隐微利害之际,往往变其所守者,何哉?志不坚也。志不坚者心不诚也。心不诚者名不称也。……然诚之一字,其实难识,稍有一息汩没,一毫矜持,皆谓之伪矣。”[44]193诚然,只要内心“稍有一息汩没,一毫矜持,皆谓之伪矣”。因此,一旦心性之不诚,其必然带来名不相称、言行不一的弊端,而亦难免使文辞流于伪饰,那么由此引发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无疑道出了众多学人的疑虑与困惑。
需要提及的是,在文学与创作主体之间,文品与人品的名实不符常被古人所论及。例如,张诩《戒庵老人漫笔》“无行无学”条引用桑悦语曰:“孙楚媚王济以驴鸣,魏收说文宣以狗斗,潘安仁拜贾谧之车尘,宋之问捧张昌宗之溺器,文人之无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则亦弗思甚矣。……黄庭坚云:‘人无古今,浸灌于中,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此之谓也。”[45]275可以说,文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契常常难以猝然断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的品质与文章彰显的道德并不具备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兼之“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语,是也”[46]163,因此每每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如其人”的失真。诚如王慎中《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遵岩集卷十》所云:“人之贤不肖,藏于心术,效于治行,其隐微难见而形似易惑,故其论常至于失实,非若有疾与否,可以形决而体定也。”[47]279观王氏之言,盖谓人文易感,而人心难测,张凤翼《谭辂》中对此亦有形象地论述,其引谜语曰:“尝闻前辈云一狂人称卖地理者,其言曰:‘尔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间,不须钱买人不见。’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儆世之言,即阴地不如心地好之谓也。”[48]477兹言心被重重包裹,人自然难以知晓测知。这样一来,可见且往往呈现道的文与不可见且或背离道的心自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即以倡言道统甚笃的韩愈论,一旦涉及言行层面,亦不能免俗。陈寅恪曾论述韩愈言行不一曰:“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夫韩公病甚将死之时,尚不能全去声伎之乐,则平日于‘园花巷柳’及‘小园桃李’之流,自未能忘情。明乎此,则不独昌黎之言行不符得以解释。”[49]尤其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之后,在其倡导的“文以载道”运动中,由于一味特别地将儒道强加于个体之上、注入文章之中,因此一旦涉及“文如其人”的层面,在很大程度上更易流于伪饰失真的境地。是以唐寅在《焚香默坐歌》中对假道学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多有揭露,其曰:“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人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悌忠信从此始。……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50]15-16逮及明朝,随着程朱理学的空前强化,因其过分强化个人对君主、国家的绝对义务与责任,而忽略了个体的自然天性和诉求,所以文如其人的理想目标似乎更难达成。而阳明心学正心的理论诉求或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结穴所在。可以说,阳明心学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而其倡言的“知行合一”又真正确保了儒道不再停留于空谈阔论,因此,在儒学载道话语依然风行之际,正心带来的心、道合一自然水到渠成地成为文如其人的过渡津筏。
具而言之,阳明心学正心的结果,免除了一切外物的滋扰与障蔽,而由此带来的“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亦自然将任何虚伪矫饰一并涤荡殆尽。与此同时,知行合一的道德践履,又进一步确保了儒家伦理意识的落实,因为阳明心学“‘知’即是‘行’,‘行’不离‘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在这里就不同于朱熹‘格物致知’的客观认识,而完全成为道德意识的纯粹自觉。”[51]244因此,心正所带来的付诸行动的道德践履便不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言,从而在扭转道德沉沦的世道人情之时,也使人洞晓“学有根本,有枝叶。在根本上做功最简要,心逸日休;在枝叶上做功,最烦琐,心劳日拙”[25]592,进而触发了时人“欲文之工美,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之文章皮毛”[52]的价值转向。这样,作者的道德之真与“文以载道”的固有传统便水到渠成地契合在一起,而不再使人有割裂失真之感。更进一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根本上促成“文如其人”到“文即其人”的转变指明了方向。钟惺评价王阳明曰:“盖学问真,性命正,故发之言为真文章。”[20]1596王艮亦曰:“身与道原是一件。”[42]37王畿则近一步阐说道:“道器合一,文章即性与天道。不可见者,非有二也。”[53]306以上钟、二王所言,庶几可作为阳明心学派诸人对文、道、人关系的理想期冀与终极诉求,所谓性命正而文真、身道为一、“文章即性与天道”者,似乎均可视为心学派“文即其人”观的形而上表达。
综上可见,有明之际,道不明却求之外,行不足而逞于文,因此,阳明心学与正学、正心、正文之间便有了热烈互动的可能与需要。具而言之,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士人学子为学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徒取儒道以资时文之用,迨至荣登科榜,便有“得鱼忘筌”之迹象,于是学而不行流衍成风。是故王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以疗救为学沉疴。在追名逐利之风的熏染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已被利欲湮没而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于是阳明又倡“拔本塞源”之论以补正人心。当然,鉴于“心口不一”在文学场域已成流弊,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题中之意,于是阳明复倡“修辞立诚”以正之,而“文即其人”观庶几可作为心学派文、道、人关系的终极诉求。
[1]胡越.王阳明[M].上海:中华书局,1925.
[2]嵇文甫.民国丛书第二编:晚明思想史论[M].上海:上海书局,1990.
[3]周振旭.王阳明论[J].大成会从录,1927(20).
[4]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柳诒徵.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9.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四:赠太守胡两台序[M]//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庄昶.定山集卷六:送戴侍御提学陕西[M]//金陵丛书丁集.蒋氏慎修书屋校印.
[10]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邵念鲁,撰.思复堂文集碑传[M].台北:明文书局,1991.
[12]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3]谢思炜著.燎之方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黄省曾.仕意篇上[M]//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薛甲.畏斎薛先生艺文类稿卷五:泮宫图记[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1.
[17]王樵撰.方麓集卷六:金坛县重修学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韩愈,著,马通伯,校注.答李翊书[M]//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9]梁储.鬱洲遗稿卷五:会试录后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0]王守仁,著,吴光,钱明,等,编校.答罗整庵少宰书[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1]王阳明,著,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3]王阳明,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J].大中华杂志,1915,1(7).
[25]孙奇逢.夏峰先生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6]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赠宗师章先生序一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8]李贽.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9]王九思.渼陂集:惑解[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0]吕坤.吕坤全集:呻吟语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J].国学论丛,1928,1(3).
[32]黄宗羲,撰,沈芝盈,校点.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3]焦竑.玉堂丛语卷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4]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35]焦竑.澹园集续集卷四:阳明先生祠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6]徐渭.徐渭集:赠成翁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3:908.
[37]章学诚,著,吕思勉,评.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8]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M]//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9]方祖猷,等,编,校.罗汝芳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40]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1]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42]王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3]张岱年.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44]郑善夫.少谷集卷十五:赠马子莘[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7]王慎中.遵岩集卷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8]张凤翼.谭辂卷下[M]//续修四库全书第11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J].岭南学报,1949,10(1).
[50]唐寅.唐伯虎全集:焚香默坐歌[M].上海:中国书店,1985.
[5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2]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2(4).
[53]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三(语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9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责任编辑卢劲英文审校孟俊一
The Relations between 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 of Xinxue and Ming Dynasty Prose
CHANG 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neon-Confucianism has become the knowledg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n most of students learn for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fortune, only taking Confucianism to get the office, learning without action became a fashion. Therefore, Wang Yangming advocated "knowledge-action unity", as a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for the study. Under the wind of steep profits, scholars' heart nature had been drown, so Wang Yangming advocated "extension of innate mor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gain the hearts. Of course, in view of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mind and speech, treating the disease of articles was on the agenda. Wang yangming advocated "xiu ci修辞" and "li cheng立诚"to rescue it. "Article is the man" could be used as a school of article, Taoism and the ultimate goa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Tao and the people.
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Rescue learning; Rescue the heart; Rescue the articles
2016-07-01
常威(1986-),男,河南睢县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阳明学、文章学。
B248.2
A
1001-733X(2016)05-0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