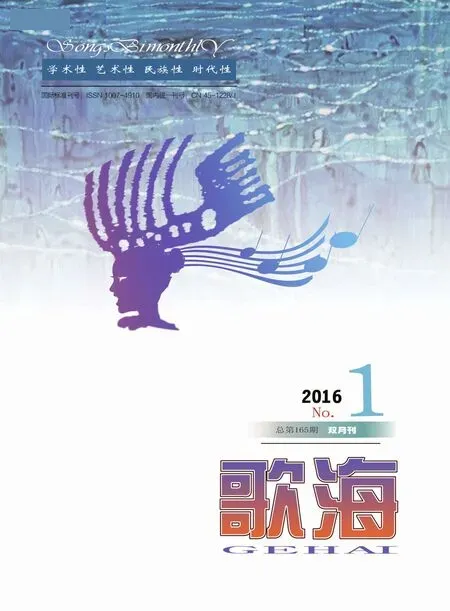谈电影《等郎妹》中的客家民歌
2016-03-18戴彦敏
●戴彦敏
谈电影《等郎妹》中的客家民歌
●戴彦敏
[摘要]通过对客家电影《等郎妹》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客家民歌进行分析,挖掘出客家民歌对客家女人的爱情、婚姻以及对客家人文民俗的反映与表现。
[关键词]《等郎妹》;客家婚姻;客家情歌
一、《等郎妹》电影的历史背景
电影《等郎妹》是根据林文祥、罗瑞曾同名客家山歌剧《等郎妹》为原型改编而成,获第36届国际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电视电影提名、第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数字电影奖等多个奖项。影片从女性视角出发,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旧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男权制度,真实地记录了福建客家大围屋生活、“走南洋”、“等郎妹”等特殊现象。原生态的客家人物,原生态的故事和自然浑然一体的演绎,把客家女人一代代的生活、情感与传统完美地展现了出来,被誉为“一部久违了的原生态艺术片”。
所谓“等郎妹”,是我国旧社会客家山区的一种畸形婚俗,是一种源于封建迷信的婚姻习俗。即年幼女孩嫁到没有男孩的家中,苦苦等待婆婆为自己生一个丈夫,而这个女孩就被称作“等郎妹”。倘若男家没有生男孩,等不到郎,等郎妹长大了,或是招郎,或是外嫁,由男家做主;有的“郎”年纪小的时候夭折了,“等郎妹”竟被迫与公鸡拜堂行婚礼,守寡一辈子的“等郎妹”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等郎妹”等不到“郎”的后果大多很惨,等到“郎”的命运也很无奈,往往造成“等郎妹”终身幸福被葬送的人间悲剧。电影《等郎妹》正是以客家大围屋几个“等郎妹”的曲折故事串起了人们对这样的真实历史的记忆。
这部影片除了有对客家女人形象的刻画,客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的展现,客家人生活环境的真实再现外,还大量运用了客家民歌。客家民歌在影片中的运用对于人物心灵深处各种思绪、情感的表达可谓是恰到好处、相得益彰。
二、《等郎妹》电影中的客家民歌
客家民歌凝聚了千千万万客家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劳动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缩影,透过它可以看到这一民系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看到其丰富的文化和多彩的风情。
其中,客家情歌以其质朴、天然的语言反映了客家人婚姻的各种形式,全方位的反映了客家婚姻习俗。对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婚姻形式既有歌唱,也有鞭挞;也表示出对“童养媳”“等郎妹”“隔山娶妻”等婚姻形式的诅咒;同时,也从发问、思求、拒绝、初恋、热恋、相思、感叹、谴责、失恋、离别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客家人的婚恋。
(一)直接反映“等郎妹”的情歌
影片中出现了两首在客家地区流传的关于“等郎妹”的客家情歌。一首是表述了“等郎妹”的凄苦人生的感叹。“月缺哩,月圆哩(那咯嘿)。等郎妹子(呀),好凄苦(呦)……”讲述了电影主人公“润月”阿爸送完“润月”到王家做“等郎妹”后,独自回家,在船上抽噎。而“润月”的儿时玩伴“春生”也在岸上希望能等到“润月”的出现。沧桑感的男声唱腔在此场景下唱出了这首情歌,可见作为父亲虽深知自己女儿未来婚姻、生活的凄苦,心疼不已,却又无能为力。而此时年幼的“润月”和“春生”哪里知道那将是一条漫漫不归路。
另一首则是“等郎妹”发自内心的诉苦情歌,述说着她们的悲惨生活,表露出“等郎妹”面对着自己年幼的小丈夫的无限辛酸,唱出了她们的苦闷、无奈和愤恨,充分折射出这种婚俗所产生的悲剧。
“十八娇娘,三岁郎;半夜想起呀,痛心肠;等到郎大,妹已老;等到花开,叶又黄”这首客家情歌,五次出现在电影中不同的场景,不仅是影片主题的反映,同时也推动着人物心理情感的发展。
第一次出现在“阿菊”(一个幼年的等郎妹)带着幼年“润月”看“数豆子的老阿姆”(一个年老的等郎妹)。音乐响起的同时配上悲凄的“数豆子的老阿姆”的沧桑面容,干瘪的数豆子的双手。让人们似乎看到年幼的“等郎妹”的“未来”,也敲打到“润月”幼小的心灵,使其开始好奇,困惑。而此次的歌唱者为中老年女性,歌声中叹息的语气,让人心里一阵酸楚。
第二次出现在阿姆生了男孩“思焕”也就是“润月”未来的老公后,“润月”晚上带孩子(“思焕”)时。只见小“润月”既像妈妈,又像姐姐一样抱着半夜哭闹的婴儿,疼爱的哄着入睡,娴熟的换洗,晾晒尿布,细心的喂着米汤。让人感受到无尽的亲情,可是转念一想,这却是“等郎妹”婚姻的起点。在稚嫩、无邪、清脆的童声唱腔中,不觉让人一阵心疼。小女孩从此就开始了她漫漫、苦难、未知的婚姻长路,让人不由开始痛恨这样不公平的封建婚姻制度。
第三次出现在“润月”与“思焕”办完婚礼,由于“思焕”一心要去“下南洋”,“润月”只有偷偷支持“思焕”,专门精心做了逢年过节才吃的米糕给出远门的“思焕”,晚上送走“思焕”后却发现忘把米糕带上,“润月”只有独自抽噎着啃着米糕。先是有声的哭泣,渐渐转为断断续续的抽噎,而后无声的难受,脸上露出无奈、失落的表情。看到“润月”一步一步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却也无力抗争,无法回头,听到了凄苦光阴的脚步。
第四次出现在“润月”与“春生”好不容易将要结婚,即将开始幸福的生活,正要放下为“润月”一直提着的心时,一纸告知“思焕”未死的来信,“润月”在巨大的悲痛中,毅然拒绝春生的爱,让她绝望地放弃了和“春生”结婚的机会,选择独自一人在漫长的岁月中等待渺茫的消息。“润月”的放弃和坚持确有悲壮之感,使人痛恨不已,甚至连带痛恨起了“思焕”。可是真正应该痛恨的是什么呢?在“润月”缓缓取下结婚发饰时,再一次响起了那带着叹息语气的中老年女性唱腔,一直延续到“润月”成为了又一个数豆子的“等郎妹”,无尽无望却又不得不等待并且永远等下去的“等郎妹”。随着岁月流逝,她的双手,面容也老去了。这与第一次的情歌出现形成了呼应,从音乐的角度,诠释了“等郎妹”的一生。
第五次出现则是电影的片尾曲,这次的唱腔却是老年女性唱一句,童声跟一句,女性唱腔的叹息与童声的清澈形成鲜明对比。听来是大人教唱,孩子学唱,恰似听到“等郎妹”一生的凄苦,听到那样的制度下一代代客家女性中“等郎妹”美好年华无情流逝的眼泪。
(二)反映客家儿女对自由爱情向往的情歌
客家人勤劳勇敢、纯朴、善良,向往浪漫而美好的爱情,有些客家情歌真实地描述了客家儿女的爱情心理,还可以看出客家人真挚健康的爱情观,有情有义的爱情崇尚,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持与坚韧。
影片中表现“润月”与“春生”的爱情发展,用了两首客家情歌。这两首情歌形成了顺承关系。
第一首是表述了“春生”真正追求他自己的爱情。出现在“润月”为支撑生活在艰难的挑盐路上突遇土匪,滑下山坡,偷偷跟随保护“润月”的“春生”这时出现安慰“润月”,却不小心透出了“思焕”死了的消息,“润月”情绪激动,欲跳河自杀,被“春生”救起。这样的场景下男声高亢的唱腔响起:“阿妹不知哥的心,哥心似火妹似冰。”表达出“春生”对“润月”深深的情感,对爱情大胆的表述。
第二首是“润月”将要嫁给“春生”,沐浴时,唱到“阿哥有心妹有心,铁杵磨成绣花针”。这一唱腔轻柔、美好,充满对美好爱情的憧憬。配上青青绿叶沾上水在娇嫩的皮肤上微微的拍打,温暖的水气映出“润月”娇美的面容。让人感受到有情有义,坚韧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
这两首情歌,简单的一句歌词,饱含深情。在唱腔和人物角色上都是对应出现,在感情线上形成顺承关系,可见这样的两首情歌在影片中为表现客家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巧妙之处。在影片中这样的美好因为“等郎妹”这样的畸形婚姻制度的影响而最终泯灭。本可喜,却又透出了可悲。
(三)客家童谣和婚俗山歌
客家童谣,是客家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特有表现形式,影片将客家人广为熟知的“月光光照地堂,骑白马过莲塘”这首童谣贯穿其中,三次在片中出现,前两次出现都是哄孩子,是在“润月”哄“思焕”和“阿菊”哄“虎仔”时,表现“等郎妹”既是姐又是娘的双重身份;第三次出现是在“阿姆”再次请回“春生”帮忙后,夜晚“润月”在床边思念“思焕”时,寄思念之情于儿时的一首童谣,含蓄且深刻。
影片中出现的反映客家婚俗的山歌。例如:“润月”与“思焕”圆房时,围屋里满坐对唱圆房山歌的客家男女唱出的“什么会暗又会光?星子会暗又会光;什么会下又会上?纸鹞会下又会上;什么会软又会硬?甜糕会软又会硬;什么会短又会长?……”这首山歌以谜语的形式,男问女答,巧妙而又寓意隐晦,却又在问答中传情表爱,使人感受到客家人表达情爱方式之热烈。
正是有了如此丰富的客家民歌元素的融入,使整部影片更加丰富和立体,极富感染力,扣人心弦,起到画龙点睛作用。
三、《等郎妹》在新时代下的历史意义
影片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和人物之间,甚至没有明显的性格矛盾,没有对坏人和恶势力的道德审判。有的,只有在人生历练的涓涓细流中,展示人丰富的情感和内心挣扎。在现代人看来,等待,显得难熬、寂寞、无助、苍白,而对于影片中的主人公“润月”,这样一个勤劳善良、坚强能干,集客家女人美德于一身的典型的客家女性,等待,成为自觉和美德,是“守得住”的道德堡垒。体现了世世代代客家女性特有的坚忍和内蕴,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对于“等郎妹”命运的思考和命运背后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典型的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影片风格始终保持忧郁的基调,画面以湿润的、雾茫茫的、阴郁的外景和经年累月烟熏成黑色的室内情景为主调。封闭的围屋、浓墨黑色的瓦顶、淅淅沥沥的雨声、木屐走过巷道的回响、贯穿头尾的山歌,流露出浓郁的岭南风情。影片淡雅,给人思考的东西很深透、很优雅。让我们近乎真实,面对面的了解到“等郎妹”制度,感受到这样一种婚俗离我们并不遥远。
现今,无法再去评价这样一段在不良婚姻制度下就注定是悲剧的无奈的婚姻与爱情,只能说爱情的脸无声无息地改变,不同时代的真挚情感经历过岁月的变迁和积淀,如今都变成了一份厚重的回忆。当代客家人在择偶、成婚、爱情方面所出现的种种新习俗,预示着客家婚俗健康发展的趋向。在新的形势下,客家人正以饱满的精神斗志、健康的婚恋思想出现在世人面前,自觉的婚姻行为,这种新观念同样也会在新的客家情歌文化中反映出来。
客家人传统的民俗、艺术、地理等各种客家文化形式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与研究。客家传统文化艺术与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结合与相融,一方面给予各种现代艺术以推动与升华之力,更是让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新的形式与依托,为其赋予了新的力量与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1]魏启清.略论客家传统情歌的婚恋习俗文化[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李小华.客家传统婚育文化的女性主义观照[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温萍.“客家山歌”的社会内涵和价值[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2,(2).
[4]方志鑫.当民俗遇上电影——浅析《等郎妹》中民俗元素的运用[J].中国电影评论,2013,(6).
[5]周晓平.客家山歌与客家女性婚恋文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2).
[6]佚名.等郎妹:十八娇娘三岁郎[J].神州民俗(通俗版),2013,(6).
作者简介:戴彦敏,女,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