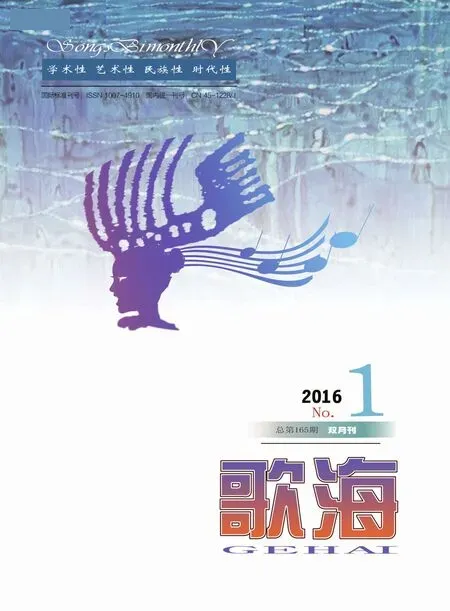由李渔之“重机趣”谈起
2016-03-18郭娜
●郭娜
由李渔之“重机趣”谈起
●郭娜
[摘要]李渔在填词度曲中提出的“重机趣”,也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深谙“机趣”真义的李渔,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度过了自由丰盈的一生。被一些人诟病以“俗”的李渔,也被更多的人激赏为“雅”。“俗”“雅”之间本无界限,“俗趣”“雅趣”义理相通。缺少“机趣”,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难免高冷;“机”“趣”兼备,方成上品之戏,上品之人。
[关键词]机趣;雅趣;俗趣;填词度曲
——《李笠翁曲话·词曲部》词采第二章:重机趣
谈起李渔,十分亲切。
2003年,笔者在备考武汉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时,一长串的书单中,李渔的《闲情偶寄》是古典戏曲理论的重头戏。但当时笔者崇洋媚外的心态甚嚣尘上,加上国学根底浅薄,戏曲剧本、戏曲演出从未接触,一本薄薄的《闲情偶寄》读了一个学期,仍然生涩艰辛、懵懂、莫名其意,只隐约记得填词度曲理当有“趣”。
当这些本不该空缺的功课一点点补上时,才渐渐明白李渔之“趣”,不仅在填词度曲,更在琴棋书画、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总之层层叠叠、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李渔之“趣”是生之趣,不独词曲。或赞其生之趣为雅趣,如尤侗“度其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如林语堂“(《闲情偶寄》)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或视其生之趣为俗趣,鄙薄之辞尽在他对平俗生活尤其女人的过度关注,其戏写尽男女之情事、穷尽俚俗谑浪。
在这里讨论李渔之“趣”为雅趣抑或俗趣并无意义。因为无论雅趣之赞或俗趣之恶,都只关注到其人其行之一面,或是对其言论、其文只言片语的过度解读。雅与俗,本就是一个相依相成的概念。或雅或俗,全在人心之不同,甚或一念之间,不同的民族尚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界定: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惠柱教授多年前就撰文写道,我国把引进的原版百老汇音乐剧抬举为“高雅艺术”,在它们的家乡实则“高俗艺术”——艺术水准很高的通俗艺术。而李渔的戏文,一“专为登场”,二“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此两点已经与仅博文人雅士“案头阅读”一笑的“高雅”之作划清了界限,其填词度曲、敷写宾白,力求“近俗”“贵浅显”“戒淫裹”“忌俗恶”等等,活泼泼的都是老少咸宜的“高俗”两字。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贺欧阳少帅致仕启》)。李渔之“趣”,大俗若雅,大雅若俗,若雅若俗。但此趣为“机趣”却十分明确。一“机”字,让李渔之“趣”远离“恶趣”,在雅趣与俗趣之间往来无碍、自由穿梭,道尽天上“谪凡”李笠翁的品味情怀,享尽风流才子“李十郎”的浪漫逍遥。据说,天雪地冰时,李渔为看梅花绽放的一瞬,支起帐篷在山中过夜;据说,为尽揽园中美景,李渔用纸屏建一座就花居,“四面设窗,尽可开闭”……李渔的芥子园,取佛家“至大的须弥山藏于微小的芥子之中”的意境,纳轩廊亭阁、花木流水于不及三亩之地,在这“流莺比邻”“藤花满架”的小天地大世界中,李渔对当时所谓风雅文人不屑一顾之事乐此不疲:组建家庭戏班,调教乔、王二姬,创作《无声戏》《一家言》《闲情偶寄》等著作,往来巡演于达官贵人之家,度过了一个大俗若雅、大雅若俗之人最辉煌、最惬意的时光。
李渔曾经给戏曲创作者开了一个书单:“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分明是修身养性、见心明性之方!古人修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别名“仙侣”“谪凡”“笠道人”的李渔借填词度曲中隐于市,参透世间百况、人间百味,进得了野村人家,入得了将侯厅堂,读得了圣贤书,写得了通俗文。填词作曲也好,生活处事也罢,“机”如同智商,“趣”仿佛情商。“机”“趣”兼备,方成上品之戏,上品之人。
寥寥三字“重机趣”,看似讲填词度曲,“词采”之下,却是活色生香、丰盈饱满的生活。我国传统曲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便是李渔的一生最好的注解。有人说这正是今人所追求的“慢生活”的品质、所喜爱的“轻喜剧”的格调,深以为然。
所以,李渔对“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致使传奇语言“满纸皆书”的反感可想而知。写到这里,想起一出摇滚京剧《荡寇志》,与李渔痛斥的“满纸皆书”不谋而合的是,这部被赞誉为吴兴国大师的作品“满台符号”:偌大一个舞台,到处滚动着各种莫名的人物与元素——白脸的宋江、超短裙的天寿公主、黑丝袜的李师师、白无常一样的吴用;摇滚、街舞、网游、时装造型秀、京剧;李师师色诱、梁山好汉光着膀子泡澡、宋江铁牛饮毒酒前后的缠绵不尽恣肆的场面,让剧情如野马奔腾,令观众难以驾驭审美。填词度曲,粉墨登场,无论古今,高大上的缘由——京剧改革也好,探索国际化路线也罢,解救不了“满纸皆书”与“机”“趣”全无的困顿。如摇滚京剧《荡寇志》,终究“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充满了“断续痕”和“道学气”。
深谙“机趣”之道的李渔,不但要求广涉群书“寝食其中”,更要求“为其所化”。如何“化”?“本之街谈巷议”,“形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觅古人”,“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让文学艺术与生活、大雅与大俗互相渗透相得益彰,于大雅中享大俗,于大俗中品大雅。关于李渔的“于浅处见才”,可以用王骥德的一句话来解释:“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方是妙手。”
笔者又想起林怀民来。一直对林怀民云门舞集的“亲民性”非常好奇,其观众上至七十老翁老妪下至三岁黄口小儿,从满腹经纶之学者到目不识丁之农工,皆可赏之乐之舞之。林先生是怎么做到“与众同乐”“全民共舞”的?2014年10月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创想周,请来了林怀民先生做讲座,题目为《咖啡与盐》,笔者找到了答案。这答案竟与李渔所身体力行的“机趣”不谋而合。林先生学识渊博、交往甚广、无物不纳却又虚怀若谷,他能够在热闹的街头市集与一个公交车司机、卖菜大妈言笑畅谈,也可以在安静的书房与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儒释道心交神会。他看得到芭蕾、希腊神庙、John Cage音乐的奥妙,也参得透中国舞、长城、书法、宋瓷的玄机,体悟古与今、中与外的契合相通之处。他说艺术家要做垃圾桶,把形形色色的东西都装进去,才能产生最奇葩的东西;他说艺术不是神秘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每个人都天生有艺术性,好的艺术家能够通过他玩的艺术激发每一个人的艺术性……林先生在最平俗、最真实的生活中踏紧中华大地起舞名曰“云门”——今人林怀民竟与古人李渔如此相似,最相似的地方是深谙“机趣”之妙,换做现代词汇便是“接地气”。
庄子在《秋水》篇最早提及“趣”字:“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对于庄子的“趣”,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解释是唐朝成玄英的“物之情趣”和清末郭庆藩的“心之旨趣也”,这在今人看来极雅却各执一端的解释,却正好道出了“趣”的两端:一边物情一边人心,其精神与今日极俗的一词“地气”灵犀相通,“地”是一方水土的“地”,“气”是时俗之风“气”,“地气”里包罗着生猛泼辣的世间万象。而真正的艺术家,既懂物情又晓人心,“接”得上“地气”,才可成“机趣”,其结果必定是“雅俗同欢,智愚共赏”。
真正的艺术家,首先是当下生活中的艺术家。
作者简介:郭娜,女,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上海戏剧学院人类表演学专业2013级博士生。
李渔:“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