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 张糖纸
2016-03-17文/铁凝
文/铁 凝
一千 张糖纸
文/铁 凝
责任编辑:江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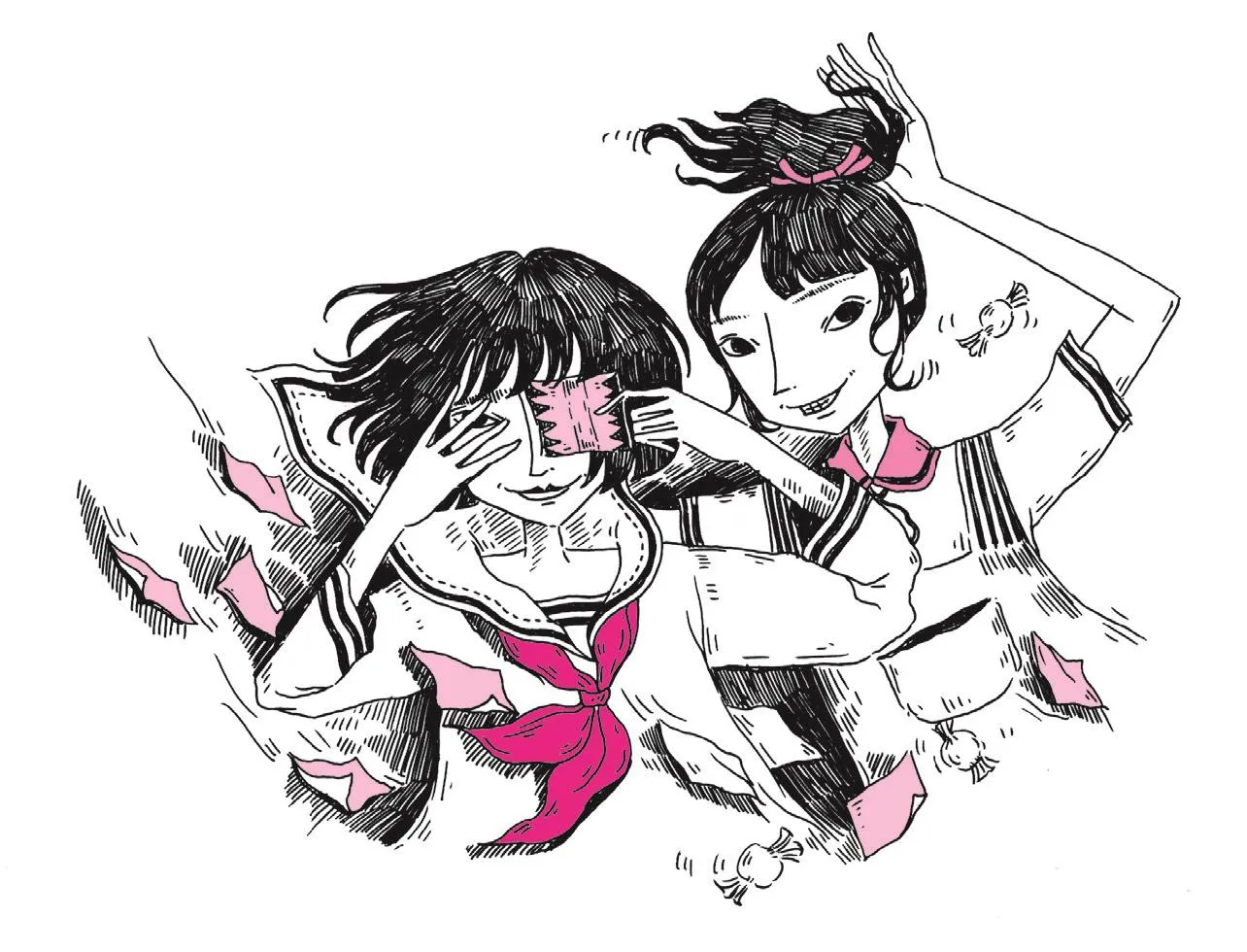
那是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我们两个人的种种游戏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笑呀,闹呀,四合院里到处充满我们的声音。
表姑在外婆家里养病,她被闹得坐不住了。一天,她对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相互看看,没名堂地笑起来。是啊,什么叫累呢?我们从没想过。累,离我们多么遥远啊。有时听大人们说,“噢,累死我了”,便觉得他们累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呀。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觉得糖纸有什么好玩。世香却来了兴致。“您为什么要我们攒糖纸呀?”“攒够一千张糖纸,表姑就能换给你一只电动狗,会汪汪叫的那一种。”
我和世香惊呆了。电动狗也许不让今天的孩子稀奇,但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玩具匮乏的时代,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玻璃透明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褶皱。攒够了交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给我们换。
从此我和世香再也不吵吵闹闹,外婆的四合院安静如初了。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那时候糖纸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我们会追逐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我和世香的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颗,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我们还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里,就飞速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一张糖纸就是一点希望呀!
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把它们洗干净,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干了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终于每人都攒够了一千张糖纸。
一个下午,我们跑到表姑跟前,献上了两千张糖纸。表姑不解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她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园子里闹,不得清静。”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我们玩的人是我的表姑啊。
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常说的累,原来就是胸膛里的那颗心突然加重吧。
我和世香走出院子,把那精心整理过的糖纸奋力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随风飘去。
孩子是可以批评的,孩子是可以责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骗的。欺骗是最深重的伤害。
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但所有的大人不都是从孩童时代走来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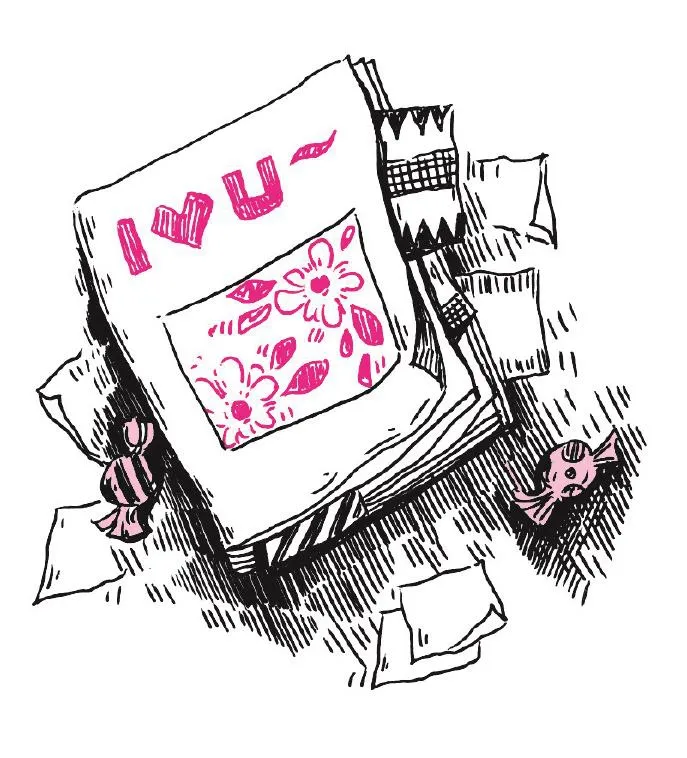
编 辑 絮 语
这篇文章,每读一次都会感到沉痛。它让我想到了“悲剧”这个词,并同时想到了鲁迅对这个词的定义:“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无疑可以这么理解:越是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就越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因此我便也明白了自己感到沉痛的原因:这是一篇具有“悲剧力量”的文章。
文中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那两千张糖纸。它们是“我”与世香两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这一过程越是不易,就越能凸显它们的“价值”,所以作者详细写了她们是如何获得糖纸的。两千张糖纸,在“我”与世香眼中,本是等价于两只电动狗的,但因为表姑的一句话,它们的价值就被毁灭为零,以至于被丢弃。在这里,那么多“劳动价值”被毁灭,已足够让人痛心。但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个从不知道什么叫累的孩子感到了累。因为表姑的欺骗,“我”和世香走出了五彩斑斓的明媚世界。从此,她们的世界不再透明,她们的内心不再轻盈——这样的毁灭,和那两千张糖纸被“毁灭”相比,孰轻孰重,无需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