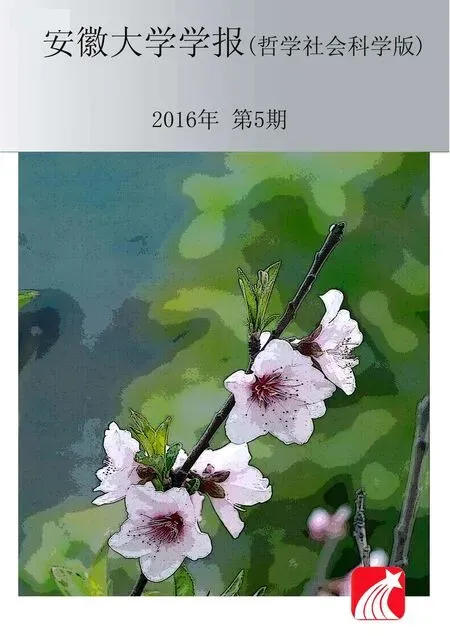语言和音乐的魔力
——《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流放”与“身份”
2016-03-17朱蕴轶
朱蕴轶,戚 涛
语言和音乐的魔力
——《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流放”与“身份”
朱蕴轶,戚涛
作为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流放”一直是澳大利亚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由流放而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一直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戴维·马洛夫和蒂姆·温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品《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依托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主人公的地域流放、文化流放和心灵流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讨。在两位作者看来,语言和音乐,同时作为文化符号和人类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形式,或许可以成为迁移者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而这种语言或者音乐,必须建立在地方认同感和人际纽带之上。在此对比研究基础上,读者不难发现澳大利亚两代人对“流放”和“身份”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其中的延续和演变,从而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和文化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未来的命运进行思考。
流放; 身份; 《一种想象的生活》; 《土乐》;戴维·马洛夫;蒂姆·温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互联网的兴起,人类加快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人口开始进一步大规模地迁徙和重组,旧有秩序和传统权威被打破或消解,绝对中心不复存在,世界变得更加开放、自由和包容。对于澳大利亚——一个最早由欧洲的流放犯组成的定居者殖民地来说,“流放”已经成为其民族记忆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下,这一记忆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加深。因此,“流放、寻根和定义‘家园’的困境、对新‘领土’以及固有传统所产生的身心冲突”*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 Routledge, 2002, p.23.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在澳大利亚文学长廊中,很多作家对新、旧秩序下 “流放”形成的原因和随之而产生的“身份”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认真的思考,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性情乖戾、离群索居,不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但他们虽处在社会的边缘,却并不消极遁世,而是在不安和迷茫中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不幸的是,他们的探索通常以失败告终,主人公的命运也通常以悲剧结尾。可是,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坛中,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和蒂姆·温顿(Tim Winton)却另辟蹊径,努力跳脱这种困境,为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作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现已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作家,马洛夫和温顿的出生年代、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创作背景和写作技巧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多部作品中却有着相似的主题和人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马洛夫文学生涯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Jim Davidson, Sideways from the Page: The Meanjin Interviews, Melbourne: Fontana/Collins, 1983, p.274.,《一种想象的生活》(AnImaginaryLife, 1978)自出版之日起就引起了国内外批评家和学者极大的兴趣,他们分别从放逐、异化、家园建构等不同主题以及作者的独特创作手法和语言入手,对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和马洛夫相比,少年成名的温顿虽已获得众多奖项的认可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圈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只在近几年内得到了一些改善。关于《土乐》(DirtMusic,2001),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在从空间和地方理论来探讨人物的孤独、迷失和自我追寻。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学者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过任何对比研究。马洛夫和温顿的年龄相距二十多岁,通过对其代表作的对比研究,我们能够看到澳大利亚两代人对不同时代背景下,因流放而产生的身份危机和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并可以发现其中的延续和演变。他们不仅对迁徙者的流放状态做了细致的描述,还探讨了新、旧秩序下流放产生的不同原因,并为迁徙者寻找理想家园做了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在《一种想象的生活》中,马洛夫提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是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二十多年后,当澳大利亚仍然无法拥有一门自己独立的语言时,温顿在《土乐》中尝试了用一种没有国界的语言——音乐,实现了自我的回归和民族认同。因此,《一种想象的生活》之于《土乐》是一种启发和引导,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继承和反思。本文拟以马洛夫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和温顿的《土乐》为基础,从地域流放、文化流放和心灵流放几个方面来分析后殖民语境中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感,探索身份建构的新模式。
一、地域流放:从故乡到他乡
本文所涉及的“流放”是个较宽泛的概念,它首先包括地域意义上的流放,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不仅是“一种被外力驱逐于家园之外,并放逐到异地的政治和文化性活动”*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更多的是指带有自觉意识上的自我放逐,主动地离开自己的故乡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散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动的地域流放正在逐渐减少,主动的地域流放却日益增长。比如有些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自愿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一个新的国度,生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以寻求一种边缘化的视野。马洛夫和温顿都是有着地域流放经历的作家。马洛夫出生于布里斯班,1958年前往英国任教,十年后回悉尼大学教授英语,1978年移居意大利,从事专业写作,1985年返回澳大利亚。此后,他常常往返于澳大利亚与意大利之间。温顿生长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1987年在法国、爱尔兰和希腊居住了两年,1989年回国后一直定居在珀斯北面的一个沿海小渔镇至今。他们散居异乡的经历在很多作品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种想象的生活》中的主人公奥维德(Ovid)是古罗马著名诗人,因为“他似乎强烈地反对统治集团”,被奥古斯都逐放到黑海边的托米思 (Tomis)。在这个“没有鲜花,没有水果,位于地球尽头的小村落”,奥维德与一群不知社会为何物、法律为何物的盖特人和一个狼孩生活了十年,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相较于《一种想象的生活》中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地域流放,《土乐》中的地域流放则是变化的、流动的。女主人公乔治娅(Georgia)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离职护士,虽是家中的长女,但从小就是个特立独行的孩子,不得母亲的欢心。她很早便离家读书,毕业后做了护士,在很多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流浪、对城市的厌倦以及几段无疾而终的恋爱,让她最终决定放弃这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和工作,在离故乡珀斯不远的一个小渔镇白点(White Point)和吉姆开始了同居生活。在这个小镇,乔治娅偶遇了故事的男主人公——音乐人路德·福克斯(Luther Fox),两人随即开始了一段恋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福克斯在无奈之下逃离了白点,一路北上,最终找到乔治娅记忆中的小岛。在故事的结尾,乔治娅也追随福克斯的脚步,来到这个小岛,两人就此再度相逢。
从《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三位主人公的地域流放来看,奥维德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乔治娅是主动的、自愿的;而福克斯的流放则是最复杂的,既有外部环境强迫的因素,也有主观意识的自我放逐。这三种不同原因造成的地域流放正反映了澳大利亚移民的主要构成方式。在《一种想象的生活》的开始,奥维德和托米思的关系无疑是澳大利亚早期移民和这片土地关系的真实写照。最初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大都是欧洲的流放犯,他们大都由于政治或法律因素被迫来到这个边远荒凉的国度,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悲苦的流亡生活。赛义德曾在“知识分子的流亡”一文中写道:“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止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爱德华·W ·赛义德: 《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4页。在随后的移民中,有因为经济、政治或者心理上的原因自愿或不自愿地来到澳大利亚的。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全球化,更多的移民是完全自愿地移居澳大利亚。地域流放的政治性已逐渐淡化,它正成为更多世界公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地域流放的成因以及状态的差异性和作者的创作时代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种想象的生活》出版于1978年,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两极对立和冷战状态之下,澳大利亚也结束了“黄金时代”,进入七十年代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下,主流文化的主导作用依旧比较明显,因此,正如《一种想象的生活》中的奥维德一样,对强势话语的挑战被视作一种文化叛逆,被迫流放也就成了挑战权威者的常规宿命。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旧的世界格局和绝对中心已不复存在,互联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更是把全球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自由、宽松和包容,人口的迁徙也更加频繁。《土乐》中的乔治娅和福克斯的流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人口迁徙在原因上的复杂化和形式上的多样性。
二、文化流放:语言和音乐的丢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身处异乡的流放者,远离自己的故乡和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自然而然就遭遇了语言的流放。海德格尔曾说过,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就是存在之家”*转引自胡壮麟《人· 语言· 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6期。,人在说话,话在说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更是人存在的寓所。同语言相似,音乐是另一种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作为一种声音文化,它反映了一个地域或民族的文明、文化特征和风土人情。因此,语言和音乐的流放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模糊甚至丧失。《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男主人公分别经历了语言和音乐的文化流放。
《一种想象的生活》的主人公以罗马诗人奥维德为原型。奥维德公元前43年生于罗马附近的苏尔莫,与贺拉斯、卡图卢斯和维吉尔齐名。他的诗歌技巧娴熟灵巧、语言流畅优美,在修辞上精雕细琢,诗歌风格却随性直率。公元8年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边的托米思,十年后在此郁郁而终。马洛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把一个诗人(奥维德)流放到语言边界之外:诗人所赖以生存的是语言。剥夺诗人使用语言的权利是最残忍的惩罚。如果语言对一个人极端重要,那么剥夺他的语言,让他借新语言或其他别的方式重新经历一切会是如何?我对此很感兴趣。”*M. Fabre, Roots and Imagin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Malouf, Commonwealth Essays and Studies, no.4,1979, pp. 59-67.在《一种想象的生活》的流放地托米思,村民们听不懂奥维德的拉丁语,奥维德也理解不了当地的部落语言,他们根本无法用语言交流。于是,奥维德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经历着“失语”的痛苦。他不得不“像孩子一样从头学习。……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其原本名称所赋予的魔力”*David Malouf, An Imaginary Lif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8, p.22.此后文内所引本书内容只随行标注页码,不另注。。这种痛苦在很多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在殖民过程中,语言是摧毁民族文化强有力的武器。殖民地人民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尼古基·瓦·西昂戈(Ngugi wa Thiong’o)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语言作为殖民者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它可以从底部腐蚀并彻底摧毁另 一种文化,使一个民族因为失语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载体,从而导致这种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隐没或淡出。”*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因此,奥维德所遭受的“失语”的痛苦实际上正是文化流放的一个表现,他正面临着失去罗马文化的危机。
同语言一样,音乐也是人们沟通的桥梁,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但不同于语言的是它没有确定的语义,音乐的动机、乐句、乐段等无法用语言来表现,而只能通过旋律、节奏、力度、调式等要素表现出来。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符号,音乐是用超越语言的表现方式来直接唤起人的情感波动的。“乐也者,其感人深”,任何一首乐曲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特定的情感需要而创作的,它比语言艺术更直接、更密切,也更能打动人心和激起感情共鸣。《土乐》中的男主人公福克斯是个民谣吉他手,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之家,一家人曾快乐地生活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一个叫白点的小渔镇。没有像大多数当地居民一样靠海吃海,借助着捕鱼业的繁荣而发家致富,住着“粉色砖墙的别墅”,开着“崭新的陆地巡洋舰 ”*Tim Winton, Dirt Music, Sydney: Picador, 2001, p.18.此后文内所引本书内容只随行标注页码,不另注。,福克斯一家三代生活在白点的边缘,以音乐为生,经常在当地的各种庆典活动中进行表演。在一次演出的途中,一场车祸夺走了除福克斯以外所有人的生命。作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福克斯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时常回忆起和家人在一起以音乐做伴的幸福生活,沉浸在悲伤、自责和内疚中,久久不能自拔。音乐作为他和家人的纽带,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他想要逃离痛苦的过去。于是,他开始远离音乐,并焚烧了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在福克斯离开白点,一路搭顺风车向北时,这个创伤仍没有丝毫的愈合,“哪怕是让他听最无聊的板球比赛也好过任何音乐”(219页)。音乐不仅是福克斯谋生的手段,更是他存在和自我价值的体现。烧毁文件使福克斯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个“隐形人”;逃避音乐则成为他自我文化流放的一个手段。
作为《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重要的文化流放形式,奥维德的“失语”是被动的、不情愿的,福克斯的音乐流放虽有外界的诱因,但更多却是其自发、积极、主动的。这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文化流放正是各国移民在澳大利亚异域文化中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他们在处理澳洲同母国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澳大利亚第一批的移民大部分是流放的犯人,他们像奥维德一样被迫远离自己的故乡,在边远的地方开始痛苦的流放生涯。远离欧洲文明,他们被动地进入了一种文化流放的状态。之后,越来越多的移民自发地来到澳洲,如福克斯一样,在遭遇了新的文化冲击之后,他们中有些人主动地切断与过去的种种联系,试图摆脱旧的“自我”,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中。
三、心灵流放:无根的漂泊
后殖民文学作品的流放主题往往表现在地域、血缘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这些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必然导致主人公心灵的流放。心灵的流放未必以地域流放为前提,“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语言、生活方式、宗教等面临消亡的危机时,或者不得不接受另外一种文化评判标准的仲裁时”*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第133页。,心灵流放的状态就产生了。这些流放者要么身处异乡,远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要么徘徊在社会的边缘,与当地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在这个状态下,旧的自我无法再延续下去,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当新的环境很难融入,新的自我尚未建立时,流放者就成了“无根”的漂泊者。因此,心灵流放可以理解成一种“无根”的感觉。《一种想象中的生活》中的奥维德、《土乐》中的福克斯和乔治娅都经历着由地域和文化流放而带来的心灵流放。
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边,奥维德与熟悉的帝国文化处于一种割裂状态,作为罗马著名诗人的身份已不复存在。在托米思,当地的盖特部落文化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语言不通,奥维德连和他们交流都成了障碍,难以适应新的社会语境,新的自我自然无法建立。此时此刻,奥维德便成了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这种“无根”的状态使他的心灵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正如王宁所言,流亡者的“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土乐》中的乔治娅是个典型的漂泊者。她天生具有一种孤独感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如果别人都往东,她偏要往西”(166页),与三个妹妹不同,她有点男孩子气,不讨母亲喜欢。“母亲最大的爱好是逛街购物。可正是这个爱好让乔治娅远离加特兰德家的女人们,而让她的姐妹们和母亲更加亲近”(168页)。和家人的疏离让乔治娅早早就离家读书,四处漂泊。当她最终厌倦了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她便辞去工作,在白点和吉姆过上了相对悠闲、稳定的同居生活。可即便这样,她也丝毫没有归属感,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位白点的“局外人”。吉姆的财富和地位不能排遣她内心的孤寂和空虚,她的努力也没赢得两个孩子对她这个“继母”的信任。在她眼中,白点只不过是另一个只注重名誉和金钱,而缺少理解、尊重和关爱的地方。于是,她只有靠网络和酒精度过了一个个无眠之夜。马克·奥格(Marc Auge)认为网络是个虚拟、流动的空间,具有“非地方”(non-place)性*Britta Kuhlenbeck, Creating Space in Tim Winton’s Dirt Music. In Dose Gerd & Britta Kuhlenbeck(eds.), Making Space Meaningful, Tubingen: Stauffenburg Verlag BrigitteNarr Gmblf, 2007, p.61.。因此,此时的乔治娅虽然看似有了安定的生活,但本质上还是个漂泊者,她的“无根性”让她不仅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白点人”(18页),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和乔治娅相似,福克斯也是白点的“局外人”。虽然和白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但在那次灾难性的车祸发生之前,福克斯的心灵并未有丝毫的“流放感”,因为家人和音乐才是他心灵的归宿。可是,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家人,让他不敢再碰触音乐。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失去音乐和身份的福克斯,为了生存,不得不偷偷出海捕鱼,成了当地居民排斥的“非法渔民”(shamateur)。和乔治娅的相遇和相恋虽然让他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慰藉,可得知乔治娅是吉姆的同居女友后,他的内心就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十字架。在经历多重创伤之后,福克斯逐渐失去了在白点的“根”,最终选择逃离这个伤心之地,一路北上。
人类学家乔治·斯班德勒(George Spindler)指出,人类永恒的自我“是一种对过去的延续,对个人生活经历、生活意义以及社会身份的延续。这些能够帮助人们确认自我”。而这种自我的延续是需要相应的社会语境的,“社会语境中的自我总是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语境的要求,而当永恒的自我被现实语境中的自我不断强暴时,自我就失去了安全感”*George Spindler & Louise Spindler, The Processes of Culture and Person: Cultural Therapy and Culturally Diverse Schools. In Patricia Phelan & Ann Locke Davidson (eds.), Renegot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 &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3, p.36.。显而易见,奥维德、乔治娅和福克斯这种“无根”的漂泊感就是因为自我失去了安全感,而这正是后殖民语境中心灵流放的主要内涵。
四、自我回归和民族认同:语言和音乐的重构
在《知识分子流放:放逐与边缘化》一文中,赛义德这样来描述流放的状态:“流放存在于一个中间位置,他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它处于与旧的系统半牵连半脱离的位置,它一方面是怀旧的和感伤的,另一方面又是模仿的能手,并偷偷地放逐。”*爱德华·W ·赛义德: 《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49页。《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主人公们就处在这一中间位置,流放不仅表述了他们远离故乡和家人的状态,更表达了对他们对“家园”的渴望和追求,这个“家园”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隐喻的,“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结果,一种心理归属的结果”*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第136页。。对于如何追求自己的“家园”,在“偷偷地放逐”中获得超越,不同的后殖民作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为后殖民语境的人们获得自我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马洛夫和温顿则结合各自的流放经历,分别在《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通过语言和音乐的重构,实现了主人公自我的回归,表达了作者对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思考。
流放在托米思的奥维德,就处于这样一个微妙的“中间位置”,一个罗马文化和盖特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交融和相互趋同的位置。弗兰兹·法侬(Franz Fanon)认为:“话语是承担文化的,它支撑着文明的重量。”*Fran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1967, p.17.面对完全陌生的盖特文化和语言,奥维德经历着“失语”的痛苦,面临着失去罗马文化身份的危机。因此,如何重新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语言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初,他像个孩子一样,被迫用手势或咕哝着表达着自己,可这样交流很困难,因为发生在这儿的一切无法用以前的经验来解释。奥维德的“失语”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发现了一片鲜红的罂粟花从。这一片鲜红的罂粟花在奥维德的语言重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罂粟花和奥维德一样,本都不属于托米思,是被风“吹进了”这片土地。其次,罂粟花让奥维德意识到他竟然可以用以前熟悉的拉丁语来描述这个陌生的环境中的景象。于是,当拉丁语中的“鲜红”“罂粟”这两个词重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其他有关颜色和花卉的语言随之涌现,他又可以“创造春天了”(31页)。此时此刻,在罗马文化和盖特文化的对抗和融合的张力中,奥维德第一次在这个新环境中重构了原有的语言。
马洛夫认为,对于一位诗人来说,“只有语言才能让他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语言的魅力让奥维德决定学习盖特语,因为只有这种语言才能帮助他了解这个环境中的一切,让周围的事物变得真实起来。很快,这位拉丁语大师就被质朴的盖特语吸引了,认为“它所表现的是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统一。我相信我能用这种语言作诗。从这种语言的视角来看世界,我有不同的领会。这是个不同的世界”(65页)。
就在奥维德的罗马文化身份逐渐消退,向盖特文化逐渐靠拢时,一个狼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个在托米思森林里发现的孩子显然不属于托米思或其他任何人类居住的地方,他身上的“野性”让奥维德很是好奇,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秘密玩伴,他们在一起交流时使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语言:“在某个时间,我的身体开始改变,长大成人,那个孩子离开了,再也没有出现……我忘记了我们曾经使用的语言。”(10页)他把狼孩带回盖特部落,教他盖特语,教他学会使用人类的工具。可是不久,村里的一个孩子和部落首领相继病倒,人们开始认为这个狼孩是个不祥之物。于是,奥维德主动地跟随狼孩离开部落村庄,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在这儿,奥维德惊讶地发现狼孩使用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的语言。他把自己等同于自然,没有“事物是他者”的概念,宇宙万物仿佛都是他的“延伸”(96页)。因此,当天下雨时,他说“我在下雨”;当他模仿鸟鸣叫时,他把自己想象成那只鸟。奥维德顿时明白真正的语言是和自然合二为一的语言,只有像狼孩这样,“万物的精神才会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间,我们才会因此变得完整”(96页)。于是,他开始学习狼孩的语言,并发现“它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那么和谐。我们曾经掌握这门语言。我在小时候曾经使用过。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它”(98页)。狼孩的出现让奥维德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他神秘的玩伴再次教给他已经遗忘的语言,引领他走出语言的流放”*刘宁:《此地即中心——马洛夫〈一种想象的生活〉中的语言流亡感和文化身份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年第5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与生活形式浑然一体的日常语言是人的真正家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页。至此,奥维德通过语言的重构完成了新的身份建构。最终,在一片没有时空界限的旷野中,奥维德惊喜地发现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他发现了自己生命的“足迹”。他看着狼孩“光着身子,迈着轻快、愉悦的步伐”远去,与天地融为一体。在奥维德坦然走向死亡之际,时空已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夏季。冬季。我欣喜若狂。我三岁。六十岁。六岁。我就在那里”(152页)。
马洛夫在一次采访中曾坦承他“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发生在澳大利亚,而描述这些生活经验的语言却来自另一个国家。这一直是澳大利亚的大问题”*Ray Willbanks, Australian Voices: Writers and Their Work,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p.148.。麦克斯维尔(Maxwell)也说过,来自于定居者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作家在写作中“将自己的语言即英语置于一个异域环境和一套全新的体验……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文字和意义的扭曲”*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p.22.。如何消除语言的扭曲,读者显然可以在《一种想象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借助奥维德的经历——从流放到身份迷失再到自我回归,马洛夫似乎在告诉后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人,只有学习和创造一门新的语言,才可以实现对澳大利亚民族的认同和新的文化身份建构。
在第一批移民踏上澳大利亚两百年之后,他们的语言为了适应本土的经验和使用者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遗憾的是,纵使有了明显的口音和词汇变化,澳大利亚英语仍然只是英语的一种变体,而不是一门全新的语言。马洛夫认为:“它所描述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并不相同……我们的语言和这片大陆之间的鸿沟让我们感到非常失落。”*Paul Kavanagh and Peter Kuch, Conversations: Interviews with Australian Writers, North Ryde: Angus & Robertson, 1991, p.185.批评家万斯·帕默(Vance Palmer)说过:“我们的艺术必须是原创的,就如同我们的动物和植物是原生的一样。”*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p.133.没有原创的语言,马洛夫似乎在提醒读者,奥维德的经验可能只是“一种想象的生活”。
在原创语言暂时缺失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身份的建构呢?温顿在《土乐》中借助音乐做了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如同语言是奥维德作为诗人的工具和价值体现,音乐毫无疑问是福克斯作为一名吉他手存在的必要条件。远离音乐,他就远离了家人和社会,从而丢失了他原有的文化身份。奥维德通过语言的重构走出了“失语”的状态,完成了新的身份建构,那么福克斯可以通过音乐的重构来实现自我的回归吗?
如果说奥维德新的文化身份建构主要得益于狼孩的启发和引领,在福克斯的实现自我的道路上也有着类似的引路人,乔治娅就是其中一位。在福克斯逃离白点,踏上北上的流放之旅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他只是不想像“一只野狗一样生活在白点的边缘……他要去一个干净的地方。那儿有水和食物,不必为了生计而偷偷摸摸。一个完全只属于他自己的地方。没有马路,没有城镇,没有农场——没有残忍的人类。四周树木环绕,可以在那儿散步”(294页)。他一路走,一路追寻着心中的圣地,直到有一天在布鲁姆(Broome)他猛然想起乔治娅的故事和她在地图册中标注的那座位于加冕礼海湾的小岛,意识到“就是那个地方,那就是我的目的地”(294页)。
在福克斯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之后,他迎来了第一次重构音乐的契机。他遇到了两个神秘的土著少年。一个是没有肚脐的孟西斯(Menzies),一个是深受先兆性梦境困扰的阿克塞尔(Axel)。阿克塞尔喜欢音乐,有一把吉他,但总弹不成调。在两位少年的请求下,福克斯终于再次拿起了吉他,开始演奏,沉浸在音乐中的少年也不由得低声吟唱起来。同语言一样,音乐也是一种人类用来交流思想、表达情感、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遗憾的是,福克斯的这次演奏并非发自内心,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完全是被动的,与两位少年没有任何的交流。看上去福克斯虽然再次接触了音乐,但他还没有能力、也不情愿借助这个工具与他人和社会产生任何联系,因此,福克斯在这个阶段的音乐重构是失败的。这次失败也从侧面印证了长久以来欧洲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冲突与磨合,以及欧洲殖民者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所造成的两者之间的不和谐关系。
这两个土著少年虽然没有帮助福克斯走出音乐的流放,却让他意识到“音乐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伤害”(307页),并指引他找到了加冕礼海湾中的那座小岛。正像乔治亚所描述的那样,“小岛的表面是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 沙滩上长满了猴面包树,鸟儿在绿荫间穿梭(315页)。在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上,福克斯每日潮落而作,潮起而息。他和大海里的鲨鱼嬉戏,给他们喂食。海里丰富的资源让他不再为生存而发愁,他甚至开始尝试岛上的绿蚂蚁、无花果和浆果。“这里总有意想不到的乐趣”(353页),福克斯似乎渐渐忘记了痛苦的过往,心里创伤逐渐愈合,但“时不时他会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焦虑”(355页)。在这个世外桃源,“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一本书都没带……哪怕是一本电话簿或者购物清单也会让他心满意足”(355页)。此时,对外面 “文明”世界的思念,唤醒了福克斯心底对音乐的渴望。幸运的是,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岩壁上布满土著人绘画的山洞,山洞里的一轴尼龙鱼线给了他再次重构音乐的可能。他把鱼线拴在两棵树之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乐器,“它发出好听的‘嗡嗡声’,虽然不是自然界的声音,却和自然完整地融合在一起。福克斯犹豫着清了清嗓子,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368页)。福克斯为这奇妙的声音而兴奋,他拨弄着琴弦,在音乐中他仿佛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他穿过沙漠、山峦和平原,最终重回“家园”。这个“家园”不仅仅指他和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农场,也暗示着他内心的家园——音乐的重构。音乐让他终于可以不再害怕和逃避过去,能超越自我、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创伤。他沉浸在“土乐”的演奏中,“黎明时分,周围一片寂静的蓝色,福克斯醒来,走向他的乐器。他用音乐迎接每一天的开始,在落日时分才和它说再见。寻找食物和吃饭倒成了一种娱乐和消遣”(402页)。至此,福克斯的音乐回归之旅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唯一的缺憾是音乐作为交流的工具或沟通的桥梁的功能还未体现,因为无人来分享他的音乐和内心的感受。在最后时刻,乔治娅再一次扮演了他的拯救者。身为护士的她,似乎是上帝派来给福克斯疗伤的。就在福克斯一面享受着“土乐”带给他的兴奋和狂喜,一面思念着乔治娅时,乔治娅已经踏上了追寻福克斯的道路。终于,他在岛上发现了乔治娅的踪迹,他知道她就在这儿。“他觉得真实的自己又回来了……他知道他还活着,整个世界都在他的体内活着……无花果树在微风中摇曳。袋鼬躲进了岩石下。他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451页)。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是一种形象的感人的沟通方式。在受地域、文化等因素制约而无法通过重构一种新的语言来实现自我的回归和民族的认同时,音乐作为语言的延伸和补充,不啻为一种新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土乐》,温顿似乎想告诉身为澳大利亚主流的白人移民,逃避过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要像福克斯一样放下心里的包袱,去勇敢地直面自己曾作为流放者和曾屠杀、驱赶土著居民的历史。只有把宗主国文化和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像福克斯一样的“土乐”,真正地融入这块土地,建构新的民族身份。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迁移异常活跃,如何消解因地域流放而带来的文化流放和心灵流放,把“流放”变成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体验,成为各国移民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马洛夫到温顿的探索和实践,读者不难发现,澳大利亚的当代作家已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积累了一些较为成熟和成功的澳大利亚经验,那就是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桎梏,重新审视“我他”的对立,建设一个“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多元共生的中间道路。在两位作家看来,这个中间道路可以具体到某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既可以是《一种想象的生活》中“没有事物是他者”的狼孩的语言,也可以是《土乐》中福克斯用一根鱼线演奏的“土乐”。正如德里达所说:“对我而言,我相信,总是而且必须不止有一种语言……我必须尝试以这种方式写作,即他者的语言不会在我的语言中受损失,并允许我介入而又不使我从中受到损失,接受我的语言的好客,而又不在我的语言中迷路或被吞并。”*德里达:《解构的时代》,何佩群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期。换言之,这些语言都是个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诠释世界的不同方式。当然,马洛夫和温顿也提出这个中间道路必须建立在地方认同感之上,即“人对这个地方的依恋、融入和关爱等”*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Books, 1976, p.114.。比如:奥维德是在对托米思的逐渐接受过程中开始学习盖特语,而最后他更是认识到只有与自然合二为一的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福克斯则是在对加冕礼海湾小岛的追寻和认识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土乐”。地方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海德格尔以‘栖居’(dwelling)概念描述了自我与地方之间连接与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地方与自我之间的社会、文化与情感连接表明地方对于自我来说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抽象的、物质的生存空间,更体现出了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体系”*转引自朱竑、钱俊熙、陈晓亮《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人文地理》2010年第6期。。除此之外,人际纽带也是建设中间道路的必要条件。《一种想象的生活》中的狼孩以及《土乐》中的两个土著少年和乔治娅在语言和音乐的重建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狼孩引领奥维德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语言,并最终和自然融为一体;土著少年帮助福克斯寻找到理想中的圣地,乔治娅不仅给福克斯指明了自我流放的方向,还成了“土乐”的见证人和分享者。通过这两部作品,作者似乎在暗示,语言和音乐同时作为文化符号和人类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形式,或许是帮助迁移者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工具。同时,这种语言和音乐又必须在某位引领者的帮助下,在一个适当的地方才得以建构。通常,这个引领者是一个非现代文明人或是一位女性;这个地方远离城市,是一片旷野或是一座孤岛。如此种种,不仅和澳大利亚由于重洋包围而远离其他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也反映了其异质文明杂交生成的民族个性,同时也是两位作者对现代文明一种反思和追问。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在享受着各种便利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迷惘、焦虑、危机和灾难。环境会如何变迁?人和土地的关系应该如何发展?文化碰撞会产生什么结果?迷失的身份该如何定位?这些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一直以来探讨的主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校:刘云
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5.009
I106.4
A
1001-5019(2016)05-0063-09
朱蕴轶,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安徽 合肥23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