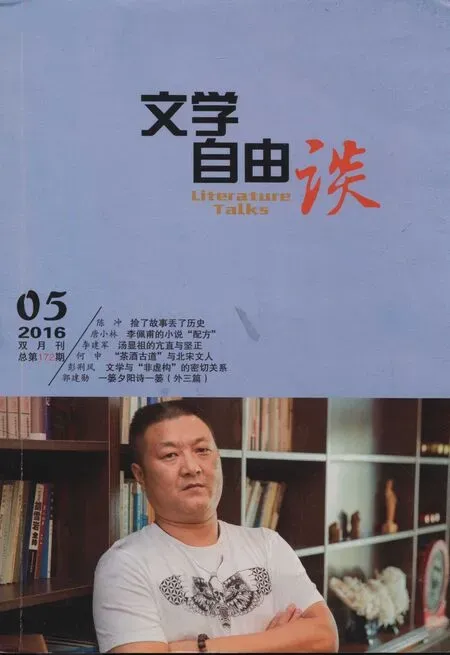杂说桂圆与文学
2016-03-17何永康
□何永康
杂说桂圆与文学
□何永康
一
四川泸州市有个张坝桂圆林,在长江边,整个林带约10公里,沿江铺开一条长长的绿色长廊。当地人骄傲得很,说是天赐水土,就这一段江岸得天独厚,出产别样的桂圆。其实,我想泸州人老祖宗也未必就知道这里适合桂圆生长,只是偶然发现一种野果,一品,味儿还不错,于是栽培,于是改良,于是推广,前提是充分认识这方水土的奇妙,并保持水土不“流失”。
我就想到了文学创作,也有一个“水土”的发现和“保持”问题。每个作家诗人都有一方适合自己耕读的水土,或者早已生出鲜美的野果了,你没发现;或看到了没引起重视,以为那是野果,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去艳羡别人的家花。假如真是这样,你就是暴殄天物了,或者说是“抱着金饭碗讨口”。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水土”,不管风水如何,土质如何,都不要妄自菲薄,而应该敝帚自珍——毕竟是自己的自留地。
其实,也不必急着让野果“修成正果”。实践证明,“正果”修成后要么味道纯正但口感庸常,要么被普遍栽种,产量太高以至于烂市,还不如保留原汁原味的好,套用一句电影台词——“让野果再野一会儿吧”。
二
这片桂圆林有句广告词,叫“人神共居”。我不知道人与神能居住在一起吗?或许是到了一个好地方,神明也癫狂成凡人了,凡人也飘飘然忘乎所以,觉得自己过上了神仙的日子。这也说得过去。然而,文学殿堂能够人神共居吗?我看不能,那要打架,要么神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要么人掀翻了神龛。因为各自的位置不同,使命不同。神的文字是神谕,人的文字是人声。在神的眼里,那文学的桂圆是禁果或者是供果,凡人是不能偷食的;在人的眼里,文学的桂圆就是大家来品食的,谁都可以拈几颗尝尝。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著名”人士把自己当成了神——比如王母娘娘——把桃子垄断起来,美其名曰要搞“蟠桃会”,其实私下早与玉帝老儿一起啃食了不少。这蟠桃会很讲地位和品级。为省事,不妨把百度的词条粘贴过来——蟠桃会是盛大而庄严的,低层次神仙们在蟠桃会上要注意行为举止,否则很容易出轨被严厉惩罚。例如,根据“神界权威史书”《西游记》所述,卷帘大将(沙和尚)仅仅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破一个琉璃盏(琉璃制的盛东西的器皿,其实就是个灯盏),就被罚落入凡间;而天蓬元帅(猪八戒)则因为酒后性骚扰天宫头号交际花——蟾宫的嫦娥小姐,被罚转世到凡间,并且因操作失误转为猪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曾经因为地位过低而得不到参加蟠桃会的资格,引起他暴怒而搅乱了一届蟠桃会,被擒获后判处死刑。
与其这样,还去参加个什么鸟蟠桃会!俺们花果山、高老庄有的是野果。
我听到一个学者恭维一个诗人,说他是诗歌界的殿堂级人物。我掩口窃笑,使不得也,哥哥!上了殿堂,只有正襟危坐供人朝拜的份儿了,哪有我等兄弟在庙宇之外的荒山野地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痛快啊!
三
张坝桂圆林,除了生长桂圆,还生长荔枝,早一个月成熟。荔枝和桂圆树之间还生长着一种相近的植物叫桢楠。早先的张坝人用桢楠作隔离带,隔开一家一户的园子,也隔开荔枝和桂圆。天长日久,就因风的吹送和鸟的“衔接”,某些桢楠被嫁接上了桂圆和荔枝,成为异树。荔枝果实硕大,色泽鲜红,一串串激情饱满,加之有诗人广而咏之,比如“日啖荔枝三百颗”,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颇有名气,我以为就很像诗歌;而桂圆在其后才慢慢成熟,不温不火地堆在枝头,呈现的苍黄是低调和厚实的颜色,其实就是散文的做派。那隔在中间的桢楠,也可以说是边缘文体如散文诗,或新兴文体如非虚构什么的。
同一方水土,长出不同的果子,是造物主的恩赐,也是植物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因为都是“无患子”科,所以群居,一起抗拒灾难,彼此遮风避雨,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根须相通,纠缠不断,养分交叉,各自的味觉元素搅合混杂后相互吸收,才有了彼此独有的风味,这正好可以说明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
不妨把荔枝和桂圆剥开皮看,结构完全一样,都是肉包核,不同的是肉有厚薄,核有大小。当然,味道也是有些差别的。
四
交20元钱,换了个标识牌挂在胸前。挂这标识牌是为了区别于那些可以免费游览但不能采摘桂圆的游客,表示你付了费,可以在桂圆林中的任何地方任何一棵树采摘桂圆,吃多少都可以,吃不完的可以买走。我于是四处游走,但见桂圆果实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我就选那大个的吃,但味道一般,还有些淡。一老者在旁边隐笑,问其何故,说,选小的吃,小的是老树子结的,味道要浓厚一些。一试,果然。原来,桂圆树龄越长果实越甘美。树老了,和人一样,代谢功能差一些,果实就小一些,也少一些,有的老树是几年才挂一次果,果实的孕育期生长期很长,加之老树都高达二三十米,阳光照射更充足,吸收天地之精华就更多,虽然个头小,颜色深沉,不受看,但好吃。
我就想到我们这些在文学圈内瞎混的“老家伙”了。以我们现在有限的才力和精力,就慢慢写一些“小东西”吧,和年轻人拼个头、比花色、讲效益、论产出,我们毫无优势可言。年轻的果子虽然不免酸涩,但外形圆润,汁液充盈,品相也好,是很有市场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写文章,不妨让孕育时间更充足一些,“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否则就是早产儿,早产的新生儿总会有这样或那样发育不良的问题。
小,是浓缩;少,是稀缺。大餐当然可以大快朵颐,小吃却更值得慢慢咀嚼和品味。
五
泸州的桂圆和其他地方的桂圆味道有些不同。我在岭南地区吃过桂圆,在台湾吃过桂圆,出国在新马泰也吃过桂圆。那些热带桂圆个大肉厚,味道却是极为普通的纯甜。泸州这桂圆入口时的味道十分奇妙,一瞬间的感觉没人能说清楚,也就是说有点“异味”,慢慢地,把人的味蕾引入正规,最终被甜美裹挟。经验告诉我们,“异味”往往就是美味,比如榴莲,比如杨桃,比如橄榄……都不是一般意义的“甜美”所能概括的。写文章也是这样。好的文章往往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 “异味”,但又不是无休止地“异”下去,这其实有点与“和而不同”相反的意思。
抓住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异味”,调制后再加入寻常食材好好烹饪一番,就会抓住读者的胃。
六
桂圆,又叫龙眼。但泸州人为何把节日命名为桂圆节而不是龙眼节呢?
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得要领,只好自己胡乱猜测揣摩了。
龙眼是学名,是一个象形的叫法,剥开皮,显现出的一个圆球体,肉白,核黑,酷似动物的眼珠,只不过黑色的眼珠外面蒙一层灰白色的果肉。龙眼的叫法图腾色彩很浓,千百年来我们以龙的传人自诩,龙文化由来已久,深入人心,但泸州人为何不趋不附,不在一个“龙”字上大做文章呢?我想,一是中国龙太虚无缥缈了,看不见摸不着;或是太神圣太庄严太有象征或隐喻,反而让人退避三舍;三是把龙的眼珠含在嘴里吸吮,也有点残忍和不恭,想想都会脊背发凉。
相比之下,桂圆就接地气得多。这果子于农历八月上市,正是桂花吐蕊的时节,所以这段时间又叫桂月,在桂月成熟的圆圆的果子就叫桂圆,很好理解,也很形象,似乎还带点诗意。桂圆是民间的叫法,迎合了百姓崇尚简单朴素的审美心理。而龙眼是书面语,离人间烟火远了点。
由此我又想到当今文学的流弊,一是追求“高大上”,言必称“主义”,文必引“子曰”,写出来的“经典”和“名著”让人死活读不下去;二是沉溺书斋,凭才气和想象力描画子虚乌有的玩意,还没玩够黑色幽默、魔幻现实等老东西,又迷上了穿越、灵异等新时尚,成了一个个现代叶公;三是对现实生活熟视无睹,以为凡是观照现实就是浅薄和媚俗。其实,那是生活贫乏、思想苍白,或把持能力不强的缘故。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妨多吃点对大众口味且容易消化的“桂圆”,至于“龙眼”嘛,浅尝辄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