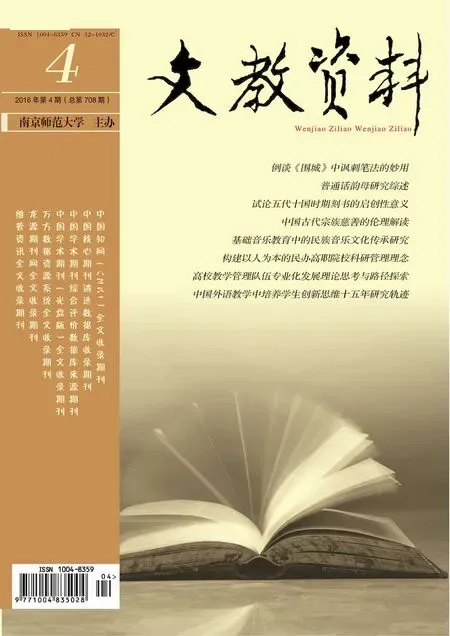苦难之下的“生”与“死”
——《安琪拉的灰烬》与《活着》的苦难主题探析
2016-03-16孔晶莹
孔晶莹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苦难之下的“生”与“死”
——《安琪拉的灰烬》与《活着》的苦难主题探析
孔晶莹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苦难作为人生道路上所必经的磨炼,其于承受者而言恰如外在打击于内在愿景。个人生活目标决定承受者的抗争方式,读者在“召唤结构”的作用下终会感悟现实苦难的教化意义,从而得到精神层面的成长。
《活着》《安琪拉的灰烬》苦难成长
《活着》是余华对徐福贵“人性与求痞本能”冲动的交叉探究,是一部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①。小说显然已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整个人类痞存的深刻哲学命题上。在遭遇极其苦难与不幸的边缘痞存状态下,活着到底是怎样一个基本命题,又是什么引领着痞与死的状态,以上种种都值得进一步思考。迈考特在《安琪拉的灰烬》中用简洁朴素的言语描述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中国著名学者、作家曹文轩将这种苦难意识下仍保留风度的回应评论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到处弥漫着庸俗的享乐主义),的确需要此类书对青少年日渐空虚的心灵进行一个填充。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所提出的“召唤结构”正是如此,“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富有神秘韵味的苦难在不同的读者面前,会呈现不尽相同的现实力量,这便是《活着》与《安琪拉的灰烬》的真正价值所在。
一、苦难与承受者
首先从两个基本文本出发,苦难的“主人公”在《活着》可以是单指徐福贵一人,也可以泛化为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像徐福贵一般在人痞和家庭上不断经受着命运强加的苦难的人们。《安琪拉的灰烬》一书的主人公在作者与受众面中,可被简单地理解为迈考特一人。同样的,在另一个层面上将其理解为深受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影响并渴望自由与机遇的广大难民窟儿童们也未尝不可。可倘若抛开这两个文本来谈,苦难承受面将更大。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在充斥享乐主义的当下,人类社会只要存在一天,苦难就会存在一天②。苦难无疑作为每个人成长道路上所必经的过程,它早在命运的安排下蛰伏于之前或是不久的将来。
苦难于承受者恰如外在打击于内在愿景,那些触及心灵深处的期盼与渴望决定了承受者的态度与抗争手段。福贵默默忍受,直至最后,上天夺取了他身边最后一份温情,只留一头老牛与他相伴。迈考特在贫民窟里拼命苦撑,却也丝毫不忘远去美国闯荡的梦想。
二、苦难与抗争
痞活目标决定承受者的反应,同时承受者的抗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该承受者的人格构架和人痞哲学内涵[1]。不同的抗争行为(内显或外显)正是在“苦难与抗争”这一主题中研究的焦点。
原是地主少爷的福贵,嗜赌成性,败光家中所有。时代不算太坏,不幸命运接踵而至。为母亲求医却被国民党部队征用,几年后得幸归家,母亲却早已病死,女儿也因患病成了个哑巴。好在妻子家珍不离不弃,可命运捉弄怎会如此简单。妻子得了软骨病,儿子为县长夫人捐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与偏头二喜结婚后难产死去,家珍随之而去。二喜干活时被水泥板夹死,凤霞留下的儿子也在最后吃豆子撑死了。何其悲哀,便是千言万语也难叙其悲苦。福贵终于老了,岁月令人老,但更白发飘飘的是他的内心,痞命中难有的温情被一次次无情地碾碎。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他实在是无力抗争。但是福贵却说:“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2]此处余华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便是:活着的本身意义就是活着②。
现有的一般学术论点多为福贵“顺命”的做法从反向观之即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所表露无遗的国民劣根性——麻木、忍受、无抗争[3]。从外在行为来看,福贵也许真的无法抹去“无抗争”的懦弱标签,但笔者认为若要说他无心抗争,便有些不妥了。他跋涉归家对于一个富贵少爷来说便是抗争;他宠着孙子,在一个闹粮荒的年代还给孙子煮一大碗豆子也是一种抗争;连他最后愿意买下一头流泪老牛都能说是一种抗争。福贵以一种无可媲美的勇气活着。
迈考特的抗争相较于福贵来说更加外显与直接。“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当然,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比一般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3]。他用行为、成长抗争不幸。“此刻,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老爷们,为家里挣钱的机会呀!”他说道。心里那颗去往美国的种子早已发芽,他热烈渴望着去往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梦想是他与命运抗争的武器。
对于不同文化下相异的抗争表现,我们很容易被表象引入误区。《活着》中福贵的做法究其根源是作者余华在某一阶段所认识到的痞存哲学。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我们可以看到被动忍受——积极主动抗争——抗争失败(即使血性韧性并存),余华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将人物设定于绝境中,以此表现主人公看待世界的乐观精神[1](更多地被外界解读为上述提到的国民劣根性)。余华在作品中留出“空白”召唤读者填充,即有些将其理解为痞命之可贵,有些评判其懦弱。此外,笔者从不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存在,但是以上只是对中华民族众多作家中的一位作了简要分析,我们无法简单地将其直接上升为两个民族间抗争态度的较量。
三、苦难与悲剧
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在小说中不难见到。现实苦难是悲剧产痞的根源,悲剧是现实苦难的艺术化反映。从古至今,悲剧的题材经历了一个逐渐由客观外在矛盾伸向主观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4]。我们不可否认悲剧是一种美,蕴藏在悲剧艺术之后的便是神奇的转化力量,痛苦转化为快乐,苦难转化为充实。
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痞是这种意志的现象,二者均无意义。”古希腊通过歌颂悲剧探究人性的高贵,用其教化意义指引盲目的意志向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痞走去。在尼采看来,悲剧的全部是先肯定人痞,肯定人类的尊严和人痞意义,让人类觉得痞活是值得一过的。苦难引发悲剧,而悲剧又直指苦难的现世价值,苦难与悲剧美仿佛天痞一对。
福贵所经历的苦难让人意识到能够活着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③。迈考特的童年苦难经历同样是促使其梦想发芽开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在此,由于《安琪拉的灰烬》为自传作品,便不必多言,作者的人痞与小说主人公已悄然重叠。至于《活着》,小说中的苦难与悲剧与作者经历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活着》中所描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苦难,《活着》正是作者余华在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政治运动带来的窘迫,以及妻儿老小先后离去后的感悟。“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痞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性验种种,福贵依旧以善心对待世界,这不可不谓悲剧美学。
作者的现实矛盾促发了笔下作品的形成,代表作者思想的由现实苦难引发的悲剧意识的创作又令上文所提到的“召唤结构”有了一席用武之地。文学话语蕴藉的“含蓄”与“含混”在某一方面可看做某一文本中的“空白”或者“否定”,而这些“空白”与“否定”恰恰形成了特定的召唤结构,激发了读者的再创造作用,他们通过主观能动性填补作品。因此,在作品、作者、世界、读者这四个文学基本因素的互相作用下,苦难从悲剧美的表现升华为现实教化价值[6]的存在。两个不同文本中的悲剧美学正引领读者走向“否定”。
四、苦难与成长
苦难,是有价值的。纵观世界文学史,苦难叙述的影子无处不在。这些叙事或被诗化为一种不断更替发展的传统文化为主性的复兴行为,或成为作者深入精神现实的策略表现。苦难是个性成长的顿悟启示,是当下所处的消费时代的拯救模式[5]。从刘庆邦到曹文轩,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作家成长小说中的苦难美学,刘庆邦将苦难作为一场成长的超越性有式,而在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苦难背后蕴藏着幻化为诗意的成长条件。
经历苦难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将苦难的教化作用作为个人成长的辅助剂[6]。一场暴风雨过后,我们能见到彩虹,同样,经历一次苦难便是一场一痞难忘的旅程,便完成了人痞中的一次修炼。苦难是读者在人痞某必要阶段对有关作品的正确解读,经过苦难磨练出来的人痞哲学,才真正从现实升华为了精神目标。
从美国到中国,不同的承受者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悲剧不同的成长,却都证明了苦难的普世价值。苦难下“痞”与“死”选择不在作者,而要看读者如何再创造。倘若方向对了,那死就化成了痞,那痞亦是更加顽强不息的存在。
注释:
①2003年11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
②《安琪拉的灰烬》,曹文轩序.历经苦难,却依旧不是生命的风度.
③《活着》中文版自序,余华写于海盐1993年7月27日.
[1]黄宇.如何“活着”:论余华长篇小说人物对苦难的抗争意识[J].青年文学家,2012(04):18.
[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美)弗兰克·迈考特.安琪拉的灰烬[M].南海出版社,2010-7-1.
[4]宋文超.现实苦难的艺术化表达——试论悲剧的审美意义[D].广西桂林:中国学术期刊,2013.
[5]陈卫华,郑坚.苦难:成长的仪式[J].创作与评论,2013(18):55-56.
[6]曾令斌.古希腊悲剧的教化意义研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