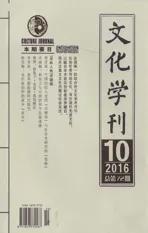和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2016-03-16洪晓楠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学林人物】
和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并启动了国际与国内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我国著名哲学家张立文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研究、继承和传播,他不仅于20世纪90年代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的和合学,而且还率先提出并论证了“和实力”这一概念,从而向世界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国家实力研究的“中国话语”。本文考察了和实力提出的背景,揭示了和实力的理论基础是和合学,分析了和实力概念和理论提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步西方大国所谓的“国强必霸”的后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理据。
和实力;和合学;和平发展道路
一、“和实力”概念提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随后发展了“软实力”理论,从而他被世人誉为“软实力之父”。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仅仅只看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要从文化的方面去影响其他国家从而获利。“软实力”这一概念一经提出,随即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专用词汇,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软实力”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表明一个国家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发展软实力理论,其根本出发点是为美国领导世界、称霸世界、当世界警察辩护,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正鉴于此,在全球都在跟随软实力研究潮流的时候,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张立文教授,提出了“和实力”这一概念,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和实力?和实力和软实力、巧实力有什么样的差别?和实力的特征是什么?和实力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和把握张立文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以及他由此所创立的“和合学”。
二、“和实力”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和合学”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冲突、融合,与再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所谓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和合这个概念最早是春秋时代《国语·郑语》卷16记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契是人名,保是养育的意思,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属于伦理学范畴。当时春秋时代主要讲怎样治理国家,稳定社会,和合能把各种关系、规范协调起来,这样国家就安定了,这是和合最初的意义。“和”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文化选择。“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人与人之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小人只搞同,意见完全一样,君子的和是有差别的同。“和”的意思是“他”与“他”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和合资源,儒家从差别中求和合,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分别中求和合,佛学从因缘中求和合,墨家从兼爱交利中求和合,阴阳家从对立中求和合,法家从守法中求和合,名家从离坚白与合同异中求和合。总之,各家都以达到和合为其最高境界。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同归”“一致”之道。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和合资源为创造和合学打下了理论基础,那么,现代和合学则是传统和合论的转生,这个转生是批判、转换和创新式的新生,是化腐朽为神奇、转神秘为科学的转生。在张立文先生看来,和合学既不是知识体系,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关于化解价值冲突的战略思维。
当前,基于人类共同面临着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人的心灵和各文明间的冲突)和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关系着每个国家、民族、种族和每个个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未来人类可以通过共识获得五个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来融突五大冲突和危机,这便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2]和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的体现。和生意识是以共生意识为基础的,共生的核心就是和,所以称为“和生”。“共生”意识与“共处”意识相联系,“共处”以“共生”为前提。“和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精神的体现,有差分而和谐相处。“和立”以“和生”“和处”为基础。“和立”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立己立人的精神的体现。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和达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己达达人的精神的体现。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和爱,这是一种“泛爱众”“兼相爱”的人类之爱精神的体现。和合五义,都蕴涵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和合是涵容了冲突的融合,融合的冲突。无论是和、和合,还是合、合和,都以不同、冲突、差异的存在为前提,而否定“一律”、独尊、独断。和合有三个阶段:冲突、融合、新生。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这个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就此而言,和合既是事物的根源,是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个过程。
三、“和实力”概念的内涵
“和实力”这个概念内在包含着“力”“实力”“和实力”三个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在物理学中,力是指一个物体对另一物体的作用,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一定有另外的物体施加这种作用。前者是受力物体,后者是施力物体,只要有力发生,就一定有受力物体和施力物体。有时为了方便,只说物体受了力,而没有指明施力物体。但施力物体一定是存在的。就此而言,力就是一种相互作用。后来,力这个词逐渐引申出多种含义,比如力量、能力这样的基本词义。
“实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说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较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企业、另一个人比较有实力,也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具体来说,“实力”包含哪些内容,真是见仁见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实力”一词的解释是“实在的力量(多指军事或经济方面)”。实力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通常用高低强弱来表述,它是国家的属性之一,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相应的实力,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的新现实是:实力的性质和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实力赖以产生的资源已变得越来越复杂,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就此而言,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
和实力是指军事、经济、话语、制度等实力的融突和合,以及其在融合的实践交往活动中和合为一种新实力的总和。和合的“生生”文化精神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是指核酸、蛋白质等物质和合而成的生物体所呈现的特殊现象的能力,而是指一种文化能吸收、利用、改铸外在与内在的因素、成分,形成、发展、完善自己和繁衍后代,以适应于时代环境变化的生命力及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新诠释的能力。[3]
和实力实际上是按照和合学理论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衡量和评价,就此而言,和实力是对于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超越,是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的融突和合。和实力的和,意蕴多元冲突融合,而非二元对立的潜在冷战思维,它的目标是和平、发展、合作。
和实力既然作为一种实力,它就像其它实力一样,应该具有大小、方向。我们运用和合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和实力可以测量和评价。其中,文化实力的判断标准是,在现代它能否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化解之道。和合学的宗旨就是依据对人类文化新世纪发展前景的战略预见,建构和合的和合解构系统,作为和合学立论的主体和骨架。和合学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无限实力。
四、“和实力”的特征
1939年,英国著名学者卡尔(E·H·Carr)认为,国际权力格局分为三种——军事权的威慑力、经济权的收买力以及话语权的吸引力和舆论控制力。1989年英国学者肯尼思·E·博尔丁在其出版的《权力的三张面孔》一书中提出了威胁权力、经济权力和整合权力,或称为大棒、胡萝卜和拥抱。[4]据此,约瑟夫·奈按照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前两者称为硬实力,后一种称为软实力。后来,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约瑟夫·奈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提出了巧实力,主张软硬兼用。其实,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新鲜的,如邓小平早就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思想,这一思想更具中国气魄。同样,我们今天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有中国气派。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和实力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综合性、和合性和开放性。
和实力具有综合性。和实力是对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超越,是从整体高度看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一种综合国力。根据前述的五大中心原则,和实力具体包括人与自然和生的和实力、人与人和处的和实力、人与身心和立的和实力、人与社会和达的和实力以及人与世界和爱的和实力。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3种基本资源,分别为该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就此而言,和实力包含了软实力,又高于软实力。如何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怎样才是合理的,值得称道的?答案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如果达到了和合的状态,就是最佳的。如果说,硬实力是阳,那么软实力就是阴,只有和实力才是阴阳和合,融突和谐。和实力是一种和合架构的最佳的实力。另一方面,巧实力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体。巧实力理论强调软硬兼施,重在灵巧。和实力可能是巧实力,但也可能高于巧实力。巧实力强调灵巧,和实力强调和合、融突。灵巧只是和合、融突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认为,和实力包含了巧实力,又高于巧实力。
和实力具有和合性。很明显,和实力是军事、经济、话语和制度的和合,缺一不可。正如张立文教授所说的,没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话语权就没有力量,腰杆子不硬。没有经济作为基础,话语权的底气就不足,话语没有分量,人家不理你,等于没有话语权。没有制度的保障,军事权、经济权、话语权也无法实践。相反,光有军事权的威胁施于人,这是侵略者、占领者;光有经济权施于人,这是经济掠夺和殖民;光有话语权,是不可能吸引人的;光有制度施于人,这是政治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实力强调军事权的后盾功能、经济权的基础作用、话语权的精神指导作用以及制度的保障作用。唯有四力和合起来,能够发挥其效能,促进综合国力提高,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和实力具有开放性。和实力的“和”表示多元冲突的整合和包容,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和实力具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目标是为了推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而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必然导致其独断专行,即对所谓的“非民主国家”采取制裁等方法。和实力的实践形式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和实力的目标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是为人类谋福利的。
五、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2002年中国著名学者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他指出,“和平”是针对某些国际舆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而“崛起”则是针对国际上另一些人鼓吹的“中国崩溃论”。[5]2003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他指出:“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6]
2004年8月24日,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研究借鉴其他大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崭新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大抉择,也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回答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新形势下所面对的四个课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走得通?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之后,他多次反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我个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综合作用而导致的:
第一,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决定了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从先秦时代开始,诸子百家就开始对“和”的意蕴、价值、实现途径和理想状态等进行了理论阐发,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和”成为涵盖自然(天地人)、社会(群家己)、内心(情欲意)等层面的基本原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质规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来仍然极富活力,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和”的价值理念的践行。因为“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延续这种传统思维理念,而尊重不同事物或对立因素之间的并存与交融,相成相济,互动互补,即是万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门。数千年过去了,传统的“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贯穿其中的人文精神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等价值取向,仍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和为贵,忍为高”,“不与邻为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合大和”等等,这些信条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
第二,“和实力”的理念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首先是基于中国一贯地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思维,以及我国在一切国际争端和冲突中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严正立场。其次,我们试图用中华民族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实力这个概念能够很好地体现国际的核心话题和当前的主流趋势。再次,和实力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以及中国自汉代以来“和亲”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最后,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和实力正是根据这一需求而提出来的。[7]西方国家强调软实力的背后是其政治价值观,我们的政治价值观与他们不同,所以特别需要我们自己的话语。
第三,“和实力”的价值导向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三个超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搞计划经济到推进各方面各领域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状态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到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合作;从以意识形态划线到主张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和谐并存,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这一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牢把握现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我们谋求实现“三大超越”:一是要超越西方大国近代以来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完成工业化的老路;二是要超越当年的德国、日本等军国主义依靠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老路;三是要超越前苏联霸权主义搞超级大国争霸和争夺势力范围的老路。[8]
第四,和平发展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中国的战略意图就是4个字:和平发展,即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所谓和平发展,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自身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通过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和发明创造,通过同世界各国持久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来实现上述目标,使占人类1/5的中国人能告别贫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使中国成为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和睦相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都协调发展的国度,成为国际社会最负责任、最文明、最守法规和秩序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把这一过程称为“和平发展”,把实现和平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称为“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条道路已庄严地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之中,这些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是欢迎而不是害怕,应该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应该是支持而不是遏制,应该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正当和合理的利益与关切。(本文曾于2015年10月在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宣读,特此致谢)
[1]张立文.和合学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1.
[2][3]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54.16.
[4]肯尼思·E·博尔丁.权力的三张面孔[M].张岩,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郑必坚.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和平发展之路[J].国际问题研究,2013,(3),2.
[6]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N].人民日报,2013-12-11.
[7]张立文.和实力:我们中国自己的话语[N].中国教育报,2013-10-25.
[8]郑必坚.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在“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演[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
【责任编辑:王 崇】
B26
A
1673-7725(2016)10-0030-06
2016-06-3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3AZD016);2014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项目编号:中宣办发【2015】49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洪晓楠(1963-),男,安徽桐城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哲学、科学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