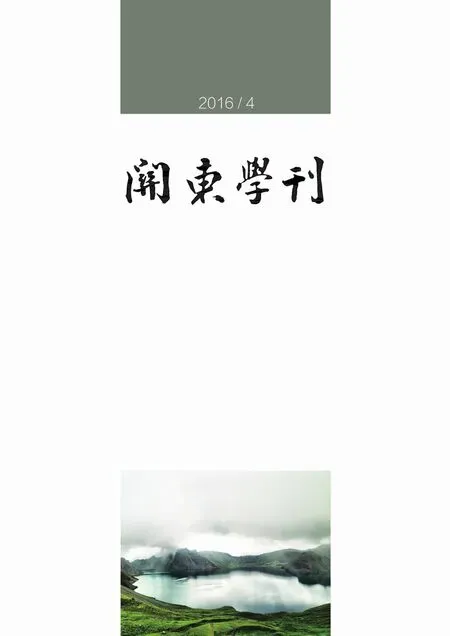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检审分立与矛盾探析
2016-03-16陈晓林杨树林
陈晓林 杨树林
南京国民政府检审分立与矛盾探析
陈晓林 杨树林
北洋政府时期,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之中,组织、业务上独立,有权监督审判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则撤废检察厅,配置检察官于各级法院,承担指挥侦查、提起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责。这样,法院包括审判和检察两个部门,分别称为院方和检方,检察官和推事合称为法官。检审机构虽然合并,但除财政预算外,双方人事、业务均各自独立。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不同的部门置于一处,矛盾和冲突成为二者关系的主要表现。回顾历史对当代社会实践具有明鉴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检审关系;矛盾;探析;思考
南京政府检察制度源于清末司法改制。清末检察厅分别配置于各级审判衙门之内,为审判厅之附庸。北洋政府时期,为加强对审判权的监督,检察厅实现了组织上和业务上的独立,与审判厅居于同等地位,独立行使其职权。*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页。其时,审判官称推事,与检察官并称司法官或法官,简称为“推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司法改革,撤废检察厅,配置检察官于各级法院之中。由此,法院包括审判和检察两种职权,分别称为院方和检方。审检机构虽然合署办公,但是由于审判权和检察权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业务内容、权力行使方式迥异,除财务预算院检合并在一起外,其人事管理、业务进行均各自独立。两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国家权力配置于一个部门,矛盾和冲突成为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检审之争是国家权力无序配置的结果。民国时期,经费是制约司法机关发展的瓶颈,检察官配置于法院,节省司法经费为直接原因之一。中国近代检察制度师法德日,检察官为国家之代表,代表国家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检察制度本身就是司法分权、司法民主的产物。检察官不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监督法官的审判活动,确保侦查、公诉、审判权不集中于一个机关,避免司法专断,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而置检察署与法院于一体,自然与分权、监督的初衷相悖。此事件虽已过去近乎百年,但博稽古今,重温历史,对我们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审判与监督具有历史明鉴意义。
一、从分立到合并:审检机构的变化
同清末、北洋政府时期一样,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司法经费紧张。为节约司法经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指出“穷查检察制度以检举及执行两项为最大要素,故论其职掌,只是法院中司法行政部分之一种,”建议国民政府裁撤检察机关。*张妍、孙燕京:裁撤检察机关改定法院名称延期实行呈(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前司法部呈准),《民国史料丛刊·增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第5册),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1927年南京政府发布政令称,检察制度,体察现在国情,参酌各国法制,实无专设机关之必要,应予以裁撤,所有原日之检察官暂行配置于该各级法院之内,暂时仍旧行使检察职权,其原设之检察长及监督检察官一并改为各级法院之首席检察官。此后,各级检察机关陆续撤销,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并入法院。1928年秋,最高法院颁布法律,规定在最高法院配置检察署,该署设检察长一人,指挥监督并分配该管检察工作,设检察官七人至九人,处理监督、检察相关的事务。*张妍、孙燕京:裁撤检察机关改定法院名称延期实行呈(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前司法部呈准),《民国史料丛刊·增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第5册),第285页。
1930年夏,南京政府通过《法院组织法》,该法的立法原则指出:“改革以来,仅于法院设置检察官,颇有疑检察官系附属于法院者。兹更进一步,定位凡法院均配置检察署,以表示其独立执行职务之精神,非复旧也,乃从宜也。”然而,为进一步削减司法经费,南京政府对法院组织法的上述原则又予以修正,指出“中央之最高检察机关,固宜崇其体制,称之曰署,并名其长官曰检察长,至各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暨其分院,因检察官之职务,视前大为减少,将来所设员额,亦无复今日之多,自无庸别树一帜,仅配置检察官可矣。关于检察事务,虽得独立行其职权,若关于会计统计,及其他行政事宜,则应属于其所配置之法院,虽节糜费,亦可免历来互争权限之弊。”决定“于最高法院内置检察署,其他各法院均仅配检察官,其有检察官二人以上者,以一人为首席。”*张妍、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法院组织法释义》(第11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第249页。
根据这一立法精神,1932年10月28日颁布的《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将法院分为三级,可见,在当时的法院机构设置中,为了节减经费,将法院改为“地方”、“高等”、“最高”三个级别,其作用和智能并未削弱,但检察厅经撤销后,并无三级设置,而是采取配置制,即最高法院设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检察官若干人。因此,当时李光夏、吴鹏飞等法律学者将法院分为最广义之法院、广义之法院与狭义之法院三种。“所谓最广义之法院,系泛指一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而言,故不论司法审判机关、行政审判机关、军事审判机关以及官吏惩戒机关,均包括在内。广义之法院,乃专指普通之司法审判机关而言,其他行使特别司法权之特别法院,则不包括在内。所谓狭义之法院,则专指普通法院内实施审判之民事庭及刑事庭而言。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之检察机关,则不包括在内。”*李光夏:《法院组织法论》,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第33页。可见,检察机关虽然被撤销,但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检察权依然存在,学者力图通过对法院等法学概念的解释来区分检察权和审判权这两种权力,为法学研究提供理论前提和可能性。
检察官虽配置于法院,但于法院内设检察处,作为检察官办公的处所,业务和行政领导上独立。院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检方则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检察官与推事事实上处于对立的地位,对于法院得独立行使其职权。*张妍、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法院组织法释义》(第11卷),第59页。因业务管理上的独立,法院之“院方”常常将检察官视为异己,如各省高等法院的处务规则并不包括检察业务方面的内容,检方亦如此。关于检察人员的办公地点及设置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多是在法院内另行设置。业务上同样不包括审判部分的内容,除独立行使职权外,处务等方面也是独立的,如收发处接收的非法院方的文件及资料应迳送首席检察官,由其进行统一分配。但在文件的签章方面,检察官可自行签名或盖章。在办公经费上,无论例行支出还是临时产生的费用,检察官亦无独立的权限,均是由法院依据实际情况以及检察人员的建议编制预算,并依照固定的时间支取。前项事件不能解决时,应呈司法行政部核准办理。上述各项内容,在地方法院规章中也有相关规定。*张妍、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增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第5册),第608页。
二、矛盾与冲突:检审关系的常态
古代中国的司法监督主要由御史来执行,御史最早是皇宫负责文书方面的官员,其多为皇帝的心腹。在魏晋时期,御史成为皇权控制地方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其依然属于行政权力,在运行上时刻会依据需要进行调整乃至剥夺,因而并不具有稳定性,无法有效监督权力。在清朝后期,一些仁人志士开始主张学习西方,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1906年,清政府设总检察厅,统管全国的司法监督。但受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作用有限。于是,反对并废除该制度的主张不断增加。尽管部分志士有改革专制的意愿,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民国时期,在西方列强发达的经济与军事的背景下,上层社会决定效仿西方的三权分立,但由于内部集权统治,三权分立体制依旧停留于形式,受清末废除检察制度以及经费拮据的影响,设立独立的检察机构的思想并不坚定,最终毅然撤销了各级检察部门,将其合并于各级法院之中。*《王宠惠之司法改进谈》,《申报》,1927年7月24日。该重大改革也受到了社会诸多人士的赞誉。当时的检察官虽配置于法院,但在人事、业务等方面独立于院方,独财务由院方独掌。法院内司法行政事项由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共同负责,首席检察官负责司法警察之进退奖惩以及检察方面书记官之监督,会计、统计、赃物等事项则由法院院长负责,首席检察官无权过问。
司法行政事务的交叉,使各省高等、地方法院院检两长常常因经费等问题发生冲突,此种现象,在国民政府各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比比皆是,为不可调和之矛盾。更有甚者,推检之间互相控告倾轧。如海南澄迈地方法院院长吴丹华为排挤该院检察官廖麟材,诬陷其受贿、枉法,被廖察觉,复控告吴丹华受贿,徇私枉法。*廖麟材:《民国年间司法回忆》,《合浦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浦县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第87页。湖北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蒋宗述分析此类问题时说:“行政大权尽操于院方,一面义务相同,权利各异,各地院检之发生摩擦,均坐是之故。又如检察处因公动支款项如勘验具体搜索办公等费用,院方不曰经济困难,即曰限于预算比重。紧急措置稍一迟延,即影响于办案之进行,减少工作之效率。”*蒋宗述:《湖北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提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宗号LS64,目录号5案卷号66。针对检审矛盾,张知本也指出:“盖年来各级法院与该处检察官,每因经费等关系,互相摩擦,甚至倾轧排挤,希图取代。此固官箴不肃之咎,而事权不相统属,恐亦不无多少原因。然审判与检察,性质各异,合署办公,系图便利起见。若检察官受院长监督,则与建立检察制度之精神根本冲突,宁以完全独立为是。”*张知本:《司法制度之商榷》,中央日报,1946年3月14日。毫无疑问,院检冲突成为二者关系的常态,严重阻碍审检工作的正常开展。
如何调处院检两方的矛盾成为司法院颇为棘手的问题。早在1938年8月16日,司法院法规研究委员会第七次委员会讨论认为,关于检察制度问题,应在各级法院及分院所在地,分别设置同一级别的检察署,形成对立,以提高机构级别和地位,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责。检察官毛家祺曾提议,应将高等法院及分院、地方法院所在地,各配置同级检察部门,各级检察机关设长官一人,其他人员若干,地方法院分院所在地,由地方法院本院检察署,酌派检察官书记官录事警丁常驻办事,不另设地方分院检察署,经费并入法院本院检察机关的预算内,或于高等法院及分院与冲繁地方法院所在地设置同级检察部门,其简单地方法院所在地检察事务,由高等法院检察署酌派检察官书记官录事警丁常驻办事,所需经费,并入高等法院检察署预算内,至监所监督权,恢复民国十五年以前旧制,该隶检察署并将法院组织法监所法规以其他法令关系条款修改或补充。”*毛家祺:《拟明定检察官署,并将监所监督权划归检察官署,另定预算,以明系统而一事权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宗号LS7,目录号5案卷号66。为划清法院两长之间法警管理权限,1947年时司法行政部指令法警任免奖惩等事宜,应由首席检察官主管,倘院长发生异议时,应提出理由,会同首席检察官呈请上级长官核办。
三、褒贬不一:时人对检审关系的观感
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官配置于法院之后,检察官无独立办公的官厅,检审对立、平等的关系发生变化,无形之中降低了检察官的地位,检察官对审判的监督更加困难,给检察官的工作带来难度,也进一步激化了检审之间的矛盾。对这一变化,时人有深刻的认识。
就国民政府将检察机关配置于法院之后所引起检审关系的变化,1930年时,即法学学者从检察官的性质、地位出发,指出了裁撤检察机关的弊端,批评说:“检察官者,立于国家代表之地位,破灭犯罪恶行,纠正非法裁判,而以除暴安良维持民权为目的也。故凡采行检察制度之国,无不严其保障,遵其职位,并使其办事有独立之机关,行动有联敏之精神。从前法院编制法,采审检对峙制度,实为立法上之进化规定;迨至民国十六年,革命军兴,政多草创,司法改革之下,致将检厅裁隶法院,各地检察长,均降称首席检察官,特任待遇之总检察长,降为简任。”强调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检厅可以命令本县各警官,高检厅可以命令全省县知事”,检察官的地位下降之后,“今则效用均失矣。盖县长与公安局长,官居荐任,可比高等之首席检察官,机关独立,足拟地方之法院院长,其视附随于人之地方首席,不过为院长之一属员。即有公文嘱托,请求协助等事,亦多漫不为理。如遇检察官下乡勘验,虽至区官村长,指挥均觉不灵。”而社会“战事甫终,政治未就轨道,各地军宪机关,以及县政府,公安局等,擅理诉讼,滥押无辜,几于司空见惯,愚民敢怒而不敢言,法院熟视而无睹。”遽变检察制度,带来司法秩序的混乱。*文山:《论法院组织法上关于检察官之待遇》,《法律评论》1930年第8期。国民党元老、法学家张知本也指出:“一方面,除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外,而高等法院以下的检察官,在法律上并无办公的独立官署,仿佛为法院的一个附属人员,另一个方面,在官级上也略有差别,如高等法院院长为简任,其较该院中设置的首席检察官的级别高。这等情形,均足以贬损检察官的尊严,而更易为一般人所轻视,由是在行使职权上,或许要发生种种的困难也不可知。”*张知本:《检察制度与五权宪法》,《法学杂志》1937年第6期。
由于机构变更造成社会地位下降、工作窒碍难行,检察官则更是不满。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认为审判、检察合并为一个机关之后,审判、检察职权的行使仍各别独立行使,“且以首席检察官对外之机系为尤多,盖刑事案件检举之责,属于检察官。凡抗御权势摧抑豪强搜集罪证拘捕凶暴,皆检察官首当其冲。由于检察官的地位和级别较低,普通检察官对此更为不满,抱怨说:“检察为法院附庸,职责虽重,权位较低,窒碍滋多。而高分院管辖下之各兼检察职务之县长得为简任,分院首席检察官尚只为荐任,不无颠倒之嫌。另外,院方各项人员类比皆数倍于检方,而检方仅设有书记官一人或二人,办案已感困难,录事二人或三人,办理缮写分案收发及庶务各事宜顾此失彼,更不敷支配。”*王翼:《湖北浠水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王翼关于司法行政检讨会的提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宗号LS64,目录号5案卷号66。要求政府对检察官“崇高其地位与优厚其待遇”,与推事“同等重视”。*蒋宗述:《湖北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提案》。而法官从自身利益出发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如湖北汉口地方法院院长刘泽民认为检察官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几近重复,尤属误会,盖侦查程序,为有无罪嫌之依据,而审判程序,则为应否处罚之依据,性质迥然各异。”“检察官应减少内部事务,加强检举职权。”*刘泽民:《湖北汉口地方法院院长刘泽民条陈改良司法意见报告书》,《中华法学杂志》1936年第1期。
就如何改进检审关系,时人认为,须提高检察官的地位,与推事对等。张知本主张检察官应拥有独立的官署,在官等、待遇等方面与法官平等。*张知本:《检察制度与五权宪法》。郑烈强调相对于审判权,检察职权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分性,“要想增强检察制度的效果,……要从改善检察的机关着手,……要于中央设一总检察署,各省设省检察署,各地方设地方检察署。总检察署直隶于司法院而统辖各省各地方检察署。所有各级检察官,除由总检察署指挥监督外,其他荐用考核之权,亦畀之于总检察署。”*郑烈:《检察长国家组织中所占之地位》,《组织》1943年第1期。检察官周炳雄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应脱离法院而独立,如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检察厅与法院对应而设。而王用宾则批评“回复昔日检察厅为不当,且指为落伍,不前进。”*周炳熊:《检察制度存废问题之商榷及其改进之方案》,《中华法学杂志新编》1937年第1期。还有观点认为“与其维持现存之附庸制度,不如直截了当将其机关裁撤,仅设检察官若干人,由院长监督指挥。检方行政事务亦由院长掌理,惟院长不行使检察官之职权耳。则检察官之行使职权与推事庭长处于同等地位,同受院长之指挥监督。对内行文以检察官个人名义行之,对外行文则以院长名义行之。院长不由推事兼任,又不行使检察官职权,其执行职务与院长之行使指挥监督权并无窒碍。”*元:《对于现行司法制度的几个补充意见》,《法令周刊》1937年第2期。
观点常常和利益牵连在一起,所处之位决定其思想,因自身职业关系、职业立场的不同,时人关于检审关系的看法众说纷纭,法官认为应当弱化检察官的独立地位,检察官应该在行政事务上从属于院方的领导;而检察官则反驳检察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力,应该拥有独立的官署,应该有行政事务上的完全独立,应该在司法经费方面不受院方掣肘,方能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监督法院审判活动。
四、结语与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官采配置制,一改清末民初以来的审检对立格局,检审关系也随之改变。归纳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审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检审的矛盾充斥于司法和检察的各方面直至政府倒台。学者虽界定为广义上的司法权,但检察权和审判权的权力属性、内容、行使方式迥异,检察官和法官具有不同的职业特点。从职能上看,检察官负有监督法官之责,二者本身即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两个相互竞争的部门同一个预算,为检审之争埋下了祸根。终南京国民政府存续的二十余年,检审关系较以往更为紧张。
其二,检审之争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空耗。检察官和法官为了办公经费,互相倾轧,恶化了相互协作关系。检方要求经费时,院方则以预算无款予以拒绝;而则检察官挟侦查监督职权以及操纵法警威逼院方。互相破坏,两者竟成水火,于是法院与检察之长官,应付行政上之纠纷而不遑,欲求彼此努力合作,以增进司法之效能难矣”。*孙晓楼:《我国检察制度之评价》,《法学杂志》1937年第5期。
其三,该时期检审关系的变化是中国法制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清末,检察厅配置于审判厅,为审判厅的附庸,无法有效监督审判工作。北洋政府为便于监督,增强了检察厅的独立性,使业务和组织得以独立,但检察厅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为国人所不喜,以至于在民初即有要求废除检察制度的呼声。本着审慎的态度,南京国民政府撤检察厅,实行检察官配置制,而非完全废除检察制度。由于政治、经济、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同,清末以迄南京国民政府,检审关系的变化是检察制度中国化的尝试,也是中国移植西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作为我国法律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检审关系变更是对完善法律制度的种种努力和探索之一,其间的反复是法律移植和调整以及适应特定社会环境的需要。受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尝试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轨迹,其显示出中国法律制度的曲折历程和艰难探索。时至今日,我国现代法制已有较大的完善,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已分立设置,检察机关的级别和地位与审判机关并无差异,其检察、监督权力得到极大加强。然而,其无法有效发挥监督的痼疾难以根除,“庸监”、“懒监”以及不作为的缺陷犹存。近些年来,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法院虽是主要的责任方,但相关检察人员也难辞其咎。这表明检察院需要加大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而该监督不仅应存在于审判阶段,更应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当错案发生后,对沉寂几十年后的既定结果予以纠错显然非问题解决之根本,其关键还在于事前监督、检察。在发挥检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同时,对玩忽职守、不作为等行为予以规制,完善检察人员的责任自担机制,以减少错案的发生,这对推动社会的管理和我国现代化法制进程具有实际意义。
陈晓林(1976-),男,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西宁 810008);杨树林(1973-),博士,男,中原工学院法学院讲师(郑州 4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