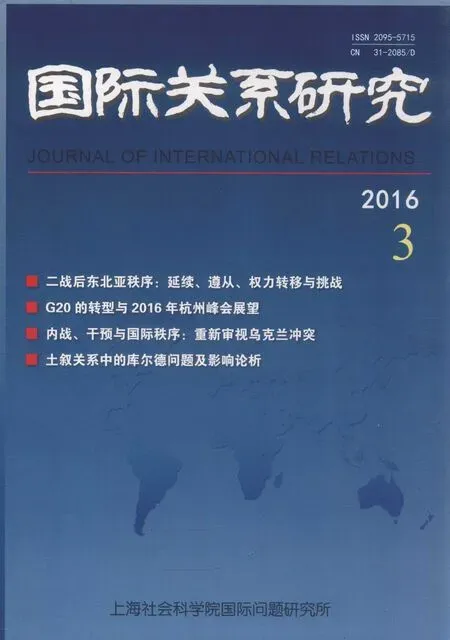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一种美学的维度
2016-03-16何伟
何 伟
国际关系
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一种美学的维度
何伟
[内容摘要]政治本质是象征性的,分为临摹性表征和美学表征。在国际关系的表征中,临摹性表征长期占主导地位,试图将政治现实原封不动地以理论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反之,美学表征认为,表征形式与被表征对象之间总存在“距离”,任何理论建构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诠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和学理争辩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美学研究,议程主要集中在视觉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美学形式。美学表征不仅从根本上质疑了以临摹性表征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渠道,有助于打破国际政治情感研究难以从私人领域进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学术困境。此外,从美学维度出发思考中国美学经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临摹性表征美学表征情感国际政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创始人亚历山大·温特曾指出:“诗歌、文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使我们了解许多人类的情况,但并不以解释世界大战或第三世界的贫困为目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这类问题,最大的希望还是社会科学,尽管这种希望是渺茫的。”*[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但是,有着百年发展历史并以社会科学方法自居的国际关系学科,仍未能给人类提供有效解决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指导方案。*Yale H.Ferguson and Richard W.Mansbach,The Elusive Quest: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e Press,1998,p.220.当今世界虽然整体和平,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极端贫困仍触目惊心,恐怖袭击、种族屠杀、局部战争和冲突暴乱也时常发生。美学探讨的是美和人类审美体验,该学科及其实践对国际关系的借鉴似乎无关紧要,那为何还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这是因为世界政治的性质复杂多变,单纯依靠理性逻辑思考国际问题困境并寻找解决方案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从美学维度去认识国际关系现象,探讨理论的发展,思考其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借鉴意义。在方法论层面,文学、绘画和音乐等美学艺术是政治现实和社会生活的浓缩和意义的载体,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的有效窗口。在理论思考层面,与临摹性表征(mimetic representation)不同,美学表征(aesthetic representation)认为表征形式与被表征对象之间总存在“距离”,任何理论建构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诠释。而美学维度考察可以针对这种差距,破除国际关系学科追求理论与现实之间镜式对应的迷思,突出研究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主动性,从而释放理论研究的动力。在现实借鉴层面,美学维度考察揭示人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并非局限于武力或暴力。例如,艺术作品在号召人们解决国际冲突和维护和平方面便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研究美学与国际政治,从美学中获取新的启示和见解,能帮助我们讨论美学引发的情感和道德因素在建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正如艾克哈特·克里彭多勒夫(Ekkehart Krippendorff)所言:“世界政治如此重要,其实践和研究不能仅仅依赖政客和政治科学家。”*Roland Bleiker,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2.美学的视角能让我们从情感出发,以开放的精神思考国际关系现状和理论发展趋势。从美学实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理性视角无法揭示的东西,比如权力的性别化基础、政治事件的情感性质和结局等。*Moore Cerwyn and Laura J.Shepherd,“Aesthe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Global Politics,”Global Society: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3,2010,pp.299~309.本文首先探讨表征与国际政治,阐述临摹性表征和美学表征的概念,强调后者对国际关系在认识论上的解释作用和在本体论上的建构作用;其次,从表征内涵、产生背景和主要研究议题三方面分析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美学维度,并指出美学表征有助于国际政治的情感研究,为情感的表达和社会建构提供了多样的渠道;再次,总结全文,指出美学表征对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作用。
一、美学、政治表征与国际关系
美学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又被称作感觉学和审美学,*杜学敏:《美学:概念与学科——“美学”面面观》,《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第113页。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美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的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64页。美学实践不仅仅包括绘画、摄影、音乐和电影等艺术活动,其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导人风格等方面。亚里士多德曾把人比作是冷酷无情的政治动物。但是,人具有丰富的情感,是感性的思考者,而政治的诸多领域都体现了审美的精神。可以说,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使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骆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07页。美学不仅仅只有艺术及其形式,更是感知、品味、情感和意义的集合,关涉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做什么。*Emma Hutchinson and Roland Bleiker,“Art,Aesthetics and Emotionality,”in Laura Shepherd,ed.,Gender Matters in Global Politics:A Feminist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14,pp.349~360.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人们对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理解和回应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样的理性方式主要体现为国家层面的安全和军事应对措施,比如,进行战争动员,制定和执行更加严格的国内安全监管政策等。例如,“9·11”事件后,画家拿起画笔,歌手走进录音棚,导演投入拍摄,博物馆开辟专门陈列区,纪念馆破土施工——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民众通过丰富多样的美学和艺术作品表达内心的悲痛,对遇难者的哀悼,对幸存者的抚慰,以及对恐怖分子的强烈谴责。*Roland Bleiker,“Art after 9/11,”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31,No.1,2006,pp.77~99.这些活动通常是自发的,与国家层面的安全政策和行动(如以武力为后盾的全球反恐战争)截然不同,可以说对民众情感的抒发、集体身份的建构和整体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国际政治本质是表象政治,有两大表征形式,即临摹性表征和美学表征。*Roland Bleiker,“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p.510.政治理论家汉娜·皮特肯认为临摹性表征为“现实的再现”,通过表征使公众的声音、意见和观点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得以体现。*Hanna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临摹性表征认为,国际领域的政治现实是外在的和事先存在的(pre-given),主体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是分离的。为了分析国际关系困境并给出解决方案,研究人员必须用实证的方法将“客观现实”原封不动地体现在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中。但问题是,研究者个人能摆脱主观诠释,而将政治现实毫无改变地呈现在对外政策中吗?答案是否定的。归根结底,临摹不是建构国际关系的表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临摹性与表象政治是对立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在于表象。详见Roland Bleiker,“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p.512。因为理论话语中的客观现实从来就不是事先存在的,不同的观察视角、立场、语境和言语叙事都会导致临摹性表征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即便理论与现实之间能实现理想的契合,这对于理解国际关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例如,三大主流国关理论均致力于在反映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为前提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它们自诞生近百年来,对于如何避免战争、寻求和平这一学科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学科仍未给出合理充分的解决方案。因为此临摹过程也仅是复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就事论事。*Roland Bleiker,“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p.512.此外,临摹性表征隐含的理性思考压抑了人类其他的思维和感官能力,比如感性、审美和想象等。所以,为了充分理解当今国际关系困境,研究者有必要打破理性思维的桎梏,充分调动情感等审美感官,从美学这一维度出发从事多方位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美学表征认为,在认识和建构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研究人员不能局限于简单地摹仿现实,而是要承认表征形式与被表征对象之间总存在“距离”,而这便构成了研究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是政治权力和创造性得以产生的根源。*Roland Bleiker,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4,19,21,134;F.R.Ankersmit,Aesthetic Politics: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5~46.在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只能存在于表征中,*John Street,“Celebrity Politicians: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4,2004,p.444.在符号和话语体系的意指实践中才能产生意义。政治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认为,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和知识谱系研究来看,政治是权力关系的场域,围绕着“……对其所见所闻,以及谁有这样的视觉权和话语权”*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4,p.13.等表征形式展开激烈的辩论。在国际政治的表征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临摹性表征,正如大卫·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义革命高峰时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我们如今可以使国际政治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了”。*David Singer,“The Incomplete Theorist:Insight Without Evidence,”in J.N.Rosenau and K.Knorr,eds.,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68.这种一元表征论的学术霸权话语和实践影响至今,极大地压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探索和发展,例如关于文本、话语和实践的研究。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美学表征则有望改变这一垄断局面,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开放和包容态度,与当今学术界愈来愈执迷于控制和压迫的研究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Morton Schoolman,Reason and Horror:Critical Theory,Democracy,and Aesthetic Individuality,New York:Routledge,2001,p.4.
任何形式的表征也是抽象的过程。*Roland Bleiker,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28.临摹式表征是对客观政治现象过度归纳、分类并使之科学合理化的结果,将情感和感性等人类的美学审美能力排除在外,也将“人排除在国际关系的建构之外,阻碍了人们认识国家的视野,将国家以一种‘空盒子般的隐喻’呈现出来”。*Christine Sylvester,“Art,Abstra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p.544.与此相反,美学表征提供了理解国际政治现实和建构理论的另一种途径。美学表征本身是一种表象力,一种权力,*Roland Bleiker,“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 p.515.而政治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表象力(例如表达权利和诉说权利)的争夺。在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体系中,知识即权力,能建构社会现实,而美学表征则能提供关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知识。*Peter L.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Anchor Books,1966.因此,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加入美学维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人们考察国际关系的思路,启迪研究人员从艺术、诗歌和音乐等形式元素出发来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
二、国际政治研究中美学维度
在过去10年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继出现了“语言转向”和“实践转向”。除了关注文本、话语和行为者的实践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美学维度拓宽研究思路。如今这一趋势愈加明显,正如罗兰·布莱克所言:“……如今的确可以提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学转向了。”*Roland Bleiker,“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2001,p.523.
象征是政治的一大根本特征,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骆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07页。当以临摹式表征为标志的理性视角无法充分解释冷战后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化时,美学表征所特有的创意、猜想和感性等能启人心智,给予决策者全新的见解,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困境、危机和灾难背后涉及的人类情感和其他无法量化的因素。美学研究倡导以非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能使学者保持冷静,后退一步,以新的方式来理解和看待政治冲突和困境。*Emma Hutchinson and Roland Bleiker,“Art,Aesthetics and Emotionality,”in Laura Shepherd,ed.,Gender Matters in Global Politics:A Feminist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14,p.354.从美学维度可以考察临摹性表征不能呈现的地方,即表征形式与被表征对象之间的距离,探讨人的情感和感性活动在理解和建构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面对突发的政治事件,例如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东南亚海啸和埃博拉病毒等,以目的明确、计划详实和逻辑清晰为特征的理性思考方式往往是无效和无力的,也无法表达事件亲历者的愤怒、悲痛或恐惧的情感体验。而此时,一件艺术作品,比如一幅油画,则可以很好地表现亲历者的感性、理性、记忆、幻想和欲望等情绪表达和交织。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和美学这两个看似相距遥远的领域拥有人性这一共同层面,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即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和发展。
1.美学维度的产生背景
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促使国际政治研究中美学维度的开拓。作为全球安全实践的转折点,“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传统国际关系有关安全的理论和实践。“9·11”事件打破了“人类正常的理解能力”,导致了“人们对世界最基本信任的崩溃”。*Susan Neiman,Evil in Modern Thought: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Melbourne:Scribe Publications,2003,pp.1~2.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顿时沉默,人们陷入悲伤和困惑中,无法找到答案。*Jenny Edkins,“Forget Trauma?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2,2002,pp.243~256.美学作品捕捉了这种沉默,聚焦了恐怖袭击给人们造成的情感创伤,而这些都是理性视角所忽视和无法表达的。*Emma Hutchinson,“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s:Constituting Identity,Security and Community after the Bali Bomb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1,2010,pp.65~86.此外,艺术作品给人们提供了表达悲伤、愤怒和痛苦等情感的渠道,人们借助多种艺术形式缅怀失去的亲人,表达对战争的抵制,对和平的向往。相关题材的美学作品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在建构恐怖袭击后美国民众情感倾向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学理争辩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的美学研究。布莱克认为,在国际关系的美学转向出现之前,有两次小的转向。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后现代主义前所未有地冲击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主义质疑临摹式表征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挑战传统实证主义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实践。*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Shapiro,eds.,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1989;Richard Ashley and R.B.J.Walker,Special Issue,“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Dissid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3,1990,pp.259~268.后现代理论激发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争辩为美学维度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背景。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言,“最重要的是哪种形式的表征占据统治地位”。*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p.35.因此,后现代理论重新发现和强调了国际关系是表象政治的本质。第二次小转向是理论研究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布莱克认为,有意识地“遗忘”国际关系理论,能让我们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观察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派系间的纷争和不通融的态势,打破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Roland Bleiker,“Forget IR Theory,”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22,No.1,1997,pp.57~85.突破此束缚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国际政治不仅存在于高层政治领域和国家行为中,更是交织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而美学及其实践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美学维度的研究议程
自2001年布莱克提出美学转向以来,国际政治的美学研究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议程不断拓宽,思路日渐扩展,内容集中体现在大众文化中的美学维度考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大众文化涵盖领域广,涉及人数众多,其内涵的政治意义和权力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发挥文化表征的政治建构作用。*Iver B.Neumann and Daniel H.Nexon,“Introduction,”in Nexon and Neumann,eds.,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6,p.6,pp.14~17.
(1)文学与国际关系。
文学是美学最普遍和集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不仅描述世界,更能建构社会现实。文学是描述政治的主要艺术形式,很多作家通过小说描述政治现实和思考政治困境,也有学者研究文学叙事在理解和建构表象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国内关于文学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参见陈玉聃:《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82~106页;陈玉聃:《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第27~35页。文学对国际关系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上。布莱克认为,诗歌的语言是精炼的和反叛的,其语言创意和想象更能发挥美学感知对政治事件的思考。据此,他重点阐释了诗歌在反映现实、反对殖民统治、记载历史年代、集体记忆和塑造民族群体身份中的作用。*Roland Bleiker,“Towards a Culture of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North Korea,”Peace Review,Vol.14,No.3,2002,pp.121~148.在小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菲利普·达尔比系统地阐述了科幻小说在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与亚洲、殖民主义者与被殖民对象之间关系中起到的作用。*Philip Darby,The Fiction of Imperialism:Reading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stcolonialism,London:Cassell,1998.在他看来,小说是西方殖民霸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小说中的人物和历史叙事往往将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活动合法化。此外,殖民地的本土小说在反抗西方殖民占领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视觉艺术与国际关系
除了文学之外,视觉是美学表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把语言当作智性活动的最高形式,认为图像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不能成为理性思维的载体。但近年来,随着影像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发展,视觉文化*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详见W.J.T.米歇尔著,范静晔译:《图像转向》,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研究日益兴盛,视觉图像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也越来越明显。*关于国际安全中的视觉研究,详见Lene Hansen,“Theorizing the Image for Security Studies:Visual Securitization and the Muhammad Cartoon Cris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1,2011,pp.51~74;Lene Hansen,“How Images Make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con and the Case of Abu Ghraib,”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First View Article,2015,pp.1~26;Axel Heck and Gabi Schlag,“Securitizing Images:The Female Body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4,2012,pp.891~913。在视觉表征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重点关注政治漫画、照片和电影等图像形式对认识和建构国际关系的作用。例如,图像作为视觉语言能在话语体系内指涉和建构国际安全,诸如漫画等视觉形式能引发全球危机,人们通过观看照片或电视画面来了解国际政治,由此引发的情感、记忆和认知在塑造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重要作用。*何伟:《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以安全化研究为视角》,《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107~123页。诺伊曼的研究考察了美国流行电视剧《星际迷航》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该电视剧的剧情浓缩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人们通过观看此剧了解美国对外政策,而剧情本身也建构了观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Iver B.Neumann,“‘Grab a Phaser,’Ambassador:Diplomacy in Star Trek,”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3,pp.603~624.
(3)音乐与国际关系。
音乐是艺术美学和人类审美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形式抽象的音乐能够跨越不同语言、文化和国别的限制,具有形式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此外,音乐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功能,涉及普遍的人类情感性知识。可以说,音乐已经渗入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政治思想和表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传统国际关系对“生存性”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音乐和艺术等偏向于人类精神完善而非物质利益的“发展性”问题。*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20页。富兰克林在其开创性学术著作《奏响国际关系》中探讨了音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音乐在促进不同国家民众交流和文化融合方面起到的作用。*M.I.Franklin,ed.,Resou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 Music,Politics and Cultur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国内学者陈玉聃研究指出,音乐既能发挥诸如建构认同、服务外交和促进和平等工具性作用,其本体更能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为独立变量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音乐对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而这又会影响到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判断和行为。*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1页。尤其是音乐关涉到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产生、流动和集散,塑造着跨国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其间的权力关系。*陈玉聃、[赤道几内亚]何塞·穆巴恩·圭玛:《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35~57页。
三、美学表征与情感表达
与国际政治中美学研究相类似,情感研究也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与美学的遭遇相类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以来情感被认为是女性所具有的特征,因而是非理智的、情绪的和脆弱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男性话语激辩”中是没有地位的。详见 Carol Cohn,“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12,No.4,1987,p.688。国际关系中最早关于情感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政治心理学和外交政策分析的学者开始探索情感在对外决策和外交谈判中发挥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危机时刻的决策不是依靠理性作出的,领导人的智慧和启发更多的是源自“……情感,而非大脑层面的深思熟虑”。*Christopher Hill,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Houndmills:Basil Blackwell,2003,p.116.然而,此阶段的研究依旧延续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关于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传统,*Jon Elster,Alchemies of the Mind: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将情感看作是理性决策的障碍,是“错误知觉”的主要根源。*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57.为了批判此二元对立,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论证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No.1,2008,p.119.乔纳森·默瑟和内塔·克劳福尔德等学者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默瑟认为,在政治过程和外交决策中,情感与理性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情感是理性思维的依托,是建构群体认同的关键所在。详见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77~106。克劳福尔德在其研究中指出,情感一直贯穿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中,我们不能以理性的思维看待国际政治中的情感表现,对个人情感到集体情感建构这一过程的探索能够重新释放国际关系理论对人及其施动性的研究,重拾学科的人文关怀。详见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2000,pp.116~136.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情感研究的阵地,他们不仅从宏观层面考察情感在建构社会身份认同和影响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还借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微观层面探索具体情感表现方式(比如恐惧、愤怒、怜悯和热情等)从个人到集体的转移和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建构作用,以致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情感转向”的研究趋势。*Janice Bially Mattern,“A Practice Theory of Emo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Emanuel Adler,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3~86.然而,正如布莱克和爱玛·哈金森所言,到目前为止,学者关于情感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完善,理论流派过多,相互间的借鉴和交流较少,没能形成集中有效的研究议题和理论范式。*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3,2014,p.492.而造成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政治中的情感研究还未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情感如何上升为集体情感、从私人领域进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问题。*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3,2014,p.497.
美学表征可以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思路,情感具有审美的向度和社会的维度,而美学表征是理解情感从个人到集体过渡和建构的关键所在。*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3,2014,p.505.
第一,美学表征可以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和交流提供多样的渠道。国际关系中情感研究的棘手之处在于,情感是无形、短暂和易变的,而研究者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无法直接潜入个人大脑并探索他们的所思所想。多数研究只能依赖被观察者的行为和动作来分析其情感反应,*Shaun Gallagher and Somogy Varga,“Social Constraints on the Direct Perception of Emotion and Intentions,”Topoi: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hilosophy,Vol.33,No.1,2014,pp.185~199.或者从日记、传记、随笔或事后访谈中分析他们在决策情境下的情绪和感情的细微体现。*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2000,p.131.而诸如散文、诗歌、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往往最能集中呈现个人的情感和体验,能为行为者情感的传达提供多样的载体。研究表明,亲历过恐怖袭击或重大灾害的人群因为心灵震动和创伤会突然“失声”,即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为了排解内心的恐惧、愤怒、悲伤或怜悯,很多人借助绘画或其他艺术形式宣泄自己的情感。*Emma Hutchison,“Emotional Reconciliation:Reconstituting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fter Trauma,”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11,No.3,2008,p.388.这也是“9·11”事件后,关于恐怖主义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诗歌和绘画还是音乐和电影,数量都具有很大增长的原因。
第二,美学表征能建构个人情感扩展为集体情感的过程,并使其具有社会和政治维度。美学表征提供了情感表达和交流的媒介,可以表现为各种文学、视觉、音乐和建筑等艺术品。类型多样的展览活动,无论是出自个人行为还是机构组织,可以使这些作品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内得到传播。自然而然,在人们观看行为和欣赏过程中,寄托着个人种种微妙而强烈情感的艺术作品会无声无息地塑造一种“感性的流通”,*Andrew A.G.Ross,Mixed Emotions:Beyo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14.在公共展览中逐渐造成一股集体情感的宣泄和特殊身份的重塑。因此,美学表征的过程可以使个人情感的传播渠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视线,其意义在群体的观看和体验后能得到进一步的界定和传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群体态度、行为和记忆可以将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建构集体身份和认同的情感纽带。*K.M.Fierke,“Whereof We Can Speak,Thereof We Must Not Be Silent:Trauma,Political Solipsism and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4,2004,pp.471~491.例如,“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学作品寄托了人们的哀思,抚慰了幸存者的心灵,经过公共展览后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形成了一股集体审美思潮和情感宣泄的洪流,而美国政府也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怖和愤怒等情感为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了合法性。*Andrew Linklater,“Anger and World Politics:How Collective Emotions Over Time,”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3,2014,pp.574~578.
四、结语
本文将国际政治作为表征系统来研究,并将国际关系的表征分为临摹性表征和美学表征。与临摹性表征认为理论与现实必须实现无缝对接的镜式观不同,美学表征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表征过程中总存在着表征形式与被表征对象之间的差距或缝隙,而人的解释和施动性在此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此外,学科和学术领域并非只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更是人关于世界观察的特定方法和知识创造。Michel Foucault,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69. 转引自[英] 巴瑞·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世纪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30页。这正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理论推陈出新的动力所在。研究者并非只是被动地把事先存在的现实用理论化的语言描述出来,客观现实只有在人的话语和意指实践(如美学实践)中才能获取意义。因此,加强美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能重拾美学的政治价值,而且能突出研究者个人在理论建构以及普通大众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代表着理论研究的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性回归,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主流理论重理性(忽视感性)、重国家(忽视组织和个人)、重军事安全(忽视社会和个人安全)等在认识上的垄断局面,有利于理论的多元发展。
此外,诸如诗歌、小说、绘画、电影和音乐等美学形式不仅是社会政治实践及其意义反映的所在,也是建构国际政治的重要载体。体现在情感领域,美学表征不仅寄托了个人的情感,而且为个体情感汇入集体情感提供了多样化的表达渠道,更发挥着协调社会情感和建构群体身份认同的作用。因此,美学表征的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的情感研究提供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国际政治的美学维度考察对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的美学范式与西方审美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美学主张表现论,而西方美学主张再现论。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西方美学传统一直主张艺术摹仿论,而中国古典美学、艺术精神、哲学精神甚至整个民族精神都显示出表现的旨趣。中国的美学史是围绕着意象而展开的,而人的诠释、情感、施动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意象生成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西方哲学注重理念,西方民族的基本精神和性格表现为对理性和秩序权威的追求,因为理性和秩序在西方民族精神中有着深刻的根基,这一点也反映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中。而中国哲学是道的哲学,重视本体和生命,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外界、伦理与实践的统一。*有关中西美学的差异,参见肖鹰:《论中西美学的差异》,《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第24~34页。张法:《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的几点差异》,《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第5~12页。近年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掀起一股历史文化转向的潮流,*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参见王江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7~92页。关于从历史文化角度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从以往朝代哲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经验来建构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相关学者主要以秦亚青和阎学通为代表。详见Qin Yaqi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No.3,2007,pp.313~340;Qin Yaqing,“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China,”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No.1~2,2009,pp.185~201;秦亚青:《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Yan Xuetong,“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2,No.1,2008,pp.235~265;阎学通:《先秦国家间的政治思想异同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更好地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在中国也可以发起国际政治的美学研究,参照本土审美思维和美学实践,努力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以理性认知为核心的思维定势,从我国自身审美文化出发来思考和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何伟,外交学院2014级国际政治语言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