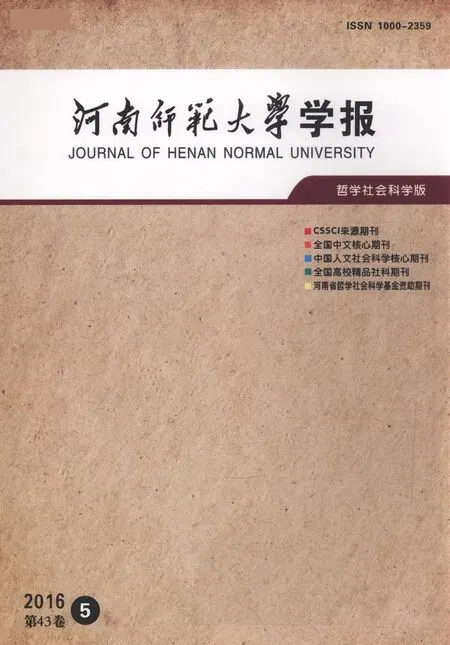创伤叙事与救赎可能
——以福尔小说《异常响,特别近》为中心视域
2016-03-16吴玲
吴 玲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创伤叙事与救赎可能
——以福尔小说《异常响,特别近》为中心视域
吴 玲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乔纳森·萨佛兰·福尔的第二部作品《异常响,特别近》是一部关于人类战争、创伤以及如何自我安慰、告解和救赎的创伤小说。作者通过凌乱的谋篇布局、嘶哑的声音、古怪的对话、一系列的数字、混乱的照片、几乎空白的页面、黑漆漆的页面等后现代主义拼贴手法,再现了谢尔一家心灵的创伤。这部“灾难写作”把伤痛的不可言说性发挥到了极致,三位叙事者兼主人公试图用语言来呈现创伤,却又难以言表,因为史无前例的灾难抗拒言说。一方面想要否认可怕事件,一方面又想把它们宣讲出来,如此的纠结构成了心理创伤的核心逻辑辩证法。
灾难;沉默;创伤叙事;失语;书写;救赎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身处表象和平中的人类面临的挑战和灾难丝毫不亚于上世纪之初。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开启了新世纪人类历史的黑暗篇章,近年来恐怖主义组织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反恐”已然成为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沉重话题。在世界文学领域,一大批当代作家拿起笔杆,奋力描写、述说、和阐释着战争的苦难与创伤,其中尤以美国本土作家为首。在《好牧师之子》中,雷诺·普莱思讲述了一位艺术品修复师的离奇经历:在“9·11”的早晨返回纽约的途中,他所乘坐的飞机忽然偏离航道驶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与此同时,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也被夷为平地。琳恩·莎朗·施瓦茨在其新作《凶兆》里描述了一个长期生活在自我封闭世界里的图书管理员目睹了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后内心产生的巨大变化。在《坠落的人》一书中,唐·德里罗通过描绘基斯一家三口在“9·11”恐怖袭击中各自不同的创伤体验来映射整个美国社会和美国家庭所遭受的集体创伤,剖析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给后“9·11”时代美国社会普通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犹太裔美国作家乔纳森·萨佛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2002年因出版有着杂乱而奢华情节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EverythingIsIlluminated)一举成名。2005年,第二部作品《异常响,特别近》(ExtremelyLoudandUnbelievablyClose)问世,并于2011年被改编成电影,为他带来更大的荣誉和更广泛的认知度。
《异常响,特别近》围绕一把钥匙展开,主人公是9岁男孩奥斯卡·谢尔(Oskar Schell)。他的父亲小托马斯·谢尔(Thomas Schell Jr.)是一位珠宝商,在世贸大楼105层办公,于“9·11”事件中丧生。灾难发生那天,奥斯卡提前放学回家,在录音电话里听到了父亲去世前的5个电话留言,这些留言一条比一条悲观,从此便留下了失眠、害怕电梯等后遗症。无意中,奥斯卡打碎了父亲书柜上的一个花瓶,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把钥匙,信封上写着“布莱克”(Black)。奥斯卡认为,这把钥匙可能会使他了解到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更加拉近他和父亲之间的距离。为了解开这个谜,奥斯卡利用周末走遍纽约五个街区,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逐一拜访了纽约电话号码薄上能查到的所有姓“布莱克”的人,寻找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寻找是对父亲的追忆,是谋求心灵解脱的途径。在寻找的路上,他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痛苦的人们。在不停的寻找中,他走进了历史,走进了祖父母扭曲的爱情和三代人布满伤痛的情感回忆。
一、寻访之旅:创伤的自我救赎
创伤一词(trauma)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中“损伤”,其原来的意思为“伤”,既可指由某种直接的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也可指由某种强烈的情绪伤害所造成的心理损伤;在西方学界,卡鲁斯(Cathy Caruth)对创伤的精神分析研究以及范德科克(Bessel A.van der Kolk)等人的神经学创伤研究常常被用于文学作品中的创伤解读。卡鲁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灾难年代里,正是创伤事件本身为不同的文化建立了联系。”创伤研究表明,创伤对于儿童的影响尤其通过儿童不断重复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游戏行为得以表现,创伤儿童往往在游戏过程中表达创伤主体的真实感受[1]。
丧父之痛使奥斯卡的语言充满忧伤,创伤的难以言说使得他只好求助于“病态的安慰机制”[2]172。从父亲的五个电话留言中,奥斯卡知道,9月11号这个“最糟糕的一天”[2]42,父亲被困在燃烧的大楼里,曾发疯般地试图与家人取得联系,他知道那是父亲绝望中的呼叫。然而,父亲离开了,来不及再说一遍“我爱你”。纠结于失去父亲的痛苦以及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能力救父亲的负罪感,奥斯卡感到茫然:“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漆黑的漫无边际的大海中,或是在遥远的天空中,但并不是以让人着迷的方式。”[2]176失去了父亲这位人生的向导和老师,奥斯卡感觉迷失了方向,“发现的越多,理解的越少”[2]10,沮丧的心情就像穿着“沉重的靴子”[2]163,奥斯卡忍受着创伤的所有症状:失眠,过分警觉,害怕乘地铁、渡船、电梯(一切可能是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避开长胡子或缠头巾的人,满腹怒火,情绪极易波动,自我封闭,把自己搞的鼻青脸肿,等等。这种自残是一种觉醒过度,以至于他无法松弛下来,只好狂热地发明东西。他希望父亲复活,发明了能以父亲的声音说话的茶壶,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能记录心脏跳动的麦克风、穿上去之后能飘在空中的鸟食衬衫、摩天大楼的气囊,等等。
灾难带给奥斯卡的是心灵的黑夜。在班级戏剧表演中,奥斯卡扮演《哈姆雷特》中已故的宫廷小丑约里克,一个躲藏在骷髅下的无言的角色,这时,奥斯卡想到了死,感受到了的吸引力:
那个晚上,在舞台上,在骷髅下,我感觉距离宇宙间一切东西是特别地近,
然而又异常地孤独。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怀疑,生活是否值得我们所做的一
切,到底是什么使它值得?永远的死亡,什么也感觉不到,甚至连梦也没
有,这一切为什么糟透了?感觉和梦想为什么如此重要?[2]142
这段话句法混乱,思维紊乱,它表明极度痛苦的奥斯卡徘徊在精神错乱的边缘,变得情感麻木,忧郁自闭。在课堂上介绍广岛原子弹轰炸时,他根本不为所描述的极端痛苦所动,而是漫不经心地提到,几周前,他把心爱的猫带到学校,“从房顶上扔下去,以测定速度”[2]193。奥斯卡似乎没有了残忍的概念,没有了同情心,他的令人震惊的举动背后隐藏的是麻木的情感或者是过度的情感。他自己承认:“我的人生正经历着一段难以忍受的时光,我的内心与我的外表不一致。”[2]196
灾难破坏了言述自我的能力,难以承受丧父之痛的奥斯卡只好踏上了寻觅之途,寻找“父亲”,寻找迷失的自我。在寻找钥匙的秘密的过程中,奥斯卡遇到的第一个人是48岁的阿比·布莱克(Abby Black),她与奥斯卡很快成为朋友,但没有提供一点有关钥匙的信息。之后不久,阿比又给他打了电话:“(她)没有跟奥斯卡说实话,(她)想(她)或许能提供帮助。”[2]91奥斯卡又回到了阿比家,阿比让他直接去找她的前夫威廉·布莱克。与威廉·布莱克交谈之后,奥斯卡获悉,那个花瓶曾经属于威廉的父亲。在遗嘱中,威廉父亲留给威廉一把打开保险箱的钥匙,但是,在家产变卖时,威廉已经把花瓶卖给了托马斯·谢尔。最后,奥斯卡给了威廉两把钥匙,一把是威廉父亲的保险箱钥匙,一把是奥斯卡自己家的钥匙。
奥斯卡终于为钥匙找到了主人,也找到了打开心结的钥匙。他的寻找之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包括患有严重残疾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霍金在信中强调要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当我坐着轮椅四处走动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思想,就像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其实很简单:今天正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一天。”[2]329霍金的信使奥斯卡逐渐意识到:既然明天是不确定的,那就要好好的珍惜现在,愉快地接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把每一天都看做是一个礼物。在寻找过程中,奥斯卡终于成功地对现实进行了重新编码和重新译解,使故事有了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
二、失语与书写:创伤的后遗症
根据霍尔曼(Judith Herman)的研究,创伤记忆是“无语静默的”,通常在“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中”展现[3]。而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等认为,创伤经历最具破坏性的是造成“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的失去”[4]231。因此,创伤叙事通常作为衡量创伤痊愈与否的标志。
詹尼特·皮埃尔认为,创伤的核心就是创伤记忆。在创伤记忆中,创伤者往往因为经历一些骇人听闻的创伤事件而会失去对其主体的判断,这就造成创伤者虽然能够记得事件的种种细节,却无法看清事件的全貌,将其融入自己的认知结构当中[5]。当经历者想要表述创伤记忆的时候,其语言往往缺乏逻辑性、连贯性和整体性。和创伤记忆相对的是叙事记忆,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熟悉的经验会被自动整合入认知体系,无需对特殊情况的细节加以自觉意识,通常来讲,叙事记忆会呈现出线性的,有情节的特点。所谓叙事,简言之就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引导创伤经历者恢复其叙事能力,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就成了疗愈创伤的一个重要途径。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深受创伤的困扰,与故事主线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两个叙述声音,即奥斯卡的祖父母。祖父老托马斯·谢尔(Thomas Schell Sr)的未婚妻安娜在二战德累斯顿轰炸中死去,当时已经有孕在身。失去心上人和未曾谋面即夭折的孩子之后,祖父常常感叹:“我已经失去了唯一能与我共度此生的亲人。”[2]28再也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感情投资。几年后,安娜的姐姐,即奥斯卡的祖母,在纽约的一家面包房与祖父偶遇,相互认出了对方,但祖父矢口否认他是托马斯·谢尔。实际上,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健谈、和蔼、有抱负的托马斯·谢尔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就是他的名字谢尔(Shell)的含义:德累斯顿灾难之后,他只是那个曾经的他的‘外壳’。共同的“失去”以及对逝去的安娜的共同的爱是连结他们的纽带,为彼此拯救,他们冲动地结了婚。可怜的祖母只不过是她死去的妹妹安娜的替代品,他们的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对现实、命运、创伤的妥协,但是,含有某种“妥协”的婚姻是不稳定的,注定是要失败的。祖父母创造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沉默的婚姻生活:“从不谈过去”,“从不听忧伤音乐”,“从不看有关患病儿童的节目”[2]110,希望通过回避生活中的创伤,忘却一生中最为糟糕的记忆,结果却出现情感停滞,即创伤理论上的“压抑”。他们的时间停滞了,虽然居住在纽约,却完全沉浸在德累斯顿的过去,他们生存的每一秒都充满了难以忘记的恐怖。结婚初期,他们决定把房子分为无物区和有物区。无物区是他们都不允许看的地方,是一个“完全私密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人可以暂时不再存在。”然而,无物区并不是一个忘却的极乐区,而是展示历史给个人生活所带来的极度震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人与人的交往,祖父母完全沉浸于过去而无法自拔,上演着生存的创伤,他们的生活因此而陷入虚无和静止。当祖母违反他们之间“不能要孩子”的婚姻协议,通过计策怀孕时,祖父收拾好行李,悄悄地离开了,回到了最终的“无物区”,回到了他永远无法逃避的地方:德累斯顿,在对死者的思念中度过余生。祖父母在各自隐退的地方,不停地给他们所残酷遗弃的人写信——祖母写给孙子奥斯卡,祖父写给他从未见面的儿子,除其中一封之外,其他都未曾寄出。
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等认为,创伤经历最具破坏性的是造成“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的失去”[4]232。沉湎于过去的伤痛而无法自拔的祖父上演着压抑的一幕幕,最明显的症状是失语。他失去的第一个词是他未婚妻的名字,不会喊“安娜”;第二个词是连接词“和”(and),或许是因为and的发音近似安娜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的按逻辑顺序排列事情的组合能力日渐瘫痪(and的作用是连接并列的名词、代词或数词);他失去的最后一个词是“我”。痛苦日渐增长,他的语言世界随之缩小,他的整个世界萎缩了,直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我想理清头绪,解开蒙在头上的沉默,一切从头再来,但是我说的还是“我”。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能力,祖父被禁锢在逐渐缩小的微不足道的自我世界里。“我”孤独地站在引号中,后面不可避免地跟着句号,这些符号象征着祖父的孤独与隔绝。祖父无法与过去割裂,无法从头开始,不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只好设法压制记忆中的“安娜”,而不是设法走出来,他就这样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了,并一步一步走向灾难性的自我封闭,最后说话能力完全丧失,仅靠在日记本上写下一串串简单的短语交流。尽管他拼命地抓住了这些语言碎片以使自己看起来无异于常人,但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短语无不透视着他生活的无序,象征着他生存的残缺。纸张短缺时,只好借助于以前草草写下的短语,即使是最重大的决定——比如涉及他和祖母的婚姻——也不得不妥协于循环使用的涂鸦,祖父自我世界的枯萎由此可见一斑。为了交流,祖父分别在左手和右手上纹出“是”和“否”,作为他基本的符号语言,通过举起左手或右手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一手势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二元逻辑当中,使他不能像常人那样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自己的观点。
强烈感受到家的牵挂,祖父决定从德累斯顿返回纽约,看望他的儿子。在机场的那一刻,祖父一时冲动,决定在电话里告诉祖母所有一切事情:“我为什么离开,我去了哪里……我为什么又回来了,有生之年我需要做什么。”[2]260由于不会说话,祖父只好按电话触摸屏上的数字,一连串的数字长达两页。祖母听到的是不同节奏的嘟嘟声,读者读到的是一大段无法破解的密码。祖父试图用他的手指打破横亘于他与他的生活之间的那堵墙,但是又有谁能听懂他的话呢?
祖父特别期望打破语言的禁锢,从1963年5月到2003年9月这40多年间,他给儿子写了无数封冗长的信件(未出世时期,成长期,死亡之后),然而,除了一封信之外,其他的均未寄出,祖父只是虔诚地书写着保管着这些信,因为它们承载了祖父无法释怀的记忆、痛苦、愧疚。相反,祖母每天收到一封空信封,她把这些空信封都藏匿起来,直到有一天被奥斯卡发现。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那么的牢固,永不缩减,日日更新,然而却又是一片空白。缺席的父亲与被遗弃的儿子之间因心灵的创伤而没有得到完整的情感与体验,连基本的对话都没有。一封封未寄出的信字字句句都是祖父滞留不去的伤痛,生活的每一天都上演着过去的故事。故事的每一页都没有理性顺序,没有段落,随便画上一个句号或问号思维意识就中断了,多数句子由逗号连接起来,让人感觉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能听见我的骨头在生活的重压下扭曲,我没有活着。”[2]210信件充斥着以幽闭恐怖症词汇形式出现的“创伤性写作”,现在进行时的应用表明,祖父的视野永远逃不出难以抗拒的压抑,生活的每一处似乎都在实践着无法言说的创伤。在最后一封信中,作者采用了视觉手段。祖父一直担心时间和空间不够,他开始压缩行间距,能写字的地方都用上了,不留任何空隙,直到行与行重叠起来,页面字迹模糊,黑黢黢一片。这模糊的字迹正是模糊的历史,这漆黑一片正是奥斯卡试图寻找的“布莱克”,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试图从语言上重新书写创伤性历史,其结果要么是一片空白要么是漆黑一片。祖父不断涌现的思想最终消失于彻底的无言和一片黑暗中,这黑色的一页完成了祖父的失声:超负荷的无言和符号是一种无法理解。对祖父而言,失去语言与语言过剩是同样的效果,二者都会导致交流能力的丧失。黑色的页码象征着死亡和压抑以及祖父彻底的与世隔绝。这黑色的一页,使得灾难的书写实现了真正的困惑:越是想在这一页讲清楚,越是不能讲清楚。当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时,祖父又接着写了密密麻麻三页,一页更比一页黑。他的书写是无法传递的最消极的书写,他的书写是自我毁灭。
祖父回到纽约,和孙子一起打开他儿子的空棺材,并把从德累斯顿带过来的未寄出的信填充进去。在这位“9.11”受害者的坟墓旁,祖孙三代——祖父,父亲,儿子——团聚了,这种缺席的团聚何等的凄惨!怎能减缓祖父的焦虑情感,怎能让伤者得到真正的宣泄。掩埋了心中的秘密也不能使他重新开始婚姻生活,不能使他和刚刚找到的孙子建立永久的关系。原本打算留下来的他,在重新埋葬儿子之后,还是选择回到德累斯顿,因为他所受到的伤害是这些象征性的调和行为所无法治愈的。
三、空白书写:创伤的疗愈
饱受情感折磨的祖母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只好以空白书写来展现心理的不确定性。“空白”也是一种艺术,是以“无”来表达“有”的艺术表现方式。“空白”是一种“消失”,是一种“不出场”,“空白”意境成为审美时序的一个“断点”,秩序的中断、突变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暗示,形成了需要填补的空白和心理的紧张感。
《异常响,特别近》中祖母那些可观可感的空白书写,实际上是“空缺”、“无”和“不在”,有形的空白页码汇集了含混的意味,彰显了祖母的不确定状态,实际上也是祖母思维过程中的无形的意义空白。祖母一再唠叨:“我的视力很糟糕。”[2]33可能她真的视力很差,但更重要的是,她仍然被以前在欧洲时所发生的事情所羁绊,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地方,她辨不清方向,无所适从,无法看清任何事情。祖父建议她用写作疗法来“减轻负担”。一连几年,她消隐在客房的“无物区”,专心写她的回忆录,试图记录创伤性的过去。但是,由于“视力模糊”,没有注意到打印机没有色带,结果,当祖母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她递交的只是几千页的空白纸张,其中的一部分被记录在小说中。作者采用这种插图/印刷技巧,实现了对交流缺席的魔幻现实主义隐喻,极度的痛苦与失去只能用没有文字的文字来表述。后来祖母解释说:“我走进客房,假装在写,我不停地敲空格键。我的生活故事就是空白。”[2]120祖母写给奥斯卡的信段落很短,一段往往只有一句话,非常喜欢空格键,且句与句之间有很长很长的空格,结果,整个页面几乎是空白。句与句之间非常显眼的空间是祖母沉默的表达,象征着她生活中的裂缝和空白。只要伤痛是不能叙说的,它就会遭遇空白问题,并一直抹杀着现在。对于祖母而言,过去之所以确定,是因为它无法言说,所以表现出来的是空白。
祖母的空白页是对祖父的漆黑页码的补充,黑白对照共同见证着语言的匮乏、语言的局限性以及创伤的无法言说性。当人们面临创伤时,即人类正常经历之外的可怕事件,他们经历的是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恐怖。这种经历无法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组织,无法用词汇和符号来整理,只好借助体觉层面或图像层面。作为践行的语言和作为空白的语言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或者说,表达与沉默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可以说,《异常响,特别近》是一幅布满泪水的后现代主义拼贴画,三位叙述者以各自不同的形式伤心欲绝地表达着不可言说的伤痛。小说中年纪尚小却内心强大的奥斯卡凭借其积极勇敢的生活态度和不懈努力,最终走出创伤,开启了新生活,变得“开心和正常”,他的人生实践为后9.11时代普通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民树立了榜样,即唯有自我救赎,才能告别创伤,继续生活。
[1]Dodman,Trevor.Going All to Pieces:“A Farewell to Arms”as Trauma Narrative[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006,52(3).
[2]Foer,Jonathan Safran.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M].London:Penguin Books,2005.
[3]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Contemporary Symbolic Depictions of Collective Disaster[M].New York:Lang,1995:175-177.
[4]Shoshana Felman,M.D.Dori Laub.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M].New York:Routledge,1992.
[5]刘荡荡.表征精神创伤,实践诗学伦理——创伤理论视角下的《极吵,极近》[J].外国语文,2012(3).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8
2015-11-27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2015BWX028)
I106.4
A
1000-2359(2016)05-0161-05
吴玲(1980-),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