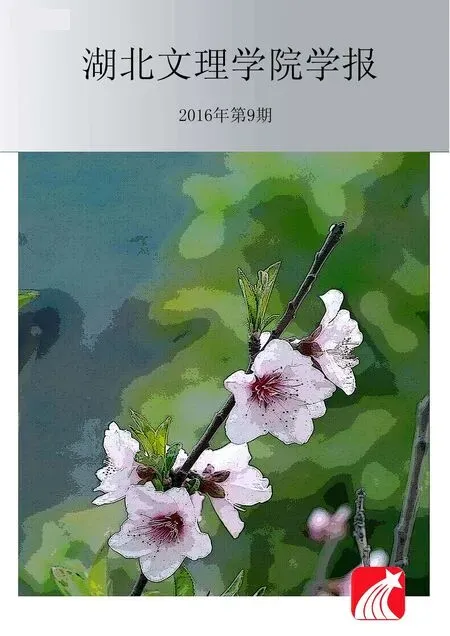卡夫卡作品中的“约伯”原型研究
2016-03-16赵雯芊
赵雯芊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卡夫卡作品中的“约伯”原型研究
赵雯芊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原型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在人物形象的创作中也可以取材于比之更早的意象。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主人公受难的情节屡屡可见,仿佛书写着世界的残忍和暴戾,而这一切与《圣经》中《约伯记》表达的理念不谋而合,可以说约伯是作为原型存在于卡夫卡作品中人物身上的。无端变形的格里高尔是受难的约伯,为艺术献身的饥饿艺术家是殉道的约伯,莫名被逮捕的约瑟夫·K是蒙冤的约伯,不断寻找城堡的K是追寻的约伯。卡夫卡身为犹太人,他的书写隐约带有犹太民族文化心理的印记。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发出了自己的呐喊,这也正是卡夫卡的魅力所在。
《圣经》;《约伯记》;卡夫卡;约伯
《圣经·旧约》中的《约伯记》是希伯来智慧文学的经典之作,讲述了主人公约伯突然在一天之内经历妻离子散、家产散尽、身体受难的悲剧。他不断的探求着自己无故受难的原因,并不断的询问他人询问上帝。他品行纯良、笃信上帝并且受人尊重,他每时每刻监督自己的行为,杜绝自己做丑恶之事。他同样对家人严加要求,恐怕触怒于神。但神之子撒但质疑约伯对神信仰的纯正性,耶和华遂允许撒但毁掉约伯的一切来证明约伯是否真正的虔信自己。于是,约伯无故受了巨大的灾难。《约伯记》在开篇就提出了“义人受苦”的问题。“义人命运多蹇,坏人诸事亨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接受的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永恒探讨的话题。它折射了对公平与正义、神义与人义乃至苦难等人类发展历程中本质问题的关注。《约伯记》试图对“不知道为何受苦时,如何应对苦难”这个问题抛砖引玉,做出自己的思考。约伯最后虽然恢复了起先的一切但创伤依旧还在。这种创伤仍会使得人们不断反思,约伯最后选择了与上帝和解,依旧做上帝最虔敬的仆人,但是面对强大的不可控的灾难,他依旧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与抗争。这是约伯面对强力的无奈,也是为了保全自身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世界文学史上,卡夫卡的作品深受《约伯记》的影响,正如弗莱曾指出: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就是对《约伯记》的注释。[1]115卡夫卡本身作为犹太人,对自身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理解犹太民族自身的苦难也对苦难感同身受,他笔下人物面对莫名灾难时的无奈与彷徨,无疑是约伯的影子。可以说约伯作为原型植根于卡夫卡的作品中,在现代社会迷茫颓败的大坏境中,如何认识苦难,化解苦难成为卡夫卡笔下的“约伯”们共同面临的抉择。
一、格里高尔——受难的“约伯”
格里高尔是《变形记》中的主人公,他一大早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恐惧和焦虑伴随着他,但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是自己作为旅行推销员的工作,他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因迟到的缘故莫名失去。这份工作虽然很累人,“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2]107但是格里高尔作为父亲的好儿子、妹妹的好哥哥,还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并攒钱为父亲还债,为妹妹交学费,并且照顾家庭开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面对上司的不公与刁难他坦然承受只为了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妹妹能实现自己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他单纯地将家人当作自己前进的动力以及自己坚定的信仰。自己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家人的幸福快乐。而无故的变形打乱了他的生活,他原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变形却赋予了他反抗现状的勇气与力量。但是“变形更深刻的含义与其说是反抗,勿宁说是受罚。”[3]253这个被迫变形的偶然的无妄之灾造成了主人公自责、矛盾反抗乃至毁灭。他的身上隐约有着约伯的影子。格里高尔与约伯相似的是,首先,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们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约伯崇信的是神耶和华,格里高尔崇信的是自己的家人。其次,他们都同样遭受了无故的灾难,即好人受难。约伯:有一天内接到三个噩耗,由当地首富变得一贫如洗,其乐融融家庭变得悲悲戚戚,家破人亡,达到了不堪忍受、天塌地陷的境地,又雪上加霜,从头到脚全身长满毒泡。而格里高尔也遭到了不堪忍受的生命变数,一夜之间变成异类,惨遭家人及外人的排挤。再次,他们都无法被旁人理解安慰,反而遭到误解,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苦痛。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为何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4]243当约伯诉说自己的不幸时,他们冷眼旁观,无法感同身受。他们用传统申命派神学理论来解释约伯的痛苦,即“苦难来自对罪恶的惩罚”。他们认为约伯之所以无辜受难,是因为他罪有应得。约伯是孤独的,在神义论的统治下,他的受难只是一种对他信仰的检测,是一种考验他对耶和华是否虔信的手段,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同时神也是威力无边必须值得敬畏的。没有人可以理解约伯的痛苦与孤独,他只有通过不断的叩问上帝,才能寻求解脱。格里高尔也是如此,陷入了人生的孤苦无援状态,他变形之后家人应该理解包容他,但恰恰相反,母亲开始一见到他就吓得惊叫起来,后来一直不敢到屋子来,更不用说照顾关爱儿子了,尤其厉害的是他的父亲,最初是用手杖无情地把他往后赶,然后相当长时间从精神上冷落他,不让他进房门,厨娘将他的房间当成了臭气熏天的储物室,并且不照顾他的饮食,他出于好心走出卧室给拉提琴的妹妹助威却吓跑了三个房客,作为他精神支柱的家人在他变形后却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和怪物,想方设法离他而去。他在异化后感受不到温暖只有冷漠与苦痛,最终在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双重迫害下死去。最后,他们都是饱含悲剧意味的。约伯虽然恢复了之前的财产和名望,但是是以“隐忍”为代价的,他隐忍神对他恶作剧般的“考验”,并不得不抹除伤痛的记忆,甚至在此后的生命中更加虔信神,因为他深知神力的强大,自我的渺小,他仍是神忠诚的仆人,苦难也必须深埋在记忆里,成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痛。格里高尔以绝望的死去作为抗争苦难的结局无疑是悲壮的,他是“受难”的约伯,他无法像约伯一样奢求结局的圆满,他的异变只能遭受毁灭。卡夫卡对格里高尔结局的处理无疑是残忍的,他以让敏感脆弱的好人受难来彰显人生的荒诞无常,读之令人心痛。
二、饥饿艺术家——殉道的“约伯”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塑造的令人心碎的人物形象之一,饱含着作者的寄托和感情。主人公饥饿艺术家无名无姓,他是为了顺应饥饿表演而诞生的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与其说他的存在是为了献身艺术,不如说他已被视为娱乐大众的赚钱工具。在之前的时代,“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2]222但是大众对饥饿艺术的兴趣并不是持久的,在他们眼中,饥饿艺术只不过是博人眼球的表演而已,对饥饿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全然不解,甚至连看守也无法相信饥饿艺术家会一直不进食下去。饥饿艺术家对他人无法认可自身艺术成就的行为感到愤恨不解,所以当他到马戏团进行饥饿表演时,人们已然完全忘记并抛弃了他的饥饿艺术,谁也不知道他成就的伟大,甚至连他自己也在质疑自身的成就。最后一只黑豹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的尸体也和一堆稻草一起销声匿迹。饥饿艺术家正像是一个指向标式的人物,一种象征。他终其一生不断追求着世人无法理解和认可的艺术,甚至最后不惜以死亡进行无声的呐喊。可以说他是殉道者一般的存在。“他没有能通过死来达到生,他死的时候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承认,而那些人正是他自己一辈子都拒绝接受的。”[3]165他的困境在于画地为牢的孤独与试图使人理解的悲哀,他存在本身就是具有悲剧意义的。饥饿艺术家与约伯相似的是,首先,他们都为了信仰而甘愿忍受苦难,饥饿艺术家的信仰是他引以为豪的“饥饿艺术”,他甘愿不断忍受饥饿,即使不在饥饿艺术表演时,他也甘愿忍受饥饿。约伯的信仰是神耶和华,为了证明自己对神的虔信他默默的忍受着神对他考验的苦难,虽有怨言,但他也选择忍受,在这里约伯是“忍耐”的代名词。其次,他们都不被世人理解。约伯在受难的过程中无法获得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和帮助,认为他的受难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对他冷嘲热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得以展现。饥饿艺术家更是如此,他献身的饥饿艺术事业却是经理捞钱、民众消遣的娱乐,他存在的价值在于是否能提供金钱与娱乐,与他的艺术追求相差千里,这无疑是讽刺的。再次,他们都是孤独的。约伯无法找到自己无端遭罪的答案,饥饿艺术家也无法找到欣赏自己艺术信仰的人类,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皆是徒劳。唯有孤独永恒伴随着他们。最后,他们都是“西绪弗斯”,不管约伯还是饥饿艺术家都像西绪福斯一样日复一日的忍受着苦难,而这种苦难却是一种充满悖谬性的存在,约伯的苦难是上帝与撒但打赌之下调戏般的产物,而饥饿艺术家的苦难是他的精神追求无法适应物质社会下大众审美要求的无奈。不管是诚意地接受苦难还是无奈地接受苦难他们都是无法选择的,也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卡夫卡以约伯为原型注入饥饿艺术家的形象之中,相较约伯的圆满性结局,饥饿艺术家则更显悲凉,他是殉道的,以死亡为代价完成了对苦难的嘲讽,这也正是卡夫卡作品的伤痛之处。
三、约瑟夫·K——蒙冤的“约伯”
约瑟夫·K是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人物。讲述的是主人公K在他30岁生日那天莫名被警察逮捕,他本是一家银行的襄理,工作体面还拥有仆人,平时作风正派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警察逮捕,失望和恐惧包围着他,虽然可以正常工作、生活,但被冤屈的苦难始终包围着他,使他心神不宁。他不断的借用他人的力量如律师、与法院相熟的画家、法官、所谓的证人来为自己脱罪,但一切皆是徒劳。K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5]177,他自己何尝不是在荒谬的被审判中冤屈地死去。他说“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直到最后一刻保持冷静和理智。”[5]181但是他崇信的世界本就是一片谎言的废墟,所谓的公义始终无法可得。与约伯一样,彼此都是冤屈的灵魂。与约伯相似的是,首先,他们都是被冤屈的。约伯并没有犯任何过错却遭遇了亲人死亡、财产散尽,自身皮肤溃烂的灭绝性灾难,而K则是在没有犯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判有罪。其次,他们都在探讨着罪感意识。罪感是个体性的,只有当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开始探询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时候,罪感才会油然而生。K和约伯都在反复追问自身是否有罪的问题,他们自认为无罪却被视为有罪。卡夫卡曾说:“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过无关。”[2]11一语点破了罪的问题的实质。再次,他们的故事都考察着对正义问题的追问。约伯面临的是神义的制裁,神是强大的,人是渺小的,神即公义,但是神既然是公义的,神又为何让好人受难呢,惩罚有道的秩序是否存在呢?还是神义其实是一种维持原状的空想。神义论的真正目的在于巩固一神论的主体地位,确立神的至上权威,那么人的公义又该何为?但是一神论占主导下“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4]210所谓的公义也只是神的意志。K面临的是人的审判,在神缺离的现代社会,人制定的法律起着维持公义的作用。可是人义是否又是绝对公正的呢?神都无法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公义更何况人。法律被滥用,好人无故受难的现象更是屡屡可见,失去了对神的信仰人更是为所欲为,人义的公正性更是无法得到保证。K最后寂静地死去,申冤更是寥寥无期。卡夫卡如外科医生般精准地将赤裸裸的真相抛开给人看,虽然血淋淋但是引发了对“约伯式”无故受难的思考,令人阵痛。
四、K——追寻的“约伯”
K是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讲述了K突然接到城堡的来信邀请他到城堡附近的村庄进行土地测量。他满怀希望的到达村庄却被质疑其真实身份,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接近城堡的主人克拉姆,并企图证明自身身份的合法性,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城堡是富有权威的,也是遥不可及的,村庄的人们也以城堡的意志为转移。最后K无法得到克拉姆的接见,只得永不停息地为证明自身的合法身份而不断奋斗。“克拉姆是远不可及的”[6]126K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见他一面,而弗丽达对他爱情的欺骗,两个助手对他隐藏身份的监视也意味着他永远无法摆脱城堡的控制。他存在本身就是荒谬和吊诡的。与约伯相似的是:首先,他们都受权威力量的控制并且无法摆脱。在约伯的世界中,上帝是富有绝对权威和绝对意志的存在,人不可违逆神的意志,只有顺应神的意志,哪怕是考验的灾难才能获得美好的结局。约伯虽然不断质疑神的公义,但还是顺应神意接受苦难,最终赢得称颂。而K的世界里,城堡即权威,城堡伯爵克拉姆虽然以一种不体面的官僚措施统治着村庄中的人们,但是人们不得反抗,反抗与质疑的后果就是像奥尔嘉家一样被全村的人排斥。K也不例外,他从踏入村庄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要服从于城堡的控制,即使对城堡权威性产生质疑也不得不受制于城堡。其次,他们都是富有追寻精神的,即都是在追寻探究着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约伯本是神认可的最虔信之人,但是突然间遭到飞来横祸,不禁对自己以往的做法产生质疑,甚至宁愿自己没有出生。人在面对强大的一神统治下,连存在本身就是由神创造的,探求神做法的合法合理与否本身就是令人质疑的。所以犹太哲人曾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6]150探究自身存在是否合法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极具英雄主义的,虽然悲壮但是勇敢。K的出场是反英雄叙事的,作为无关紧要的土地测量员,他的一生都在为争取人们认可自身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而不断奋斗。他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留在这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6]454但是他身份的荒谬在于他莫名召唤进了受城堡控制的村庄,但又无法获得城堡给予的身份认同,作为一名外来者的尴尬笼罩着他,迫使他不断追寻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这一点来说,K是孤独的,约伯又何尝不孤独。但是即使孤独无助,而一切努力皆是徒劳,但是又不得不在命运的吊诡中乘风破浪,做一个西绪弗斯。正如卡夫卡所说:“目标却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为路者,乃踌躇。”[7]28卡夫卡站在犹太文化的层面上,在历史与现代之巅颤栗着书写着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与孤独迷茫。他的K虽然彷徨迷茫,但步伐却像约伯一样的犹太先贤那样坚定,他的身上倒映着犹太民族不断探索追寻,即使失败也要奋斗的民族精神。这也正是K的魅力所在。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约伯原型的背后是犹太文化的影子,是犹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卡夫卡身为西方犹太人,本身就与犹太文化渊源颇深,他拥有大量的犹太文化典籍,对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作品乃是整个民族的神喻。格里高尔是受难的“约伯”,他的身上折射了犹太民族颠沛流离的磨难史。“感受到自己是犹太人”[8]274的卡夫卡对此感触良深。从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开始,犹太民族便迈上了艰难的生存之路。而卡夫卡的时代正是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身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更深刻地感受到世界的疏离与残忍。约伯质问的是上帝,而卡夫卡创造的格里高尔只能哀怨地质疑这个混乱的世界,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在上帝死后的现代世界,人既是自由的,也是孤独的。人无法虔信信仰,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饥饿艺术家只能以殉道的方式悲凉地死去。法的钳制作用代替了神,失去了敬畏审判也就更加随心所欲。但质疑法的权威比质疑神的代价更大,神尚且有公义,法的公义则在人为。约瑟夫·K与约伯一样质疑公义,但对象不同,后果也就不同,国家机器没有神的仁慈宽厚,冷冰冰的判决只能服务于死亡。但是现代社会虽然无望,但是追寻与奋斗是值得的,约伯的追寻质疑得到了反馈,赢得了圆满,K的追寻就更显艰巨。即使权威近在眼前,却又遥遥无期,即使追寻到了真理与权威,但是权威本身又何尝不是残忍暴戾、漏洞百出。卡夫卡在那样一个时代,感受到了整个时代走向崩塌的真相,他的犹太人身份赋予他的敏感与恐惧,成为他作品的整个基调。而希望与未来也是有的,正如犹太民族坚忍不拔、艰辛万苦的生存。卡夫卡怀着对人类的悲悯,以苦难而敏感的犹太人身份去感知世界,体味现代社会人们的挣扎与痛苦,在历史与时代之巅发出自己的呐喊,这无疑是令人感动的,也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感受卡夫卡的魅力所在。
[1]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宏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 叶延芳.卡夫卡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叶延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14.
[5]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 罗纳德·海曼.卡夫卡传[M].赵乾龙,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8] 曾艳兵.卡夫卡《城堡》研究述评[J].外国语言文学,2005(4):273-278.
Job,a Prototype in Franz Kafka's Works
ZHAO Wenqian
(School of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The prototype theory holds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ry works,and characters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re often based on some early characters.In Kafka's works,the plots of protagonist's suffering are always visible,and the world seems ruthless and tyrannical,which seems similar to Job in The Bible.We can see that Job lives in Kafka's works as the prototype.Gerry Gore,deforming without causes,seems like the suffering Job.The hunger artist who devoted his life to art seems like Job who is a martyr for religion.Joseph K arrested inexplicably seems like Job who is wronged by God.K constantly looking for castle seems like Job who is pursuing justice all his life.As a Jew,Kafka writing contains factor of Jewry's culture and psychology.He speaks his own word during the past and modern times,which is just the Kafka's charming.
The Bible;The Book of Job;Franz Kafka;Job
I106
A
2095-4476(2016)09-0054-04
(责任编辑:刘应竹)
2016-08-24;
2016-09-21
赵雯芊(1993—),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