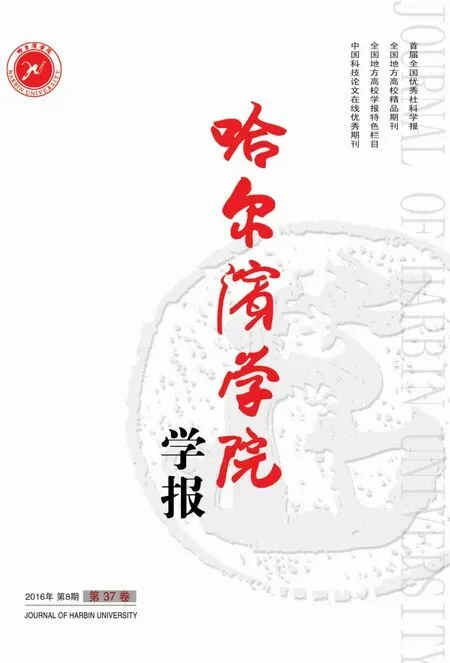卡夫卡:生存哲学与变形美学
2016-03-16张红雪
张红雪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卡夫卡:生存哲学与变形美学
张红雪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摘要]人是肉体与精神的共时性存在。然而,在异化的时代里,这种共存的平衡难以实现。于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变形”作为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巧妙的实践了或肉体或精神的拯救与解放,从而平和了小人物生存上的分裂和灾难;“变形”更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心灵和思想上的微妙波动通过身体和生理上的异常变化凸现出来,在实现以“身体叙事”传递“心理真实”的形态基础上,探索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本实质。
[关键词]卡夫卡;人格困境;“变形”艺术;生存哲学
弗朗茨·卡夫卡的尘世生活决定了他的创作走向,他的创作也完成了他对现实自我的描绘和对理想自我的勾勒。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均是作家以生活的现实世界为基础,依据身心体验、主观感受及人格因素所创造的第二世界,两个世界既紧密关联又相互疏离。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一方面书写了两个世界的分裂带来的小人物身心失衡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充分构想了为实现两个世界的统一小人物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本文将卡夫卡的生存理念与格里高尔的人生实践作一平行对比,试图用身体感知触发人格建构的解析模式来探讨“变形”的艺术功效:即以最客观的形式表现最主观的形象,综合分析艺术灵感与身体特质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变形风格是其现实世界分裂人生的折射与升华。
在世人眼中,卡夫卡是一个成功商人的儿子,且自身条件优秀,受到同事的爱戴和朋友的尊敬。一个法学博士,外表俊秀,举止文雅,性情温和,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对朋友忠实、可靠。这样一个拥有美好品质的人理应乐观开朗,胸襟豁达,充满生活的激情和力量。然而,谁曾想:这却是一个内向敏感、怯懦自卑的人,“他的四周好象镶上了一道玻璃墙。他很文静,而且是微笑着,把世界朝自己打开,而把他自己封闭了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1]这道玻璃墙围蔽了他整整四十一年的人生,让他在自我个体世界与外在公众世界之间,忍受着分裂的煎熬,“变形”作为一剂重要的生存药方,缓解了他肉体和精神的苦痛,寻求着两者统一的路径。
一、“变形”的生存策略
卡夫卡一生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城市,一生未曾离开过父母的庇护,他如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孤独的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为了生存,他从事着保险公司的工作,遁形在群体中,努力完成一个社会人肩负的责任;工作之余,则通过写作来维持心灵的丰富和精神的满足。在《变形记》中,他化身为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忙碌生活的同时,也在孤独的憧憬着理想的未来。卡夫卡将自己融入作品中,展现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的小人物的基本特点,即:身体受到限制,心灵却自由发展;他们在生活的重负之下,却不失浓郁的艺术家气质,与物质需求相比,更注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滋养。因此,在物化的、被金钱所统治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支撑起精神大厦的支柱便成为他们存活下去的关键。
卡夫卡在《变形记》里首先强调和渲染的是身体的受限,即个人在世界的捆绑中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人的生存是在个人与他人结成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即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所以,个体在与他人、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只有同化在群体中才能安全地生存下来。世俗秩序、社会制度的强大,导致弱势的个体只能屈服与顺从集体的需求。这种生存的法则注定了卡夫卡、格里高尔们首先要遵守世俗规范,履行社会职责的命运;然而,长期精神与肉体的压迫,会使人陷入“生存的失望”。卡夫卡这一类人与现实格格不入,就源于他们强烈的失望与失落感。他们无法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充实和满足,因为他们的工作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生存强压给他们的重担。他们对生命有更高的期望,摆脱物质的困境,走向精神的丰盈。何况,卡夫卡的小人物们大多身体羸弱、意志脆弱、身份卑微,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更没有自主选择生活的力量和权利,也就无法实现个体真实的生存意图,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必然会带来主体的失落,因此世人眼中的他们大多是平庸无能的。人们眼中看到的大抵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是被迫戴着“面具”求生存的小人物的卑微形象和日常生活在单调循环中的抽象记忆。人们看不到的是他们心灵的内在波动,是他们平庸肉身与超凡精神的撕扯与斗争。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记录的便是身心交战中的生存策略。
“正是思想使生活转型并产生了新的生活。”[3]卡夫卡运用二元对立思维,将自己的生活分化为彼此独立的两个层面:职业生涯和写作生涯;他的身份也一分为二:现实世界里平庸的受难者及艺术世界中伟大的拯救者,他用艺术的形式给出了实现主体愿望的可能答案。卡夫卡的理想,就是逃脱父母、婚姻、家庭乃至外部世界的牵绊,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封闭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4]以这一理想为出发点,将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完全分离,卡夫卡把格里高尔从俗世中解放出来,放置于他纯粹的主观世界里,考察着实践这种生活的可能性。若异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每日有家人送来饭食,不也就实现了变形的初衷——牺牲自己受苦受难的肉身,卸下沉重的养家的负担,只为维护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在人们的想象中,身心的分离与裂变是逃离现实的某种方式,又是追求理想的策略和对别样人生模式的体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变形的模式注定是一种灾难。作为人形的格里高尔,为家庭忙碌奔波乃至任人宰割;作为虫形的格里高尔,虽尽量不给家人添麻烦,努力探索并适应新生活,一厢情愿地等待与家人一起快乐地生活下去;然而,卡夫卡已从自己的生活中敏锐地意识到,在异化的时代里,爱不再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金钱、财产的基础上,格里高尔一旦变成一只毫无利用价值的甲虫,无法维持家庭经济的时候,依附在金钱基础上的亲情就荡然无存了。父母的冷漠、妹妹的憎恶乃至整个世界的嫌弃,是连甲虫也做不得的,只能悲凉的放弃生命、走向死亡。格里高尔异化的只是身体,他的灵魂还是那样纯真、善良。借由甲虫的外壳,他实践了对内在自我的寻找,并以死亡实现了肉体与灵魂的合一。
卡夫卡明智地认识到,一方面: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小人物不能与现实决裂,想要过正常生活,就必须用理性束缚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冲动,不能让自我个性恣意生长。因此,生活是痛苦不堪的,外在世界的法制规范与内在世界的本真意图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另一方面,独异的个体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能突破社会规范的束缚,内心便充满了不安、愤怒与绝望,灵魂的痛苦、精神的创伤首先体现在身体的苦难上。除非死亡,出路是不存在的,活着就得寻求缓解痛苦的良方。卡夫卡借由文学创作,让自己从群体的机械生活中抽身出来,借助冥想、写作来超越苦难、拯救绝望。《变形记》是一部描绘了在一个异化的时代里,这类“外的弱者,内的英雄”[5]如何调节自己的内在世界,以便与外部的异化世界达成某种平衡的血泪史。卡夫卡下意识里追求的“虫”的生活,最终证明只能是一种空想,人类的集体生活断断不能抛弃。所以,他终其一生品味着肉体与灵魂的分裂之苦。
二、“变形”的艺术手法
卡夫卡的文学成就不仅表现在小说内容上的惊世骇俗,更反映在形式上的奇特怪异。简言之:他的“变形”艺术手法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传统认知上,人们把变形看成“是一种扭曲,扭曲导向丑恶,它在价值上与崇高和神圣是对抗的”。[6]事实上,卡夫卡的“变形”艺术不是对丑恶、怪异、恐怖的现象的集中呈现和审视,不是像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主张的为了追求怪异、制造感觉的混乱而刻意违反自然、违反人类经验。《变形记》恰恰是因为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类经验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成为经典。卡夫卡从具体的形象入手,有机结合客观描述与心理分析,将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与甲虫的习性细节平行并置比较,以一种分裂的双重结构模式,纵深揭示人类生存的真相。
《变形记》的开篇就是一长串的心理活动,陈述着格里高尔的每日行程。累人的职业、日复一日的奔波、老板的压榨、同事的冷漠等,主观思绪和客观事实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尽其所详地交待琐碎事务和细腻感受以期唤起每个平民百姓的同理心,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小人物生存的艰辛和苦难。此外,格里高尔成为甲虫后,卡夫卡又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甲虫的体形特征、动作变化和饮食喜好,建立起两者结构上的平行并置。心理活动的铺陈概括,形体特征的细致描绘完全忠于现实生活和自然规律,铺垫出了变形这一内容上的理所当然。“被禁锢了的身体、被压抑了的愿望”,人与人之间这些惊人的认同性和相似性自然勾起了读者的感同身受;再加上卡夫卡在创作中,使用当事者的叙述视角,让事态的发展随着进程有条不紊的延续而不加入任何主观的陈述和权威导向。卡夫卡冷静的用身体来感觉思想和推论,令人信服的将他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形象。现代人被抛弃或主动选择放弃外在世界的生活后会是怎样的命运?甲虫的挣扎和最终归宿给出了最生动的答案。卡夫卡的作品本身是情感的产物,他的“变形”不是胜在作品的技巧和结构,而是心灵感受到的形式与内容的整体合一感。在某种具体的情境氛围中,从身体的真实反应入手,读者能轻易领悟到身体与情感和思想的关系。艺术与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艺术家深邃的思想只有渗透进某种具体可感的东西里去,这种情感和思想才能传达给读者并留下具体的印象。正是这种具体可感的实在性,在无意识中将读者的认知情感升华到了审美情感的高度,丑恶、恐怖就如同崇高、神圣一样可以坦然理解和接受了。换句话说,卡夫卡的“变形”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动态发展,人们完全可以参照自身的生理和心态,对生命中的突发事件、重大变故做出各种可能的应对和合情理的感悟。在那样生动具体、循序渐进的情境之下,任何奇特恐怖的“变形”也变的顺理成章、真实可信。毕竟,艺术作品是来源于纷繁杂乱的生活细节和事实,并传达高于生活的情感和思想。
卡夫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感受力,他能洞穿日常生活平静外表下深藏的丑恶实质,但如何引导普罗大众从习以为常中发现生存的真相就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智慧。卡夫卡“变形”技艺的第二个特征就表现在适当的客观对应物的选择上。他把深邃的思想、独特的心境乃至特定情感与情绪客观对应在具体的人人都有的,但又极端个人化的“身体”之上。描绘“身体”的外在形态变化是刺激读者感官的最直接方式。卡夫卡瘦削、羸弱、多病的身体让他从小对身体的关注和感受就格外敏锐和强烈。因此,他也能深切体会格里高尔处于高压下的、为拼命赚钱而沦为机器的身体的感受。心灵极力想从被控制的身体中挣脱出来,最后只能经由身体的变化,由机器般“利他”的身体蜕变为独立自主的“唯我”的身体。所以,这些卑弱、病痛、畸形的身体选用“变形”这一充满震撼、惊悚效果的艺术手法是必然趋势。甲虫的身体取代了人的身体,从理论上看,是用艺术的形式把内在的心理、主观的现实外放出来的唯一方法。这个客观对应物越直观立体,就越利于抽象的情绪、复杂的理念和稍纵即逝的瞬间感受的表达。从实践上看,人和甲虫一样任人践踏,两类身体处于同一种境地:无法自由支配,不能独立自主。人的身体只是一种社会符号,冰冷的机械生活消耗了鲜活的生命气息;而甲虫的身体却是人的受侮辱受损害的身体的一种本真体现。卡夫卡虽未身化为甲虫,但过着虫的生活,沉浸于写作就是为了弥补身体的伤痛,维护精神的独立;且他采用的这一“变形”手法,将情绪、心理、性格这些复杂难言的变化处理为直观化的身体变形,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身体叙事”传递“心理真实”的美学思想。他把生活的方方面面聚焦于身体这一点,并对身体变化与身体感受进行了极度的夸张和放大,使身体受限之下生命质量的本质暴露无遗。
卡夫卡的“变形”,从美学角度来看,是从他自身的生存理念出发,巧妙结合他的生活现状,把身体作为艺术表现的媒介,让心灵中难以言传、难以分享的感受和变化通过身体的直观展现传达出来。改变身体原本的形态和风貌,与自然的标准和美感形成一定的差距和断裂,成为具有“卡夫卡式”独特表现力和审美力的风格。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扭曲反常的表现方式,新奇怪诞的变形形象不仅是作品的外在形式,也成了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对现代社会中的普罗大众,尤其对像卡夫卡这一类具有忧患气质的人来说,身体与灵魂的合二为一是根本不可能企盼乃至实现的,所以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变形记以不同方式上演了。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凸显人物单纯的符号性和角色性——养家的工具、赚钱的机器;在艺术世界中,卡夫卡则聚焦人物迫切的精神需求与心灵渴望。卡夫卡的“变形”技巧中,身体思考触发艺术想象,人体沦为虫身不是一种感性的随心所欲的异化,而是有一番理性的富于逻辑的推导过程,我们一步步跟随着这一演变的过程,并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推导的结果。这一结果在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自在、不舒服的同时,又会是当头一棒,唤醒我们麻木、昏沉的心灵,于是我们会停下忙碌的步伐,反思一下我们在自认理所当然的习俗、规定、惯例和职责、义务的枷锁中的生存的真相。卡夫卡的作品,究其实质可称之“由隐喻伪装起来的精神自传”。[4]细读《变形记》,就会发现卡夫卡就是格里高尔,格里高尔的一生就是卡夫卡的一生;或者说,是卡夫卡“这一类人”的一生写照。“这一类人”不同于生活中的大多数——他们或是走狗似的主流社会的帮凶,或是奴隶般的蒙昧民众;卡夫卡的“这一类人”主要是小知识分子,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无法把握自身命运,却因思想情感丰富、忧患意识强烈而孤独寂寞、郁郁寡欢。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与外部世界斗争的同时,始终执著于对独特自我的坚持与守护。《变形记》便是对“这一类人”的身体困境和精神困惑的最佳诠释。格里高尔的变形之举,是卡夫卡“这一类人”对自由之我和生存理想之境的尝试,虽在无意之中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家庭的伪善面纱,却也惊醒了麻木愚钝的世人开始对个体生存质量的关注与思考。卡夫卡“这一类人”的生成也提醒世人:“童年的缺失是一粒埋藏在作家灵魂深处的种子,它带给作家创作的动力,带给作家无穷无尽的激情与幻想”,[7]也带给他们向死而生的最悲壮的生存思维和创作理念。
[参考文献]
[1]〔德〕瓦根巴赫.周建明.卡夫卡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鲁道夫·奥伊肯.张源,贾安伦.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4]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叶廷芳.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6]阎真.变形:人性扭曲的艺术表达[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7]孙梓偎.论童年经验对创作个性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10).
责任编辑:魏乐娇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8—0077—04
[收稿日期]2015-11-1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SK2013B061。
[作者简介]张红雪(1978-),女,安徽芜湖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521.0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8.019
Kafka:Life Philosophy and Metamorphosis Aesthetics
ZHANG Hong-xue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Man is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spirit. At the time of alienation,the balance of this alienation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In Kafka’s world,“metamorphos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y for survival which liberates both body and spirit so as to end up the split and destruction of small potatoes. “Metamorphosis”,as an important artistic technique of expression,presents the subtle change of body and spirit through biological change. Based on the idea of delivering “mind truth” with “body narration”,the nature of modern man’s living dilemma is explored.
Key words:Kafka;the dilemma of personality;the art of “metamorphosis”;the philosophy of surv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