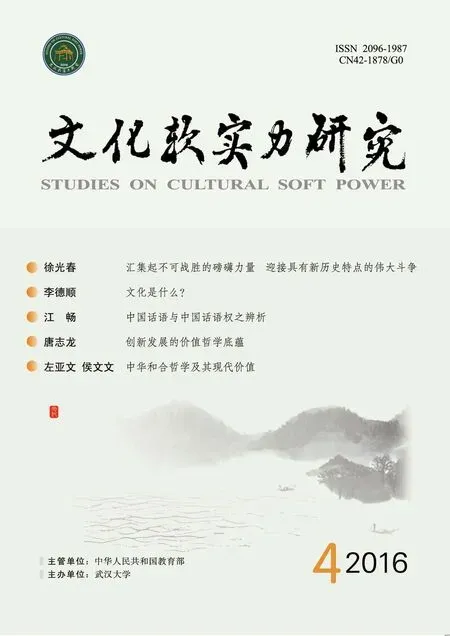中华和合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2016-03-16左亚文侯文文
左亚文 侯文文
中华和合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左亚文 侯文文
中华和合哲学是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哲学形态,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炎黄蚩三祖的“合符文化”,后经千年的发展终于在周代完成了它的哲学构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这种强调和合的辩证思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能与当时西方朴素辩证法相媲美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矛盾辩证思维相比,和合辩证思维的致思重点在于对立面的同一性、统一性、和调性和互补性,其所强调的“和谐性的原则”。随着和平和发展时代的到来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哲学形态凸显出新的时代价值,因而被推到理论的前台。
和合 阴阳 和合哲学 现代价值
中华和合哲学是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灵魂,亦是其实质和核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华和合哲学随着“和合文化”热潮的兴起开始被提了出来。什么是中华和合哲学?它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其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怎样?与西方哲学相比它具有什么样的智慧特色?其现代价值如何?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希冀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
一、中华和合哲学的提出和建构
就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目来说,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和合哲学。这种哲学独具东方智慧特色,与西方哲学既相契合,又大为不同。
这种哲学散见于全部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之中,而且处在一个朴素的状态。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建构,并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
当然,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工作是要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照,在这种比照中凸显中国哲学的“和合”特色,并在概念上加以定位。
如果从中华和合哲学的正式命名来看的话,它的明确提出并得到哲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
随着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至90年代中后期,终于形成一股“和合文化”的热潮。我们很难说,谁最先提出“和合文化”或“和谐观念”、“和合思想”的概念,并最早进行具体研究。
据资料所及,如果单纯从时间上看的话,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可以说是最早进行了这方面的思考。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钱穆先生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有意识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他认为,“融合协调、和凝为一”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而且反复强调中国人喜合,西方人喜分,这是中西文化一个不同的分野。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而著名国际儒学学者、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则在1977年就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和谐本体论”、“和谐辩证法”的概念,并发表了《构建和谐辩证法》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构想。
但是,无论是钱穆先生还是成中英先生,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本质的体认,因其超前性并没有被当时的学界和社会所广泛认同,特别是当时的历史环境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的意义凸显出来,因而他们的思考和研究纯属个人兴趣,不可能形成一种切合时代需要的社会思潮。然而,这种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为20世纪80—90年代和合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后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人们祈求和平、和谐,期盼发展、进步的心理日益强烈。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土壤里,逐渐滋长出“和合文化”的精神之花。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蕴含着丰厚的和合思想资源,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合文化传统凸显出新的时代意义。当时,在理论界和文化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民众,几乎不约而同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利用中华和合传统资源来论证倡导和谐与维护和谐的重要性,直至最终汇聚成一种“和合文化”的思潮。
在学术界,引潮流之先的要算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先生。张先生从1987年起,就从其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出发,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潜心竭思于“和合学”的研究,终于有所大成。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向研究生和博士生讲授“和合学”的课程,并在海内外发表了十数篇关于和合学的文章和多场演说,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完成了上下两大卷、78万字的《和合学概论》的创建。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关于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并苦心孤诣地建构了一个包含“地”、“人”、“天”三界以及理论公设和形上、道德、人文、工具、形下、艺术、社会、目标八维等新学科分类在内的宏大的和合学理论体系。
张先生认为,和合学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既与西方的神创思维(实质上是一元化的思维)大异其趣,也与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提出的应对西方挑战的种种方案和主张(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说;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解释、综合创新论;全盘西化、儒学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说,等等)有所不同”。②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对于张立文先生的这些观点以及他所构建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尽管学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所提出的和合学构想特别是其大力倡导开掘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理念,对于后来和合文化热潮的兴起,以至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战略思想的实施,都产生了不容否定的积极影响。
当时,国内理论界还有一些学者与张立文先生一样,也在思考和探索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及其现代价值问题。例如,杨建华教授于1999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早期和合文化》。
值得一提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王煜教授,他在1967年就出版了专著《儒家中和观》,对儒家中和观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释。
除此之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明华教授、辽宁省委党校的田广清教授也较早探讨了中华和谐思想。1992年初,在广东省召开的“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讨会”上,李明华教授作了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学术报告,引起学界的注意。田广清教授于1998年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
当时,思考和探索中华和合文化与和谐思想的人远不止上述几位学者,还有一些人士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讨过这个问题。在这里,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机缘和社会心理基础上,以及一些充当了先驱者的人士的感召下,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探讨和合文化的热潮。
这股和合文化热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底,由人民日报理论部、光明日报评论部、《科技智囊》杂志社、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情调查工作委员会等新闻单位和学术机构发起的“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开始启动。该项工程的宗旨是,研究、阐发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和国际和平事业。程思远、楚庄、范敬宣、邢贲思、张岱年等担任该工程的组织领导和学术指导工作。程思远不顾年迈任组委会主任,邢贲思任执委会主任。
这个弘扬工程启动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发表了不少文章,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其带动之下,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探讨和合文化的热潮。
根据知网统计,自1988年至2004年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前,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题中有“和合文化”的文章计124篇,发表题中有“和谐思想”的文章35篇,发表题中有“和合思想”的文章46篇,至于在一些诸如中国传统文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他的理论文章中,从另外不同的角度探讨和宣扬中华和合文化、和谐思想的文章则更多。
“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以及和合文化的讨论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重视。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屡次谈到“和为贵”、“和衷共济”等。李瑞环同志则多次专门论述了“和合”与“和合文化”的问题,给予和合文化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曾亲自调看有关中华和合文化的资料,对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作予以肯定。2000年11月7日,李瑞环同志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强调“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人和、祥和、和睦、和谐、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内和外顺等词语经常使用,随处可见”。这一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和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对弘扬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亦予以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对如何贯彻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在该决定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并列,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后,这个决定又首次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能“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十六届六中全会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针对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诸如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非此即彼的斗争性思维,和谐文化大力宣传和倡导和谐理念、和谐精神与和谐思维,“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提出“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①刘云山:《和谐文化是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4日。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之中加以传播和贯彻,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的新觉醒以及思维方式的一次大转变。
笔者对中西哲学关系的这种认识,特别是从辩证思维多样性的高度来反思这种关系,包括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及其地位,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笔者对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程度首先在拙著《智慧之恋——哲学启示录》一书中有所表达:
几乎在与古希腊哲学诞生的同时,在东方中国,产生了重和谐、均衡即强调“同一性”的阴阳辩证法。
阴阳辩证法所始终强调的是对立两个方面的“合”,而不是“分”。如《周易》在论述天道、地道、人道时就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在这里,作为天道的阴阳、作为地道的柔刚和作为人道的仁义,不是一种对立的斗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济、相合的关系。
……
西方的矛盾辩证法虽然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改造和发展,但是,它重视对立、冲突的“斗争性”特征并没有改变。它始终强调,矛盾两个方面的斗争性、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同一性、平衡性是相对的,甚至认为,同一性所代表的是事物的保守方面,斗争性所代表的是事物的革命方面,因此,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源泉都取决于矛盾的这种斗争性。
因此,在我国哲学界曾发生的关于“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争论,借助的虽然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但反映的却是中西两种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前者所代表的是中国重和谐、统一的阴阳辩证法,后者所代表的是西方重冲突、斗争的矛盾辩证法。正如今天西方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都是研究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方法一样,阴阳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也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征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它们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交相辉映。无论是中国的阴阳辩证法,还是西方的矛盾辩证法,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世界辩证发展的本质规律,因而都是人类哲学智慧宝库中熠熠生辉的辩证法明珠。②左亚文、潘伯祥:《智慧之恋——哲学启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9页。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要大段引用在1999年初出版的书中的段落,是为了说明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而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理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笔者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以自身为个案,来记录那个时代的学人们是如何通过艰难的求索而冲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一点一滴地开辟出一块哲学的自由天地的。
在这些思考和研究中,笔者对和谐辩证思维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关于“和谐”与“矛盾”的异同问题,关于和谐思维、矛盾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华和谐思维中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和谐与多元系统和谐及其关系问题,笔者都作了一些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方面,笔者愈益感到和谐辩证思维是如此贴近中国的民众和现实生活,特别是随着全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宗教冲突、恐怖威胁、信仰危机、精神疾病等问题的恶化,和谐理念与和谐思维的世界性意义更加突显,已逐渐被全世界的人民所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和谐辩证思维作为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特色的相对独立的辩证法形态,在其原生的形态上,毕竟处于古代朴素的水平,是不能现成地被我们所利用的,必须对之进行清理、改造,给予现代的重释,使之升华到科学的形态,才能被我们运用,而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和繁重的历史任务,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
二、中华和合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和合思想最早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炎黄蚩三祖的“合符文化”。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之后,又在阪泉之野战胜了炎帝。两战之后,黄帝继续南征北战,“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①《史记·五帝本纪》。,直至统一天下。在这种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黄帝将所有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召集于涿鹿县的釜山,举行了政治大会盟,即司马迁所说的黄帝“合符釜山”。至此,黄帝与诸侯在釜山合符契,“诸侯咸尊轩辕为太子”②《史记·五帝本纪》。,天下共认黄帝为共主,一统天下。
在当时“方国林立”、征伐无常的部族时代,黄帝与众诸侯釜山合符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将从原始野蛮中脱颖而出。与此相伴的是,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征的文化思想即和合思想从这种“合符”中应运而生。因此,当我们今天探讨和谐文化的起源时,不应该忘记在釜山这个地方寻求其思想之源和文化之根。
和合文化源远流长。釜山合符后,这种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终于在周代完成了它的哲学构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
学界一般认为,真正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明确提出和合思想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史伯论和同的一段千古名言: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匿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究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兆民,取经入以食万官,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
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将无弊,得乎?”①《国语·郑语》。
笔者把这段话简单地解释一下:郑桓公问史伯:周朝必然要衰败吗?史伯说:这种衰败是必然的。《尚书·泰誓》说:人民的愿望,上天是要服从的。现在的君王(指周幽王)抛弃高明有德之士而喜好进谗弄诈之人,厌恶贤能正直之士而亲近愚钝保守之人,实行“去和而取同”的政策。只有把不同的要素有机地和合起来,才能创生新的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东西机械相加,那么事物的发展就停顿下来了。以其他的东西来调理其他的东西,才能使事物得到丰盛成长并使万物尽归己有。假若以相同的东西来调济相同的东西,那么这个事物的发展就完结了。所以,先王把土与金、木、水、火等不同元素加以配合,而生成万物。因此,调和五味以做出爽口的饮食,强健四肢以增强抵御力,调节六律以创作出悦耳的音乐,端正七窍以使之为心所役使,调正身体的八个部分以形成健全之人,调理人的九脏以树立纯正之德,调合社会的十个等级以训导百官。于是,产生千种品类,具有万种方略,统计亿种事物,裁定兆种财物,获取经种收入,达到至极之境。所以,君王拥有九州之土地使万民得以生养,获得过亿的收入以供养百官,用忠信来教化他们,使他们和乐如同一家。若如此,那就是和谐的极致了。于是乎,先王在异姓诸侯中聘娶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物,选择敢于直谏的人为官,这都是讲求众多不同的事物的结合,务求达到和谐的效果。一种声音是没有什么可听的,一种色彩是没有什么文采的,一种味道是烹制不出什么美食的,一类事物是无法比较其好坏的。现在的君王抛弃了这种和谐之道,而实行专同,这是上天夺去了他的圣明,要想不衰亡,能做到吗?
这段话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批评当时的周朝君主抛弃高明有德之士,而近进谗弄诈、阿谀逢迎的卑鄙小人,厌恶贤能之士,而喜好愚钝僵化之人,实行去和而取同的政策。第二层,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把“和”与“同”相对立,并从治国、理财、选才、用人、音乐、体育、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来论证“务和去同”思想的普遍性。
“和”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异质要素的结合;“同”则是单一、均同、专一,是同质要素的机械相加。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字面上讲,就是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创生新的事物,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就会使事物的发展停顿下来。从哲学上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包含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其要点有三:
其一,差异的存在是和谐形成的前提条件。没有差异,没有对立,也就没有和谐。和谐是在差异和对立中生成的,也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发展的。“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相同的东西加在相同的东西身上,永远是相同的东西,而且还会退化。正如史伯所说,声一无听,即一个调子是不能成为音乐的,那只能成为难听的噪音;物一无文,即一种物质元素是难以形成有序的文理的;味一无果,即一种味道是难以烹调出美味佳肴的;物一不讲,这里的“讲”,有“比较”之意,就是说,一种物质是无法进行考核和比较其优劣好坏的。从哲学上讲,就是孤阴寡阳不能形成和合体,也就是说,单纯的阴和单纯的阳都不能形成和合体。
其二,只有异质要素的有序和有机的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和谐。并不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结合起来而形成和合体,一堆垃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能形成和合体吗?黑格尔说,骆驼和钢笔,恩格斯说,鞋刷子和哺乳动物,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像这些毫无联系的东西却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本身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东西,才有可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即使这些有内在联系的东西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和谐体。例如,五味只有按照一定的美食规律加以“和调”,才能形成爽口的美味;六律只有按照音乐的规律加以“和调”,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
其三,由“和”创生新的事物。当异质要素以一定方式有机结合后,就会凸现出新的性质。这是“和实生物”的必然结果。例如,当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事物——水分子。当硫磺、硝和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事物——火药。当男女由相爱而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家庭从此产生了。家庭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简单相加,当一加一之后,它不是等于二,而是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作为他们爱情结晶的子女出生了,一加一变成了三或四。所以说,“和”创造新的事物。
通过对上述这段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既包含了阴阳和合的辩证法的思想,也包含了朴素的系统论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史伯是第一个明确地把“和”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提出来的,也是第一个明确主张实行“务和去同”的政策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
“和”,《说文解字》解为:“和,相应也。”即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谐一致。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字作“龢”,从龠,禾声。《说文》释为:“龢,调也。”“龢”属于形声兼会意字。“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①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龢”字的左部是古代竹管乐器的象形写法,它本身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声音之和”的发生是不同音素按照音乐规律相互配合、协调的结果。“和五音以悦耳。”五音者,宫商角徵羽也。要创作一首优美的乐曲,不仅需要运用“五音”这些不同的音阶作为创作的元素,而且根据音乐的节奏、韵律、情感、意境的需要,将音素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调和配合,才能形成悦耳之声。
在古代金文中,“龢”通“盉”。“盉”的写法是禾在上,皿在下。《说文》:“盉,调味也。”盉者,本为调和水酒之器具,意为饮食之调和。古人对饮食之和多有论列。《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梅盐。”对于“和羹”,《郑笺》释:“和羹者,五味调,腥热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在郑玄看来,和羹,不仅能使五味和调,食之悦口,而且能使人性情平和,利于养心。
与“和”有关的是“合”,“合”也是表达中国传统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解为:“合,合口也。”即口的上下唇和上下齿的闭合,引申为符合、相合、吻合之意。“和”与“合”在中国最早的哲学文本中其意是相同的。孔颖达疏为:“和,犹合也。”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和”与“合”二字合并,构成“和合”范畴,这是语言表达愈来愈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史伯之后,这种强调和合的辩证思维不绝如缕,特别是在儒家和道家那里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能与当时西方朴素辩证法相媲美的哲学思想。
首先,齐国的政治家晏婴从如何和谐君臣关系入手,进一步论证了和同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和谐政治的主张。史载,齐景公时,有个叫梁丘据的人,是专门讨好主上喜欢的佞臣,景公对他十分满意。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与我相和的,唯有梁丘据啊!”晏婴直言说:“梁丘据只能算是与您相同一,不能算是相和谐。”景公就问和与同的分别,于是晏婴从君臣关系入手,讲了一大通关于“和谐”的哲理。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主认为可行的,其中可能包含不可行之处,当臣子的就有责任向君主指出来,以便使君主所做的决策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其中可能包含可行之处,当臣子的也有责任向君主指出来,以便真正去掉那些不合理的东西。而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他也说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他也说不可行,只知一味附和。这就如同烹调食物时只知道往水里再加水,这样的食物谁又能吃呢?也如同弹奏乐器时只知道发出一个音,这样的音乐谁又能听呢?相同的东西在一起不利于事物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啊!
这里,晏婴不仅提出了如何和谐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关系的方法,而且进一步把它扩展到和谐政治的层面,再进一步升华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其次,儒家创始人孔子一生以倡导“中和”和“中庸”思想为己任,把史伯和晏婴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政治以及“和合”哲学具体化为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出了一种如何达到和谐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和”和“中庸”的最深刻和最有创意之处,也是孔子对“和合”思想的最卓越的贡献。
“中”、“中和”与“中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与“和”、“和合”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如果说和合思想主要阐述的是世界观理论,那么,“中”、“中和”与“中庸”所主要阐述的就是如何使我们的言行符合“道”和“理”的方法论问题。
“中”最初的含义是指旗杆之正和中矢之正,具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所谓“中道”、“中庸”,也就是如何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的准则的方法和途径。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②《二程遗书》。在社会实践中,孔子深切体悟到,为什么有些人天下国家能治理好,官爵俸禄可以辞去不受,甚至可以上刀山入火海,却不能坚守“中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执两用中”。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③《中庸》第四章。在认识上不懂得“道”的适用范围和时空限度,在行动上就会出现“过”与“不及”左右摇摆的错误。在孔子看来,这里的关键是,要懂得道的度量界线,才能“执其两端而用中”,否则,“执中”、“用中”就是一句空话。
问题是,如何认识道的这种“度量”界线?孔子提出了“扣其两端而竭焉”的研讨方法。他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④《论语·子罕第九》。
所谓“扣其两端”,就是指将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反复推敲、比较,以便把握其本质,认清其两个极端的“度量”界线在哪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执两用中”。例如,孔子曾谈到“勇敢”、“直率”等就有一个“度量”界线的问题。如果在一端“过”了勇敢的度量线,就成了胡乱蛮干的鲁莽;如果在另一端“不及”勇敢的度量线,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弱。直率也是这样,如果太“过”直率,就成为尖刻;如果“不及”直率,就成为油滑,如此等等。⑤孔子的原话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见《论语·泰伯第八》。孔子发现任何一个事物的“道”都是如此,其“两端”都有一个超越了度量线而向反面转化的问题。今天我们无法描绘当年孔子发现这一伟大真理时的欣喜之情,但是,从孔子的大量言谈中却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建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一再强调“执两用中”并将其概括为“中庸之道”的原因。
除此之外,孔子还把“和合”思想具体化为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例如,在道德和法制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把德与刑、猛与宽结合起来,使之达到和谐。他说:“政宽则民慢,民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①《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就是说,如果为政过宽,那么人民就会放纵自己,怠慢法律;如果为政过猛,则人民就会受到残害。只有将二者协调起来,互为补充,才能达到“政是以和”的效果。
在“礼制”的建设上,孔子坚持“和为贵”的原则。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②《论语·学而》。在这里,孔子不仅把“和为贵”作为礼仪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而且把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境界,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然而,孔子并不要求无原则之和,在社会生活中,“和”应“以礼节之”,明知不对,“知和而和”,不惜牺牲礼的原则,那是不行的。可见,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和为贵”与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因与革、质与文、速与缓、义与利等一系列矛盾关系上,孔子都主张将两个方面协调、整合,防止执其一端的极端化行为。过去,我们说,孔子反对改革,害怕变革,被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吓破了胆,这种评价是不公道的。其实,孔子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反对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过激行为。孔子与子张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继周者,虽十世,可知也。”可见,孔子对于时代的变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并不主张因循旧制,而是认为应对其有所“损益”,即把变革与继承、继承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把这种原则上升为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身心修养上,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一种“仁人君子”的形象。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仁人君子,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一举手、一投足,都应合乎礼仪,符合中道,而且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失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当然,孔子更强调,君子重在培养仁爱之心,不为富贵所累、名利所困、淫欲所害,并且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君子形象,虽然具有理想的性质,但不像尼采心目中的“超人”可望而不可及,而是经过努力可以日益趋近的。
孔子其时及其后,不仅儒家及其后继者们,而且道家、墨家等也都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和”、“和合”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例如,道家创始人老子在所著《老子》五千言中,不仅贯穿着“和合”的思想,而且把和合思想与他的阴阳之道相结合,将其进一步发展、升华为一种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老子把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和总规律,但道不是僵死不动的绝对,在其内部包含着阴阳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阴阳矛盾的和合作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老子》第四十二章。
墨子不仅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君民之间要相和合,而且国与国之间也要相和合,在和合中达到“交相利,兼相爱”,在“交相利、兼相爱”中维护和发展和合。可以说,墨子最早明确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和合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抽象思辨领域内,而是广泛渗透在政治、文艺、美学、医学、军事乃至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巨大的穿透力和实用性。
以音乐、美学为例。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视礼乐的国家,不仅注重用音乐来培养人的德性、情操,使审美主体的心灵和审美对象达到和谐统一,而且主张“乐从和,乐从平”,倡导“中和为美”的美学原则。孔子在评价《诗经》时,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以及“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评价文学、音乐及其他审美对象的。所谓“中和为美”、“和谐为美”,就是把“中和”或“和谐”作为美的本质来看待。一个对象,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在的诸要素处在有序的、有机的高度和合状态时,不仅表明它符合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且表现为一种真善美的统一,给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例如,一个人,当其本我、自我和超我处在高度和谐的状态时,他就表现为人格精神之美。一幅山水画,当它的冷暖色调、整体布局,特别是其表现意境的元素构成能高度协调时,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如钱穆先生在分析中国画时所说的:“中国的画境,有自然必有生命,有生命必有自然。如杨柳燕子,如野村渔艇,如芦雁,如塘鸭,要以自然为境,以生命为主。”①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联经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7页。这里的自然和生命就组合成为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图,因而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即便是一株垂柳,一只飞燕,一艘渔船,也透露出自然中盎然的生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中国传统医学是贯彻和合文化一个活的典型。按照“阴阳和合”的理论,中医认为,人生病,是因为阴阳失调——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所致。辩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就是“阴病阳治,阳病阴治,补弊救偏,调理阴阳”,以达到恢复肌体健康之目的。中医这种从整体和谐原则出发医治疾病的机理,是别出一格的。西医治病的原则和此不同,它遵循的是微观分析的方法,实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则,此处有病就在此处治疗,彼处有病就在彼处治疗。应该肯定,西医由于采用了现代的检查和诊治手段,它的治疗效果是明显的。西医的先进治疗手段都应吸收到中医当中来,而实际上,现在的中医也是这样做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医即使不借鉴西医,也会依靠自身的力量,逐渐地发明和创造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因此,中医不能排斥西医。反过来,西医也不能排斥中医。因为中医有它的独到之处,它治病的思路与西医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医是此处有病在此处治疗、彼处有病在彼处治疗的话,那么,中医则是“此处有病在彼处治疗,彼处有病在此处治疗”,肝上有病在肺上治疗,肺上有病在胆上治疗,尽管这种医治方法还停留在抽象哲理的层面,缺乏科学的实证,这是中医需要加以改革和发展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同于西医的独特的治疗思路和原则,却是西医所不能替代的,而且长期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中医没有被西医吃掉也不可能被吃掉的根本原因。
中华的和合文化还广泛地渗透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中国人根据阴阳二气的变化来决定农时,正月,正是一阳复始、大地回春的季节,农民们开始准备春耕和播种了;中国人还根据阴阳的特性来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食疗是中国人饮食的一大特色,是中国人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有效方法;中国人也根据阴阳的向背来决定住宅的位置,靠山向阳、坐北朝南,是人们对住宅位置的首选;中国人甚至根据阴阳和合的观念来修养身心,身心相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进退有据、能屈能伸,能张能合,等等,都是中国人所赞赏的品性。可以说,和合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专门学习,甚至也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只要你进入这一“文化场”或“文化圈”中,你就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熏陶,于是你的心理、思维、精神、个性乃至你自然的身体,都融入到这种和合体之中去了。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讲的,中国人就生活在阴阳五行的和合文化之中,吃阴阳五行,喝阴阳五行,言阴阳五行,行阴阳五行,乃至生死祸福都在阴阳五行之中。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辨像这样能够普及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和逻辑思维方式,能够这样长久地流传下来并被广大的社会成员所接受,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罕见的。
三、中华和合哲学的独特智慧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文化精神与精髓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因此,和合文化在哲学上表现并升华为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
大家知道,西方的辩证法,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马克思,所强调和论证的是“矛盾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矛盾体,即“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这两个方面既对立、斗争,又统一、同一,由此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根据这种理论,它自然得出了“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一结论。尽管这种辩证法也讲矛盾对立面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但是,它强调的侧重点,或者说它的致思取向却是矛盾的斗争性、对立性、冲突性,它突出的是“否定性的原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自古希腊到自己为止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西方人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为“冲突理论”。
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既相契合,又大不相同。和西方辩证法一样,它也讲矛盾的对立统一,不过它把矛盾叫作“阴阳”。阴阳首先是指日月、男女,后来抽象为一种基本的哲学范畴,用以表征宇宙间两种基本力量、特性、要素、方面、环节的关系。一般来说,阳代表刚健的、主动的、积极的、进取的方面,阴代表柔顺的、被动的、消极的、退守的方面,它们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构成一个阴阳和合体。中国传统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阴阳和合体,所谓“无物不阴阳”、“凡物必有合”、“万物莫不有对”、“物生有两”、“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等等,都是对这一哲学原理的高度概括。
但是,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和西方辩证法又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方辩证法的理论致思是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性、对立性和冲突性,其突出的是“否定性原则”的话,那么,中华和合辩证法的理论致思则是阴阳对立面的和合性、和谐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其突出的是“和合性原则”。如果说西方辩证法得出了“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结论,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法则得出了“和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结论。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体现出来的独具东方特色的哲学智慧,由于这种智慧特色,它理应在人类辩证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具东方智慧的特色是予以否定的。我们习惯于用西方哲学为模本来解释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强行地套在西方哲学所预制的一个模子里,用唯物、唯心这个“对子”来裁剪中国哲学。其结果是把中国哲学搞得面目全非,将中国哲学消解于无物。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实际上,辩证法的形态是多样的。西方有西方的辩证法,中国有中国的辩证法。东西方各具其自己的智慧特色。它们的存在是“和而不同”的,决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替代一个的关系。这就是东西方哲学的一种本然关系。我们提出“和合哲学”、“和合辩证法”,其意就是还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为中国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上争取合法的地位。
四、中华和合哲学的时代价值
和合文化的基本思想虽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它仍然显示出迷人的魅力,不失其真理的光辉,特别是在时代主题发生变换、我国进入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之后,这种文化愈益凸现出时代的价值。当然,我们对于传统的和合文化不会原样照搬,而是要对其进行清洗、批判、改造,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给予重新诠释,赋予其时代的新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的和谐文化。
具体地说,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至少具有如下几点:
(一)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文化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合文化包括和合哲学的引领与支撑,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又必将大大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不可分割。而要建设和谐文化,就需要发掘和弘扬中华和合传统。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和谐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既是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继承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深厚的和合文化传统,是不可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的和谐文化的。
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要达此目的,决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离开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来谈论民族文化的建设,无异于南辕北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逻辑悖论。自鸦片战争之后,在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的曲折探索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复兴必须建立在自己文化的基地上,而且必须认清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精华,把它加以发扬光大,将其推向世界。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精华就是和合文化,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创造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因此,在继承和弘扬我国和合文化的传统的基础上,建设和谐文化,必将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必将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为深化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开辟道路
继承和弘扬和合传统,也为深化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开辟了新的道路。长期以来,我们宣扬革命文化和“斗争哲学”,这种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但是,当我国进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如果我们继续把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革命文化上,如果我们还继续片面地宣扬“斗争哲学”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会落后乃至阻碍时代的发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要一次又一次地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呢?原因是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特别是受过去“左”的二值对立的“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一事当前,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问姓“资”姓“社”,把阶级性无限泛化,把对立面的斗争性推向极端。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人在考虑问题和判断事物时,不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不是从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出发,而是从抽象的阶级性、斗争性出发。这些僵化和保守的思想,其深层的哲学根源就是绝对化的对立思维和“斗争哲学”,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危险过去是、现在是、以后必定还是来自这种“左”的教条思维。因此,建设新型的和谐文化,树立和谐思维,对于我们消除“斗争哲学”的遗毒,进一步肃清教条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将是大有裨益的。
(三)为拓展辩证视野和树立真正科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条件
过去我们认为,辩证法只有一种形态,这就是西方的形态,结果,这样一种辩证法就变质为一种僵化的体系,这种教条的态度是必须予以克服的。
对辩证法我们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如果我们以辩证的态度来观照辩证法自身的话,那么,辩证法形态决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样的和多形态的。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人们几乎可以从无限多样的维度来观照这个世界,揭示它的本质的规律。这样就必然会产生辩证法的多种形态或形式。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就从不同于西方矛盾辩证法的角度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新的本质规律,是西方的矛盾辩证法所替代不了的。所以,继承和合传统,确立和合辩证思维,对于我们拓展辩证法的视野,把西方和东方的辩证法经过整合在更高的层次上“和合”起来,从而确立真正科学的辩证思维,是大有好处的。
(四)为确立和合系统思维和制定正确的国际外交战略提供启迪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由于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我们这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强化。当然,这个世界还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整个世界并不太平,但是,和平和发展毕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却是一种客观必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国际战略思维也应从过去的“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转到“多极互动”的多向立体思维,这样,和合系统思维就成为我们在制定外交方针时一种可供选择的卓越的战略思维。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 ony and Its M odern Value
Zuo Yawen(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Hou Wenwen(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is a philosophical form with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wisdom,and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oken matching culture of Yan,Huang emperor and Chiyou three ancestors five thousand years ago.Underwent the thousands of years'development,it finally completed its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in the Zhou Dynasty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in which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this dialectical thinking,which laid stress on harmony had been greatly developed,and then formed a philosophic thinking that can be compared favorably with the western simple dialectics at that time.The thinking focus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harmony,compared to western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contradiction,lies in the opposite sides'identity,unity,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this philosophical form highlights the new times value,and is pushed to the front desk of the theory.
Harmony;Yin and Yang;Philosophy of Harmony;Modern Value
10.19468/j.cnki.2096-1987.2016.04.006
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哲学原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研究”(12AKS002)。
侯文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