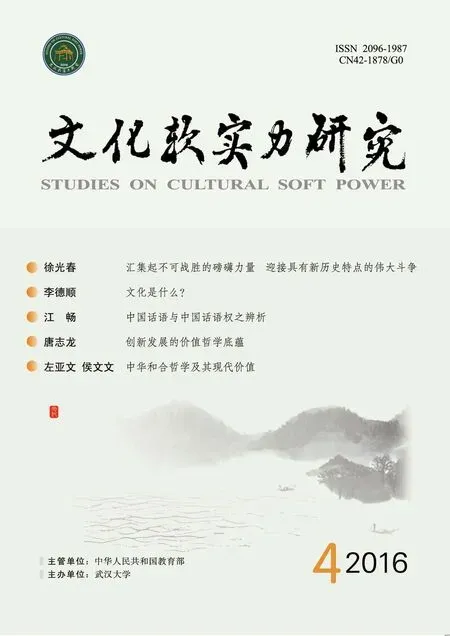从“中国话语”走向“话语中国”
——“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学术论坛评述
2016-03-16刘小莉陈雪雪
刘小莉 陈雪雪
从“中国话语”走向“话语中国”
——“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学术论坛评述
刘小莉 陈雪雪
2016年9月23日,武汉大学成功举办了以“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话语与话语权,话语建构的现实境遇,话语建构的策略思路,话语建构的方法自觉以及同心打造话语中的中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提出了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讨成果。
中国话语 话语中国 评述
“中国道路”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故事”异彩纷呈,然而中国形象却主要源于“他塑”,中国依然是西方话语表征其“世界性”的“沉默他者”。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塑造真实、有效的“中国形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2016年9月23日,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发起成立的“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论坛举行第一次活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提出了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讨成果。
一、话语与话语权
关于话语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巴赫金到福柯,从语言学到经济学、政治学,话语理论似乎成为理论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准确把握话语、话语权、中国话语等概念的内涵与实质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前提和基础,明晰话语与话语权、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等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中国话语、打造“话语中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对话语理论进行了解析。他认为,话语理论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话语。作为对事实的一种描述,它是比较客观、中性的。但是,话语的存在不仅仅是要去描述一个事实、一个事件或者某种东西,而是要讲述一种价值主张、利益诉求。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话语是一种立场、一种权力。因为话语实际上就已表明了对事实和价值做出的选择,并有所取舍。话语不是中性地描述价值,而是肯定了某种价值,站在一个立场上捍卫某一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价值面临争论或事实面临多样性的时候,话语就变成了一种加入一个社会群体的必要条件,甚至牵引、左右社会对于某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或者产生分化。所以,话语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表述,一个载体,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第二,话语权。话语权是对话语的一种肯定、让渡、剥夺或者认同,甚至是对于他人、群体和社会影响力的一种表征。第三,话语主导权。它是与社会权利的分配和让渡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的话语主导权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群体的主导权的丧失,尤其是社会在意见对立的情况下,它可能引起严重的话语对立和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话语主导权在一个社会里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以什么主导模式来建设、运行和发展的问题。
中国话语作为话语的衍生概念,它的提出是话语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湖北大学江畅教授对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两个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话语,是指中国自己独有的一套东西,如中国孔孟、中国儒学等都是中国比较权威的话语体系,而话语权不一定非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如通常所说的“在欧洲开的花,在美国结的果”,美国把欧洲的花拿过来,最后美国有了话语权。因此,中国话语与中国话语权两个术语要做区别。他指出,当前中国话语权不强,与国力不相适应,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话语,而在于我们的话语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先进。江畅教授还列出了中国话语权较弱的四个原因:一是西方率先获得了话语权,而中国的话语权刚刚才得到重视;二是西方话语已经在西方兴起,而且音量强劲,中国话语还没有力量与西方较量;三是中国话语实质上是存在西方话语的中国版的缩影;四是中国话语特别强调中国特点,不容易被世界所普遍接受。他认为这四个原因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理论已经提出来了,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在实践上没有得到普遍的证明。
欧阳康教授认为,中国话语其实是和中国近代的思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过去有话语权,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败,话语权逐渐丧失。现在话语权的重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话语主导权的重建。他认为,决定中国话语的因素,一是中国的传统是否还具有现代的意蕴,二是西方的话语能否诠释中国,三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他提出,决定中国话语权核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道路走得好不好,走得对不对,能不能走得通。
与会专家还就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世界话语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中山大学钟明华教授指出,学术话语的实质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事件认知、解释和构建的一种活动的方式及其结果。中国观念落后、文化落后,最主要的是学术落后,只有学术强中国才强,因此,学术话语的构建是中国话语构建的主体,是主要的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既不能让政治话语掩盖学术话语,也不能让学术话语来对抗政治话语。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道路既是自己的路也是世界文明的路。中国话语是与世界话语是相连相通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世界都能理解、接受和吸纳的,也是共同需要的,说到底是中华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指出,“中国学术应该积极建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自己走出来的路,岂容他人说三道四!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①陈曙光:《多元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二、中国话语建构的现实境遇
中国话语的建构总是在具体的现实境遇中展开。中国已然崛起,中国奇迹应运而生并大放光彩,然而中国的发展奇迹和话语建构的现实境遇不甚合拍。在国际话语场,“失语”、“自语”抑或“无语”屡见不鲜,话语贫困、话语被动以及话语弱势的局面依然严峻。
(一)话语劣势和发展优势的悖逆性
当下中国话语建构的现实境遇相当尴尬,对内表现为一种悖反性和滞后性,对外则表现为一种窘迫性和被动性。就前者而言,话语言说的乏善可陈和中国道路的独树一帜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中国话语的劣势处境更为彰明较著。郭建宁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既有成就,也有问题。成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发展,问题在于经济硬实力走在文化软实力的前面,经济影响力大于文化影响力,发展的优势没有转化为话语的优势,话语优势严重落后于发展优势。质言之,有中国道路,没有中国话语。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说的却是别人的话。如何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如何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如何把中国打造成为经济上和理论上的双重“巨人”,如何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话语,确是我们当前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武汉大学袁银传教授同样指出,中国学术话语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并不相称。我们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没有相应的话语优势,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手中。而且在对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故事的解读当中,我们也居于失语之境。
(二)中国话语创新和思想创新的滞后性
话语是思想的载体,“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①李韬:《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3年9月17日。话语体系背后总是有相应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一旦思想理论的建设和创新不足,就会直接以话语体系的滞后不前折射出来。中国的话语建构亦是如此。正如秦宣教授所言,思想创新是话语创新的前提。当前中国话语存在着创新不足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缺思想,即思想创新的滞后性。那么,思想创新不足又缘何而起?秦宣教授认为,中国的话语创新和思想创新不足有五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学者缺乏学术自信。中国学者总是力求按照西方的范式来解读中国,总是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说中国的故事,结果反而致使我们对自己的话语体系缺乏自信。其次,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制约了学术话语的创新和发展。再次,学者的急功近利,把学术当成副业而不是事业,缺乏创新的真正动力。复次,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知识分子多依附于资本和权力。最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正确的做法是既不能让政治话语掩盖了学术话语,也不能让学术话语来对抗政治话语,促进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协调互进。
(三)中国话语呈现方式的晦涩性
“话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人们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②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简言之,话语总是要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话语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话语的建构,进而关涉着话语的对外传播。目前,中国话语的表达方式带有浓厚的艰涩性,不是深入浅出,而是深入深出,甚至浅入深出,使中国话语既晦涩难懂,又佶屈聱牙,这就不免导致中国话语传播的窘迫性。对此,秦宣教授指出,话语的呈现风格对我国话语传播造成的困扰: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话语传不出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话语传出去后,大家不愿意听;第三个问题就是听不懂,对方听了之后不理解。因此,应当开启中国话语的正确打开模式,用最明白晓畅的言说方式表达最至理深刻的话语内涵,以促进中国话语的对内建构,推动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扩大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的影响力和角逐力。
三、中国话语建构的策略思路
中国道路只能用中国话语诠释,中国实践只能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验只能用中国话语提炼。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中国最有发言权,其他话语无权发声,也无法发声,于是构建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的看法,中国话语建构,势必要实现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话语要走以“我”为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创建之路。
第一,基于实践。立足中国实践,把握中国问题,才能更好地说话,说中国话。袁银传教授指出,当今的话语建构,要立足实践,立足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前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三重叠加。中国既要走向现代化,又要弘扬现代性;既要批判现代性,又要反思现代性。现代化无法避免,势在必行,但现代化的模式不止一种。所以,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原则,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也要反映时代潮流。江畅教授也认为,增强中国话语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并不断完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建构之所以不够彻底,是因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给出应有的确切的回答。当今中国面临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冲突问题,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中国话语,同时也决定着我们将选择何种话语体系。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更是将厘清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视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前提性问题。因此,中国话语要建构起来,必须对此问题作出深刻而有力的回应。
第二,注重学术话语创建。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建构、提升密切相关。在钟明华教授看来,学术话语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主体和主要领域,而学术话语的建构首先要有理论自觉。在理论自觉的前提下,钟明华教授提出创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四条路径:一是祛魅。彻底抛弃按照西方话语范式来解释、认知和建构中国话语的陈旧套路。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是建构学术话语的现实基础。三是综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西方现代性的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进行综合创新,这是当代学术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四是变革语言表达方式。语言表达的变化引起思维方式的转换,进而关涉着学术话语的构建和创新。随着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完成,中国的现代话语体系也就能真正地立起来。
第三,端正学风。构建中国话语,就是要“有做有概”。只有先概括出了“理”,然后才能去谈有“理”说得出、有“理”传得开的问题。我们有好的故事,好的蓝本,但是没有很好地概括出其中的“理”,这也是我们话语建构不足的原因之一。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由此,湖北大学杨鲜兰教授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和中国话语建构进行了联系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当前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理论脱离实践的不良风气。具体而言,盲目崇拜西方,用西方理论任意裁剪中国国情,用西方话语任意指摘中国实践;脱离社会实践,不关注社会现实,热衷于从抽象的理论到理论的抽象;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或自以为知之甚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妄加评断,指指点点。如此不良学风致使中国话语建构异常之艰难。唯有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着眼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才能做出准确而深刻的理论提升,这对于中国话语的建构和话语权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借鉴历史经验。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上,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则强调要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毛泽东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一些做法,对于当前中国话语构建确有启发。赵士发教授总结了毛泽东话语创造对我们建构中国话语的三点启示:其一,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当中,注重历史语境的变化。其二,关注话语主体的建设。其三,高度重视话语权的把握,善于占据历史逻辑和道义逻辑的制高点,即为人民服务和为绝大多数人的解放发声。客观上讲,我们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一种话语霸权,我们强调话语需要建构,话语权则需要争夺。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的现状,面对话语权的“西强我弱”、中国话语长期受制于西方的格局,我们国家的话语颇有沦陷之势。所以,话语权的掌握要靠斗争和争取,首要的是获得国内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然后才能在国际上争得自己的话语权。
四、中国话语建构的方法自觉
中国话语的建构不是单一方法的制造,而是多种方法和智慧的创造。中与西的结合,古与今的融通,隐与显的呼应,时与势的一致等等构成了今天中国话语建构的方法自觉。
(一)中与西的结合
西方话语霸权既有它背后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也有它话语建构的方法策略。建构中国话语应充分运用“中”与“西”的辩证法,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话语。在话语建构的总体方向上,钟明华教授提出,西方文明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中国话语的建构也应该有一种祛魅,这个祛魅就是要改变西方为中心的状况。西方话语的哲学基础,西方话语的文化类型、思维方式已然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整体主义、人文主义的新传统,也许是化解西方不足的一个重要武器。所以,以“中”为体,“西”为“中”用,是中国话语构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具体的方法上,江畅教授提出,西方话语把他们的价值观、理论都打造成普遍意义的,如人权,是普通的人权,正义是永恒的正义,它们是适用于全球的,普适性的。而中国话语特别强调中国特点,这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这种话语只适合于中国,不适合于其他人。建构中国话语,应该摒弃过分强调中国特点的特征,借鉴西方话语建构的策略,将中国价值观打造成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提出,西方谈到的很多话语其实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但是它们能占据文化的制高点,从而被接受和推广。中国要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必然要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还要显示出高端性,站在一个思想的制高点上,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断产生出新的话语、新的概念、新的范畴。
(二)古与今的融通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道路’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单向的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运动,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根据现在的中国了解过去。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离开先辈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无所有地去生活和创造;先辈们也不可能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特定的历史遗产,不留痕迹地成为历史”。①陈曙光:《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求是》2014年第12期。建构中国话语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资源,又要超越传统的局限,真正做到古与今的融通。钟明华教授将中国话语的历史分为10世纪的自我建构时期、10—16世纪的与世界各种文化共同发展时期、16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衰弱和过渡时期以及现在的文化复兴时期。他指出,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近代以来的落后不过两百年,我们对话语的构建应该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臧峰宇教授指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应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四方”、“贵和尚中”等观念,是今天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话语资源。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典话语进行有效结合,有可能构建出一种有世界历史视野的话语体系。
(三)隐与显的呼应
中国话语的建构,话语中国的言说,是隐性的思想理论建构与显性话语建构的遥相呼应。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实质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呈现。欧阳康教授说,“今天中国的话语困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困惑和社会模式的困惑”,也即是说,目前还没有一套理论可以解决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这也造成了中国问题在世界话语舞台的扑朔迷离。其实,传统的中国话语根本解决不了当代中国问题,西方话语无法诠释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无法言说当代中国,只有思想创新,才可能说新话,才可能说“中国话”;只有理论自觉,才可能推动话语自觉。在会议中,欧阳康教授还以“南海问题”为例指出,表面上看,我们要夺取南海的主权,争夺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诸如九段线、主权线这些最基础的理论搞清楚,我们的话语权谈何而来?因此,我们要谨记,“中国话语”和“话语中国”的主语是“中国”,最终的落脚点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与解释上。“隐”与“显”相得益彰,“隐”是“显”的根基和源泉,“显”是“隐”的表现与折射,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四)时与势的一致
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必须顺应时势的发展。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给中国话语建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而美国一家独大时代的结束,国际话语舞台需要中国声音,加上国内学术界对话语构建的集体自觉,建构中国话语正逢其时。秦宣教授指出,当前中国话语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时候,经过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等到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够了,我们的学术话语概念提炼也够了,那个时候估计会产生一些学术大师、思想家。钟明华教授说,经过中国道路奠基,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话语可能在全世界立起来。在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也是事实,但一定是暂时现象。的确,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必将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①陈曙光:《论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及演化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五、同心打造“话语中的中国”
建构中国话语,其终极目标在于打造“话语中的中国”。陈曙光教授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了“话语中国”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话语中国’,指的是由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或者说,隐匿在话语中的‘中国图像’。‘话语中的中国’是相对于地理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而言的,它所表征的是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是标识中国‘身份自我’的文化符号”。②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话语中的中国”理应由中国话语自己塑造。然而在现实境况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却基本上是由西方话语塑造的。袁银传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在当前的国际话语中,英文占68%,中文不到6%,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中,中国故事都是以西方的话语资源进行解读。欧阳康教授也指出,从总体上来看,世界对中国的误解超出对中国的正解,中国在国际上真正展示出有力量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中国的建设性的、当下的东西,而是传统的、粗俗的、恶劣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世界对中国很多的误解。西方的话语框架、分析范式和思维逻辑已经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
如何打造“话语中的中国”,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陈曙光教授认为,西方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性”的缺失和“西方性”的附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虚假的甚至妖魔化的中国随处可见。“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不尊重人权”、“中国没有大国责任”、“中国欲称霸世界”,如此等等,遮蔽了中国的面目,同时也将中国“破相”了。“澄清中国形象,界定中国道路,摆正中国位置,评估中国的意义,将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呈现出来,是话语中的中国存在的价值”。①余伟如:《“话语中国”及其建构策略和评判标准》,《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2期。
如何评价“话语中的中国”是否成功出场?陈曙光教授提出了他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有关涉中的话题是否由中国主导,“讲什么”是否由中国决定,“怎么讲”是否取决于中国,“讲得对不对”是否由中国判定。一句话,“涉中”的话题中国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故事”的国际话语由西方主导,西方人反客为主、到处点火、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那就失去了话语权。②陈曙光:《让世界知道中国》,《光明日报》2016年8月15日。
陈雪雪,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From“Chinese Discourse”to“Discourse about China”—Review of the“Chinese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bout China”Forum
Liu Xiaoli(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Chen Xuexue(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On September23,2016,the forum of“Chinese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bout China”successfully held in Wuhan University.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carried on a extensive and 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discourse and discursive power,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bout discursive construction,the strategy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the method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creating of discourse about China commonly.They 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these problems,put forward a lot of academic issues that deserve to be discussed further,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Chinese Discourse;Discourse about China;Review
10.19468/j.cnki.2096-1987.2016.04.012
刘小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