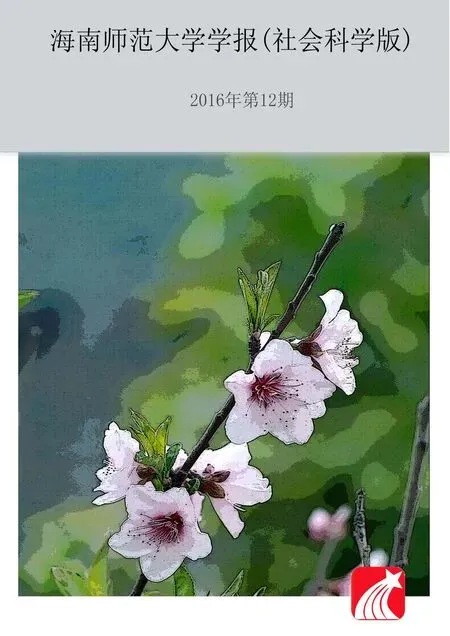诗歌何为?
——改进大学新诗教学的思考
2016-03-16张文民
张文民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诗歌何为?
——改进大学新诗教学的思考
张文民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大学新诗教学的知识化、学问化导致诗性内涵的消解,从而影响到新诗对学生人格及价值观的培养。从青年学生的阅读、接受角度看,新诗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品格与价值:提供一种艺术地认识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途径,真实地袒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与心灵历程,充分体现想象、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改进大学新诗教学,首先要回归作品,重视阅读与感悟,其次要构建行之有效的新诗解读理论与方法,再次要完善新诗教学的体制环境。
新诗;大学新诗教学;诗教传统
近年来,新诗教学是一个引起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这些讨论大都集中于中小学语文中的新诗教学,而对于大学新诗教学却关注甚少。如果把新诗教学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就应该贯穿于中小学到大学,事实上两者也是有紧密联系的,中小学阶段新诗教学培养起学生对新诗的兴趣,打下阅读、鉴赏基础,进入大学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从新诗中获取精神滋养;反之,大学新诗教学良性发展,也能为中小学培养新诗教学师资力量: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本文旨在反思大学新诗教学现状,从青年学生的阅读、接受角度挖掘新诗的独特品格与价值,并提供改进大学新诗教学的思考。
一
中国有深厚的诗教传统。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89页。这是在强调诗歌对个人的认识教育功能。而《毛诗序》则上升到家国兴亡的高度来讨论诗乐教化:“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②《毛诗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页。小至个人修养,大至家国兴亡,诗歌的干预、感染、教化功能无处不在,诗歌之于传统中国,诗教之于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存在。
反观当下,诗歌尤其是新诗正在淡出公众视野,传统诗教环境下诗歌的那种经天纬地、无所不在的功用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文学的诗歌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就目前的大学课程来讲,中文专业的基础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诗歌教学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在总课时量日益缩减的情况下,新诗教学所占比重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一些大学在基础课之外开设新诗选修课,但这些课多是专题研究,授课教师是新诗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们倾向于把新诗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知识传授给学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至于如何让学生感受到新诗独特的灵动飘逸之美、智性沉静之思以及丰厚的精神内涵,如何让学生领略到新诗给予的思想启迪、思维创新、情感濡染、美的熏陶,则是考虑较少的问题。侧重于传授理论知识和培养新诗研究人才,这种精英化的大学新诗教学以专门的、繁复的新诗学问慢慢消解掉新诗的精神内涵。如果说传统诗教重点关注的是诗歌的“功用”,那么现今新诗教学却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技术性”。
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新诗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是诗的国度,长期以来诗歌是文学的主流,直到元明清,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样式蓬勃发展。近代以来,伴随着救亡图存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社会思潮,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普及并产生影响的小说受到格外推崇,地位越来越高,以至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夸张描述与《毛诗序》对诗歌教化功能的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小说备受垂青相比,保持长久辉煌的诗歌至此显得黯然失色。“五四”文学革命一大实绩便是新诗的创立,从此,一种迥然有别于古典诗歌的崭新的诗歌形态诞生,中国诗歌经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鼎盛、衰落之后,迎来一次较为彻底的涅槃新生。新诗走过百年发展历程,其间有曲折坎坷,也有可喜成绩,至今还谈不上成熟、定型、完美。与新诗蹒跚向前的过程相伴,一种质疑甚至否定新诗的声音时有出现:鲁迅说即便是最优秀的几个诗人的诗作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斯诺整理:《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毛泽东断言“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诗刊》1978年第1期。。如果说这些只是对新诗印象式的评判,有些笼统、绝对,那么诗人郑敏在20世纪末对新诗的反思则更具学理性,也更彻底。她认为新诗由于采用白话,拒绝古典诗歌传统,致使“自我饥饿,自我贫乏”,未能出现世界公认的杰出诗人诗作。*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新诗道路及其评价问题已经争论百年难有定论,特别是以几千年古典诗歌为参照来评判百年新诗发展,这种做法本身也许值得反省。*洪子诚谈到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形成的“巨大压力”时,认为新诗评价应该首先考虑到新诗自身的“特殊性”,但也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犹疑。参阅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117页。然而,历史短、不成熟、未定型、不完美,无疑影响到新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从外部大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市场化转型,这种转型带来文学巨变,最明显的是文学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其神圣、崇高的精神内涵被消解。在一个市场化、消费型社会里,日益勃兴的大众文化以其世俗性、娱乐性渐渐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博得人们青睐。由于大众娱乐的勃兴、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观念的流行,严肃文学由中心退守边缘,取而代之的是迎合市场的流行读物。追求世俗、娱乐、消费,拒绝神圣、崇高、深度,成为阅读时尚。在此背景下,诗歌这种高度凝练概括、抒情性强、直逼心灵、需要细细品味咀嚼的语言艺术就难以引起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社会分工的细密化、知识学问的专业化、高等教育的系统化与标准化使得新诗教学甚至包括整个文学教育的目标不再停留于泛泛的“修身养性、审美愉悦、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层面,而是要努力造就专业研究人才,这种培养目标无疑满足了高等教育专业化的想象与规划。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与教育框架下,新诗的诗性内涵、精神价值被逐步消解,诗歌成为一种塑造、武装专门人才的理论知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体制之下社会的原子化、文化的观念化与教育的标准化(normalization)使得诗歌教育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个体与诗歌之间,失去了人的天生诗性,而必须经过体制力量的中介与协调,诗歌自身也就是在这样的规范系统中被细化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林喜杰:《新诗教育:群体性解读与想象的共同体》,《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大学新诗教学面对的是青年学生,他们正处于诗样的年华,对诗有天然的亲近,渴望从诗中汲取精神、感情的滋养甚至是人生的经验,至于将来从事专业的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毕竟只是少数,认识到这一点,传统诗教在当代仍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当然,大学新诗教学完全回归诗教传统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不仅是新诗与古典诗歌具有不同的品格、价值与地位,而且传统诗教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某种程度上回望诗教传统,反思当下大学新诗教学的现状及其问题,则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反思的逻辑起点是:诗歌何为?新诗对于青年学生何用?换言之,反思、重视新诗教学的前提是,新诗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古典诗歌,有别于小说、戏剧、散文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而当下新诗教学对这种新东西的挖掘远远不够。
二
与古典诗歌相比,与小说、戏剧、散文相比,新诗自有其独特的品格与价值。在百年发展的历史中,新诗以对现代性的追求,对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参与,对独立自由人格的塑造,对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展现,对新的诗学价值与艺术形态的建构,从而自足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百年新诗也是青年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现实、丰富人生、充实自我的无可替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诗提供一种艺术地认识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途径。在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文学无法抛开对时代、民族、家国的担当责任,新诗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新诗发展史同样是中华民族觉醒抗争、涅槃新生、变革进步的艺术呈现,承载百年苦难与沧桑、光荣与梦想。郭沫若《女神》中的《凤凰涅槃》等诗已经很难引起今天青年学生的阅读兴趣*中国现代文学课上,学生诵读《凤凰涅槃》总会引发哄堂大笑,这种笑显然代表着一种历史隔膜。,然而就是这种直率粗糙、狂放雄强的诗歌弹奏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昭示着中华民族青春朝气的勃发,而其对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古典诗歌传统的彻底反叛,又恰恰构成初期新诗之“新”的内质。《女神》最典型地映照出“五四”这样一个狂飙突进、破旧立新的时代。百年新诗史上不乏《女神》这样的“时代之诗”,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革命呐喊,40年代抗战炮火中的昂扬战歌,50-60年代的政治颂歌等等。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今天读者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道出这种诗歌的诸多缺陷,可以用“纯文学”的标准质疑这种诗歌的艺术生命力,却无法否定其记录一个时代的真诚与努力。阅读这些诗歌,人们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感受到社会的变动,了解到特定时代与社会里人的精神面貌。这类诗歌积极拥抱时代与历史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是不应该被完全否定的。
新诗最真实地袒露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与心灵历程,他们的挣扎与奋斗,失落与哀伤,追求与希望,诗人之情与智性之思,这一切同样能够引起青年学生的震撼与共鸣。知识分子是敏感而脆弱的时代精灵,他们率先觉醒,同时感受到“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既有献身于民族新生、社会进步的一腔赤诚,又不放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索与探求,诗歌成为真实传达这种感情与思考的最佳载体。闻一多的《红烛》《死水》集中表达身处异域与本土二元对立文化环境所感受到的心灵错位与冲突,那种关乎追求与幻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那种炽热灼人的对国家、民族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情怀,同样能够引起当今生活在社会转型和文化碰撞中的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戴望舒的《寻梦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追求与付出、实现与衰老的矛盾与两难,诗人超越现实生活的层面,进入普遍性的人生哲学的思考。而穆旦无疑是现代中国最能够抒写知识分子精神痛苦的人,在他的诗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交织融合、相互诘难,既表达“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时代主题,又呈现属于知识分子独有的那种“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在对残缺、矛盾、分裂的“自我”反复抒写中透露出知识分子多思敏感心灵的冲突与搏斗。因此,中国新诗史同样是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思想史、精神史,阅读新诗,能够得到心灵涅槃与精神升华。
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更充分体现出想象、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蕴含着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形态。新诗总体上是一种自由诗,打破古典诗歌篇幅、字数、格律等形式藩篱,真正实现自由抒写诗人的心灵、感情与思想。形式的突破带来艺术思维的创新,废名指出旧诗是以“诗的文字”表达“散文的内容”,“情生文,文生情”,“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新诗则是以“散文的文字”表达“诗的内容”。*冯文炳:《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6页,第24-26页。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综合废名的论说,这里“散文的文字”指自由体式,“诗的内容”指属于现代诗人个体的、鲜活具体的思想情感,废名对新诗、旧诗的区分很能给人启发。古典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臻于完美,但也形成一套较为固化的表达模式,见明月思故乡怀远人,观落花叹韶光怜红颜,临流水知逝者如斯,至清秋觉伤心寂寥,这种“情生文,文生情”在很大程度上束缚思想情感的自由表达,束缚自由无羁的艺术想象与创造。新诗在打破整齐划一的形式藩篱的同时,也颠覆古典诗歌思维定势,呈现出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独立无羁的艺术创造,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比如闻一多的《死水》前两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在古典诗歌里,“翡翠”、“桃花”、“罗绮”、“云霞”这些意象被赋予精致、高雅、灿烂、美好的内涵,而在这首诗里,这一切美好的内涵都被消解掉,用以形容“死水”的肮脏、丑陋,这种化美为丑的写法对古典诗歌思维定势无疑是一种彻底反叛,体现出诗人别出新意的想象与创造。冯至的《蛇》中“蛇”与“姑娘”、“茂密的草原”与“浓郁的乌丝”、“梦境”与“花朵”等一系列相去甚远的意象奇妙地组接在一起,写出现代意义上的人生孤独,这种看似神秘荒诞的观念联络使诗歌获得突出的抒情效果和多向度的思维品格,日常意象获得丰富的内涵。想象、自由、创造的现代艺术精神催生现代艺术思维方式,从而使新诗呈现出新的美学形态:打破古典诗歌的玲珑精致、醇美和谐、温柔敦厚、含蓄蕴藉,追求张力、矛盾、残缺、异质,努力以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与思想情绪。
三
与几千年古典诗歌相比,仅有百年历史的新诗还远谈不上成熟、完美,但已形成迥异于古典诗歌的品格、价值与美学形态,奠定了新的诗歌传统。同时新诗也是一种丰厚的教育资源,通过大学课堂教学,新诗转化为知识,得以积累、传承,更重要的是使青年学生从中得到情感陶冶、精神滋养与人格提升。
改进大学新诗教学,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破除理论知识的迷思,回归作品,重视阅读、感悟、思考。目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小学通过新诗读写进行审美教育,大学则更应该强调新诗理论知识教学与研究,这实际上是把新诗的鉴赏审美与理论认知对立、割裂开来,机械地置于不同的教育阶段。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其不尽之意、难言之美必须通过诵读来体味、把握,不仅中小学如此,大学也是如此,“诗歌教学应从诗歌本身特性出发,多在阅读中去品味,把握诗的韵味和意趣,不能机械化,不能死板。……诗歌的意蕴只有在读中去品味,不读永远不能得其神韵”*龙泉明、左晓光:《读——诗歌教学之魂——龙泉明教授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9期。。通过诵读、想象、感悟、琢磨、思考,实现对诗歌的整体审美判断,培养对诗歌的悟性,获取诗歌中的无穷韵味。阅读是从中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最有效的新诗教学方法,只不过在阅读层次、对象选择上不同教育阶段应该有所区别与侧重,从而形成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新诗阅读鉴赏过程。中学新诗教学一度为人诟病的是诗篇选择的单一政治化视角,目前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强调选篇的丰富多样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并非越多越全就越好,一些理解难度较大的现代主义诗歌(比如李金发、穆旦的诗歌)还是留待大学课堂更为合适,这再次说明阅读这一核心环节并不能终结于中学课堂,大学新诗教学同样要坚持阅读、感悟、思考第一。
新诗教学要重视阅读,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生命、情感体验对诗歌做独立的鉴赏、感悟与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否定教师的解读,构建行之有效的新诗解读理论与方法并运用于实践对于改进大学新诗教学必不可少。与散文的直抒感情、戏剧的直观表演、小说的具体形象等特征不同,诗歌具有一定的“隐藏度”,“诗人通过想像创造作品,然后隐藏自身,拆掉读者理解的桥梁”,而教师就要努力挖掘诗歌所隐藏的东西,在诗人传达与学生接受之间“做搭桥的工作”*孙玉石、戴皓:《关于诗歌的赏析与教学——孙玉石教授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4期。。如果说古典诗歌“情生文,文生情”的表达方式客观上提供索解途径,那么新诗的想象创造、自由表达无疑增加了解读难度。为此,孙玉石倡导“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并积极投身其中,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比如:从诗歌本体出发,肯定现代主义诗歌审美本质,强调解诗与写诗同样重要,都是创造美的过程;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诗歌生产与意义阐释过程,解诗学在注重诗歌文本的同时还要尊重读者的主体性、创造性,而悟性、智慧、想象则是撑起读者与诗作之间桥梁的支柱;尊重中国新诗艺术发展规律,走中西融合的解诗之路;逐一梳理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废名等人的解诗理论与实践,为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储备资源,等等。*有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主张可参阅孙玉石以下论著与文章:《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卷、1937—1949卷、穆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再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论闻一多的现代解诗学思想》,《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朱光潜关于解诗与欣赏思想的阐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以新诗文本解说进入大学课堂——重建现代解诗学思想杂记之一》,《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对话”:互动形态的阐释与解诗》,《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重建现代“解诗学”》,《文艺报》2015年12月23日。此外,常晶:《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浅论》(《阅读与写作》2007年第6期)对孙玉石的解释学研究作了概括性介绍。孙玉石倡导的中国现代解诗学与纯粹的新诗理论、新诗研究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解诗学的成功建构有赖于新诗理论、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但解诗学更强调实践品格,易于操作,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教师解诗、学生读诗,从而推动大学新诗教学更好开展。
大学新诗教学的改进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新诗、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课堂,还涉及到外在的体制环境。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渐渐向系统化、标准化、体制化方向发展,存在着销蚀人文内涵、精神价值的危险。反过来说,良好的教育体制对于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也是有力的保障。正如高考语文试题向新诗倾斜对中学新诗教学是一个重要导向,大学新诗教学如果能在体制内占有更重要地位,无论是对于新诗的传承、经典化还是对于教育终极目标的实现都大有益处。《诗经》能够穿越几千年历史长河流传至今,本身的艺术成就、魅力固不可否认,但更与它作为儒家经典尤其是科举考试科目从而获得体制内生存大有关系。新诗发展历史短,不成熟不完美,进入教育体制实现初步合法化、经典化,转化为知识、资源、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另外,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强调实用工具理性的同时更要注重人文精神内涵,在当今社会后一点尤其重要,而新诗本身独特的品格更能给现代高等教育注入人文精神之光。改进大学新诗教学的体制环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专门的新诗教学师资力量(应与新诗研究学者有别);适当增加新诗教学课时量;在学生中有组织地开展新诗诵读活动,形成爱诗读诗氛围;在课业考试考核方面向新诗倾斜,等等。新诗教学的体制改善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海德格尔提出的“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这一命题穿越大半个世纪的世俗、浮华与喧嚣,成为萦绕在现代人心头的一帘美梦,哲学家对这一命题作出形而上的论证,普通人关注的是它犹如高天彩虹般的幻美。“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亦即意味着诗之中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技术的眼光与态度。”*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这里的“诗意”不仅是一种自然、浪漫、高雅、温情,更是对自在本真生命的呼唤,对超越客观现实限制的自由精神的渴望。而“诗意”首先存在于诗歌里,百年新诗建造起一个艺术自由的王国,期待更多的人进入、徜徉。
(责任编辑:王学振)
Reflec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New Poetry Teaching at College
ZHANG Wen-mi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knowledge and academism in new poetry teaching at college has led to the negation of poetic wisdom, thus having reduced the role of new poetry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sense of worth.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reading and acceptance, new poetry has its following unique quality and value: firstly, new poetry can provide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history and reality in an artistic manner; secondly, new poetry can truly reveal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personality, soul and spiritual journey; and finally, new poetry can fully reflect the artistic spirit of imagination, freedom, and creation.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new poetry at college,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o return to poems and to take reading and sentiment seriously; secondly,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advance effective theories and methods as to poetry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hirdly, pain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the milieu of new poetry teaching.
new poetry; new poetry teaching at college; poetic education tradition
2016-08-12
张文民(1976-),男,河南浚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2
A
1674-5310(2016)-12-00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