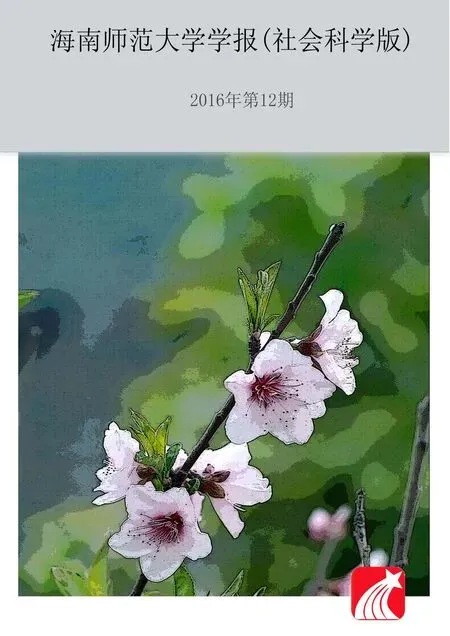王安忆《天香》的空间叙事
2016-03-16郑浩月
郑浩月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王安忆《天香》的空间叙事
郑浩月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小说中的空间因素越发受到重视,为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在《天香》中,空间一方面意味着园、宅与上海城等实体的空间,它们参与、影响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表达着等级之间的隔离及突破,而小说中上海空间的建构,也流露出当代中国自我追寻与表达的诉求;另一方面,空间也指抽象意义的空间,是审美与文化心态上向市井的俗文化的位移,但并不意味着混淆其与雅文化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次在二者之间重设边界的努力。
王安忆;《天香》;空间叙事
小说是公认的时间艺术,然而其空间因素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叙事学界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先验的感应形式’,时间只有以空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正如空间只有以时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①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1页。事实上,提醒人们注意小说中向来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的确为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王安忆的《天香》正是一部值得用空间叙事学方法进行分析的作品。小说出版的2011年,王安忆曾写道:“空间惟有生发含义,才能进入叙述,或者说,我们必须以叙述赋予空间含义,才能使它变形到可以在时间的方式上存在。”②王安忆:《小说的异质性》,《花城》2011年第3期。写作的过程意味着空间转化为时间、客观转为主观,让疏离的存在充盈人性。这表明王安忆本人对于小说中的“空间”亦有清醒的认识。
《天香》故事起讫嘉靖三十八年至康熙六年,叙事跨度很大;而学者型作家王安忆也拥有“信史”的追求,因而小说中出现了不少的时间标记以及时代背景的交代,此后她也明确指出一年中的大事实际上与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③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然而,从阅读体验来说,这种时间感又是相当模糊的,可以说,这些时间标记不过是在一把直尺上刻下首尾的刻度,再于其中要紧处略加点出,而其余的却依赖于空间与场景的演示。“《天香》就好比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幅,人事纷繁,细密生动,却大都定格在一个个特定空间里,没有各自在时间层面的持续性”,是定格的人事,“阅后即焚”。④张诚若:《小说家自己的命运:读王安忆〈天香〉》,《上海文化》2011年第4期。并且,小说的空间特征不仅是阅读感受,即叙事效果,也是叙事策略本身,即空间是如何参与、影响叙事,并具有了意识形态意味的。
一、园、宅与城:实体空间与小说叙事
(一)申家园宅:叙事的展开
“空间”首先指实体的空间:小说正是以“天香”命名的——这是其中的“园”,此外更有另外几个至关重要的空间,即申府、张宅与上海城。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小说对时间进行一个概念式的交代难以激发感性体验,但一个具象的空间被着重强调,同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却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首先要讨论的,正是空间的叙事推进功能,这是对于时间的同等功能的一个替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空间并非等待填充的空洞之物,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得以表现、生产、强化的关键。*余新明:《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申家的建筑风貌,及其变动的过程,意义也超出了建筑物本身。
对《天香》而言,叙事推进指的是空间的变易(即“造园”)对于人物及其命运的展现所起的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些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人物的标记,与之具有了二而一的品格。申家的建筑包括两个主体部分:一是宅子,另一就是天香园。申宅在故事开端已有基本格局:中轴线上是前堂、中庭、正院,东面是平房院落,西面兼有楠木楼。老太太居中,儒世在东,明世在西。*王安忆:《天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这种东西延展、中轴对称的建筑形态,象征着传统的封建大家族权力的中心所在,以及鲜明的等级礼仪意识。小绸是第一个出现的与“天香园绣”关系密切的女性人物,她嫁与明世之子柯海为妇,居于宅子西侧的花厅;这也是申家空间与人物之间明确互动关系的第一次呈现。花厅在整个家族建筑中的位置当属偏屋中的小中心,江浙一带的民居,“在边落的一组建筑中,相应正落中大厅的位置设花厅”,“气氛与正厅完全不同,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却又没有另立中心之嫌”;*郭鑫:《江浙地区民居建筑设计与营造技术研究》,重庆: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小绸初嫁时,作为申家次子的长媳居于花厅并无不妥。但西面的楠木楼却住进了镇海媳妇——这也是与“天香园绣”关系密切的人物——这种气势上的不对等成为小绸起先对她产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久,老太太亡故,儒世被作者“赶”出申宅,住进梅家巷,这一方面是为继续维持“中轴对称”的居住格局(改以明世为中心),因为老太太的亡故使申家失去了中心,或者说拥有了两个中心;另一方面,节俭清高的申儒世离开,也是为“余下这帮人挥霍起来就没了阻力”*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尔后天香园绣才有流入民间市场的可能。此后,东侧与西楠木楼相对位置上又成一座楠木楼,其建造有建筑美学观念的作用,但根本上是为小绸而建,以表明其身份地位——正因此,小绸最终负气不进楠木楼才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闵女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住进了这座楼,造成了她与小绸、柯海三人之间难堪的局面,也使她在申家被孤立,便终日以绣艺为伴——这是“天香园绣”的缘起。不过,这两处楠木楼却都不是各自主人的久居之地:镇海媳妇与闵氏各有因由地退出来,为子辈阿昉、阿潜腾挪地方,而后才有蕙兰、希昭这二人进入读者的视线。
如果说申宅的格局变易展现的是其中人物的来去与命运流变的话,那么天香园则是绣艺名字的由来,也是三代女性学习绣艺的场所;而其兴衰起落则是申家兴衰的一个表征。最初此地不过是一处桃林,就地建成了天香园(《1桃林》)。随后莲池(《2喜盈门》)、中轴线上的碧漪堂(《2喜盈门》)、西北角的莲庵(《4莲庵》)、莲庵与万竹村之间的墨厂(《8墨厂》)、西南方向临池而起的白鹤楼(《11绣阁》)一一出现。对于申家建筑格局,已有的专门研究认为:“作为私家园林的天香园,在自然随性的空间表象之下,依旧隐藏着深层严谨的等级秩序。”*喇诗韬:《〈天香〉的物质文化与个体命运》,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这种等级秩序的最突出体现就是仍将碧漪堂置于中轴线上。不过,更应强调的是,其余建筑分布显然是自由随性的。另一方面,造园缘起于“中了进士,出去做官,或者本来在外面做官,如今卸任回家”*王安忆:《天香》,第1页。,而申家显然是后一种,不再有意于官场——天香园的建造目的即在游乐,且天香园建成后,即成申家人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宴饮、弄糨、制墨、赏景、学绣、养蚕、祭祖、礼佛、红白事等等,特别是白鹤楼被用于女眷日常刺绣闲谈的场所,更是文本着意强调之处。于是,园中自然物的生机、人事的互动带来了园子的活泼自由气息——事实上,相对于对申家宅子进行一般性的描述而言,作者显然更钟情于更多着墨于天香园,且字里行间暗含赞叹。正是在这里,宅子森严的等级与天香园的去等级化,暗示了申家女眷的绣艺成为流通的商品,并流入寻常巷陌的可能性。尔后,天香园内的墨厂再易为蚕房,而后破败,又平出九亩地,种上甘薯,甚至驻进崇明水师——天香园见证了“精致的淘气”如何热闹了园子,又如何冷落了园子;而申家又是如何衰落至需仰仗沽售女眷的绣品以维持生计的——这也是天香园绣流入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从申府到张宅:流入民间
不少研究者在《天香》中发现了《红楼梦》的影子,其中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天香园与大观园的对照,申家与贾府家族兴衰史的对照。然而,尽管《天香》写及园兴、园败,却与后者大异其趣。小说前两卷集中于天香园内,似乎确有大观园的影子。但实际上,以“造园”起笔,以“天香”为题,联系着王安忆本人的写作动机:“顾绣”自闺阁流入民间,甚而成为家道生计的“逾矩”引起了她的兴趣。*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正是从这里出发,王安忆开始了写作的逆向推理:针黹绣艺与女性命运相连,而女子的活动范围,又止于闺阁之内。但也正因如此,王安忆写作绝不会止步于闺阁。小说第三卷出现了突然的空间转移——第三卷正是作者的得意之笔——随着蕙兰的出嫁,视线几乎完全转向张宅,除了与蕙兰有着隔辈交谊的叔叔阿暆以外,对园中人物的命运、对园中的景况其实“不太关心”,即便提及,不过也是跟随着蕙兰回娘家的脚步偶然一窥(《33张遂平》《35修佛》《37求师》),或三言两语简略一提(《33九亩地》)。
张宅自然与申府无法相提并论,仅是一处“多少是有些促狭的”院子:“从北门进去,先是一方天井,一眼水井,年头不小了,井壁上布了苔藓。天井两侧各是灶房和仆佣的屋子。走过天井,便是正厅,北墙上横一块匾,书几个大字:永思堂。匾下案上供一尊弥陀,一炉香,案两侧各置几具桌椅。厅堂东西厢房为老爷夫人居室与书斋。厅堂前是院子,院子两边各有连通的两间侧屋。”*王安忆:《天香》,第279页。张家没有造园,宅子仍是严正的中轴对称格局;然而,院子窄小、人口素简,却拉近了主仆之间的距离——李大、范小与其说是张家的仆人,不如说是张家的朋友,甚至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他们占据了相当的笔墨,并非脸谱化、空心化的下人形象,而是具有了个性与情感,且别具趣味。在这样的情势下,戥子这一使“天香园绣”从贵族之家流入平民之手的关键人物,也得以自然而然地走进蕙兰的绣房。这便是空间转向的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小说第三卷也出现了更为活泼的社会因素。张家作为一个窗口,成为天香园绣流入民间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贵族家庭与市井生活沟通的通道,甚至可以说,张家本身就具备开放性的因素,是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前两卷在申家之外,也写及园外人事:白鹤村木匠章师傅家、苏州闵家、龙华寺、杭州沈家、香光居士宅、西城薛家巷、日涉园等。然而,这些看似广泛的园外空间,却又向内指涉着园内的人事,服务于园内人物的出现与性格的塑造,从其中的笔墨趣味上说,也相对的稳重、保守。然而,在第三卷(包括第二卷的后两节)中,情况却大为不同,除了集中于张宅的人事以外,广泛涉及了阿昉的豆腐店、沉香阁、九间楼与徐光启、大王集庙会、洋人仰凰,更因为阿暆的交游而多处写及市井中的奇人异事。这些张家以外的种种景象,自然大部分是是越过申蕙兰的视线,直接由全知视角展现,但其中唯市井才有的生机与活力、热闹与繁华,却是从张家出发便于展现。
(三)上海地理志:万物皆备于我
《天香》中无法忽略的实体空间,同时也是文本空间边界的,正是整个上海城市。上海城市空间的表现,主要借助于上海地图在文本中的准确勾画,以及各类器物掌故的说头。对于已经被标记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来说,《天香》的出现势必使这标记再度加深:小说被认为是上海的“前史”,天香园则是城市的寓言。作者的认真、用功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是写到哪查到哪。写到哪一节,临时抱佛脚,赶紧去查……其中那些杂七杂八的所谓‘知识’,当然要查证一些,让里面的人可以说嘴,不至太离谱。”*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联系此前的创作,小说被认为对上海前史的追述不难理解。而在当代的小说观念中,对小说家的最高评价大概就是有“史家”之味了。但实际上,王安忆的工作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仅仅是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徐健、王安忆:《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文艺报》2013年4月1日,第1版。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即为故事的发生建构一个合理的空间,而并无为上海著史的野心——上海地理志其实是无意中成就的,因为作者发现“一旦去了解,却发现那个时代里,样样件件都似乎是为这故事准备的”*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我们的确可以按作者本人的说法列举出诸多证明,比如,“天香园”的建造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想法,而是在上海普遍兴起的造园风气的影响下而成;明末上海商业资本的繁荣,也为天香园绣用以交易提供了可能。
用以营造小说的历史氛围的,除了对历史细节与掌故不厌其烦地讲说以外,典雅流利的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与之相比,20世纪历史题材的小说、话剧中,无论是这种模拟想象中的明末语言,还是“格物”式的写作方式,都无法找到,甚至于“失事求似”也未尝不可。对所谓“历史精神”的追寻可以放弃历史细节的求真,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对历史与读者双方面的不负责。我们对历史故事的写作提出了“真实”的要求,以至可以无视《天香》中器物、掌故的堆砌、繁复绵密的描写给情节发展造成的迟缓甚至停滞,以及人物形象相比之下的苍白逊色。实际上,将这种“真实”落脚于“器物”并不是“本应如此”,相反,它可能联系着当代隐秘的拜物教心理。物对空间的实体性占据保证了心理安全,似乎占有了物品的“真实”,就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如果联系到2015年秋天上映的电影《聂隐娘》,我们也能获得同样的感受。
另外,整个小说写作的初始动机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部分,前文提到令作者动容的,是“天香园绣”的原型“顾绣”从贵族的闺阁流入市场的过程。但不难发现,在这一追溯的起点,已经蕴含了为当代上海城市“寻根”的意图。而这种寻根锚定在明末上海,显然受到了中国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论”分析模式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证据是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而这一证据最集中地出现,是在明清之际。对于王安忆而言,对当代上海的历史追溯,跳过了近代的民族血泪史,直奔“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上海,显然与历史学家的工作目标一致。这种追溯中透露出的,是排除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目标,是证明走出自己的道路的可能性与渴望——尽管这种追溯将起点设置在现代上海可能已经意味着他者的规定在暗中起着作用。这种目标在文本中也有显性的体现:在小说第三部分,洋人仰凰是一个特异的角色,他是惟一的外国人(欧洲人),也是似乎可有可无的人物——“可有可无”指的是游离于故事的主干,但仍可能成为“为这故事准备的”时代因素的一部分——这个洋人身上散发出的温和可亲、平易近人的气息,时人对他以及基督教流露出来的坦然与宽容的心态,可能正属于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明末上海,但更重要的是,前者迥异于近代以来侵略者的狰狞面目,而后者也迥异于近代国人对“列强”广泛存在的鄙薄和惊异,甚至延伸至今的潜在畏惧。
二、隔离与突破:抽象空间与雅俗分野
(一)侯门与市井
前文讨论的是小说中的实体空间。相比之下,下面要讨论的心理意义上的“空间”,则显得抽象得多。这些讨论将侧重于空间分割,与相互间的隔离及其突破的方面。这种心理空间的隔离是一种类似障壁的感受,相对于具体可触的实体空间,它源自于内心界限的设置——这种界限显现在文本中,同样指涉文本以外作者的意图。为便于讨论,这里将抽象的空间清晰地分为侯门与市井、男性与女性、雅趣与俗情三个方面,但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方面,即雅俗文化界限设定的问题。
侯门贵族与市井之间的封闭是被普遍接受的,甚至于在贵族家庭内部,等级也如此明确、森严——这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在小说中,这种“阶级”之间的隔膜更具体地体现在“天香园绣”上。这绣艺最初由闵氏从娘家带来,闵氏是小家女子,绣艺虽精湛,却无诗心画意;还得要经小绸,读过的书和临过的元人小品才让绣品添了几分雅致。随后申家闺中绣艺渐渐声名外传,坊间竟有仿造之物,柯海为不污闺中女子清名,这才想到给园中绣品一个名号——“天香园绣”。在这里,侯门(闺阁)与市井之间的空间间隔被十分清晰地标出了。到希昭“绣画”,则使绣品失去了原本的实用价值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堪比书画,又另成一体;绣艺则是更进一层,几要惊为天人——且不说不容市井女儿染指,便是天香园中任一旁人,也无法达到这境界。“天香园绣”的生长过程,就如同采集于民间、又必要经过文人之手点染才可登上大雅之堂的诗歌一样,需要添上小绸与希昭等人的“一颗锦心”。更有甚者,在绣艺本身之外,“武陵绣史”沈希昭赋予绣工的仪式感更值得注意:“一个人,拉上幔子,事先多了一道洗手,再又焚上一支香。有几次,阿潜进到幔子里,与希昭说话,见她神情肃然,有一种虔敬。”*王安忆:《天香》,第235页。——这仿佛不是在作绣,而俨然一种修行。因而,“天香园绣”的高蹈姿态达到了顶峰;也正于此,侯门与市井之间的隔离似乎森然不可突破。
然而,天香园绣毕竟得以“外传”,从侯门大户走向市井女儿遍地开花于民间。究竟如何才能使已经高不可攀的“天香园绣”降下姿态?其实整个文本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此:前文所述种种都在为这一结果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些又还是不够,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申家自身也需要将绣品在市上沽售、用作稻粱谋——自然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虽仍有觅得知音才肯出售的意思——但渐渐也不以此愧怍难当。将绣品当成商品用以交换的商业行为,正具有打破不同阶层之间间隔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赋予“天香园绣”高蹈风范的希昭也能宽容、认可绣艺的外传,却是因为看到了民间的勃勃生机:“希昭想起天香园里的绣阁,早已成残壁断垣,荒草丛生,不想原来是移到坊间杂院,纡尊降贵,去尽丽华,但那一颗锦心犹在。”*王安忆:《天香》,第400页。这种来自市井中的生机,如前文提到的,在第三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实际上也早已伏线千里:在天香园建成不久,园中诸人即颇有兴致地模拟起集市;而阿昉则有模有样地在金龙四大王集庙会上经营起的“亨菽”豆腐店——这些园内人物文人化的市场活动,是明末上海民间市场活跃的一个反射,也使“天香园绣”进入市场成为顺势之举。在侯门与市井之间的隔离被打破的过程中,市场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过程,则最大程度地集中投射在“天香园绣”从贵族化到进入市场的叙述逻辑中。
(二)男性与女性
《天香》中的两性之间的心理空间同样存在显著的分野。小说中女性占据了叙事主体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叙事聚焦于女性人物,同时表现在女性人物对男性的排斥中。在形象设置上,小说一方面塑造了诸多英气的、有生命力的女性,另一方面男性形象却是不通人事、不解忧愁的申家男性,与慑于女性气势的、孱弱的张家男性。再者,小说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却显然未在男女爱情上过多落墨。相反,在男女之间总是有些“隔”:小绸与柯海虽有短暂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很快因闵女儿的到来而决裂,闵女儿在尴尬中更受冷遇;阿潜则不是希昭的“对手”,在蕙兰眼中,“婶婶和叔叔有些声色,可却不怎么像夫妻,而是像男人和男人,又有些像倒过来,叔叔是女,婶婶是男”*王安忆:《天香》,第289页。。再说蕙兰,丈夫张陛是个纸扎般的人儿,性情木然而冷淡,虽说有情却只是背地里嗅妻子的枕头。这些在小说中处于中心的女性人物,无一人拥有完美的婚姻;而相对照的,却是女性之间的心心相印:“我有意让她们结成闺密……第一卷里,小绸和镇海媳妇是至死不渝的一对……希昭多少曲高和寡,只一个蕙兰有些姐妹亲,却未必懂得自己,心中有着朦胧的偶像,比如小时候在杭州珠市上遇见的女子,显然是青楼中人,无法接近,只能存于想象中。现实中最懂自己的人是小绸,可不是有情绪吗?就像人们常说的冤家。蕙兰的闺密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我自己很得意,就是她的婆婆,夫人。”*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
在这部小说中,性别问题不仅仅是性别问题本身,而承载了文化含义。最初,女性人物在与男性相“隔”的同时,却表现出对男性文化的认同,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一个独特的人物——沈希昭身上:她虽说是女子,却是自小被当成男孩来养育,男性文化的熏陶赋予她英武之气,心性抱负非寻常女子可比。事实上,她不主动上绣阁,而独自在房中绣画,正是出于对于闺中女儿俗气的不屑一顾。希昭将绣艺理解为“以绣作画”,以针线比笔墨,也正暗示着她对男性文化的认同。正因有了这一前奏,希昭登上绣阁、在落款的“武陵绣史”下面添上“天香园绣”才别具意义。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性别认同。这种认同,并非因为希昭对自身女性身份的“屈从”,而是在对男性文化的失望与遗弃之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来自于阿潜的出走,更来自于小绸亲自登上西楠木楼的一番劝说:“人都道‘青衿之志’,其实无非是进官进禄,一旦不成,便怒气冲天,怪世道不均,君王不智,将自己比作菊啦,兰啦,梅啦,还有就是竹,总之,专找那些时令偏的草木作比,方才气平!其实,每一样草木都自有繁荣热闹,就说竹子,那竹根在地下盘桓交互,都能掀起一幢楼阁,哪是那么洁身自好的性子!”*王安忆:《天香》,第245页。
希昭这种性别认同的转变,同时也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而用希昭的转变将这种文化认同的曲折过程展示出来,则是为了显示出它相对于男性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独具的魅力。在这一象征逻辑中,女性人物成为新兴的经济因素,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的代表;而这一逻辑的具体表达则是,申家男性在家族败落之际表现出颓丧,甚至一如既往沉迷于精致的玩乐,而女性却能坚毅地承担起整个家族的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将女性与新兴的市场因素所代表的文化形态相联系的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与女性人物的边缘地位有关,但也与当代普遍接受的女性人物作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消费文化的代表这一观念一致。并且,当新一代的男性表现出对新的文化形态的认同时,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重新获得女性人物的情谊,例如蕙兰与叔叔阿暆之间的交往。
(三)雅趣与俗情
至此,我们发现贵族与市井之间的隔离被突破,而主要以女性承载的商业文化则意味着向俗文化的认同。但这种空间建构的工作并未止步于此。对《天香》中的雅俗问题已经有讨论,并且,皆倾向于认为其中具有以俗为雅的审美取向;作者也自云:“小说不是诗词赋,而是曲,它表现的是俗情”,这俗情是一种“兴致勃勃做人的劲头,永无倦意”。*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但实际上,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作者在写作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首先,对于申家人奢靡的生活方式,作者的态度就是不能统一的。一方面似乎是,“持盈保泰不是上海的本色。颓靡无罪,浮华有理,没有了世世代代败家散财的豪情壮举,怎么能造就日后的五光十色?”*王德威:《虚构与纪实:〈天香〉:王安忆的上海“考古学”》,《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天香园中传出“一夜莲花”、“香云雪”诸样奇闻,不断地扩建修缮园与宅,各样红白事等皆是“靠银子堆砌”,此外,多的是不避俗事的玩乐:园中设市、养蚕、开豆腐店,虽说并不真能盈利,却样样关涉着生计俗务。这些似乎的确在表达着同样的观念。但另一方面,申家的这些出格之举,在贵族中却并不普遍,而是因为申家根基短浅,虽富庶奢华、锦衣玉食却没有“渊源”——这似乎又是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表达对申家生活的责备;同时,申家的奢靡与败落,是在与质朴但独具生机的民间生活的对比中展开的,这同样诉说着与“认可”不大相同的另一种态度。
另一矛盾的态度表现在对“民间”本身的书写上。“民间”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交错着两种不同的观照方式。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得出在集市中活跃着的“民间”。这种民间生活方式的描写更多集中于场面的、器物的描写中,而对人事的描写却泛泛,这种偏向,自然联系着古典文学传统中相应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古典文学中对“民间”的理解却更突出地在小说中起着作用:白鹤村的章师傅、苏州闵家、鉴画的赵伙计等等,都代表了经过不同于前一种的目光过滤的民间生活,他们似乎更可以归于隐逸的黄老之流。这种审美态度也落实到申家男性对女性的审美上,他们的审美若有对正统的偏离,如荞麦、小桃、落苏诸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也是将其视为《诗经》“国风”的一派;小说中也特别提到柯海第一次见闵女儿的印象:“活脱是乐府诗的意境。”*王安忆:《天香》,第52页。这分明仍是古典意味的审美。
值得注意的是奎海这个人物的塑造。奎海是明世的庶子,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憨傻、愚昧又争强好胜的人,尽管并没有像《红楼梦》中的贾环那样心怀恶念,但一番胡作非为也给申家带来重创,助了申家败落的一臂之力。更重要的是,这事故中暴露出来的还有他审美能力的匮乏和附庸风雅的鄙俗——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已将俗与雅作了另外的区分,而并非混淆了俗雅之间的界限。在雅俗表现之间流露出的游移,则表明在重设界限中雅文化仍在起着关键的作用。由此可见,这更新的雅趣乃是自俗情中抽取的,标志的是一种雅文化的开放心态,但却不意味着雅俗不分。天香园绣从闺阁之物变成可供赏玩的风雅之物,是开放风气的产物。在雅俗之间,王安忆所做的是“以俗为雅”,将部分俗文化也厘定进入审美之维。前两部分始终存在着这界限的移动的标识,正是意图说服读者;第三部分告别了古典的诗美,而投入进这俗世的趣味中来,因而研究者认为第三卷相对于前两卷而言,因为回到了王安忆所擅长的“生计”问题而显得更加“从容”*胡晓:《〈天香〉:写回去与写上来》,《上海采风》2012第2期。。
如果此时再回过头去思考“天香园绣”从贵族家庭流向市井的过程,则有不同的发现。我们看到,申家渐渐家道中落以后,申家女眷出卖绣品的被迫情绪,因为觅得知音才肯出售而被淡化了;而希昭登门拜访蕙兰,感慨绣艺流入民间葆有的生机时,仍是保持着贵族的姿态;最重要的是,蕙兰设帐收徒,却有这样的考虑:“铁定心不嫁人,不出阁,一是免去滥传之虞,二也不至过于受生计之累,最终蹈入沽鬻衣食,弃道背义”,*王安忆:《天香》,第398页。也就是说,流入民间仍然意味着一定的限制,也正是在“民间”中重设边界。
(责任编辑:王学振)
Space Narration in Wang Anyi’sTianXiang
ZHENG Hao-yue
(SchoolofLiberalArts,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The space in the novel has been given increasing attention, thus providing lots of new ideas for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s narration. InTianXiang, the space refers to the space of entities like gardens, houses and Shanghai City, which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substantial space including the garden, the house and the Shanghai city,thu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 and expressing the grade isolation or its break. More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hai image suggests a pursuit of self-construal and self-expre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ace also refers to the abstract space. The novel suggests a kind of tolerance in aesthetic value, which indicates an attempt to rebuil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cular and elite cultures,instead of confusions between them.
Wang Anyi;TianXiang; space narration
2016-09-25
郑浩月(1992-),女,江苏泗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6)-12-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