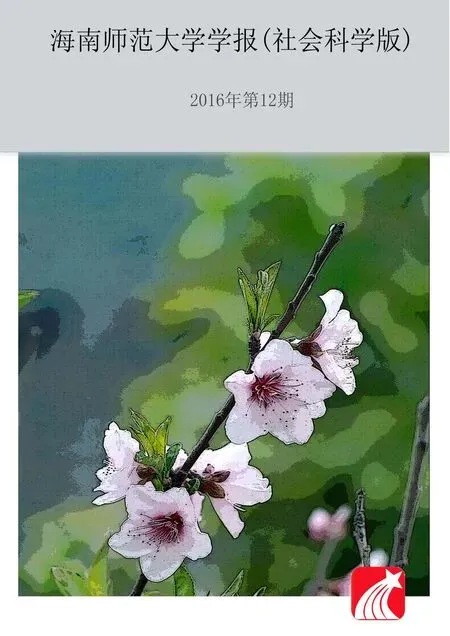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
2016-03-16王德领
王德领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011)
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
王德领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011)
对于乡村的书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如何表述城市,我们似乎没有准备好。我们看到的只是雷同化和类型化的城市,千篇一律的城市人。城市并没转化为作家的血肉,作家与城市,是疏离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带有模式化的弊端,很难看到有创意的个性化书写。这主要表现在伪小资化模式、欲望化模式、外来者与打工者模式、都市与乡村对照模式。近年来,一些作家的创作突破了对城市的这种固化认知,主要体现在:一、突出对城市的家园意识,展现城市的诗意与魅力;二、超越物质时代的表象,将都市重新意识形态化;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书写城市的“文化之维”。城市写作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文本,但仍存在着很大的缺憾,缺少哲学层面的透视,缺少俯瞰城市生活的精神高度。
新世纪;城市书写;模式化
一提到西方现代主义,我们总是用荒诞、异化等一套固定的词语来评述。若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题材划分,大多数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可以归为城市题材的范畴。西方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城市文明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城市,也有一套语汇诸如荒诞、异化、物欲、堕落等来表述。是城市提升了人类的文明,也是城市承载了人类的罪恶,城市介乎天堂和地狱之间,这几乎成了我们对城市的标准化认知。我们一直认为,波德莱尔的诗歌《恶之花》,就是隐喻了以巴黎等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罪孽。20世纪4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的开篇写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是中国作家对待城市的典型态度。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学对于城市,陷入了一个道德化评判的误区。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一个资本化的时代。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截止到2014年末,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4.77%。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两千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正跻身于世界发达城市的前列。北京与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给中国作家提出了新的表现课题。对于乡村的书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一大批经典文本,而如何表述城市,我们似乎没有准备好。在城市文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雷同化和类型化的城市、雷同化和类型化的城市人。庞大的城市并没转化为作家的血肉,作家与城市,是疏离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很难看到有创意的个性化书写。
一、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推土机和挖掘机如此轰隆隆昼夜不停地工作,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城市无所顾忌地扩张,财富像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在GDP至上的时代,一切仿佛都是在围着财富旋转,连梦想都是金色的。这种疯狂的造城运动,给中国人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暴力的拆迁、凶蛮的城管、汹涌进城的农民工……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在这个城市化进程中被迅速放大。而中国大多数作家尽管生活在城市,似乎还没有认真消化城市这个日新月异的庞然大物,还停留在西方文学对城市所持的批判与反思的旧模式中。这只是对城市的一种想象性的书写,是表面化、肤浅的。
城市不仅是建筑物的高大和街道的宽广,不仅是灯红酒绿和财富的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城市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城市里的人生是这个时代最为丰富和复杂的人生,城市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人,城市生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生活,体现了时代的病症、荣光与梦想。中西方现代城市在建筑样貌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对于21世纪中国的城市生活而言,如果我们的作家对待城市的立场,还停留在西方19世纪、20世纪对城市的表述上,显然是落伍了,我们需要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对于城市文明的书写方式。
遗憾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城市书写呈现模式化倾向。这种模式化,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伪“小资化”倾向
这是就人物塑造而言的。之所以加上一个“伪”字,是因为“小资”*小资在本文中是在属性词的意义上使用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小资指“有一定经济条件,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的”,例如“小资情调”、“小资生活”。这个词所具有的带有商业企图的做作和卖弄色彩。在50—70年代的阶级分属里,小资排在工农之后,带有贬义,是被改造的对象。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退隐,小资的涵义渐趋中性。90年代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小资一跃成为一个带有炫耀色彩的褒义词。而到了新世纪,小资身上的光环消失,被更加具有炫富意味的词汇,如“土豪”等所代替。从90年代以来,小资被作为一个带有炫耀性的热词,被一些“美女作家”频频使用。像70后的卫慧、棉棉,她们出道之初,就是凭借对城市小资的欲望化书写而成名。《上海宝贝》将时尚化、欲望化书写推向极致。小说将上海这个城市身体化、欲望化了。青春所推崇的所有的东西,在这里都齐备了:流行时尚、性、毒品、欲望,在这里,借助美女的身体、酒吧、世界顶级奢侈品等实现了。而80后文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她们不满足于卫慧、棉棉的“宅女”式写作,而是主动出击,不仅写青春文学,还办杂志、拍电影、经营文化传媒公司、建网站,深度介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像“超女”“中国好声音”一样,在文学艺术领域引领时尚文化。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也不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一代人在消费主义观念的驱动下,对这个资本化时代的最大迎合。尤其是郭敬明和韩寒,俨然已成为文化产业的弄潮儿了。这些“小时代”的文化产品,更像是这个消费时代所推崇的时尚商业广告,带有鲜明的迎合大众消费主义欲求的伪小资倾向,哪里还有什么真小资可言?
而真“小资”所推崇的,首先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生活方式。其次,小资追求内心体验,多半是文艺青年,具有独到的鉴赏眼光,不随波逐流。再次,小资不做清教徒,也不是苦行僧,对爱情敏感且易受伤害,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最后,小资喜欢流行文化,但不随波逐流,具有不俗的品味和眼光,可以引领大众风尚。可见,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小资”,内涵已经大大窄化,甚至庸俗化,已成为消费、欲望和金钱的代名词了。90年代以来小资的“去政治化”、“消费化”,使得“有主体自我的小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主体自我的小资产阶级”,“小资已经瓦解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在这种“消费化的小资”面前,“历史、道德、身体等等这些都失去其具体含义,变成一团混沌的消费物被小资拿来消费”*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77页。。作为时代文学的“症候”,如何拯救“小资”,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赋予“小资”以鲜明的主体性,使“小资”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不仅是80后作家,也是许多热衷于书写城市“小资”的作家需要认真思考的。
(二)欲望化模式
这是目前许多书写城市的小说最为常用的模式。这以邱华栋、刘震云、朱文等作家的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家的小说大量描绘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情感,着力塑造一系列都市意象,高档别墅、酒吧、夜总会、高档会所、摩天大厦等在作品中频繁出现,人成为消费者和被消费者;欲望,尤其是物欲,成为推动城市人生存的基本动力。欲望化、孤独、焦虑等,是这类作品所揭示的“都市人”的心理状态。邱华栋写了大量的北京人生存状态的小说,譬如《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电话人》《钟表人》《化学人》等“XX人系列”小说,以及60篇“社区人”系列小说。这些被称为“商业中产知识分子”的北京人,不是王朔笔下大院里的北京人,更不是老舍笔下胡同里的土著北京人,也不是叶广芩笔下的晚清贵族,而是富有当代新移民色彩的“北京人”。陈晓明对邱华栋的这类小说有过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述:“过去的小说家,不管是王朔还是其他任何作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0K舞厅酒吧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场、午夜的街道、囚笼一样的公寓……”*陈晓明:《邱华栋“社区人系列”小说:生活的绝对侧面》,《文艺报》2011年12月16日。这些城市外表,具有坚硬的物质外形,无一不指向都市人的内心,搅动城市人内心的欲望。欲望化模式的核心,是城市病理学*城市病理学是邱华栋在《我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病理学以及其它》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详见《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式的。邱华栋曾在《环境戏剧人》中说:“城市已经彻底改变与毁坏了我们,我们在城市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杀人犯,窥视狂,嗜恋金钱者,自恋的人和在路上的人。”这一论断,其实已经把城市人类型化了。这些城市人,往往沦为物欲的符号,灵魂是缺失的。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也打上了欲望化的烙印。《手机》中的人物和情节,都由欲望化来推进,由权力欲支配下的物欲、性欲等,形成了故事演进的基本动力。小说里的严守一这个成功男人,游走于一系列女人之间,生命中似乎仅剩下“力比多”了。这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21世纪的城市人,人性是否已经彻底异化了?在《我叫刘跃进》这部小说里,刘震云把北京写成了一个物欲极度膨胀的都市。刘跃进所联系的人物,都被物欲所控制,丰富的人性缩减成了物欲的私利。对城市生活进行欲望化书写的模式,迎合了这个唯物欲是瞻的时代,但是却没有写出灵魂的深,没有写出在物欲时代灵魂的挣扎。对都市欲望化书写的研究已比较深入,在此不再赘述。
(三)底层书写模式
表现城市底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表现外地打工者漂在城市的生活,是许多作家热衷表现的。在1949年至“文革”结束,“底层”是一个带有魅力的字眼,是光荣“身份”的象征,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优越性。90年代以来,在资本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底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仅指贫困乡村的农民,更指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这些城市贫民的成分比较复杂,由农民工、下岗工人、流浪者、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等组成。随着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急剧增加,表现城市底层生活的作品大量涌现,是90年代以来被称之为“底层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安忆、方方、陈应松、刘庆邦、荆永鸣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2013年发表后引起轰动,讲述的是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涂自强在武汉求学、打工、患病死亡的悲剧故事。特别是小说里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在一个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一个出身寒门的底层青年,无论如何进行生存的挣扎,只是徒自强而已。这是一个辛酸的故事,也是当今城市“蚁族”的真实写照。徐则臣的《跑步经过中关村》,荆永鸣的《外地人》《北京时间》《候鸟》,刘庆邦的《北京保姆》系列小说等,讲述的是“京漂”生活。特别是荆永鸣的小说,表现了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状态,是在以打工者的视角,描写老北京的生活故事。荆永鸣的叙述,更多地是展现一个外来者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类题材常见的“苦难叙事”模式。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打工者创作的表现城市底层生活的诗歌,给人以灵魂的悸动,不像那些书写底层的小说,总觉得和现实隔了一层。“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郑小琼的诗歌,具有灼热的现实体温,她的《在五金厂》《在电子厂》《女工记》等作品,表达了流水线生产对工人的“异化”,写出了底层工人所经受的非人的折磨和所经历的真实的痛楚,无疑对这个时代具有惊人的概括力量,具有令人震惊的深刻性。在《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郑小琼这样写道:
时间张开巨大的喙 明月在机台
生锈 它疲倦 发暗 混浊 内心的凶险
汩汩流动 身体的峭壁崩溃 泥土与碎石
时间的碎片 塞满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
混乱的潮水不跟随季节涨落 她坐于卡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这么快
老了 十年像水样流动……巨大的厌倦
在脑海中漂浮……多年来 她守着
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
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看着
苍白的青春 一路奔跑 从内陆乡村
到沿海工厂 一直到美国某个货架
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
卡在喉间 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
猛烈地咳嗽 工厂远处的开发区
绿色荔枝树被砍伐 身边的机器
颤抖……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 将自己
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在资本的驱使下,有多少像郑小琼这样的女工,埋头在东莞的工厂里,在流水线上和商品一起昼夜运转。青春是一场残酷的献祭,向资本的献祭。郑小琼在东莞的五金厂,发现了这个时代最为惨烈的诗意。
24岁在富士康工厂自杀的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写的第一首诗,就是《流水线上的雕塑》:
双手如同机器
不知疲倦地,抢,抢,抢
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
茧,渗血的伤
我都不曾发现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这样的诗歌,不仅仅是揭示工业文明对现代人的异化,还包含更为沉痛的现实体验。“异化”一词,在这些流水线上的诗人这里,已经是用血肉之躯进行献祭。资本的压榨,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四)都市与乡村对照模式
城市的急剧膨胀,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观,都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伦理、消费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在都市里进行“乡村记忆”写作的作家,越来越感到都市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怪物,潜伏在他们的作品里。许多从外地进京的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在作品中一再用城市做参照叙述自己的乡村记忆,这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叙事模式。在都市的对照与互渗中书写乡村,成为新世纪都市文学的重要主题。伴随着城市的崛起,乡村的凋敝成为不可避免,家园的荒芜、污染的河流和干涸的土地,以及蛮横的村霸、留守的儿童、候鸟一般的打工者,已经被许多作家反复吟唱。留住乡愁,似乎已成为一代作家的共识。
近年问世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林白的《北去来辞》等,都是在城乡对比中展开情节。
林白的《北去来辞》讲述了一个名字叫海红的南方文学女青年在北京的经历。小说以柳海红和史道良为核心,笔墨集中在两人的家族上,描写了柳青林、史慕芳、史银禾、王雨喜、陈青铜等众多人物的生活轨迹,时间跨度自建国后至新世纪的2010年,尤其是集中在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地点在湖北东部村镇和北京之间展开,在城与乡的交替叙事中,展现了宏阔的社会生活面。在林白的创作历程中,这是一部转型之作,由书写“个人经验”“女性生活”,转向以“个人经验”的视角书写“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城市经验和乡村生活,相互纠缠相互生成,共同阐释着这个时代。与此类小说普遍存在的不足相同,《北去来辞》城市与乡村的叙述存在着割裂感,二者并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作家难以在城与乡之间进行成功的切换。
以上的四种模式说明,中国作家对城市经验的书写,在表现内容上有类型化之嫌,所塑造的人物过于平面化,深陷在欲望化叙事里,对城市的想象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作家们显然缺乏处理复杂的城市经验的能力,即便那些带有救赎意识的作品,如余华的《第七天》,也有“新闻串烧”之嫌。虽然身在城市,作家离城市还很远。新世纪城市文学还缺乏可以称之为传世文学经典的文本,尤其是缺乏大气魄的、触及当代都市人灵魂的鸿篇巨制。
二、突破模式化的努力
如果仔细辨析新世纪以来的城市书写,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落窠臼,没有受到流行观念的影响,对城市生活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城市不是欲望化的代名词,也不是异化的发生地,更不是罪恶的渊薮,城市是我们赖以栖息的家园。正是有了这种家园感,我们对城市的书写才是自然的,真实的,才会有老舍的北京、池莉的武汉以及王安忆的上海。
具体说来,新世纪文学的城市书写,在突破模式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城市作为风景,展现城市的诗意与魅力
从《诗经》开始,我们在作品中反复叙述四季的轮回,描述大自然的万千繁响,用大自然来抒发我们内心的情愫,把自然万物作为人存在的风景来膜拜。而城市崛起之后,对自然的这种亲近感消失了,人失去了寄托情感的“风景”。特别是现代城市崛起以后,钢筋水泥铸就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千篇一律的黑色柏油街道无限延伸,人愈来愈远离自然。传统“风景”的消弭,造成了城市人的“焦虑感”、“压抑感”。这种焦虑感和压抑感,构成了对城市文化进行否定的心理基础。
如何消弭城市所带来的焦虑感和压抑感?关键在于在城市重新发现“风景”。我所谓的“风景”是一种现代“风景”,这是一个内涵复杂的词语。这个风景的涵义,不仅仅是大自然的,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道德、文化、情感,更不仅仅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谓的“风景之发现”,一言以蔽之,“风景”是一种家园感,一种归宿感。将城市作为“风景”,拥有一种家园感,进而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提炼出城市生活的现代诗意,这是城市文学的重要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发现王安忆的一些写上海的小说,如《长恨歌》《众声喧哗》等,就有一种特别可贵的家园感。《长恨歌》里的主人公王琦瑶,她的人生起伏固然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但是更是和上海水乳交融。在《长恨歌》里,王安忆更多地写到了弄堂,写到了上海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而在《众声喧哗》中,王安忆发现了上海的诗意。王安忆不急于对城市做道德判断,而是从声音的角度感受上海的魅力。这篇小说从本质上看是有关声音的,有人间的声音,有灵魂的声音,也有人性的声音,这些都汇聚在喧嚣的都市车水马龙的声音洪流里。小说里的“欧伯伯”与“保安”基本“沉默”,东北女人“六叶”,聒噪得可以,称得上“喧哗”,在沉默和喧哗的切变之间,一个城市的诗意被呈现出来。小说这样描写上海的马路:
欧伯伯方才发现,这条马路在夜晚里其实是相当繁忙的。来去几条车道,全是首尾相接的车阵,车前是白灯,车尾是红灯,转弯的黄灯一闪一闪,等待前面路口红灯转成绿灯。然后无声无息地流淌过去,寂静中升起一股喧哗。欧伯伯被震惊了,他凭着柜台,望着眼前壮观的一幕,简直是灯河啊,河面宽阔,对岸变得遥远而且莫测。
在别的作家一笔带过的马路,王安忆把它审美化了。很难想象,一个对城市没有家园感的作家,能够这么贴心贴肺地描写一条柏油马路上来回穿梭的汽车。作为一个城市的老居民,小说里的欧伯伯发现了上海的魅力。把马路上拥挤的汽车灯光比作河流,把马路两边的大楼比作河流的堤岸,欧伯伯把传统的自然风景和现代的城市风景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从而在繁华的都市拥有了一个异常宁静而强大的内心。
正是王安忆的这种对于都市的家园感,才使得她的文字和上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联系,说是血肉相连也不过分。王安忆在《众声喧哗》里这样写上海午后的阳光:
午后二三点时分的光线,令人想起过去的日子。太阳经过路南老公寓的山墙折射,收集了一些颗粒状的影,那是外壁涂层上的拉毛所形成的。过去的日光都是这样,毛茸茸的,有一种弹性。那时候,对面没有层峦叠嶂的高楼,天际线低矮而且平缓,路却是狭窄的,不像现在开拓得宽和直,所以就也会有开阔的错觉。汽车从街心开过去,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声听起来很远,比无声反显得静谧,这静谧也是过去的。静谧中的闲散与慵懒,又有些气闷,让人恍然,就不仅是过去的,似乎还是将来未来的,无论世道如何千变万化,都是沉底,要说这城市有丝毫的悠古心,就是它了。
钢筋水泥丛林中的阳光,以及汽车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声,在别的作家那里是被忽略的,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则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升华成一种特别的诗意。
而金宇澄的《繁花》,则描绘了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碎图。生活一如繁花,破碎,但艳丽,似锦。所谓的宏大叙事,与这些弄堂生活相比,显得苍白而没有肉感。迄今为止,这是最为接近都市日常生活的叙事。这样的都市书写,是将都市视为“家园”的叙事,骨子里透出对都市的爱。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爱意在当前的城市文学里,是极为稀少的。作家对于城市,更多的是呈现一种隔膜感、陌生感。从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对都市没有表达爱意的人,大都是被乡村记忆缠绕的异乡人、失根者、怀乡病患者。鲁迅、沈从文、莫言等作家比较典型。他们从外省到北京定居,在北京成名,但他们的笔一接触到北京,就变得生涩而笨拙了,远远不如像写自己的故乡那样游刃有余。他们在北京没有家园感,自然也就不会写好北京。
(二)超越物质时代的表象,对城市进行形而上的精神审视
在50—70年代文学里,城市是被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由于城市是工商业的集中地,是滋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温床,对城市的改造一直在进行,有关城市的文学,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城市文学一直背负着不能承受的意识形态之累。新时期以来,淡化意识形态,强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一直是作家们致力追求的。这样一来,有关城市的文学逐步演变成书写欲望化的文学,内容大多集中在都市情感、职场升迁、物欲膨胀等方面,缺乏宏大叙事,更缺乏形而上的精神高度。而一贯书写城市的作家宁肯是一个例外。他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城市生活作了形而上的审视,欲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他的《沉默之门》《天·藏》《三个三重奏》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视角,超越了庸常的物质表象,展现了城市的精神维度。《沉默之门》是对于80年代末期的北京的缓慢叙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规训与惩罚的精神命题,绵延其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内心的拷问,对时代的审视。里面反复出现的精神病院,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心结。《天·藏》有两个文本,显性文本写一位北京援藏的知识分子在西藏的故事,潜在文本是写经历了80年代末期洗礼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带有巨大的内心隐疼。小说一再追问的是:具有内伤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该如何通过重建主体性获取精神上的力量?小说的力量,就在这种追问中。《三个三重奏》将注意力放在对新世纪以来的现实的书写上。在这部小说中,知识分子是作为旁观者存在的。小说对权力带来的腐败进行了拷问,人性在这种拷问中逐步显露出狰狞的一面。面对城市,宁肯的小说,如一把异常锋利的尖刀,挑开这个时代浮躁的表面,直取最为核心的所在。宁肯将难得一见的硬度和力量,以90年代以来早已缺失的“主体性”书写城市,构建了当代城市写作的精神维度。
(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书写城市的“文化之维”
这是当代城市小说最具有潜力的增长点之一。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作家,如现代文学史上的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1980年代,随着城市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一些作家意识到了地域文化对于城市书写的独特意义。在寻根文学思潮中,刘心武的《钟鼓楼》、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作品,对北京的风土人情的叙述,令人耳目一新。9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地域文化因素得到加强,如叶广芩之于北京,王安忆之于上海,池莉之于武汉。女作家对当代城市,更容易找到归属感和家园感。城市性格,或者说城市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都在这些作家笔下有着精彩的呈现。就“京味”而言,叶广芩是继老舍之后,对于北京的书写最为成功的作家。叶广芩身为皇族后裔,她的书写带有挽歌特质。老舍的北京是平民的北京,胡同里的北京,而叶广芩的北京则是皇族的北京,她着力书写的,是曾经显赫一时的皇族骤变为平民过程中的坎坷、辛酸与无奈。她的长篇小说《采桑子》和《状元媒》,写得一唱三叹。她以自己的家族为主线,以急速变化的时代为背景,将人物的悲欢离合徐徐道来,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京味。这种老北京的味道,是当代写北京的其他作家难以追摹的。
需要指出的是,因笔者的阅读范围所限,以上对突破模式化书写的概括,还很不全面。我注意到,让人欣喜的是,还有一些作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述城市的视角,在他们的笔下,城市的面影不再那么千篇一律了,比如80后作家文珍对都市的书写,70后作家姬中宪对城市所作的社会学式透视,邓一光以深圳为样本对城市生活的思考,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城市写作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文本,如《长恨歌》《繁花》《采桑子》,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缺憾,即缺少哲学层面的大透视,缺少俯瞰城市生活的精神高度。即便是像宁肯这样具有哲理意识的作家,也难以逾越这一点。作家的写作止于现象,止于大众的悲欢离合,和大众贴得太紧,缺少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游荡者,缺少对大众的震惊体验。在城市里,人群是风景之所在,要像浪漫派作家对待自然风景一般审视大众。要有一个波西米亚人的眼光,在大众之中又疏离大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获得独特的都市体验,写出元气淋漓的城市文学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Stereotyped Trend in the Urban Writing of the New Century
WANG De-ling
(Teachers’College,BeijingUnionUniversity,Beijing100011,China)
We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rural writing, but we do not seem ready as to urban writing, for what is presented in urban writing is similar and categorized cities as well as stereotyped city-dwellers. As such, the city has not been translated into writers’ flesh and blood so that the writer and the city are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Urban writing in the new-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marked by its stereotyped trend, is short of the innovative individualized writing, as is manifest in the pseudo-petty bourgeois mode, the desire mode, the outsiders and migrant workers mode, and the mode of contrast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In recent years, some writers have broken through such a solidified cognition of the city in their literary writing, namely, highlighting the homel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city and demonstrating its poetic appeal and charm,delv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spect of the city by transcend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material era,and portray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Although urban writing has produced some important text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nd of the spiritual height overlooking the city life.
new century;the narration of the city;stereotype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都市经验的拓展与乡村记忆的重构——新世纪北京文学发展趋向研究”(项目编号:13WYB016);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计划人才资助项目“新世纪北京与上海文学中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2016-10-02
王德领(1970-),男,山东嘉祥人,文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6)-12-0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