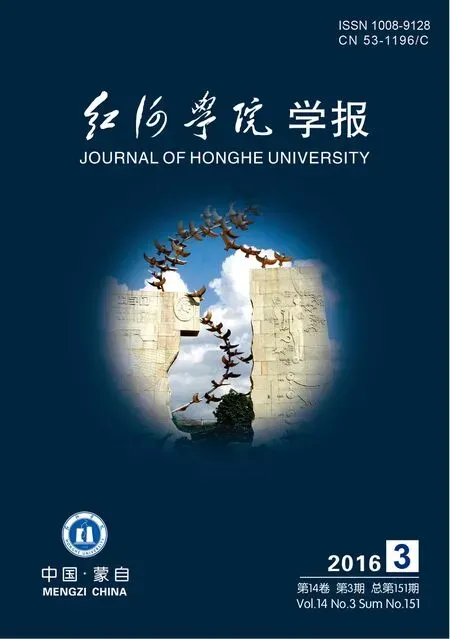津巴布韦文学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2016-03-16汪琳,方圆
汪 琳,方 圆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津巴布韦文学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汪琳,方圆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津巴布韦文学作为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绍纳语文学、恩德贝莱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三部分组成。其中,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发展更为丰富多彩,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萌芽期,20世纪50-70年代的成熟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独立后的繁荣期三个阶段。津巴布韦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对较少,以英语文学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后,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空白,直至21世纪初才又重新有所发展。总体来说,中国对津巴布韦文学的译介存在译介数量少、译介缺失、作家及作品名翻译未形成统一标准、专门研究性论文缺乏等特点。
关键词:津巴布韦;非洲文学;中国;译介;研究
第一作者:汪琳(1983-),女,浙江兰溪人,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非洲文学。
一 引言
津巴布韦共和国(Republic of Zimbabwe)位于非洲东南部,人口约1300万(2008年),其中黑人占总人口的99%,主要有绍纳族(Shona,占79%)和恩德贝莱族(Ndebele,占17%)两大民族。英语是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主要语言还有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津巴布韦有58%的人口信奉基督教,40%信奉地方宗教,1%信奉伊斯兰教。因宗教因素,津巴布韦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同时津巴布韦是艾滋病泛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津巴布韦于1980年宣布独立,独立前被称为罗得西亚(Rhodesia),更早前被称为南罗得西亚,是非洲南部重要的文明发源地。津巴布韦的殖民历史相对复杂。1888年它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1895年白人在此正式建立殖民国家,并用殖民者罗得斯的名字命名为南罗得西亚。直至1964年,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宣布组成以伊安·史密斯(Ian Smith)为首的罗得西亚阵线政府。1965年11月,该政府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管辖而独立,并于1970改名为“罗得西亚共和国”,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至此,长达15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境内黑人团体与白人政权不断地进行激烈的游击战争。最终,白人政府在各方压力下,被迫与津巴布韦境内诸多黑人势力低头。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宣布独立,由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出任政府总理,内战宣告结束,黑人赢得了国家政权。
津巴布韦文学在非洲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权威非洲经典作品名单“20世纪非洲百部最伟大的作品”中津巴布韦就占据5席,分别为查尔斯·蒙戈希(Charles Mungoshi, 1947-)的《修纳儿童故事集》(Stories from a Shona Childhood, 1989)、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Dambudzo Marechera, 1952-1987)的短篇故事集《饥饿之家》(The House of Hunger, 1978)、陈杰莱·霍夫(Chenjerai Hove,1956-2015)的小说《骨头》(Bones, 1988)、依温妮·维拉(Yvonne Vera, 1964-2005)的《蝴蝶在燃烧》(Butterfly Burning, 1998)和齐齐·丹格仁布格(Tsitsi Dangarembga, 1959-)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惴惴不安》(Nervous Conditions, 1988)。
二 津巴布韦文学发展
津巴布韦文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绍纳语文学、恩德贝莱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其中绍纳语文学和恩德贝莱语文学都有着绚烂多彩的口头文学,包括历史、神话与寓言故事、民间故事、谚语和诗歌等。20世纪之前,津巴布韦尚没有以民族文字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但当时以口头传说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已经很丰富。这些口头文学作品随后都被翻译整理,并发表于殖民统治时期出版的《土著事务局年鉴》(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Annual,Nada)①中。随着欧洲传教士的到来以及学校的出现,20世纪中期之后,以当地民族文字书写的津巴布韦作品逐渐增多。
(一)绍纳语文学
绍纳语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良好的发展。1953年南罗得西亚非洲文学局建立,提倡和鼓励出版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品。第一部用绍纳语写作的小说是所罗门·M·穆兹瓦伊罗(Solomon Mangwiro Mutswairo, 1924-)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费索》(Feso, 1957)。《费索》最初出版于1957年,当时正值英国殖民时期,其英译本出现于1974年。除了用绍纳语写作外,小说还带有些许政治色彩,并且融合了多种传统口头文化的特点,包括歌谣和故事讲述的技巧等。《费索》曾被广泛传阅,甚至出现在南罗得西亚的课堂上。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曾一度被罗得西亚政府列为禁书。第一本绍纳语诗作则出版于1958年,是由赫伯特·契提波(Herbert Chitepo, 1923-1975)创作的长诗《一个无头的故事》(1958)。这首诗的篇幅相当于一首史诗,表达了主人公想在混乱中探求精神意义。第一个绍纳语剧本《我以前警告过你》(1968)是由剧作家保罗·契迪奥斯库(Paul Chidyausiku, 1929-)创作完成的。它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戏剧,但内容上却是以传统主题为基础,取笑那些不能严守家庭秘密的妇女。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在政治和文学上都迎来了新气象,一些知名作家既使用英文也使用绍纳语进行创作,其中部分作品以绍纳的口头文学、传统故事和谚语等作为创作的基础,如查尔斯·蒙戈希的《修纳儿童故事集》,以及陈杰莱·霍夫的《大地的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Soil:Meeting Zimbabwe's Elders, 1996)等。
(二)恩德贝莱语文学
恩德贝莱语文学中传统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为早期的恩德贝莱语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第一部恩德贝莱语长篇小说是由恩达班宁尼·西索莱(Ndabaningi Sithole, 1922-2000)创作的《姆兹里卡兹的恩德贝莱人》(1956)。西索莱既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品中的政治色彩浓厚,以致罗得西亚的伊安·史密斯政权把这部小说列为禁书。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得西亚出现了长篇小说写作的高潮。这一时期小说的主题是社会性的,聚焦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困难,以及伴随而来的贫穷、失业和娼妓之类的问题。西瑟姆贝莱·O·姆里洛(S.O.Mlilo, 1924-1995)的《已经过时了》(1975)和《哈的兰纳的人们》(1977)、恩达贝辛莱·西戈戈(Ndabezinhle S.Sigogo, 1932-2006)的《世上无天国》(1971)和巴巴拉·马卡里萨(Barbara Makhalisa, 1949-)的《结婚》(1977)等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相较于小说而言,恩德贝莱语的诗歌与戏剧发展较为落后。诗歌方面未有影响力大的诗人出现,而在戏剧方面较为有名的分别是西戈戈的《谁是继承人?》(1976)以及马卡里萨的《什么世道》(1977)。前者表现了与传统生活有关的社会问题,后者则叙说了青年妇女在现代城市遭遇的苦难。新时期的津巴布韦恩德贝莱语文学著名人物有诗人阿尔伯特·尼亚蒂(Albert Nyathi,1962-),他以诗歌《你知道吗?》(Senzeni na?)而闻名。
(三)英语文学
不同于津巴布韦的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文学发展,津巴布韦的英语文学发展更加丰富多彩。它的英语文学可以分成两个使命感的潮流:一派歌颂欧洲征服所确立的各种事态,另一派抨击欧洲征服所确立的各种事态(克莱因 316)。津巴布韦的英语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888-1980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无论是1888-1965年的英国殖民时期、1965-1979年的内战岁月、还是1980年独立以后,其文学发展始终与政治情况、种族主义密不可分。此外,在津巴布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存在于津巴布韦的各种思想认知、宗教信仰和婚姻习俗等传统文化与逐渐渗透的西方文明相互碰撞,迸发出强劲的文学火花。
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这个时期的英语文学大多是白人的个人回忆录,记叙了欧洲征服的系列冒险故事,歌颂了欧洲征服所确立的各种事态。例如弗雷德里克·塞鲁斯(Frederick Selous, 1851-1917)的《罗得西亚的阳光与暴雨》(Sunshine and Storm in Rhodesia, 1896)和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 1857-1941)的《马塔贝莱战役》(The Matabele Campaign, 1897),以及后来查尔斯·布洛克(Charles Bullock, 1880-1952)颇具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里纳》(?, 1949)。这些故事包含了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适应了伊安·史密斯政权多年来国内宣传的需要。
20世纪50-70年代,津巴布韦英语文学步入成熟阶段。在50-60年代期间出现了一些由白人书写的以非洲为背景的故事。虽然这些作品中非洲人没真正起作用,但表现了白人殖民社会在二战以前、期间和以后逐渐衰败的情景(克莱因 317)。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诺贝尔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她虽然在去世时为英国国籍,但这位以非洲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女作家却在津巴布韦度过了其童年与青年时光。她1924年就随父亲移居到南罗得西亚,在那经历了两段婚姻后,于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她创作了以南罗得西亚为背景的系列故事——暴力的孩子系列(The 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分别为《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 1952)、《良缘》(A Proper Marriage, 1954)、《风暴的余波》(A Ripple from the Storm, 1958)、《壅域之内》(Landlocked,1965)和《四门城》(The Four-Gated City, 1969)。小说以诚实细腻的笔触和颇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写实风格,展示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玛莎的人生求索。此外,她以罗得西亚为背景写作的篇幅较短的小说被收录进了短篇故事集《非洲故事》(African Stories, 1964)。她还将自己访问津巴布韦的故事写入人物传记《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African Laughter:Four Visits to Zimbabwe,1992)中。
步入成熟期的津巴布韦英语文学并不局限于白人作家的作品,黑人作家们也开始用纸笔发出自己的声音。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一些黑人作家们以历史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对殖民制度批判、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为自身的文化身份而抗争的共同主题。如斯坦莱客·萨姆坎奇(Stanlake Samkange,1922-1988)的《我为我的国家受审》(On Trial for My Country, 1966)、《被哀悼者》(The Mourned One, 1975)和《起义的岁月》(Years of the Uprising,1978)。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尔逊·卡蒂约(Wilson Katiyo,1947-2003)的《大地的儿子》(A Son of the Soil, 1976)和《走向天堂》(Going to Heaven,1979)。而另一些黑人作家却用悲观的笔触道出了60-70年代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津巴布韦社会存在的文化弊病。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是查尔斯·蒙戈希、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和斯坦利·尼亚姆富古德札(Stanley Nyamfukudza, 1951-)。蒙戈希的故事集《旱季来临》(Coming of the Dry Season, 1972)和长篇小说《待雨》(Waiting for the Rain, 1975)聚焦传统的非洲家庭。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下,这些家庭的血缘关系纽带逐渐出现裂缝。马里契拉的短篇故事集《饥饿之家》用零散的情节和大胆的笔触写出了此时非洲社会的满目疮痍,并获得了英国卫报小说奖,更被评为20世纪非洲百部优秀作品之一。尼亚姆富古德札也在《不相信者的历程》(The Non-believer's Journey, 1980)中展现了西方殖民意识对非洲本土文化的致命冲击。
1980年对于津巴布韦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分水岭,更是其英语文学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标志。当被殖民制度残害和压迫了90多年的黑人们终于拿到了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奖杯时,过去严苛的文学审查制度也随之一扫而空,留给津巴布韦作家的是创作的极大自由。然而在独立后最初的五到六年里,津巴布韦英语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人们似乎过份沉浸于胜利带来的喜悦,而忽略了过去的惨痛和现实的困境。直至独立后的七、八年,才迎来了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真正的繁荣时期,一些黑人女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一时期文学主题主要为:1.国家独立初的混乱与破坏;2.对白人的驱赶;3.贫富悬殊与性别歧视;4.精神上的无所皈依;5.在西方文明和原始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张毅 95)。
20世纪80-90年代,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陈杰莱·霍夫,女作家依温妮·维拉和女作家齐齐·丹格仁布格。陈杰莱·霍夫致力于津巴布韦的文化复兴和人权进步,他的第一本英文小说《骨头》提升了他在国际文坛的知名度,为作家先后赢得了津巴布韦文学奖(1988)和非洲出版奖(1989)。通过一个普通农妇寻子的故事,《骨头》表现了内战时期复杂的阶层矛盾和严重的性别歧视。齐齐·丹格仁布格的《惴惴不安》则是首部由津巴布韦女性创作的作品,曾获1989年的英联邦作家奖,被誉为后殖民和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依温妮·维拉则是独立后最多产的女作家,擅长妇女伤痕小说写作,被冠以后殖民女权主义作家的称号。小说《无名》(Without a Name, 1994)、《无语》(Under the Tongue, 1996)、《蝴蝶在燃烧》和《石处女》(Stone Virgins, 2002)都展现了在动荡的津巴布韦社会中,妇女们虽笼罩于男权的阴影,身心倍受创伤,却仍坚忍不拔的品格。21世纪以来,值得关注的是两位黑人女作家佩蒂纳·加帕(Petina Gappah, 1971-)和诺维奥莉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 1981-)。佩蒂纳·加帕凭借短篇小说集《东区挽歌》(An Elegy for Easterly, 2009)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短名单,并获得了英国卫报首作奖,在全球多个国家译介发行。《东区挽歌》聚焦于一夫多妻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境遇,清晰描绘了21世纪津巴布韦各色人等魔幻般的人生悲剧。另一位女作家布拉瓦约则凭借《抵达布达佩斯》(Hitting Budapest, 2010)获得2011年度凯恩非洲文学奖(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而其小说处女作《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 2013)获得多个奖项,更是在2013年入围英国布克文学奖,使得布拉瓦约成为45年来首位入围提名的非洲黑人女性。该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津巴布韦女孩戴琳(Darling)移居美国底特律的故事。
相较于小说,津巴布韦的英语诗歌和戏剧发展更为缓慢。诗人中值得关注的是同为小说家的陈杰莱·霍夫。其代表诗作有《家园的红色山丘》(Red Hills of Home, 1985)和长篇诗作《尘埃中的彩虹》(Rainbows in the Dust, 1998)。前者表达了殖民统治时期其悲痛和苦难的心情,后者则表露出其对现实的不满。直到独立之后,津巴布韦的戏剧才有了真正的发展。斯蒂芬·齐凡伊斯(Stephen Chifunyise)是其中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选集《爱情良药等剧本选集》(Medicine for Love and Other Plays, 1984)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国内的社会问题。
三 津巴布韦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由于语言限制,中国对津巴布韦的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作品未有相应的翻译作品。
中国对津巴布韦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和津巴布韦政府于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独立当天正式建交,两国于1981年5月14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1982年夏季,根据两国文化协定,中国出版印刷代表团曾到津巴布韦共和国访问。次年夏末秋初,津巴布韦代表团也到我国访问,促成了津巴布韦战斗诗集《战旗》的翻译与出版。这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的《战旗(津巴布韦诗选)》分上下两辑,上辑专门收录1983年8月来我国访问的津巴布韦第一任总统卡南·巴纳纳创作的16首诗篇,下辑收录了津巴布韦当代诗人陈杰莱·霍夫、塞缪尔·吉姆索罗等人的29首作品。整本诗集都围绕“战斗”这一主题,但上辑诗歌中的政治性更加明显,“解放”“信仰”“国家”“自由”“团结”是16首诗中的高频词汇。诗歌中涉及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对殖民主义的痛恨,呼吁津巴布韦人民团结向前、奋起反抗,为国家尊严,为民族解放而战。而下辑中当代诗人的作品则更加具有文学性,运用多种意象,各种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更细致地描写了西方殖民者对黑人兄弟的压迫,表达了捍卫国家权力,打破奴隶枷锁,赢得自由、胜利和希望的渴望。此诗集由吴岩、吴劳、吴中一等16名翻译家翻译,翻译质量尚佳,但译本中也存在少数错字。
查尔斯·蒙戈希是80年代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津巴布韦作家。198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蒙戈希的长篇小说《待雨》,反映了非洲人民的真实生活。小说用近似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了佟古纳(父亲)与鲁希孚(儿子)等丰富的人物形象,着重表现了新旧两代人间因西方文明的侵蚀而造成的情感与观念上的分歧。蒙戈希笔下的人物似乎在这个充满西方文化侵蚀的非洲大陆上毫无抵抗能力。《待雨》一书由郑大民、文伊等4人共同翻译,译者在前言中表明,之所以翻译介绍《待雨》,是为了让我国读者能对当代非洲的社会状况以及人民生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过去一直被称作为‘黑大陆’的非洲,那儿的人民现在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对这块古老大陆的冲击使当地的人们的生活起了什么深刻的变化?”(蒙戈希 6)。1988年《世界文学》杂志第6期上刊登了查尔斯·蒙戈希(当时译为查·芒戈希)的两篇小说《乌鸦》和《墙上的影子》,由晨星翻译。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津巴布韦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现了些许断层,直至21世纪初才有了新的进展。2011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毅编写的《非洲英语文学》一书,于第五章简要地介绍了津巴布韦的历史和文学情况,并着重介绍了津巴布韦四位著名作家陈杰莱·霍夫,依温妮·维拉,齐齐·丹格仁布格和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的人物生平和著名作品,内容详尽充实。其中出现的书名与人名的翻译多数不同于1991年李永彩翻译的非洲文学专著《20世纪非洲文学》。如作家Stanlake Samkane分别被译为斯坦雷克·散康哥(张毅 95)和斯坦莱客·萨姆坎奇(克莱因 317),其作品《On Trial for My Country》分别译为《国家的考验》和《我为我的国家受审》,《Years of the Uprising》则被分别译为《揭竿而起》和《起义的岁月》。作家Wilson Katiyo分别被译为威尔森·卡提育和威尔逊·卡蒂约,其作品《A Son of the Soil》译名为《土地之子》和《大地的儿子》。Dambudzo Marechera分别被译为丹布佐·马瑞彻拉和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作品《The House of Hunger》译名为《饥饿之所》和《饥饿之家》等。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佩蒂纳·加帕的短篇小说文集《东区挽歌》,隶属于王安忆主编的短经典系列丛书。此书收录了《听,最后一声军号》《东区挽歌》等13篇短篇小说,聚焦于一夫多妻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境遇,文风幽默讽刺更含悲悯情怀。201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录了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书中译为丹布佐·马雷切拉)的《原生生物》和当代作家丹尼尔·曼德肖纳(Daniel Mandishona, 1959-)的《荒芜之地》。曼德肖纳的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著有短篇小说集《白色的神,黑色的魔鬼》(White Gods, Black Demons, 2009),其作品集中关注津巴布韦的社会与生活。
津巴布韦文学在中国的研究表现得较为贫乏,在研究性论文和相关文艺动态中只能见到零星几位作家的身影。相较而言,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是中国学者比较偏爱的研究对象。马里契拉是津巴布韦最具争议的后殖民主义小说作家,被称为“非洲的乔伊斯”或“非洲的坏小孩”。他的写作风格一如他的性格大胆反叛,著有短篇故事集《饥饿之家》(1978),长篇小说《黑色的阳光》(Black Sunlight, 1980),文集《心灵爆震》(Mindblast,1984)。1987年马里契拉死于艾滋病引起的肺部衰竭,后人整理出版了其遗作《黑色的局内人》(The Black Insider,1990)和诗集《心灵之墓》(Cemetery of Mind,1994)。1984年《外国文学研究》在第1期刊登了白锡堃编译自西德《宇宙》杂志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文中提到了达布姆佐在其作品《饥饿之家》中,对于“人们企图把欧洲文学传统中的‘殖民’观点传授给非欧洲人(140)”这一观点的看法:“我在读大学时很晚才发现,除了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鲜明的‘人类学’小说之外,我竭力对象吉卜龄、福克纳、康拉德、沙士比亚(《奥赛罗》《暴风雨》)等人加给我们的这些污点采取‘客观的’态度,但这种努力除却给我留下郁结的不快之外毫无结果”(140)。2008年《当代外国文学》第3期中,罗世平的《后殖民小说与主体性》中提到“查尔斯·蒙戈希的小说《待雨》中的卢希法(Lucifer)、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的《饥饿之家》中的叙述者等都受过西方殖民教育而以不同的方式疏离了本土传统文化和生活”(36)。同年11月25日,此文又被刊登在《国外文学》上。《文艺报》在2014年1月3日刊登的韩继坤的简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文学中的非洲》中提到了非洲文学的创作特点。非洲文学在创作上并非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会积极尝试外来的各种创作手法。例如在马里契拉的《原生生物》中则可以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中国学者对津巴布韦的女作家也有部分研究。后殖民女权主义作家齐齐·丹格仁布格也在《后殖民小说与主体性》一文中被提及。文章描写了丹格仁布格(文中译为慈慈·丹格姆芭卡)的小说《惴惴不安》(文中译为《神经症状》)中由主人公苔布(Tambu)体现的对西方教育和文化的推崇。2014年《中国图书评论》第1期中,郑春光、钟娟的《奇异的海岸:最期待议成中文的十部小说》一文介绍了其《惴惴不安》一书。此外,2013年《外国文学动态》第6期中,胡朗在《两位非洲裔女作家出版新作》中提到了津巴布韦新晋女作家诺维奥莉特·布拉瓦约。文章简要地介绍了布拉瓦约的背景和作品。
由于我国对津巴布韦文学的研究较少、译介相对不成熟,以致专有名词的翻译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标准。这一情况在上述译作、研究性论文、相关文艺动态等中得以体现——我国对津巴布韦作家和部分作品名字翻译相对混乱。如:Dambudzo Marechera的译名有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达姆布左·马莱谢拉、丹布佐·马瑞彻拉、丹布佐·马雷切拉等。作品Nervous Conditions曾被翻译为《惴惴不安》《不安之地》和《神经症状》。女作家Tsitsi Dangarembga的译名有齐齐·丹格仁布格、慈慈·丹格姆芭卡、琪琪·丹格兰娃等。
四 结语
总体而言,津巴布韦文学在国内的译介相对较少,可以表现为:1.相对其它非洲文学,如南非文学,翻译的文学作品较少;2.译介缺失,如达姆布达佐·马里契拉、陈杰莱·霍夫、黑人女作家依温妮·维拉和齐齐·丹格仁布格等重要作家的作品尚未译成中文。位列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名单的5部作品也未有中文译本;3.作家和部分作品名字翻译相对混乱,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标准;4.未有专门针对津巴布韦文学和相应作家的专门研究性论文。有涉及到津巴布韦作家作品的论文大多是为了主题需要,用此作家的相应作品作为佐证,而非具体分析这个作家的作品和风格。新时代的今天,我国同津巴布韦的经济交流愈发密切,然而在文化交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译介上发展缓慢,亟需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
注释:
①《土著事务部年鉴》是一份1923-1980年间由官方出版的定期年刊。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集中在根据多种口头传说翻译、加工整理出来的涉及历史、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当地风情习俗等方面的文章。1964年,该期刊正式更名为《内政部年鉴》(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nual),但原期刊缩写Nada习惯上一直被人们沿用。
参考文献:
[1]African Oral Tradition, History, & Literature[EB/OL].[2015-09-15].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http://library.columbia.edu/subject-guides/africa/subjects/othl.html.
[2]Rino Zhuwarara.Zimbabwean Cultural Malaise of the 1960s and '70s[EB/OL].[2015-9-15].University of Zimbabwe.http://www.postcolonialweb.org/zimbabwe/miscauthors/rz3.html.
[3]陈玉来.列国志 津巴布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0-296.
[4]克莱因.20世纪非洲文学[M].李永彩,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316-323.
[5]张毅.非洲英语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94-108.
[6]巴纳纳.战旗:津巴布韦诗选[M].吴岩,等译.上海:上海译文版社,1984.
[7]蒙戈希.待雨[M].郑大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版社,1986.
[8]加帕.东区挽歌[M].贺晚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9]白锡堃.关于“第三世界”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1984(1):139-140.
[10]罗世平,刘德刚.后殖民小说与主体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8(3):35-36.
[11]韩继坤.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文学中的非洲[N].文艺报,2014-01-03(004).
[12]郑春光,钟娟.奇异的海岸:最期待议成中文的十部小说[J].中国图书评论,2014(1):114-118.
[13]胡朗.两位非洲裔女作家出版新作[J].外国文学动态,2013(6):18.
[责任编辑 张灿邦]
Zimbabwe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China
WANG Lin, FANG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Zimbabwe literature consists of Shona literature, Ndebel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frican literature.Among these three parts, English literature experiences a more splendid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embryo (late 19th century-early 20th century), the maturity (1950s-1970s), and the boom (1980s-).Compared with other foreign literature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Zimbabwe literature in China are fewer, and mostly in English.The first introd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in 1980s and then it goes through a blank period, and the translation hasn’t developed until the early 21th century.To sum up,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Zimbabwe literature contain some typical demerits like tiny number of translations, lack of introduction, no authority standards of authors’ names as well as their works, and short of research papers.
Key words:Zimbabwe;African literature;China;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Research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6)03-0075-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3.020
收稿日期:2015-12-21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自设资助项目(FYZS20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