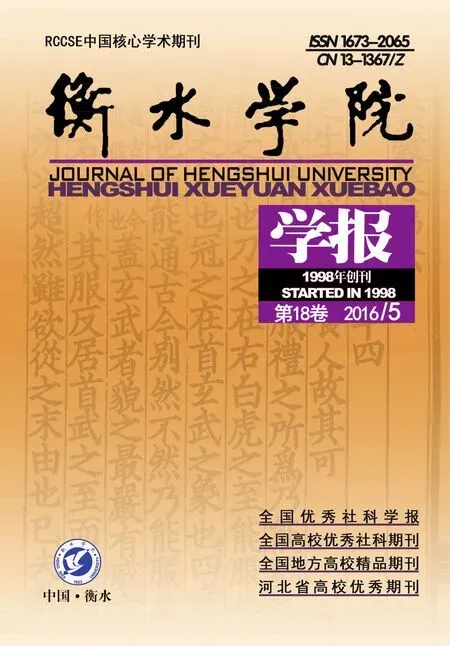“大道和生学”视阈下的“德与美”*
2016-03-15钱耕森
钱 耕 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大道和生学”视阈下的“德与美”*
钱 耕 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德‛与‚美‛,是中国哲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也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真‛‚善‛‚美‛,是中国人人生追求的最大价值与最高理想。而讲究‚德‛与‚美‛,是实现这个崇高目标和追求所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毫无疑问,我们对‚德‛与‚美‛可以从多角度进行传承与弘扬以及诠释与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中国很早就广泛地将‚美‛与‚德‛联用,称之为‚美德‛,即美好的品德。孔子论‚从政‛条件时所说的‚尊五美,屏四恶‛,即要推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行。中国以拥有历史悠久的‚中华美德‛而闻名于世。以‚大道和生学‛视阈观照‚中华美德‛中的‚德‛与‚和‛之内在联系,可以看到:《周礼》把‚和‛明确列为‚六德‛之一;董仲舒说,‚夫德莫大于和‛;‚和实生物‛,和也可生德,和可以补充德,使德更完美;‚和和美美‛,乃中国民间爱说的一句吉言,等。
中国哲学;大道和生学;‚德‛;‚美‛;‚和‛
一
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为“圣人”,理想社会是构建“大同社会”。中国道家的理想人格也是成为“圣人”(其内涵有别于儒家),理想社会是构建“小国寡民”与“至德之世”。中国儒家与道家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具体内容虽大相径庭,但是都具有“真、善、美”的本质与境界。所以,二者也都具有“德”与“美”的特色。
儒家所谓“圣人”,指具有最高美德的人而言。孟子论众圣时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这意思是说:伯夷是圣人中以清高自恃的人;伊尹是圣人中特别富于责任感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比较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能相机行事的人。孔子可说是集大成的了。可见,伯夷、伊尹、柳下惠,特别是孔子之所以被誉为圣人,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各自的最高道德品质。儒家古典文献中多用以泛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道家所谓“圣人”,老子最早谈到。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意思是说:所以,“圣人”是用“无为”的态度去处理事情,用“不言”的方式去进行教导,当万物生长时,他不为其开始,当万物生成时,他不据为己有,他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功成了而不自居。正因为他不居功,所以他的功劳反而不会丧失。可见,老子所称赞的“圣人”同样也是具有最高美德的人。
“大同社会”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迭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意思是说:“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的是信谊,所修习的是亲睦。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是爱抚自己的子女,要让老年人有归宿,壮年人有用处,幼年人能得到抚育,男子老了没有妻子的、女子老了没有丈夫的、幼儿无父的、老人无子的以及残废的人,都有地方瞻养。男人有职业,女子有好的家庭。货财,怕的是抛弃在地上不用,不必要归自己收藏起来;劳力,怕的是没法贡献出来,不必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堵塞住,不会兴起,盗贼作乱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连外面的大门也用不着关上。这就叫做‘大同’。”显然,儒家的“大同社会”,既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又是精神极大丰富的社会;既是最和谐的社会,又是最道德的社会。诚可谓美德蔚然成风!在美德的基础上,中国能成为一人,天下能成为一家①。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构建“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80章)这意思是说:国家要小,人口要少。即使有很多种的器具,也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和车,但没有必要去乘坐它们;虽然有铠甲和武噐,但没有必要陈列它们。使人民回到古代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让人民吃到美食,穿到美服,住得安逸,习俗快乐。邻国之间,彼此可以看得见,听得鸡叫狗吠,但人民从生到死都不相往来。在老子的理想国里,除了“结绳记事”和“老死不相往来”,令人颇为费解以外,其余的,特别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无疑是很道德的!很幸福的!很美好的!
“至德之世”,是庄子的理想社会。庄子说:“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遊,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又说:“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庄子·马蹄》)这意思是说:“所以,在道徳最高尚的时代,人民的行为悠闲稳重,人民的心地质朴纯真。那时,山中没有小路和通道,水上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众生,比邻而居;禽兽众多,草木滋长。因而,可以随意牵着禽兽遊玩,可以任意爬上树窥视鸟巢。在道徳最高尚的时代,可与鸟兽同居,可与万物共处。哪里还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呢!面对这种区别,大家都是无知的,只要人的本性不丧失,大家都是无欲的,这就叫做纯朴。纯朴就能保持人的本性。”庄子又说:“在传说中上古帝王赫胥氏的时代,人民安居而无所为,悠遊而无所往,口含食物而嬉戏,挺胸饱腹而熬遊,人民意态安然自适如此。”庄子把自己的理想国称之为“至德之世”,充分表明了庄子对最高尚的道德是极其崇尚的。而庄子的“至德”养成于并体现于“和”“和谐”。
所以,在庄子的理想国里,人的身与心是很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并无处于上流的君子与处于低层的小人的区分,而是很平等的,是很和谐的。不仅如此,人与动物也是很和谐的,和谐到了人与禽兽竟然可以同欢乐!这就完全实现了庄子所追求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最高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最高的和谐境界,难道不正是当前全人类所竭力追求的生态文明的新的历史时代吗?
二
“礼”文化存在于周代,也存在于夏、商二代。否则,孔子就不会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但以周代,特别是以西周为主。周公是三代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他为西周制礼作乐,开创了三代的鼎盛时期,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儒家称周公为制礼作乐的圣人。礼乐的主要功能,既是制度的,也是德性的。礼乐的最大价值就是实现人文化成。但是,到了孔子之时,已经是“礼坏乐崩”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孔子为了挽救“礼坏乐崩”的局面,提出了“仁”的理念。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渊问他什么是“仁”?他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又问实行仁德有哪些具体的条目?他又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可见,孔子是为了维持并加强礼对人们的视、听、言、动的行为的制约,才提出了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仁”。“仁”源出“予仁若考。”(《尚书·金滕》)(“若”当作“而”,音近借用。“考”当作“巧”,古时二者通用)指一种好品德,即我有孝敬的仁德。孔子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它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爱人”是“仁”的核心。
孔子及其弟子为了挽救“礼坏乐崩”的局面,又提出了“和”的理念。他的又一高足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本来是通过分别尊卑贵贱与远近亲疏的责任与权利,以维持稳定与和谐的秩序。但是,往往被统治者与既得利益集团强化了甚至僵化了统治的秩序,从而影响了甚至破坏了稳定与和谐。所以,有子就提出了应用礼的时侯,应该以和谐为可贵。他并以历史上的成功的经验来作证。“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以前的圣明君王治国理政的方法,这一条做得很好,无论小事大事都按这一条去做。有子以和补充礼,所提出的“和为贵”的理念,既具有理论的历史意义,又具有实践的现实意义。
“和”,不仅是方法,而且是道德。《周礼·地官·大司徒》(周代称作地官大司徒,为六官之一,负责以礼教导人民)记载以乡学的三种教法来教化万民时,所采取的第一种教法就是“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和”,被明确列为“六德”之一。又说:“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即以乐礼教民和睦,那人民就不会乖戾。“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即以六乐节制人民的情欲,教导他们心地平和。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论述“中和”时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董仲舒在这里,不仅也把“和”视为“德”,而且还把“和”视为“最大的德”,因为“和”“能生成天地”;“和”比“中”更为重要,“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故曰和其要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和”既然“能生成天地”,那末“和”,就不仅是方法,是道德,而且还是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发展的动因了,是形而上的大道了。而这滥觞于史伯与老子的思想,笔者特称之为“大道和生学”。
三
史伯的生卒年月不详。他是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公元前781-前771年)的太史,又称左史,为史官与历官之长。周幽王是臭名昭著的昏君,他为了引诱宠妃褒姒一笑,竟然上演了一折“烽火戏诸侯”的恶作剧。社会危机四伏,亡国之日危在旦夕。公元前774年,周幽王任命郑桓公为专管教化的大司徒。郑桓公与史伯讨论国家前途命运之时,史伯预言周朝必亡。果然,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西戎和缯国一举灭了西周,杀死了周幽王。
史伯判断的根据是周幽王用人时采用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原则,只与那些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人朋比为奸,排斥异己的正人君子,大搞党同伐异。史伯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应该用那些虽与己意相左但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即采用“去同而取和”的正确原则。被称之为“和同之辨”。史伯开创的“和同之辨”,产生了深远影响。二百多年后的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的名言,显然是受了史伯的影响,以“和同之辨”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史伯不仅是一位很明智的政冶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很智慧的哲学家。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意思是说:和确实能生物,同则不能生物。不同的东西(即他、他……)在互动中达到平衡就称之为和,和了就能生产万物;而以相同的东西与相同的东西相加,达到了顶点,就要失败。例子俯拾即是,诸如:孤男寡女是生不出小孩子的,健康的男女婚配后才可以生出小孩。种植单一品种的马铃薯,年年退化减产,到了一定的年头只好弃而不用。种植杂交稻,年年增产丰收,乐意不断加以改进。可见,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史伯所说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事实,是真理。
但是,“和”为什么“能生物”呢?史伯认为“和”之所以“能生物”,首先就在于“和”与“同”不一样,“同”只是单一的,只能自我重复,而了无新意!但“和”则是多元的,“他”与“他”是相异的;其次就在于相异的“他”与“他”之间一定会发生互动,并且当互动达到“平”“平衡”,即“和”“和谐”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出既源于“他”与“他”,而又不同于原有的“他”与“他”的新事物。
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之中的“他”字,是指彼此本不相同的事物、相异的事物不得少于两个。如果少于两个,就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岂不就还是自我同一吗?而“同则不继”,相同的东西再多也不会产生新事物,如以水济水,再多还是水,仍然变不成新事物(质量互变的辩证法,史伯并不知之,这需另当别论)。所以,“两个他”是以“和”构成新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下限。至于以“和”构成新事物所需要的他的数量的上限,则不封顶,多多亦善,才能产生新事物,不断产生万物。
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之中的“平”字,一般论者把它解读为“平衡”一义,笔者认同并补充“平等”与“公平”两义。这样,就将一个“平”,诠释为三个“平”,即“平等”“公平”“平衡”。
例如: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子(公元前?-前500年)所举“和羮”,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厨师要调制成一份广受众口欢迎的美味的鲜汤——“和羮”,既要有鸡、鱼、肉、蛋等主料,又要有油、盐、酱、醋等佐料,还要有水、火等资源。在厨师调制成和羮之前,这些原材料,都是各自的“他”。而和羮正是由这些“他”“平等”地参与而成,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例如:“三鲜汤”,就不能少于三种材料(即三个他);中药“六味地黄丸”,就不能少于六种材料(即六个他)。这是其一。
其二,厨师在调制的过程中,这些“他”,都把各自所固有的味道尽量地释放出来。这就意味着各自的“他”“公平”地行使了自身的权利,在公平的竞争中,大家都能做到物尽其用。
其三,厨师则一定要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同味道调匀,某味过了,就减少点,某味不及了,就增加点,达到最高度的“平衡”,要调到恰到好处,能受到众口的称赞。而所谓“调匀”“恰到好处”,决不是只要把各自的“他”“放”到一起,“合”在一处,“混”到一块……,就能得到的,而是一定要由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甚至很智慧的厨师,精益求精地反复去调制,去“平”“平衡”才能做出来一种全新的美味可口的浓汤。
可见,“和羮”的美味,经过上述的“平等”“公平”“平衡”的三阶段的“平”“平衡”化,即“和”“和谐”化,则既不失去各种材料自身的“他”所固有的独特的原味,但是又决不等于各自的“他”的那一种味道,而是能使各自的“他”的味道互相渗透,融合成为一种崭新的美味可口的浓浓的鲜汤。而其中的关键,无疑则是厨师的“平”“平衡”的功夫了。换而言之,也就是“和”“和谐”的功夫了。所以,这种美味可口的汤,就被冠之以“和羮”之美名。如此这般鲜美的羹汤,原来是“和生”出来的。
以上是传统的例子。我再补充一个新例子:“联合国”应成为世界各有关国家的和谐统一体。世界各国,只要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愿意遵守联合国章程,就可以要求参加联合国。各国参加联合国的条件,应该是不分大小、贫富、历史长短、种族、民族、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等的差异,而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提出议案、参与辩论、付诸表决的,无论是投赞成票,或者是投反对票,还是投弃权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该是完全“公平”的,大家都是一票制,大家都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联合国所形成的决议,总是要以兼顾各成员国的,至少是多数成员国的意愿,即使做不到绝对“平衡”,也要尽量做到最大限度的“平衡”,至少是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必须以此为前提与基础。否则,决议难以形成,更难以执行。
世界各国,换言之,就是世界各“他”国。世界上的“他”国与“他”国,如果能认真地做到上述的“平等”“公平”“平衡”的三阶段的“平”“平衡”化,即“和”“和谐”化,则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联合国就大有希望了。
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乃是联合国的宗旨与口号。而联合国的这一理念与史伯的“和生”的理念,显然是相通的。二者都主张以和、和平、和谐的方式去谋求发生与发展、可持续发展,反对以斗、暴力、战争去解决问题。
史伯的“夫和实生物”的新理念与“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新判断,充分表示他明确主张“和”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与发展的动力。他在宇宙万物的本体论与生成论的形而上的问题上构建了新的哲学体系。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首创,而且也遥遥领先于西方哲学。古希腊毕泰戈拉学派也大力提倡“和谐”。他们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这种观点与本文的立意是相通的。)又说:“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结论则是“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1]。但是,该学派的创始人毕泰戈拉(又译作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他的鼎盛年在公元前532-前529年(一说约在公元前532-前531年)[2]。而史伯于公元前774-前771年就已提出了“和”的哲学体系,比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的哲学思想要早二百多年。
史伯关于“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和”所下的定义。这是中国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中国和文化史始于五千年前的中华民族诞生之日的轩辕皇帝的“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但是直到公元前7世纪的史伯之前尚无人对“和”下过界定。
由于史伯关于“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定义,深刻揭示了“和”的两个最主要的本质属性,即“多元性”与“平衡性”,所以它非常精当,十分丰富,极其智慧,成了历久弥新的经典性的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晌。
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就受到了史伯的“和生万物”说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只要一说到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大家很快就会背诵出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的很形象、很生动的名言,以为这就是老子的“道生万物”说了。这样说,没错,但不全面,也不深刻。因为,老子紧接着这句话之后,还说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更精彩的话。前一句只是从数量的增加来说明“道生万物”的,体现了老子所说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70章)的通俗面。但是,“道”究竟是怎样生出万物的呢?老子在后一句话里,从道产生万物的内在结构及其规律进行了诠译。万物中的任何一物,都是“阴气”与“阳气”二者共同构成的。阴阳二气各异,并不断互动,即“相冲”,可称之谓“冲气”。当阴阳二气相冲达到“和”,即“和气”时,新生事物就瓜熟蒂落产生出来了。中国有句众所周知的谚语“和气生财”,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财富是万物中很重要的一物。和气既然能生出财富,当然也就可以生出其他的东西,直至生出万物。老子如此从万物的内在的阴阳结构及其不断“相冲”,并达到“和”“和气”时,就能生物,来揭示“道生万物”的内在规律,用以说明“道生万物”说,充分体现了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1章)的精深面。至此,一言以蔽之,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即“和生万物”说,史伯早在二百多年之前,就已说过了。所以说,史伯乃是老子和孔子的先驱。但是,老子在传承史伯的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发展。老子的创造性主要在于:
1) 把“道”引进来了,而“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因为它是“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最大的形而上的理念[3];
2) 把“阴阳二气”引进来了:“万物负阴而抱阳”;
3) 把“冲”与“气”结合起来了:“冲气”;
4) 把“和”与“气”结合起来了:“冲气以为和”;
5) 把经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上升到理性的“冲气以为和”;
6) 把具体的现实的“和生万物”说,提到了抽象的哲理的“道生万物”说的高度。
总之,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则建立了“和生学”。并且,老子后来居上,超越性地创新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并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形而上的体系——“道生万物”说,笔者则打通二者,并明确称之为“大道和生学”。
史伯和老子共同创立的“和生”说、“道生”说以及笔者构建的“大道和生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疑也是我们构建生态和谐、世态和谐、心态和谐,以及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资源。
四
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哲学中,把“德”与“美”,以及“和”与“和生”加以贯通,予以联用,不断创新,蔚然成风。
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于80岁那年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它的主要内涵与基本精神则是:第一句话,肯定了不同的文明各有其长,而不应该自以为是,排斥异己,唯我独尊,不能认为我是优等的,视他人是落后的、劣等的,而是不同的文明都可以“各美其美”;第二句话,要虚心学习不同的文明之长,因此不同的文明都应该“美人之美”;第三句话,不同的文明之长,应该是“和生”,即相互和谐共生,而不是彼此对立、冲突,因此不同的文明都应该“美美与共”;第四句话,不同的文明,都能切实做到前面的三点,则各国的和谐社会与全人类的和谐世界就能构成,则儒家所追求的以“天下为公”的最高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天下大同”的境界就会实现。
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4]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首先“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制定长期战略、采取有效措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以达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目标[4]。
我们同时又正在努力建设“美好家园”。我们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方面,努力做到“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我们对中华美德现代转化与传承,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5]他又说:“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5]
注 释:
①《礼记·礼运》原文为:‚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36-37.
[2]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47.
[3] 金岳霖.金岳霖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09(1).
[5]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05(1).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Virtue and Beauty in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QIAN Gengsen
(Philosophy Department, A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virtue” and “beauty”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and Chinese thingking and culture.“truth”,“goodness”and the “beauty” are the best value and the highest idea of Chinese life persuit. Paying attention to“virtue” and “beauty” is the indispensible segment。Undoubtedly, we can inherit, develop and interpret “virtue” and“beauty” from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is that “beauty” and “virtue” have long been used together in china since the ancient time to be called “meide”,that is ,the fine virtue.Confucius called “respect of five beauties and rejection of four evils”when he talked about the qualifications of entering politics. China has been known for her long history” “Chinese fine virtue”. In examining the inner link between “virtue” and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 in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the fact that “harmony” in Zhou Li is definitely listed as one of the “six virtues”, the idea of Shi Bo who considers everything is derived from the state of harmony and the theory of Dong Zhongshu who thinks that one's greatest “virtue” is “harmony”, one can conclude that harmony can produce virtue and replenish it as well, and thus makes it more perfect. “Being harmonious and happy” is a propitious speech which is popular in Chinese.
Chinese philosophy;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virtue”; “beauty”; “harmony”
B2
A
1673-2065(2016)05-0064-07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12
2016-02-20
钱耕森(1933-),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衡水学院顾问。
* 该文系作者为出席意大利威尼斯大学2015年3月25-27日举行的‚中国哲学中的‘美与德’国际研讨会而写,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科《伦理学》2015年第12期转载全文,《新华文摘》2016年第4期摘录,本刊所发经作者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