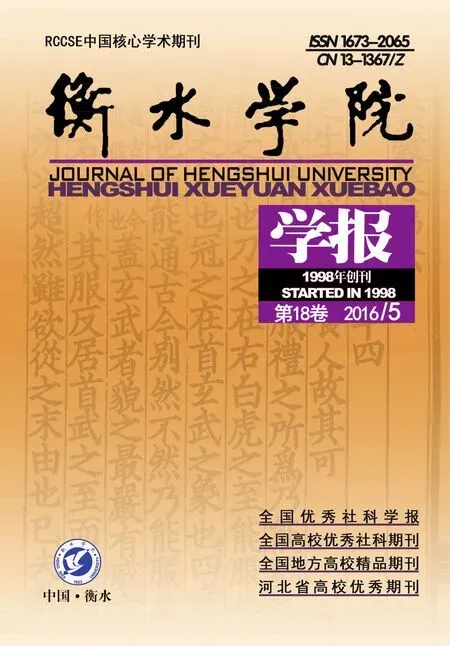新儒家梁漱溟教育目的论述评
2016-03-15吴洪成李阳阳
吴洪成,李阳阳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新儒家梁漱溟教育目的论述评
吴洪成,李阳阳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梁漱溟是一位思考并行动着的新儒家与教育家,自北大任教到后来从事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活动中,随着人生经历变化和思想逐渐成熟,构建了深邃的乡村教育理论。其中的教育目的论包括了社会理想教育目的、全生活教育目的及乡村建设教育目的,内容丰富而具有特色。梁漱溟的教育目的论不仅具有教育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今教育改革仍有启发意义。
梁漱溟;新儒家;教育目的论;乡村教育;现代教育
教育目的实为教育活动的方向和灵魂,至为重要。教育目的的问题关系到教育活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关“教育目的”的概念虽众说纷纭,但其解释大同小异,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总要求,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并根据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确定。梁漱溟作为一位在现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新儒家、教育家,虽其本意并非为教育而教育,而为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省思再三,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1]然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离开教育,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以教育为利器,以图达到社会理想的目的。尤其在乡村教育运动实践中,梁漱溟形成了独具一格,富有特色的“全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教育目的观,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有创新性价值。当今我国教育改革中对思想理念的选择确立至为重视,教育目的诸多内容依然是困扰当今中国教育的大事,认真研究梁漱溟对此的探索及理论观点,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今教育事业有着现实意义。
一、社会理想教育目的
梁漱溟早年受其父影响,形成了所谓“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人生思想,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烦恼不断涌现,继而转入佛学出世思想。1917-1924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此间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思想转向,归宗儒学。儒家本身强烈的入世思想,使归宗儒学的教育家梁漱溟,更加关注民族前途和社会现实生活,直指教育的社会理想政治、经济及文化目标,肯定教育具有现实、社会的目的诉求及人生价值。他指出数十年来中国教育之所以失败,虽有教育本身导致失败的缘由,但吃亏的还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出路,因为社会没有出路,加重了教育的惨败。
过去中国教育之错误,论者已多,现在亦不须细数但核实之言之,总不外误在一切抄袭自外国社会,不合中国社会之条件,此为主要一层。其次为自己有所参酌变动之处,或失原意,或恰恰蹈袭中国旧弊,此为附属两层。然假使中国社会正将以外国社会的出路为出路,则此教育设施纵不合于社会固有条件,犹不违于将有之新条件。尽管枝节上错误甚多,而大方向不差,必无惨败之理。[2]163
由此可见,梁漱溟认为教育没有出路是因为教育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相差太多,批判当时的教育无利于中国社会出路的解决,并对教育的失败感到痛心。教育应具有配合社会运动,完成社会改造的义务。这是教育本质的要求,也是教育目的中的应有之义。
我们要记住这一定理:若社会的出路在此,而教育的大方向与之相顺,便彼此相成,同有出路;反之,若社会的出路不在此,而教育却以此为方向,便彼此相毁,一齐没有出路。因为教育故不能外于社会自有出路,但非为教育的命运,就只能是被决定的。吾人可以体认把握社会的出路所在,而努力以求之。在力求社会出路之时,教育亦是要运用的一件法宝;同时即从社会出路里面,教育亦得其出路。[2]166
梁漱溟认为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息息相关,他的教育目的思想在于教育为时代所用,致力于社会出路,服务于社会发展,并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目的。换言之,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须符合社会时代的要求,实现社会理想,这是教育发展的出路,也是教育具有的时代社会价值以及所应发挥的责任担当。
在通过教育探索实践以实现寻求社会理想的奋斗历程中,梁漱溟要求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组织方法及测评项目要求等均以社会出路为基准。以教育为利器来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配合社会,为社会所运用,使教育能够承担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拯救民族危亡,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职责。怀着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美好信仰,梁漱溟毅然于1924年初夏走出北京大学书斋,到山东曹州从事教育改革实践,用儒家社会教育及人本教育的功能理念,融合西方近现代教育制度设施及思想主张去办属于自己的教育,从而为乡村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二、全生活教育目的
梁漱溟对现实学校教育的实施情况感到痛苦与不满,认为所施行的教育只关注对学生单纯的知识传授,而缺乏对学生身心的疏导,忽视对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导。他在山东曹州办学(1924-1925年)之时所作《办学意见述略》一文中对此作了描述与阐发:
现在的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即在知识技能一面也说不到帮着走路。单说在知识技能一面帮着走路,就当是对每个学生有一种真的了解——了解他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而随其所需加以指点帮助;像现在这样只是照钟点讲功课,如何能说到此。而且教育只着眼知的一面,而遗却其他生理心理各面,恐怕是根本不对的;何况要讲求知识技能,也非照顾上生理心理各面不行。我的意思,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对他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3]778
由此得知,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只注意智育,没有涉及到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导,这是不可取的。教育应该注重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即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传给学生知识,还要注重每个学生生活,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使他们在德、智、体及知、情、意、行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得以健康的成长。
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想的新教育,则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共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4]
上述两段引论也透露了梁漱溟关于教育,尤其是教学问题的主张或倾向,如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必须是教育共同体双方的沟通交往基础上达成;教育活动应以学生的特点及需要为基础,不是高压灌输、强制被动,而要激发学生主体精神及自觉能动性;教学应以学生差异性设计作为组织及评定的合理依据,而不是绝对地统一或共同标准要求作为活动过程及结果的衡量工具,“长善救失”、弥补差距恰是卓越或有效的教学理念。如此等等,既可视为全生活教育目的论的组成内容,也是达成理想教育目标的途径方式。
为青年而教育是梁漱溟早期的办学志向,对青年实施“全生活教育”是梁漱溟教育目的论的闪光之处。在他出任曹州中学校长后,甚至采取“量力乐输”“以人情行之”的方式听凭学生自愿交纳学费,足以体现一切为了青年学生的教育信念。他不愿采用权利义务、买卖交易以及法律条文的方式处理、解决学校教育及管理中的矛盾冲突,而是倾向于选择人情关怀的手段建构学校的校园文化,尤其是师生的人际关系。期以善良、真诚与信任的态度行为打动学生,以高尚的道德情感感染学生,倡导教育要着重学生的身心成长,教育者要顾及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这种主张尽管有理想化以至于不乏浪漫的一面,实际推行的社会条件也不够充分,从而也无法在现实意义上全然实现,但在教育理论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乡村教育目的
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场延续时间长达20年之久的乡建运动,其中教育活动是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是众多乡建流派中的典型代表、鲜活样本。他的乡村建设与教育活动发端于1925年山东曹州的教育设想与1929年广州的乡治讲习所活动;产生于1930-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实践;稍后延续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渐趋高潮;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后转向重庆,重心在文化学术传承及社会教育,以期达到民族复兴、富国强兵。其中教育目的思想遂通过乡村教育的实践模式作为载体得以实现。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由于东西文化相遇,中国文化相形见绌,为应付新环境而学西洋,结果老文化破坏殆尽,农村破产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建设问题归根到底是“乡村建设”,教育目的也就在于乡村建设。
(一) 乡村教育的内涵及其对教育目的的影响
梁漱溟认识到现存的学校教育不合于教育的道理,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成无能的废物。他在《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一文中作了如此描述:
使得乡间儿童到县城里入了高等小学以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过不来:旧日饭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知识能力,又一毫无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做,代以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惯。在小学亦如此。[5]26
学校教育模仿西方,严重脱离乡村实际需要。正是基于此,乡村教育势在必行:“所以三十年间新式教育的结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将农村人家子弟诱之驱之于都市而不返。……故新式教育于乡村曾无所开益,而转促其枯落破坏。然中国固至今一大乡村社会也;乡村坏则根本摧。教育界之有心人发见其非,于是有乡村教育之提倡。”[6]
为适应乡村教育特定对象范畴的探讨及建构,就势必对于教育的含义从大教育视野加以考察与界定。梁漱溟在《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中对教育的含义作出这样的表述:“什么是教育?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庭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州官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来是很宽泛的东西。至于教育的功用,不外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换句话说,就是‘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止不进’。人类不能不有生活,有生活就不能不有社会,有社会就不能不有教育,教育是很天然的”。[7]433同时,在《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中还指出教育有两个必要条件:“教育之一事应当一面在事实上不离开现社会;而一面在精神上要领导现社会。”[5]19-20因此,教育理应存在于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
因教育两字很活而阔,教育这一回事,是人类社会自然之作用,人类社会无教育,即无任何前进,故社会之进步,全靠教育,要推进社会之运动,无疑的为教育运动,此运动以社会为对象,而下工夫,如改善乡村风俗习惯,指导农民合作,启发农民智觉等,都是教育,故可以认我们的乡村运动,就是乡村教育运动。[8]
他把乡村建设等同于乡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一文中指出:“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7]436“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法可行”[9]。于是,又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让教育往乡村跑”“让地方自治往教育上跑”。乡村建设即是知识分子带领民众完成文化改造的活动,其着重点始终全在教育,乡村建设的用意在于整个社会的综合发展。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认为乡村建设的意义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10]149。其二,“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10]153。其三,“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10]155。其四,“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己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最后一层的意思,“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梁漱溟认为,今日整个中国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实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所能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10]161。
综上所述,在梁漱溟的理论视野下,由于教育内涵及对象从制度化学校教育向大部分属于非制度化乡村教育转移,教育参与者也从青少年儿童的在校生变为包括失学儿童、少年、成年农村大众在内的全体乡村人员,教育目的自然不能限于社会对教育部门机构的规范要求以及在校学生的成长发展上,而应在非制度性及社会生产与生活方面着力。由此教育目的设计视野突破了学校质性因素的组合,而走向了乡村社会民众素质的转变及提高,既有物质技术,也有道德规范、行为习惯,更有伦理精神、文化风尚。从另一方面来看,教育目的内涵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发展乡村教育的需要,以乡村教育改造或重建实现乡村建设的整体任务,进而达到复兴农村、重振中国社会的理想愿景。当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教育实验虽然以大农村为基地,体现大教育的思路,但其中也有以带有组织计划及干预控制手段、方式的学校教育机构,即山东邹平、菏泽及济宁等实验区的乡农学校、村学、乡学,甚至还办理过简易乡村师范以及成人教育的专门教育培训机构。当然,这些机构都带有社会特性及组织管理行政化色彩。无论如何,这样就增强了教育目的论的教育学意义及话语概念陈述的依据。
(二) 乡村教育目的的主要内容
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萌芽时期。梁漱溟1925年夏秋时节,在广州乡治讲习所进行有关“乡村立国”的演讲标志着其乡村教育理论的初生。第二,形成时期。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从初创进入基本形成阶段。1928年秋至1931年春,通过河南村治学院办学实践活动,他试图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整个建设的和谐与统一,并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欧洲国家道路,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中就提出“知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3]911。第三,完善时期。1931年秋冬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山东邹平等地以“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为目的进行乡村教育与建设实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乡村教育理论体系。随着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梁漱溟的教育目的论也更为丰富及深化。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的目的从教育功能论表现层面可以从受教育者个体和乡村社会及国家民族三个方面加以衡定:在个人方面旨在提高受教育者学识的文化知识教育、增进体魄的健康教育、生产与生活技能的职业教育、启发心灵的品性教育、引导乡农参与并改进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公民教育;在乡村方面是为了改良农业,倡导自卫,除暴安良,奠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础,减去乡村建设的阻力,增大乡村建设的势力,使乡村建设事业推行;在国家方面是为了加速普及教育、培养健全国民、实现民本政治、扶持民族生命。
乡村教育是与乡村建设紧密相关的,不仅是手段或方式,抑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有主从概念的内构包容关系。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称:“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即建设新的礼俗。”[10]276而“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10]278。这个新的组织只能通过理性来求得。所谓理性,也就是教育。这就是说,乡村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一组织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的优点:民主与科学,民主即团体组织的平等生活,科学就是改革社会、转变人生所应具有工商业性质的科学文化,尤其是增进效率的工具手段和实用技术。这就避免了大教育观下教育目的论泛化而无法捉摸,或者“学校教育消亡论”者对教育目的的淡漠乃至边缘化的偏颇,使其具有教育制度框架内的分析空间。他所设立的乡农学校、村学及乡学等教育机构实际上就是这一社会组织的雏形。
乡村教育目的主要通过具体的教育活动来落实或实现。教育活动开展的构建要素则可大略包括教育机构组织、教育内容及教育主体参与者的师生三方面。而就教育目的指向而论,则必然会反映在受教育者学生、失学者及民众的发展要求及规格中。梁漱溟在开展乡村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教育组织机构、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提出其自身相应的目的。
第一,从乡村教育实施机构来看,主要包括前期的乡农学校及后期的村学、乡学。在《乡村建设理论》一文中梁漱溟认为“乡农学校”的教育目的:“我们必须启发村人自觉……乡农学校是个安排,这个安排干什么?就是让乡村人发生自觉。”[10]353又在《乡村建设大意》中设想通过选择一系列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及乡土风情民俗的课程资源,以多种组织方式及教学活动加以编制并实施,藉以增强乡村儿童少年及民众的知识技术、能力素养,达到提高村民自觉意识的目的,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这样事情才有办法,乡村以外的人才能帮得上忙”[11]620。
村学、乡学的目标在于从上述乡农学校所采用各类教育资源中加以合理编选,培养新政治习惯(即新礼俗),启发大家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在《我的一段心事》中主张应该“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积极团结”[7]535。所以,“以乡村为根,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11]614。这也注定了乡村建设所成就的乡村组织并非完全是东方化的产物,必然是一个“中国固有精神”和“西洋文化长处”这两样“中西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10]278。既然乡村建设做的是“改造中国文化和补充中国文化的工夫”,那么村学、乡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组织,其担当的使命乃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带领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
第二,从教育对象来看,乡村教育的主要成员包括民众及未成年学生,教育目的表现出差异性。梁漱溟指出中国处于社会改造的特殊时期,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乡村教育要以农村成年民众为主要教育对象。这是因为,“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不能忽视农民这一主体力量,所以农村教育要注重对农民的培养与训练。1935年前后,梁漱溟在邹平全县范围内,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有步骤、有计划地对民众开展知识文化、文明卫生,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教育,进行军事、职业技能、精神陶冶等方面培养与训练,并逐渐达到以启发民族意识、培养组织能力、增进生活常识、陶炼服务精神为宗旨的成人教育目的。
对于未成年学生教育目的的设计则有另一番图景:乡村学校突出儿童团体精神、合群意识的培植;促进学生主体性学习、心智能力的发展以及联系社会、注重实用操作技术的训练。在《今后一中改造之方向》中他所提供的思路和主张是:
是要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就是团体的,也要由他们自己去管理,去亲身经历。总要用他们自己的心思才力,去求他们所学要的知识学问。我们很不满意现代手足不勤心思不用的教育。总而言之,现在的学生,只站在一个被动和受用的地位;好像把学生时代,看作是人生一个短期的预备时代,是专门读书的时代,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时代。教育的本意,是要把人养成有本领有能力;如果要使一个人有本领有能力,就非发展他的耳目心思手足不可。[3]868
简言之,就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使心、手、耳、目统一运用起来,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使他们充满生产、生活情趣和公共道德,在完善、发展自身的基础之上,承担起改造乡村,振兴社会的责任。
第三,从教育内容来看,乡村教育实验根据乡村社会实际及民众的特点主要包括德育、智育与情谊教育三个部分,有具体的目的要求。首先,德育之目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精神已经破产,一切旧的风尚、规矩、观念都由动摇而摧毁,新的风尚规矩此刻尚未建立,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让乡下人活起来,恢复他们的安定,使之有自信力。因此,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德育就是为了帮助人创造,在《人生在创造》中他认为:“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5]221也即成就个体生命的德性。其次,智育之目的。梁漱溟主张开启民智,设立文化常识、历史社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工商贸易基础、乡村建设,以及知识文化素质、生产技术及精神陶炼科目,培养农民的道德自觉意识,开发农民智慧。在“人生向上”方面,不仅使被训练者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分子,而且使其成为能合理的运用其知识,具备高尚人格的一个人[12]。通过知识与技术的教育,促使民众努力求进步,指向人生积极性可能性的向上发展。再次,情意教育之目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国人向来注重“人生行谊”的情意教育。情意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农民养成团体合作的习惯,合作是靠大家都遵循一个“礼”的方式,凡事大家商讨着来解决。另外,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梁漱溟提出:“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不囿于法律条文。”[11]707即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以情意道德的手段代替法律进行乡村教育。
在乡村教育实验的各项工作中,一直渗透着“伦理主义,人生向上”的思想。梁漱溟他认为在这里面含藏着自爱爱人的深厚意思,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源泉,也可以视为乡村教育的人文精神。发扬中国传统伦理的情义精神,把人格平等的意识注入其中,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分析与汲取,体现了梁漱溟在乡村教育实验中对以儒学为代表的道德文化的弘扬与改造态度。揆之教育学原理,对教育内容这一概念的理解除教育资源、媒介、信息及价值之外,应该从组成部分、结构角度去把握,一般包括德、智、体、美几个方面。梁漱溟所着意探求领域是农村教育,又以社会教育为聚焦,因此相关的思考不可能是纯粹状态的学校教育,而自有其个性,这或许更能体现乡村教育的现实愿景。
梁漱溟是从教育社会学视野论述乡村建设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教育目的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认为:“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沿袭之社会组织结构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是说文化失调。”[10]162-163为此,他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提出了自己乡村建设的目的:“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的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的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那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而创造新文化的途径便是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改造,所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11]611-615,进而达到民族复兴、富国强国的宏伟理想,而这也正是乡村教育的理性诉求及最终目的。
四、梁漱溟教育目的论的现实启示
如何评价梁漱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能达到共识。笔者非常赞同美国学者艾恺博士的观点:“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情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13]在我看来,梁漱溟教育目的论的内容和思想理念有很大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对于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 增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激发求学的自觉心
梁漱溟主张教育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激发求学的自觉心。这就要拿出他们的心思、耳、手、足的力量来做自己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心思才力,去求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学问,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也就是说,学生自觉心的获得需要全身心的感受,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的释放,而能带来这些感受和力量的则是自身亲自的体验。对此他有着深刻的见解: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中国古人与近代西洋人都有很大的创造与成就。近代西洋人系向外致力,其对象为物,对自然界求了解而驾驭之。中国古人求了解自己,驾驭自己——要使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办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的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2]268-269
梁漱溟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践行了上述观点,并有所拓展和深化。如1925-1927年广东一中的改革就贯彻了这样的理念: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干了什么,是教你更会受教育,教你学习更会学习的方法,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而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中,他要求学校教育要为学生们自觉、自立创造条件,让学生们自己体验、自己做事,过自己的生活,在“教学做”中生活和成长,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本质追求在于学生“自觉”的唤醒。
在信息化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我国的学校教育中仍存在种种弊端。受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的制约,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弱化,动手能力普遍缺乏,“高分低能”现象屡屡出现,主体教育理念显得更为重要。教育活动中注重学生的主体性、自觉性,引导他们进行自主学习与创造,其间尤须充分发挥学生自身自觉心与积极性。这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二) 树立“全生活教育”观念,倡导对受教育者身心的关照
梁漱溟认为办教育的目的不仅只是关注知识的授予,更要留意身心成长中的烦闷与问题,促使青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才是我们要办的教育:
只着眼知的一面,而遗却其他生理、心理各面恐怕是根本不对的,何况要讲求知识技能,也非照顾到生理、心理各面不行。要在全生活上帮着走路,犹非对每一个学生有一种真了解——了解他的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而随其所需,随时随地加以指点帮助才行。[2]83-84
对此,梁漱溟在曹州中学的“入学须知”中,就明确指出学生既然到我们这里来上学,那么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思想情感,从身体锻炼到精神培养,我们都要顾及到,不使学生们感到有什么痛苦,有什么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态而我们不知道。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教育目的的思想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并且力图将知识教育与学生生命教育并举,从而切实地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是符合时代社会对人才培养普遍性要求的教育理念,弥足珍贵。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日益横行,社会环境也日趋复杂。所有这一切都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冲击,也波及校园中的莘莘学子,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日渐增多。其中存在心理异常,甚至心理疾病的学生,也不乏少数。学校教育能否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关系到教育事业的成败。这就需要我们在办学实践中树立全生活教育观念,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学生的心理精神,从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三) 实施“精神陶冶”的人生行谊教育,重视对受教育者道德的培养
梁漱溟的教育目的论突出对学生实施人生行谊为主的情意教育,把对道德的要求放在知识学问之上,要求受教育者要有良好的精神涵养和道德素质,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一文中他便指出:“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接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就是人的情意,“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5]4他认为人生教育、道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我可以断言;中国学术除非不复兴盛则已,如其兴也,必自人生问题之研讨入手,及引起其他一切若近若远之科学研究;抑必将始终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而发展一切学术焉。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有办法则已,如有其办法,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其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14]
因此,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教员开设了“精神陶炼”课,在村学、乡学开设有“精神讲话”课,要求教员们在努力使乡村人精神活起来上下功夫。“精神陶炼”于未成年人则称之为人生行谊教育。这些都充分表明他深刻认识到人生行谊教育对广大受教者积极向上精神的激发和振奋的意义,并具有转而促使知识技能教育著其功的独特价值。
当今社会中,“道德沦丧”事件频发,梁漱溟具有预见性的“精神陶炼”、德育思想仍有现实意义。从基础教育开始,教育者就应加强对学生进行良好的道德品性教育及行为习惯培养,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真正深入人心。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等多方面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校教育符合社会的现实需求
梁漱溟教育目的论始终与其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理论的创新来源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有效须有理论引导,每个时期的办学活动中,都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就十分突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组织结构及办学方式,在课程与教学的诸多方面力图紧密联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需要。他在《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一文中对清末民初以来学校与社会脱节的弊端作了深入反思:
如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合社会的需要,毕业即失业——此即二十年前职业教育所为提倡之由来。又如教育与社会相隔绝,受过教育转成社会的病累——此即十五年前乡村教育所提倡之由来。但至今日,职业教育、乡村教育亦未能开得出路……又如数十年屡说普及教育,但受教育的人,却日见其少,不见其多,农业教育办了几十年,而社会上新农业不兴,工业教育办了几十年,而社会上新工业不兴。凡此,自都是我们教育失败之证。[15]
这就从反面论证了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需要这一基本原理。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教育机构在人的自然性及个性化尊重满足前提下,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培养人才,以社会的发展为指导确定培养目标。针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生活现实要求进行教学和实践。这对于当今正大力进行的教育改革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只是教给学生书本知识,更要教给他们人生的知识,培养品格,健全心理精神并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在这样的教育目的方案规范与导向下,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社会生活生产技能、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建设者。
综上所述,梁漱溟身体力行,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从事教育活动,随着其人生经历的变化和思想的成熟,他的教育目的思想不断地丰富与深厚。从上述有关教育目的论内容中看到的不只是他对人生、教育及社会的思考,更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的苦苦思索,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梁漱溟的教育目的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汲取其中的合理要素,从中获得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启示。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的感召下,我们更应该对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作多向度的理性思考。
[1]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7.
[2] 梁漱溟.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3]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47-48.
[5] 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6] 梁漱溟.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G]//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8-79.
[7]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8] 梁漱溟.我们的乡村运动[G].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八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191-193.
[9]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93.
[10]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11]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12] 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484.
[13] 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14] 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85.
[15]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六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A Review of the Neo-Confucianist Liang Shuming’s Education Teleology
WU Hongcheng, LI Yang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Liang Shuming is a new confucianist and educator who is thinking and acting. While he worked as a teacher in Pek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he was later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of rural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on, his life experience changed and his thought gradually became mature, and with it he constructed profound rural education theory. The education teleology of it includes the purpose of social ideal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whole life educ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rural construction education, and its contents are rich and distinctive. Liang Shuming’s education teleology not only has academic education value, but also has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oday.
Liang Shuming; education teleology; rural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
B26
A
1673-2065(2016)05-0049-08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10
2016-01-04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阳阳(1989-),女,河北沙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