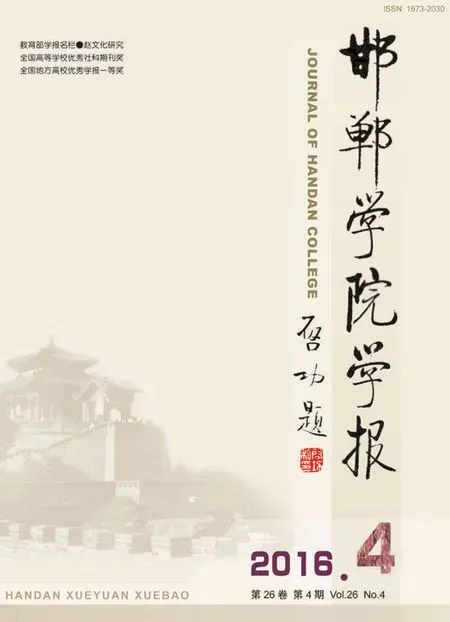荀子的道德论证
2016-03-15王楷
王 楷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荀子的道德论证
王 楷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荀子反复强调道德的必要性,并力图从理论的层面上完成对此问题的道德论证,以期教人勉力为善。就理论结构而言,荀子的道德论证包含着两个层面——社会的层面与个体人格的层面。就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而言,荀子强调道德作为群居和一之道的社会功能,因而展开为一种效果论的理论进路。并且,这一层面的道德论证之成立又是以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作为其内在的逻辑保证的;就个体人格层面的道德论证而言,荀子德行论又表现出鲜明的道义论取向。就整体而言,荀子的伦理学呈现为一种综合了效果论的道义论。
荀子;道德论证;效果论;道义论
引 言
如所周知,对于任何一种完整的道德学说而言,道德的必要性的问题都是一个无法忽视避而不谈的问题,甚至,我们毋宁说,道德的必要性问题恰恰是其中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一个道德哲学家只有对道德的必要性问题,亦即道德价值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论证,其整体的道德学说之建立才成为可能的。一般而言,在伦理学研究中依据一种道德学说对道德的必要性问题的论证的方式来判定它在伦理学上的理论定位。就荀子来说,传统的研究大多习惯于将之归为效果论(Consquentialism)伦理学。在笔者看来,这种判断可能失之于对荀子道德论证的脉络缺乏一种整体上的把握。本文的研究力图揭示出荀子道德论证的两层结构——社会的层面与个体人格的层面,就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而言,荀子强调道德作为“群居和一之道”(《荣辱》)的社会功能,因而展开为一种效果论的理论进路。并且,这一层面的道德论证之成立又是以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作为其内在的逻辑保证的;就个体人格层面的道德论证而言,荀子将道德视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相》),以之作为人之所以优越于禽兽而“最为天下贵”(《王制》)的根据所在,从而展开为一种道义论的理论进路(Deontologism)。就整体而言,笔者认为荀子道德哲学在伦理学定位上呈现为一种综合了效果论的道义论。
一、群居合一之道
在西方伦理学引入儒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儒家伦理通常被宽泛地界定为道义论,之所以说是“宽泛地”,是因为这一界定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儒家伦理中的孟子一路,而对儒家伦理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缺乏细致的了解和分疏。事实上,关于儒家伦理的探讨每每具体到特定的流派和特定的学者,学界的观点也就越发分歧。譬如,相对于孟子的道义论,今之治荀学者往往就习惯于把荀子伦理学归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应该说,这一观点也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荀子本人道德论证语言或多或少的确给人以效果论的印象。在荀子,出于其重群精神的理论性格,而比较注意从道德的社会功能的角度,亦即从效果论的角度来强调道德的价值。易言之,在荀子伦理学的建构中,至少在叙述方式上,道德首先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的概念,即其所谓“群居和一之道”(《荣辱》)而出现的,这一点在荀子对“礼”的起源的讨论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其所云: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必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制》)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王制》)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荣辱》)
在上述对道德(作为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之礼)的必要性的论证中,荀子所取的是一种社会的视角:就理论上而言,礼起源于调节社会人群分配诉求之需要,当然这种分配诉求所指向的可以是直接的物质财富,也可以是与物质财富密切相关,甚至间接决定着物质财富之分配的地位、荣誉以及名望等等。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礼之功能在于确定社会名分和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荀子重群,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认为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一旦“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而要通过“明分使群”以达致人类社会之“群居和一”则必须诉诸于礼,通过礼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名分,进而依照社会名分来分配各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这就是所谓的“维齐非齐”,即通过合理的差别而达致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应该说,荀子这种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鲜明地体现了追求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相统一的儒家传统。并且,透过荀子礼论对“知愚”、“贤不肖”等个体性素质的强调和重视,我们也可以体认到荀子时代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历史变迁。简言之,在荀子这里,道德(礼义)对于人类生活之所以是必要的,就在于它保护人类使其不相互侵犯,从而使人类作为一种族群能够拥有一种超出动物水平之上的“好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对道德生活意义的肯定还不能仅仅归结为荀子个人特色性的思想,更是出自早期儒家一种本有的、一贯的精神方向,荀子的意义则在于对这一精神方向做了系统的、理论化的论证和阐述。就早期儒学思想发展而言,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一直严于“人禽之辨”。而“人禽之辨”之提出,其中一个潜在的预设就在于:作为一个特殊的、优越于禽兽的物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停留在动物对待其同类的层次上。简言之,一种道德秩序支配下的社会生活应该成为人独特的、优越于动物的存在方式。荀子在这所要解释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因而,荀子着重从道德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强调道德的价值,体现出一种后果主义的论证进路。
二、吾之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
在对善之必要性问题的考察中,如果我们的视角从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叙述回归到一种哲学层面的反思,我们就会深切地体会到,荀子这种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之成立是以儒家一贯的“忠恕之道”作为逻辑上的保证的。《荀子·王霸》称引夫子所言:“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①按,“人之所以来我”之“人”字前本衍一“适”字,引文依王念孙据《群书治要》删。。”就是说,对自己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有了清楚的了解和反省,也就知道了别人会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及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行为方式)对待自己。质言之,自己对待别人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决定了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这种提倡以自己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别人的思想,与《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同样,这一“忠恕”思想在七十子及其后学那里也有着鲜明的表现,且如: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大学·第十章》)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第十三章》)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第十四章》)
不独《大学》、《中庸》,孟子亦提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离娄下》中,对这一思想更有集中、明确的阐发: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其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吾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禽兽奚择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
在这里,孟子所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即君子,如何对待别人加于己身的暴虐之道(横逆)。在孟子看来,出于“人心之同然”,一个人通常会根据别人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决定如何对待别人,亦即“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从正面说,反之亦然。——至于那些德行完全败坏不可以情理喻之的“妄人”,从社会道德生活的角度看则无异禽兽(“与禽兽奚择焉”),对于禽兽则不足为难(“于禽兽又何难焉”)——因而,君子要自我反省是否由于自己待人“不仁”、“不礼”、“不忠”,以至于招致别人以“横逆”加我。从而,君子最终落脚于自我的德行修养,“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爱人以仁,敬人以礼”,“非仁无为”,“非礼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有终身之忧”,忧在己身之德行人格是否如尧舜一样完满;“无一朝之患”,己之德行既修,则不以人之加我横逆为患。
由上可见,“忠恕之道”在早期儒家那里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想。这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包含着一种深刻自我反省意识(“自反”),亦即张子所谓的“以责人之心责己”,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以“修己以敬”为立足点,提倡“适人以己之所欲人之来我者”。那么,一个人愿意看到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呢?荀子说:
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
一个人既然愿意别人以“礼义”、“辞让”、“忠信”对待自己,而不愿意别人以“污漫”、“争夺”、“贪利”对待自己;那么,根据儒家的“忠恕之道”,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在于自己首先以“礼义”、“辞让”、“忠信”,而不是以“污漫”、“争夺”、“贪利”来对待别人。或者,易言之,出于一种“好的生活”的考虑,我们都愿意与“礼义”、“辞让”、“忠信”的人相处,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在于自己首先做一个“礼义”、“辞让”、“忠信”的人,而不是“污漫”、“争夺”、“贪利”的人。当然,选择以“礼义”、“辞让”、“忠信”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对自己的欲望、情感、自由等等生命冲动和意志的一种约束和限制。但从长远来说,选择做一个道德的人,则是对一种“好的生活”的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说:
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礼论》)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强国》)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荣辱》)
对于那种希望拥有一种“好的生活”(“贵生乐安”)而又与道德秩序(礼义)的要求相背离的人,荀子称之为“愚”、“陋”。这里的“愚”、“陋”不是就一般认知意义的智力水平而言的,而更多地就一个人对于自己人生方式、行为方式之自我反省能力而做出的判断。在人生方式与道路的选择上,“愚”“陋”的人缺乏一种基本的明智和长远的眼光,不懂得为了长远的根本的目标,一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限制是必要的。无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愚”、“陋”是一种良好的道德生活之建立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因而,荀子称之为“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
作为对这种“愚”“陋”消解的努力,现代伦理学从德福关系的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甚至针对各种情形建立复杂的博弈论模型,试图从逻辑上对良好的道德人格与“好的生活”之间的一致性做出充分的证明。然而,即使最精细的博弈论也不能对人类的道德行为做出充分的解释。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证明的努力又重新回到了伦理学上的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知识即德性”,而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内在的缺陷。不仅如此,在这种伦理观背后潜在着这样一种预设,即道德本身是外在于人的,道德的价值也只是一种功能性的价值,一旦失去道德与“好的生活”之间一致性的保证,对善之必要性的道德论证就将沦为一种无根的努力。事实上,对这种“保证”的需要,与其说是现实上的,毋宁说是逻辑上的。易言之,即使在经验世界中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只是偶然的,但至少在理论上,亦即在人的理智世界中,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必须是完满的、周密的。因而,这种伦理观与那种将道德生活之可能建立在外在的超越性的力量的保证之上的伦理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可能的共通性。
三、人之所以为人者
儒家伦理之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学说,也同样关注于德福关系的问题,但并不因此而将诉诸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甚至,在儒家道德学说中,惩善罚恶意义上的人格化的“上帝”的出现也是不必要的(儒家哲学中“天”这一概念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儒家对道德的必要性的论证并没有完全建立在单纯的德福一致关系的理论诉求之上,而是更专注于完善的德性人格自身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回到这里所讨论的主题,荀子的道德论证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的讨论,而是进而延伸到德性人格层面。从社会层面到人格层面,并不意味着前者追求德福一致而后者与之相反,反之,也同样不意味着后者崇尚良好的德性人格而前者与之相反。所谓社会层面到人格层面的转换,只是说两者出自两种观照道德的不同视角,与之相应,也就当然地导向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论证进路。以现代伦理学的语言来说,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所取的近于一种效果论的进路,而人格层面的道德论证所取的则近于一种道义论或者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进路,或者,易言之,前者近于一种社会学的进路,而后者则近于一种哲学的进路。
在人格层面的道德论证进路之下,我们所面对是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种哲学话语中,人在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价值的存在,而所谓的文化、价值之核心则在于道德。因而,一个人只有具有完整的德性人格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亦即一个实现了自身潜在本质的人,否则只能停留在“二足而无毛”之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人格之培养的过程也正是从“偶然所是的人”到“实现其本质性而可能所是的人”转化的过程。在荀子那里,论及道德(礼义)之于道德行为主体自身的意义,亦每言“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从而,道德是作为一种决定一个人是否实现其自身本质的内在价值而存在的。简言之,如果说在社会层面的道德论证之下,关注的是道德对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功能性价值,那么,在人格层面的道德论证之下,我们所关注的则更多地在于道德之于道德行为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
今之论者,蔽于荀子对道德社会功能的强调,遂遽而论定道德在荀子伦理学中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道德修养也只是客观的道德规范(礼义)约束下的他律论。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荀子道德论证的两层结构——社会的层面与人格的层面——尝试做整体性的把握,那么,这一判断就不能不说毕竟过于简单化了。就道德修养而言,在荀子德行论的内部,德性人格的完善显然要比纯粹出于他律约束下的行为在价值序列上处于更高阶的位置,不仅如此,依礼义而行为之本身的意义也不是孤立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消极地”不与客观的社会规范相违背,而更在于其本身也正是完善的内在德性之养成的必要条件。相对于外在强制他律的约束,荀子显然更重视出于内在心志和精神的德性,如《劝学篇》所言: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在这里,照“目非是无欲见也”、“口非是无欲言也”、“心非是无欲虑也”诸种讲法,道德显然不再停留在外在于人的规范层面,而是内化于人心,成为人内在的德性,以至于人按照道德而行动不再出于外在他律的勉强,而是一种自内而外,内外一气贯通自自然然的表达,即其所谓“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修身》)、“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枝①按,“若运四枝”原作“若生四枝”,依久保爱校改。”(《儒效》)。正因为道德作为人本身内在的德性而存在,于是,道德(德性)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工具性的层面,而在于道德(德性)本身。也就是说,随着道德修养的不断积累,“长迁而不返其初”,内在的德性逐步成长,“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以至于“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在必要的时候,人要准备着为道德而献身,这完全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道义论精神之重申。于是,我们看到,从社会的层面到人格的层面,荀子从效果论出发而于道义论处落脚,在道德论证进路上完成了从“知者利仁”到“仁者安仁”②杨伯峻先生将“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释之为:“有仁德的人安于仁(实行仁德便心安,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聪明人利用人(他认识到仁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实行仁德)”,颇能藉以概括荀子道德论证的两层逻辑结构。不过,这里需要特别申明的一点在于:这里的所谓“知者利仁”之“知”是就人生道路与人生方式的选择而言的,亦即对“道”的选择上的明智,而不是特定情形下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自我粉饰、标榜的虚伪的道德机会主义。也因此,荀子指谪春秋五伯,称其“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仲尼》)。的转换。或者,如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所说:“荀子为‘采纳’一种道义论的道德主张而提供了一种结果主义论辩。”[1]256
四、知与力
在上文对荀子道德论证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荀子德行论的道德论证综合了效果论的和道义论的两方面的因素。从而,社会与人格两层结构论的分析解决了荀子伦理学的在理论性质上的定位问题。然而,我们因此又要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解释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理论张力?申言之,如前所述,在荀子,道德的社会功能在于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尽可能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以最大的满足,然而,道德之为道德,又意味着对人的欲望与生命意志的一种限制和约束,当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激烈化的情形之下,崇高道德人格之实现甚至意味着选择死亡,是所谓“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而死亡本身无疑是对欲望满足的最大否定。于是,对于在生命本性上寻求欲望满足的人而言,完善的道德人格之建立所要求的心理基础又从何而来?
对于这一问题,倪德卫倾向于归结为人具有一种“优越的智慧眼光”:“在本质上,荀子争辩说,人虽然是自私的,但有审慎的理性去经受一种伦理的转变,从而使人变为利他主义者:由于人性和我们的‘环境’(广义解释的),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只有作为利他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这种欲望才能满足。”[1]11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人选择一种道德秩序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也就意味着对“道”的选择,即“从道”。“从道”并不意味着在每种特殊的情形下都做正确的事,而是指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与选择做一种人。如荀子所言:“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正名》)“从道”则须先“知道”,而“知道”则要诉诸于人的理性。然而,这里所说的“理性”,还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认知理性,而更多地指向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以“远见”、“明智”和“审慎”为特征的自我反思能力,接近于古希腊之所谓的理智德性。如倪德卫所说:
理智自由地选择做还是不做,但它总会全面考虑为感官选择最好的,如果它成功地考虑了所有的东西的话。对荀子来说,道(它是儒家之道)是一种道德生活,也就是一种接受社会的规则、标准、约束,并满足人们正当和使这些欲望保持控制的社会生活。[1]105-106
在倪氏的这种解释中,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人们选择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一种当下的、直接的满足而否定了多种长远的、更为根本性满足,而看不到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有秩序的生活本身的价值,因而他们在所谓思维上纯粹是混乱的,或者用荀子的语言来说,这样的人在心智上是“愚”“陋”的。然而知识并不就意味着德性,“知道”显然也并不必然导致“从道”。从“知道”到“从道”,出于自由意志的主体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或毋宁说是最根本的。于是,在这里,我们对荀子德行论的讨论就过渡了道德行为主体所赖以造就德性质量的内在根据问题。
最后,在荀子那里,人没有自然的德性,但拥有自然的获得德性的能力。《荀子·赋篇》论“知”,称之为“志意之荣也,血气之精也”。显而易见,在荀子这里,人这种理性的能力出于自然,尽管在发展程度上存在着一个逐渐成长完善的过程。然而,吊诡的是,坊间亦颇有据此而引申认为荀子人性论实可归为性善说者。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理解角度的问题:对于德性内容的理解从来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比如,在荷马时代,诸如“体力”这一自然的禀赋也被视为一种德性,而在后世西方伦理学的讨论中,“体力”显然不再作为一种德性而受到肯定和赞扬。事实上,如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所指出的,荷马时代“德性”的概念更接近于后世“优秀”(excellence)这一概念。[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志自由问题被引入伦理学的讨论之中,从而有了“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分别。以此为参照,在荀子这里,理性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智德性”:它显然有助于“道德德性”的获得和培养,但其本身并不就是“道德德性”。申言之,理性在荀子那里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优秀”(良好的禀赋和能力)而不是“德性”被看待的。因而,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荀子对理性的重视而将其人性论与性善说联系在一起,以避免问题的讨论人为地复杂化。
余 论
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荀子反复强调道德的必要性,并从理论的层面上出色地完成了对此问题的道德论证。正如上文的分析所显示的,就整体而言,荀子德行论呈现为一种综合了效果论的道义论。然而,一直以来,相对于孟子的道义论,荀学研究者大多倾向于将荀子伦理学归之于功利主义。这种对荀子的误读,一方面,正如本文分析所揭示的,固然出于对荀子道德论证独特的两层结构缺乏一种深入、完整的分梳和把握;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儒学之为儒学的学说性格本身缺失一种真切的认知和体会。作为对儒学学说性格的了解,“就先秦儒学所担负的时代使命言,孔、孟、荀实可说有一共同的理想,此理想即欲以周文为型范而重建一新秩序。”[3]1“儒家政治,以君子为主体。君子者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此儒家所持之理想也。”[4]23“周文”理想也好,“德治”政治也好,若以普遍性的语言来表达,儒家之为儒家,就在于其追求社会秩序,特别是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一致性。于是,在这种学说性格之下,很自然地,个体修身养性成就良好的德性人格与实现良好的社会政治治理,在儒家那里,也就成为了道德之为道德所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所不同者,只是这两个侧面在不同的儒家思想家那里的表现会有或隐或现、或强或弱之个体差异而已。
进而言之,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君子’。”[5]271揆之早期儒学思想家以观,孔子如是,孟子如是,荀子亦如是。基于一种共通性的理解,梁启超先生亦有言:“质言之,则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哲学,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6]84应该说,如果不做狭隘的理解,任公此论当不失为对儒家思想特色了解之一洞见。准此观之,长期以来的荀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偏颇:过多地集中于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视角展开阐释,而对荀子以德行人格为中心关切之修身哲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失一种立足于道德哲学本位的荀子研究的意识与情怀。——也因此,对于荀子道德论证的两层结构,荀学研究者视野所及习惯上只限于其中显性的社会层面,而对于其深处作为整个荀子德行论旨趣所归的个体人格层面则不能给予充分的注意与重视。——这种处理方式,借用荀子本人的用语而言,亦可谓:有见于其“治人”,无见于其“修己”;弊于其“治人”,而不知其“修己”。直言之,以道德哲学为基点解读荀子伦理思想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而这不能不说是现有的相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点。
[1]倪德卫.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M]. 周炽成,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 A.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 宋继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韦政通. 荀子与古代哲学[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4]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5]余英时. 儒家“君子”的理想[M]//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
[6]梁其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苏红霞)
B222.6
A
1673-2030(2016)04-0034-06
2016-08-15
王楷(1976—),男,河南封丘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