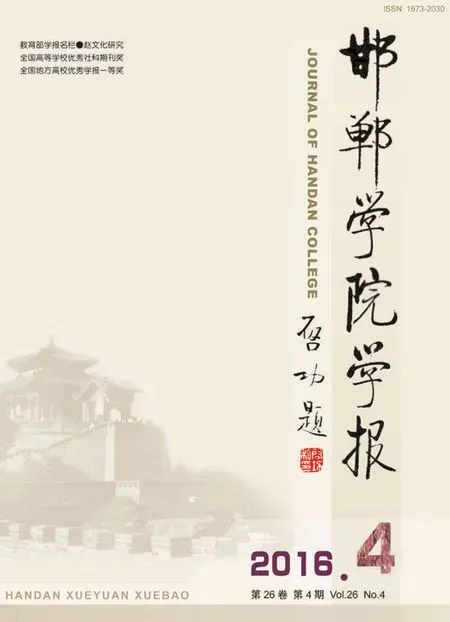荀子的“分”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乱”吗?
2016-03-15郑文泉
郑文泉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马来西亚 八打灵 46200)
荀子的“分”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乱”吗?
郑文泉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马来西亚 八打灵 46200)
荀子的“礼”学是起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原因,其手段为——“分”学,其目的则为——“群”学,则旨在对此一学说的客观有效性作一评析。按荀子的“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之所起也”的发生学来看,暗示社会秩序是起于资源配置的结果,其“乱”则为“人生而有欲……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所致。针对这个“分”的原理假设,指出(一)荀子以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而必须“分”,才能避免“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的乱局,还存在着一些变数,不尽为实;(二)在 19世纪以来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趋势下,“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的“物不能澹”的资源稀缺也可能不是当下人们所面对的全部问题;(三)荀学将人类社会的“乱”归诸于资源稀缺的终极原因,使其理论或不免有——“资源决定论”的偏执导向而有失真之虞。
荀子;礼学;分;资源稀缺;等级配置
一、荀子眼中的“乱”是指怎么问题?
荀子或《荀子》之学是“礼学”,为学者所共认。在这套礼学的一连串“礼义”、“礼法”、“礼治”等术语之中,“礼”对“义”、“法”、“治”等内涵都起了决定的作用,表合乎“礼”的“义”、“法”、“治”等现象,属主谓式名词。按《荀子·不苟》“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一语来看,“礼”在作用上同时还是“治”的同义词,足示“礼学”在荀子心目中也是一套“治学”。
荀子的礼学或“治学”是用来治“乱”的,这点不在话下。《荀子》一书所谓的“乱”,表面看来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其中还是有根源性问题和派生性问题的不同。所谓派生性的问题或“乱”象,荀子举的不少,如《荀子·非十二子》之“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指导致世人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邪说、奸言;《荀子·解蔽》则具体而微指其为认知上的偏差或“蔽于一曲”: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
这里导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乱”源是认知上的“蔽于一曲而失正求”;甚至,荀子还针对认知乱象进一步指出其概念构成上的“乱”源,如下《荀子·正名》一段: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而慎率民则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
按上使民疑惑、人多辩讼的是“析辞擅作名”的产生和出现。诸如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如《荀子·大略》所说社会“治乱之衢”取决于“好义”还是“好富”的治国政策之不同等,一直到“乱民”、“乱国”、“乱世”诸说,可谓不胜枚举。然而,这些可能都是派生性的问题,即它们之所以是邪说、奸言(如)的原因,不在于其为思想学说,而是此一学说所承载的内容问题。以邪说、奸言为例,《荀子·儒效》确实也这么重复道: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按上述,凡治或乱均不外于“事行”、“知说”二端,而各有“益于理”之中事、中说或“失中”的奸事、奸道之分别可言。从这个意义来说,中事、中说与否是由“理”来决定的,奸事、奸道也取决于其有悖“中”的原因。至于“理”或“中”指的是什么,同上《荀子·儒效》进一步阐释道:
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言下之意,凡事行、知说如果合乎“中”或礼义,就是中事、中说,反之则为奸事、奸道。这表示礼义才是决定性的原则,礼义性的问题由此也才是根源性的问题。所以,上提“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之说的另一含义是,从根源性的角度来看,凡事行、知说必须直面礼义才为得治之中事、中说,反之则为乱之奸事、奸道。
荀子眼中的根源性“乱”象是指什么,或“非礼义之谓乱”是怎么样的一种局面?我们知道,在荀子用语之中,“礼义”是个主谓式名词,重点在“礼”而不是“义”。《荀子·强国》对“义”有这样的界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可是“义”的内涵为何,并不清楚。实际上,荀子的“义”很多时候是“礼义”连用,表示限禁人为恶为奸的标准在“礼”,可见要从此来得其实蕴。换句话说,荀子的“礼”的实指,我们可能要从以下《荀子·礼论》一段来求解: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上引显然不是“礼”的好界说,因为它近似同义反复地用“故制礼义以分之”来解说“礼”,可说是一无所解。然而,《荀子》这一段引文旨在解说“礼起于何”的发生学背景,表示它产生自人类社会的物、欲不能“两者相待而长”的根源性问题,且此一问题处理不好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礼”起于这样的资源供给的背景,在《荀子》一书还有不少例子,如《荀子·王制》就这么解释道: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在这些例子当中,“礼”的内涵其实已暗含其中,即“制礼义以分之”、“群而无分则争”例子所见的“分”,基本上动词意义的人群(“群”)与资源(“物”)的分划、配给等大于名词的职分,表示荀子的“礼学”也是“分学”之意。关于这点,《荀子》一书对“礼”有多处的外延解释,如《荀子·富国》: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又如《荀子·荣辱》: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按上引指出资源(“物”)分配最终是透过人群(“群”)的分划来达成的,而这些“分”在现实上则有“等”、“差”、“称”等办法。不唯如此,《荀子·大略》更是直截了当的如此界定“礼”的内涵: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
《荀子·礼论》也重复道: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
“礼”在这里,被明言直以财物(资源的另一说法)的配给为对象,这个配给不是均分而是有多少的不同,而多少又是隆杀的原理表现,最终反映在社会上的贵贱形式或阶层的区别。由此可见,荀子的“礼学”起于他所说的人群社会中的“物”、“欲”如何“两者相待而长”的问题,是他心目中的“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的根本认识与判据。
二、荀子治“乱”之方:分
承上所析,荀子的“乱”是指“非礼义”现象,说白了就是“物”与“欲”的“分”出了乱子,破坏了“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的治理原则。《荀子·富国》以下一段,更是重申其“礼学”作为“分学”的学理原因: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按上引,荀子明白宣示“有分”、“无分”是天下“本利”和“大害”的分别,“利”、“害”之前分别都加上了高级形容词“本”和“大”,可见其于荀学理论奠基之重。至于这个“分”的必要性,上引还分别提出了“人之生不能无群”和“群而无分则争”的外部物种和内部物种的两个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析。
按“人之生不能无群”之所以属于外部物种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放在人与非人的物种间竞争来看,而谓“群”为人的永续物种生存的必要。关于这点,《荀子·王制》一处有极好的阐发: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随后的总结也强调“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可见一斑。单从物种条件来看,人是不如牛、马之力和走的,但后者却不能与人竞争,靠的正是“人能群,彼不能群”,由此而发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的最终“宫室可得而居”的群体与竞争力量。所以,人在物种竞争上要永保其优势,就必须永保其“能群”的力量与地位,而其关键就在“分”此一“群居和一之道”。
相对来说,“分”是怎样起了人类这个物种内的“群居和一之道”,也就是怎样起人类社会的“争则乱,乱则穷”之乱局的解决作用,可能更为荀学理论重中之重。针对这点,荀子自有他的说法,原因一如《荀子·王制》前文另说如下: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同样意思也可见于其他篇章,如《荀子·富国》: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按上引指出人群不能“均”、“齐”、“同”的原因,一方面是“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的群体共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势位齐而欲恶同”而会引起“物不能澹则必争”的资源配置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两贵”、“两贱”必须有一“贵贱有等”的“分”,而这个“贵贱有等”同时也是“谷禄多少厚薄之称”的“分”,就是荀子所说的“人能群”的核心原则与关键。
为此,荀学理论的自然归宿,就是人群之中谁能起“人能群”此一作用的人,始能充当领导人或“君”(或“君子”、“先王”、“圣人”等术语)的角色。对荀子来说,“君”就是“能群”、“善群”的代指,如下《荀子·王制》所示: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同一界说也可在《荀子·君道》等篇看到: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对“能群”、“善群”的完整阐发,则出于《荀子·儒效》以下一段: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综合以上三引,君子所道之礼义,并非是一种具体的“贤”、“知”、“辩”、“察”等行业本领,而是“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从而“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的“群居和一之道”得以体现出来的统合能力,方是“君子之所长”。从这一点来说,荀子“礼学”作为“分学”如果还只是手段的说法,那么“群学”则是这一手段的目的标志了。
至于“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之下所形成的具体人群之等级构造与社会,更是《荀子》一书通见的立论焦点之一。关于这点,荀子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构成之“德”与“能”,很有阐发,如上《荀子·儒效》之分论“民德”、“劲士(之德)”、“厚君子(之德)”、“圣人(之德)”为下: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对荀子来说,这些阶层的“分”一旦不被遵守,也将是人类社会的另一“乱”源与乱象,如下《荀子·君道》所释: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按上引不过是孔子以来儒家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通义的重申,并不殊特。不唯如此,一如孔、孟等其他儒学大家,荀子对这些人群阶层的“德”、“能”构成,并不采“性成命定”的立场,而是《荀子·王制》一文所认为的: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而归之卿相士大夫。
换句话说,谁是现实的“君”(或其它)是不定的,但是对“君”的“能属于礼义”的要求却是固定的,且人人均有此一“能”,端在努力与否。为此,《荀子·性恶》另有“涂之人可以为禹”的人性宣示与总结,可说回归孟子“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儒家人性论的大传统。
三、荀子的“乱”是人类社会的“乱”吗?
承上述,如果本文对荀子(或《荀子》)以“分”治“乱”的理解大致不误,那么现在是到了评析此一荀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荀学所说和人类社会的实况有多接近?简单地说,荀子所说的“乱”和人类社会的“乱”是同一回事吗?荀子对此一“乱”的乱源分析是否可信?连带的荀子的治乱之方(“分”)的有效性是否也带上了问号?仔细地说,本文仅针对荀学的三大理论假设作一探析:(1)“人生不能无群”的“乱”源于“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的说法,是否可信?(2)“物不能澹则必争”假设了人们在资源的满足上有一“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的“乱”象,是否和我们现时代的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实况有所出入?(3)荀子将人类的“乱”源归诸于资源稀缺的问题,是否使其理论有“资源决定论”的偏执倾向?换句话说,荀子的“礼”学所识之“乱”还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乱”象,故其“分”作为手段也仅有局部的有效性可言?
首先,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是对的,但是把这一必要性归纳为“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的“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的问题,则不无可议。实际上,这可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两贵能不能相事,是不是人类社会乱源之一;另一是两贵的“欲恶同”是不是为稀缺资源所不能同时满足而有争夺之事,由此也为人类乱源之一。只是在荀子这里,前一问题很快就和后一问题联结起来看,两者之间的必然性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确实,说一国之内有“两贵”会导致乱局是符合某种政治常识的,如《荀子·致士》所言: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按上引指一国之内有两个君主即“两贵”之治理不会长久,终将以乱局结尾,是有根据的。由于这样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的认识,荀子的治乱之分就是要求“贵贱有等”,一个国家只能有“一贵”,他所谓的“一天下”(统一天下)或“天下”本身就是假设了只有一个君主的世界。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种“一贵”式的天下通常只在国内关系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只是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华、夷(周边国家)相处,就是今天的世界以强权论也是“多贵”的世界,“一贵”式的“贵贱有等”仍然是子虚乌有的梦幻世界。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再回头看看荀子的“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说法有多大的可信度:国际关系中的“两贵”是否果真不能相事?是否“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关于这点,近年以《人性中的美好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享誉中、外学坛的平克(Steven Pinker)以为,在近代文明商贸的基础下,我们应该“看到资源控制未必涉及暴力”的事实:
也就是说,资源竞争并非必然……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所有这些资源?①见平克著、安雯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按:这是节本,全本为同一出版社的同一译者之上、下两册本。[1]263
平克的说法可信吗?我们知道加拿大和美国都是八大工业国(G8)之一,前者虽然不是后者意义的世界强权,但也算得上是旗鼓相当的“两贵”之国,而“二而乱”之事则未尝有闻,彼此之间更没有“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之类的争端。这也是说,“两贵”会不会“二而乱”,会不会“欲恶同”而“物不能澹则必争”,还有很多变数,并不如荀子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必然。
其次,荀子的“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说法背后,还有一个“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的资源稀缺的问题,然而它的真实性也还是可以再商榷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荀子所说“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是有根据的,也能理解。问题是人类社会并不经常与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相伴随,特别是在 19世纪西方工业化以来到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物质财富空前繁荣的时代,人类的健康和寿命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现在回看荀子《荀子·礼论》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的说法,我们对这个“欲而不得”会有新的思考空间。荀子的说法预设了资源稀缺的现实,一方面对“势位齐”的人可能会有“物不能澹”、不能均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个别人求索无度造成进一步的争夺物资之事,总体来说就是“供不应求”。但是,随着近世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的改变,我们面对的却是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现实。简单地说,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是对的,但是不是会进一步“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还存在着一些变数,因为在满足欲望上人们受到以下三点约束:
(1)生理约束:欲望可能无限,但生理能力不是无限的,如一个人吃两碗饭就饱了,断不会也无法再吃第三碗;
(2)时间约束:满足欲望也需要时间,同一时间是无法满足所有甚至无限的欲望的,如一个人在五星级大饭店吃饭的时候,是无法同一时间到高尔夫球场挥杆击球的;
(3)预算(收入)约束:一个人可能打算这个时候在五星级大饭店吃饭,下一个时候到高尔夫球场挥杆击球,但受到个人收入的限制,欲望总归欲望,而不能不有所自制;[2]6
由于以上的三大约束,我们对欲望的满足要求,或不至于到“求而无度量分界”的地步,“不能不争”一事可能无从说起。这也是说,在“供过于求”或生产力过剩的这个时代,人类的问题恐怕不是起于资源的稀缺,而是如何消化这些资源不致浪费,所衍生的问题(如)已远非荀子所说的“争则乱,乱则穷”一事了。
最后,荀子的这一套“礼学”(或手段上的“分学”、目的上的“群学”),是不是有一学人所说的“资源决定论”(resource determinism)的色彩,亦不无可议。我们知道,荀子在《荀子·礼论》一再强调“礼者养也”的“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基本功能,并且以为“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才能根本地解决人群的资源争夺之乱局。关于这点,上提平克在《人性中的美好天使》将其概括为“资源决定论”的说法,并如下评论道:
资源决定论的一个典型,它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如土地、水、矿藏和战略地带。有一种见解认为,冲突的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如果能够公平地分配资源,人类就能实现和平……
在历史上,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对资源的争夺却无法解释暴力的大趋势。过去 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如宗教、革命、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人类的灾难真的和钨或者其他什么资源没有关系,但是,所有要证明这些灾难起因于争夺资源的努力,都象是偏执的阴谋论。[1]262-263
按上引,平克以为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历史众多暴力事件的起因,但要将后者归诸于资源争夺的单一或唯一原因,则不无有以偏概全之嫌。换句话说,荀子将人类社会的“乱”归诸于“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的原因,是否也是“偏执的阴谋论”之一,值得深思。
总结地说,荀子的“礼学”在“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这一方面的认知是合理的。但是,在“分”的必要性、“争”的起因是不是源于“使欲必不穷乎物”的原因和界说上,则还有商榷之处。按《荀子·性恶》的“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的说法,荀子的“乱”是否是人类社会根源性的“乱”,还有待进一步“辨合”与“符验”,它的“分”的“张而可施行”的效度还存在一些变数。这是我们今天重提荀子或《荀子》一书的“礼”学时,务须留意的时空变迁所带来的不同条件与形势。
[1]平克.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M]. 安雯,译. 北京:中信银行,2015.
[2]卢映西. 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J]. 经济学家,2005(5).
(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苏红霞)
B222.6
A
1673-2030(2016)04-0028-06
2016-08-15
郑文泉(1970—),男,祖籍福建永春,现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双溪毛糯,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教授兼中华研究院副院长,近著《东南亚朱子学史五论》(2014)、《殊途不同归:东南亚儒家思想的阶层分化》(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