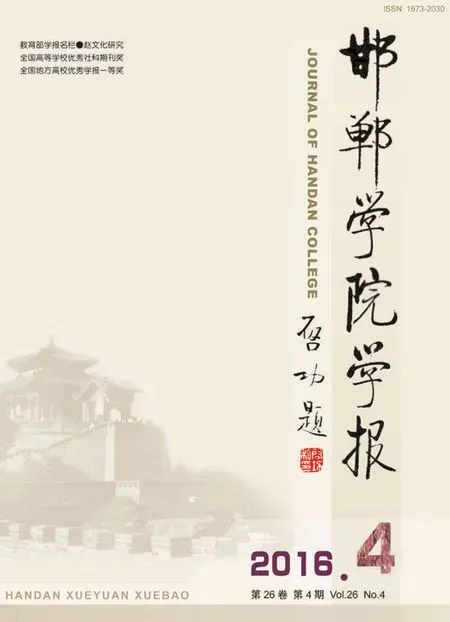秩序与方法
——荀子对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理解
2016-03-15东方朔
东方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秩序与方法
——荀子对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理解
东方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学者在讨论孟、荀两人的理论差异时,大多集中在他们各自所持的人性论上,但他们在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主题上却目标相同,此即如何在一个充满“争”与“乱”的世界中重建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若因其所“同”而观其所“异”,则其所“异”的可能解释之一便表现在“如何建立秩序”的方法问题上:孟子主张以“仁心”之直推以求政治秩序之实现,荀子则坚持以客观化的“礼”为架构来重建政治秩序。孟子对建立政治秩序的思考完全取资于个人自足的内在“仁心”,就即道德而言道德的角度上看,其思想无疑成就了道德的尊严和人格的伟大;但若必欲借此而言政治,却会因其对政治之特性缺乏可靠的认知基础而导致政治上的空想主义。荀子对重建政治秩序的致思则委诸于先王制作的“礼”,礼的内涵虽然包容甚广,但与孟子的“仁心”不同,荀子言礼的首出的意义是政治学的而非伦理学的,是为了去乱止争以实现“出于治”“合于道”的政治目的而形成的一套制度设计。即此而言,在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主题面前,若与孟子言仁心之兴发和推扩相比,荀子的此一主张无疑更具有客观和可实行、可设施的特性。然而,荀子的礼既是政治学的,又是伦理学的,其间各自在根源上的分际并不明确;同时,由于荀子心目中紧紧绞固于政治秩序的实现,道德则不免沦为维护政治的手段,乃至常常以政治的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其结果则导致对专制政治的强化。学者谓荀子尊君、重势、倾向于独断,良非无故也。
荀子;孟子;政治秩序;仁;礼
赵文化研究•荀子专题[教育部名栏]
学者普遍认为,在先秦儒家中,相对于孔子而言,孟、荀两人在理论上各有偏失。孟、荀的偏失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学者对此已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孟、荀之间不仅有相似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相同的时代任务和主题,此即如何在一个充满“争”与“乱”的世界中重建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盖凡“如何”之疑问皆有方法入路上的讲求。换言之,是由心性道德直线以求政治秩序的实现呢,还是由政治和政治目标为首出原则以言道德的规范法则?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先秦儒家作为一个整体大体上皆表现为一种德化政治的形式,荀子思想虽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礼治主义,但也与孔孟的德治主义相类。然而,孟子以“仁”之直推以求政治秩序之实现与荀子以“礼”为架构以重建政治秩序,这两种看法实即蕴含着方法上的差异:一者由道德而说政治,一者由政治而说道德;前者表现为道德化的政治,后者表现为政治化的道德,其间的理绪和长短得失正是本文所欲检讨的主题。
一、政治、道德与政治的道德基础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不特儒家——之兴起,大体皆面临着一个“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问题,因此,如何克乱成治,安顿社会秩序便成了他们立言指事的一个中心议题。张舜微曾经说过,“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1]前言理论上,救时之治指向秩序之安顿,而秩序问题则指向政治之主题。虽然,在孟、荀之时,重整政治秩序之主题已被时代推到了前台,但是,如何建立秩序?建立何种秩序?此类问题在各家各派乃至在同一学派内部依然纷争不断,前者涉及到方法,后者则涉及到目的①Loubna El Amine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一反学界认为的儒家的政治主张乃是其伦理思想的自然延伸的看法,认为儒家的政治观念并非直接来自于儒家的伦理学,政治秩序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推动原则,并认为,早期儒家所提倡的许多政治行为并非严格意义上服从于自我修养的伦理学。Amine之说有其自己的理路和脉络,本章不欲对此进行全面的评论。参阅Loubna El Amine, Classical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A New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pp15-16, p26, p146.。
就孟、荀而言,在“建立何种秩序”(目的)的问题上,笼统地说,他们之间有大体相同的理论诉求,亦即指向寻求一种儒家式的王道秩序②此处所谓“大体相同”一说,只能笼统言之,若细究之,此间自然仍有差别。;然而,在“如何建立秩序”(方法)的问题上,孟、荀却存在着分歧,简单地说,孟子希望从道德而说政治,荀子则试图从政治而说道德;由道德而说政治,其结果则可能由道德的理想主义转而成为政治的空想主义,而由政治而说道德,其结果则可能由政治的现实主义导致道德的“控制主义”。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则孟、荀各自的偏失可得一解,而荀子对孟子的批评亦还可见其“意义剩余”。
不过,在具体说明此一分歧之前,我们还必须区分清楚:“从道德而说政治”或“从政治而说道德”与“政治的道德基础”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政治的道德基础或政治为什么必须讲道德讨论的是从道德的立场而要求的政治的正当性问题,人有权要求得到国家的公正对待,我们也常常从道德的角度去要求政治和批判政治,因此,作为制度的政治必须接受来自道德的咨询,亦即从道德的观点去评判政治本身是否合正义。而本文所谓“从道德而说政治”或“从政治而说道德”讨论的则是政治秩序建立的次序与方法问题,无论孟子还是荀子皆十分注重政治的道德基础,但政治(秩序)问题不能即是道德问题,反过来,道德问题也不能即是政治问题。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虽然会认为政治与道德两者有密切的关联,但毕竟道德是个人修身之事,无限之事,而政治治人却是大众之事,平面之事;道德是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而政治是从制度上立人权的命③参阅徐复观:《为生民立命》,载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190页。,两者对象不同、性质不一、方向各异。
就西方而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大概可以从马基雅弗利那里算起,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他(指马基雅弗利)所写的几乎都是治理之道、强国之术、扩权之策以及导致国家衰亡的各种错误。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注的唯一课题,而且他还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因素几乎完全分隔开来,除非后者影响到了政治策略。”[2]14-15由此可以看出,马基雅弗利已将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德性概念加以剥离,把政治理解成与道德无关的、纯粹权力运作的技艺。逮至霍布斯,政治哲学已完全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规则、条令、责任、义务等概念取代了德性,他“旨在证明的并不是实然的统治,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必然的统治,其目的就是要成功地控制人,因为人的动机也就是人为机器的动机。”[2]177
无疑的,将道德完全从政治中剥离出去,在理论上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儒家在此一问题上则始终坚持政治对道德的承诺,坚持两者的统一。当然,儒家持“政治的道德基础”此一立场并不同时意味着混淆道德与政治在理论上也有其合理性,这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在终极的理想上,孟、荀都认为,道德秩序即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秩序即是道德秩序,但在“如何建立秩序”的次序问题上,孟、荀两人却有方法入路上的差别,牟宗三先生认为:“孔子与孟子俱由内转,而荀子则自外转。孔孟俱由仁义出,而荀子则由礼法入。”[3]120又云:孟子“特顺孔子之仁教转进悟入而发挥性善……荀子特顺孔子外王之礼宪而发展。”[4]203牟先生此说是从总体上阐述孔孟荀思想的特点,今暂且撇开孔子不论,即就孟、荀而言,此处“由仁义出”和“由礼法入”也可以看作是两人在安顿社会政治秩序上的方法的不同,“由仁义出”表现为“从道德而说政治”,“由礼法入”则表现为“从政治而说道德”。从重建秩序这一时代课题而言,这一不同也是导致荀子强烈批评孟子的原因之一。以下我们只就孟子言“仁”与荀子言“礼”之意义及其关系略加说明。
二、道德的可欲性与政治的可行性
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孟子立言的问题意识,此即面对霸术横行、世衰道丧,“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现实,孟子主张,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推扩每个人内在的仁心(道德心性)。孟子的逻辑十分清楚而明确,首先,给出历史和理论的说明,“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离娄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其次,奠定由道德说政治的理论基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故秉此不忍人之心“苟能充之,足于保四海。”(《公孙丑上》)最后,阐释实现的途径和方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于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梁惠王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以上三点就孟子由道德说政治之内容表现而言或有遗漏,但核心当不偏不差。
若仔细观察孟子的这种思考逻辑,其中蕴含了一个核心观念,此即在孟子看来,个人内在的心性道德或人的怵惕恻隐之心乃是政治秩序实现的充分条件,由道德而政治是直贯地表现出来的,而且两者在内容上是同质的。刘殿爵先生认为,“孟子的政治哲学……不仅与他的道德哲学相一致,而且是从道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5]4孟子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个人自我之身是道德和家国天下的基础,德化自我之实现即是国家天下秩序之完成。只不过这样一种核心观念似乎仅止于“理”上的“应然”,而不能成为“事”上的“实然”。何以故?盖“理”上的“应然”所表现的只是个人心性道德的“可欲性”(desirability),而“事”上的“实然”却要说明政治秩序建立的“可行性”(practicability)。问题在于,成德活动可只求诸个人,欲仁而至仁,无需假借和旁代,而政治行动及政治秩序的建立却需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量,涉及到权力与支配关系;成德活动可依于个人内在心性的觉悟,随感随应,随应随润,而政治秩序的建立却必需有一个法度常规的形式上的安立。假如没有对政治和政治秩序之相关概念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反省,纯持一道德实现之思路与方法而言政治,那么,其间之转进也就不免会由道德的理想主义变成政治的空想主义。孟子可以让齐宣王认识到他有恻隐之心,并且经由其指点齐宣王也意识到自己应当对其治下的百姓施以好处[6]322-323,然而孟子却终不能让齐宣王恩及于百姓。从道德的角度上看,我们当然会赞同孟子对齐宣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的评判,然而,若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则无论是齐宣王的“不能”还是“不为”似乎皆含有待说明的空间。史华兹教授就认为:“孟子向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作了如下说教:要与他们自己心中的善的根源保持接触。但这些似乎全都是无用的,只能使得不同情这种学说的人们确信:儒家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7]327为何孟子对齐宣王的“劝导”“全都是无用的”,是“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因为政治不同于个人的道德修身,政治是事上的现实关心,有其自身的对象和逻辑,也有其自身独特的方法。今且撇开其严刑峻法不论,韩非子倒以其冷峻的目光对政治现实有着深刻地打量,其云:“处多事之秋,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礼,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八说》)然而在孟子的思维中,政治独立于道德的特性已被彻底地取消,政治秩序建立的“可行性”已完全等同于道德修身的“可欲性”。此或正是荀子批评孟子“无参合符验”(概念的不确定)、“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形式的法度常轨没有安立)的原因之一。
三、“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转至荀子,学者皆认为,与孟子重“仁”相比,荀子思想之核心在“礼”,而言“礼”通常又让人想起道德的行为规范,只不过与孟子的“仁”相比,一个重在内,一个重在外而已。一个确定的事实是,无论孟子言仁还是荀子言礼都与其各自所持的人性论主张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孟子由性善论直接引出的是道德哲学,荀子由性恶论直接引出的却是政治哲学。因此,当荀子说“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荀子言“礼”的首出意义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伦理学或道德的行为规范①此处需特别注意,笔者所说绝非意味着荀子之礼不是或不含道德的行为规范义,荀子言礼的范围至广至大,上至人君治国之道,下至百姓立身处世之节,莫不涵摄,道德自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只是为了突显荀子言礼的首出意义是政治的,道德规范义当在此一前提下得到理解。何谓“首出意义”?“首出”的意思主要强调其“第一序意义”(the first order meaning);“首出”绝不意味着“独出”、排斥“次出”,其还包含有“第二序意义”(the second order meaning)。——因为作为人的自然情性的性恶根本不能直接引出道德规范——而首先是为了去乱止争、为了满足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换言之,在荀子那里,政治和道德均需要礼(礼义),但与孟子言仁不同,荀子言礼的首出意义是政治的而非伦理的,是服务于去乱止争以实现“出于治”“合于道”的,其根源在于人性恶,而所谓出于“治”合于“道”,其实质意义即是为了政治秩序之达成①Eric Hutton教授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指出,在荀子那里,“出于治”并不等同于“合于道”,认为“治”乃“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治”也包含道德修身的内容,而非全部都是政治的,这些见解,甚中肯。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无意将“治”的意义悉数归于政治,只是强调了它的首出意义或根源意义;第二,从“出于”和“合于”的措辞看,似乎恰恰印证了这样的看法,即礼之作为“治”的初始的、第一序的意义是政治的,但此一意义却不是礼的全部内容,还需上升到“道”即包含道德内涵的高度;最后,我之所以强调荀子“治”的首出含义为政治,主要出于荀子对礼之根源的看法。在荀子那里,礼的根源与礼的来源不同,后者荀子将之解释为圣王之制作,而前者则出于“欲多而物寡”的矛盾。依荀子,此一矛盾的发展在逻辑上将导致“争乱穷”的结果,故荀子认为圣人“恶其乱也”而制礼义以治之。这样,从礼的根源处看,礼所对治的“争乱穷”显然首先应从政治上得以解释,而非从道德上或道德与政治平列的意义上来解释,但这种说法并不排斥礼所包含的道德意义,这两者在荀子那里完全、也应该是兼容的。。
事实上,荀子所处时代的情状与孟子大体相同,皆是一个以声色货利和争战所搅动的世界。然而,与孟子信心满满地诉诸于个人的仁心以实现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不同,荀子乃是反思性地着眼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欲多而物寡”的特殊状况,并据此作为自己重建新的政治秩序的理论前提。所以,荀子论礼的根源必归本于“欲多而物寡”,依荀子的逻辑,若“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荣辱》),因此,若无必要的度量分界(礼),其结果必将导致“争、乱、穷”,及其至者,则将会是一幅“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性恶》)的恐怖图景。不难看到,荀子言礼在根源上首先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所存在的“欲”与“物”之间如何能够“相持而长”的一套制度安排,故云“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又云“国无礼则不正”(《王霸》)、“隆礼贵义者,其国治”(《议兵》),若铺排而散开地说,此礼所呈现出来的理想秩序则是“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或许正有见于此,面对重建秩序的时代主题,荀子似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孟子的道德天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人的天性,亦即所谓的“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荣辱》)根本承担不起建立任何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基础,道德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
果如是,则荀子立言指事的问题意识在理论上似乎就必当有所交待。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萦绕于荀子思想中的问题意识当是,面对以物力呈精彩,“乱国之君,乱家之人”各呈其私的时代现实,在荀子看来,孟子那种试图以道德“推恩”的方式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努力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劳而无功的,其结果不仅不能有效地重建秩序,而且也不能成就仁德自身②如果把荀子将思孟“五行”批评为“无类”、“无说”、“无解”的看法,从重建社会秩序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显然可以发现更多的“意义剩余”,此处不予以展开说明。。事实上,荀子对此有着相当自觉的理论反省。荀子云:
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大略》)
对于上一段所引“仁有里,义有门”一说,学者可能会想起《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之比喻。实则,依杨倞,“里与门,皆谓礼也。里所以安居,门所以出入也。”这一段固然可以从纯道德哲学的意义上理解,然而,联系到荀子言礼的首出义以及孟子劝齐宣王“推恩足以保四海”的言说脉络,此段之理绪依然可以是政治哲学意义的。依荀子,仁之情爱所表现的亲敬,义之合理所表现的能行,必待乎礼而后成。言仁行仁而不合乎礼,则不是仁;事属义举而行之不合乎礼,也不是义。由此在荀子看来,徒心存仁恩,而行之不由礼(意即在政治行动层面没有建立起客观制度意义上的法度常规),即此仁恩顶多只是个体的主观内部的必然性,而秩序之建立和贞定却非徒出于个人内在的怵惕恻隐之仁心,必有赖于安顿社会人群之法式亦即制度之建立方可维系,此观孟子对齐宣王之劝说可一目了然。仁心仁恩之推扩固清渟精微,但对于秩序之达成而言,却是“坐而不可设,起而不可施行”的;而且作为一种自我意识,这种主观心存的仁恩在其内部只是与其自己相关,因为它忽视了外在的客观规定(“非其里而处”)的特殊性③参阅拙著《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316页。此处所谓“只是与其自己相关”并非说仁心仁恩不及于外物,唐先生即谓“我自己之尽心,即将外之人物涵摄于我心之内。”(氏著《中国哲学原论·上册》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年,第83页)而是说孟子未尝对仁心所面对的政治事务的独立性作必要的简别。。平情而论,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即主体意志之自由自决以成就道德的尊严,就即道德以言道德而言,实乃光辉所及,在山满山,在谷满谷。然必欲即此而言政治秩序之实现,依荀子,至少在理绪上是无条贯的,隐幽而闭结的,相反,礼才是仁心真正是其自身、在其自身的实现场所,仁心只有藉礼才能获得其社会历史内容的客观规定性。若只重仁心反身上提之一缘,没有广披及人之客观规制,则这样一种反身上提只是通过某种先验的保证,而不是通过使世界辨证化的方式赋予自然、社会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8],如是者,则仁心如何获得“真理意义”上的有效性并进之于客观化其自身,至少在荀子看来是可深致怀疑的。正因为如此,荀子必进而言“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事实上,正是这句言简意赅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荀子面对孟子时的整个思想的立言的问题意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推行仁恩仁心而不借助于礼,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就真正的仁德,无疑的,若想以此进而求政治秩序之落实,则无异于刻舟而求剑,南辕而北辙。
四、“礼义之谓治”
明乎此,我们便可明白何以荀子要提出“隆礼义而杀诗书”(《儒效》),因为荀子断定“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不苟》)治、乱当然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说的,换言之,在重建社会秩序的主题面前,荀子自觉地放弃了孟子由道德(仁)说政治的思考方式,而采取了由政治(礼)说道德的基本进路。孟子长于《诗》《书》,而荀子之学正以“隆礼义杀诗书”为特色。荀子为何要“隆礼义而杀诗书”?此即涉及对《诗》《书》特性之了解。《劝学》篇云:“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其意是说,上不能尊贤者以为师法,下不能以礼法约束自己,只学到一些杂博的知识,顺诵《诗》《书》之文字,则到死亦不免于陋儒而已。“顺诗书”,《诗》言情,《书》纪事,《诗》《书》固可以兴发,然而,此所谓“兴发”所表现者只是主观精神之跃动,或恻隐之心之觉感,不能有规范,不免于飘忽,而难于凝制,难于坚成。况《诗》《书》“故而不切”(《劝学》),“必待乎礼之条贯以通之”[4]196,故荀子必云:“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只是一味地向高处提,向深处悟,“兴”之无边,“发”之无际,则不免了无崖岸,乃至空发议论,兀自吟而已。
荀子以一句“不可以得之”批评了孟子,与《诗》《书》的兴发相比,强调了礼之统类和法度常规的庄严与凝重,我们亦可以说,此礼乃是社会政治秩序所以可能之基础和保证。但我们从何处可以看出此礼具有政治秩序之“基础和保证”的功能?简言之,即是此礼不仅具有规范的正确性,而且具有规则和设施(制度、秩序)的公正性、客观性。平情而论,礼具有规范的正确性,乃向为儒者所雅言,而礼具有“辨合符验”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具有“起而可设,张而可施”的设施义和轨道义,则为荀子再次阐释而出。为何说是荀子将礼的公正义与轨道义“再次”阐释而出?盖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荀子礼的主张与《左传》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①参阅张亨“荀子的礼法思想试论”,载氏著《思文之际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150-191页;又见蒋年丰《文本与实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79-310页。,而在《左传》中,“礼”原就具有“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政之舆也”(襄公二十一年)之义,尽管《左传》言礼之根源与荀子有所不同,但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之意昭昭然,此后《左传》的此一观念随周文疲弊而渐次不显,至孟子即一句“仁义礼智根于心”,将礼的根源作了主观内在化的处理。事实上,当孟子说“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时,在这种说法中,礼只是“门”而已,礼之实,不过“节文”仁义而已(《离娄上》),“这意味着‘礼’丧失了其独特的地位。若将《孟子》与《论语》相比,就能看出礼之重要性的减低。”[9]152至与《左传》相比,礼之重要性的降格更令人不堪。故逮至荀子,即再举礼的客观义与政治法度之义,只不过荀子言礼之根源与必要已既不同于《左传》,也不同于孟子,而是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欲”与“物”的紧张中逻辑地推出②一般而言,《左传》言礼之根源乃从“天地之经”上说,故云“礼以顺天,天之道也。”(文公十五年)荀子亦言“天有常道”,但此常道并没有人为的政治秩序义和价值义;同样,荀子言礼也不从人的天性中的自然情性出发,恰恰相反,正正因为人的这种自然情性若任其发展乃必然导致争乱,故礼才有其必要。。因此,在荀子看来,孟子靠仁心的兴发和“推恩”的方式以求政治秩序的实现既不可得,则其恰当之途彻必当资之于“礼宪”。但是,什么是“礼宪”?何以荀子针对孟子顺《诗》《书》之主观的兴发要强调“礼宪”?此中关键即是荀子要突出礼之作为“宪”的特殊意义。但什么是“宪”?从字义上看,“宪”作动词,其义为“公布”,如《周礼·小司徒》云:“令群吏宪禁令”;若作名词,则多作法和法令解,如《尔雅》谓“宪,法也。”又,据《管子·立政》篇记载,“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气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又云:“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不难看到,“宪”之原义乃是君王所颁布的治国的准则或法册,宪之所及,则政治秩序井然如风动草偃,如百体从心。可以肯定,荀子言“礼宪”既与《左传》有关,也与稷下学的《管子》有关①参阅孙红连《荀子礼法思想渊源考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管子》一书的学派归属一直存有争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列入法家,此后历代官志也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等学者又将《管子》归入杂家。,而荀子所以重言“礼宪”,其所欲表达的正是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准则义或法册义,故礼是政事之规则、制度之标准和组织人群的法式,牟宗三先生认为,荀子重礼宪,而“礼宪是构造社会人群之法式,将散漫而无分义之人群稳固而贞定之,使之结成一客观的存在。故礼宪者实是仁义之客观化。”[4]200
翻检《荀子》一书,礼之作为治国之准则和法册的说法所在多有,且遍及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王霸》)故《大略》篇又云:“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是治国的车挽,治国不以礼,则政令不通。荀子甚至以礼作为国家之托命,而谓“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王霸》)而作为正国之具,礼所表现的秩序、法度若要为人所守而不乱,则客观、公正之规则、设施必为第一悬设,故荀子又云:“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所谓“绳墨”、“衡”、“规矩”等等言说所表达的乃是礼之理具体化于社会国家之组织制度,并凝结于社会国家之组织制度本身之中,作为形塑和构造秩序与人群的准则和法式,荀子言礼之“分、养、节”三大作用俱表现出此一特点[10]145-160②此处“礼”与“礼义”可通解。,故云“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王霸》)又云“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姓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富国》)如此等等。一句话,在重建政治秩序此一坚硬而严肃的现实面前,与孟子言仁心之兴发所具有的灵动和飘忽相比,荀子言礼则显发出别样的郑重与肃穆。
五、“善者,正理平治也”
荀子重礼的客观义与制度义,认为礼是实现和重建政治秩序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故礼的首出意义是政治的或政治哲学的。但正如前面所说,在荀子那里,礼并不仅仅只是政治的,同时也是道德的。凡个人之治气养心、饮食衣服、居处动静、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等等,在荀子看来皆当以礼为规范。实际上,《荀子》一书前四篇之《劝学》《修身》《不苟》《荣辱》皆言以礼作为个人进德修身之规范,故云“礼者,所以正身也。”(《修身》),“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陈大齐先生认为,在荀子那里,“礼义之用以为治国规范的,特别称之为政治,礼义之用以为修缮个人人格的准绳且用以为个人处世接物的规范者,特别称之为道德。”[10]182那么,作为政治的礼与作为道德的礼,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陈大齐似乎并未指明。有一种看法以为,在荀子那里,礼既具有政治义,又具有道德义,两者是重合的,统一的。一般地说,这种看法并非无据。但在“既……又……”的句式中,礼之政治义与道德义无形中被置于并列或平列的地位,其间的前后轻重关系则不易看出。其实,当我们判定荀子思想的特点是“从政治而说道德”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便已有了确定的分位,换言之,礼的首出意义既然是政治的,那么,礼的道德意义当在此一前提下得到说明,道德从属于政治,但又不止于政治③我们可以从《非十二子》篇中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此即荀子对诸子缺憾之评述几乎全部落在政治层面,如谓它器、魏牟“不足于合文通治”、谓陈仲、史鱿“不足于合大众、明大分”、谓墨翟、宋钘“不足于容辨异、悬君臣”、谓慎到、田骈“不可以经国定分”、谓惠施、邓析“不可以为治纲纪”、谓子思、孟子“不知其统”。。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荀子对善、恶概念的理解上来。理论上,道德是讲求为善去恶的修为活动,所以,一般而言,道德哲学皆有其对善、恶的特殊定义。但荀子对善、恶的理解却颇具意味,值得我们认真分析。荀子对善、恶的说法颇多,但最具定义效力的莫过于《性恶》篇的一段,荀子云: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
此处,荀子对善、恶的概念似乎给予了明确的定义,而其动意即是针对孟子“人之性善”说而来的。在荀子看来,“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性恶》),并借此提出了自己善、恶的概念。就此而言,荀子显然认为,孟子的性善说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此即无辨合符验和不可设施,前者无法征之于经验,后者无法张之于制度。“经验”与“制度”所透显的皆是可衡断、可把捉的规则义、客观义,这种理解一方面印合了我们前此对荀子礼的分析①在荀子,合于礼才是善的,不合礼,则无善可言,故云“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论》)而礼在修身方面正表现出规则设施的客观义。参阅拙著《合理性之寻求》第235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理解荀子的善、恶概念提供了某种指引,至少荀子的言说脉络给了我们理解善、恶以某种暗示。因此,对于上引一段之了解似乎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正理平治”?其二是“正理平治”是否足以涵盖荀子言善的全幅意义?
有关“正理平治”一词之理解,王先谦《荀子集解》、李涤生《荀子集释》、梁启雄《荀子简释》、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皆无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简称“北大本”)《荀子新注》谓:“正理平治: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11]395张觉将此四字翻译为“端正顺理安定有秩序。”[12]342与此相类似,王天海则将此四字分别解释为“正,端正;理,合理;平,安定;治,有序。”[13]948北大本的解释与张觉和王天海的解释有所不同,未就“正理平治”四字作单独的了解。实则“正理平治”既可以拆分成单独的字来理解,也可以作一个词组来理解,同时,若将其与“偏险悖乱”相对,则似乎也可以将之分为“正理”与“平治”来理解,因为荀子就将“偏险”与“悖乱”分开,而言“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就此而言,以“不正”对“正理”,以“不治”对“平治”在文字对应上也可相通。
应当说,北大本将“正理平治”解释为“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可以说扣住了荀子的思想,呈现出了荀子所欲表达的善的可衡断、可把捉的规则义,此规则义显然是偏重从政治一面说的;而张觉和王天海将“正”理解为“端正”,张觉把“理”理解为“顺理”,似乎有偏重于主观态度的一面,与荀子言礼(善)的用意当有一间未达之病。其实,海外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Burton Watson将“正理平治”翻译成“upright, reasonable, and orderly”[14]162,而John Knoblock则将此译为“correct, in accord with natural principles, peaceful, and well-ordered”[15]155,相比之下,最值得注意的是,何艾克(Eric Hutton)将此译为“correct, ordered, peaceful, and controlled”[16]288。以上三位学者对“正理平治”的理解各有不同,Watson把“正”理解为“正直”,偏重于德性义,不如Knoblock和Hutton浃恰;但Knoblock把“理”理解成“合于自然法则”,解释空间颇大,可能也与荀子思想不侔;在我看来,上述三位学者当中,何艾克的解释最为得当,也最切合荀子之意,尤其他将“理”理解成“合于秩序”②荀子盛言“君子理天地”、“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王制》),此“理”即具有明确的秩序义,请参阅本书第六章的相关内容。、将“治”理解为“管控”,颇具点睛之功,若无对荀子有深造自得之熟见,则断不能出此心解,可谓深得荀子思想之精义,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若合符节。果如是,则荀子所谓“善”乃是指规正、有序、平和与(得到有效的)管控。
可是,明眼人一看即明白,上述所谓“规正、有序、平和与(得到有效的)管控”在在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学意味的概念,结合荀子重建政治秩序的主题以及他对孟子的批评而言③李涤生认为:“由‘正理平治’言善,即由客观之表现以言善,孟子是以主观之动机以言善,二者亦相反。”氏著《荀子集释》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548页。,如果我们把此处的“善”理解为一个伦理学的概念,那么,荀子以这一意义的“正理平治”释“善”则显然蕴含着由政治说道德的意思,换句话说,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道德(善)是由政治(正理平治)来规定的、来理解的,道德的意义首先不是个人善的完成,而是“公共善”(common good)的实现。[17]27
不过,另一方面,所谓“善”是“规正、有序、平和与(得到有效的)管控”之意,显然是作为一种结果的描述,而且这样一种描述在荀子的言说脉络中又各以正、反的方式关联到“古今天下”和“人之性”。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荀子“善与恶的界说和分辨,是在‘古今’的时间纵轴以及‘天下’的空间范围论述的,‘天下’尤其值得注意……。”[17]27因为天下(国家)指向的正是政治的议题,因此,当“正理平治”关联到天下(国家)时,其“善”的特点表现出强的约束性规范特征。但是,荀子的“正理平治”也还以否定的方式关联到“人之性”,虽然此一方式也与天下国家相连。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情性)并不能直接引出“正理平治”的结果,因为“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恶》)若人之性本就是正理平治,则毋须圣王与礼义。不过,此处可分两面说,就人之情性而言,若任其发展而无礼义的度量分界,则会导致争乱而不合于善(正理平治);就人之材性而言,则又包含了“质具知能”的可学、可积、可塑造之意。[18]101-102无疑的,荀子言积学、塑造的内容不离礼义,而礼义又是“善”的另一种说法,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即此而遽然断言礼义教化的作用仅在于实现正理平治?或者说,荀子言“善”的意义只在于确保和实现社会的政治秩序?
许多研究荀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虽然荀子与霍布斯有大体相似的自然状态理论,但与霍布斯纯粹以政治方式处理问题不同,荀子还注意到对人的行为的修养与转化[19]416,而黄百锐(David B.Wong)则认为,荀子的自然状态理论与霍布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荀子那里,当人们认识到他们在求取欲望满足的过程中需要有所限制后,人们不仅知道需要限制他们的行为,而且还认识到需要透过礼(ritual)、乐(music)和义(righteousness)来转化他们的品格。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兴趣上喜爱这些东西,而不仅仅只是让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20]203假如我们认同这种理解,那么,当荀子在《性恶》篇将“善”了解为“正理平治”时,我们就应当看到,一方面,“善”的首出意义的确在于安顿社会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善”所包含的礼义教化又不止于安顿社会政治秩序,而同时也指向人格的教化与养成。明乎此,《劝学》篇所谓“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便可得到圆满的解释,因为按照荀子的说法,“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劝学》)然则,什么是“美其身”?J.Knoblock认为,“美其身”就是“使人的品格变得优雅。”①John Knoblock, Xunzi: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s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40. John Knoblock将此句译为“The learning of the gentleman is used to refine his character.”此外,J.W.Schofer则在“Virtues in Xunzi’s Thought”一文中着重探讨了荀子思想中德性获得的“发展模式”,请参阅T.C.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nhoe,ed, Virtue,Nature,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 2000,pp69-88.② 余英时先生曾用“离则双美,合则两伤”来说明其中的关系,参阅氏著《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1页。无疑,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所包含的理论后果涉及到各个方面,如道德的工具化、道德说教、以政摄教的道德控制主义等等,今不赘。
六、规范的“奠基”与“动机”
沃林(S.S.Wolin)在《政治与构想》一书中认为,与洛克相比,霍布斯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强调政治范畴的特殊性,因为洛克将一个符合理想化社会的有利条件设定为自然状态,但在沃林看来,如果在没有冲突和抗争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政治秩序,便已不再是“政治性”的秩序,因而也无形中贬低了政治范畴的地位[21]323,而霍布斯与洛克不同,在他所设定的自然状态下,由于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境况,因而政治秩序和权威等便具有了维护社会与文明的特殊作用。
大体说来,荀子的思想与霍布斯相似,具有强调政治范畴与秩序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的特征,这从其在重建秩序过程中采取由政治而说道德的方式上可见一斑。不论是出于理论的预设还是出于现实的关怀,在一个天下离乱而亟待重整的时代中,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可选择性显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辩护,换言之,韩非所谓“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礼,非圣人之治也”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为荀子接纳。然而,理论上,这样一种方式又会存在何种问题?似乎一种为人所熟知的了解方式就是从概念上区分政治与道德的特性。政治是事上的现实关心,它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政策和法令等来建立秩序,实现对社会国家的有效管控和治理,因此,它面对的是公共领域,需要解决的是权力的运用以及利益的平衡;而道德是理上的终极关怀,它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律以及自我修养和说服教育,以实现个人德性的提升,并保持自由的思考和批判的心灵。如果即此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采取由政治而说道德的方式,或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其逻辑结果必定强化政治的专制,扼杀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生长②。
在荀子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皆认为,荀子的思想具有导致专制、独裁的倾向,易于堕入强制性的权力机括之中。此种看法,或非只是空穴来风,相信必有其所以得出如此看法之依据。在论及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Bernard Williams曾引入“制定模式”(enactment model)与“结构模式”(structure model),以为在“制定模式”中,政治理论表达原则、规范与理想,而政治则通过说服、劝导和权力的运用在政治行动中对此给予表达,而此一模式在理论指向上则通常表现为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22]466-480或许在具体分析上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认同Williams的看法,不过,荀子有关由政治而说道德的主张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制定模式”的特点,道德在政治的强力面前颇难独立地被说出,乃至于常常只成了实现政治秩序和维护政治理想的手段和工具。陈来认为,荀子对礼义始终坚持“先王制礼说”,突出政治权威和历史实践的作用,“但是,如果突出政治权威,则人对礼义的知能只是对政治权力及体制的服从,价值上的认同又从何而来?”[18]115牟宗三先生则认为,荀子言礼义只是经验论与实在论地言之,然而,“礼义究竟是价值世界事。而价值之源不能不在道德的仁义之心。其成为礼文制度,固不离因事制宜,然其根源决不在外而在内也。此则非荀子所能知矣。落于自然主义,其归必至泯价值而驯至亦无礼义可言矣。其一转手而为李斯韩非,岂无故哉?”[4]226-227牟先生此言直指规范的正当性的基础问题,盖对礼义法度之了解必须优先区分“奠基”与“动机”问题之不同,所谓“奠基”所涉及的是礼义法度之作为道德规范的义务性或道德性之最终的理性根据问题;所谓“动机”所指涉的则是礼义法度为了何种现实的目的而去实践的问题。若对礼义法度之最终的理性根据之追问转成对礼义法度之现实性和目的性使用(“因事制宜”)之考量,则在理论逻辑上便可能导致堕入对外在权威之服从的机括之中。对此,劳思光先生似乎说得更为决绝,劳氏云,在荀子那里,“礼义之产生被视为‘应付环境需要’者,又为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者。就其为‘应付环境需要’而论,礼义只能有‘工具价值’;换言之,荀子如此解释价值时,所谓价值只成为一种‘功用’。另就礼义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而论,则礼义皆成为外在(荀子论性与心时本已视礼义为外在);所谓价值亦只能是权威规范下之价值矣。”“如此,荀子价值论之唯一出路,乃只有将价值根源归于某一权威主宰。实言之,即走入权威主义。”[23]339-340劳氏对儒家义理之了解固与牟氏别有理绪,但对荀子因价值根源之旁落而可能走向专制和权威之看法,则两人多少有其相似之处。荀子汲汲于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之主题,因而对理论之思考更偏重于其所具有的可“符验”、可“设施”的效果性质。即就政治之“事”的现实关心而言,其动机似乎并非一无是处;然而,至其即此而言道德,即道德所必当具有的自由而超越的奠基便可能遭致萎厄而终沦为政治权威之附庸。
与牟、劳相似,徐复观先生对荀子思想中所包含的走向独裁政治的倾向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认为荀子所言之礼完全限定于经验界中,否定了道德向上超越的精神,且此一不以仁心为基底的礼,也引出重刑罚、尊君、重势的意味来,以致多少漂浮着极权主义的气息[24]258-259。在“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中,徐复观又进一步认为,在荀子那里,“礼义既由先王圣王防人之性恶而起,则礼义在各个人的本身没有实现的确实保障,只有求其保障于先王圣王。先王圣王如何能对万人予以此种保障,势必完全归之于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这样一来,在孔子主要是寻常生活中的礼,到荀子便完全成为政治化的礼。礼完全政治化以后,人对于礼既失掉其自发性,复失掉其自主性,礼只成为一种外烁的带有强制性的一套组织的机括。在此机括中,虽然有尚德尚贤以为其标准,亦只操之于政治上的人君,结果只会变成人君御用的一种口实。于是荀子的‘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的理想社会,事实上只是政治干涉到人的一切,在政治强制之下整齐划一、没有自由、没有人情温暖的社会。”[25]94-95如前所云,荀子言礼义之目的是否完全即是政治的,或可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徐氏所言的确看到了荀子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殊非只是格于学派的偏执之见。
当然,学者的上述看法似乎多是一种理论的逻辑推导,但若揆诸荀子文本,则荀子的相关主张亦的确所在多有。事实上,由于荀子心目中紧紧绞固于礼法秩序的落实,已经表现出摒弃一切“闲谈”的独断论倾向,“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非相》),又云: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儒效》)
“理”者,治理也,而治理之道则为礼义。依荀子,凡事行、言说有益治道,符合礼义的,立而为之,而那些对秩序之建立,国家之平治,毫无裨益的行动,则目之为奸事,必须坚决给予废除;至于那些徒呈辞巧,枭乱是非之言论,荀子即直斥之为奸道。而奸事、奸道乃乱世之征,必禁而除之。顺此思路,唐君毅先生看出了荀子思想中以政摄教的流弊,并给予了深切的反省。应该说在当代新儒家中,唐君毅先生是对荀子的思想最富了解之同情的一位,但即便如此,唐先生对《正名》篇中荀子言君子何以必辨之理由的分析依然颇值得注意。荀子云:“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正名》)荀子此段文意,原在说明在“理想”的政治状态之下,明君只当守其国君之名分,以道一民,而不必与民辨说是非,盖民众愚而难晓,故明君可临之以权势,导之以正道,申之以命令,晓之以道理,禁之以刑罚,如是,则民化道神速,毋须辨说。然而今君子所以汲汲于辨说,正在于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荀子念念于先王之道的落实以及政治秩序的重建与维护,其著《正名》之目的或主要不在定名辨实,而在行道通志,“率民而一”。虽然荀子此一用心的着眼点之一在于解决思想的纷争,以使名闻实喻,文通辞顺,但其目的始终不离“王业”和治道之极成。正因为如此,荀子乃不惜将圣王的权力引入语言用法统一的时代课题中,至是而开以政治控制思想之旁门。唐先生由此看出问题,认为“荀子此言,固有流弊。因以势以刑临人而禁人之言,正为下开李斯韩非之以政摄教之说,导致焚书坑儒之祸者。荀子于《非相》篇,亦已有奸人之辩,圣王起,当先诛之之意。孔子之杀少正卯,正缘荀子此意而为法家学者所传,为孟学者,盖决无此唯以势与刑临人之论也。”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东方人文学会1974年,第276页。徐复观先生亦有相关看法,参阅《学术与政治之间》第96页。今复案《非相》篇,荀子有云:“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若撇开当时的历史处境,站在今天的立场,细味荀子的上述言论,它的确强烈地表示出,圣王之治何以“民易一以道”,又何以“恶用辨说”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以恐怖和绞刑架为后盾的,同时,它也强烈地暗示出,在荀子所理想的圣王政治之下,以风刀和霜剑、极权和专制以禁人之言乃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26]249
七、简短的结语
我们说过,孟、荀两人理论相异,但他们在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主题上却目标相同。因其所“同”而观其所“异”,则其所“异”的可能解释之一便表现在“如何建立秩序”的方法问题上:孟子主张“由道德而说政治”,荀子则主张“由政治而说道德”。孟子对建立政治秩序的思考完全取资于个人自足的内在仁心,就即道德而言道德的角度上看,孟子的思想的确成就了道德的尊严和人格的伟大,并为后世儒家批难现实政治,彰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开拓了空间;但若必欲即此而言政治,却会因其对政治之特性缺乏可靠的认知基础而导致政治上的空想主义。荀子对重建政治秩序的致思则委诸于先王制作的礼(礼义法度),而礼的内涵虽然包容甚广,但其首出的意义是政治学的而非伦理学的,是为了去乱止争以实现“出于治”“合于道”的目的而形成的一套制度设计,故荀子顺孔子外王之礼宪,正名定分,辨治群伦,知统类而一制度。在面对重建政治秩序此一时代主题面前,若与孟子言仁心之兴发和推扩相比,荀子的此一主张无疑更具有客观、凝重和可实行、可设施的特性。然而,荀子的礼既是政治学的,又是伦理学的,其间各自在根源上的分际并不明确;同时,由于荀子心目中紧紧绞固于政治秩序的实现,道德则不免沦为维护政治的手段,乃至常常以政治的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其结果则导致对专制政治的强化,扼杀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生长。学者谓荀子尊君、重势、倾向于独断,或非无故之论。
要言之,从道德与政治的角度看,面对重建秩序的课题,孟、荀两人各有自己的得失,而他们共同的所失之处似乎皆未对道德与政治各自的特性作出必要的理论简别,此固不特孟、荀两人为然,后世儒家大凡皆不免于此病。
[1]张舜微. 周秦道论发微[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上[M]. 邓正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牟宗三. 历史哲学[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4]牟宗三. 名家与荀子[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5]C.f. Loubna El Amine. Classical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A New Interpret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6]Kwong-loi Shun. Moral Reasons in Confucian Ethics[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89(16).
[7]本杰明·史华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8]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9]尤锐. 荀子对春秋思想传统的重新诠释[J]. 台湾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03(11).
[10]陈大齐. 荀子学说[M].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6.
[11]北京大学荀子注译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张觉. 荀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王天海. 荀子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B.Watson, Hsun Tzu:Basic Writing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5]J.Knoblock. Xunzi: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Ⅲ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6]E.Hutton, Xunzi: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M]// Philip J.Ivanhoe, Bryan W.Van Norden.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1.
[17]潘小慧. 荀子以“君——群”为架构的政治哲学思考[J]. 哲学与文化,2013,49(9).
[18]陈来.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M]//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9]David Nivison, Review of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88, 38(4).
[20]David B.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M]// Philip J.Ivanhoe. Chinese Language,Thought,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1996.
[21]沃林. 政治与构想[M]. 辛亨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C.F. Edward Hall. Bernard Williams and the Basic Legitimation Demand: A Defense[J]. Political Studies, 2015, 63(2).
[23]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M]. 台北:三民书局,1984.
[24]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25]徐复观.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M]//徐复观. 学术与政治之间.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6]东方朔. 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M].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B222.6
A
1673-2030(2016)04-0005-11
2016-08-1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荀子政治哲学研究”(批准号15AZX010)、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批准号13JYA720011)阶段性成果
东方朔(1963—),男,原名林宏星,江西寻乌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