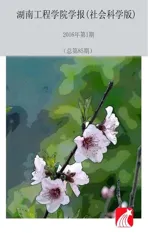解释学关照下的《八十日环游记》翻译研究
2016-03-15李晓燕
李晓燕
(福建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解释学关照下的《八十日环游记》翻译研究
李晓燕
(福建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哲学解释学认为任何理解都具有历史性,因为任何存在都是历史的。语言以其开放性开启了理解的自由,译者以前结构来对文本以及文本所处历史语境进行阐释和创造,汇聚了译本、文本以及译者、原语文化等前结构,对各种前结构进行历史性的融合。从哲学解释学理论出发,探讨陈寿彭和薛绍徽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中翻译的语言性以及翻译前结构等在翻译中的历史融合。
《八十日环游记》;翻译前结构;理解历史融合
《八十日环游记》是由清代女翻译家薛绍徽和其丈夫陈寿彭共同翻译完成,该书不仅获得很高的评价也成就了薛绍徽翻译家的历史地位。该书主要介绍了英国人福格如何依靠广博的地理知识,周游世界,途中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和阿荣、阿黛披荆斩棘、力挽狂澜,最终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环绕世界的任务。薛绍徽在序里交代翻译的缘由,“天钧地轴,日御风轮,以惊心骇目之谈,通格物致知之理,诚已归墟八统,能戴大园,来越梯航,无分畛域矣。”[1]“格物致知”始见于《礼记·大学》,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对待。[2]归墟,传说为海中无底之谷,谓众水汇聚之处,译者在这里寓指该书探究事物原理,涵盖天文地理,历史文化等,包罗万象。在翻译该书的内容时,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宣扬西方的科技知识以及道德理念,向时人展示不同风俗习惯,如“雕题黑齿,椎结纹身”[1],用中国古典来介绍西方的新事物和现象,描绘了世界各地山川风物,给民众真实详细地展示中国之外的风土人情,“戈壁有牛羊之迹,盐泽飞蜃蛤之乡”[1],掀起一股探索世界的风潮。在翻译过程中薛绍徽和陈寿彭以自己的前理解来创造和阐释文本,这也增加了译本的阅读性和普及性,这本书读来如同“聆海客奇谈,诠写寰瀛稗乘”[1]。
伽达默尔解释学认为任何一个理解对象的译本,都是译者应用前理解视域阐释的产物,因此,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会受制于历史和传统,这些历史和传统包括了译者所存在的历史环境、语言结构、翻译的方式和手段等,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完成对文本的创造,文本的理解必然烙有历史的偏见性和局限性。因此本文拟从解释学的理论出发来阐释翻译前结构对译本的影响,探讨薛绍徽的《八十日环游记》中译文的语言、翻译的方法、前结构以及陈寿彭和其合作翻译的方式所体现的翻译的历史融合。
一 文言文的使用以及翻译灵活多变
翻译的过程是通过“语言的虚拟性向我们开启了继续说话和互相说话的无限性,开启了自己说和听人家说的自由”[3],伽达默尔理论道出了理解的语言性,语言不但没有制约的我们的思想,而是召唤着我们的思想与文本进行对话。语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了翻译不是简单的搬运原文,译者总能选择最适合的意义来阐释文本,语言是历史和传统的载体,理解的历史性是语言关照下的理解历史性。
谢天振在《译介学》一书中谈到,文学文本的语言特点是造成文学翻译创造性和叛逆性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文学文本翻译中,尤为明显。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的翻译中,选择使用文言文或是白话文也成了译者创造性的表现,因为涉及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社会地位以及译入语文化的接受程度、接受视野等。在翻译《八十日环游记》时,选择浅近文言文作为翻译的语言,这是一种“介于文言文和白话的文学语言”[4],选择文言文翻译的译者大多认为,用文言翻译的小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言文有白话文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文言文精练优美、结构紧凑、含义隐晦、一词多义。薛绍徽和陈寿彭受到自身的教育和传统思想等前结构的影响,对文言文作为翻译的语言也是情有独钟。薛绍徽从小就饱读诗书,而且精通诗词、骈文等文学创作。陈寿彭在《亡妻薛恭人传略》这样记录,“五岁与兄妹共笔砚颖悟过之六岁从向外姑邵儒人学画八岁学诗颇有警句既失怙恃寄居方姨家以女红自给……余游泰西恭人始治史汉文选乙丑余归应乡试虽侥幸忝列副车自视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远甚乃求旧籍读之期有补我不足而恭人亦猛力攻苦弗少让余刚得尺恭人且越寻丈矣”[5],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陈寿彭对薛绍徽的才华欣赏仰慕,也向我们展示了薛绍徽在语言上面的造诣、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 “正因为有这样的学习态度,融汇贯通的能力,薛氏后来通过陈氏兄弟接受西学,亦很少障碍。”[6]因此在译文里,译者总能引经据典,以文言文句式结构传达新事物,“变六书之妙法,会意谐声”[1]。就晚清时期的读者而言,陈寿彭和薛绍徽把以接受儒学思想教育的士大夫作为期待的读者,这些士大夫的知识结构、思想理念、接受水平也必须成为翻译的前结构,“这些旧文人的知识结构和心理定势都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传统文学概念出发来理解和接受翻译小说”[7]。因此翻译时,夫妇二人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对文章进行编排,每章都简洁利落,讲究遣词造句,如第二章 “In Which Passepartout Is Convinced that He Has at Last Found His Ideal”[8]译成“契注心欲倾肝胆 见仆约整理寝房”[9],第七章“Which once more demonstates the uselessness of passports as aids to detectives”[8]译成 “英领事验照放行 小包疑团误实据”[9],原文都是以疑问句作为开头,是有意让读者深入阅读以便探究结果,然而翻译成中文,薛绍徽采用传统章回体小说叙事方式来翻译标题,让读者一目了然理解章节讲述的内容,使用读者所熟悉的中国传统章回体方式来译小说,这显然符合晚清民众的欣赏习惯,便于读者接受。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相对浅显易懂,“对白话的提倡在当时是为了服务于教育程度不高的贫民,这个时期的白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白话,知识词汇是掺杂了以新技术为代表的外来词汇,并不涉及语言本体的变革”[4]。《八十日环游记》中涉及大量的科技和地理词汇,这些词汇一般都是以白话文来翻译,可以让读者对于外来词汇理解变得更为容易,如electric bells “电气钟”, speaking tubes翻译成“传语筒”。选择浅近的文言文翻译科幻小说,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不同读者群的认知的习惯,同时又能输入新的科技词汇,是译者所处历史语境以及译者前结构的选择结果。
《八十日环游记》以流利忠实的文笔,描绘了世界各地风土人情,虽然不免添枝加叶,译文也存在增译、改写以及误译,如eighty-four degrees Fahrenheit “八十四度”这里的“度”应该为 “华氏度”而不是“摄氏度”; twenty minutes past eight “八点后二十分钟”应该为“8点20分”; “ the Daily Telegraph alone hesitatingly supported him.”译为“即《地利电报》亦不能未知定决”,纵观原文上下文,《地利电报》的态度是犹豫不决,但是比起其他报纸唱衰福格环球计划还是表现出了支持福格在八十天完成环游世界的计划。但夫妇二人译书时并没有追随当时翻译小说的风潮,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对小说随意的改动,相反他们格外慎重严肃看待自己的译文,完整保留原文的结构和体例的完整,即使对译文有创造也还是浅尝辄止,求忠实于原著。而对于为何不像当时众多译者以政治小说为题材,而选择了科幻小说作为翻译对象,陈寿鹏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余意谓欲读西书,须从浅近入手,又须取足以感发者,庶易记忆,遂为述《八十日环游记》一书。”[10]可见陈寿彭在选择以《八十日环游记》作为自己的翻译的对象时,态度很谨慎,不是单纯以“改良社会”为目的,而是以译入语读者作为出发点,选择简单易懂,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文言文翻译,这也是他们在面对中西交流冲突过程中对读者接受视野的严肃审视。 因此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观也构成薛氏翻译的前结构,文言文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沟通读者视野和译者视野的桥梁。
在《八十日环游记》一书,读者不难发现译者尊崇翻译传统和规则,翻译传统和规则也在规范着薛氏翻译视野,也构成薛氏翻译的独特视野的一部分,它不时地出现在薛氏的翻译前结构之中。在译文中,薛氏在外国地名和人名以及时间的翻译都是非常规范,这是难能可贵的,晚清时期的很多译本普遍存在专有名词译名错译、误译等现象。最早提出译名统一问题的是徐继畲,他最早在《瀛环志略》里谈到译名的标准“ 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然亦不能遍及也。”[11]后来高凤谦和梁启超在这一问题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观点,高凤谦认为“极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伊苏,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西国以英语为主,以前译书多用英文也;中国以京音为主,以天下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12]梁启超则又补充到“一、官制名称应列一种西何必表,使中西官名与官职相恰。如古今悉无相称之译名,则按西音译之。二、中西历年号不同,应列为表。他日译书,则以其国几年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使读者一目了然。”[11]《八十日环游记》地名、时间以及人名翻译很明显受到这些翻译思想的影响,也反映出他们翻译的专业水准。
原文:Mr Phileas Fogg lives ,in 1872, at No.7, Saville Row, Burlingtong Gardens, the house in which sheridan died in 1814.[8]
薛译:“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壬申), 有非利士(名)福格(姓)者,居于摆林塘花园沙菲尔路(在伦敦城内)第七号门牌,是屋,乃一千百十四年(嘉庆甲戌),许儿母利登(福格先代祖父之名)所遗。[9]
这段文字同时涉及到地名人名以及时间的翻译,薛绍徽的翻译就做得相当详尽得当,薛绍徽把“1872”翻译成“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文内注释清朝皇帝的年号;文内注释的方法是以读者熟悉的语言规范来翻译一些陌生的事物,既能方便理解,又能忠实于原文。把“Saville Row, Burlingtong Gardens”翻译是音译加上注释的方式,让当时的读者对新的地点不会产生误解,通过注释让读者能一目了然地理解地名以及国家,薛绍徽在地名、报纸等专有名词的翻译方法基本都是采用音译加上注释的方法,如“Sydenhan”译为“色登夏母(距伦敦桥东南南六迷当)”这里的“迷当”应该是mile一词的音译;如Standard译为“《士登打得(太晤士,译言时也。士登打得,译言旗也)新报》”。音译是当时翻译专有名词的普遍方法,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薛氏和陈寿彭只能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让读者深入了解专有名词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信息,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和接受度。 在句法上原文中in 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跟在先行词the house 后面,但是汉语并没有同样结构的定语表达方式,译者在融汇了中英文的文法,处理成为两个句子,在英语中名词跟个句子作为定语来修饰,让英语的语法顺利地移植到汉语中,薛绍徽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定语位置进行调整,名词先译,薛氏利用文言文对原文的思想和结构以及思维表达方式进行提炼,让原语在译文文化中植根,并得到译文文化读者的认同和接受,消除原语文化和译文文化的前结构的之间的差异对译文读者理解的影响。
语言的特性还在于通过叙事方式转换、语言结构调整以及词语搭配来超越自身的文化的有限性,给译者创造的自由和空间,译者通过前结构和语言的开放性来融合文本、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视野。薛氏善于借助语言的特性,弥补中西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的差异,把个人思想巧妙地介入译文中,行文如流水,对译文进行创造,这才给读者以忠实的错觉。
原文:Phileas Fogg contented himself with say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It was quite unlikely that he should be arrested for preventing a sutte. The complainants would not dare present themselves with such a charge. There was some mistake. Moreover , he would not, in any event, abandon Aouda, but would not escort her to Honkong.”[8]
薛译 :“福格独自安心,乃答曰:”不妨,此不似拿获阻扰萨提之事,若辈必不敢因是事来此诉冤。盖彼亦有错耳。我必送卿至香港者。诚不欲舍卿,仍与虎穴为邻居。”[9]
原文中以第三人称叙事,叙事声音来自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然而在翻译成汉语时,薛绍徽却以与阿黛对话的形式,把福格那种冷淡的性格一下写的有人情味,使福格与阿黛的距离一下子拉小,让福格内心的独白显得更为真切,从而使整个文章的行文通畅、娓娓道来,同时也把福格对阿黛的爱意描述得淋漓尽致。译者添加自己的主观视野,对原文进行增译,对福格表面冷酷但内心对阿黛不离不弃描述得非常到位,译者利用文言文特点把福格复杂心情展现出来。原文是以阿黛叙述的方式与前面阿黛同福格对话互相呼应。
原文:sir ,you must leave me to my fate! It is on my account that you receive this treatment, it is for having saved me.[8]
薛译:“君宜舍侬,听侬命运,据侬观之,君遭此厄,殆因救侬乎?”[9]
如果按照原文的方式把句子的表达方式,以第三人称翻译描述福格的心理活动,虽然可以能够比较自由灵活地反映客观内容,但是无法表达福格内心的矛盾的思想,不如第一人称那样让读者感到亲切,福格心里活动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把福格的个性译活了,因此薛氏在翻译文章时,并不是被动地对文字进行转换,她深处文学发展前沿,了解文学的表达方式,同时深谙中西语思维文化差异,薛氏以自己的文化结构和生活经历和审美观来重新塑造和阐释福格的叙事的方式。薛氏这种让福格的鲜活形象跃然于之上的手法在表达福格对阿荣的忠信之情,薛氏再次用到,突出福格重情重义的一面,突出了旅行艰险面前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的维系。在原文三十章中:
原文:“Ah, Mr.——Mr Fogg! Cried she , clasping his hands and covering them with tears.
“living”,added MR.Fogg, if we do not lose a moment.”
Phileas Foggs, by this resolution, inevitably sacrificed himself; he pronounced his own doom. The delay of a single day would he thought, “It is my duty,”he did not hesitate.[8]
薛译:“阿黛紧握其手,泪痕如雨,曰:‘呜,福格先生,先生’遂哽咽不能成声。福格曰:‘倘我辈不失期则生,盖自念此去纽约,若搭轮船不及,此身终不免一死。’然阿荣之事,又属分所应为,无疑义者,故不觉得其辞之哀也。”[9]
阿黛当听到福格为阿荣事情焦心并发誓不管生死都要救阿荣,阿黛听到这句话时候是非常的难过,薛氏在翻译时,增加一句,“遂哽咽不能成声”,薛氏感慨阿黛的遭遇,增加对阿黛心里活动的描绘,也把阿黛对福格的爱意箴默于心,如今有情人却要誓死找回自己仆人的悲伤质感流入于纸上,折射出那时阿黛对福格爱恋表达的被动以及羞怯感,“让人物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体现”[12]而在后面的翻译,薛氏把一段福格内心的独白,译成对阿黛的对白,诠释了福格救阿荣心切,对阿荣不背信弃义,主仆患难相依,舍生死也要救阿荣的心里状态,这种叙事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也正是薛氏在译文序言里所强调的“凡此艰难,胥关智力,全凭忠信”[1],薛氏在序里谈到福格旅途的艰险,所有的种种的艰难险阻,如果单纯靠自己的智力纵然有苍练应变之才,也不可能最终完成环球之行,还要靠阿荣以及阿黛的精神和道德上的支持。薛氏译文的行文方式的改变其实是译者利用汉语的表述方式来嵌入自己的创造视野,她破除原语和译文叙事的藩篱,让原文在译文中创造。只有通过薛氏的理解,译本才被赋予文字的生机和表现力,译本是薛氏与文本以及原文作者通过语言获得历史性共识的产物,构成薛氏意义理解的历史性体验。
二 薛绍徽翻译视野的创造
哲学解释学认为译者总是以自己的文化取向、所处的历史环境、个人经历、知识结构、价值导向以及个人风格等前结构对文本进行不同阐释,不同译者的翻译总是会对文本进行历史性的创造。翻译的历史性是任何译者的翻译行为的历史传统,每一个时代特定的翻译就是对这种翻译传统的传承和延续。
虽然在译文中,薛绍徽一直遵循忠实的翻译原则,想让自己置身于度外,表现出她的客观,但是她还是有意无意地应用自己的前视野在诠释译文。薛氏生活在风起云涌的晚清时期,她目睹国运衰退,在面对复杂的时局和西方文明所带来新兴事物的兴起,她的笔端流露出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对现实的深深不安。在诗词创作中,“她往往惜怀古诗以表现恢弘的宇宙意识和纵深的历史感,或咏史诗而讽喻现实社会政治腐败,民生凋敝”[13],她的历史感、家愁国恨、史识政见等同样也不时地表现在译文中,在翻译《八十日环游记》十四章的一个章节中,她在翻译阿黛回想自己准备用自己殉葬的一幕,薛氏并没有循规蹈矩地直译,而是增加自己的一番感受。
原文:As her thoughts strayed back to the scene of the sacrifice, and recallled the dangers which still menaced her , she shuddered with terror.[8]
薛译:“盖铭感于中,复思葬祀时景,倘被追回,险阻犹然可谓,尚若不胜栗折。今欲逃遁,而苍茫天壤,又不知何处得称乐土,故娇涕纵横,大有无言之苦。”[9]
译文中多出一句“今欲逃遁,而苍茫天壤,又不知何处得称乐土,故娇涕纵横,大有无言之苦。”这明显是薛氏有意把自己的个人感情放置其中,感叹时局的动荡,对民众流离之苦的不安,借阿黛遭遇寄寓了对中西文化交汇下国家命运以及民生的现实忧虑,字里行间流露出惆怅之情。薛氏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当时读者,在译文中不断增加自己的想法来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来重塑和影响读者的接受习惯,这一点在表达她的倡女权兴女学的思想尤为明显。 如在《八十日环游记》十四章中,法兰西斯要与大家道别时。
原文:“The parting of Aouda, who did not forget what she owed to Sir Francis, betrayed more warmth.”[8]
薛译:“阿黛不忘弗兰诗士之惠,以脸与温者数次(西国男女亲爱则亲嘴为礼,次则以脸偎脸,欲亲未亲,殆即亲嘴之渐。”[9]
其实原文并没有谈到阿黛与弗兰西斯先生的以脸偎脸的道别方式,但是薛氏却把“betrayed more warth”翻译为“以脸与温者数次”,在这里阿黛并没有主动与弗兰西斯以温脸道别,只是表达因为阿黛深觉得自己不应该忘记弗兰西斯对自己的救命之恩,所以她和弗兰西斯的分别就比较热情一点,这一点其实是较之于原文“Mr Fogg lightly pressed him by the hand.”[8]中lightly一词而言,因此这里用了比较级来表达“betrayed more warmth”。薛氏误译的目的在于以西方男女之间交往的礼仪来批判中国传统的男权思想,使男女平等思想能够通过西洋小说来影响人们的观念,通过外来礼仪来宣扬女权思想。薛氏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前结构其实是和她积极参与兴女学运动分不开的,她主持《女学报》,主张女性尊崇传统文化道德,她认为女性要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提倡学习西洋的新学。
但是薛绍徽认为西洋的新学不是女学的全部,女学还应该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薛氏虽然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兴女学运动,但对传统文化中对妇女身心束缚和摧残却持矛盾的态度,这个矛盾思想直接隐射于她的翻译作品之中。翻译“feet” 一词,我们可以窥见薛氏在“缠足”文化中内心的矛盾。
原文: her little feet,curved and tender as the lotus-bud, glitter with brilliancy of the loveliest pearls of Ceylon, the most dazzling diamonds of Golconda.[8]
薛译:“纤趺菡萏尤妍妙(西国妇女虽不裹足,而贵家妆束亦鞋底高跷鞋头束削以为轻雅。此诗竟以菡萏为比,则印度之俗亦复尔尓然。钿尺裁量之习,奚怪于中国哉)。锡兰(印度南一大岛)如意珍珠灿,哥尔康打(印度一邑名。此地亦产宝石诸矿)金刚钻。”[9]
在这里薛氏把feet一词放在中西方文化的大语境的含义中诠释给当时的民众,虽然其他国家不缠足,但是那里达官贵族为了表现出高雅也要穿尖头高跟鞋,其实是对于缠足保守态度的发声,是薛氏故意用外来文化传统来强化了自己的保守心态,虽然中国有缠足之苦,但是国外的尖头高跟鞋的体验也同样让人感觉不适。薛绍徽在《覆沈女士书》一文中,针对于沈女士所提出的缠足之苦以及缠足是清朝特有的习俗等问题时,薛绍徽认为缠足无伤大雅,只是削足适履,妇女恪守妇道罢了,无需与亡国遗制相提并论,“全凭十指,压针线于连年,黾勉同心,课米盐于中馈”[14],“西国细腰是好,饥死几希;东瀛黑齿犹存,养生奚碍乎?”[14]薛绍徽这里的观点很明显是想通过各国的风俗来说明任何文化习俗是任何民族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细腰黑齿等让外人难以忍受的恶俗在当地人的文化世界里,却是习以为常的。缠足同样也是一种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男权思想等的演变形式,内嵌于人们日常的行为和心理文化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薛氏博古通今,贯通中西,宣扬男女平等思想,但是她仍是旧知识的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摆脱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她所接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她谨言慎行,和陈寿彭的生活不算宽裕,甚至捉襟见肘,“炊烟一缕,视馆谷为断续”[14],但是她始终能安贫乐道,“恶食不知耻,蔽刨犹能温”[14],即使家里有闲钱,也会“即嘱购书籍图画不屑屑簪珥服饰或强之亦闭藏箱箧平居以布衣适体”[5]薛氏怡然自得地享受这种恬静的生活,她的生活经历以及长期儒学思想浸染让她不能深刻体会女性缠足之苦,这些前结构在她的翻译视野中无意有意地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何在翻译过程中为了阐述自己缠足的看法,薛氏对原文内容的创造性地增删改易的缘由。
三 陈寿彭和薛绍徽翻译视野的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和解释是一种世界体验,这种体验独特性是无以复制的,历史性的体验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塑造和丰富着文本理解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理解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任何理解都带有历史前见,文本意义的理解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翻译和阐释是特定历史语境中视野融合的具体应用。本文所选的译文是出版于1906年小说林社的版本,署名陈绎如的译本,陈绎如是陈寿彭的字。陈寿彭和薛绍徽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谈到他们二者在选书和译书上的分工以及角色,“宜人一妇人耳,遽所学而从我”[10],陈寿彭帮薛绍徽选择翻译文本和充当口译还对薛绍徽的译文进行润色修改,“逸儒又从润色之, 笺注之”[1]译文中薛绍徽和陈寿彭的角色就是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陈寿彭润色。因此该译文里面融汇了薛绍徽和陈寿彭的理解的历史性,包含着薛氏和陈寿彭的理解循环,那么探讨陈寿彭的历史视野也成了理解这种合作翻译历史性的必要条件。
作为《八十日环游记》的口译者,陈寿彭精通英法日语,有着丰富的海外游历经验,陈寿彭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被派留英三年,学习英国各种律法以及英国文学,每次游学回来,陈寿彭总能带很多的外国图籍,“穷经世载,游屐半环,扶桑东经,佛兰西渡,薄六百馀部经典,收图籍于归装”[1]。 除了精通各国典籍,陈锵等在《先妣薛恭人年谱》中记载陈寿彭充当口译的经历,“家严应船政出洋监督之聘充舌人游学英法国”[5]”舌人一词就是指古代的翻译官,充当舌人为陈寿彭积累很多的翻译经验,他在1900年就翻译出版对于晚清外交史和军事史具有标杆意义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22 卷。不仅如此,陈寿彭还和陈季同合办报,通过翻译的方式来借鉴西方思想,引进西方先进知识,由于陈寿彭务实的翻译态度和坚实的翻译基础,翻译《八十日环游记》对于陈寿彭来说就是“雕虫小技”[1]。该书中涉及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交通方式,当时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该书了解各国科技发展和文化宗教习俗等,这要归功于陈寿彭翻译中的用心,“爰取其稿,略加删润,间有意义难明者,并系以注,至注无可注,姑付缺如”[10],读者读译文都会发现在文章中译者对文化、历史、地名、宗教等等进行大量注释翻译。如在翻译宗教名称时,就不是单纯的简单的介绍,一笔音译带过,而是用非常详实的史料让民众了解该宗教的风俗、礼仪等。
原文:The travelers crossed, beyond Milligaum, the fatal country so often stained with blood by the sectarian of the goddess Kali.[8]
薛译:“行旅既越马利左毋(一郡名),是处全郡任命,皆系女菩萨嘉利(此佛三眼四手,做两手一提刀,一握人首,右两手一仰一俯,浑身黑胖,祖无衣,腰围短裙,首花冠,耳明珰,项璎珞,复挂骷髅一串,长逾膝,手足皆有钏。足踏一尸,亦三眼两手。向上袒腹,受其足。然其像亦有雕刻微异者,离奇诡怪,默克究诘。殆即佛氏所谓罗孛欤)。”[9]
在这段翻译中,用长篇的解释一个简单的单词“Kali”,通过对嘉利菩萨的体型,体貌特征,所持的法器等进行详尽的描述,让译入语的读者能在脑海里构建出嘉利菩萨的形象,这样直观的描述让读者轻易地接受了印度教中的嘉利菩萨。其实这样翻译表达手法在文章中我们随处可见。熟悉西方思想以及丰富的翻译经验,让陈寿彭在翻译该书时总能兼收并蓄,得心应手。薛绍徽在序里谈到陈寿彭的翻译心得里这样描述“运三十六国语言,入淋漓之健笔。”[1]
作为口译和译文修饰者,陈寿彭的很多翻译思想无疑得通过薛绍徽来表达,陈寿彭在生活中也是通过新事物和先进理念来塑造和影响着薛绍徽前结构。陈寿彭鼓励薛绍徽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游学英法期间,总能带些奇珍异宝激起薛氏对西方新事物的兴趣,奇闻异事也让薛氏流连其中。在《八宝妆》薛氏这样记录陈寿彭送给薛氏当地的特产,并对当地风土人情和地理历史文化详细阐述,“绎如寄珍饰数事,内有条金条脱一对,以钻石箝为花鸟,玲珑光耀,状扁,有锁有链,可开闭,轻巧工雅。书言:拿布仑第三称帝时,其后欧色尼有宠,西班牙女主欲结欢,令使臣赴荷兰选砖石,觅法之良工镶配之,因荷兰精切钻而法人善箝钻也……拿布仑第三与普龃龉,成普法战争,法兵败,被废。国人群起围宫,后青衣出走,遇牙医载以后车脱奔英,一切服御皆为法人所得,藏诸库。”[14],在这段文字中,陈寿彭让薛氏不仅了解奇珍异宝,还了解欧洲各国轶事趣闻,薛氏对新知识和新事物,喜不胜言,所以她每回都会填词报答陈寿彭,如在《十二时慢》里面谈到瑞士出产的金表,《江城梅花引》记录陈寿彭用化学法蒸百花为酿酒,“味香美,惜余不能饮,无以赞其妙,因取数瓶馈英姊,媵以词。”[14]这些事物和趣闻也改变薛氏对西方的印象,陈寿彭在序里这样记录薛氏思想的变化“今而知天地之大,学历各有所精,我向者硁硁自信,失之固矣。”[10]这改变了薛氏“天朝大国”自信, 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明动摇了薛氏长期“以中国为中心、他国为蛮夷的偏见”,[6]也迫使她的思想意识在求变与拒变的冲突中悄然改变,因此她走出深闺,跟随丈夫游学四方,扩展见识,贯通中西思想表达方式。陈寿彭在谈到自己翻译《八十日环游记》目的这样写到“秀玉宜人,归余二十年,井臼余暇,惟以经史自娱,意谓九州之外,无文字也。迩来携之游吴越,始知舟车利用。及见汽轮电灯,又骇然欲穷其奥,觅译本读之”。[10]陈寿彭知道妻子对车船、汽轮、电灯等新事物的兴趣,就想通过译本让妻子穷尽新事物的奥秘,就能帮助薛绍徽了解世界各地的人文景观,译介各国最新科技发展以及天文景观,历史文化。《八十日环游记》包罗万象,知识之全足以涵盖一切,“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圣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合天算及驾驶法程等”。[14]陈寿鹏用西方的知识激发了薛氏探索政治、地理和科技文明的兴趣,因此这些西学兴趣也造就了她丰富的翻译理解力和创造力,信手拈来,因此她的翻译速度之快也令人艳羡, “历年仅半,阅月者五,划然脱稿,褒然成帙。”[1]《八十日环游记》的忠实不仅要归功于陈寿彭丰富的学识、游学经历以及翻译经验,而且还在于薛绍徽精通文言文微言大义的特点,触类旁通,传递西方的理念,对译文巧妙的创造,因此译作的成功是陈寿彭和薛绍徽前结构的沟通创造的成果。
四 结 论
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表明了翻译是译者发挥自己前结构对原语文本的创造,薛绍徽通过文言充分发挥前结构对《八十日环游记》进行解读和创造,但是薛绍徽按照自己学识结构从自己所处晚清的历史背景对文本进行阐释和翻译时,由于未能精通西语,总有一些翻译的失误,陈寿彭的丰富翻译经验和精通中西文化也弥补了薛氏在翻译该书的不足,这正表明其翻译的历史融合性。
[1][清]薛绍徽. 八十日环游记·序二[A].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2]SFWS.格物致知[EB/OL][2012-09-27/2014-03-03].http://baike.haosou.com/doc/3040450-3205435.html.
[3]邓安庆,等译.伽达默尔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5]陈锵,等编.先妣薛恭人年谱[A].张爱芳.历代妇女名人年谱:全二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6]钱南秀.晚清女诗人薛绍徽与戊戌变法[A].陈平原,王德威,商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7]章艳. 在规范和偏离之间——清末明初小说翻译规范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8][法]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英对照全译本)[M].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9][法]房朱力士. 八十日环游记[A].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M].陈绎如,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10]陈寿彭.八十日环游记·序一 [A].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1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12]罗列.女翻译家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的重构[J].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08(4):262-270.
[13]花宏艳.世变之际的历史书写与家国记忆——略论近代女诗人薛绍徽的咏史与怀古诗[J].名作欣赏,2011(32):27-29.
[13][清]薛绍徽.薛绍徽集[M]. 林怡,点校.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Research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LI Xiaoy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China)
Hermeneutics assumes that understanding features historicity due to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historically exists. Language is open to everyone and triggers the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provides the scope for the translators to bring their forestructure to full play in interpreting the text and the underlying historical context. The translators are capable of incorporating the forestructure concerning the translated text, source text , translators and source language into his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deliberates the historical fusion in translatingAroundtheWorldin80Daysbased on the language,foresturcture in the light of hermeneutics.
AroundtheWorldin80Days;forestructure ;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
2015-10-12
福建省教育厅社B类项目“薛绍徽翻译的哲学研究(2014-2016)”(JBS14129)。
李晓燕(1980-),女,福建仙游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与翻译。
H315.9
A
1671-1181(2016)01-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