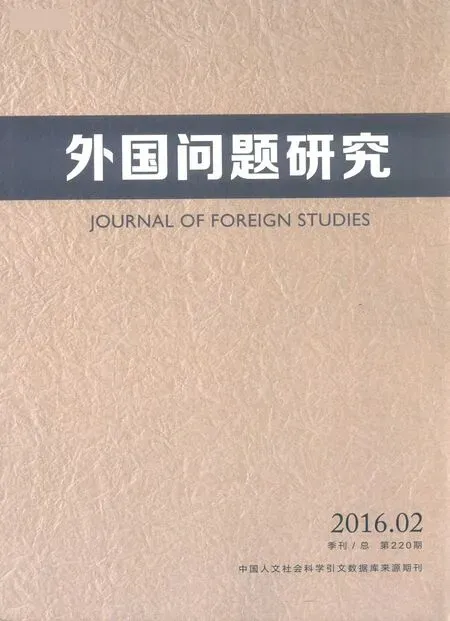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
2016-03-15晏绍祥
晏 绍 祥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
晏 绍 祥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兴起于何时仍是中外学术界争论激烈的重大问题。部分学者期望在迈锡尼世界发现古典城邦最初源头的尝试,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迈锡尼世界与荷马社会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中断。本文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系统梳理了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希腊大陆上尼科里亚、雅典和勒夫坎地遗址的资料,认为这些黑暗时代的共同体虽然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某些特征,但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表现出与迈锡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即使在雅典和勒夫坎地等继承性相对明显的地区,迈锡尼时代的官僚和宫廷体系也趋于消失,居民重新回复到相对平等的状态,领袖也重归大众之中,与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如果古典希腊城邦的起点要到荷马社会寻找,则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当发端自黑暗时代的新式共同体。
城邦起源;黑暗时代;共同体;原始城邦
一、迈锡尼与荷马:关于城邦兴起的争论
城邦何时兴起?这是著名古史学家埃伦伯尔格(Victor Ehrenberg)193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题。他采用回溯式的研究方法,先从古典时代成熟的城邦讨论起,将城邦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如果不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演化过程的长期性与多样性,则构成本文标题的问题的答案也许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如果我们假设其在该世纪的前半期,假如考虑到斯巴达的例证,甚至比如公元前800年左右,可能更好,因为对达摩斯和瑞特拉的深入分析表明,这个国家至少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以前,也就是说公元前8世纪初,就已经巩固下来了。伊奥尼亚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在城邦的发展过程中,从东到西的潮流发挥了作用。但小亚细亚的早期城市不应该在政治意义上毫无限制地被称为城邦。”具体到荷马史诗,他认为,“在《伊利亚特》中没有出现城邦的任何迹象,而《奥德赛》显示出来了。”易言之,荷马史诗中的某些城邦是可以被称为城邦的。*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37,in Victor Ehrenberg,Polis und Imperium,Zurich und Stuttgart: Artemis Verlage,1965,pp.92-93.
芬利(M.I.Finley)的《奥德修斯的世界》和《荷马与迈锡尼:财产与土地所有制》等论文,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埃伦伯尔格观点的合理性。对芬利来说,迈锡尼社会与西亚和埃及的专制主义国家更为接近,荷马社会才是古典希腊历史的起点。*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2nd ed.,London: the Penguin Groups,1991,p.25; M.I.Finley,“Homer and Mycenae: Property and Land Tenure”,Historia,vol.6,No.2(Apr.1957),pp.133-159.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和柴德威克(John Chadwick)对线形文字B的解读,几乎把芬利的观点变成了历史事实,因为宫廷的档案文书表明,迈锡尼世界确实是一个以宫廷为中心,以瓦纳克斯(Wanax)为最高统治者,由官僚系统和书吏严格管理的国家。地方共同体即使存在,可能也不过如原苏联历史学家安德列耶夫(Juri Andreev)所说,承担征收赋税和劳役、完成国家下派工程的角色,不可能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John Chadwick,The Mycenaean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70-73; 安德列耶夫:《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古代东方城市国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60页。所以,芬利的结论为包括默里(Oswyn Murray)、奥斯邦(Robin Osborne)在内的众多权威学者认同。*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30页;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London: Routledge,1996,pp.19-31.
然而,荷马与迈锡尼之间的关系,是否如芬利所说那样一刀两断,仍有待争论。如果林志纯先生关于城邦乃人类文明初期普遍的国家形态,并保存着部分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的观点成立,则克里特和迈锡尼世界的国家,也与古代苏美尔城市国家、埃及最初的国家和列国时代印度的部分国家一样,是某种类型的城邦。*有趣的是,林先生深入讨论过苏美尔、列国时代的印度、先秦时代的中国的制度及其与城邦发展的关系,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克里特和迈锡尼的政治状况。关于林先生的城邦理论及其影响,参见晏绍祥:《博通中西、影响深远——林志纯先生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4期,第128—138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有部分法国学者试图到希腊文明最初的起点爱琴文明那里寻找古典希腊城邦的源头。凡埃芬特里(Henri van Efenterre)在主持发掘克里特的马利亚宫殿时,发现了一座他认为属于公民大会会场的设施,进而推测那里可能在宫廷之外,还存在类似公民大会的机关。音德利卡托(Silvia Damiani Indelicato)证明,至少在克里特宫殿的早期,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等地仍存在类似后来希腊城邦广场的设施,也就是说,可能有公民大会之类的机关存在。*Helen Waterhouse,“The Palace and Place of Assembly in Minoan Crete”,The Classical Review,vol.35 (1985),No.1,pp.151-153.可是,仅仅依靠广场断定公民大会存在,进而推论公民大会是一个重要机关,在完全缺乏可靠文献佐证的情况下,中间的跳跃程度不言而喻。克里特文明严格的再分配式的经济体系以及国王巨大的权威,不大可能给地方自治与公民大会的政治积极性留下空间。*学者们公认,克里特文明实行的是以宫廷为核心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中央权力机构控制周边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权,其中大量土地直接隶属王宫或神庙,土地产品集中于宫廷和神庙,由王宫决定分发给各个村落。王不仅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权威,他与身边的谋士们、祭司们决定着在国家的大事。参见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与文化史》(第二版),傅洁莹、龚萍、周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5页;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陈恒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68页;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50页。就迈锡尼而言,虽然线形文字B文献中出现过后来代表人民的达摩斯,在管理地方共同体土地中,达摩斯好像还能发挥一定作用;迈锡尼宫廷对农业生产的控制,由于希腊大陆缺乏埃及、两河流域那样的灌溉系统,也远不够严密,主要限于能够用于交换的橄榄以及小麦等重要粮食作物;在派罗斯国家中,所谓的远省因距离宫殿相对较远,地方可能也享有一定的自治权,*Lin Foxhall,“Bronze to Iron: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Lat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Greece”,The Annual of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90:Centenary Volume,1995,pp.239-250; 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ce,1200-700 B.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3.但后期希腊底第三期宫殿的崛起,让迈锡尼宫殿的势力急剧扩张,可能直接控制了包括阿尔哥斯在内的周边地区;在派罗斯,由于恩格里亚诺(Engliano)宫殿的扩张,连城堡周围精英阶层的权力都不断受到侵蚀,*Bryan E.Burns,“Life outside a Mycenaean palace: elite houses on the periphery of citadel sites”,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tudies,vol.15,Building Communities: Houses,Settlement and Society in the Aegean and Beyond,2007,pp.111-119.更不用提地方共同体的权威了。派罗斯的泥板文书中,明确记载了农民从宫廷获得种子的情况,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基本被宫廷掌握;*W.Edward Brown,“Land Tenure in Mycenaean Pylos”,Historia,Bd.5,H.4 (Nov.1956),pp.385-400.最近的考古发掘,则是在派罗斯国家的一个次级中心伊卡拉伊那(Iklaina)发现了泥板文书。用发现者科斯摩波罗斯(Michael Cosmopoulos)的话说,它不仅意味着迈锡尼人使用文字的程度超过我们曾经的想象,也意味着派罗斯国家的官僚体系足够发展,能够掌控伊卡拉伊那这样的地方手工业生产中心。*豪似乎仍然认为,迈锡尼国家能够使用文字的人仅限于宫廷中的少数书吏,但随着伊卡拉伊那文书的发现,这个结论需要重新考虑。见Jonathan M.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ca.1200-479 BCE,2nd ed.,Oxford: Wiley Blackwell,2014,p.56; Amanda Summer,“The Birth of Bureaucracy”,Archaeology,vol.65,No.4 (July/August,2012),pp.33-39。科斯摩波罗斯的看法见该文第39页。这样看来,要从迈锡尼世界达摩斯出租土地的少许记载中推论出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和重要,进而论证它们是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前身,可能不太现实。
从迈锡尼世界寻求城邦起源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是迈锡尼世界与荷马世界的关系。如芬利等大多数学者证明的,荷马社会是古典希腊城邦的起点,但荷马与迈锡尼的世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社会,因此希腊城邦的发端,应该到迈锡尼与荷马之间的所谓“黑暗时代”去找。然而勒夫坎地等地的发现,让芬利的迈锡尼到荷马断裂论逐渐遭遇挑战。部分学者如凡埃芬特里转而认为,迈锡尼世界与古典希腊的城邦之间,也许并不那么一清二白,城邦的起点,还是应当到迈锡尼世界的达摩斯那里去找。*法国学者卡利尔试图从迈锡尼时代的达摩斯(人民)中寻求古典希腊城邦的萌芽。这种看法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得到恰当的论证,参见黄洋:《迈锡尼世界、“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 2010年第3期,第32—41页。遗憾的是,黄洋教授的重点在于揭示这种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着墨不多。
然而众所周知,迈锡尼文明灭亡于公元前13世纪前后,而所谓的荷马社会,无论它属于芬利所说的公元前10—9世纪,还是如多数学者认为的公元前8世纪,抑或如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的公元前7世纪,或者是多个世纪社会的复合体,它们之间都相隔数百年。*有关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的讨论。参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50页。在这数百年中,迈锡尼世界的宫廷国家消失了,且再也未能恢复;为宫廷服务的官僚体系和记录宫廷收支的书吏,也一并被埋葬;迈锡尼世界再分配的经济体系,也失去了踪迹。更重要的是,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希腊大陆有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人口下降与社会衰退时代,当时几乎所有政治体系都归于瓦解,剩下的只有几十人或百余人组成的小型共同体。如伯罗奔尼撒西南美塞尼亚地区的尼科里亚、阿尔哥斯、阿提卡的雅典、优卑亚岛上的勒夫坎地等,不足以支撑复杂的社会组织,其社会生活也与迈锡尼世界存在本质性的区别。*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32-114.而荷马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应当是从这些小共同体逐渐发展起来的。用奥斯邦的话说,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希腊大陆,近似一块被“擦光了的白板”。新近出版的豪的著作,也更多地强调了迈锡尼世界与荷马时代之间的断裂而非继承。*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London: Routledge,1996,pp.19-32; Jonathan M.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pp.59-66.虽然完全否认迈锡尼世界与荷马时代之间存在任何连续性不免过分,毕竟荷马社会基本的经济部门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如他们饲养的牲口、种植的农作物、耕作的技术等,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革。*Lin Foxhall,“Bronze to Iron: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Lat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Greece”,pp.239-250.黄洋注意到迈锡尼世界与荷马之间的连续性,进而质疑黑暗时代以及西方学者如此论断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可惜不曾就延续性的具体表现提出论证。见氏著《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 2010年第3期,第32—41页。然而,要在迈锡尼世界的达摩斯与荷马的德摩斯之间寻求社会政治职能上的类似,进而证明荷马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自迈锡尼时代的共同体,仍有相当的难度。
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因涉及希腊城邦与国家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近几十年来考古学的发展,让所谓黑暗时代的资料日益丰富,为新的讨论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本文的意图,是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对迈锡尼与荷马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城邦的发端问题,尝试做出某些初步的解释。
二、“黑暗时代”的转折
既然迈锡尼时代的国家与后来的希腊城邦迥然不同,既然希腊城邦在荷马社会初见端倪,则它最初的发端,只能到迈锡尼文明灭亡后东地中海地区一系列社会变动中去找,而不必如某些西方学者那样,发明所谓“八世纪革命”,将其片面归到公元前8世纪的突变。*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伊安·莫里斯,见Ian Morris,“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in Kurt A.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s,eds.,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p.64-80.中国学者的反应请见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 2010年第3期,第32—41页;周洪祥:《八世纪革命——古风时代希腊城邦民主化观念与国家形成》,《国外理论动态》 2009年第8期,第113—117页。如莫里斯指出的,“逐渐积累起来的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我们不深入到(公元前)8世纪爱琴世界革命性因子的内部,就无法理解古风时代的希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探索黑暗时代,也就无法解释(公元前)8世纪的转变。”*Nick Fisher & Hans van Wees,eds.Archaric Greece: New Approaches and New Evidence,London: Duckworth,1998,p.70.他还强调,平等是希腊城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平等观念可一直追溯到荷马和赫西奥德时代,希腊是先有了贵族间的平等,然后才有了公民间的平等。他借用达尔的强势平等理论,说明希腊人的这种平等,具体表现为中态意识形态(middling),即欣赏中间阶层,对大富大贵和贫穷之辈则都表示鄙薄。表现在考古文物中,便是墓葬陪葬品在古风时代中后期的减少乃至消失。*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Oxford: Basil Blackwell,2000,pp.109ff; Ian Morris,“The Strong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Archaic Origins of Greek Democracy”,in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Hedrick,eds.,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Ancient and Moder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32; Ian Morris,“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in Kurt A.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s,eds.,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Oxford: Basil Blackwell,2009,pp.64-80.然而,他对所谓中态意识形态的论证不够有说服力,尤其是就文献而论,它主要来自上层阶级,那是他们在酒会上表演的,本身就是贵族生活的产物。同时,他征引的那些作家们,更多地表现出欣赏精英而鄙薄普通平民的倾向。*Jonathan M.Hall,“The Rise of State Action in the Archaic Age”,in Hans Beck,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2013,p.14.而且将希腊人的平等归之于某个抽象的意识形态,显然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得益于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斯诺德格拉斯(A.M.Snodgrass)的倡导,考古学家们开始转向对考古证据的历史学解释,而历史学家们则求助于考古资料说明问题,让我们对迈锡尼向荷马社会的转变,即希腊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有了更多的认识,大体弄清了荷马时代之前共同体的演变历程。
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地方共同体的情况,人们通常用尼科利亚(Nichoria)、雅典、阿尔哥斯和勒夫坎地作为例证,一方面是这些遗址资料相对较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延续性,更能说明迈锡尼与黑暗时代以及荷马社会的关系。尼科利亚自然环境比较优越,有一片较大的草原,迈锡尼时代,它可能是派罗斯王国远省的行政中心,并且在那里发现过线形文字B文书。恩格里亚诺的宫殿被摧毁后,这里像希腊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出现了人口严重下降的趋势,公元前11世纪左右,该地大约仅有数十人。黑暗时代初期(约公元前1075—前975年),它不过是个只有13—14家、人口可能在60人左右的村庄,房屋大多是一间房子的小屋子。在大约100年中,那里似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阶级分化或者存在领袖的迹象,是一个无领袖的共同体。在接下来的100多年中(公元前975—前850年),该定居点的人口有所增加,约有40户200人,且其中出现了一座相对较大的房子。但这座房屋最大时不过长15米,与其他房屋差别仍不明显。托马斯等认为,该地最初可能是一个牧民的村庄,混杂着少量的农民。*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36-47; 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96.最近的研究否定了牧民为主要居民的结论,强调了其混合型农业定居点的特征,牲口主要集中在富人家中,因此与荷马时代共同体的经济状况更为接近。*Oliver 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pp.98-104.除人口减少外,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变化。遗址虽然系从迈锡尼时代延续而来,但与前一时期比较,官僚系统在这里已消失,使用文字的迹象阙如,可能也没有任何领袖。公元前9世纪,那里或许产生过一个类似首领的角色,但他的房子除面积稍大并拥有某些金属、从事某种程度的崇拜活动外,其结构与其他大体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位领袖家里有一个较大的空间,也许是供祭祀或集会之用。虽然如此,这座房子并不比其他住所大多少,暗示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作为领袖,他不是独自生活在宫廷中,而是与他的村民聚集在一起。此外,他们的权力可能也不够稳定,面临着其他与其权势相当者的竞争。*Oliver 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pp.110-111; 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36-47.当然,这里与迈锡尼时代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定居点仍在原地,种植的农作物仍是小麦、橄榄等,但仅此而已。它更多地表现了变化:即使有政治和管理,也是被迫重新起步,而且开始走向公开;首领虽然存在,却与共同体普通成员没有明显区分。也就是说,这里可能盛行平等原则。
延续性更明显的是雅典。迈锡尼时代末期的雅典卫城曾有宫殿,且有一道周长约700米、高约10米的城墙。*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64.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并未受到毁灭整个迈锡尼世界的入侵的波及,反而成为接纳逃亡者的中心,并组织了对伊奥尼亚的殖民。后来的传说,更具体地提到了派罗斯的涅斯托尔的后代逃亡雅典,并在那里成为国王的故事。*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2,vol.1,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3-25; Strabo,9,1,7;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2,18,7-8,vol.1,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41-343.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所谓雅典组织移民之说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初因雅典给予伊奥尼亚人援助才被创造出来的假说,目的是为雅典霸权服务,与黑暗时代无关。*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34-37.但考古发掘确实证明,雅典不仅在迈锡尼末期的动荡中幸存,而且在残余迈锡尼和原始几何陶时代一度兴盛,是希腊发明因之命名的两种陶器的中心之一。在当时的阿提卡农业仍相当繁荣,考古发掘找到的谷仓模型,证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那里也可能真如修昔底德所说,是接纳逃亡移民的中心。后因人口膨胀,它组织了前往小亚细亚的移民。把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远渡重洋到相当陌生的小亚细亚沿海殖民,需要相当的组织能力、资源以及勇气,显示了雅典在当时的活力。*A.M.Sndo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Eleventh to the Eighth Centuries BC,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1,pp.373-380.所以,即使在公元前11世纪希腊世界势力最为低落、尼科利亚可能已经沦落为无国家状态的时候,雅典仍存在某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不过在这里,迈锡尼时代的社会组织可能也在动荡和接纳移民的过程中被摧毁,其最明显的证据是移民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如果这些人真是迈锡尼逃亡居民的残余,却没有保留迈锡尼时代国家与政治组织的痕迹。王的称号固然保留,但强大的瓦纳克斯的权力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巴赛列斯。*德鲁明确否认这些早期的巴赛列斯有资格被称为国王,认为他们不过是一般贵族。见Robert Deres,Basileus: The Evidence for Kingship in Geometric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0-35.墓葬显示公元前11—10世纪的雅典社会有明显的分层,公元前9世纪,这种趋向有所加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权威,而是一群相对富有的人在统治着共同体。如果真有管理机关存在,则这群富人可能是主角。即使如此,与迈锡尼时代比较,这群富人也难真正号称富有,“在已知属于这个时期成百的希腊墓葬中,至少有很少的几座肯定属于那些贵族和统治者。可是,在马其顿以南,(公元前)11世纪初到(前)10世纪末之间的墓葬中,几乎没有一座可以称为富裕的。”*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这些人是共同体中的贵族。见A.M.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pp.387-388.社会重新回到了相对平等的状态。陶器生产在继续,并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对外联系也仍然保持,铁器被引入且在黑暗时代逐渐取得优势,意味着后世的生产将发生重要变化。*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47-49; 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61-84.所以在这里,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过渡过程中,迈锡尼的君主制和官僚系统也消失了,社会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和建设。
延续性表现最明显的是勒夫坎地。该地位于后来的埃莱特利亚和卡尔西斯之间,地处著名的拉伦丁平原边缘,以牧场和出产大麦知名。自公元前3千纪后期到公元前8世纪初,勒夫坎地一直有人居住,并与希腊大陆、爱琴海中的岛屿、小亚细亚西岸、克里特、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等地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遗憾的是,这个地区的发掘并不完整,主要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以及部分墓葬,其居民点可能位于附近某个尚未发现的地区。迈锡尼文明末期,这里并未发生中断,但居民到底是荷马笔下的阿班特斯人还是后来的伊奥尼亚人,并不确定。与尼科利亚陷入彻底的孤立不同,公元前11—10世纪的原始几何陶时代,这里仍保持着与外界、包括西亚地区的联系,墓葬中发现的各类物品,如黄金饰品、青铜武器和三足器、陶器、胸针等,暗示那里有专业手工业者和商人存在。*Keith G.Walker,Archaic Eretria: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490 B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pp.76-80.所发现的多座墓葬以及可能的房屋中,有一座属于约公元前10世纪的长45米、宽10米、有众多房间的大型建筑,其规模是尼科里亚同类建筑的4倍。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建筑原本可能是一座房屋,屋子的主人去世后,被改造成了墓葬。其中一座墓葬中埋有一个武士的骨灰,以及一位妇女,还有在当时看来相当丰富的陪葬品,包括雕花青铜器、铁质长矛和剑、覆盖在女性胸部的两个金盘等。另一座墓葬中有4匹马,显然是被殉葬的。*被殉葬的女性,庞大的建筑,暗示了共同体的组织和强制力量。见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41; Oliver 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p.107.在一个绝大多数墓葬仅有陶器和少量其他饰品出土的时代,它的奢华引人注目,不由让我们想起《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帕特洛克鲁斯的葬礼。*Keith G.Walker,Archaic Eretria,p.81.墓葬的规模和构造,都暗示墓主人可能利用了共同体的劳动,并且拥有一定的强制权,以及社会分层的存在。
然而公元前10世纪末的墓葬也表明,拥有如此地位的可能并非一人,声望也不会由他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垄断,他的房子直接变成墓葬本身,是否意味着他的权力随着他的去世一起被埋葬?答案无法肯定,但权威不太可能总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与同一时期该地区其他墓葬的比较,这座墓葬的确比较大,但类似的墓葬并非只有这一座,附近的斯库布里斯和帕拉伊亚佩利沃利亚都出现了类似的墓葬。房屋被摧毁且变成墓地,显示“这座庞大建筑背后的社会权力,像建筑本身一样,似乎很快就部分崩溃了,因而基础不足以好到能让其延续”。*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43.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座墓葬的继承者,似乎在公元前10世纪突然的爆发后,该地再度归入平庸。公元前9世纪的墓葬只表示当地有人居住,并与近邻雅典保持着联系,但再无某个家庭能够支配或者统治共同体的迹象。墓葬和定居点遗址不断的迁移,暗示权力和组织并不稳定。有些人猜测,如果当时存在某个首领,那他可能像荷马世界的首领一样,有一些随从,并以自己的勇气、慷慨和演说能力,成为共同体的保护人和领袖。*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93-114.
三、从共同体到城邦
以上对黑暗时代几个延续性表现明显的遗址的回顾,基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虽然迈锡尼时代的居住点仍然得到应用,社会基本的物质基础并无本质变化,但随着宫殿被摧毁及人口迁移与动荡,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和官僚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机构,都在公元前13—10世纪之间的动荡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数量不大、组织相对原始的小型共同体,“每座主要城市都是作为相互分割的村庄的集合体发端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墓地,但仍为一种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感情联系在一起。”*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 900-700 BC,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p.50.尼科利亚、雅典、勒夫坎地、阿尔哥斯,都是这类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组织,至少从目前考古提供的证据看,与迈锡尼时代迥然有别。*黄洋教授强调的延续性,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地方共同体而非政治组织或社会结构层面。见黄洋:《迈锡尼世界、“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 2010年第3期,第32—41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该时期的埋葬习俗非常多样,“在这方面,没有两个地区是一样的,希腊世界已经被分裂成大量有自主意识的小共同体,各自有它们自己的葬礼传统。”它们分裂发展的状况,至少都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 900-700 BC,p.50.那么,这些小型共同体可以称为国家吗?它们与后世希腊城邦的兴起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并未意识到这类共同体的存在。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大多数人接受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看法,把荷马时代作为血缘氏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就是无国家时代。类似的提法,在新的教科书和著述中仍然存在。但也有部分学者敏锐地发现了氏族理论的问题。早在1980年,林志纯先生已经指出,黑暗时代的雅典是一个早期国家;王敦书教授在1985年发表的有关希腊英雄时代的文章中,提出荷马时代希腊的某些地区如雅典等存在国家;*日知、际陶:《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97—204页;王敦书:《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收入氏著《贻书堂史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25页;郝际陶:《黑暗时代的雅典国家》,《东北师大学报》 1995年第2期,第27—31页。胡庆钧、汪连兴认为荷马社会属早期阶级社会,前者更明确地将其定义为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7—241页;汪连兴:《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科学战线》 1994年第5期,第131—137页。黄洋和笔者自己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认为,荷马时代的共同体不仅是国家,而且已经是某种原始的城邦;*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世界历史》 1997年第4期,第52—59页,收入氏著《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晏绍祥:《荷马社会的polis》,《历史研究》 2004年第2期,第145—161页。郭长刚教授则主张,荷马时代的共同体既非国家,也非氏族社会,而是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酋邦形态。*郭长刚:《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史林》 1999年第2期,第99—107页。
上述论断大多基于荷马史诗的材料提出,对于考古学揭示出来的更早的黑暗时代的共同体,学者们很少涉及。笔者曾经认为,既然迈锡尼世界已经存在国家,则迈锡尼之后的黑暗时代和荷马社会,国家理当继续存在。*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5—76页,第307页。但新近考古资料揭示出来的那些共同体,是否够资格称为国家,看来不无可疑。尼科利亚那样的共同体,规模既小,组织也非常简单,或许根本没有组织,更不用说代表国家权力的其他统治机关。即使到公元前8世纪初年,那里也难说存在真正的国家形态。如果说迈锡尼时代美塞尼亚地区的派罗斯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地区性国家,则这个国家随着迈锡尼世界的消逝,彻底从地平线上消失,社会再度倒退回原始状态。
雅典的情况与尼科利亚有别。由于在那里发现的线形文字B文书很少,我们不清楚迈锡尼时代雅典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状况。如果雅典可以与派罗斯和克诺索斯等地的国家类比,则迈锡尼时代那里似乎也应当有某种形式的君主和官僚统治。在希腊人的历史传统中,雅典不曾受到所谓多利安人入侵的影响,迈锡尼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留。哈蒙德接受修昔底德保存的传统,认为雅典接纳了大量逃亡者,因人口太多,故组织了对小亚细亚的移民,它表明当时的“雅典是一个组织强有力的国家”。*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2nd ed.,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67,p.84.与其他地区比较,公元前11—前9世纪的雅典的确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力。这里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也是陶器生产中心;农业的基础地位,首次体现在阿提卡墓葬中出现的谷仓上;雅典还组织了对小亚细亚的移民,表明那里仍应当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但是,虽然修昔底德将雅典组织的对小亚细亚的移民与后世希腊人的殖民活动相提并论,*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2,4,vol.1,pp.23-25.但我们应保持适当的警惕:“我们不应把移民活动想象为官方的事业,由国家派出甚至是支持。那里根本不可能有我们在历史叙述中听到的此类程序,当时国家可能利用抽签进行挑选,并对不情愿的移民施加压力。这些移民显然是独立的群体,由个别的贵族率领,他们后来在记忆中成为了伊奥尼亚城市的国父;他们航行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理上的考虑。”*A.M.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pp.373-374.从考古学上看,即使陶器风格趋同暗示迈锡尼末期雅典曾确立对阿提卡的统治,*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62.但在黑暗时代的动荡中,原本不够巩固的统一,随着人口减少和收缩到雅典,实际上崩溃了。*Karl-Wilhelm Welwei,Athen: Vom neolithischen Siedlungsplatz zur archaischen Grosspolis,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2,pp.51-52.后迈锡尼时代雅典的定居点数量不仅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卫城及其周边地区,广场和陶工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居民,但其他地区定居点显著减少甚至消失,显示了雅典的动荡和某种程度的衰落。*Oliver 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pp.88-89.更重要的,是随着宫廷体系的崩溃,雅典的瓦纳克斯,如果曾经在迈锡尼时代存在过,此时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贵族逐渐成为雅典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且掌握了权力,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势的阶级。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到荷马史诗中,迈锡尼时代的巴赛列斯,如今上升为国家的统治力量。然而,他们的资源和权势都相当有限,大多与普通农民混居一处,不复高高在上和远离大众视线。希腊城邦的面对面社会,应萌芽于此时。相反,为巩固自己的影响,他们需要依靠追随者的支持。*Karl-Wilhelm,Athen,pp.57-75.所以,迈锡尼的某些传统尽管在雅典保留,其社会和政治组织,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必要的文献对这个过程给予基本的说明。
勒夫坎地的情况与雅典类似。那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性。首先是定居点不曾发生根本的变动,除公元前1150到前1100年有过大约半个世纪的中断外,它包括了从早期迈锡尼到公元前825年左右完整的人工制品系列。*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其次,当迈锡尼文明末期到公元前10世纪希腊世界其他地区陷入不同程度的低谷时,这里未中断与外界的联系,与东部地中海以及叙利亚的联系相对密切。勒夫坎地墓葬中盛装武士骨灰的青铜瓮来自塞浦路斯,随葬女子的装饰品来自西亚。*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37-838; 波默罗伊等:《古代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二版),第62页。第三,当其他地区不同程度地陷入物质文化衰退状态时,这里仍保持某种程度的繁荣。那座庞大的墓葬,殉葬的马匹和妇女,以及武器、青铜器、装饰品,都暗示了首领的权威和富裕。“公元前9世纪中期,勒夫坎地成为一个有阶层划分的社会。地方长官和他的支持者有权享用外来的奢侈品,并且有能力调动社会内部劳动力去完成大规模工程。”*默里:《早期希腊》,第8—9页;波默罗伊等:《古代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二版),第63页。由于缺乏相关文献记载,而且遗址并未全部发掘,对于当地的社会组织状况,仅能做必要的推测。但有限的资料显示,虽然首领拥有某种程度的权威,然而,与迈锡尼宫殿及豪华的阿特利乌斯宝库和克吕泰奈斯特拉陵墓比较,他的墓葬和住所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此外,墓葬和定居点不断的迁移以及勒夫坎地本身发展上的时断时续,*Carol G.Thomas and Craig Conant,Citadel to City-State,pp.95-99,105-107.都表明他可能并不是当地唯一的首领。一旦首领故去,权力就有可能转移到其他人手里。在这里,我们也同样难以见到迈锡尼那样的官僚机构,首领仍与他的追随者共同生活在共同体中。
与迈锡尼时代的国家和社会比较,这些黑暗时代的共同体显示出相当不同的特征。首先,庞大的宫殿、强大的君主,连同为他们服务的官僚系统和文字,都在从迈锡尼到荷马之间的数百年动荡中消失了。在迈锡尼文明废墟上产生的新共同体,首领缺乏必要的权力基础,其地位相当脆弱而不稳定。雅典对阿提卡的统一可能瓦解了,所谓的殖民伊奥尼亚,尽管雅典作为移民接纳地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传统透露的更像是贵族与流亡者个人的行为而非国家组织,也可能是居民自然流动的结果;在勒夫坎地,也很难认定那里出现了世袭的首领。社会好像再次回到了相对原始的状态。其次,迈锡尼时代再分配的经济体系,在尼科利亚、雅典和勒夫坎地等地区,似乎都消失了。如果荷马后来的证据可以前推,则表明税收系统并不存在于希腊。*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157—158页。尽管在历史上,论证某个东西不存在,较比论证某个事物存在更加困难,但荷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农民成为不受他人管制的独立小生产者。其代表是荷马笔下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特斯。汉松将迈锡尼到荷马的转变视为农业解放的过程,*Victor Davis Hanson,The Other Greeks: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pp.25ff..固然属于夸张,但农民随着迈锡尼灭亡摆脱宫廷控制,能够自主生产,应无疑问。而构成后世希腊城邦公民队伍基础的,正是这些自由农民。最后,是这些共同体的规模。就其领土规模而言,虽然迈锡尼世界的国家可能也不大,修昔底德所谓迈锡尼时代阿加门农的霸权,更多的是想象而非实际,但尼科利亚和勒夫坎地等地的共同体,规模显然较迈锡尼时代的国家更小。尼科利亚一度不足百人,勒夫坎地的人口规模可能不比尼科利亚多太多;阿尔哥斯的人口,据估计在600—1200人;只有雅典是个例外,人口可能超过2000人。*Jonathan M.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pp.61-64; Karl Wilhelm Welwei,Athen,p.62.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也许就是定居点周围不大的地区。在规模如此微小的共同体中,首领生活在他的追随者之中,尼科利亚和勒夫坎地的大房子,不知是否为共同体集会之用。但无论如何,首领无法把自己封闭在迷宫里,对周围的人故弄玄虚,宣示自己乃神灵的后代,而需要像荷马所描绘的领袖们那样,成为民众眼中会做事情的行动者和会发议论的演说家。*荷马:《伊利亚特》,9,443,罗念生、王煥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前者显然是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能力和领袖资格,后者更多的是暗示领袖并无强制权,他需要通过公开的说服让追随者服从。芬利所说的地中海式的面对面社会,*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3—105页。大约应萌芽于此时。如黄洋教授指出的,就社会和政治组织而论,迈锡尼与荷马之间最大的变化,是政治的公开化和长老会、公民大会之类公共议事机构的出现。*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2页。
在这些黑暗时代共同体的基础上,逐渐兴起了希腊人的城邦。可惜因为文献资料缺失,我们无力重建这个详细的过程。所肯定的是,到公元前8世纪,即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荷马社会,城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存在。*关于荷马时代的社会与城邦更详尽的讨论,参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拉夫拉勃指出,各种迹象表明,“史诗的世界充满了城邦,”“史诗的行动大多在、或者围绕着4个城邦发生,”不过,这些城邦能否被视为古典希腊那种意义上的城邦,关键看它们是否是公民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答案似乎再度是肯定的。虽然史诗关注的是个人,他们对家族的忠诚在史诗中仍占主导地位,但“个人对家庭和家族的主要关注并不排除人们对为城邦服务做出高度评价……英雄们意识到,他的家庭的幸福依赖于共同体的幸福……综合起来看,资料显示,荷马的城邦确实是一个人类的或者公民的共同体,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自治家族的总和。”而是一个城邦。*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 E.J.Brill,1997,pp.629-633.对荷马来说,“他的社会学(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城邦是共同体组织的常态,不管是对外国人还是希腊人。我已经揭示出,他关于城邦的观念在两个主要方面预示了古典时代的城邦:首先,它是一个由堡垒保护的政府中心;其次,对一个特定范围的人民来说,它构成了人们主要的居住地区。”*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iod”,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vol.78,Sect.C,1978,p.15.斯库里认为,荷马史诗虽然包含着从迈锡尼经黑暗时代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史实,但有两点是清楚的:“城邦的早期形式,如果说还处在萌芽时期的话,即使不是在此之前,至少在荷马所处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已经产生。虽然两首诗中所描绘的是希腊历史上相互冲突时期的拼合,可是,如果当时新的城邦没有形成的话,那无论是《伊利亚特》、尤其是《奥德赛》,都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城邦比家族更加突出,因此,史诗的背景是当代的产物。”*Stephen Scully,Homer and the Sacred City,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90-91.拉夫拉勃的观点更加明确,“家族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是人们忠诚和认同的核心。可是,它排除对城邦的忠诚或者认同吗?或者说它排斥对城邦的义务感吗?”荷马时代的城邦“当然不是古典和法律意义上绝对的公民共同体,但它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他提醒人们注意荷马城邦的两个方面:一是公、私领域的分离,一是英雄对城邦共同福利的关心。这些事实表明,“荷马的城邦确实是一个人类、或者说是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它就不仅仅是自治的家族的总和。”*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pp.622-623.
四、结 论
在希腊城邦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的争论不太可能马上结束。然而当前的研究,大体上能够证明,它是在迈锡尼文明瓦解后地方共同体的基础上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迈锡尼文明灭亡后,部分地区确实可能倒回无国家状态。但在雅典和勒夫坎地之类的地区,某种形式的社会与政治组织继续存在。不过它们是铁器时代兴起的共同体,已非迈锡尼那样的官僚国家,但也不是后世的希腊城邦,而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组织。它们似乎既不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统治的结果,因此不足以给希腊传统中的多利安人入侵摧毁迈锡尼文明并建立统治提供支持,也没有给现代学者假设的下层阶级造反夺取权力导致迈锡尼文明灭亡和新组织出现提供证据,更像是迈锡尼文明的宫廷体系因某种原因瓦解后造成的社会动荡与居民迁移的结果。这些共同体的典型特征,是缺乏集中的权力和成型的官僚系统,首领既缺乏超出共同体一般成员之上的权威,也缺少让自己权威延续的经济基础和手段,易言之,它们的成员大体平等。各个共同体都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相互之间少有联系,除勒夫坎地外,在所谓黑暗时代的孤立中,尝试集体面对外部世界,并找到解决自己面临问题的方法。集体议事和决策的机制,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们肯定不是迈锡尼那样以宫廷为中心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和组织,如狄金森所说,都更接近荷马笔下的城邦。*Oliver 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pp.110-112.它们是否有资格被称为国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也许并不相同。如果我们承认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是国家,则黑暗时代的这些共同体,如雅典和勒夫坎地那样的,最多也就是原始形态的国家。*贝兰特曾否认希腊城邦的国家性质,并与汉森等就此展开论战。如果希腊城邦失去了“国家”资格,荷马原始城邦作为国家的资格自然更加可疑。相关讨论见Moshe Berent,“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War,Violence,and the Stateless Polis”,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0,No.1,2000,pp.257-289; Moshe Berent,“Greece: The Stateless Polis (11th-4th Centuries B.C.)”,in Leonid E.Grinin(et al),The Early State,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Volgorad: ‘Uchitel’ Publishing House,2004,pp.364-387。中国学者的反应,参见石庆波:《城邦:无国家的社会——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世界历史》 2011年第4期,第89—96页。它们如何演进为荷马那样的城邦,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让我们勾勒出具体的进程。但基于目前的证据,它们是荷马时代原始城邦前身唯一的候选者。因此,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也许不应当到荷马时代寻找起点,而应当到所谓黑暗时代的小共同体中去找。
(责任编辑:郭丹彤)
2016-05-3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政治”(编号:11YJA770059)。
晏绍祥(1962-),男,安徽金寨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A
1674-6201(2016)02-0004-10
*徐家玲教授、徐建新研究员、张强教授、李晓东教授和郭丹彤教授等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