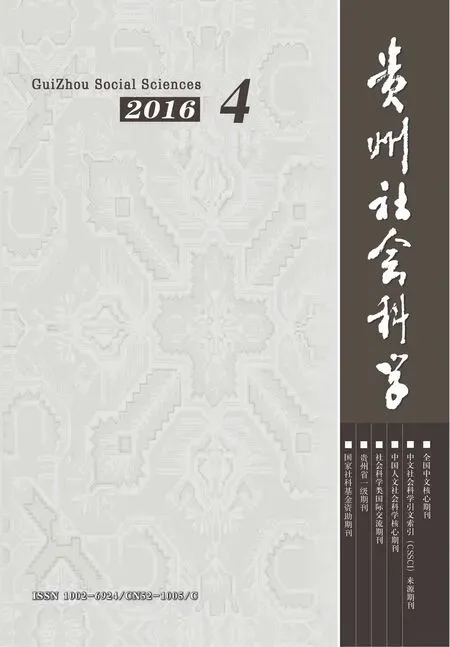“减增长”理论及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反思与借鉴
2016-03-15陈弘
陈 弘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3)
“减增长”理论及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反思与借鉴
陈弘
(南开大学,天津300353)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持极端反对见解的“减增长”(degrowth)理论。这一理论反省了工业化进程造成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进而认为,任何形式的经济增长都内在地不可持续;削减消费、降低经济规模才是人类社会当下唯一的正确选择。“减增长”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在面对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之时提供了一个另类的逻辑思路;其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批判更具有特别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减增长”理论的特征,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经济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审视“减增长”,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减增长”;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
一、“减增长”理论的形成
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催生了各种反省“生产至上主义”(productivism)理论的不断涌现;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减增长”(degrowth)理论无疑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任何经济增长都内在地导致不可持续,主动降低经济与消费规模才是人类社会面对巨大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减增长”理论将过度的生产与消费视为全球生态问题与社会不平等根源,倡导以减少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改善生态条件和实现平等。在“减增长”的理论框架中,生产与消费规模的降低与福利改善并行;在“减增长”的理想社会中,“足够”原则替代了“更多”原则,创新被定义为实现快乐与节约的社会与技术安排。
“减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可以回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年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稳定状态”(stationary state)[1]——穆勒认为的如果经济扩张超过了其应有的量级水平,社会的经济目标应该从数量扩张转变到质量提升,是与“减增长”逻辑最为贴近的古典经济学基础。1944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又将环境变量引入“稳定状态”概念后提出,“稳定状态”是维系生态环境可供人类生存的必定要求。[2]此外,反传统经济学家埃兹拉·米香(Ezra J. Mishan)对工业化国家唯增长论的质疑、激进生态政治学家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以“适度”原则替代“更多”原则的呼吁、圣雄甘地倡导的“自愿简朴”(voluntary simplicity)生活方式,也都是“减增长”理论的思想沃土。
标准的“减增长”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罗马尼亚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墒定律与经济过程》[3]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考虑能量的衰减以及墒的提高*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其他影响,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热使之完全转换为有用的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熵是动力学测量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的概念,不可逆热力过程中熵的微增量总是大于零。熵是在动力学中测量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名为《增长的极限》[4]的报告,将污染、原料短缺以及生态损毁等全球问题归结于经济增长;尽管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增长”(zero growth)对策与“减增长”尚有距离,但这一报告无疑是后来“减增长”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同年,“生态主义”(Ecologist)杂志编辑爱德华·戈得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和罗伯特·P-艾伦(Robert Prescott-Allen)在《拯救蓝图》一文中提出,必须实行激进的反工业化与反城市化措施才能避免“社会溃散和地球生命支持体系的瓦解”,[5]他们的提议还推动了全球生态主义政党的广泛建立。1973年,环保主义者、佛教经济学家舒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在《小的就是美的》中指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追求荒谬地将提升消费水准视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是在减少消费的同时提高福利水平。[6]
1979年,乔治斯库-罗根的论文集被译为法语以“明天,减增长”(Demain la décroissance)为题出版,“减增长”这一新词汇正式进入人们视野。新千年之后,“减增长”理论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继续扩展着影响力。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Serge Latouche)在《减增长经济学》(Degrowth Economics)[7]、《全球减档》(Globe Downshifted)[8]等文献中反复强调,人类为增长而增长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严重恶化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现代经济的主要目标应该从增长反转到其对立面——缩减生产与消费的规模。拉脱谢尔的理论还形成了与“减增长运动”(Degrowth Movement)的互动,在其理论的推动下,2008年首届“为了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的减增长”(Economic De-Growth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会议在巴黎召开,“减增长经济学”随之兴起并成为激进绿色理论复兴的标志;201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二届会议通过的《“减增长”宣言》(Degrowth Declaration),也是拉托谢尔理论蓝图的展现。
二、“减增长”理论的特征
(一)依托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反省经济增长
“减增长”理论是对发达经济体生产与消费模式生态反省的产物。其基本理论逻辑是:经济增长必定依赖资源的不断投入,而以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资源必将在经济增长中耗尽,可再生性资源同样在过度使用中也注定面临同样的境地。这样的担忧造就了寻求以缩减经济与消费规模的方式化解人类困境的“减增长”理论,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是这种对经济增长反省的基础——标准“减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乔治斯库-罗根率先引入了墒、热力学第二定律等物理学概念反省经济增长;此后,生态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进展也持续地成为对经济增长反省的理论基础。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的概念被“减增长”倡导者广泛使用,是“减增长”理论依托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例证。1992年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William E. Rees)通过比较人类需求与地球生态再生能力提出了“生态足迹”概念——能够为支持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持续提供资源和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其具体度量指标为“全球公顷”(global hectare-gha)*gha是在给定年份中以全球平均生产力计算的所有“生物生产力地域”的面积单位;“生物生产力地域”包括耕地、森林、渔场,而沙漠、冰川与公海不计算在内。。[9]根据独立科学家组织“环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05年官方报告,满足人类消费水平人均需要2.7gha,而全球65亿人口共计拥有134亿gha,人均拥有量为2.1gha;而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全球公顷”的比例为6.4:1,北美居民人均“全球公顷”是孟加拉的22.3倍。据此推算,倘若全球人口都能过上欧洲人的生活至少需要3个地球。而关于地球自然承载限制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是“减增长”理论的另一重要源泉。2009年,28位自然科学领域知名学者共同界定并量化了确保地球安全运行的9项“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指出一旦这些边界被突破,“突然和不可逆的环境变化将侵害人类的福祉乃至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损失”;而9项边界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物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s of the planet)3项量化指标边界已被突破,其他6项指标中能够被具体量化的4项指标数值正在向逼近临界点边界的方向恶化。[10]
这些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是对“生产至上主义”生态反省有力的科学支撑,而“减增长”理论是这种生态反省的必然逻辑结果。
(二)从根本上否定以技术进步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性
“减增长”理论必然面对的挑战是科学技术的“绿色”功能——技术进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进而会减少能源耗费,科技创新开辟的新能源也可以补充乃至替代那些即将耗尽的资源。而“减增长”理论于此的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技术进步的“绿色”作用——在“减增长”理论家们的认识中,所有可用于保护环境的有效利用能源以及其他资源技术的“绿色”效果,最终都将被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吞噬,以回弹的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技术进步对资源回弹压力的分析可以追朔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 Jevons)。1865年杰文斯在《煤的问题》中对英国工业化早期最重要能源——煤的消耗考察发现,尽管技术进步提高了煤的使用效率,但煤的消耗总量却伴随着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11]这一被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的假说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验证;而20世纪石油危机之后的“Kaazzoom-Brookes假定”(Khazzoom-Brookes Postulate)则成为了“减增长”理论对技术“绿色”功能否定的直接依据。1992年,哈里·桑德斯(Harry Saunders)因循Khazzoom[12]和Brookes[13]分别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能源技术进步与石油消费关联的研究成果提出,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节约能源,但同时又增加了对能源的新需求,其净结果是能源消费总量的提高。[14]尽管“Kaazzoom-Brookes假定”在能源经济学中并非毫无争议,但能源效率提高会导致能源使用反弹的观点被理论界广为接受,而且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2007年一项对石油危机后技术进步对石油消费的市场调研报告以详尽的数据分析证明,“石油危机促进了所有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石油使用效率提高尤甚。但30年之后所有效率提升的净效果是全世界更为依赖原油”;“能源使用量的上升吞噬了效率提高的成果,我们最终见证的不是能源需求受到控制而是能源效率改善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15]
在“减增长”的理论认识中,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足以挽救经济增长导致的能源耗尽前景;技术进步从来不是解决与经济增长伴生的能源与生态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唯一有效的只能摒弃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运转模式转向削减经济规模与消费规模。从这个意义上,“减增长”理论与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有一致的逻辑,如保罗·斯威齐指出的,“我们已经无法继续拥有容纳更大的经济规模、更多人口的环境承载力,唯一的出路就是调整等式的另一边;而等式的不均衡已经如此危险,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经济趋势的改良已经毫无作用,彻底颠覆过往的经济模式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16]
(三)寄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体自愿与社会改良
“减增长”理论将经济与消费规模的缩减寄望于价值重塑基础上的个体自愿行动与整体社会改良。“‘减增长’不仅仅是数量缩减问题,它更是价值范例的重塑——尤其是社会与生态价值的重新确立,是经济的再政治化”。[17]在“减增长”理论家们看来,价值重塑基础上的“自愿”才是经济与消费规模缩减真正可靠的基础。拉托谢尔强调,“减增长”是一种社会主流变迁,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项目而是一个关键词”;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主导太过长久的社会,“构建于一个缩减社会之上的有关理念是摆脱其束缚的思想动力”。[18]第二届“为了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的减增长”全球大会更开明宗义——“‘减增长’肩负的理念是自愿削减经济系统规模”。[19]
引人注意的是,尽管“减增长”理论家自己也怀疑经济与消费规模缩减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实现的可能,但他们却坚决反对将问题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更对颠覆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现“减增长”的方案忧心忡忡。他们笃定“减增长”的实现需要的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颠覆而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正如“减增长”的旗帜性代表人物拉托谢尔所坚信,“取缔资本家、禁止受雇佣的工人以及货币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使社会陷入混乱”;“我们需要寻找另一条非发展主义的道路,摆脱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主义与增长的局限;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货币、市场乃至工资等原有社会机制的颠覆,而是对其按照另一种原则进行改造和重构”。[20]
显然,在维持资本积累结构前提下以改良的方式驯服资本主义体系实现经济与消费规模缩减,是“减增长”理论家们期盼的结果。他们认为,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可以被驯服的一个样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能够将其引上一条“生态资本主义的良治之路”;这样的改良也如同物价管制一样是资本主义价值关系的代表。而改良之外的道路则完全不在“减增长”理论家们的考虑之内。
三、“减增长”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
作为走的最远的一种对“生产至上主义”的反省,“减增长”理论诞生之后面临着各种批评。其原因显而易见:尽管“减增长”理论宣称缩减经济与消费的规模可以与福利水平提升并行,但这样的社会在历史上未有先例;尽管经济增长不能给所有人均等地带来福利,更有社会阶层在增长中受到了相对乃至绝对的福利损害,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教育、卫生保健水平的必要条件是显而易见的;而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在《终极资源》*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编译本中,我国学者将书名《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意译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直接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中阐述的与罗马俱乐部对立的观点——技术进步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也自有其理论逻辑支撑与现实佐证。[21]
笔者认为,“减增长”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在面对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之时提供了一个另类的逻辑思路;其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批判更具有特别的、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问题是“减增长”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里笔者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经济体与马克思主义三个视角对“减增长”理论做一简要评论。
(一)“减增长”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的可能性
那个在不到一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至今显然早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甚至也创造出了从维系生态平衡到乃至让劳动者更为自由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从未因此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更不断以制造并满足人为需求的方式支撑经济增长。1913-2005年期间,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GDP增长了300倍,但资本主义体系在漫长的经济增长过程展示的,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损毁和底层群体利益的受损。其根源在于对利润无止境追逐下的资本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23]这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根本的法则。
“减增长”的倡导者试图重塑经济增长价值观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一个兼顾生态可持续性与公正的社会也是社会的需要。但“减增长”理论不认为其目标的实现需要打破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只关注了经济增长这一表层却忽视了其背后更具实质意义的资本积累,无视无止境追逐利润对“减增长”的根本阻碍,更没有与劳工阶层结盟的愿望。这样,逻辑正确的“减增长”就成为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空中楼阁——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减增长”存在着根本冲突,它注定无法与奉资本积累为根本法则的资本主义体系抗衡。而每当资本主义体系中现实的“减增长”——经济衰退出现之时,都毫无例外地伴生着贫困人口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一切都表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现实的“减增长”不仅无从实现社会公正,反而会给公正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害。如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的,“减增长”理想的实现不能仅仅简单地以缩减经济规模为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减积累”(deaccumulation),彻底告别以无止境的积累作为动力的社会。[24]只有如此,恩格斯在1880年预见的那个“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5]的社会,才可能真正到来。
(二)“减增长”可能蜕变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毒药
“减增长”理论认为,缩减经济与消费规模不仅适用于富裕的发达经济体,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同样适用。拉托谢尔明确提出,认为“减增长”不适用于经济后进经济体的观点,是对增长盲目崇拜思维作祟的表现,“南方的问题不是发展而是解开纠结,消除那些阻碍其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障碍”,“南方需要的是摆脱对北方的经济与文化依赖,从被殖民主义、发展主义与全球化打断的历史中重建本土文化”;“将经济增长作为摆脱由增长带来困苦的唯一途径,只会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26]这些“减增长”理论家们坚持认为,缩减经济与消费规模才能使发展中经济体摆脱被发达的中心国家控制与剥削的局面,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才能得以通过自给自足的道路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
客观地说,发展中经济体通过经济增长改善福利的道路并不顺畅,他们的经济增长更多展示的是不断的资源损毁与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很多发展中经济体以经济增长给予人民利益满足的允诺被腐败、贫穷乃至社会撕裂所瓦解,最终获益的不过是少数富人。但增长结果的不如人意不是否定增长的充分条件;从经济增长中获取物质性福利改善,是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需求;对于那些食品、卫生保健、教育需求还很难满足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更是福利改善的基本前提。正如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于此所言,“在那些发展过度的国家限制其人口与人均消费之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稳态原则的道德说教毫无意义”。[27]
如同不将资本积累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减增长”的根本障碍一样,“减增长”理论家们将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盲从,漠视源自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发展中经济体影响。这样去寻求发展中经济体的“减增长”道路不过是缘木求鱼。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28]的景象,今天正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深刻地制约着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而发达经济体政治家们对发展中经济体探寻“新道路”的呼吁更值得警惕——奥巴马曾在澳大利亚给中国“指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中国应该寻找到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29]倘若发展中经济体听信了这样的规劝而走上“减增长”的道路,那么“减增长”就必定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吞下的一剂毒药。
(三)马克思主义与“减增长”
自本·阿格尔(Ben Agger)1979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理论回应了资本主义的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以生态视角批判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学界的最主流思潮之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也大有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的趋势。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减增长”理论有着一致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增长动机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在利润的牵引下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过度增长的社会;而与其不同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认“减增长”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可以通过自愿的改良实现。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支持“减增长”吗?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考察,资本主义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替代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而非生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30]所以必须首先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经济增长的支持者。但也必须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更从来不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者。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济增长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服务于劳动者福利改善目标的增长,另一类是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的增长。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是要让经济增长成为劳动者有更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的物质基础;脱离了这样目标的经济增长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增长。
而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减增长”理论给予当下中国的最重要启示是,经济增长必须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的物质基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绝不会单纯因经济增长本身迎刃而解;而倘若经济增长速度在必须的结构性调整中有所降低,也并非注定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1] John Stuart Mill.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M]. London: John W. Parker, 1848.
[2] Lewis Mumford. Condition of Man [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4.
[3]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5] Edward Goldsmith; Robert Prescott-Allen.ABlueprintforSurvival[J]. The Ecologist Vol. 2, No. 1, January 1972:1.
[6] E. F. Schumacher.SmallisBeautiful:EconomicsasifPeopleMattered[M]. London: Blond and Briggs, 1973.
[7] Serge Latouche.DegrowthEconomics[EB/OL].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Nov. 2004. http://mondediplo.com/2004/11/14latouche.
[8] Serge Latouche.TheGlobeDownshifted[EB/OL].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Jan. 2006. http://mondediplo.com/2006/01/13degrowth.
[9] William Rees.EcologicalFootprintsandAppropriatedCarryingCapacity:WhatUrbanEconomicsLeaves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Oct, 1992.
[10] Johan Rockström, Will Steffen and 26 others.PlanetaryBoundaries:ExploringtheSafeOperatingSpaceforHumanity[J]. Ecology and Society. Vol.14, No.2, 2009.
[11] William S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M].London: Macmillan, 1865.
[12] J. Daniel Khazzoom.EconomicImplicationsofMandatedEfficiencyStandardsforHouseholdAppliances[J]. The Energy Journal, Vol. 1, No. 4, 1980.
[13] Len Brookes,ALowEnergyStrategyfortheUKbyGLeachetal:AReviewandReply[J]. Atom, No.269, March 1979.
[14] Harry D. Saunders, The Khazzoom-Brookes Postulate and Neoclassical Growth[J]. The Energy Journal, Vol. 13, No.4, 1992.
[15] Jeff Rubin. TheEfficiencyParadox[R]. Stratecon, 27, Nov.2007:1.
[16] Paul M. Sweezy.CapitalismandtheEnvironment[J]. Monthly Review, Volume 41, No. 2 (June 1989):6.
[17] V. Fournier. Escaping from the Economy: Politics of Degrowth [EB/OL].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articleid=1751573.
[18] Serge Latouche.DegrowthEconomics[EB/OL].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Nov. 2004. http://mondediplo.com/2004/11/14latouche.
[19]WhatisDegrowth?[EB/OL]. http://www. barcelona.degrowth.org/What-is-Degrowth.22.0.html.
[20] Serge Latouche,TheGlobeDownshifted[EB.OL].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January 13, 2006. http://mondediplo.com/2006/01/13degrowth.
[21] Julian L Simon.TheUltimateResour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86.
[24] John B Foster.CapitalismandDegrowth:AnImpossibilityTheorem[J]. Monthly Review, Volume 62, Issue 8, January, 2011.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7.
[26] Serge Latouche,DegrowthEconomics[EB/OL].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November 2004, http://mondediplo.com.
[27] Herman E. Daly.Steady-StateEconomics[M].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148.
[28]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5.
[29]FacetofacewithObama[EB/OL]. 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s2872726.htm.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责任编辑:赖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研究”(15BKS081)。
陈弘,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转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F014.36
A
1002-6924(2016)04-1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