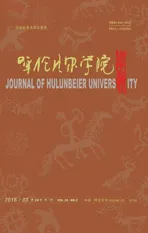谁 是“胡”?
——也谈中古时期的“胡”称
2016-03-15徐汉杰
徐汉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众所周知,“胡”的概念一般是指与“汉”相对的外民族群体。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如果细究,“胡”的概念从产生以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中古中国,由于北方民族大量内迁,“胡”作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指代含义发生过一些变化。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行成主要与华、夷双方对于“胡”概念的重构有关。
一、“华夷”:两种立场下的“胡”称
在汉文文献中“胡”最早是作为指代匈奴的专名而出现的。①后来可能受匈奴的“胡”称影响,汉人在其他北族后面也加上了“胡”字,诸如“东胡”、“西胡”、“羌胡”、“林胡”等等。于是乎诸多与中原农耕人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群体就与“胡”称扯上了关系。但如同岑仲勉先生所说“《史记》、《汉书》中单称‘胡’者,率指匈奴言之”。②较之先秦、秦汉的其他文献,情况也多相似,其实在东汉以前若单言“胡”则仍是匈奴的专名。
东汉初年,匈奴南北分立,势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伴随着其他北族地兴起,改变了匈奴在中国北方“一家独大”的形势。与此同时,原本作为匈奴专名的“胡”称在汉人的脑海里开始模糊,或者说对于当时北族的更替,反映到汉人的眼里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前代的“胡(匈奴)”和如今的北族一脉相承,从而在称谓上亦可以延续。因此最晚到东汉末年,文献上就开始出现单言“胡”称来指代北方诸族的现象。如《太平御览》卷706引《风俗通》曰:“灵帝好胡床,董卓权胡兵之应也。”③此处“胡床”、“胡兵”之“胡”并非特指匈奴,而指其他北族已很明显。所以专指匈奴的“胡”毕竟只是一个属于历史特定时期的称谓,准确地说它只在东汉以前适用。
从魏晋开始,中国进入了北族大量内迁的时代,而此时汉人也几乎把北来的诸族都称之为“胡”。《晋书·元帝纪》载:
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④
又《梁书·西北诸戎传》载:
晋氏平吴以后,少获宁息,徒置戊己之官、诸国亦未宾从也。继以中原丧乱,胡人递起,西域与江东隔碍,重译不交。⑤
可见东汉以后除匈奴之外,汉人把羯、鲜卑、氐、羌等民族也纳入了单言之“胡”的范围。可以说此时在汉人的观念里“胡”已经成为了一个与“华(汉)”相对的概念,它几乎就成了汉人对北方外族的通称。
但是在那些体现中古时期北族民族意志的文献上,对于“胡”的记载我们看到的又是另一种景象。《宋书·臧质传》保存了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给臧质书信,说: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质。⑥
拓跋焘以“胡”与“丁零”、“氐”、“羌”对举,可见这里的“胡”仅仅表示的是某个民族,而非北方民族的统称。那么鲜卑人口中之“胡”到底是何人?根据《魏书·尉元传》记载,北魏大臣尉元的上表云:
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围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⑦
周一良先生根据胡人子呼延之姓,认为此“所谓胡人者为匈奴无疑”。⑧因此前文拓跋焘所言与“丁零”、“氐”、“羌”对举之“胡”很有可能也是依附于北魏鲜卑政权下的匈奴人(或其别部)。另外,由于鲜卑和“胡”的混血,在中古时期还形成了“铁弗”这个部落。《魏书·铁弗刘虎传》载:
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⑨
刘虎为南单于之苗裔,此南单于确指匈奴无疑。故北人所谓“胡父”就是“匈奴父”已很明显。
那么在鲜卑人观念里的“胡”多指匈奴人,是否说明鲜卑人依然延续着秦汉时期的传统不像汉人那样恣意建构“胡”的概念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中古中国流行着一种“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的观念。⑩东汉以后,汉人世界里出现的这种泛化的“胡”称,后来被作为阻碍外族对中原政权攫取的意识形态保留下来。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梁大臣陈庆之出使洛阳时在宴会上对北朝大臣萧彪、张嵩等说:“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11]可见胡人政权想要统治中国,不管它实力多么强大,首先在正统性上它是很难得到论证。这种观念甚至还影响了一些北族。《晋书·姚弋仲载记》载:
(姚弋仲)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12]
可以说中古时期汉人把外族称为“胡”旨在标榜自己的“华夏正统”。与汉人一样鲜卑人多以“胡”专指匈奴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在汉人的建构下,当时的“胡”称已经不仅仅表示一种种族区分了,鲜卑人要想名正言顺的攫取中原政权,光有武力是不够的,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必须脱离汉人所建构的“胡”的范围,所以他们常用旧俗,“胡”还是多用来指代匈奴人。另外,为了迎合这种趋势,鲜卑人甚至还学习汉人,把当时内迁的其他北族也称为“胡”。《广弘明集》载:
(北周武帝宇文邕)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奏曰:“佛教东传时过七代刘渊篡晋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称为五胡。其汉魏晋世,佛化已弘宋、赵、苻、燕,久习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请如汉魏不绝其宗。”[13]
可见鲜卑人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也认同胡人“非中夏以非正朔”,盗取中原政权是不合法的。[14]但鲜卑人为了其自身的政治目的考虑,他们并不认同汉人的那套区分华夷的概念,于是鲜卑人开始标榜自己并非“五胡”,并建构符合其民族利益的“胡”的概念体系,甚至还附会出鲜卑拓跋氏出于黄帝,[15]宇文氏出于神农的世系,[16]标榜鲜卑与汉人同根同源。因而我们看到在体现鲜卑人意志的文献中的“胡”也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对前代“胡”称的继承。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在中古这个非常时期,为了让鲜卑人脱离“胡”的指代范围而对当时情况的一种妥协。
上述主要论述了建立北魏、北周的鲜卑人,其实想要从汉人建构的“胡”称下脱离出来的现象在有心与汉人争夺天下的北族之间是普遍存在的。后赵的建立者羯人石勒的例子也极具代表性。《晋书·石勒载记》载:
(石勒)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崇(王)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17]
石勒当时自称“小胡”主要是出于向拥有汉人血统的王浚示弱、麻痹对方的考虑。而等石勒政权稳固之后,他立马下令禁言“胡”称,[18]甚至改胡物名称以“胡饼曰麻饼,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19],似乎想把后赵政权从“胡国”中脱离出来。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汉人与北族之间对“胡”称的不同认识主要源于“胡”的概念在政治需要或民族意志下而进行建构与改造的结果。对于汉人来说他们往往并不在意北方诸族具体的种族区分,他们的视野更多的仅停留下“非我族类”的华夷之别,故在匈奴衰败之后,作为其专名的“胡”其指代范围反被扩大。而此时对于觊觎中原政权已久的北族来说,他们入主中国后深受华夏正统观念的影响,都想试图脱离汉人用来指代外族的“胡”的范围,于是他们也试图建构有利于自身的“胡”称。另一方面,中古时期的北族也不同于前代扰边争夺财物的外族,他们在武力上的优势促使了他们与汉人争夺中原统治权的野心,也为他们争取到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话语权,所以北族建构之“胡”和汉人建构之“胡”就一同被文献记载下来,从而导致中古文献中的“胡”称出现华夷之间指代不一的现象。
二、“异类”:西域人与“胡”称
上文论述了华夷之间的建构导致了中古时期“胡”称的混乱。另外六朝以后,“胡”称又开始向专指西域人转移。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是在汉人和北族的主观意识下建构完成的。
众所周知,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从此西域人和汉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而对于广大的西域人的命名,起初汉人以匈奴(“胡”)为方位标准把在其西边的西域人称为“西胡”。如《说文解字》邑部云:“鄯善,西胡国也。”[20]有时亦称作“西域胡”。如《汉书·元帝纪》:“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21]但是,考西汉之前的文献,单言“胡”则一般不指代西域人。后来,汉人把“胡”的指代范围扩大,作为北方诸族的通称,那么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西域人自然也包括其中。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22]此所言“胡某”物很多为西域之产。当然此处“胡”的概念很可能只是广义的北族,并非西域人的专指。
魏晋之后,以“胡”专指西域人的现象开始出现。《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
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23]
睕睕,作目深陷貌,此为西域人的特征。按,过去学者讨论羯人是来自中亚的白种人,[24]我们并不否认羯人中有中亚血统的混入,此处石宣很有可能就是羯人与中亚混血的产物,但“宣诸子中最胡状”之语至少说明羯人石氏以高鼻深目之种为异类。文中以“胡状”形容石宣,此“胡”称西域人已很明显。
六朝以后“胡”称用来专指西域人就更加常见了。《旧唐书·突厥传》载:
思摩,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启民归国,乃去可汗号。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25]
《安禄山事迹》载:
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26]
又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在记载西域诸国时说:
至建驮国,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䫻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郍,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皆是突厥。[27]
上述所载高鼻胡人,亦或建驮国、谢国的土人,都是西域人无疑,可见不管是汉人还是北族六朝以后很多情况下北族已经脱离了“胡”的范围,而“胡”多用来专指西域人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讨论到此,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为什么此时的“胡”又被用来指代西域人了呢?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考证在“胡”与西域人的关系时,根据匈奴别部胡羯高鼻深目的体貌特征,认为“胡”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高鼻深目,它的借代义的转移主要是匈奴人和西域人在形貌特征相似,故匈奴衰败后西域人就继承了其“胡”称。[28]岑仲勉先生则根据《火教经》语ahu(主)一词,指出西域人称之为“胡”,是因“其信仰火教而得名,或者取家主(Hauoherr)之义而得名”,并认为由于匈奴之先与西域(中亚)人存在“尚为明了之一种关系”,匈奴之“胡”称很可能亦是“直接或间接输入波斯语言”,[29]得出了与王国维正好相反的结论,但两者都认为匈奴之“胡”与西域人之“胡”存在着继承或被继承的关系。
其实我们并不同意王国维所说的,西域人之“胡”称是因为形貌与匈奴同,而从匈奴那里继承下来的。其一,匈奴别部羯胡并不能代表秦汉匈奴之族属,而且根据现在的研究,匈奴也并不只有高鼻深目之种,他其实是一个欧罗巴和蒙古利亚人种的混合群体。[30]其二,如果“胡”称只能用来称呼高鼻深目之人,是无法解释魏晋时期鲜卑、氐、羌等东方种也被称为“胡”的现象。另外岑仲勉先生所说的匈奴之“胡”本来源与西域人,匈奴消失之后,“胡”称回归西域人也是不能解释“胡”的概念曾经被扩大的事实。另外,汉人以单言“胡”用来称西域人和称其他北族(除匈奴外)几乎是在魏晋时期同时出现的。而且“胡”称趋向于西域人时,匈奴还未完全“消失”,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认为“胡”称在六朝以后多专指西域人主要是当时重新建构的概念。中古时期的“胡”含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异类”。汉人称外族为“胡”自不必言说,即便是对于当时突厥、羯等北族言“胡”也多了一种异类的味道。前面所举的石宣被人嘲笑,阿史那思摩不得为设都是因为长相另类。中古时期作为东方种的北族其实形貌和汉人类似,生活习性上即便开始有些不同,但入主中国后受汉文化影响,其实是很容易改变的,发展到后期可以做到和汉人无异。例如:唐代的代北贵族几乎都是外族血统,但论阀阅世家,甚至还高于许多汉姓高门。而西域人则不同,即便在生活习性上一如汉人,但其形貌不易更变,其很难融入华夏群体。因此,北族也抓住了西域人这个的特点在提到“胡”时经常会提到其高鼻深目与东方种迥异的形貌特征。吕思勉先生根据《南史·邓琬传》记载的“刘胡南阳涅阳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长单名胡焉”认为南人亦可以称为“胡”。[31]其实这个现象还是因为其长相异类,不同于“中国人”罢了。六朝之后,西域人大量入华,中国人接触之“异类”多是西域人,所以这个“胡”称变慢慢多用来指代他们了。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虽然六朝以后的“胡”有专指西域人的趋势,但如果把此扩大到如王国维所说:“后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32]这种逢“胡”便是西域人的理论也未必尽善。中古时期汉人与北族之间由于立场不同,对“胡”称的建构存在的差异其实在六朝以后还是没能很好的统合。即便到了唐代,对于汉人来说作为区分华夷的“胡”称,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因此汉人有时为了炫耀自身身份还是会把“胡”的概念扩大到北族。如《旧唐书·高祖纪》记载了高祖在未央宫设宴,“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33]此处的“胡”指代的是突厥。显然,这里的“胡”与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所记载的“突厥”和“胡”的概念截然不同。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唐代的文献中还有很多。如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34]此“胡”也是泛指北方诸族,而非专指西域人。唐人崔融则说的更加直白:“夫胡者,北狄之总名也。其地南接燕赵,北穷沙漠,东接九夷,西界六戎。”[35]可见六朝之后“胡”确实有向西域人专名的情况发展,但像“胡”这样被汉人长期沿用作为指代外族的概念一时想要完全消除也是非常困难的。
三、结论
在古代中国,汉人的恶习总是喜欢用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词汇来给外族命名。“胡”这个词即便早期含有“天之骄子”之褒美,[36]但到了中古时期,可能因为汉民族在文化上拥有强烈的自我优越感,亦或是对此时大量外族内迁的反感情绪下产生的故意贬低,此时的“胡”已如美国学者丹尼斯·塞诺所说已“用作‘野蛮人’的通称”。[37]在这种贬义化影响下,北族纷纷希望与“胡”称脱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总的说来,“胡”这个称谓是一个具有很强时代性的概念,“胡”这类敏感的词出于政治目地被华夷两族建构,从而不断注入新的含义。中古时期汉人因为出于自身正统性的考虑以“胡”区分华夷,而北族为了使其能真正融入中国,也开始建构“胡”的概念,这些都导致了此时对“胡”概念的重新认识。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38]故华夷之间在争夺实际权力时又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因而双方都乐此不疲的去解释华夏正统观下“胡”的概念。但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又不能很好的统合,就使中古时期“胡”的概念复杂化。
另外,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包容的民族共同体,“胡”字概念变迁的背后其实蕴藏这一个“种族”与“文化”的认识问题。被文献记载而保留下来的汉人与北族之间关于“胡”称的分歧其实反映了中古时期北族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上升。“胡”的概念在中古这个奔溃与扩大的时代被重新塑造,其实也是汉人与北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一种表现。
注释:
①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西胡续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11页;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胡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8页。
②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原载1944年5月《真理杂志》第1卷第3期,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91一19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③《太平御览》卷706《服用部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147页。
④《晋书》卷6《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页。
⑤《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09页。
⑥《宋书》卷74《臧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2页。
⑦《魏书》卷50《尉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13-1114页。
⑧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
⑨《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54页。
⑩《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1页。
[11][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0页。
[12]《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61页。
[13][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0,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
[14]即使有学者提出北周宇文氏很可能出自匈奴族(详见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但宇文氏讳言其出于匈奴而自称鲜卑人,故至少在族群认同上宇文氏依然是鲜卑人的代表。
[15]参见《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16]参见《周书》卷1《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
[17]《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1页。
[18]详见《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7页。
[19]详见《艺文类聚》卷85,“豆”条引晋人陆翙所著《邺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53页)
[20][汉]许慎:《说文解字》卷6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页。
[21]《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页。
[22][晋]司马彪,[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13《五行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72页。
[23]《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6页。
[24]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16-417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页。童超:《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考证》,《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等。
[2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3页。
[26][唐]姚汝能撰,曾貽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2页。
[27][唐]慧超撰,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93页。
[28]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西胡续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3-314页。
[29]参见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原载1944年5月《真理杂志》第1卷第3期,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91一19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页。
[30]详见陈立柱:《三十年间国内匈奴族源研究评议》,《学术界》,2011年第9期。
[31]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胡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8页。
[3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西胡考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33]《旧唐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页。
[34]《全唐诗》卷18《出塞》,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4页。
[35]《全唐文》卷219《拔四镇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6页.
[36]详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0页。
[37][美]丹尼斯·塞诺著;罗新译:《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6—8世纪)》,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5页。
[38]邢义田:《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收入《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