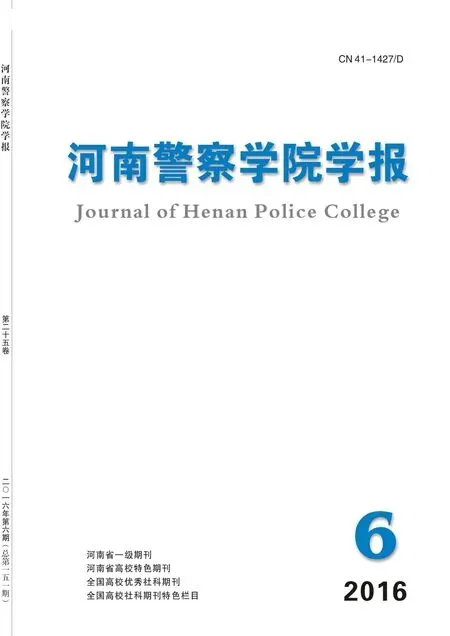微信个人隐私权保护探究
2016-03-15丁冠天
刘 斌,丁冠天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微信个人隐私权保护探究
刘 斌1,丁冠天2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大数据时代下,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工具之一,因此承载着个人隐私保护的重任。微信好友、第三方网络服务提供商都有可能成为侵权主体,微信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机制包括: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完善微信隐私管理规则等。
微信;朋友圈;隐私权;保护机制
大数据时代下,微信作为即时通讯服务的代表,开始改变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微信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了解到圈内好友的生活动态,也因其强大的数据储存功能,使个人隐私面临着被泄露和利用的危机。近几年来,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剧增,截止到2016年3月份,微信的活跃用户量已经突破9亿,庞大的用户群积攒了大量个人隐私信息,这也导致许多微信用户个人隐私信息外泄,给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更有投机分子利用隐私信息进行欺诈,同时,第三方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对用户信息的分析,进行广告精准投放,也给用户带来诸多困扰,而这一切都源于微信中的个人隐私没有被妥善保护。
一、微信中的个人隐私权问题
隐私权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开始,2009年《侵权责任法》才第一次明文提及隐私权,所以,对于隐私权的理论研究比较滞后,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尚无定论。随着新媒体时代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隐私的边界显得更加模糊,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其著作《隐私权》中提到:“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应当受到充分保护,然而人们发现这一保护的确切性质与范围需要不时地重新界定[1]。”微信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个人隐私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王利民教授提出,“未来我国的《人格权法》中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构建隐私权的内容,即生活安宁与生活秘密”[2]。现在来看,微信中的隐私信息完全可以影响到用户的生活安宁。
(一)微信中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范围界定上争议较多,世界范围内美国、欧洲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尽相同,在探讨微信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微信中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这一范畴,也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才能够用隐私权去主张权利保护。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个人信息纳入到个人隐私去保护,理由在于,个人信息实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体现了一定的人格利益,应当作为隐私权保护。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下,人们使用网络过程中已经遗留下太多个人信息。并且,如果将个人信息全部纳入隐私保护,会造成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例如:姓名信息、身份证信息等,也被列入到隐私保护中。实则在社会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信息已经具有很高的公开性,甚至在某些网站注册信息中都能够查找到,那么这无疑不符合隐私权的保护范畴。通常来说,“隐私权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在该权利遭受侵害之前,个人无法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利,而只能在遭受侵害的情况下请求他人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3]。而个人信息是一种控制权,具有主动性。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应当分别进行保护,而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微信中的个人隐私还不能简单地对应所有个人信息,还应当具备隐私信息必要的性质,即不被打扰,不愿让人知晓的特征。
(二)微信中的“隐私保护区域”
微信系统将用户交流划分了不同的板块,从微信主界面来看,具备信息传播和交流功能的板块有两个部分,即微信聊天和微信朋友圈。微信聊天主要包括个人好友之间的单线交流与微信群的群体交流。微信朋友圈是通过发布文字,图片,视频到公开的朋友圈中以获得好友观赏和评价的交流方式为主的交流区域。这两个部分都具备个人隐私传播的机会和途径,也都拥有被他人知晓个人隐私的可能,那么是否应当将这两个区域都视为隐私区域而加以保护?
首先,微信聊天这一区域属于一对一或微信群聊天的方式进行交流,一般来讲,从传播的范围和广度来看,和普通的手机短信一样,具备高度私密性特征,所以一对一交流方式无需多作讨论,而对于微信圈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微信群具有公开传播的属性,微信群可以多达几百人同时在一个群内进行交流,此时微信用户应当知道自己发布的信息是在向一个多达几百人的群体发送,从受众群体的数量来看,已经构成公开传播,即这种情况下发布的信息视为发布者放弃了隐私权而自愿公开,不再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即使被群内的成员转发也不构成隐私侵权。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微信群依然属于私密空间,虽然群内人数可以达到数百人,但是,这种传播依然具备“指向特定人”这一要素,而并非向不特定的人群公开传播,微信群中的好友也应当知悉,群中的某一好友发布的信息,只在该群范围内,那么其他群内的好友对于群里所发布的信息具有谨慎的使用义务,即在未经信息发布者授权时,不能随意转载、使用包含其个人隐私的信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更贴合当下对隐私权保护的趋势,微信聊天这一区域的设置,在功能定位上应当是以小范围的信息沟通交流为主,从使用目的和方式上来看,这一区域的信息交流还具备“私密性”的特征。当一个人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个与自身相关的隐私信息,群里其他成员都有权利知晓这一事实,但是,不能够就此推定权利人允许其向群外的人披露这一隐私信息,王利民教授认为,“如果披露隐私的空间具有特定的范围,具有相对的非公开范围,那么也应受到隐私的保护。”[3]
另外,空间隐私权理论是近代隐私权研究的新方向,这一理论源自“隐私止于门前”的传统观念,网络时代下,空间隐私权的范围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而延展至虚拟网络空间。传统空间隐私权将个人私密空间看作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和影响之地,未经许可甚至不得窥视屋内。在网络空间下,虽然无形,但也应当坚守空间隐私的基本理论。微信群实则就属于网络空间的一种,从微信群建立的初衷来看,一般的目的是只允许信息在特定的人群间传播,也正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外流,微信群应当具备私密性。因此,微信群中的好友应当对所接收到的信息使用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当然,对于特殊情况也应作特殊分析,例如:权利人发布了与自己相关的隐私,同时还在群内与其他人进行文字讨论并传达出不受转发限制的意思表示,或者在数百人的群里发布隐私信息并能够从其表达中明显得出不受转发限制的意思表示情况下,微信群中的其他人可以不受隐私保护的限制,因为权利人有处置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对于所有信息都进行限制,有碍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其次,微信朋友圈这一区域更具讨论价值。微信朋友圈这种传播方式与微博存在较大差异。朋友圈属于一个半封闭环境,微博发布的状态,只要使用微博的人都可以查看到,而微信朋友圈的状态只有好友能够看到,那么朋友圈属于“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就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将其认定为公共空间,就意味着,权利人发布的信息是对不特定人公开的。但是,微信朋友圈的状态只有好友能够看到,若将其认定为私人空间,那么在朋友圈发布状态的公开性要远远高于前述的微信群,朋友圈的人数上限和好友数是一样的,其数量远高于微信群,可以一次让数千人看到自己发布的状态,这种程度是否还能被视为私密?笔者认为,对于微信朋友圈应当作为公共空间来看待。理由如下:首先,从特定人群与不特定人群的界定来看,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应当对这一概念进行扩张,因为在现实中,判断对象数量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在网络空间下,需要认识到,网络的信息传播速度远远高于现实生活的人人对话,朋友圈的信息一旦转发至其他人朋友圈,此信息的传播速度以几何倍数增长,并且传播的手段极其简单,不需要面对面进行,瞬间完成传播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仅认为朋友圈中的好友数量就是传播范围,应延展性地来看待。其次,从微信好友的数量来看,如果权利人的微信朋友圈数量极多甚至已至上限,而权利人在发布信息时又未配以任何文字去明确禁止传播,那么我们应该推定,权利人放弃了对于这一信息的隐私权,即权利人在发布信息时已经默认圈内好友对于信息是可以转载的,因为,隐私往往是人们最私密的信息,而权利人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公开,我们应该认为,其能够预见到隐私会有遭受到侵害的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性是极高的,权利人依然为之,可以认定为放弃权利或者其本身并不将所发信息视为隐私。
但是,微信朋友圈面临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第一,微信朋友圈是可以进行分组的,即权利人在发布信息时,可以通过设置分组限制观看,一般情况下,这种设置是为了避免某些信息使大范围的人所知晓,只愿意让一部分人了解,但是这一部分人又无法通过微信群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分组设置成为微信的一个特殊功能。然而,被分组到可以观看的好友,并不知道权利人发布的信息是指向特定人的,因为其看到的状态与不设分组时的状态没有任何差别,这就出现发布者与接受者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有学者指出,“在分组管理中发放的个人信息并没有特别标注以明示或者暗示信息的边界规则。被选中的这些好友并不能分辨出哪些信息是分组发送的,哪些信息是公开发布的”[4]。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认定权利人分组发布的信息应当受到隐私保护?笔者认为,根据上述结论来看,分组发布也尚不能视为隐私,原因在于,虽然权利人主观上有限制信息传播的意图,但是,对于接收者而言,是无法识别的,这一点权利人是可以预见到的,也就是说,约束权利人谨慎发布信息的难度要远远小于苛责不明知的接收者去使用隐私的难度。从微信现有的功能看,还不应当认定为隐私。
二、当前微信个人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及方式
从侵权的主体划分来看,微信朋友圈的侵权主体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微信好友与非微信好友。首先微信好友是能够最直接获取信息的人,其侵权方式主要表现为:1.将个人微信信息或微信群中的私密信息进行转发。2.未直接进行转发,通过对隐私信息的描述进行披露。其次,非微信好友的侵权方式大致如下:1.第三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各种APP授权,获取个人信息,COOKIES搜集大量个人信息,进行精准广告投放。2.非微信好友在搜索到他人后,系统默认可以查看对方的十张照片,这一功能是需要用户手动关闭的,但是很多用户在使用了微信很长时间后还不知道拥有这项功能,造成了隐私外流。3.主动侵入的黑客,通过盗取好友的微信号进行隐私窃取。4.腾讯公司的系统内存有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收集数据并不侵犯隐私,但是,背后是否存在出卖数据的行为,还需要腾讯公司严格按照隐私条款进行保护,防止泄露或被窃取。
从侵权的主观心态划分来看,可以分为故意披露、过失泄露和未授权使用。故意披露是通过窃取、试探、侵入等方法获取他人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所知,具备这种主观心态的人大多来自非微信好友。过失泄露是指并不知晓权利人的意图,无意间转发或者泄露了隐私信息,这种情况经常来自于微信好友的行为,误认为权利人发布的信息无关紧要,只是抱着单纯转发的心理作出的行为。未授权使用主要针对有能力搜集到微信隐私信息的网络信息服务者,大多数是一些与微信相关的APP和广告商,明知所搜集的信息有个人隐私属性,在权利人未授权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商业利用。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三方应用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不经同意获取用户信息是否构成侵权。从《腾讯微信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使用规则第六款来看,“腾讯微信提供的服务中可能包括广告,用户同意在使用过程中显示腾讯微信和第三方供应商、合作伙伴提供的广告”。也就是说,目前腾讯的隐私政策并未禁止第三方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搜集信息。目前,微信的注册使用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于微信刚刚进入市场时,用户注册并不需要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只需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即完成注册进行使用,当前,微信的注册必须绑定手机号进行注册。2016年国家开始实施SIM手机卡实名制,这样一来的后果是,微信所储存的信息可以精准锁定到每一个用户的真实身份,从这个方面来看,第三方应用及网络服务提供商搜集到的不仅是用户习惯,而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个人真实信息,这与通过搜集用户喜好提供精准服务的理念已经发生偏离,因为,这种喜好信息只是针对用户群的生活喜好而不涉及更进一步的真实身份。在2011年,facebook曾经允许第三方应用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获取用户的住址和手机号码,但是在次年就开始对这项功能进行限制。微信当前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求微信不进行商业运作,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对第三方获取的信息进行严格限制,是可以实现的。
三、微信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机制
(一)完善微信隐私管理规则
如上所述,个人隐私是否能够被使用,最关键在于权利人是否有授权使用的意思表示。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意思表示通常无法通过语言直接传达。因此,需要一个在微信中好友能够识别,达成信息对称的标志,由权利人控制。有学者指出,“朋友圈的信息传播并没有重视边界传播规则的制定,忽略了商讨的重要性[4]。”这里的边界即指权利人决定对谁公开,公开的范围,如果没有边界标志,则相当于省略了类似商讨一下的环节,也即上文提到的意思表示过程,因此,微信需要增加一个“隐私按钮”的功能,权利人发布信息后,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打开或者关闭,用以表示自己对于所发信息的保密程度以及是否授权转发使用。其次,腾讯应当对于关联APP或者第三方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微信获取信息的途径进行必要限制。目前,微信用户使用关联APP,用微信账号登录前都会出现一个授权信息的提示,而一般这个信息授权都无法取消,否则将不能使用,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公司对于数据的合理运用可以理解,但是,社交软件最大的隐患就在于隐私保护问题上,如果微信爆发隐私危机,那么将给微信带来巨大的用户流失风险,这也许比商业信息使用的缺失带来的危险更大。同时,尊重用户隐私从世界范围内的社交软件隐私规则来看,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facebook,instagram等软件都被用户质疑过隐私信息保护的问题,并作出了改进。因此,对于完善微信隐私管理的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不同国家对于网络隐私的保护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在1974年出台了《隐私权法》,已经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而我国在2009年侵权责任法中才第一次将隐私权视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1986年美国又出台了《电子通讯隐私权法》,1999年美国出台的《在线隐私保护法》规定,“开展在线经营活动的企业一定要对经营主体的身份进行网站公示,并且对经营主体在收集以及利用公民信息上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对外公布”[5]。可见,美国已经较早注意到了对于网络信息搜集监督的重要性。另外,美国的行业自律协会机制十分发达,有专门的网络隐私认证组织,如果网络平台加贴了组织的认证标示,则该组织可以对此网站进行监督。欧盟对于网络信息的保护也十分超前,倾向于采用立法规制,如《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电子通讯隐私保护指令》等,以《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为例,该指令要求,“成员国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对非法处理个人数据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受害人取得司法救济的途径和形式进行规定”[6]。可见,欧盟对成员国都要求严格遵守信息传播的法律规范。
我国目前在网络隐私侵权方面主要依靠《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保护,在很长一段时期,隐私权都依附于名誉权进行保护,而未取得独立的保护地位,我国目前有三十余部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但却没有专门针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2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需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的规则。”可以看出,对于网络隐私信息的保护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并且对于收集信息的方式都作出了严格规定,然而,以微信的使用为例,用户在被收集信息时往往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也就根本谈不上条文中所谓“双方的约定”一说,只有少量的信息使用提示,而且多数是用户不可选择的。因此,目前虽然已经有了相关规定进行约束,但是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用户的个人数据还是大量外流。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男士在旅行出门前就收到了旅游相关的广告推荐,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程,只是通过手机安装的一些旅行的APP,并且在微信上分享了一些旅行攻略,可知,这时其个人隐私就已经被第三方收集并且通过广告精准定位投放,这个精准度已经相当之高,用户根本无隐私保护可言,并且还难以进行法律救济。所以,加强对信息搜集、存储的限制才能从源头上保护用户隐私安全。
四、结语
微信作为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社交软件,如今已经有近十亿用户,其影响力之大可谓空前,微信不仅承载着沟通交流的功能,也承担了支付,转账,交易等职能,随着微信功能的不断扩大,势必会有更多的信息需求,那么对于微信个人隐私保护的力度也应该不断加大,试想,如果人们对微信的安全产生了怀疑,将不会再有人愿意尝试将个人信息放入微信中,那么微信的“危机”恐怕也会随之到来,我们也都希望,这款“中国创造”能够通过重视隐私保护,给微信用户以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样才是微信长久运营之道。微信作为众多网络信息传播媒介的一个代表,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刻不容缓。
[1][美]布兰代斯(Brandeis,L.D.),等.隐私权[M].宦胜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2]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J].法学家,2012(01):108-120.
[3]王利明.隐私权内容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7(03): 57-63.
[4]殷俊,冯夏楠.论微信朋友圈中的传播隐私管理[J].新闻界,2015(23):50-53.
[5]王一任.论网络环境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D].西南大学,2014.
[6]赵利燕.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D].华东政法大学,2013.
(责任编辑:岳凯敏)
Research of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Right on WeChat
LIU Bin1,DING Guan-tian2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era of big data,WeChat has become one tool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people's daily life,which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We-Chat friends and third-party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are likely to become the subject of infringement.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personal privacy on WeChat includes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network privacy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WeChat privac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WeChat;moments;privacy right;protection mechanism
D616
A
1008-2433(2016)06-0124-05
2016-10-16
中国政法大学创新项目“微信朋友圈个人隐私权保护探究”(2015SSCX0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 斌(1956—),男,山西朔州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治文化、法制新闻;丁冠天(1993—),男,河南信阳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