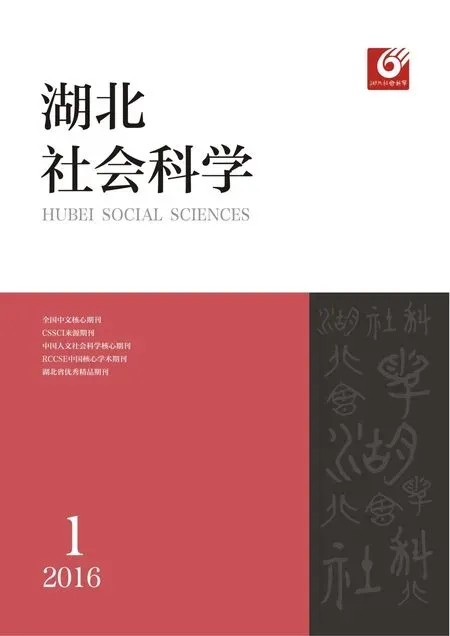《才子牡丹亭》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的价值
2016-03-14高雯
高雯
(福建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流动站,福建 福州 350007)
·人文视野·文学·语言
《才子牡丹亭》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的价值
高雯
(福建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流动站,福建 福州 350007)
《才子牡丹亭》是徽州吴震生、程琼夫妇合作完成的评点《牡丹亭》的与众不同之作。全书以程琼的《绣牡丹》为蓝本,仍可视为女性对《牡丹亭》的批评。该评点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彰显女性对戏曲的评点能力,是《牡丹亭》评点的标新立异之作;不应仅被视为文人的自娱抒怀之作,而是具有社会目的的戏曲批评,反映了闺阁才媛的精神追求;评点的刊行将女性的戏曲评点从小众传播走向大众视野,是女性传播思想的手段之一;对《牡丹亭》在女性中的传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才子牡丹亭》;女性戏曲评点;价值
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问世以来,便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与汤显祖同时的沈德符曾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p643)其后,《牡丹亭》的评点本与改编本层出不穷。其中,大致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际,由徽州吴震生、程琼夫妇合作完成的《才子牡丹亭》是评点《牡丹亭》的与众不同之作。
《才子牡丹亭》虽为夫妇合作评点,且吴震生在其妻程琼去世后,将该书付梓刊行,但全书以程琼的《绣牡丹》为蓝本,“叹世人批书,非啽呓则隔搔,即贯华知耐庵未至,钱塘三妇知开辟数千年始有《牡丹亭》,顾其所批,略于《左绣》。试味玉茗‘通仙铁笛海云孤’一绝,应思寓言既多,暗意不少,须教节节灵通。自批一本,出文长、季重、眉公知解之外,题曰:《绣牡丹》”。[2](卷四p49)鉴于此,仍可将《才子牡丹亭》视为女性对《牡丹亭》的批评。本文拟对《才子牡丹亭》在女性戏曲批评史上的价值作一探讨。
一、《才子牡丹亭》彰显女性对戏曲的评点能力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许多文人官宦之家非常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与程度普遍提高。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宽容,不少通达之士多以女子能文为荣,支持、奖掖女性进行文学创作。一部分女性凭借自身的天赋与才思,结成文学社团,拜师学艺,诗词唱和,女性文学明显呈现出繁兴的趋势。毛先舒《皆绿轩诗序》云:“大江南北,闺秀缤纷,动盈卷轴,可谓盛矣。”[3](p2)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著录清代上自顺治,下迄光绪三百年间1262位女性作家,并加以述评。据严迪昌《清词史》记载,仅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南陵人徐乃昌所辑刊的《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与《闺秀词钞》,就收录清代女性词人617家。[4](p539)正如胡明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所言:“入清,诗学极盛,词学复兴,诗人、词人如过江之鲫,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风动潮涌。中国妇女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5](p100)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清两代女性作家有3750余人,特
别是清代女性作家超过3500余人,“超轶前代,数逾三千”。[6](p1)明清女性作家创作题材丰富多彩,除常见的诗词文赋外,还有散曲、戏曲、弹词等。以戏曲为例,第一位写杂剧的女性当为明代马守真,后有叶小纨、梁孟昭、王筠、吴藻、刘清韵等女性戏曲作家。沈自征为才女叶小纨的杂剧《鸳鸯梦》作序云:“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绸甥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其意欲于无佛处称尊耳。”[7](p387)
然明清女性作家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成绩,较诗词创作则明显逊色很多。明清女性从事戏曲创作始于明万历年间,已知明代女性剧作家有6人,分别为马守真、阮丽珍、叶小纨、梁小玉、梁孟昭、姜玉洁。清代女戏曲家共有19人,其中作剧于康雍乾三朝者有12位,嘉庆至民国前有7位。[8](p31)这与明清女性作家生活时代与空间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妇言不出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典训,女性生活圈子狭小,多被封闭于庭院、闺阁之中,少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社会地位与个人见识受到相当的限制。此外,戏曲是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文学,需要反映广阔的社会与人生,又具有舞台的表演性,需要具备一定的曲学知识,创作难度远甚于诗词,以及戏曲总体上长期处于被“鄙弃不复道”的境地,使得明清时期女性对戏曲的驾驭相对困难,剧作家及作品相对较少。
女性参与戏曲批评则更晚,据已掌握的资料,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女性理论批评者是晚明金陵妓女刘丽华,直至康熙年间,女性对戏曲的批评方始兴盛,总计明清两代约73人,其批评的主要形式为序跋和评点。《西厢记》与《牡丹亭》是被评点最多的两个作品,《牡丹亭》又是被女性评点最多的作品。“如果明清女性读者有一个共同的词汇,那它就是源自《牡丹亭》的。”[9](p77)谭帆《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统计,明清两代《牡丹亭》的女性批评者有俞二娘、冯小青、叶小鸾、黄淑素、浦映渌、陈同、谈则、钱宜、林以宁、顾姒、冯娴、李淑、洪之则、程琼、林陈氏、程黛香共16人,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其中有不少还难以称之为批评者”,但由于女性批评的稀少,所以“这已是戏曲批评史上颇为珍贵的史料了”。张大复《与临川汤先生书》云:“敝乡俞氏女,年十三,偶读先生所演杜丽娘事,适感心疾,把玩四年,手不停批,能以细楷注先生之所不欲言,冀丽娘之所未尝言,大是奇事。惜乎十七竟夭。”《词余丛话》引《小青传》云:“姬小青有《牡丹亭》评、跋,妒妇毁之。”[10](p274)“夫自有临川此《记》,闺人评跋,不知凡几,大都如风花波月,飘泊无存。”[11](p151)闺阁才女对《牡丹亭》的评点不乏知音,惜多数评本不存,确为憾事。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关于《牡丹亭》的最早女性评点为晚明黄淑素的《牡丹亭记评》。此文不长,对《牡丹亭》的主题、结构、关目、人物性格都做了点评。
吴震生、程琼夫妇合作完成的《才子牡丹亭》则为《牡丹亭》的标新立异之作。全书内容庞杂,引经据典,从人性自然需求出发,围绕情色问题,对《牡丹亭》一剧主旨“情”的阐发,另辟蹊径,超越前人,其思想之大胆、风格之尖锐为当时所罕见。
《才子牡丹亭》强调女性追求情色满足的合理性,认为情欲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权利,“人在世间本无甚趣,细思之,即牝牡亦无甚趣。难得人弄出一种情才来,遂有许多享人趣者,不然愈觉有生之苦矣”(《惊梦》批语),[12](p142)“有情者以‘痴’故妙,但有欲者,以不‘痴’故不妙也。……此其人但知男女之乐在触耳”(《诊祟》批语),[12](p265)“在‘日’下行事,庶几得此相状。若以怕天瞧见,坐失此趣,亦复不必。何也?此事原是天教人做的,况蝇交蚁合,天瞧见何尝怒之,天之视众生,宁异蝇蚁耶”(《寻梦》批语),[12](p182)进而提出“不以身殉教,不以名殉情,皆不‘痴’也”(《诊祟》批语)。[12](p265)对各种鼓吹封建礼教的贤文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把人禁杀’是若士借丽娘口,自道其心语,单指理所必无,情所必有而言。与后《回生》折,‘人间天上,道理都难讲’,‘一点色情难坏’等句,为通部之枢纽”(《闺塾》批语)。[12](p76)
《才子牡丹亭》主张情色自主的同时,强调女性与男性一样,同样也有对情欲的需求,“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诸天且因情幻出,何况于人。‘何人见梦’已谓天下有之,‘独坐思量’四字,为害不浅。男女同性,而男人欲情有间者,以事多则其萎,且名利所分也。若女人既无经营进取之事,得暇则自抚玩,又无不可用之时,故入土方休。惟不拨动则已,一拨动则安心受侮,渴不择浆”(《寻梦》批语)。[12](p177)甚至还认为女子应当自我满足情欲的需求,“‘玩花’与每自开看同一意智。赏‘花’女子无不自‘玩’其杜鹃者,恨男子纵欲而亡,却是未知‘玩花’耳”(《冥判》
批语)。[12](p347)“‘女郎’日用‘柳’而不知‘玩柳’,已属可惜,至于‘花’在自身,知‘玩’者尤少”(《硬拷》批语)。[12](p671)
《才子牡丹亭》鼓励男女之间的爱恋,也提倡男与男、女与女同性之间(尤指女性之间)的欣赏爱悦。“推而广之,则女之玩女,亦春情也,不必谓已受触,思惟中既有如许相状,则‘难遣’矣。非孤身所能遣,则须觅人遣之,故蓦地怀之也。所‘怀’之‘人’,不必专指儿夫,凡可以与吾助诸相状,共遣此情,互遣此情者,皆是‘蓦地’者。忽觉一‘人’之可,或在天涯,或在目前,俱不可知,而想像者固属渺茫。”(《惊梦》批语)[12](p145)“花之爱妇、妇之爱花,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独妇尽爱花,而鲜爱如花之同类,为人间世一大恨事”(《惊梦》批语)。[12](p141)
当时的社会,注重门第关系与父权、夫权、君权的婚姻观念仍然广泛存在,而对婚姻生活主体之一的女性的意愿几近忽视,《才子牡丹亭》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今空有所怀,其人未见,则以吾父欲‘拣名门’耳。然彼之所拣,附远厚别,一例仙眷耳。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彼之所谓‘良缘’,即天坏王郎一辈,我之所谓‘甚良缘’也,智不盖世,貌不入格,材不善狎,心不解情,皆非良缘。岂平日所怀乎!使其所拣,即我之所怀,则‘青春’虽‘抛’,尚或未远。惟其所拣,非我所怀,真乃南辕北辙,终无日到”(《惊梦》批语)。[12](p146)
郎才女貌一直被视为理想的婚姻,《才子牡丹亭》独辟蹊径,对男性也提出貌的要求,“一千部传奇做不尽,好处只是男子才美,为妇人苦苦要嫁,甚至众多妇人生生认作伊家眷耳。再深一层,则众多妇人不但爱其夫之才色,而并爱其妻子才色,愿与共夫,不惜屈辱,极尽款昵也”(《圆驾》批语),[12](p695)“盖男子亦必须姝好有色,方为良配,天上人间第一妙事,而触者受者,全在女子十三至十八之五年,过此皆为坏形之花”(《惊梦》批语),[12](p149)“要知女之贪男色,较男看女尤甚。何也?以男子有色者尤少也”(《惊梦》批语)。[12](p159)在对男性提出貌的要求的同时,《才子牡丹亭》亦对女性提出了才的重要性,“无‘才’者虽有‘情’,不能引之使长,浚之使深,是‘才’者‘情’之华,亦‘情’之丹也。有‘色’无‘情’,则‘色’死;有‘色’无才,则‘色’止;是‘情’者‘色’之焰,‘才’者‘色’之神也。然徒有‘情’,亦终不能代‘色’;徒有‘色’者,必非绝世之‘色’,果有绝‘色’,必无无‘才情’者,以绝色是父母‘才情’所结也。有‘才情’而无‘色’者,却有之,以得自宿生,非得自父母也”(《如杭》批语)。[12](p149)
二、《才子牡丹亭》反映闺阁才媛的精神追求
儒家正统伦理的长期教化,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合理社会关系,导致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失落,她们没有资格干预政治,建立事功,个体生命与人生价值受到了漠视,读书不能成为她们获取社会身份的途径,创作也大多成为她们的娱乐和消遣的方式。古代女子的活动圈子十分有限,因此创作的动机与意图大部分为深闺消遣、倾诉情感。王璊在《读史》中云:“足不逾闺闱,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若拘束。少小依膝下,识字无专督。信口诵诗书,义解不求足。但当趋庭时,谈古意相属。世界亦云遥,往事更难仆。十二万年中,是非分两局:某者流清芬,某者贻羞辱。南董笔一枝,千秋有定狱。……风雨恣搜罗,得意必抄录。自笑女子身,乃如书生笃。学问百无能,探讨性所欲;岂能填枵腹,或可启芳躅。遥遥一寸心,前修自勉勖。”便道出了女性自娱消遣的创作态度。[13](p60)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才媛,省察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意识到自身才能不输于男性但不能参与事功的残酷现状,渴望获得与男性一样独立的人格,实现人生价值,因此她们带着这种才女兼怨女的心态进行创作,通过作品来倾泄女性不平的声音,抗争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
《才子牡丹亭》决不仅仅是闺中才媛的自娱抒怀之作,程琼深知《牡丹亭》深受闺中女性的追捧,“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12](pv)她在序中明确指出此书是专门为女性读者而作,“我恨形寿易尽,不能与后来闺秀少作周旋,愿得为洒翰事姑之媚媳,以娱之”。[12](pvi)
程琼在《才子牡丹亭》中频频以纸笔代口舌,为女性同胞发声,彰显女性的才华、德行、情感与欲望。她关注身边闺阁女子的婚姻生活,描摹了理想的闺阁生活。理想的婚姻生活是建立在“才”、“色”、“情”三者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不仅要求男子有才、女子有色,而且提出女子有才、男子有色的要求。两人之间的情投意合是婚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摈弃了占有欲的爱情观,不赞成把配偶作为自己独一无二的私有品,并充分肯定同性之间(尤其指女子之
间)的相互爱慕,认为与一位同样有才情的女子和睦相处,共事一夫,这也是令人向往的。不仅如此,她还将目光转向饱受动乱之苦的女性,借助历史予以披露。如“‘掳的妇人送他帐下’,是妇人所愿否?徐陵与杨愔书,以清河公主之贵,余姚书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驱掠。谢道韫遭孙恩乱,夫被害,方命婢肩舆,抽刀出门,手杀数人。梁元帝时,江陵城内火烧数千家,以为失在妇人,尽于市东。魏破元帝于江陵,兵至仅二十八日,选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读诗至‘白骨马蹄下,谁言皆有家,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寄言丈夫雄,苦乐身自当。’‘诀别徐陵泪如雨,镜鸾分后属何人?主将泪洗鞭头血,扶妾遣升堂上床。幸无白刃驱向前,何忍将身自弃捐。’每为呜咽。安得如周之破齐,兵马不入人村也。”(《牝贼》批语)[12](p276-277)
由于封建礼教的长期压迫,女性长期生活在闺阁中,与外界的接触及交往十分匮乏,《才子牡丹亭》的批点者程琼也不例外。正是由于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及生命体验,程琼在评点《牡丹亭》时,从杜丽娘游园因美好春色唤醒了对爱情的渴望上,激发了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强烈感受到对现实束缚的不满与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因此在评点时能够与杜丽娘感同身受,更好把握住她的内心世界,并且联系自身境况来抒写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将自己的感受与剧中人物的遭遇联系起来思考,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更能引起其他女性读者的共鸣。程琼将自己评点的《牡丹亭》取名为《绣牡丹》,意在要像绣鸳鸯一样,将《牡丹亭》的主旨揭示出来,其“色情论”的阐释是为女性读者的情欲表现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再使她们内心受那些伪道学的摧残而焦虑不安。
三、《才子牡丹亭》是女性传播思想的手段之一
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是十分严格的,“言不出闺阃,足不出厅屏,目不观优舞,身不近巫尼”是当时妇女生活的写照。“内言不出阃外”导致了大多数女性在历史中无言、失语,即使留下了文字,也大多散佚失传、湮没无闻。
《牡丹亭》的问世,在闺阁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女性皆留下了评点文字,且不乏赏音者,如叶小鸾《题牡丹亭》诗三首:“凌波不动怯春寒,觑久还如佩欲珊,只恐飞归广寒去,却愁不得细相看。”“若使能回纸上看,何辞终日唤真真,真真有意何人省,毕竟来时花鸟嗔。”“红深翠浅最芳年,闲倚晴空破绮烟,何似美人肠断处,海棠和雨晚风前。”浦映渌《题牡丹亭》诗一首:“情生情死亦寻常,最是无端杜丽娘,亏杀临川点缀好,阿翁古怪婿荒唐。”可惜这些评点文字大多在历史的长河中散佚失传。“夫自有临川此《记》,闺人评跋,不知凡几,大都如风花波月,飘泊无存。”[11](p151)“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又有赋害杀娄东俞二娘者,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11](p151)即使那些被留存下来的女性评点《牡丹亭》的文字,也多为闺阁与亲友之间传播。
娄江女子俞二娘,聪慧能文,酷爱《牡丹亭》,悉心阅读之余,详细批注,“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如《感梦》一出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语,络绎连篇”,[14](p471)“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15](p654-655)戏曲家张大复希望能够得到俞二娘评点《牡丹亭》的文字,但其母亲不愿意轻易示人,于是只能抄录一本,通过谢耳伯邮寄给《牡丹亭》原作者汤显祖,“某尝受册其母,请秘为草堂珍玩。母不许,曰:‘为君家玩,孰与其母宝之,为吾儿手泽耶!’急急令倩录一副本而去。……吾家所录副本,将上汤先生。谢耳伯愿为邮,不果上。”[14](p471-472)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序也印证了这件事,“吴士张元长、许子洽前后来言,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元长得其别本寄谢耳伯,来示伤之。”[15](p654-655)虽然俞二娘的评点文字仅仅只是在几个文人之间的传阅,但毕竟被保存下来,同一时期的冯小青就没有如此幸运,她命运多舛,16岁嫁给冯生为妾,后被幽禁于孤山,几乎与世隔绝。她也曾读过《牡丹亭》,并留下评点文字,惜被付之一炬,“姬有《牡丹亭》评、跋,妒妇毁之。今但传‘挑灯闲看《牡丹亭》’之句耳。”[16](p219)在极度的孤独中,冯小青寄托诗词创作,在留下的诗歌中叹曰:“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流露出希望把女性的声音传播出去的愿望与意识。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的问世与出版填补了《牡丹亭》女性系统评点的空白。“今三嫂之合评,独流布不朽”,[11](p151)事实上,其在刊印之前也曾有被“秘之笥中”的经历。吴人的未婚妻陈同对《牡丹亭》的评点大部分被其母亲焚毁,只有上卷被其乳母得
到,给女儿作夹花样之用,被吴人购得,“同病中,犹好观览书籍,终夜不寝,母忧其恭也,悉索箧书烧之,仅遗枕函一册。媪匿去,为小女儿夹花样本,今尚存也。人许一金相购,媪忻然携至,是同所评点《牡丹亭还魂记》上卷。”[11](p145)吴人得到陈同评点的《牡丹亭》上卷后,“对之便生于邑”,[11](p145)并不公之于众。后来,吴人的妻子谈则“见同所评,爱玩不能释……暇日仿同意补评下卷……则既评竟,抄写成帙”,谈则为礼教所拘,“不欲以闺阁名闻于外间,间以示其姊之女沈归陈者,谬言是人所评”。[11](p145)吴人的第三任妻子钱宜是在嫁入吴家后才看到陈同与谈则的《牡丹亭》评本,“则又没十余年,人继娶古荡钱氏女宜。……启,得同则评本。”[11](p145)
三妇评本刊印之前,传播的圈子并不广泛,仅限于家庭、亲族之间。谈则在作了评点之后,还曾把自己与陈同评点过的《牡丹亭》拿给自己的外甥女陈门沈氏看,“以示其姊之女沈归陈者”。为三妇评本作序跋的林以宁、冯娴、顾姒、洪之则、李淑,这些女性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姻亲或世谊的关系。林以宁在序中说“予家与吴氏世戚,先后睹评本最早”,冯娴在跋中说“予与吴氏三夫人为表妯娌”,[11](p150)李淑称吴人“四哥”,洪之则为清代戏曲家洪昇之女,“吴与予家为通门,吴山四叔,又父之执也”,[11](p151)洪昇与吴人亦为至交,吴人还为其评点过《长生殿》。即便三妇评本在周遭男性亲友中传播,也未标明评点为女性所为,以至于被误为吴人所作,“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谈经,徐丈见之,谓果人评也,作序贻人”。[11](p145)直至钱宜“愿卖金钏为锲板资,意甚切也”,[11](p145)希望自己出资将评本保存下来。三妇评本在康熙三十一年付刻,康熙三十三年冬天刻成,此后还重刊重印,至此,三妇评本才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才子牡丹亭》是在程琼去世后,由其夫吴震生将该书付梓刊行。吴震生在此书序中说:“使偶观经史欠伸思睡者,即俳谐而旨胜地;挟曲一部,腹已果然,用作诗文,总非凡料”,[12](piii)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些商业运作的可能,也是刻书者自然而合理的扩大读者群的愿望的体现。《才子牡丹亭》曾经数度刻印,又曾被假托为袁枚所作,甚至被朝廷列为禁书,“此本在乾隆时曾被禁毁”。这些影响足以证明《才子牡丹亭》出版后在公众领域引起的传播效果。《才子牡丹亭》的出版,在《牡丹亭》问世后的一百多年之后,对《牡丹亭》主旨“情”的阐发,言人所未言,高举“色情难坏”,思想大胆,见解独到,并且自觉自发地以女性读者为预设对象,而又涉及女性情色论述,是女性传播思想的手段之一。
四、《才子牡丹亭》对《牡丹亭》在女性中的传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牡丹亭》问世后,传播迅速而广泛,清乾隆时石韫玉在《吟香堂曲谱序》中说:“汤临川作《牡丹亭》传奇,名擅一时。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持板,又一日而旗亭树赤帜矣。”不仅年轻人“心窃许《牡丹亭》为第一种”[16](p190)(石韫玉《吟香堂牡丹亭曲谱序》),而且年长者亦“为此曲惆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牡丹亭》尤其受到女性读者的喜爱与追捧,风靡闺阁,正如程琼在《才子牡丹亭》中所描绘的“崔浩所云:闺人筐箧中物。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12](pv)她们不仅悉心捧读,“挑灯闲看《牡丹亭》”,“因读而成癖,至于日夕把玩,吟玩不辍”,而且热衷评点解读,蝇头细字,密密批注,且多有独到见解,“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献出了卿卿性命,金凤钿直至气息奄奄弥留之时,仍想着“我死,须以《牡丹亭》曲葬”。“《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拼为他伤心到死”[16](p215)(俞用济题《醒石缘》)。有些闺中女性甚至还从《牡丹亭》中选取若干精华诗句,将其排列成一种双关语,称之为牌谱,以用作闺阁中的一种游戏。
《牡丹亭》不仅在文本传播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在剧目演出上也是长演不衰、广受欢迎,在社会各阶层的观众中广泛传播。不仅帝王后妃、显宦商贾能够大饱眼福,就是平民百姓也可以经常欣赏《牡丹亭》的演出。《牡丹亭》的散出演出始于明万历末期,至明清交替之际而扩大,到乾嘉年间,随着折子戏演出的兴旺而大放异彩。“《牡丹亭》曲谱当筵,风雨烟波句欲仙,要识临川汤若士,一生爱好是天然。”“追忆昌华放苑中,翠盘深夜出东东,才陪玉茗听珠贯(原注:己酉年后同年宴演《牡丹亭》剧),旋伴樱桃滴酒红。”“春暖花楼酒未醒,新腔闻演《牡丹亭》。通侯厂内观灯早,帽上新簪孔雀翎。”[16](p155)有清一代的统治者认为女性观剧听曲是伤风化之举,上至中央法令,下至地方法规,对女性观剧、听曲做出了诸多约束,不仅反对妇女外出看戏,即使家宴演出,妇女垂帘观剧,也会惊呼“妇女垂帘坐看,罗袜弓鞋,隐隐露于屏下,浓妆艳服,嬉嬉立
于帘前,指座客以品评,聆歌声而击节,座中浪子,魂已先销,场上优人,目尝不转;丑之至矣!耻孰甚焉!”而当时的妇女对观看戏曲有着极大的热情,江西遇迎神赛会时,“男女杂沓,观者如堵”,陕西逢丧中演戏时,“恒舞酣歌,男女聚观”,甚至由于“俗妇女好看庙戏,禁之不革”,张观准知河南某府时亲自率属下坐于庙门前围堵拦截。《牡丹亭》一剧在明清时期的女性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演出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女性是《牡丹亭》最忠实的观众。
女性对《牡丹亭》的文本与演出如此热情与痴迷,除了《牡丹亭》自身的魅力外,包括《才子牡丹亭》在内的诸多对《牡丹亭》的品评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戏曲作品的评点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手段,而且体现了评点者对戏曲作品的接受,也是再传播的开始,是促进戏曲作品进一步传播的重要途径。虽然这种作用不可以无限扩大,但其存在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才子牡丹亭》是徽州吴震生、程琼夫妇合作完成的评点《牡丹亭》的与众不同之作。全书以程琼的《绣牡丹》为蓝本,仍可视为女性对《牡丹亭》的批评。该评点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彰显女性戏曲评点能力,是《牡丹亭》评点的标新立异之作;不应仅被视为文人的自娱抒怀之作,而是具有社会目的的戏曲批评,反映了闺阁才媛的精神追求;评点的刊行将女性的戏曲评点从小众传播走向大众视野,是女性传播思想的手段之一;对《牡丹亭》在女性中的传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清]史震林.西青散记[M].北京:中国书店, 1987.
[3]赵雪沛.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5]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J].文学评论,1995,(3).
[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明]叶绍袁编,冀勤辑校.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8]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M].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
[9][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清]杨恩寿.词余丛话[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1][清]汤显祖,[清]陈同,谈则,钱宜合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清]吴震生.才子牡丹亭[M].华玮,江巨荣点校.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
[13]段继红.清代闺阁文学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14][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明]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邓年
I06.
A
1003-8477(2016)01-0125-06
高雯(1986—),女,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