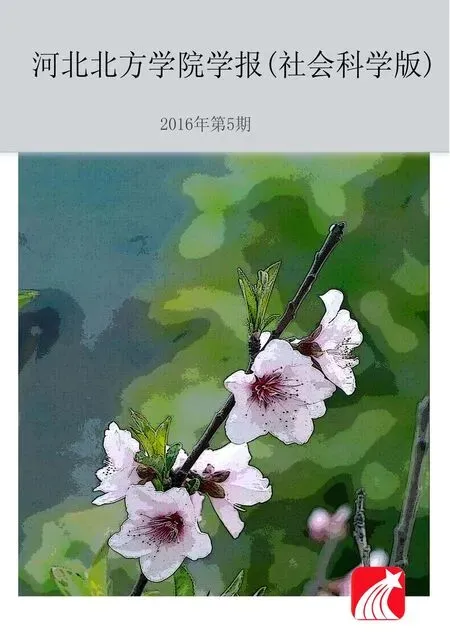《毛诗序》“发情止礼”说探微
2016-03-14耿英杰
耿 英 杰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毛诗序》“发情止礼”说探微
耿 英 杰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毛诗序》是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理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孔子和荀子的思想中已有与“发情止礼”说相类的诗学观念。“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在《毛诗序》文本中得到全面贯彻,其对象、主体、前提、必要性和实现形式等因素在文本中皆有体现。然而,近代以来,学界对“发情止礼”的内涵却存在诸多误读。就此,将其置于《毛诗序》的文本语境中,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毛诗序》;诗学观念;“发情止礼”说
网络出版时间:2016-07-13 09:38
汉代传《诗》有鲁、齐、韩与毛4家,前3家诗先后亡佚,唯毛诗独传。流传于东汉的毛诗中,第一篇《关雎》题解下的大段文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内容、体裁和艺术表现手法等问题,后世一般称之为《毛诗序》《诗大序》或《毛诗大序》。《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可视为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对此后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学观念历来备受学者重视。但近代以来,学者于此争议颇多。笔者从“发情止礼”说相类诗学观念、其在《毛诗序》文本中的贯彻和内涵以及学者对此说的不同评价等3方面对“发情止礼”说进行探究。
一、“发情止礼”说相类诗学观念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已有类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论语·阳货》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46由“《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知,孔子对诗歌“吟咏情性”的特性持肯定态度,但后世对“诗可以怨”的阐释极易让人误解为孔子主张诗歌要倾诉痛苦与发泄愤懑,甚至进一步歪曲成“诗可以怒”。但孔子所说“怨”与现代意义上的“发愤抒怨”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在古代,“怨怒”向来都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孔子真正想通过“诗可以怨”表达的情感,应是朱熹所说的“怨而不怒”,即借诗讽谏怨刺,但要避免怨刺过度。究其根本,“怨”的主要目的在于沟通上下关系,使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可以有效交流,进而能和谐有序地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为了实现有效交流,下对上的“怨”诗情感就应当被限制在统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闻之者足以戒”,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而非激化,这种上下间的有效交流就要通过“礼”来实现。《论语·雍也》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1]79通过“礼”的规范和限制,使人的情感和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从而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158。将这一标准贯彻到作诗和用诗中,就可以达到孔子认为的文艺的最高境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33。儒家主张诗歌在表情达意方面要坚持适度原则,这也是儒家最基本的文学价值观之一,对《毛诗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及至荀子,儒家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且相比于孔子,荀子的诗学理论更偏实用性,因而被纳入政治话语系统。《荀子·儒效》:“先人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2]82荀子理解的“中”即“礼义”;梁启雄《荀子简释》解释“中”为“适当”之意。可见,“礼义”即适当和适度之意,是“人之所道”,即人在行事时应将“中正适度”作为行为准则。在诗学理论方面,荀子同样认为“《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2]89。这里所说的“节”,是诗歌情感的一种节制和约束,即诗歌情感的抒发应有一定的限制:只有做到“节”,诗歌才不至于流荡。荀子在这里提到的“节”和“中”与“礼义”有相似之意,也涉及言行的适度和情感的节制,对《毛诗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发情止礼”说在《毛诗序》中的贯彻及其内涵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汉代的诗学是经学语境中的诗学。儒学变为经学,这意味着先秦儒家从民间话语上升为官方话语。”[3]61儒家典籍在汉代得到空前推崇,但实际是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汉儒为实现政治抱负,也利用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服务。汉儒依据“经世致用”的原则解读儒家典籍,决定了《诗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在解读《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诗学理论时,应承认其为政治服务的前提,进而将它置于相应语境中加以理解。
首先,要明确“发情止礼”的主体和对象。“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体和对象在《毛诗序》中未被明确交代,但可根据文本进行推测。“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4]14-15关于“国史”一词,《毛诗正义》表述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曚歌之。其无做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4]15。“史官自有作诗者矣,不尽是史官为之也。”[4]15可见,“国史”承担采诗的责任,凡收录之诗必经其筛选和加工,故国史可视作诗的最后定稿者,即后文所言“达于世变而怀其旧俗者”[4]15。《毛诗正义》云:“作诗者皆晓达于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于礼义。”[4]15-16国史采诗和作诗的目的即使之“合乎礼义”,故“发情止礼”的主体应为“国史”。由“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4]15一句观之,“发情止礼”的对象为“变风”,而《毛诗正义》有云:“诗人既见时事之事变,改其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虽俱准旧法,而诗体不同,或陈古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故各发情性,而皆止礼义也。此亦兼论变雅,独言变风、变雅双举其文,从省而略之也。”[4]16结合《毛诗正义》这一解释及“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所言,可知经国史采集并加工的对象除“变风”外,也有“变雅”,故“发情止礼”的对象也应为此两者。但应注意,虽然《毛诗序》中“发情止礼”是针对“变风”与“变雅”提出,但其所指并不局限于此两者。“发乎情,止乎礼义”作为儒家诗教体系的一项重要写作准则,其规范的对象应是所有被儒家用作政教功能的文学作品。
其次,“发情止礼”说的前提是对“情”在诗歌中地位及作用的肯定。先秦时期,“诗言志”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如《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18《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6]633《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3]89上述观点代表先秦时期人们对诗的认识——“诗以言志”。但是,这些“言志”说皆只“言志”而未“言情”。《毛诗序》第一次将“情”与“志”结合起来,不但肯定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6,还强调诗歌“吟咏性情”的特点,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4]6。“情”与“志”的不同之处在于“情”不属于理性范畴:“志”是经过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后表现出来的,而“情”是“未经太多伦理道德思考和社会意见就流露出来的”[7]92。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正义》中提到:“在己为情。”[8]2 108可见,“情”是较个人化的情感。所以,它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约束和规范,而这一约束即《毛诗序》中的“止乎礼义”。只有得到一定约束和规范的“情”才能被正统的文学作品接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而由“情”达“志”,真正实现“情志一也”。这样的作品既能起到教化作用,又能打动人心,进而扩大诗歌教化作用的范围和影响。
第三,“发乎情,止乎礼义”作为一种诗歌的情感规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或试图达到的最终效果。由“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10可知,诗通过“发情止礼”所达到的效果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10。诗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但部分诗歌所表达的情感难免与“礼”有不合之处。统治者利用诗对人们进行教化,就必须使得诗所传达的情感及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标准,从而“上以风化下”,最终实现上述目的。《乐记》云:“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廉直、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顺成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4]9可见,文学作品对人们的影响之大。但是,“变风”与“变雅”产生的条件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4]14。因此,为了社会安宁和人心稳定,统治阶级自然要对诗歌的思想和情感加以限制,限制的标准就是“礼义”。通过“礼义”的限制和修正,“变风”与“变雅”中也渗透了先王礼乐教化的影响,寄托儒士的淑世情怀。
第四,“变风”和“变雅”的目的是“刺上”,其原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毛诗序》的作者还提出了这一原则的实现形式——“主文而谲谏”。从字面理解,“主文而谲谏”是让作诗者重视文辞的作用,以达到迂回进谏的目的。“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4]13-14“主文而谲谏”是汉儒提出的一种中和之法,既使臣民对君主的不满得以发泄,又使这种发泄限制在君主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上下间的有效沟通。在《毛诗序》中,“比兴”是“文”的主要手段。劝谏君主需要利用政治话语,而《诗三百》中却多男女欢爱与鸟兽草木之类,将两者联系起来需要一个转换中介。所以,汉儒选择“文”来过渡两者间的关系,从而实现“谲谏”。由此,《毛诗序》的作者将《关雎》阐释为“后妃之德”也就不足为奇了。汉儒的良苦用心实则是对“止乎礼义”的践行,以这种方式表达劝谏之意,从而既能与《诗》的文本相联系,又能将劝谏之意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虽然这种阐释有时显得牵强附会,但其委婉含蓄的讽谏之意却能被统治者发现并接受。“主文而谲谏”是儒家诗教观和温柔敦厚处事原则的表现,它将“发情止礼”的原则诉诸文本,贯彻在整个用诗的过程中。儒家士人借此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对其加以限制,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
理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内涵,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止乎礼义”是指“情”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符合儒家的诗教精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作为儒家诗学理论的经典总结,必然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处事原则,这就要求诗歌情感的抒发和表达不能过于奔放和露骨。孔子对郑声曾评价:“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250他认为郑声乱雅乐,究其原因在于郑声“淫”,即对感情的渲染过于强烈,未如“雅乐”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限制地抒情应符合创作的辩证规律,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述:“夫‘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感情之天然发泄,而歌者感情之艺术表现也。‘发而能止’……则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矣。”[9]57-58有节制地抒情非但不会削弱文学作品的表达效果,反而能“言有尽而意无穷”。其二,“止乎礼义”是指“情”的内容要符合礼义规范,遵循儒家的“适度”原则。“变风”与“变雅”中的怨刺之作就是汉儒实现统治目的的工具。为避免统治者的反感并取得较好的“刺上”效果,“变风”与“变雅”中诗歌的内容应遵循儒家的“适度”原则。汉儒希望通过“止乎礼义”的文学作品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使其及时调整统治政策,进而巩固统治地位。文学作品“止乎礼义”使民间的不满得以一定程度的抒发,且这种抒发可以被统治者接受,上下间的矛盾不会进一步激化,从而实现有效沟通。由此观之,“止乎礼义”是儒家中正平和与温柔敦厚的处世原则在文学作品中的践行,但同时“发情止礼”说也含有利于封建君主统治的政治因素。
三、对“发情止礼”说之评价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对“发乎情,止乎礼义”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10]75。袁济喜认为,《毛诗序》在肯定“变风”与“变雅”讽谏作用的同时,“又强调这种讽谏必须掌握好尺度,不能过分”[11]69,其中提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窒息了《国风》与《小雅》之怨诗的愤慨之情,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模式”[11]69。李建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情必须受到‘礼义’的规范和约束”[12]107,这种作法使得诗歌“沦为了经学的附庸和政治教化的工具”[12]107,“具有极大的封建保守性”[13]86。上述学者对“发情止礼”说基本持批判态度,究其原因,是他们深受“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影响,对民族文化中历史与哲学等方面的了解不足。“儒家的观点是情中有礼义,礼义中有情”[14]182,但许多学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凡是强调情或者肯定礼义的都被认为是所谓封建的东西加以批判”[14]182。刘文勇认为,“情”有向上和向下两个运动方向:向上的“情”升华为“礼义”或“理”,向下的“情”堕落为人的本能,儒家所反对的情感即是这种向下堕落的情感。如果发乎情,不止乎礼义,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只以感性作为最高准则,一个民族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明。正如汪春泓所说,“礼义可以使人摆脱禽兽,并且不断升华”[15]87,“《诗》之为体,其真美往往在于其含蓄婉约”[15]。
可见,“止乎礼义”对人来讲是一项重要的行为规范,对文学作品而言则是一种重要的审美理论。不可否认的是,在《毛诗序》创作的时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确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教色彩,发挥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客观上对此后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不能以偏概全将其彻底否定。儒家一贯主张中庸平和,“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是此种处世态度在文学上的反映。“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指导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朝温柔敦厚和含蓄婉约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学不同于其他国家文学的独特风格。
“发乎情,止乎礼义”作为《毛诗序》中一项重要的诗学观念,总结了孔子所认为文艺的最高境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对荀子“《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的内涵作出了明确概括。这一观念在《毛诗序》全文中得到了全面贯彻,并在贯彻中体现了其具体内涵:一方面,“情”的强度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情”的内容要符合礼义规范,遵循儒家的“适度”原则。“发情止礼”说不仅对后世诗学理论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认为,只有将《毛诗序》置于其创作的社会背景并回归到其文本语境中,才能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1] 孙钦善.论语本解[M].北京:三联书店,2013.
[2]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王世舜.尚书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 王世舜.庄子译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7] 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 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3] 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 刘文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M].成都:巴蜀书社,2011.
[15] 汪春泓.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87.
(责任编辑 张盛男)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of“the Affection Restrained by the Ritual”inThePrefacetoMao’sBookofSongs
GENG Ying-jie
(School of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ThePrefacetoMao’sBookofSongsis the classic summary of Confucian poetic ideas.The idea of“the affection restrained by the ritual”in it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ater generations.The similar ideas are found in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Xuncius.The idea of“the affection restrained by the ritual”is manifested in the text ofThePrefacetoMao’sBookofSongs,including such elements as the object,the subject,the premises,the necessity and forms of realization.In view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the affection restrained by the ritual”in academic circles,the paper tries to make an impartial comments on this idea in the context ofThePrefacetoMao’sBookofSongs.
ThePrefacetoMao’sBookofSongs;poetic idea;the idea of“the affection restrained by the ritual”
2016-02-17
耿英杰(1993-),女,河北保定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I 222.2
A
2095-462X(2016)05-0005-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713.0938.0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