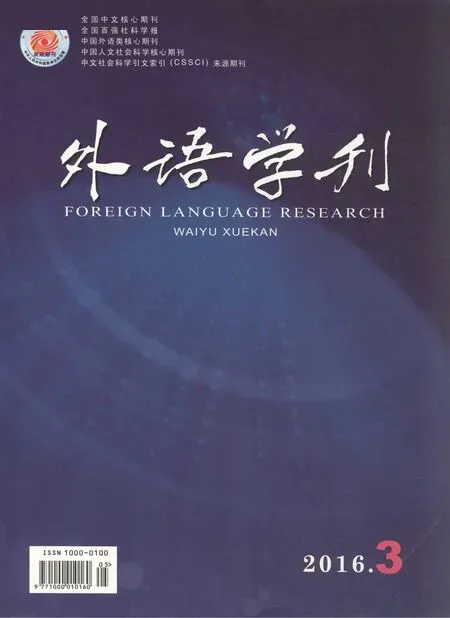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与规划”概念的演变及意义*
2016-03-13李英姿
李英姿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语言政策与规划
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与规划”概念的演变及意义*
李英姿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语言规划与政策在西方渐趋成熟,而在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概念的出现和使用还非常短。本文探讨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出现时间、意义演变等,认为今后对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与细化。
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学科发展
1 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还不长,西方率先建立语言政策与规划这个学术研究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较深厚的积累;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中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则出现得较晚,在中国语境中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概念、内涵以及随时间发展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以及与西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异同点,从而认清目前的不足以指导今后研究的深入发展。
2 西方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根据Spolsky(2004:11)考证,第一本包含“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字样的著作出现在1945年。西方最早提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的学者是Uriel Weinreich,Haugen把“语言规划”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使用,认为语言规划是在一个非单语社会中为作家和演讲者提供指导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等进行规范的活动(Haugen 1959:8)。此后,他也承认所列举的内容实际上是语言规划者执行语言政策之后形成的产物或结果。Cooper(1989)列举字面上与“语言规划”相近的词语,包括“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语言政治(glotto politics)、语言规范(language regulation)、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等,还有其他用来描述影响或者改变语言行为、语言态度的术语,比如“语言治理、语言恢复(language normalisation)、语言复兴(language revita-lisation)、语言复活(language revival)、语言改造(language reclamation)和语言唤醒(rewakening)”。Cooper引用一系列重要期刊的名称证明“语言规划”的受欢迎程度,比如《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LanguageProblemsandLanguagePlanning)、《语言规划通讯》(LanguagePlanningNewsletter)和《语言政策》(LanguagePolicy)。“语言规划”在以上术语中最受欢迎,因为它可以概括所有类似的研究。Cooper认为,语言政策这个术语“多数时候指语言规划的目标”,而不是方式,不过他并没有对此展开更多说明(Cooper 1989:29)。
在英语语境中,language policy和language planning使用比较普遍。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必要严格区分两者,基本可以混为一谈。也有人认为二者应该严格区分:“语言规划更重控制,个体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管理机构不仅决定人民应该知道什么也决定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而语言政策则试图减少干涉,并且最大程度尊重语言使用。伴随着降低干预这一理念的出现,语言规划的角色慢慢消退,语言政策变得名副其实。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应该注意规划和政策的界限是明确的”(Shohamy 2006:49)。
通过提取1959至2005年间相关文献中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三十余种富有代表性的定义,刘海涛(2006)认为,语言规划正在经历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这主要是针对西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学科发展情况做出的判断。
3 中国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时期
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早已存在,从秦代“书同文”开始到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再到建国后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等。即使在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这个学科正式出现之前,也不能说在中国没有相关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关于汉语规范问题的讨论,同样引起重视的还有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其实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工作的3大任务,即汉字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具体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文字改革机构,直属国务院,从机构隶属的级别之高以及名称上可以看出当时文字改革的重要地位。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规范、推广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他同时期类似的学术术语包括:语文现代化、语文建设、文字拼音化等,所有这些内容都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范畴。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针对新中国亟需解决的语言文字问题,并确实起到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从整个学科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后期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正式出现及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重要的过渡及衔接阶段。
4 中国语境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
4.1 语言政策
“政策”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早已存在,不过“政”和“策”分开使用。“政”是指控制社会、管理国家事务、治理民众。“策”有两个词义,“策书”相当于今天的政令、文件或规定。因此在古代汉语中,“政”和“策”就是治理国家、规范民众的谋略或规定。
英语本来并没有policy一词,只有politic(政治)。后者源于古希腊语的poiteke,意为关于城邦的小学问,后来随着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从politic逐渐演变出policy,具有政治、策略、谋略、权谋等意义。日本学者在翻译po-licy时,从早已传入日本的汉字中挑选“政”和“策”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成为“政策”。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随着大量日语词汇进入中国,“政策”又被借回中国。近代中国首次使用“政策”一词始见于梁启超1899年《戊戌政变记》一文,“中国之大患于教育不兴,人才不足,皇上政策若注重于学校教育,可谓得其本矣”。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6年版)解释“政策”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比如“民族政策”。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发现,“语言政策”一词在文献中最早出现在1960年(祝敏彻1960),这个时期的“语言政策”实际上和西方没有任何交集,是中国本土意义上的语言政策。建国后到1988年之间出现的几篇涉及语言政策的文章基本上都把语言政策与民族问题相联系,比如王均(1983)、陈鹏(1987)和周耀文(1987)等人的研究,这一时期语言政策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凸显,因此语言政策也自然地与少数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语境中对语言政策最早的理解和认识。也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制定的民族语言政策较多,相关研究也开始的早,成果丰硕。1988年研究澳大利亚、法国、加纳等国家语言政策的文章相继出现,这是中国语境中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政策”开始和西方的language policy相对应的起点。其后几年出现的关于语言政策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评介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涉及到前苏联、比利时和挪威等。1998年学界开始出现深入研究我国语言政策的学理性文章,以道布的《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代表,并且该文章首次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两个学术术语并用。
4.2 语言规划
在古代汉语中“规”和“划”分开使用,“规”意为谋划、规划。“划”意为谋划、筹划。“规划”两字并用在古代汉语中出现比较晚,在元杂剧中可见。虽然“语言规划”现在为学界所熟知,但在中国语境中此前并没有“语言规划”这个名词。1979年,张丹忱、唐长荫翻译加拿大学者莫舍·纳希尔的文章,最早和language planning相对应的汉语词汇是该译文中的“语言计划”。“计划”在汉语中指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强调事前打算,而不强调结果如何。在凡事讲计划的年代,将planning对应为“计划”也是情理之中的做法。苏金智(1992)也提到语言的声望计划。
1984年,林书武翻译Haugen的《语言学与语言规划》并发表于《国外语言学》,这是国内学界首次将planning译为“规划”。早期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比如孙宏开(1989)。1991年柯平在《语文建设》上连续4期发文系统引介语言规划的相关理论,胡壮麟赴美考察后,1993年发表《语言规划》一文,对多位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规划”定义进行评价。
从词义来看,汉语中“规划”与“计划”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概括性和鼓动性。(1)“规划”的基本意义由“规”(法则、章程、标准、谋划,即战略层面)和“划”(合算、刻画,即战术层面)两部分组成,“规”是起,“划”是落;从时间尺度来看侧重于长远,从内容角度来看侧重(规)战略层面,重指导性或原则性;一般用作名词,对应英语一般为program或planning,如国家的“十二五规划”。(2)“计划”的基本意义为合算、刻画,一般指办事前所拟定的具体内容、步骤和方法;从时间尺度来看侧重于短期,从内容角度来看侧重(划)战术层面,重执行性和操作性;一般用作名词,有时用作动词,英语一般为plan,如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3)“计划”是“规划”的延伸与展开,“规划”与“计划”是一个子集的关系,既“规划”里面包含着若干个“计划”,它们的关系既不是交集的关系,也不是并集的关系,更不是补集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内学术领域,“语言计划”的称谓几近绝迹。可以看出,在“计划”与“规划”并用的时期,“规划”显然比“计划”更受欢迎,并且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有较高使用频率。一个术语从西方引进之初,出现多个对应的翻译也是正常的。从建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表意工具,从“计划”到“规划”,符号能指虽有变化,但其指称对象都与planning高度重合。而与“计划”相比,“规划”显然从内容、时间长度等方面更符合language planning含义,经由自然选择和竞争,“语言规划”的说法得以保留。这种选择主要是“规划”与“计划”在词义上的细微区别以及学者对该领域认识逐渐深化形成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来看,“规划”与planning含义基本对应,而“政策”和policy并不完全对应。Policy比“政策”包括的范围更广,可以指官方政策,也可以指策略、措施和办法等。而汉语语境中的“政策”更偏重官方、宏观。区分“政策”与policy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在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也正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中大多数学者对“政策”意义的普遍认同,所以我国目前的语言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领域,多涉及从上至下的官方政策,也可以说是刚性政策,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别研究,尚未深入中观或微观领域。这种研究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语言政策作为一个学科研究在更宏大范围的纵深发展。现在已有学者强调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也应考虑家庭、个人和社区领域的语言问题,研究路向也更应自下而上(李宇明2015),“语言政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和研究领域应被赋予更多的含义。
4.3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
在中国知网(CNKI)分别检索篇名包括“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期刊论文或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可发现2000年之前只有零星文章,经过若干年的沉寂期,从2000年左右开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
2000年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在2000年正式改组成立不无关系。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研究并审定语言文字标准和规范,制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指导地方文字规范化建设;负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与应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拟订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组织实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监督检查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组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以及普通话师资培训工作;承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两司的改组成立表明国家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及实施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相关研究的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由此更加顺畅地展开,相关理论研究也受到国家、社会和学界更进一步的重视。
和西方学界相同,我国学者对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认识也不一而同。冯志伟认为,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冯志伟 1999:91)。陈章太也认为,语言政策等同于语言规划或者计划(陈章太 2005:148)。他认为,语言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宏观方面,如确定并推广国家的官方标准语言和民族共同语、标准语,制定或改革文字以及对共同语、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推行等;(2)微观方面,如对共同语、标准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的正字法和正词法等确定规范标准,推行共同语、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宏观和微观的区分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大致对应。
总体来说,中国语境中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延续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务实传统,着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目前的研究态势呈上升阶段,吸引汉语学界和外语学界的大批学者积极参与。同时,和西方语言政策和规划相关研究一样,中国语境中其他一些相关术语也开始频繁出现,比如语言舆情、语言生活、语言管理、语言治理、语言问题和语言资源等。这些概念各有侧重,包含不同的研究重点及趋向。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会更加清楚、明确。
专门的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以语言政策与规划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有《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和《语言规划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15)。其他类似的刊物还有《中国语言战略》(南京大学,2012)。《语言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将于2016年发刊。从论著出版来看,《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周玉忠 2004)、《中国语言规划论》(李宇明 2005)和《语言规划研究》(陈章太 2005)都是较早有影响力的著述。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于2015年6月28日成立,这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宣告成立,该学科从此具有学术研究阵地。
5 结束语
Hodge指出,“语言和交流一样是控制的工具”(Hodge 1996: 6)。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国家管理社会和解决政治矛盾的重要机制,语言政策在引导公众观点、增强政治能力、集中经济资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从来就不是消极地任其自流,总是要积极地、有意地影响语言的发展。这是人类主宰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主动施加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大。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语言规划逐渐成为各国执政者十分自觉的行为。”(许嘉璐 2000:481)伴随着实践的自觉,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应该成为各个国家自觉的行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在当今社会显得日益重要,各个国家都在探索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政策,同时也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西方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目前在研究方法上已有长足的进步,学者应用更多跨学科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时语言政策涉及的研究对象也比以前更加丰富多彩,仅从微观领域看,有针对驾照考试(Schiffman 2012)、新媒体、家庭语言教育(Spolsky 2012,Fogle 2013)等的研究。可以说,西方的语言政策研究正趋于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当下的特点之一是“多学科共同参与”(李宇明 2011:4),整体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相对更加成熟,而这些都是目前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所缺失的,中国语境中的语言规划与政策在今后发展上应该突破汉语本来的思维,扩大研究范围,借鉴、融合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及研究范式,提升理论自觉性,方法论上要更多元、更宏大,研究对象更细微,从而促成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纵深发展。
陈 鹏. 浅谈外国民族政策中的语言政策[J].民族研究, 1987(3).
陈章太. 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道 布. 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J]. 民族研究, 1998(6).
冯志伟. 应用语言学综论[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李宇明. 中国语言规划论[M].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李宇明.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J]. 世界华文教育, 2015(1).
刘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A].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第四届全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6.
莫舍·纳希尔 张丹忱 唐长荫. 语言计划的五个方面[J]. 语言学动态, 1979(4).
苏金智. 语言的声望计划[J]. 语文建设, 1992(7).
孙宏开. 我国开展语言规划工作的基本情况[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9(2).
王 均. 民族语言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J]. 民族语文, 1983(3).
许嘉璐.未成集——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仲哲明. 关于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 1994(1).
周四川. 语言计划[J].语文建设, 1987(6).
周耀文. 开展民族语言广播是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J].贵州民族研究, 1987(2).
周有光. 二战后的语言计划[J].语文建设, 1989(4).
周玉忠 王 辉.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祝敏彻 田 明. 党的语言政策[J].西北师大学报, 1960(1).
Cooper, R.L.LanguagePlanningandSocial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e Bres, J. Free Your Stuff Luxembourg! Language Policies, Practices and Ideologies in a Multilingual Facebook Group[J].LanguagePolicy, 2015(4).
Fettes, M.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A]. In: Wodak, R., Corson, D.D.(Eds.),LanguagePolicyandPoliticalIssuesinEducation[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7.
Haugen, E.LanguageConflictandLanguagePlanning:TheCaseofModernNorwegia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odge, R., Kress, G.LanguageasIdeology[M]. London:Routledge, 1996.
Schiffman, H.F., Weiner, R.F. The Language Policy of State Drivers’ License Testing: Expediency, Symbolism, or Creeping Incrementalism[J].LanguagePolicy, 2012(11).
Spolsky, B.LanguagePolic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polsky, B. Language Policy: The Critical Domain[J].JournalofMultilingualandMulticulturalDevelopment, 2012(1).
Shohamy, E.LanguagePolicy:HiddenAgendasandNewApproache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Wright, F.L. Parental Ethnotheor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Transnational Adoptive Families[J].LanguagePolicy, 2013(12).
TheEvolutionandSignificanceoftheConceptof“LanguagePolicyandPlanning”intheContextofChina
Li Ying-z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lthough the practice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human history has long existed, but the time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in China is not long. After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West has gradually become mature.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tim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reason. We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research on should be deepened and refined.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discipline development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汉语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跨文化适应研究”(NKZXB1435)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韩国‘去汉字化’政策研究”(AS15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蒙业师李宇明教授悉心指点,谨致谢忱。
H002
A
1000-0100(2016)03-0015-5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04
定稿日期:2016-03-10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