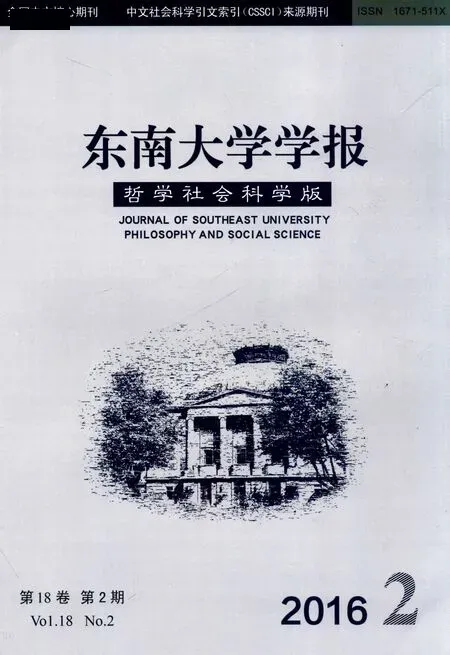论汉族人坐姿变化的美学意义
2016-03-12傅小凡陈冬梅
傅小凡,陈冬梅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论汉族人坐姿变化的美学意义
傅小凡,陈冬梅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汉族人的坐姿,从席地而坐,到屈膝而跪,再到垂足而坐,表面上看是生活习俗的变化,也有异域文化的影响,但其中却蕴含着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寓意着人类的生活体态从自然→规矩→自由的发展轨迹,因此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汉族;坐姿;跪坐;箕坐;美学意义
人席地而坐是最自然的坐姿,甚至某些动物都会。屈膝而跪,则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这种坐姿本身就是规矩,它意味着宗教意识、等级制度和人类压迫的存在。北方游牧民族以床为坐具,既是生活习性使然,也反映了他们等级观念的淡薄,因此,胡床的传入与北方民族彪悍的性情一道冲击着中原汉族的等级制度。而代表印度文化的结跏趺坐,则使坐姿从人际交往的方式变成自我冥想的体态,更有益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一旦冲破了跪姿规矩的束缚,其坐姿或自由潇洒,或慵倦悠闲,或弱柳扶风,或放浪形骸,真可谓千姿百态。然而,坐具和坐姿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的意义在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
一、跪姿含义的转化
双膝着地的跪,无论是坐还是立,都是人类特有的体态,它的含义颇为复杂。从人类文明历程的角度分析,跪姿不同含义出现的顺序应该是:面对大自然、神灵等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时,全体社会成员一起跪倒,表达着人们的宗教意识和观念;面对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敌人时,战败者放下武器投降,并跪倒乞求对手不杀自己,此时的跪具有屈从的意味;而对位高权重之人,弱势者跪倒表示臣服或者顺从,或者强势者逼迫弱者双膝着地,进行体罚、施暴和侮辱。然而,人一旦习惯于双膝着地的体态,屈辱便转为臣服,奴隶就成了奴才。当然,主动跪倒还可以表达感恩、谢罪、乞求和忏悔等复杂的情感。跪姿中哪一种含义最古老已经无法追溯,但是,跪姿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则一定是较晚出现的。因为,身份不同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不同,这是阶级出现之后的事。当全体人民都跪倒时,那一定是面对着神灵;当一部分人先站起来并且接受同类的跪拜时,那就是压迫和阶级产生了。所以,跪姿最初一定象征着奴隶或者被压迫者的身份。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古人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使用跪这一坐姿。但是,从考古材料中发现,古人有一种特殊的葬式——屈肢葬,即下肢骨相并,胫骨向后弯曲,并与股骨重合在一起,脚跟紧贴臀部,类似于跪坐的姿态。人死后僵硬挺直,直肢葬是最自然的,而屈肢葬则必须在人死后立即对尸体进行捆绑才可获得如此的效果。死者身体被强制成这样的形态,具有象征性或者符号意义,表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宗教观念或者礼仪规范。这种葬式的使用,与现实生活中的跪姿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种体态,才可能在墓葬中出现这种葬式。而且,葬式体态所表达的观念与现实生活中肢体表达的观念应该是一致的。
屈肢葬是表达宗教观念,还是表现礼仪规范,这可以根据一个葬区内这种葬式的普遍程度做出推测的。如果某一葬区的全体死者无一例外地被屈肢葬,那么就可以肯定,这种葬式与宗教观念有关,因为在神灵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比如,甘肃毛家坪秦墓中就没有见到直肢葬[1],当然,也有可能他们都是奴隶。如果,在一个葬区内,仅一部分人尤其是极少数人使用直肢葬而大多数人使用屈肢葬,那么就可以肯定,这种葬式与社会制度有关。比如,在秦景公一号大墓中,埋葬殉人166个,均为屈肢葬式[2,3]。在凤翔八旗屯秦墓挖出的20名殉葬者的尸骨均为屈肢葬式[4]。陕西凤翔一号秦公大墓中发现的6具屈肢殉葬的尸骨,位置分布在墓主人之四周,性别有男有女,均系成年[5]。这些殉葬者生前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墓主人的奴隶。
当然,屈肢葬者不一定就是奴隶。比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主人及墓室内的为直肢葬,秦公墓地附近同时期中小型墓的主人却使用屈肢葬[6]67,这表明,地位低的贵族与地位更高的贵族葬在一个区域时,也得使用屈肢葬式。葬式的不同,表现着地位的不平等,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如果,仅殉葬奴隶屈肢,那么跪姿便成为奴隶身份的象征;一旦身份较低的贵族也葬以屈肢式,那么跪姿就从屈辱的身份象征,过渡为臣服观念的表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秦文化的观念中,跪姿具有顺从、屈辱和臣服等多重含义。
这里有个难解的谜。在已发掘的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屈肢葬都出自秦文化区域的墓葬,与中原周朝其他诸侯国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秦人使用屈肢葬是受到西北地区古代羌戎文化的影响[7]182。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北地区古代羌戎文化的墓葬中,很少见到屈肢葬,所以很难确认秦墓所使用的屈肢葬式,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8]122。既然西戎诸族没有屈肢葬俗,中原周人又完全都是直肢葬,那么这些秦人的屈肢葬俗是从哪儿继承来的呢?
也许追溯一下嬴秦族人的历史渊源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早在夏桀之时,嬴秦先祖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嬴秦族另一支的首领中衍,为商王太戊之御,且受太戊“妻之”之宠。因此,“自太戊以下,中衍以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本纪》《史记》卷五)。当嬴秦近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的时候,其子蜚廉和孙子恶来,正在商中央王朝为纣王服务。恶来得纣王宠幸,喜欢在纣王面前进谗言,疏离诸侯。为此,武王灭纣后,亲手射杀恶来。蜚廉,为纣王出使北方,虽免遭商纣败亡之灾,却因纣王已死而无法复命,只好设坛霍太山向殷纣的在天之灵汇报,可见蜚廉对殷纣的忠心。蜚廉、恶来父子二人,不仅是商王朝的重臣,而且为商王朝而献身,殷商与嬴秦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由此,笔者大胆推测,秦人的屈肢葬式很有可能是殷商文化的遗存。
如果,秦人的屈肢葬式是对殷商文化的保留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得出殷商时期跪姿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和规范已经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从秦墓葬中殉葬者均屈肢这一点可以推测,在殷商时期,奴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跪姿是有屈辱、臣服和顺从等多重意味的。所以,殷商时期的跪姿还不大可能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它是人们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必须采用的一种体态。虽然,表示臣服是跪姿最普遍的意义,无论是对神灵还是对君主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要过渡为贵族身份的象征,还需要其他社会要件。
根据《周礼》,在周朝时期,跪姿无论是立还是坐,都是贵族重要的礼节。它不仅没有屈辱的意味,甚至臣服与顺从的意味也消失了。因为,跪姿是君臣相聚时共同使用的体态,尊卑区别只在于就坐的方位与朝向。一般情况下,上座为尊,下座为卑;正坐为尊,傍坐或侍坐为卑。当跪姿没有了屈辱、顺从和臣服的意味之后,便成了贵族必须恪守的礼仪规范。那么,跪姿从殷商时期的屈辱意味向周朝时期的贵族礼节形式转化又是如何完成的呢?笔者以为,其中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周朝废除了奴隶制,实行农奴制,使跪姿不再是奴隶身份的象征;其二,周朝禁止人殉,表现出人的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其三,按照周礼的要求,从君主到平民大家都跪,一视同仁,使跪不再有屈辱意味;其四,周礼虽然严格繁复,但是同时规定“礼不下庶人”,那么跪姿作为周朝贵族必须恪守的礼节而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一旦跪姿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是现实生活中贵族之间交往时所普遍采用的体态,其内在的宗教性内容就被外在的礼仪形式所取代,因此,死者入葬也就不会再以屈肢为葬式。秦人墓葬从西周初期均为屈肢葬,到战国时期出现少量直肢葬,到秦汉时期屈肢葬消失,这个历史变化的轨迹,也可以说明秦人在接受中原周文化的同时,跪姿也从屈辱、臣服和顺从意味向贵族身份的象征和礼仪形式的转化。
二、作为规范的跪姿
床或者榻,作为卧具,汉族人古已有之。在作为坐具的“胡床”传入中原之前,汉族人基本都是席地起居的。人在平地之席面上的日常生活中,可以采取任何体态,怎么舒服怎么坐。但是,周朝礼仪为什么要选择极不舒服而且在今天看来具有屈辱意味的跪坐为贵族必须恪守的坐姿呢?我们将跪姿与其他种人在地面起居时的姿态比较就可以发现,跪姿本身除了原来的屈辱之意外,还有特殊含义。比如,席地而蹲,这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体态。但是这种体态与人类排泄时的姿势一样,所以无论在东方社会或是西方社会,这种体态在社交场合出现,都会被看作是一种不文明、没礼貌的举止。再如,席地箕坐,这是人最自然最放松的坐姿,但是,这样的坐姿在周朝时期极其不雅。因为,周朝时期的中原人的服装主要是上衣下裳和深衣制,裳内着胫衣,胫衣就是一种腿筒,后发展为一种没有裆的裤。身着这样的服装,箕坐时以正面对人,是很难看的。因此,《礼记》严格规定:“坐毋箕。”据《论语》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原壤,鲁国人,与孔子自幼相识。原壤听说孔子要来访,便伸着两脚,箕坐于席上等候孔子。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不礼貌的体态,既表示对孔子的不敬,也包含对周礼的不屑。
据《庄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因此非常不高兴,斥责道:“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一方面,惠子对庄子妻死不哭反歌感到不满,另一方面,箕子比庄子年长,庄子箕坐以待吊唁之人,是极其无礼的举动。
汉以前,人们多是席地而跪,汉以后,便多跪坐于床榻之上。古人围绕席、床榻,各自衍伸出一套完整的礼仪,从摆放的次序、位置,到席或床榻的材质,以及跪坐的姿势等各方面,要求极其繁复。到了汉代,这种礼节依然保持着。《后汉书·鲁公传》甚至说“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史记·汉高祖本纪》中记载郦食其求见沛公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但不拜且指责其“不宜踞见长者”(司马迁:《高祖本纪》《史记》卷八)。又据《汉书·英布传》记载:“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班固:《英布传》《汉书》卷三十四)跪坐是当时接待客人的基本礼仪,刘邦却垂足坐在床边洗脚,便召英布入见,英布自然“大怒”,觉得受到侮辱,所以吵着要自杀了。
跪,在人的体态中是极不自然的姿势,跪坐也极不舒服。那么,当跪姿中的屈辱、顺从和臣服的意味逐渐消失之后,古人为什么选择这种极不舒服的跪姿,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时规范的体态呢?这就要从跪姿本身寻找答案了。
跪,虽然不舒服、不自然,但它却是人化的。羊羔虽然跪乳,但那是因为母羊之乳悬垂过低,羊羔不跪不足以吮乳,所以那还是动物本能,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而人之跪,正是因为它的不自然,才与社会规范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因为,规范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人性自然和抑制本能。自然状态的席地而坐,姿态各异,一群人如果随意而坐,统一起来非常困难;而跪坐只有一种形式,它的存在便是对坐姿的统一,它本身又有方向性。只要方向一致,多少人都可以整齐一致。因此,跪坐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当跪坐习惯已经成为形式意义上的礼仪规范,人们显然已经不是用它来标识自己的“人”的身份,而是用以标识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特定身份。当跪姿以规范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之于恪守规范的人而言,就会成为特殊身价的象征。乡野村夫在田间地头劳作之后,游牧民族在林间草原打猎之余,是不会遵守跪坐之礼的,因为这种体态显然无法达到休息的目的。因此,跪坐的礼仪便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用以标识自己的高贵身份的标签,并借此与乡野村夫和蛮夷之人相区别。
规范虽然是对人性自然的一种束缚,但是它作为自然的人化,也有一种形式的美。因为,它代表和谐,体现了一种秩序之美。就像大型集体舞之所以美在于它体现了高度的统一与和谐一样;另一方面,在这种和谐与秩序之美中,人们得以将自己的个性寄托在形象高大的、光辉的集体里,以渺小的自我分享群体耀眼的身份而骄傲。就跪坐礼仪而言,高贵的身份感在这种美里便占有很大的成分,这种崇高的身份之美比秩序的和谐之美更吸引人。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周朝局势早已“礼崩乐坏”,但是各诸候的贵族们,依然恪守着“坐毋箕”的礼仪规范。因为,这种规范对于这些贵族而言,不仅仅在于维护周礼,更重要的意义是维护自己特殊权利和高贵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军阀割据,南北对峙;战争频仍,灾难不断。中原贵族和士大夫的生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皇室贵族、士大夫中的多数人,即使被迫南迁,屈居一隅,依然恪守着跪坐的礼仪。比如,汉灵帝时人管宁,“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五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皇甫谧:《管宁》《高士传》卷下)。晋武帝与王浑下棋,孙皓在旁边观看,当时王浑“伸脚局下,而皓讥焉”(房玄龄撰:《王浑传》《列传》第十二《晋书》卷四十二)。南朝梁宗室萧藻性情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姚思廉:《长沙嗣王业》《列传》第二十,《梁书》卷二十三)。这里的床指木榻,木榻上有膝痕,是萧藻长年跪坐的缘故。从“宗室衣冠”的反应来看,梁末贵族依然崇尚跪坐的姿势。然而,他们“莫不楷则”的强烈反应,又透露出这并非平常的、习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楷模,是常人所难以坚持做到的事。当时,宗室之所以将这种行为奉为楷模,原因是跪坐以及围绕跪坐形成的一套礼仪规范,虽然为唐以前的汉人特别是贵族遵守,但在私下里,尤其是独处一室的情况下,依然恪守跪坐礼仪的人已不多见。从东汉政权瓦解以来,跪坐的礼仪便受到各方因素的冲击,到了梁末,虽然被南朝贵族、当权者所倡导,但已经岌岌可危。
三、坐姿改变的原因
从跪坐到垂足高坐的转变,既是坐姿习惯的改变,也意味着作为规范和身分象征的跪姿的消失。这个过程,从东汉灭亡开始,一直到北宋才完全结束。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胡床等坐具的传入以及广泛运用,佛教的传播与盛行,人性的觉醒与审美追求,贵族逐渐被消灭等因素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推动作用。人们的坐姿习惯从席地跪坐向垂脚高坐转化,最终使跪坐这种贵族礼仪规范和身份象征走向衰亡。
学界普遍认为,胡床、坐墩等异域家具的传入,使中国古代家具从低矮向高形发展,并且使坐姿也由席地而跪转变为垂足而坐。笔者认为,异域家具的传入固然对中国的家具的发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不是促使古人改变坐姿的根本原因。一方面,胡床最初传入中原的时间,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搜神记》:“胡床、貊盘,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干宝:《搜神记》卷七)“太始”是汉武帝于公元前96至公元前93年使用的年号,也就是说“胡床”传入的时间,离跪姿受到巨大冲击的所谓“五胡乱华”之始的公元316年大约相距四百多年。另一方面,胡床等高形坐具传入中国之前,汉人并不是只知道有“跪坐”这么一种坐姿,蹲坐踞坐等各种坐姿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比如,贾谊说商鞅治秦,弃礼义,图进取,秦俗日败,“妇抱哺其子与公并踞”,“无礼甚也”(班固:《贾谊传》,《汉书》卷四十八)。即使是贵族也只是在正规场合和特定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才使用。比如,“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就是证明。由此可见,古人采用何种坐姿,坐具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汉人也并不是从胡人那里“学会”垂足坐的。
同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一语也说明,在“胡床”传入中原,中原是有自己的“床”这种高形坐具的。区别在于,中原之床就是榻,它主要是卧具,与现在意义的床一致,因形制较大,不便于携带。而胡床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要求他们的坐具也要便于携带,轻便小巧的胡床便很好地满足了这个要求。所以,胡床的最初引入主要运用军事生活。比如,曹操西征马超,“(曹)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又如,齐末萧衍率军攻建康,其将杨公“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姚思廉:《杨公则传》,《梁书》卷十)。古人早有“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9]之说,亦即在军事活动中,身着甲胄的将士们,无法恪守跪坐之礼,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胡床逐渐从军事生活进入日常生活,尤其在皇室、贵族和达官们在郊游、狩猎、竞技等活动中,胡床的确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坐具,在这些环境中礼节的约束也相对比较宽松。
在中原民族接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的同时,这些游牧民族的贵族们,却向往中原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典章礼仪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纷纷仿效中原。比如,前燕(公元337—370年)灭亡,慕容宝被迁往长安,居然还“危坐整容”(房玄龄撰:《慕容垂》,《载记》第二十三,《晋书》卷一百二十三)发誓言以图再兴。这里的“危坐”即为“跪坐”,可见,鲜卑慕容氏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贵族的礼仪。再如,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之后,孝文帝(公元467—499年)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穿汉服,说汉语,姓汉姓,娶汉家女。同时,又极为尊崇中原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将坐姿也改为跪坐。可见,选择什么样的坐姿,虽然与坐有一定的联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坐姿本身所蕴含的意义。
影响中原汉人坐姿的另一种外在因素,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文化特有的结跏趺坐。“趺”,即足背,“跏”,本作“加”,谓两趺相加也。所谓“结跏趺坐”,即先以右足置于左髀上,次以左足置于右髀上,民间称之为“双盘”。若不能双结,也可以仅右足置于左髀上,或左足置于右髀上为“半跏”,民间称之为“单盘”。北方游牧民族也有一种盘腿坐姿,即两足均压在大腿之下,俗称“散盘”,现在北方农村坐炕的姿势依然如此。
当然,佛教僧人并非以结跏趺坐为唯一的坐姿,这种坐姿仅在僧人坐禅入静、诵经内修时使用。在佛教造像语言中,结跏趺坐是佛的象征,虽然佛不一定都结跏趺坐,但是,结跏趺坐的一定是佛,因为手足柔软是如来佛之“三十二相好”之一。在佛教界,跪不是坐姿而是面对佛教偶像和高僧大德时的叩拜之礼。由于佛教徒的坐法与中原传统的跪坐礼仪相悖,在南朝的反佛斗争中,还是引发了一场维护跪坐,反对蹲踞和踞坐的争论[10]53。这表明,跏趺坐对跪坐的确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其中的关键在于,跪坐是人际交往时的礼节,而跏趺坐是独自冥想的修行。前者的功能在于交流,后者的功能在于禅定。核心问题还是儒家入世与佛教出世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与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显然,人们对坐姿的选择,取决于坐姿本身的意义。
对跪坐姿势冲击力量最大的,是魏晋以降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魏晋时流行的“人物品藻”的风气,正是这种主体意识觉醒的证明。以审美的自觉表达个体对自由的追求,构成对传统礼教束缚的冲击。如竹林七贤的逸事可谓是个中典范:“慕竹林诸人,散首批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刘义庆:《任诞》,《世说新语》卷下之上)。这就是所谓“放浪形骸”,这是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条件下,人们从跪坐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重要表现。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魏晋南北时期,混乱的社会、痛苦的心灵,孕育了试图超脱现世追求自由的种子;不羁的人格、狂放的精神,催生了书法、田园诗,和山水画的萌芽;超凡的品味、纯净的思辨,创作了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美学论著。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到宋代,垂足高坐已经成为习惯,曾经的跪拜礼仪只存在于宗教顶礼、祖先祭祀、婚丧嫁娶等特定的仪式上。由跪坐到垂足高坐这一礼仪习惯的改变,从东汉灭亡开始,一直到北宋才完全结束,这个漫长的过程用去了中古汉人六七百年时间。这六七百年的历程,恰好与中国古代贵族逐渐被消灭的历史相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重合。跪坐作为礼仪规范,本来是贵族身分的象征,随着中国古代贵族阶级逐渐被消灭,跪坐这种贵族交往的礼节也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四、千姿百态的坐相
通过观察人们不同的坐姿习惯或对不同坐姿的推崇,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么几个截然不同的人群,以及他们迥异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的理想追求。通过坐姿,甚至分辨出不同人群的观念和身份。比如,跪坐之人,典型的坐具有席、榻,这类人多是贵族、礼教的维护者;垂足而坐之人,典型的坐具是胡床、绳床,这类人多是北方胡人或受其影响的人;结跏趺坐之人,典型的坐具是墩、须弥座等,这类人多是出家僧侣或者佛教信徒;箕坐之人,无典型坐具,抑或什么坐具都如此,这类人多是反抗礼教而崇尚老庄或玄学的隐士、方外之人和普通百姓。
坐姿本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所以它无所谓意义。当贵族、士大夫们冲破跪坐之礼仪的束缚之后,以“非商汤而薄周孔”的气魄,表现出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就使得这本无意义的坐姿在替代跪坐之姿的过程中,有了美学意义。当我们通过绘画、画像石、画像砖和雕刻,看到更加丰富的坐姿形象时,我们发现,这些造像中的佛和菩萨坐姿各异,并非一味的结跏趺坐。他们有的两腿盘于座上,有的垂双脚而坐,有的则一脚盘于座上一脚自然垂下。表现出佛和菩萨平静的内心与悠闲的体态。这时,坐姿本身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审美意味。
前文说过,跪坐本身会给人带来一种个体融入整体,进而达到整齐划一,在宏大整体中体味到崇高美。那么,个体意识的觉醒必然会努力冲破跪坐的束缚,体味各种不同的极具自由意味的审美体验。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在胡床上的垂足而坐,因其双足着地,所以坐、立、走之间转换自如,生动体现着这些北方民族的粗犷和彪悍。本用于军事生活的胡床,当它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尚武的精神。比起跪坐的典雅来,它有一种粗砺之美。
佛教中的结跏趺坐与中原汉族贵族的跪坐在形式上表现出一样的人为与不自然,但是它却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味。跏趺坐姿给人一种稳定、内敛、圆润、恬静的感觉,它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化解为内心的平静,因此呈现出一种自在的状态,表现出洞悉世间烦恼之后的坦然与淡定。如果说跪坐表现整体性的崇高,垂足坐代表尚武与剽悍,那么结跏趺坐则呈现了阴柔与恬静。这种美具有一种超越的力量,因为它反映的是个体对自身命运的关切,是在超越肉体欲望的过程中,对心灵苦难的化解。体味这种审美愉悦的人,不像跪坐的人那样分享拥有特定身份群体的典雅,也不像尚武的游牧民族那样享受英雄的粗犷,但是他们却沉浸在般若智慧的光辉之中,超凡脱俗,纯净安祥。
然而,这样的审美体验是在严格规范束缚之下的心灵超越,所以它让人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而最具影响力、最具魅力的审美主体,是那些越名教而任自然,衣无礼数、坐无端严,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魏晋名士们,因为他们都是些独立的个体,拥有反思能力和审美自觉,并且极具生命的浪漫和热情。
这些名士“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房玄龄撰:《应詹传》,《列传》第四十,《晋书》卷七十),“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房玄龄撰:《儒林传》,《列传》第六十一,《晋书》卷九十一)。他们不拘礼节,甚至是有意反抗礼教,拒绝跪坐,随意箕坐或蹲踞。在江苏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形象地表现出他们各类箕坐坐姿,有屈膝后抱膝的,有将手放在后面撑地的,也有上身后仰靠其他器物的,都是臀部着床席脚向前的箕坐的体态[11]。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会上,司马昭“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刘义庆:《简傲》,《世说新语》卷下之上)。可以想象,阮籍面对正襟危坐的帝王,随意箕坐,口中吹哨,是何其潇洒放浪,目无君王。这些魏晋的名士们,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唯美主义”[12]223,以玄理辩论和人物品藻为生活内容,推崇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他们在纵情山水时,发现了山水之美;他们愤世嫉俗,反对礼教的束缚,表现着自己高洁的胸襟。这种狂放不羁的人格与他们潇洒自如的坐姿相得益彰,使得千姿百态的坐姿本身具有了自由的意味,从而获得深刻的美学意义。
坐姿的改变,高坐具的采用,还有连带的艺术价值。汉魏晋时代书法发生突变,当与胡床等家具的“踞坐”即垂足坐和桌案的利用均有关联。沙孟海《户带书法执笔初探》说:“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能尽同,主要隋坐具不同而移变,席地时代不可能有如今竖背端坐笔垂直的姿势。”[13]乐器的演奏技巧和方式随着坐姿的变化也有了大的改善,汉画像砖上的演奏者,均为跪坐弹琴(卧箜篌),赏乐者也跪坐床榻上;但在唐、五代的绘画里,弹奏乐器者就已经基本上坐于榻或椅上了。“琵琶的横弹到竖弹琵琶转换,同样是因为了高座才有此变化,坐高座从而丰富了双手的演奏技巧和加大表现力度,使其演奏达到逐渐完美的程度。”[14]69
无论是千姿百态的坐姿对跪坐礼仪的冲击,还是坐姿本身的潇洒、随意、自在,以及挣脱肢体桎梏之后对各类艺术发展的促进,都表现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特征:生命的张扬与精神的自由。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
[2]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J].考古与文物,1988(5、6).
[3]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4]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1986(3).
[5]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7]俞伟超.古代“西戌”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C]//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8]张学正,水涛,韩忡飞.辛店文化研究[M]//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9]司马穰苴.《天子之义》,《司马法》卷上[M]//四库全书版.
[10]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J].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
[11]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1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翁志飞.晋人执笔、用笔及书风阐释[J].书法研究,2003(4).
[14]杨森.敦煌家具研究[D].兰州大学,2006.
[作者简介]傅小凡,男,哲学博士,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学,中国管理哲学。
[收稿日期]2015-12-21
[中图分类号]B8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2-01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