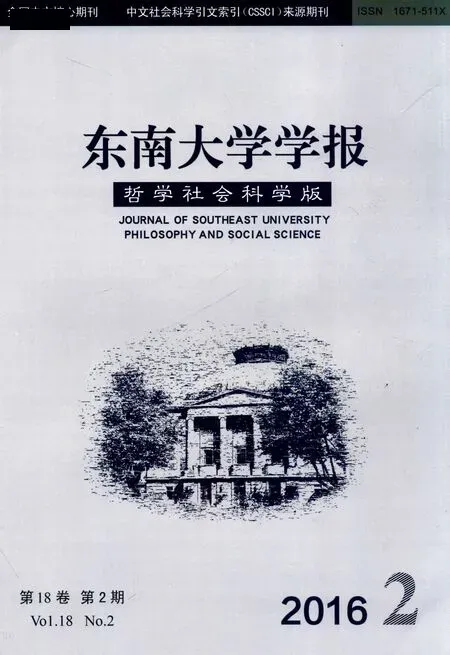生命的缔造、期许与失落: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
2016-03-12赵西巨
赵西巨
(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系,山东济南250355)
生命的缔造、期许与失落: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
赵西巨
(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系,山东济南250355)
[摘要]在人工生殖服务与侵权责任法的联结处,发生着三类案件: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一方面,三类案件形成的关注点有异: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当中,对受害人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获得性是争议和裁判重点;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的审判则与人体组织上之权利定性密切相关;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则是“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另一方面,三类案件共有一个特点,系争点不在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之构成上,而是落在了损害层面上。三类案件中当事人遭受侵害的权利难以具体定性这一点,不应影响到当事人藉由“人身权益”受侵害而获得侵权法救济。我国在人格权立法中,可以考虑重构“生育权”,凸显其“生育自主权”内核,使这种自主权的辐射区域不仅涵盖是否生育“子女”的自主领域,而且延及是否生育“亲生”、“健康”子女的自主领域。
[关键词]人工生殖服务;医疗损害责任;错植精子;胚胎丢失;不当出生
一、引言
在我国法律语境中,人工生殖服务,又称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指的是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①参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年,卫生部)第24条。。从医学技术层面讲,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分为人工授精(人工体内授精)(AI)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人工体外授精)(IVF—ET)及其各种衍生技术。
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我国并不缺乏立法规制。我国已形成了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为基本法,以《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为辅助的规范体系。只不过,此类规范体系瞄准的主要是人工生殖技术的实施范围、条件、程序、管理机构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主旨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和管理”②参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年,卫生部)第1条。,因而多属于行政管理层面的规范,与民法层面的医疗损害责任法尚有一段距离。在医疗损害责任法领域,这些行政管理规范的贡献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探寻到提供人工生殖服务的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落在何处和所应达到的注意标准,从而为医疗过失的判定提供重要依据。
在医疗损害责任法领域,我国《侵权责任法》建立了一个以第6条为统领,以第54条、第55条和第57条为具体贯彻的规则体系。《侵权责任法》第6条可适用于“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在第6条之外,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在医疗领域主体地位的第54条与关注诊疗领域的第57条(医疗过错判定标准或“医疗水平”理论)和关注信息告知领域的第55条(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构筑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医疗损害责任规则体系。一方面,这一规则体系可以一体化地适用于人工生殖服务领域。另一方面,较为特殊的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会显现个性的一面。在寻求人工辅助生殖的过程中,一个人自己配子或胚胎的丢失、精子或胚胎的错植和缺陷儿的产生总会使其本来想通过人工生殖服务拥有“子女”、拥有“自己的”子女或拥有“健康的”子女的希望落空,从而产生纷争。一者,配子或胚胎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具有较强的生命潜能和人格属性。配子或胚胎的丢失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丧失。二者,精子或胚胎,虽然错植,但仍然会带来一个生命。它不像一般物品进行调换那么简单。三者,缺陷生命的到来不免让人生出遗憾。但是,对于缺陷生命的面世,社会和法律应如何回应才能彰显公平、温情和宽容则是一个需要细腻对待的问题。
本文将目光投放在了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与侵权责任法的联结处所发生的一些较为独特的、富含争议、向传统规则发出挑战、处理较为棘手的三类案件: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
二、错植精子或胚胎案
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件并不鲜见。它在美国①参见Mark Gillispie:“2 white Ohio women sue over sperm from black donor”,载http://news.yahoo.com/2-white-ohio-women-sue-oversperm-black-230211351.html(访问日期:2014年10月9日)。、英国②参见“英国人工受孕曝错植精子丑闻”,载http://baby.sina.com.cn/news/2009-06-16/164339317.shtml(访问日期:2013年10月20日)。、中国台湾③参见“人工受孕错植精子父子十年毫无关系”,载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4/00509544889s.shtml(访问日期:2014年2 月10日)。均有报道。但是,形成的有解剖和分析意义的案件并不多。
(一)美国法的观察
美国的Harnicher案④Harnicher v. Univ. of Utah Med. Ctr。,962 P.2d 67,68(Utah Sup. Ct. 1998)。、Perry-Rogers案⑤Perry-Rogers v. Obasaju,723 N.Y.S.2d 28(App. Div. 2001)。和Andrews案⑥Andrews v Keltz 2007 NY Slip Op 27139[15 Misc 3d 940]March 7,2007 Abdus-Salaam,J. Supreme Court,New York County。基本上涵盖了在实施体外授精(IVF)时错植精子或胚胎的几种常见情形:(1)在供精人工授精情景下,医生没有植入原告所选定的供精者的精子,而是错植了其他供精者的精子(Harnicher案);(2)在夫精人工授精情景下,医生没有植入原告的精子,而是错植了他人的精子(Andrews案);(3)医生将原告的胚胎错植到了他人体内(Perry-Rogers案)。三案中原告的诉讼命运不同。
在Harnicher案中,原告夫妇接受的是一种混合使用丈夫精子和捐精者精子的体外授精方法,而且这对夫妇力求选择在身体特征上和血型上与原告丈夫非常接近和匹配的捐精者(#183号捐精者),从而使这对夫妇不能确定到底是谁的精子最终与卵子结合,让这对夫妇认为生下的孩子会是原告丈夫的。但是,孩子出生后,其外型特征明显异于原告丈夫或#183号捐精者。经DNA检查表明,孩子的父亲实际上是#83号捐精者。在本案中,原告夫妇所诉称的是,由于医疗中心错误地使用了捐精者的精子,这挫伤了他们相信和展示原告丈夫是孩子生物父亲的意图,遭受到了严重的焦虑、抑郁、悲伤和其他精神和情感苦痛,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由于这对夫妇没有遭受身体伤害,除了所支出的医疗费用外,也没有遭受其他财产损失,在诉因选择上面临困境。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诉因选择,该夫妇最终以被告的过失行为导致其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为由提起了诉讼。
在Harnicher案中,尽管存在反对意见,初审法院和犹他州最高法院均对原告意欲展示自己是孩子生物意义上的父亲这一动机和精神痛苦赔偿诉求做出了消极回应。这主要是源于,根据犹他州法律,“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因若成立,原告的精神痛苦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才可获得赔偿,即一个合理的人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处置精神痛苦的那种程度。“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因并不保护“精神和情感的安宁本身”,原告的精神痛苦需伴有“身体伤害(physical harm or injury)”。
在此案中,犹他州最高法院多数派意见持有者与少数派意见持有者在事实与法律问题上的认识均有不同。在事实方面,多数派意见持有者认为,原告夫妇有三个正常的、健康的孩子,原告夫妇感到烦扰的只是孩子长得不像原告丈夫或者孩子不是亲生的。三个正常健康孩子的外貌特征并不是一个合理之人无法充分应对的情形,幻想的破灭和被置于一个真实状态之中并不构成过失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而少数派意见持有者则认为,多数派法官轻描淡写了原告夫妇对想要生物意义上子女这一点的关切。持不同意见法官认为,案中所有迹象表明,原告夫妇对孩子看起来是否是自己的这一点很看重。法官不能轻视人类生活中父母身份中的血缘关系这一属性。在这个时代,做生物意义上的父母仍是一大追求。在持不同意见法官看来,多数派法官脑海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有孩子总比没有孩子强,有孩子——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什么孩子——总能抵消与没有获得计划中的孩子有关的任何可能损失,而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在法律方面,多数派意见持有者坚持认为,原告并没有遭受支持“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因所需要的“身体损害”。但是,少数派意见持有者则认为,在解读美国侵权法重述第313条规定时,多数意见法官混淆了其中所建标准的“疾病”因素和“身体损害”因素。二者是“或者”,即可选其一的或可替代的关系,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具有摧毁能力的精神疾病本身(不需要存在“肉体”或“身体”症状)就可以成为启用“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因的“疾病”。在持不同意见法官看来,即使精神疾病需要伴有身体损害,从临床心理医生所描述的原告夫妇的精神症状来看,原告夫妇存在身体损害。
这对原告夫妇在Harnicher案中的失利并非个案。在Creed v. United Hosp.一案①Creed v. United Hosp.,600 N.Y.S.2d 151(N.Y. App. Div. 2d Dep’t 1993)。中,原告的胚胎被植入另一位女士腹中。在Doe v. Irvine Sci. Sales Co.一案②Doe v. Irvine Sci. Sales Co.,7 F. Supp. 2d 737(E.D. Va. 1998)。中,原告的胚胎被放在了可能存在疯牛病感染的保存液中保存。两位IVF原告失利的原因均在于她们没有证明精神损害赔偿得以寄生的“身体伤害”的存在。
关于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赔偿是否必须建立在“身体伤害”之上这一问题,美国各州的法律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在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一案③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1980)27 Cal.3d 916;167 Cal.Rptr. 831;616 P.2d 813。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指出,在“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讼中,不加限制和区分地一概要求“身体伤害”这一要件的存在不再是正当的。即使无受害人“身体伤害”的存在,对于“严重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获得。
不同于Harnicher案的原告夫妇,在纽约州的Perry-Rogers案中,体外授精的受害者则幸运得多。在Perry-Rogers案中,Rogers夫妇自己的胚胎被错误地植入了另一位妇女Fasano的子宫,同时植入的还有Fasano夫妇他们自己的胚胎。这两对夫妇被告知了这一错误。最终Fasano生下了两个男婴。但是这两个男婴种族肤色的明显不同昭示着问题的存在。一个为白色人种,为Fasano夫妇生物意义上的子女,另一个为黑色人种,为Rogers夫妇生物意义上的子女。此事件催生了几个案子,其中包括Rogers夫妇指向产科医生和实验室所提起的医疗侵权诉讼。
在该诉讼中,被告意欲利用法律对“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的禁止来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指出,由于原告寻求的是由创造人类生命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应驳回原告的医疗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法院并没有将该案归类为一个基于残障孩子或计划外的健康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即所谓的“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不当受孕”之诉),因此法院没有必要去计算一个生命存在与一个生命不存在之差异。在法官看来,原告寻求的是由于被剥夺了体验怀孕、体验产前与孩子的关联、生产自己孩子的机会和由于孩子出生后与其分离四个多月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过失导致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纽约州的法律较为宽容:当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而这一义务之违反直接导致精神损害时,即使没有身体伤害,精神损害也可以获得赔偿。但是,原告必须提出足够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的真实性(genuineness),比如“同时发生的或随之发生的身体损害”,这可以表明诉讼请求是可靠的,而不是对仅具有心理后果的心理创伤的赔偿请求。参照以上标准,法院认为,可以想象,当得知被告错误地将自己的胚胎植入一个他们不能找到的其他人时,而这一消息是在此人已怀孕后才被告知的,这会导致原告的精神痛苦,去思考他们通过体外授精努力极力想要的孩子有可能由他人生下来,去想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孩子的未来命运。这些情形,加上原告确实存在客观的精神创伤,可以确保原告的精神损害诉讼请求是真实的。
在另一则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案件——Andrews案——当中,原告Andrews夫妇(女方为多米尼加人,男方为白种人)意欲通过体外授精获得自己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但是,女儿Jessica出生后不久,这对夫妇发现女儿的身体特征有些异样,感觉其具有黑人血统。后来的DNA测试验证了An⁃drews先生并不是Jessica生物意义上父亲这一事实。很显然,授精时使用的精子是他人的精子而不是Andrews先生的精子。
案中,原告方(Andrews夫妇和孩子)提出了许多诉因,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中包括:(1)在知情同意领域,Andrews夫人“缺乏知情同意”的诉因;(2)在诊疗领域,面向建议原告使用IVF并实施了受精卵的植入的医生所提起的医疗侵权之诉和面向从事精子和卵子处理、培育胚胎的人(非医生)所提起的过失之诉。原告方提出的“缺乏知情同意”诉因被法院驳回。法院基本认可被告医生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体外授精中医生可能会错用他人精子并不是体外授精手术一个可合理预见的风险,因此不应落入信息告知范围。错植精子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对于面向胚胎培育者的过失之诉,原告很快获得了法院的即时判决,因为,根据事实自证(res ipsa loquitor)原则,精子植错本身即产生了一个过失推定的效果,而被告方并没有提出有力的推翻过失推定的证据。但是,在面向医生的医疗侵权之诉中,原告的主张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被告方的两种主张:(1)原告寻求的精神损害是未曾遭受任何身体伤害情况下的精神损害;(2)原告的诉讼实质上是不被纽约州所认可的“不当生命”或“不当受孕”之诉。
关于“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纽约州法律的立场是,基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尊重,健康孩子的出生不是一种法律上认可的损害,而且具有严重疾病的孩子的出生也不认为是一种损害,这不仅是因为在此场景下原告方精神损害的不易确定,而且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能抑制孩子残疾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在本案中,原告方若主张就他们不得不抚养一个与他们只具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孩子、一个种族和肤色不同的孩子获得赔偿非常类似于原告就“一个不需要的,但是健康正常的孩子的出生”主张损害赔偿,这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
但是,在法院看来,尽管原告方不能基于其被剥夺了拥有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这一点主张损害赔偿,但是可以就Jessica出生之外的其它方面(如不能确定他们的生殖材料是否用在了他人之上、在Jessica之外也许存在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而他们并不知晓、担心与Jessica具有血缘关系的父亲也许有一天会找上门来主张对Jessica的权利从而干涉他们的父母子女关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非常类似于Perry-Rogers案中原告没有就孩子的出生主张损害赔偿,而是就其他方面(如原告方被剥夺了体验怀孕、体验产前与孩子的关联、生产自己孩子的机会和孩子出生后与其分离四个多月)主张损害赔偿。法院最终认为,由于Andrews先生的遗传材料确实没有用来培育他们的子女,而被告方未能就此事件的发生和Andrews先生精子的去向提供任何解释,Andrews夫妻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应具有“真实性”。即使不存在身体伤害,原告方也可以获得精神损害的赔偿。此案判决与Perry-Rogers案之判决一脉相承。
总之,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中,特别是在“不当出生”、“不当生命”和“不当受孕”之诉遭到禁止的法域,原告“意欲获得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这一主张很容易与获得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之情形)和获得了不需要的/计划外的孩子(“不当受孕”之情形)之类说法发生类推,从而遭到司法者的排斥。这是因为司法者并不想去做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不同生命或不同类型孩子之间价值的比较。但是,即使在“不当出生”、“不当生命”和“不当受孕”之诉遭到禁止的法域,法院也可以从其它方面入手,比如说原告丧失了体验怀孕、生产、掌控孩子命运的机会(Perry-Rogers案)、原告揪心于精子的不知去向和所涉孩子的命运未卜(Andrews案),来正视原告方的精神痛苦和精神损害。
(二)我国法的沉思
在我国,据称是“中国第一例”的生错孩子案例发生在河北。这是一个在精子调换的原因上争论不休、不仅涉及损失赔偿而且关涉对孩子的抚养的案子。据报道①参见雷博:“植错精子生错儿:这笔糊涂账谁来埋单”,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c7fbb0100h0cg.html(访问日期:2013年10月20日);“错配精子‘代’产子,悲喜父母心灵伤痛怎抚平”,载http://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d28493.html(访问日期:2013 年10月20日);“医院人工授精配错人夫妻索赔113万”载http://news.qq.com/a/20061228/001717_2.htm(访问日期:2013年10月20日)。,2005年7月,王晖和陈莉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以下简称省四院)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受孕。2006年3月,陈莉产下一男婴。2006 年6月,在例行的新生儿体检中,发现男婴血型与夫妻双方不符。经亲子鉴定证实,男婴是陈莉亲生,但与王晖无关。2006年12月19日,王晖夫妇向石家庄市桥东区法院递交诉状,以侵权为由将省四院推上了被告席,要求省四院支付医疗费、孩子的抚养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13万余元,支付陈莉和王晖的精神抚慰金100万元。据说,此案经法院调解,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而告终。系争点和相关法律规则的运用丧失了一个得以进一步聚焦和呈现的机会。
我国并不属于一个立法明确禁止“不当出生”、“不当生命”和“不当受孕”之诉的法域,原告“意欲获得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之诉求应有生长的空间。医疗损害责任法,无非是围绕医生是否对患者负有注意义务、医生是否违反此注意义务(即是否存在过失)、患者是否存在损害以及患者的损害与医疗过失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几个问题而展开的。首先,就注意义务来说,精子的采集与提供应当严格遵守卫生部制定的《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精子的植入也应遵守技术规范。其次,就医疗过错(注意义务之违反)和因果关系来说,如果不存在其他介入原因或争议因素,发生错植精子或胚胎事件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说明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违反了注意义务(从而存在过错),从而导致了受害人生育亲生子女的希望破灭,或者说,导致了非亲生子女或违背原告所期许的子女的产生。运用英美法的语言来描述,错植精子是一个可以适用事实自证原则从而产生过失推定的场合。如果没有医生的过失,错植精子就不会发生。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应就人工生殖子女的某些方面(如血缘关系的有无)承担结果保证义务。从合同法角度来看,借助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夫妇与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之间缔结的是一种近似于劳务承揽的契约,医方应确保胚胎的卫生质量,并就基于人工授精所生婴儿出生后的肤色承担结果义务②参见曾品傑:《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从法国法谈起》,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2015年第三届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4月25日- 26日·上海),第104页。。比如,一对白人夫妇通过体外授精,不能因医院在精子或卵子上之处理疏忽而生出黑皮肤婴儿。因此,如果确系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件而原因不在患者身上,该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往往不会落在是否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这两个构成要件上,而是错植精子或胚胎导致原告方亲自生育亲生子女或貌似亲生子女的希望破灭,或者说,导致非亲生子女或非期许子女的出生,侵犯的是原告的何种权利,或者换一个视角讲,原告应得到对何种损害的赔偿。因此争议焦点落在损害层面上。
具体来看,错植精子案和错植胚胎案又有所不同。在错植精子案中,自身精子或所选精子的他处移植使得原告方拥有具有血缘关系或貌似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子女的希望落空;而在错植胚胎案中,基于精子与卵子的整体错植,尽管原告方也许不会丧失拥有具有血缘关系或貌似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子女的机会,但是原告丧失的是怀有、生产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在此过程中与之建立情感关联的机会。在错植精子和胚胎案中,原告遭受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人身损害。案件的性质之界定也至关重要。原告的损害并不体现在生命的诞生和不同生命(亲生子女与非亲生子女)的价值比较上,而是在于原告方在生理意义上和过程意义上生育亲生子女的期望的落空和由此导致的精神苦痛。因此,正如美国法所展现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可及性是该类案件的一大争议焦点。
在我国,对人身权的侵犯会招致精神损害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之前,藉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包括侵害了“人格权利”、“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死者的人格利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1-4条。。其中,“其他人格利益”这一开放性用语的使用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得以扩张的可能②我国法院在侵犯“祭奠权”、“生育选择权”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等案件中曾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参见周琼,陈晓红:《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第102页。。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随后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权益”,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非穷竭性列举,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等。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集人格权与身份权于一身的人身权。关于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中所涉及到的原告的相关权利的界定,选择项可能有三种:(1)身体权。身体权指的是“自然人维护其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人格权,身体权以身体完整的利益为对象。[1]300(2)亲权。亲权指的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专属的、为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权利和义务。[2]14亲权是一种基本身份权。亲权虽名为权利,实际上也是义务,是权利义务的综合体。(3)生育权。生育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依法自主决定自己对后代的生殖和抚育的权利”,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一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生殖后代的权利,禁止他人非法干预或侵害;二是抚育后代的权利,此为监护权的具体表现。[1]357-358
从目前对上述权利的界定来看,上述权利并不完全契合错植精子或胚胎案情。相较于身体权和亲权,生育权似乎离错植精子或胚胎案情所涉及的权利更近一些。但是,现在的生育权概念更多的是聚焦于决定生育和不生育的自由。如果将对当事人在生育上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延伸至是否怀有和生产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以及是否亲自体验怀有和生产子女这些事项上,生育权的概念与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中当事人所涉及的权利就更加贴近了。我国法可以对生育权重新演绎,使其内涵更加丰富,使其不仅包括当事人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而且涵盖当事人选择拥有何种子女的权利,即生育自主不仅包括“生育和不生育”的自主,也包括“生育何种子女”的自主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并不允许在孕中阶段对胎儿的性别选择。为了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我国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参见《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2002年)第三条。人工授精方法也不应成为孕前选择胎儿性别的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国计划生育国策之下,子女的数量选择也受到限制。。已有学者将生育权重构为以下几项子权利的集合:(1)生育请求权(权利主体有请求对方帮助自己生育的权利);(2)生育决定权(权利主体有权决定是否生育);(3)生育选择权,其中包括生育数量选择权(决定子女数量的权利,包括生育的时间、子女的间隔等)、生育质量选择权(通过优生优育,确保健康婴儿的出生)和生育方式选择权(男女双方依法享有选择自然生育方式或人工生殖技术方式生育子女的权利);(4)生育保障权(男女在生育过程中获得国家提供的生育保障的权利)。[3]19-21其中,生育选择权的纳入让人耳目一新。只可惜,这种生育选择权只局限于生育数量、质量和方式的选择上,并没有延及到子女是否为“亲生”的选择上。
由此看来,在我国目前的人格权分类和概念体系中,欲找到与错植精子或胚胎案所涉权利较为契合的、对应的具体人格权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创设出较为贴切的新型具体人格权或者对某种既有的具体人格权进行重塑之前,这种局面不应影响到当事人权利遭受侵害时的救济。不管对其受到侵害的具体权利如何定性,错植精子或胚胎案的受害者的“人格利益”、“人身权益”或某种精神性人格权会遭受到侵害。因此,在此类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应是可获得的。
只不过是,侵权法下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有门槛的。这主要是基于精神损害的不可测性和缺乏外显性,以及对滥诉的担忧和控制。精神损害有时太过微小、太难证明、太容易伪装。司法者们害怕由此打开诉讼之闸,害怕出现虚假诉讼,害怕被告责任出现无节制。如前所述,就美国法来说,对过失侵权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控制和过滤机制不一而足,如要求原告有客观显示的“身体症状(身体伤害)”(physical manifestation)、要求原告处于“危险区域”(zone of danger)。在美国的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案中,即使排除了“过失导致精神痛苦”诉讼中“身体伤害”之要件的必要,法院也要求原告通过就其严重精神损害出具专家或目击者证言或者显示案情值得做出严重精神损害推断的方式来佐证其诉讼请求。即使没有了“身体伤害”这一限制,法官也要考虑损害风险的“可预见性”和诉讼请求的“真实性”作为替代控制机制。[4]1166后来发展起来的“严重”精神痛苦之标准是一种认可了纯精神损害或者非身体损害的存在、既剔除了“身体伤害”的机械限制又包容了“身体伤害”的合理存在的较具弹性的标准。精神痛苦之“严重性”的判定标准是看一个通常的、合理的人是否能够充分地处置此种精神痛苦①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1980)27 Cal.3d 916,927-928。。
就我国而言,要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作为错植精子或胚胎的受害人,不仅需要证明她的“人身权益”受到了侵害,并且需要证明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以及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严重精神损害后果指的不是偶尔的精神痛苦或心理情绪上的不愉悦,而是社会一般人在相同情况下都难以忍受和承受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1]722精神损害“严重性”的判定标准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三、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
在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中,受害人在配子或胚胎之上存在何种类型的权利(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或者说配子或胚胎的财产定性,以及权利遭受侵害是否可招致精神损害赔偿,是问题关键和争议焦点。
(一)域外法的观察
对于在人体组织(比如精子或胚胎)上所存在的权利,分析的视角大多基于一种二分法:或者为人身权(比如身体权),或者为财产权或物权。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储存精子灭失案②Federal Court of Justice(the Bundesgerichtshof),Sixth Civil Senate,9 November 1993,BGHZ,124,52。和美国的Moore案③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0)793 P 2d 479.在该案中,医生未经患者同意移取了患者的身体组织用于商业性研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原告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权。该案从保护患者自主权的角度保护了当事人对人体组织的控制。将人体组织置于“身体权”和“自主决定权”的控制之下,是人身权说阵营的代表。而落入财产权说阵营的有美国的Davis案④Davis v. Davis(Tenn. 1992)842 S.W.2d 588.案中争议双方在如何处置在体外授精中形成的经冷冻保存的胚胎意见不一。田纳西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当事人在胚前期组织上所享有的利益不是真正的财产利益,但他们确实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利益,他们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胚前期组织的处置。、美国的Frisina案⑤Frisina v. Women & Infants Hosp. of R.I.,2002 R.I. Super. LEXIS 73(R.I. Super. Ct. 2002)。、美国的Hecht案⑥Hecht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County(1993)20 Cal Rptr 2d 275.案中,法院认为,死者生前对精子的使用具有充分的决定权,死者在生前对精子享有所有权性质的利益,有权决定精子是否用于生殖,因此,精子可以构成遗嘱继承意义上的“财产”。、英国的Yearworth案⑦Yearworth and others v North Bristol NHS Trust[2009]EWCA Civ 37,[2009]3 WLR 118,[2010]QB 1,(2009)107 BMLR 47,[2009]LS Law Medical 126,[2009]2 All ER 986。、澳大利亚的Edwards案⑧Jocelyn Edwards;Re the estate of the late Mark Edwards[2011]NSWSC 478.在该案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肯定了死者伴侣对死者精子的占有权。和加拿大的J.C.M. v. A.N.A.案⑨J.C.M. v. A.N.A.,2012 BCSC 584.在该案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肯定了精子的“财产”定位,使得两个女同性伴侣在分手时可以将其分割。。这其中,德国储存精子灭失案、美国Frisina案和英国的Yearworth案涉及到了精子或胚胎的丧失或毁损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与本文主题较为契合。总体来看,不管是依附在人身权之下,还是建构于财产权之上,来自不同法域的这三个判例均肯定了精子或胚胎灭失或毁损下原告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获得权。
在早年德国的储存精子灭失案中,考虑到手术可能导致不育,一位男士将自己的精子提供给了一个诊所以备后用,但是该诊所因过失损坏了它们。德国联邦法院并没有遵守身体部分一旦与身体分离即成为物的见解,而是肯定了被告行为构成了对原告“身体权”的侵害之说。原因包括:(1)储存精子的灭失使得原告丧失了与其妻生育、同有子女的唯一机会,其情事堪称严重。(2)若原告精子的灭失构不成对身体的侵害,则无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的慰抚金请求权。(3)鉴于现代医学科技所提供的可能性(如科学的进步使身体的部分得以与身体分离,其后再予接合),基于一般人格权而生之对身体法益的自主权更具意义。(4)若身体部分的分割,依权利主体者的意思系为保持身体功能,或其后再与身体结合时,则为保护权利主体者的自主决定权与身体本身,从法律规范目的言,应认为此项身体部分在其与身体分离期间,乃构成功能上的一体性。对此种分离身体部分的侵害,应认系对身体的侵害。(5)精子的储存旨在生育繁殖,一方面与身体终局分离,另一方面又将用于实践权利主体者生育的身体机能。精子的储存实乃是已丧失生育能力的代替,对于权利主体者身体的完整及其所涉及的人的自主决定与自我实现,就其份量及内容而言,不亚于卵细胞之于妇女受孕生育的功能。[5]108-109德国联邦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方遭受苦痛的主张。不过,此案的判决应放置在德国法,特别是德国民法典中去观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现第253条)之规定,经济损失以外的赔偿请求,只有在存在人身损害或自由被剥夺时,才可以被提起。该案中原告没有金钱损失,他获得赔偿的唯一可能是将其损害定性为“人身”损害。
在美国罗得岛州的Frisina案中,原告是三位接受体外授精的妇女。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胚胎被弄丢了或被损坏了。在本案中,“过失行为导致其精神痛苦”这一诉因并不能成立,这主要是因为:(1)胚胎并不能被视为“受害人”,因为它不是“人”;(2)原告并没有实际看到胚胎的丢失或毁损;(3)原告并没有证明她们的精神苦痛伴有身体症状表现。尽管如此,法院支持了原告所提出的他们丧失了“不可替代的财产(irreplaceable property)”并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主张。考虑到体外授精—胚胎移植的“独特”性质,法院允许可就“不可替代的财产之丧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胚胎的法律地位,该法院认可了胚胎虽然不属于“人”,但可视为“财产”,因此所有者对其存在所有者利益的看法。本案中被告曾辩称,接受体外授精的人,在80%的情况下不会受孕,因此原告实际上并没有遭受损失。但是,在法院看来,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并不是“受孕可能性的损失”,而是“胚胎的损失”。与此同时,被告还辩称,罗得岛州的法律不支持可就财产丧失的精神痛苦获得赔偿。但是,法院并没有接受这一辩称。
在英国的Yearworth案中,原告为六位男性癌症患者。考虑到随后的化疗会损坏他们的生育能力,他们同意将自己的精液标本冷冻储存起来以备后用。但是,遗憾的是,后来精液融化。原告方提起了过失侵权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被告却声称,精子的丧失既不构成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也不构成财产损害(damage to property)。在此案中,上诉法院支持了初审法官关于不存在人身伤害的认定,但是却没有支持初审法官关于财产问题的意见。在财产问题上,上诉法院认为:(1)基于侵权诉讼和寄托(bailment)诉讼之目的,精子属于原告方的财产;(2)从法律上看,原告方可以在寄托法之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在过失侵权诉讼之中,一位男性对其脱离人体的精子享有所有权。就寄托诉因而言,基于当事人在精子上的所有权,当事人可以成为精子的寄托人。在原被告之间存在关于精子的寄托关系。就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通过精子保存来保存原告生育能力的安排具有安抚心灵的目的,是非商业性的,属于一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基于寄托诉因的可及性以及其存在更有利的一面,也鉴于侵权法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复杂性,法院并没有就侵权法下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进行过于细致的追究。
(二)我国法的检讨
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是以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违反注意义务构成过失从而导致配子或胚胎丢失为前提的。医方的配子或胚胎保存义务是一种结果义务①法国法上认为,冷冻胚胎可为民法上寄托契约之标的物。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身为受寄人的医院负有返还与其所受领相同标的物的义务,并承担具有结果义务性质的保存义务,受寄人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下,方可免责。参见曾品傑:《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从法国法谈起》,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2015年第三届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4月25日- 26日·上海),第103-104页。。原告主张的是“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而不是“没能成为父母”所带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告是否会使用该配子或胚胎,以及,如果配子或胚胎不丢失或毁损,原告是否会受孕成功而成为父母系不相关因素②在法国一冷冻胚胎意外毁坏所致损害赔偿案中,在决定是否给予胚胎遭到毁坏的夫妇精神损害赔偿时,法院认为,这对夫妇无法证明他们对剩余的胚胎仍有生育计划,无法证明胚胎毁坏造成其丧失成为父母的机会,无从证明其受有何种损害。损害的判断取决于胚胎提供人的外部使用意思(是否作为生育使用)。该案对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消极对待引起学者批评。参见叶名怡:《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41-43页;曾品傑:《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从法国法谈起》,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2015年第三届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4月25日- 26日·上海),第101、104页。。因此,该类案件诉讼的焦点不在于被告方是否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而是原告在配子或胚胎上所存在的权利之定性以及,相应地,原告所受“损害”之界定。
关于精子或胚胎是否为财产,在立法层面,我国《物权法》中未见有关于人体及人体组织是否为物的规定。学理层面,财产权说在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市场。已经与人体分离的人体器官或组织不能作为人格权(比如身体权)的客体,可以将其作为物权的客体。[1]316-317即使有学者择取了人格权的视角,论证的也是人体及其器官组织的“物”性。[6]57-62我国立法在人身权说和财产权说上如何站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将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界定为“物”或“财产”存在较大生存空间。
但是,对人体组织的财产性质的定性应照顾到一旦这些人体组织被毁损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获得问题。如前所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之前,藉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曾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可以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4条。。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打开了承认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一扇窗口。为了适用这一规定,受到侵害的特定纪念物品中,须具有人格利益因素,且须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我国学界也多认为,因灭失或者毁损而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物范围应扩展至“具有或包含精神利益的财物”、“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7]111,[8]24,[9]4-15也就是说,藉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精子丢失或毁损案中,即使精子被定性为财产,当事人也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但是,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似乎改变了这一景象。该法第22条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并无“财产权”遭受侵害可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层意思的表达。结果似乎是,“侵害财产权益不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10]81也有学者据此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应当适用于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侵害”。[1]711-712
与此相对,我国也有学者并不满足于对《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封闭式解释,试图为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寻求生存的缝隙和余地。有学者将《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视为授权性规范,它的存在并不必然排除人身权益之外其他权益侵害所致之精神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并且向读者展示了德国法上在现有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法律框架下(《德国民法典》第253条)采用扩展解释的方法将财产侵害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面。[11]76-86另有学者则从在侵害物的场合中受害人有精神损害发生这一事实推演出受害人相应的“人身权益”必受侵害这一事实,从而推演出了在侵害物导致精神损害的场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2条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12]89有学者则寄希望于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为“其他法律”,从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以企图解决司法解释与新法之间的不协调。[13]282
笔者不希望看到《侵权责任法》第22条演变成为我国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终结者。但需要阐明的一点是,如果在我国侵害财产权领域不存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那么在精子丢失或毁损案中,如德国法院在前述储存精子灭失案中所表现的,我国法院的对精子的财产定性就应该谨慎一些了。在这种只承认人身权益侵害才引发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环境中,将一些人体生命组织视为“人身权益”的载体从而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也许是照顾到当事人之救济的一种更好选择。从另一个视角看,如若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在人身侵权领域而不是向财产侵权领域开放有一弊端,即它会限制受害人的救济渠道和法官在人体组织定性问题上的自由思考。
如若欲将财产权之侵犯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另一个可考虑的路径是,将《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非穷竭性表达。那么,在第22条之外,《侵权责任法》中就存在着侵害财产权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空间。可以超越《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限制而寻找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可能。比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所有权”等财产权益属于法律需要保护的“民事权益”,而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赔偿损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而“赔偿损失”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10]55它并没有排除受害人因侵犯财产权而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侵害财产权——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上存在法条的支撑,并不存在逻辑障碍①此种超越《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限制而寻找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空间的努力也出现在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对《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解释当中。《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界定为被侵权人(直接遭受人身权侵害的本人)。为了让死者的近亲属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全国人大法工委引用了《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1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并认为赋予近亲属的请求权并没有明确排除精神损害赔偿。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采取精神损害赔偿法定的方式,将其适用范围明确地扩展至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受侵害之领域。
其实,精子或胚胎承载的更多是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混合,黑白分明式的“人”“物”二分法并不见得妥当。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的表述,“不育夫妇对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获得的配子、胚胎拥有其选择处理方式的权利”,而且,“患者的配子和胚胎在未征得其知情同意情况下,不得进行任何处理,更不得进行买卖”。此表述中使用了“处理”此类中性字眼。其中既显露出对当事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也透露出对当事人对配子和胚胎的控制权和人体组织的“物”性的认可。归纳起来,有三种路径可以缓和“人”“物”二分法的机械性。一是承认精子和胚胎的双重性和混合性。精子和胚胎,即使定性为财产,正如美国Frisina案法官所言,也是“不可替代”的财产;或者如英国的Yearworth案法官所说,具有保存当事人生育能力、安抚心灵的属性,系具有人格属性的财产;或者,如法国法所言,可以考虑其是否构成“珍贵生物”,②在法国一冷冻胚胎意外毁坏所致损害赔偿案中,在决定是否给予胚胎遭到毁坏的夫妇精神损害赔偿时,法院考察的是胚胎是否为“珍贵生物”。很可惜,法国杜埃上诉行政法院做出了否定回答。参见叶名怡:《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41-43页;曾品傑:《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从法国法谈起》,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2015年第三届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4月25日- 26日·上海),第101、104页。而非简单的财产。对于这种兼具人格属性的财产,法律不应否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可及性。二是,寻求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共性。人身权说与财产权说存在共性,即对当事人自主权和控制权的尊重。从这个角度讲,人身权说与财产权说的分割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对当事人自主权的尊重与认可才是实质。三是,回避人物二分的传统思路。在人物二分的传统进路之外,“行为”进路可以更多地从行为角度观察对人体组织的控制和处分问题,而不是“人”与“物”的区分。[14]54-56
四、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
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是“不当出生(wrongful birth)”或“不当生命(wrongful life)”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其关注焦点和规则适用相同,只不过是放置的领域不同。“不当出生”之诉指向的是孕有缺陷儿的父母,因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影响其优生优育的选择权,导致缺陷儿出生,父母以医疗服务提供者对该缺陷儿的不当出生负有过错为由,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而提起的诉讼。而“不当生命”之诉指的则是在不当出生情形下所出生的缺陷儿,要求医方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以医方为被告提起的诉讼。两种诉讼的区别点在于诉讼主体不同。
(一)域外法的观察
对于“不当生命”和“不当出生”诉讼,英美司法回应不太一样。英美司法更愿意允许父母就“不当出生”所增加的医疗开支获得一些赔偿,而不愿意让子女就其“不当生命”或者“本不应有的存在”获得赔偿。比如,美国的Turpin v. Sortini案①Turpin v. Sortini(1982)643 P.2d 954(Cal Sup Ct)。涉及“不当生命”之诉。案中法官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受孕前,医疗服务提供者未能向孩子的父母告知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可能性,从而剥夺了他们选择是否怀孕的机会,该孩子出生后发现患有遗传性疾病,孩子是否可以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提起侵权诉讼。法院支持了原告所提出的“特殊损害(special damage)”(即“特殊的教育、培训和听力设备所需要的额外开支”)的赔偿,并认为父母和子女均可以主张此类赔偿,这是因为这些损害的赔偿对孩子的福祉和生存均很重要,而且这些损害是“可以确定和随时计算的”。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原告所主张的“一般性损害(general damage)”(即“被剥夺了生为功能完整的、没有完全耳聋的孩子的基本权利”)。原因是此类“损害”难以确定和评估。再比如,在美国纽约州Becker案②Becker v. Schwartz,46 N.Y.2d 401,413 N.Y.S.2d 895,386 N.E.2d 807(1978)。中,两个残疾儿(一位为先天愚型,一位患有多囊性肾病)的出生是同样是源于被告医生未能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原告所提出的赔偿涉及三个方面:(1)孩子的损害赔偿;(2)孩子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3)孩子父母的经济损失赔偿。上诉法院对前二类赔偿做出了否定回答,而对第三类赔偿给予了积极回应。法院之所以否定了孩子的损害赔偿是因为孩子不存在法律上认可的伤害。孩子没有免于疾病而出生的权利。法院之所以也没有支持孩子父母基于孩子缺陷所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为在法院眼中,尽管孩子存在缺陷,父母仍会感受到爱的,残疾这一事实也不可能完全冲释这种爱。
美国Paretta案③Paretta v. Medical Offices for Human Reproduction,760 N.Y.S.2d 639(Sup. Ct. 2003)。是一个在人工辅助生殖领域产生缺陷儿从而导致诉讼并判被告赔偿原告金钱损失(pecuniary loss)的案件。在该案中,Paretta夫妇在被告处接受了由捐献者捐卵的体外授精。但是,没有人告知Paretta夫妇捐卵者是囊性纤维化携带者这一信息,也没有对Paretta先生进行检测看他是否也是这一疾病的携带者。结果是,体外授精成功出生后的孩子被诊断为患有囊性纤维化。此病是一种从父母双方遗传的疾病。在诉讼中,原告所声称的被告过失体现在:未能合适地筛选卵子、没有告知Paretta夫妇捐卵者囊性纤维化基因呈阳性、未能对Paretta先生进行检测看他是否也是这一疾病的携带者、在移植前未能对胚胎进行遗传疾病的检测。主张的赔偿有:精神损害、财产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在此案中,纽约最高法院认为通过人工辅助技术出生的孩子与自然出生的孩子应具有同样的权利,通过人工辅助技术获得子女的父母也不能比通过自然方式获得子女的父母具有更多的权利,因此Becker案的判决思路应在人工辅助生殖领域延续。Paretta案法院延续了Becker案中法院支持原告就残疾儿的照护所需要支出费用的赔偿这样一个判决思路,支持了有缺陷的和有严重依赖的残疾儿的扶养费的赔偿。
(二)我国法的展开
“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仅是一种称谓,它只不过是医疗侵权诉讼的一种形式。新型的“不当生命”和“不当出生”诉讼完全可以借用传统的侵权理论架构去完成,也就是说,去完成对注意义务、义务之违反、损害和因果关系四个要素的解读。这要考察:(1)被告是否存在产前检查、诊断和告知义务;(2)被告是否违反了上述义务;(3)原告是否因缺陷儿的出生遭受损害(包括物质和精神损害);(4)被告的义务违反(即过失行为)与缺陷儿的出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运用本土化的语言来描述,美国法的“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实际上就是医生违反诊断义务和告知义务之诉,它与通常的医疗过失侵权诉讼并无二致。
关于医疗从业者(包括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的产前检查、诊断和告知义务,我国《母婴保健法》第17条和第18条、《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0条、《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17条和第19条均有所规定。具体到人工生殖领域,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也均对供精者的疾病筛查和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做出了规范。上述规范虽属于行业规制或管理规范,但均有助于法官去判定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是否对原告存在着产前检查、诊断和告知义务等注意义务,以及被告是否违反了此项注意义务,或者说是否达到相应的注意标准。
一旦判定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且违反了此注意义务(即存在过失),因果关系的满足不应很困难,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并没有禁止堕胎的国度。在此方面,我国目前的司法过多地纠缠于“因果关系”是否形成。比如,在佛山足缺如患儿的出生引发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①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审),(2011)佛中法少民终字第91号。中,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这样一份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尽管被告存在对胎儿可能存在的肢体远端缺如的情况未切实履行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的医疗过错行为,但是,原告左足缺如是患儿自身发育异常所致,足缺如也不是医学上终止妊娠的绝对指征,因此,足缺如患儿的出生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同样,在阳芙蓉等诉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②一审: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6)番法民一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2006年8月10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281号民事判决(2007年5月28日)。中,被告医院一直辩称,先天疾病是遗传的结果,不是医疗侵害生命、健康、身体权利的结果。因果关系问题之所以在我国的该类诉讼中纠缠不清并成为中心议题,是因为存在两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和误读:一是缺陷儿的疾病(往往是先天的)与医疗过失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缺陷儿的出生与医疗过失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关注的是原告的“生育自主权和堕胎选择权”问题。[15]37医学界钟情的往往是第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多给出否定性回答;而“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关心的则是第二种因果关系,对其进行肯定性回答并不困难。
由此,在“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中,注意义务之存在、注意义务之违反、因果关系这三个要素的成立往往不成大问题,法官需要回答的多是第四个构成要素——损害——的有无和赔偿问题。关于“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从大的方面讲,一般涉及三部分:所涉孩子(缺陷儿)的损害赔偿、所涉孩子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所涉孩子父母的物质损害(经济损失)赔偿。从美国的Becker案、Paretta案和Turpin v. Sortini案的判决来看,法院一般只要求被告赔偿所涉孩子父母的物质损害,或者说“特殊的教育、培训和(其它)额外开支”、缺陷儿的照护费或抚养费。所涉孩子父母的精神损害并不属于赔偿的范围。所涉孩子(缺陷儿)的损害也无法赔偿③比较一下,在意大利的一个错误出生判例(合同法判例)中,意大利最高法院民庭2012年通过第16754号判决确认了胚胎有健康出生的权利,确立了自然受孕体的受保护的客体的地位,赋予胚胎有条件的(在出生后)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徐国栋:《人工受孕体在当代意大利立法和判例中的地位》,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9页。但是,对于不法使人出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案件,世界各地仅有少数法院准许原告(即活产出生之幼儿)之请求,多数法院则予以驳回。参见詹森林:《从不法使人出生(Wrong⁃ful life)之损害赔偿诉讼看比较法案例》,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小型研讨会系列·2015年第三届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4月25日- 26日·上海),第291-296页。。人的出生无法被视为一种损害。
关于侵权损害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就“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时的赔偿范围做出了规定。与之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也就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时的赔偿范围做出了细化,而且该司法解释第18条还赋予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尽管我国许多法院在处理“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时适用了上述规定①如在阳芙蓉等诉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法院要求被告医院赔偿医疗费(不包括后续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没有支持残疾赔偿金和特殊教育费的赔偿。在足缺如患儿的出生引发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支持的赔偿范围是原被告双方所确认的原告损失范围,即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也有法官在列举所涉的赔偿项目时参考了上述规定②参见张健,向婧:《“不当出生”侵权诉讼民事审判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第55-56页。该法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不当出生”之诉中当事人可能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项目:(1)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2)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康复费、后续治疗费;(3)残疾儿扶养费;(4)精神抚慰金。,但是人们有理由质疑上述规定在“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诉讼中适用的妥当性。需注意的是,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指向的是“人身损害”遭受侵害的场合。而此处的“人身损害”针对的主要是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10]58、或“生命、身体和健康权”[13]211、或“生命、健康、身体”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遭受损害。我国在“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诉讼中原告的何种权利遭受侵害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争议,它或许是缺陷儿父母的“生育权”或“生育选择权”,[16]54或者是新生儿父母的“优生优育选择权”,[17]127-130或者是其它更具一般性的人格权(如自主权)④参见王洪平,苏海健:《“错误出生”侵权责任之构成——一个比较法的视角》,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页(认为父母的生育自主权和堕胎选择权是受宪法和侵权法保护的一项人格自由权);朱晓喆、徐刚:《民法上生育权的表象与本质——对我国司法实务案例的解构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77页(认为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或其他人格利益已经包含了生育自主权的具体内涵)。。但无论如何,遭受侵害的权利不可能是原告(包括缺陷儿或缺陷儿父母)的“生命、健康和身体权”。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上述规定在“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的适用上存在着法律障碍。
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侵权责任法》在“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诉讼中的适用。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侵害“民事权益”者要承担侵权责任。“民事权益”包括其他未列举的“人身、财产权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15条),而损失的赔偿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10]55侵害“人身权益”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中当事人受侵害的权益应是某种“人身权益”。不同于第16条中的“人身损害”这一概念,“人身权益”显然不限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其外延更广。它包括一些诸如名誉权、隐私权等“非物质性人身权”。[10]75“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中原告所遭受侵害的权利似乎可以囊括其中。
在确定或限定“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诉讼中的赔偿项目时,我国可以借鉴一下美国法的经验,支持一些能够促进缺陷儿童成长的赔偿项目,比如为弥补残疾所需要的额外费用开支,而拒绝支持一些可能传递出有缺陷的生命不如不存在的生命这一负面信息的赔偿项目,比如缺陷儿所主张的损害赔偿和缺陷儿父母所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
五、结语
错植精子或胚胎案的发生是由于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导致的,该类案件争议的焦点不落在过错和因果关系这两个构成要件上,而是在损害层面上,即错植精子导致非亲生子女的出生侵犯的是原告的何种权利以及原告应得到对何种“损害”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是法官裁判的重点。
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也是以人工生殖服务提供者违反注意义务构成过失从而导致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为前提的,该类案件诉讼的焦点也是原告在配子或胚胎上所存在的权利之定性以及相应地原告所受“损害”之界定。对于人体组织上的权利定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财产权说似乎比人身权说来得更加强劲。在我国,人体组织上的权利归属,应照顾到权利救济,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可及性。
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只不过是“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其法律适用并无特别之处。它既可发生在诊疗领域,也可发生在信息告知领域。“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实际上是医生违反了诊疗义务和信息告知义务的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诉讼。我国应重新审视和矫正在此类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并将重心转移到对损害范围的界定上。面对缺陷儿的面世,司法者在界定“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之诉的损害赔偿范围时既要有积极回应,也应有必要节制,以防止发出对缺陷儿的歧视信号。
我国的人格权法正在发展当中。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中,当事人遭受侵害的权利的定性都十分困难。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尤其如此。如果说在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中,我们可较为容易地在兼顾到救济渠道的情况下在人身权和财产权做一选择,或者认定配子或胚胎是承载兼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混合权利之物,在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中我们可以将医生的行为认定为侵权患者的自主选择权,那么,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中,权利的选择和认定便困难得多了。
梳理一下,在这三类案件当中,当事人希望得到的无非是拥有“子女”(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拥有“自己的”子女(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和拥有“健康的”子女(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的机会和权利。掺杂其中更多的是对当事人自主权的尊重。对当事人自主权和决定权的尊重既体现在对当事人人身权的呵护当中,也贯彻在对当事人财产(所有)权的敬畏当中。此处的“自主”体现在当事人生育亲生子女上的自主(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在财产处置上的自主(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在是否继续怀有和生产缺陷儿上的自主(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有域外学者曾将三类案件所涉及的损害概括为“生育损害(procreative injury)”。[18]237-245我认为,三类案件所涉及的权利可用“生育自主权”这一概念而概括之。“生育自主权”基于一般人格权而生。所以,总体而言,三类案件对应的是更加一般的和抽象的人格权。没有具体人格权相对应,不应影响到当事人在“人身权益”之下寻求庇护和获得救济,也不应影响到当事人在“一般人格权”(包括“人格自由权”)下获得兜底和升华。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夏吟兰,高蕾.建立我国的亲权制度[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4).
[3].马强.论生育权——以侵害生育权的民法保护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13(6).
[4]W. Scott Blackmer. 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Negligence Actions for Emotional Distress and Loss of Consortium without Physical Injury[J].California Law Review,1981(69).
[5]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余能斌.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J].中国法学,2003(6).
[7]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的“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J].法商研究,2007(5).
[8]常鹏翱.论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联——一种功能主义的诠释[J].法律科学,2005(1).
[9]易继明.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J].法学研究,2008(1).
[1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朱晓峰.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产侵害中的限制与适用: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中德法律实践比较[J].法治研究,2013(3).
[12]叶金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J].法学家,2011(5).
[13]高圣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周江洪.法制化途中的人工胚胎法律地位——日本法状况及其学说简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5).
[15]王洪平,苏海健.“错误出生”侵权责任之构成——一个比较法的视角[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6]张健,向婧.“不当出生”侵权诉讼民事审判实证研究[J].法律适用,2009(5).
[17]万欣.浅析缺陷出生纠纷的法律关系——以侵权法为视角[J].判解研究,2013(2).
[18]Joshua Kleinfeld. Tort Law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The Need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Procreative Injury”[J].The Yale Law Journal,2005(115).
[作者简介]赵西巨(1969-),男,山东新泰人,法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医事法。
[收稿日期]2015-11-16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2-0054-14